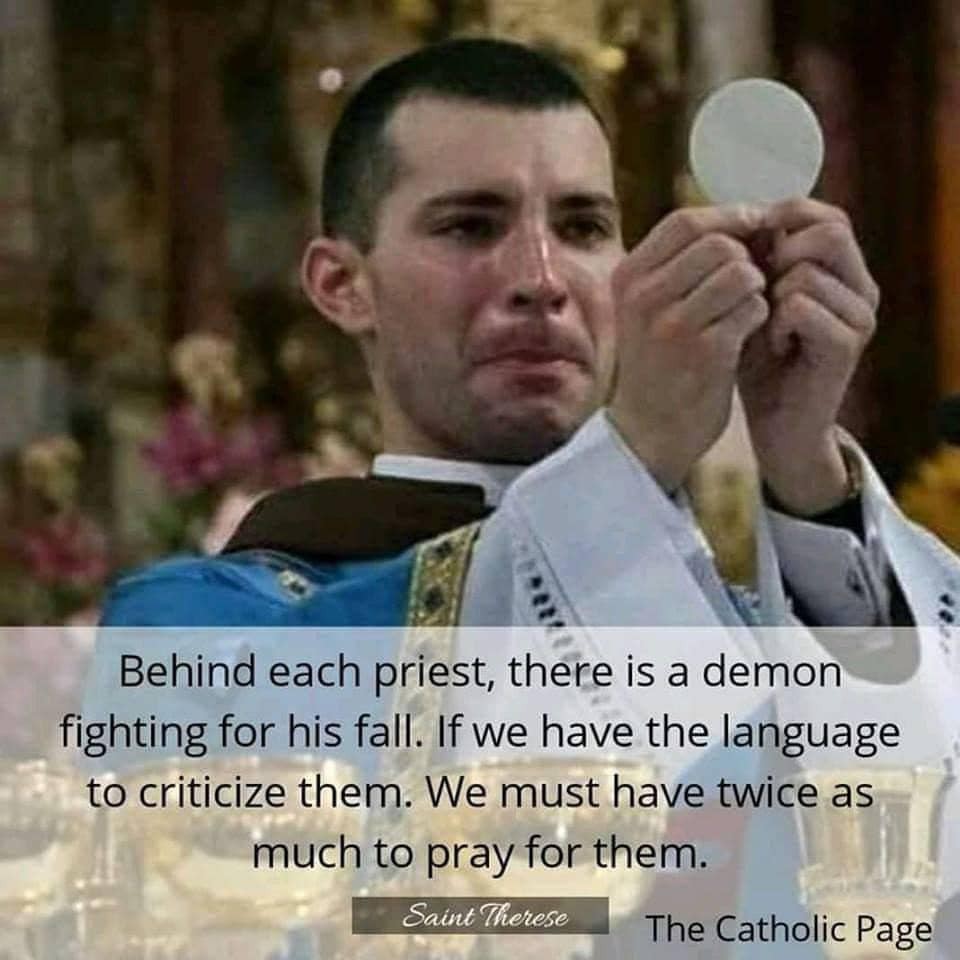教會與性侵醜聞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教會與性侵醜聞》
2019年4月10日
由2月21日至24日,在教宗方濟各的邀請下,全球主教會議的主席們聚首於梵蒂岡,商討現在信仰及教會的危機:就是駭人聽聞的神職侵犯未成年事件被揭露後,全世界所經歷到的危機。
這些報導中事情的廣泛程度及嚴重性,深深地困擾著司鐸們以及平信徒,也引起了不少對教會核心信仰的疑問。我們的確有需要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恢復教會作為萬民之光的信譽,讓人再次相信教會是有助於打擊毀滅性勢力的一股力量。
在這危機公開爆發時,以及在其後續的時間,我自己曾經背負著作為教會牧者的責任,因此,我必須反問自己——雖然現在作為榮休教宗,我不再肩負任何直接責任——我能夠為一個新的開始付出甚麼?
因此,在宣布主教會議主席們的會面後,我寫下了一些筆記,我希望能藉這些筆記,在這困難的時間貢獻一兩點的提醒。
在聯絡了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以及教宗方濟各後,這看來也很適宜將這文章刊登在《聖職人員期刊》(Klerusblatt)上1。
我的這文章分為三部分。
在第一部分,我試圖簡介這個議題的宏觀社會背景,因為缺乏這背景我們是不能理解這個議題的。我嘗試展示在1960年代發生了一件駭人的的事情,而這事情的程度是歷史中前所未見的。可以說,由1960年至1980年的這20年間,固有及規範標準的「性」(sexuality)的觀念完全崩潰了。而一個新的常態興起,這就是在持續紛亂中的主角。
在第二部分,我試圖指出這情況如何影響司鐸的培育及司鐸的生活。
最後在第三部分,我希望能夠就教會方面如何恰當地回應,提出一些觀點。
I.
(1)事情開始於國家給予並支持的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本質的教育。在德國,當時的教育部長KäteStrobel製作了一套電影,以教育作為理由,當中包含了所有從前視為不能公開展示的內容,包括性交。起初這只是被視為年青人的性教育工具,後來這便被廣泛視為一種可行的做法。
奧地利政府推行了「性箱子」(Sexkoffer),這也達到了相似的效果2。接著,性意識及色情電影成為尋常事物,甚至在紀錄片電影院[newsreel theaters, Bahnhofskinos]中上映。我依然記得有一天我在雷根斯堡巿(Regensburg)走過,看到一大群人在一間很大的戲院前排隊。在此之前我們只在戰時看過這樣的情形,就是當人們預期有一些特別的電影上映時就會這樣。我還記得當我在1970年聖週五來到這城巿時,看到廣告牌上都貼了大型的海報,上面印著兩個一絲不掛的人在親密的擁抱著。
在1968年革命中所爭取的自由當中,其中就是完全的性自由,即是性不需要跟隨任何規則。
這心理中的崩潰也和暴力傾向有關。這也解釋了飛機上不再容許有性的電影,因為暴力會在這極少數的乘客團體中發生。而當時的衣著也同樣地引起暴力行為,學校校長們開始嘗試引入校服,試圖建立學習氣氛。對很多教會中的年輕人而言,其實也包括其他人,這於很多方面也是很困難的時間。我經常也疑惑年輕人在這些處境中,還受著一切的延伸影響,如何理解並接受司鐸生活。事情發展下來的後果,就是這年代後的那一輩司鐸聖召衰竭,喪失聖職身分的案件數量龐大。
(2)同一時間,獨立於以上的發展,天主教倫理神學式微,這使得教會無力抵抗社會中的這些轉變。我會嘗試勾劃出這發展的路線。
一直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天主教倫理神學主要都是建基於自然律,而聖經只是用作解釋背景及認可。梵二嘗試建立一個對天主啟示的新的理解方法,自然律的方向基本上被摒棄,倫理神學被要求單純按聖經而成。
我依然記得法蘭克福的耶穌會如何訓練了一個極有天份的年輕神父 Bruno Schüller,希望他建立出一套單純以聖經為根據的倫理觀。以聖經為基礎的倫理觀為目標,Schüller神父的優秀論文踏出了第一步。Schüller神父後來被送到美國繼續深造,回來後發現單靠聖經作為根據的倫理觀是不能有系統性地表達出來。後來,他試圖建立一個較為實用主義的倫理神學,然而他卻不能為道德危機提供一個答案。
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假設,就是人類行為的道德價值單純只按其目的而判斷。雖然這思想沒有認同「為求目的,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這籠統的說法,但這種思考模式卻成了最終的決定。結果就是,沒有事情能被視為絕對的善,也沒有事情能被視為絕對的惡。(可能)只有相對的價值判斷。不再有(絕對的)善,只會在比較中有「較好」,而這會視乎時機及情況而有所不同。
天主教倫理在理據及陳述方面的危機在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達到誇張的程度。在1989年1月5日,由15位天主教神學教授所簽署的《科隆宣言》公布了。它討論了有關主教訓導權和神學研究的關係中的不少危機要點。這文本所引起的迴響,起初和平常的抗議差不多,但後來很快速地變為一個對教會訓導權的強烈反對,繼而號召了全球各地的力量,抗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一份預期會出現的教理文件。(參考:D. Mieth, Kölner Erklärung,LThK,VI3,p.196)3
若望保祿二世非常明白道德神學的情況,並且一直密切關注。他開展撰寫一份通諭,這通諭將會使事情重上正軌。這通諭頒布於1993年8月6日,名為《真理的光煇》(Veritatissplendor),它引起了倫理神學家的強烈反應。在此通諭之前,《天主教教理》已經以一個有系統的方式,有力地陳述了教會所宣告的道德倫理。
我永遠都忘不了當時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倫理神學家Franz Böckle,他在退休後已回到他的家鄉瑞士。就《真理的光輝》可能作出的決定,他當時宣告如果這通諭表示有些行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必然被視為惡的話,他就會以他所有可行方法去挑戰這通諭。
然而,仁慈的天主讓他不需要將這決心化為行動。Böckle在1991年7月8日去世。而這通諭是在1993年8月6日公布。事實上,這通諭確實表示有些行為是永遠不能是善的。
教宗完全明白這一個決定在那一個時刻是何其重要。在他通諭的這一個部分,他曾再次諮詢沒有參與編輯這通諭的最重要的專家。他知道他必須毫無疑問地表達出,在計算各樣善的道德判斷中,必須保護最終的那一條界線。有一些善是永不能被妥協換走的。
價值絕不能為更大的觀念而被拋棄,這些價值更超越現世的生命。例如殉道(martyrdom4)。天主是超越現世的生存。由拒絕天主而得來的生命,是一個終極上以謊話作為基礎的生命,其實是一個「假生命」(non- life)。
殉道(martyrdom)是由基督徒出現開始就有的一種基本類別。事實上,在Böckle推廣的理論中,殉道是沒有道德必要的;而同時很多基督信仰的本質也岌岌可危。
同時,在道德神學中有另一個問題也越加迫切,即以下假說:只有在信德相關事情上,而該事情能獲得普遍接受時,教會的訓導權才有最終的不能錯特恩(infallibility)。按這看法,教會訓導權在倫理問題上並不享有不能錯特恩。在這假說中,可能有一些值得詳細探討的地方。但是,道德底線與信仰的基本原則是密不可分的;這道德標準是必須堅守的,這樣信仰才能有實質的生命,否則信仰只會淪為一套理論。
「μάρτυρ」,本義為「見證」獨立於這問題之外,在倫理神學的諸多領域中盛行著一個假說,就是教會沒有也不能擁有自身道德訓導的論點。這說法的論據是因為所有道德說法都在不同的宗教有著相似的討論,所以基督信仰從不能獨攬道德。但這種質疑聖經道德觀獨特性的議題,其實不能因為每一句聖經說話都能在其他宗教找到相類似的說話而得以確立。反之,這議題的答案在於其實聖經道德觀的整體是嶄新的,而且和它本身每一個個別部分均有所分別。
這樣,我們就看得出教會的道德權威從基礎上受到質疑。那些否定教會在道德範圍上有最終訓導權的人,就是在強迫她在真理和謊話的界線受到挑戰時保持緘默。
聖經的道德信理有其獨特性,最終是基於它掛勾於天主的肖像、也是基於我們對唯一天主的信仰,這天主以人而活著的耶穌基督身上顯現了自己。十誡就是聖經中對天主的信仰,在人身上實踐出來。天主的肖像和道德觀是同一事情,最終推動基督徒對世界及人類生命的態度。再者,基督信仰由一起初就被形容為「hodós」5。
信德是一個旅程及一個生活方式。在教會早期,慕道期的設立就是為了抗衡一個文化愈加道德敗壞的棲息處。在這裡,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中的各項獨特而新穎的方面都要實踐出來,同時也防止被普通的生活方式所影響。我認為就算在今天,一些類似慕道期團體的設立是有必要的,好使基督信仰的生活能以自己的方式展現出來。
II.教會起初的反應
(1)一如我剛剛嘗試闡述的,在1960年代出現前所未見的激進主義中,基督信仰的道德觀念也在長時間醞釀及持續進行的過程中瓦解。教會在道德訓導方面的權威在瓦解,自然地影響教會各方面的範圍。單為回應方濟各所邀請各國主教團主席所聚集而進行的會議而言,我們現在集中討論司鐸生活以及修院生活的議題。有關在修
院中培育司鐸職育的問題而言,的確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崩潰。
在某些修院內形成了同性戀小圈子,他們或多或少行事開放,這大大影響著修院內的氣氛。在德國南部的一所修院,接受司鐸培育的人和接受牧民工作培育的平信徒[Pastoralreferent]住在一起。在用餐時,修生們和那些牧民工作者一起吃,而那些結了婚的平信徒有時會帶著他們的妻子和孩子,有時也帶著他們的女朋友。這種氣氛並不能協助司鐸聖召的培育。聖座知道這些問題,卻沒有接獲相關的細節。於是首先,聖座便安排了在美國的修院進行「宗座訪問」(Apostolic Visitation)。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挑選及委任主教的條件改變了,因此主教們與他們轄下修院的關係也和以往不一樣。最重要的是,現在挑選主教的條件之一是他們的「會議精神」(conciliarity),當然這個詞語可出現很不同的理解。
事實上,在教會內的很多地方,會議的精神被解讀為要對針對既有的傳統持有批評或負面的態度。這些傳統必須以新的關係取而代之,也就是向世界徹底敞開的關係。一個曾經擔任修院院長的主教更曾安排修生觀看色情影片,聲稱這樣可以使他們對這些有違信仰的行為發展出抵抗力云云。
這不單侷限於在美國,有好些個別主教,他們全盤否定天主教傳統,並尋求在他們的教區培養出一種煥然一新、現代的『大公性』。以下情況發生在不少修院,也值得一提:學生們如果被發現閱讀我的著作,就會被認定為不適合做神父。我的著作要被收起來,就像一些低劣作品一樣,成為大家枱底下的讀物。
「宗座訪問」也沒有觀察到甚麼新的事物,明顯地不同的勢力聯合起來要隱瞞真相。聖座便下令作第二次的「宗座訪問」,這就帶出了相對較多的新發現,但整體而言也不能達到具體的結論。即使如此,由1970年代開始,修院的情況大致也有改善。然而,司鐸聖召因整體情況改善而有所增強亦只屬零星的個別例子。
(2)就我的記憶來說,戀童癖的問題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變得棘手。當時這在美國已成為一個公共議題,而身處羅馬的主教便要求協助,因為按新的(1983)《天主教法典》似乎不足以提供足夠的指引。
教廷及教廷的法學家起初面對這些議題時遇到困難;他們當時認為暫停司鐸職務已足以煉淨及釐清事情。美國的主教對此不能接受,因為這些司鐸就仍然保留著在主教旗下服務的名義,因此亦有機會被視為和主教有直接的關聯。後來漸漸地,新法典中那個刻意寫得不太嚴謹的刑事法規才得到更新及深化。
然而,當時還有對於理解刑事法律一個根本的錯誤觀念。就是所謂的「保障主義」(guarantorism)6當時仍被視為「會議精神」。意思就是,被告的權益要被格外保障,甚至到達了一個地步要避免任何判罪。被控告的神學家往往都沒有足夠的辯護機會,因此引伸的保護主義卻發展到一個地步,就是幾乎造成無法判罪。
容許我先帶出一點。有關於戀童侵犯個案的規模,我們要記起耶穌的一句話:「誰若使這些信者中的一個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裡,為他更好。」(馬爾谷福音9:42)
在耶穌的語言中,「小子」一詞意指普通的信友,他們會被自以為聰明的高傲知識分子混淆信仰。因此,為了保護信仰的累積,耶穌在這裡以一個強硬的威脅警告那些會傷害信仰的人。
這句聖經的現代用法本身沒有錯誤,但這也不能遮蔽著最原始的意義。在這原始的意義很清晰,相反於「保障主義」,重要而需要保障的不單是被控告者的權益。一些重要的善/益處,例如信仰,也是同樣重要。
一個平衡的法典必須對應於耶穌在背後的整個訊息:不單必須為被告作出保證,這本身是一個法理上的善。法典也必須要保障信仰,因為信仰本身也是重要的法律資產。同時必須保護信仰。因此,一個妥當、穩健的《天主教法典》需要包含一個雙向的保證:法律層面上保護被告,亦要保護面臨危機一方的善的一面(即信仰)。如果有人試圖表達出這套清晰的概念,大抵會沒人接受,因為大家會質疑對信仰的保障是否是一個法理中的善。大眾對法律的概念,往往都看不到信仰是一個需要法律保障的善。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而教會的牧者需要認真考慮這一點。
有關在這危機的公開爆發時期的司鐸培育,我想再添加些許資料,特別是在法典在這方面的發展。
原則上,聖職部(Congregation of the Clergy)專責處理司鐸所犯的罪行。但由於當時「保障主義」盛行,我同意若望保祿二世,就是將處理未成年侵犯案件的職權交給了信理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並將案件列為「Delicta maiora contra fidem」7。
這個安排容許在法律上處以最高刑罰,就是革除聖職身分。在其他的法律安排並不能處予這刑罰。這不是單純為了給予最高刑罰而這樣做,而是基於教會信德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必須看到教士們的這般失職最終是會破壞信仰的。
唯有不按信仰行事的人才會犯下這些過犯。
然而,這懲罰的嚴重性也自然要求過犯的明確證據——保障主義的這一方面亦是存在的。
換而言之,為了合法給予這最高刑罰,一個真正的刑事程序是需要的。但個別教區及聖座也被這種要求弄得不知所措。我們於是制定了一套最簡略的刑事程序,而在教區及教省行政未能進行審訊時,聖座則有可能將這案件接收。在每個個案中,審訊會由信理部檢閱,而保障被造的權益。最後,信理部的一個小組FeriaIV當中,我們設立了一套上訴機制以進行上訴。
由於這一切其實都超越了信理部的容納能力,而延誤辦案時機的情況經常發生,而基於這些案件的本質理當加以避免延誤,教宗方濟各採取了進一步的改革。
III.
(1)有甚麼必要的事情要做?可能我們應該創立另一個教會去解決事情?這個實驗已經試過,也已經失敗了。只有真正遵守及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才能為我們指出道路。所以,讓我們首先從內在重新去明白上主一直以來在我們身上渴望甚麼。
首先,我會有以下建議:如果我們真的想非常概括地總結由聖經中所建立的信仰的內容,我們可以說上主開展了一個跟我們的愛的論述,祂想將整個受造界都蘊含在這論述內。邪惡正在威脅我們和整個世界,而一股對抗邪惡的抗衡力量最終只能在我們進入這愛的時候出現。這是真實對抗邪惡的抗衡力量。邪惡的力量來自我們抗拒接受天主。那些將自己託於天主的愛的人就被救贖。我們無法愛天主的後果就是不被救贖。因此,學習去愛天主就是人類獲救贖之路。
現在,讓我們嘗試進一步開啟天主啟示的重要內容。接著,我們可以說信德給我們的第一件最基礎的禮物就是,我們能夠肯定天主存在。
一個沒有天主的世界只會是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一切事物來自哪裡?無論怎樣,它都沒有一個靈性目的。世界就只是碰巧在這裡,沒有任何目標,也沒有意思。接著也沒有分辨善惡標準。弱肉強食。唯一的原則就是力量。真理再也不重要,因為它不存在。唯獨當事物有靈性原因,它們才是刻意被創造——唯獨有一個善的,而且渴望善的造物者天主——這樣人的生命才能有意義。
有一個創造者天主,而身為萬物的標準,祂首先是人最原始的需要。
但一個完全不表達自己的天主是不能被人認識的,這樣的天主只能永遠是一個假設,也不能決定我們生命的形態(Gestalt)。因為天主要真正作為刻意創世的天主,我們必需讓祂以某些形式表現自己。祂的確以很多方式這樣做了,但尤其決定性的方法就是當時祂召叫亞巴朗,為尋找天主的人提供了一個超越眾人所預期的方向:就是天主自己成了受造物,作為「人」跟我們「人」說話。
這樣,「天主就是」(God is)這句說話終極地轉化成為一個真正喜樂的訊息,正正因為祂不單明白「愛」,因為祂創造了──而且本身就是──愛。就是再次令人暸解到這就是天主委託給我們第一樣且最為重要的工作。
一個沒有天主的社會──一個不認識天主並且視祂不存在的社會──是一個失去自己標準的社會。在我們的日子,「神已死」成了流行語。我們被告知,當天主在社會中死了,這個社會就能自由。現實中,天主在社會中死去卻表示自由也終止了,因為死了的其實是[為社會]提供一個方向的目的。因為教導我們分辨善惡、為我們指示正確方向的指南針消失了。西方社會中,天主從公共領域被挪去,西方社會也不要天主的任何事物。這就解釋了為何西方社會愈加丟失以人為本的準則。在這點,我們突然就很容易明白邪惡及摧毀人的事物會成為理所當然。
戀童癖就是這樣。它被理論化,不久前還才被視為完全正確的事,現在已不斷廣為流傳。而我們現在才驚訝地意識到在我們小孩子及年輕人身上發生的事在威脅,快要摧殘他們。事實是,這在教會中及司鐸間流傳的事實應該尤其使我們感到不安。
為何戀童癖達到這嚴重的比例?最終極的理由就是天主不在了。我們基督徒及司鐸們都寧可不再談及天主,因為這些話都似乎不太實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德國仍然明確地在我們的憲法提到有責任以天主作為指導性原則。半個世紀之後已經不可能在《歐洲議會憲法》中包括以天主作為指導性原則的責任。天主被視為少數人的關注,不可能再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指引原則。這決定反映著西方的情況,就是天主成為少數人的私人事務。
在這個道德崩潰的時期,一個艱巨的工作就是需要我們重新再一次開始藉天主、為天主而生活(live by God and unto Him)。最重要的是:我們必定要重新學習承認天主是我們生命的基石,而非將祂當作廢話而置在一旁。我永遠都忘不了偉大神學家漢斯·烏爾斯·馮·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88)的有一次在信中寫給我的警告:「不要將聖父、聖子、聖神的三位一體天主視作理所當然,但要將祂展示出來!」
真的,在神學中,天主經常都是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實質上人們卻不理會祂。天主這個主題看來太不真實,和我們關注的事項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當大家不視天主為理所當然,但實際展示祂時,所有事情都不一樣。不是將祂放在背景中,而是在我們的思、言、行為中明認祂。
(2)天主為了我們成了人。作為祂的受造物,人是如此地貼近祂的心,祂甚至將自己和人聯繫起來,以一個很實際的方式進入了人類歷史。祂和我們說話,祂和我們生活,祂和我們受苦,祂為我們接受了死亡。在神學中,我們以學術論述及思想詳細討論了這些事情。但這樣,我們也有危險變成了信仰的專家,而非被信仰更新及指導。
我們先以一個核心問題去想,就是舉行彌撒聖祭。我們看待聖體的方法實在令人憂慮。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正確地專注於將這聖事——基督聖體聖血的臨在、祂的位格祂的受難死亡復活的臨在——回到基督徒生命的中心以及教會的存在。某程度上,這也真的實現了,我們應該為此感謝天主。
然而有一些別的態度也很普遍。常見的不是對基督死而復活的崇敬,而是一種破壞奧跡的偉大的看待方式。彌撒出席率日漸低落,反映著我們現今基督徒對如何欣賞基督親臨的重大禮物是如何地無知。感恩祭被貶為一個單純的儀式性活動,只是當我們有些家庭聚會要邀請所有人出現,例如婚禮和葬禮,我們理所當然地要禮貌地邀請祂出席。
人們經常理所當然地領受聖體也反映了很多人視領聖體是一個儀式性舉動。所以,當想到甚麼行為是最重要且首要,明顯地我們不是需要我們自己設計的另一個教會。反之,首要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更新我們對聖體聖事的信仰:在這聖事中,耶穌基督實實在在被交付給了我們。
在與戀童癖受害者的對話中,我深深地意識到這是最先且最重要的條件。一個年輕女士,她曾是個輔祭,她告訴我,她的輔祭會神師每一次侵犯她時都說:「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而犧牲。」
很明顯,這位女士每次聽到成聖聖體的說話時,都會再次經歷她被侵犯的痛楚。是的,我們必須急切請求上主的寬恕,我們要向祂起誓,及請求祂重新教導我們所有人去理解祂的受苦、祂的祭獻的偉大。另外,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去保護聖體的恩寵不被侵害。
(3)最後,還有教會的奧秘。差不多100年前,郭蒂尼(Romano Guardini)將充滿了他以及其他不少人的喜樂表達出來,很多人還記得他的話:「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開始了;教會在靈魂中醒來了。」
他的意思是,教會不再被視為一個進入我們生命的外在系統,是一個權力,反而她開始被視作真正存在於各人心中——不是單純外在的,而是從內在的推動我們。半個世紀之後,我反思這個過程,也觀察著所發生的事項,我卻認為要相反這說話:「教會在靈魂中要死了。」
今天大部分的人把教會當成純粹的政治工具。人們談論她時也只是將她以政治分類,甚至連主教也是這樣做,他們在考慮教會的將來時也只是單單作政治考量。這些眾多司鐸施加侵犯案的危機促使我們以為,教會竟是如此糟糕,務必果斷地親手重新打造。然而,我們自行塑造的教會不會帶來任何希望。
耶穌自己將教會比作一個漁網,內裡有好的和壞的魚,最終天主會自己將魚分好。[瑪竇福音13:47~50]也有一個比喻將教會比作一塊田地,天主親自撒了好種子,但「仇人」也秘密地撒了莠子的種子。[瑪竇福音13:24~30;36~43]事實上,莠子在天主的田地——即教會,是非常顯眼的,而壞魚也在網裡展示力量。無論如何,田地仍是天主的田地,漁網仍是天主的漁網。在任何時期,不單都有莠子和壞魚,但同時都會有天主的麥子及好魚。強調兩者的出現不是虛假的護教學,卻是在為真理服務。
在這背景下,有需要看看聖若望的默示祿。魔鬼被認作是控告者,日夜在天主面前控告我們弟兄。(默示錄12:10)聖若望默示錄也由約伯傳的一個中心論述中取了一個思想(約伯傳1,2,10;42:7~16)。在約伯傳中,魔鬼試圖在天主面前詆毀約伯的義德,說這只是外在的。這正正就是默示錄要說的:魔鬼希望證明根本就沒有義人;所有義人都只是在外表假扮的。如果能夠夠近距離地看一個人,他公義的外表就自然會剝落。
約伯傳的敘述由天主和魔鬼的一次爭執開始,天主說約伯是一個真正正義的人。約伯便成了一個例子去證明誰是正確。魔鬼說:打擊他所有的一切,你就不會再看到他還剩下甚麼虔敬。天主允許魔鬼的意圖,而約伯的反應也是很正面。現在魔鬼再進一步說:「那只不過是以皮換皮罷了!人都肯捨棄所有,去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你若伸手打擊他的骨和肉,他必定當面詛咒你。」(約伯傳2:4以下)
天主給了魔鬼第二次機會。魔鬼可以害他的身體,唯獨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基督徒很清楚,約伯作為人類的代表站在天主面前,其實是指耶穌基督。人性的戲碼在聖若望默示錄中完全給我們展露出來。
造物者天主受到魔鬼的挑釁,他一直對著人類以及整個受造物說盡壞話。不但對著天主,魔鬼也對所有人說:看這個天主做了甚麼?一個應該是善的創造,但在現實卻滿是悲傷及污穢。貶低受造物其實是為了貶低天主。它想證明天主自己並不是美善的,要將我們帶離天主。
默示錄所講論的實在很合時宜。今天,對天主的控告,最明顯就是將祂的教會說成完全是惡劣的,並以此要人遠離她。由我們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教會,這本身就是魔鬼的建議;透過這建議,魔鬼以一個令我們容易相信的虛假的邏輯,領我們離開生活的天主。不,即使到了今天,教會也不是單單由壞魚及莠子所組成。天主的教會今天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教會仍是天主用以拯救我們的工具。
以完整的真理去對抗魔鬼的謊話及半真話是十分重要的:是的,在教會內有罪惡及邪惡。但即使到了今天,神聖的教會仍在,她不會被毁滅。今天有很多人謙遜地相信、受苦,及愛,真正的、愛的天主藉這些人將自己顯露給我們。今天,天主在世上仍有祂的見證人(martyres)8。我們只需要留心就能看到和聽到他們。
Martyr——見證——這個字本身來自程序法。在與魔鬼對抗的審判中,耶穌基督就是天主第一個且實在的見證人,第一個殉道者,之後就跟著無數的其他見證人。
今天的教會比以往更加是一個「殉道者的教會」,因此也是生活天主的見證。如果我們四處觀看,以一顆留神的心細聽,我們可以在四周找到見證人,尤其在普通人當中;但也能在教會高層中找到,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及受苦去為了天主站出來。我們心中的惰性使我們不想去認出他們。我們福傳的一個重要的大工程就是,要盡我們所能,去建立信德的居所,並且去找到和明認他們。
我住在一所小屋,住在一個小團體中。這小團體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不斷地發現著生活天主的見證人,他們喜樂地為我指出來。看到和尋找生活的教會是一個美妙的工作,這樣加強我們,使我們在我們的信德中不斷喜樂。
在我反省的最後,我希望感謝教宗方濟各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他不斷地為我們展示了天主的光,這光即使在今天也沒有消失。教宗,感謝你。
本篤十六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NA 譯註:「Klerusblatt」是在德國巴伐利亞的教區的月刊,目標讀者為聖職人員。
2 CNA 譯註:這「性箱子」是一個具爭議性的性教育教材,在1980年代末於奧地利學校中使用1968年革命的重點之一,就是戀童癖得到「認可」甚至獲得正面評價。
3 CNA 譯註:LTHK的全名為「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德語的意思為《神學及教會辭彙》,編輯者包括拉納(Karl Rahner)以及華爾特.卡斯帕樞機(Walter Cardinal Kasper)。
4 中譯註:英文「martyr」意即殉道者,源自拉丁文「martyr」,這是拉丁化的古希臘語
5 CNA 譯註:希臘文「道路」的意思。在新約中常常用作形容在過程中前進。
6 CNA 譯註:這是一種以程序主導的保護主義。
7 中譯註:違反信仰的重大過犯。
8 中譯註:與殉道者是同一個字。
https://www.catholic.org.tw/crbc/7magazine/37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