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5 20:00:00牛頭犬
「此情可問天」(3/10)找尋變幻時代的繼承者

電影《此情可問天》Howards End的開場,像是一段導奏,編導讓佛斯特在揭開序幕時刻意模仿法國大革命前流行的書信體敘事(像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新愛洛伊絲】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和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被擱置到稍後曼綺在倫敦讀信時,才以一種高張力的節奏揭表現出來,展開了語言誤會所帶來的故事呈示部第一主題。在影片的最開始,是當時造訪豪安居的海倫,信中部分內容的影像化,她描述著魏太太「走啊走啊,她的長裙拖在濕濕的草地上」,而全片的第一個畫面,就是昏暗光線中,一襲精緻柔軟的裙擺,在草地上緩慢地拖著,背景音樂是一戰前積極保存英國鄉土民謠的澳洲作曲家帕西葛人傑Percy Grainger所創作的「新娘搖籃曲」Bridal Lullaby,低調、幽靜、緩緩流瀉,正完美地搭配著偉大的女演員凡妮莎蕾格烈芙(飾演魏如詩)自在悠閒中帶著點衰弱病樣的步伐,以及近乎慢動作的手部擺動姿勢。時間應該是夜晚,不是小說中描述的早晨,影像陰陰沉沉、有些晦暗不清,有時甚至只剩下剪影般的形體,然後,暖色系的明亮光線意外透了進來,我們這才看清楚,原來這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其實是在房子旁的草地上漫步行走著,而相較於戶外的靜謐,屋內顯得熱鬧且嘈雜,魏太太飄忽地靠近窗戶望了進去,臉上露出了快慰的微笑,最後她盪到了門旁,嗅了嗅山榆樹上開的花,便消失在銀幕上。接著,一對男女從門口走了出來,鏡頭藏在樹叢之間,彷彿是在窺視(是魏太太嗎?),窺視著這對年輕男女情不自禁的偷歡。
這一整段開場,無需對話或旁白,便交代了許多細節,除此之外,編導還同時創造出一個頗為清晰的意象:魏太太(如詩)就是守護著豪安居這個老宅的鬼魂。當然,在這個時候,魏太太還活著,她熱愛著這幢宅邸以及這片草地,她渴望真實的生命力可以充滿這裡,但她只能觀看,安靜地凝視著其中的變化(電影中並沒有拍出小說裡施家與魏家那段誤會的最後,魏太太是怎麼用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化解了緊繃的衝突),到了故事的三分之一後,魏太太病逝了,就真的化成為一縷幽魂,無聲地徘徊在她摯愛的土地上。小說後段有許多地方,都不斷地暗示著魏太太精神的存在,有些時候,讀者甚至會意識到,自己正用著魏太太那和煦溫柔的眼神,在觀看著每個人的困境。佛斯特有一段是這樣寫的:「魏太太這個始終為她喜歡的鬼魂,不斷在她腦海中浮現,曼綺覺得她一直在看著這一切,卻沒有一絲冷冷的感覺。」
顯然,在佛斯特的心中,曼綺就是魏太太精神上的繼承者,也因此,當曼綺首次造訪豪安居時,佛斯特還刻意用了個小事件將陪伴她來的人給支開,讓她獨自一人去感受這個魏太太魂魄所繫的空間。詹姆斯艾佛利在電影版中把這個初相遇的段落拍得神奇極了,他先是不動聲色地讓飾演曼綺的艾瑪湯普遜舒緩地在豪安居外散步,也嗅了嗅山榆樹上花朵的香氣,然後意外地,她發現到一扇門並未鎖上,張望了一下,她踏進了屋內,卻被樓板上的腳步聲給嚇了一跳,樓梯上走下了一個老婦人,對著她說:「哎,我以為妳是魏太太如詩呢!……妳走路的樣子跟她一樣。」驚魂未定的她只能隨著莽撞的老婦人走出門外,這時一轉,畫面變成了主觀鏡頭,以微微仰頭的角度向前悠然地推動,山榆樹白色精巧的花朵,像是在招手般笑盈盈地搖動著,而耳旁二度響起了開場時帕西葛人傑的「新娘搖籃曲」,美麗詩意得無以復加,那觀看的眼神當然是曼綺的,但在這個時刻,卻似乎也重疊上了魏太太的深情記憶。隨後,曼綺便驚喜地發現了那個魏太太曾告訴她的那個民間傳說:榆樹上的豬牙。

這也正是前文中曼綺重新找回了「空間感」的那個段落,還記得魏太太在向她描述古代人們將豬牙鑲在榆樹上治牙病的傳說時,她自顧自地講著關於英國沒有神話只有鄉野傳說(精靈和女巫)的感觸,雖然有點唐突,但那正是屬於佛斯特心中非常本土、充滿著民族精神的一塊(那個時代民族主義還沒有沾染上太多負面色彩)。相似的細節還出現在魏家嫁女兒那個段落中,曼綺來到了英格蘭與威爾斯交界的夏洛普郡,逛呀逛的,獨自一人走進宅第附近舊城堡的斷垣殘壁,此時魏夏禮正躲在高處抽菸(電影中則是夏禮與妻子在聊家產),她突然對著眼前空蕩的廢墟喊道:「喂!是誰在那裡?」夏禮噤聲愣了一下,她繼續問道:「薩克遜人還是居爾特人?」永遠生活在當下與現實的夏禮,恐怕怎麼樣也無法理解屬於曼綺的那種浪漫,她的民族性不是為了定位自己並與他人做出區隔的血統或教養(魏如詩曾說自己的兒子夏禮可以輕易地看穿外國人的心思),而是一種純然與土地緊緊相連的熱愛,一種可以聽見古代鬼魂呼喚的抽象情感。
那麼,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得到了豪安居這個英國草根精神象徵的施曼綺,就是佛斯特心目中最理想的時代繼承者嗎?看來也不是。連導演詹姆斯艾佛利在讀完這本小說之後也直覺地感受到,佛斯特其實並不真正喜愛他筆下的這對施家姊妹,甚至佛斯特還曾這麼描述她們:「如果整個世界都是施家姐妹的話,那世界就會是一個灰色而毫無血色的地方;但世界既已是如此,也許她們在其中閃亮得倒像星星一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時代,施家姊妹(特別是曼綺)才有她們獨特的意義:她們不是繼承者,而是連繫者。佛斯特還特別在這本小說的標題內頁上,為這作品落下了一個關鍵的副標與註解:「唯有連繫」Only Connect,這也正是佛斯特文學創作上非常重要的概念:跨越鴻溝、彌平分裂、找尋連繫。
為什麼找尋連繫在佛斯特的心中如此重要?這就必須要去理解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當E. M. 佛斯特在文學史上被研究或被提及時,最常被冠上的頭銜就是「愛德華時期的代表作家」,但有趣的是,1970年才過世、享年91歲的佛斯特,其實經歷過了六個英國君王在位的時期(維多利亞、愛德華七世、喬治五世、愛德華八世、喬治六世、伊莉莎白二世),但卻只有愛德華七世在位的那十年(1901~1910)才是他創作最關鍵核心的時間點,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使懼履之地】出版於1905年,創作的高峰【此情可問天】出版於1910年,一直不敢出版的自白之作【墨利斯的情人】初稿則寫於1913年到1914年間,也是廣義的愛德華時期。

愛德華七世承接著母親維多利亞女王的輝煌時代,英國的海外擴張達到顛峰,有著日不落國的稱號,而國內的工業技術與科學也突飛猛進,商業貿易的繁榮前所未見,洋溢著樂觀進步的氣氛,整體而言就是十九世紀躍動興盛的高潮總結,而又因為養尊處優、喜歡四處交際的愛德華七世非常重視生活品味與逸樂(相較於他穿著黑衣、鬱鬱寡歡的母親),所以社會上也崇尚起揮霍享樂的生活價值,於是,從維多利亞時代因殖民開拓與貿易發達,資本主義精神暢旺而導致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到了二十世紀愛德華即位後,不僅越演越烈,加上有錢商人不再忌諱財富露白,反而以灑錢炫富為樂,更導致貧窮者的被剝削感越發地嚴重,勞資的衝突不斷推升(這情況是不是挺讓人覺得似曾相識)。當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時,會知道在愛德華七世短暫的十年在位之後,他的兒子喬治五世繼任不到五年,歐洲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不僅把一整代的青年生命都捲走,也讓那積極進取的時代氣氛完全崩毀。
佛斯特創作力最旺盛的那個時代,正是英國與歐洲顛峰極盛而再下一步就將要潰解轉衰的轉折點,或許當時並沒有幾個人真能夠預測到那天翻地覆的變化即將到來,但確實很多知識份子已經更清楚地意識到劇烈的貧富落差與階級對立,在看似壯盛亮麗的社會底下,正帶來某種不安顫動的衝突危機,像是先前提到佛斯特與吳爾芙所隸屬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員們多半在政治立場上都較為左傾(雖然成員之一的經濟學家凱因斯不太像是)也較具自由精神,對於勞動者與底層生活的處境,也有較深切的關懷。而對於他們最具有思想影響力(除了【資本論】的卡爾馬克思),也最積極於倡導政治經濟上的公平正義與分配的,其實是上一世代、維多莉亞時期的文藝評論大師約翰羅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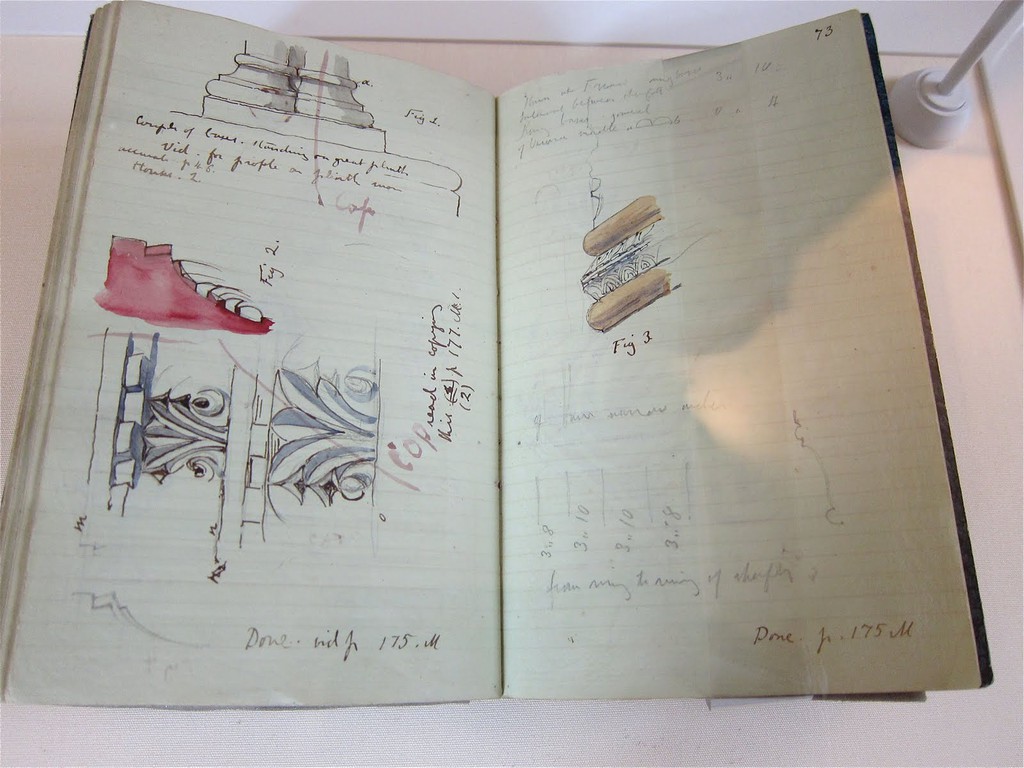
羅斯金的學識涵養豐富得嚇人,涉獵專精之處極其廣泛,所以他不只有像【給後來者言】Unto This Last這本啟發聖雄甘地的文集般,雄辯滔滔、說理清晰,從定義、概念、推論、對比、歸納一應俱全地,討論公義為何是企業、資本、國家社會在處理勞工問題時的最重要利基(不只是正確而且有利),更具代表性的,還有從美學與信仰來探討勞動價值的文章「哥德藝術的本質」The Nature of Gothic。羅斯金認為,哥德式建築的風格是1.天然粗礪的、2.富變化的、3.自然主義的、4.怪誕而有想像力的、5.頑強堅硬的、6.累贅但寬容的,也因此,這裡面便包含著一種屬於建造者的道德性,正就是因為這些作品同時兼具著巨大堅實與自由狂野,所以參與其中的勞動者都可以展現出獨立的個性,讓每座雕刻或每扇彩繪玻璃都不一樣,不完美、不精準、不一致,卻反映了製作者的創意與特質在其中,也因此,他們都是工匠,是可以生產出自己作品的藝術家,對他們而言,這項工作中有著自我、熱情與成就感,而不像工業革命之後,職能被限縮在只有生產單一制式品項的工人,遭到資本家剝削。這樣的工匠之於他的作品,一如上帝之於他創造的世界,是莊嚴而崇高的,在這樣的一個勞動的情境下,民主價值中人的自由性與獨特性才能夠被彰顯。
羅斯金浪漫理想的社會理念,對於愛德華時期(一戰前)的佛斯特來說是影響至深的,許多學者也認為,佛斯特甚至可以說是將羅斯金倡導推廣的價值想法,在文學上落實成為故事情節與主題意趣,最重要的創作者。剛提到的那篇文章「哥德藝術的本質」收錄在羅斯金1851年經典代表作【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之中,而在小說【此情可問天】裡,貧窮落魄但熱愛文藝的小職員巴連安,在那場名為「音樂與意義」的講座與拿錯傘的意外風波後,回到家中,隨手拿起來閱讀的書籍,正就是【威尼斯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