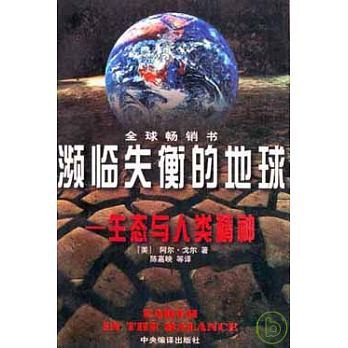【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2)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2)
《第二部分-尋求平衡》第十一章 人如其技其器
人與其他生物相區別的特點之一是人能運用資訊創造其外部世界的象徵性表述。我們通過駕馭有關世界的資訊,或同他人交流資訊,學會了如何把握外部世界本身。
對人類來說,這種和外部世界相聯繫的方式是如此之成功,乃至它現在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我們不僅把它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而且把它融入我們創造的征服外部世界的其他一切手段之中。因此,在歷史的進程中,我們日益依賴各種形式的資訊,這已成為自然而然之事。不過,這種依賴很少受到懷疑,我們很少審查我們生活中資訊的負面影響。
我們總是對知識奉若神明。每當遇上問題,我們的第一直覺就是尋找更多的資訊來幫助我們理解有關問題。在歷史上的多數情況下,在所謂的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人類分享有關世界的特別有價值的知識的複雜方式和有效運用知識的方式組成:如何讓箭頭側面有個槽,使動物的血流幹;如何編造籃子以盛容穀粒而篩去塵土;如何在狩獵和豐收時起舞,同時歌唱月亮和季節的秘密;如何講述令孩子著迷的故事,向他們傳授重要的生活經驗。
在古代文化中,積累的資訊無例外地存藏於向下一代傳述的更長的口頭故事中。在鑄造這種故事的人們那裏,無論獲取資訊還是使用資訊,其社會、文化和生態都新鮮而生動地聯繫在一起。然而,故事只是一種最簡單的技術。後來人們發明了收集、存儲和交流資訊的更為複雜的技術,例如法典和財務會計。這些技術受到重視,因為它們代表了新的力量。例如在中世紀,致力於重要技藝的專門知識的行業工會成為其成員的主要認同對象。這些新技術會使大量資訊以更為精煉,更有價值的形式一代一代傳下來,於是我們不得不重構自己的頭腦以接受這一資訊流,記住它,使用它。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有些東西丟失了。由於我們用掉了太多的頭腦接受資訊的內容,我們開始忽略交流的環境。然而,資訊所具有的力量正是在這種特定環境中形成的。例如,建造桂河橋的人全力以赴,滿懷自豪地工作,他們幾乎忘記了他們施展技藝的特定環境。我們開始忽略的事情之一是,新的資訊技術如何改變了我們,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環境。我們接受的資訊越多,我們的頭腦就越多地被代表世界的資訊所控制,而缺少了對世界本身的直感。我們日益習慣通過越來越複雜的表述方式間接地體驗世界,我們日益渴求各種資訊,於是我們也就會日益注重創造產生資訊的新方式。
當文明發現了科學方法時,這一迴圈突然加速,獲取有關自然界的知識一直是人類進取的核心。科學方法給了我們調查自然現象的有力手段,並將自然現象簡化為資訊小碎片的集合,每個信息碎片都易於解釋重述和把握。
由此產生的初始資訊的數量很快開始迅速增加,人類掌握自然的能力也大為膨脹。很快,我們也日益拜服在這種和世界相聯系的新方法的巨大建設威力之前。我們陶醉于自己的才智,先是將發明家,後是將企業家奉為英雄。我們日益確信,不管我們遇上什麼問題,我們只要採用科學方法,將問題分解成資訊部類,對之進行實驗,直到找出科學的解答,便可無往而不勝。
然而,工業時代讓位給了資訊時代,資訊的生產開始大大超過我們運用資訊的能力。約翰·穆勒曾被形容為“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現在已無人企求完全精通我們時代的知識。事實上,現在甚至已無人試圖通曉其研究領域內的一切。
我們現在面對著一個完全是自作自受的危機:我們淹沒在信息之海中。我們已生產了過多的資料、統計、詞語、公式、形象、文件、宣言,以致我們不能消化它們。我們沒有盡力創造理解和消化已有資訊的新方式,我們只是生產更多的資訊,生產速度越來越快。
我們現在對待資訊的辦法類似我們古老的農業政策。我們過去在中西部常在塔倉中存儲如山的餘糧,任它腐爛,而世界上卻有成百萬人死於饑餓。為生產更多糧食而拿出補貼並不難,但創立一個向饑餓者提供口糧的體制卻不容易。現在,我們有成倉成庫的多餘資訊在腐爛(有時是實際上的腐爛),同時,成千上萬人卻渴求獲得全新問題的答案。
我們與資訊的關係存在危機,正如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存在危機,這兩種危機頗為類似。例如,我們通過蒸汽機和汽車這一類發明,使得氧氣變為二氧化碳的過程自動化了,卻沒有同時考慮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有限能力。同樣,我們通過印刷媒體和計算機一類發明,使得產生資訊的過程自動化了,卻沒有考慮我們消化這類新知識的有限能力。
事實上,我們已生產出的龐大的資訊資料,其中很大一部分從未作為思想進入過任何人的頭腦。例如,地球資源探測衛星照像計畫每18天能完成地球表面每英寸土地的全景圖,在過去20年中,這一計畫也是如此執行的。然而,在這一期間,儘管人們急於瞭解地球表面發生的一切,但上述照片的95%以上從未有人看過。相反,這些圖形被收集起來,存儲在磁帶上,有如存入資料的塔庫中,任其蒙塵腐朽。
也許,這類資料應被稱為“外在資訊”而不是資訊,因為它完全存在於任何活人的頭腦之外。不過,不管貼什麼標籤,這種情況是在迅速地惡化。在未來幾年內,按照現在的設計,新的“飛向地球計畫”從其軌道發來的資訊,每小時的發送量將超過現在地球科學所有的總信息量。為何如此?為了幫助我們確定從現在起15年內是否真會出現所謂環境危機。無疑,這種資訊是有價值的。不過,等待這種資訊卻是危險的,特別是因為我們許多人已確信,我們已獲得了足夠的資訊做出決斷。處理這一切資訊是非常困難的事,何況這些資訊的絕大部分根本不會進入任何一個人的頭腦。
大量不加利用的資訊最終成為某種污染。例如,國會圖書館每年僅僅從印度就收到上萬種期刊。由於某些存積的資訊和知識是危險的,如原子彈的藍圖,對所有資料的監控變得既重要又困難。如果這種“有毒”的資訊洩漏給不當者,後果會怎樣呢?舉一個不那麼嚇人的例子,信用局中有關你個人的檔案就不應該讓所有想瞭解的人都能知曉。
與資訊過剩相應,我們也遇上了教育危機,這並非巧合。教育是知識的再利用,但我們卻發現,生產新資訊比保存和利用已有知識來得容易。這樣,每當遇上不瞭解的情況,我們馬上生產越來越多的資訊,卻似乎未能意識到,資訊也許是有價值的,但它不是知識的替代物——更不是智慧的替代物。事實上,我們正前所未有地大量生產初始資料,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已開始干預資訊最終成為知識的過程。當這一過程可以正常進行時,它實際上有些類似發酵——資訊首先被提純為知識,隨後在一定時間中,知識經發酵而成為智慧。然而現在,每天收集的資訊比以前多得不可比擬,信息轉為知識的緩慢過程被這種新資料的雪崩壓垮了。
如果我們需要更好地處理這大量的資訊,我們也需要更好地瞭解人類傳播資訊方式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有利亦有弊。人類的第一種資訊技術是口頭語言,它的力量一向為人尊崇。我們的宗教傳統教導說:“言詞為萬事之始”。確實,在猶太-基督創世神話中,上帝正是通過說話完成其意願的:“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第二種資訊技術是書面語言,它的出現一般被歸因為有組織文明的真正發端。
然而,人們多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人類所運用的資訊傳播方式能夠改變人本身。資訊技術和任何技術一樣,在我們與資訊所描述的物件之間起到仲介調整作用。在我們企圖以象徵性表述把握一個真實現象的全部意義的過程中,我們會遺漏某些特徵,同時通過有選擇的接納,歪曲某些其他特徵的意義。出於必需,我們按照象徵表述的圖式塑造自己的頭腦。所有的資訊技術——碑上的銘文,僧人抄錄的漂亮手稿,印刷的報刊,衛星電視和光纜傳輸的電腦圖形——這一切都擴大了我們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但是,這些技術也創造出特有的歪曲模式,從而改變了人類頭腦接受、記憶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們通常是完全適應了所採用的傳播交流技術,以致忽略了它的歪曲效應。例如,口頭語言使得經驗平整劃一。即使口語在傳達區別、對比和微妙的含意,它也起著同一化和規範化的作用——這僅僅因為,一個人的直接經驗常常與達意之詞而不是與意義本身相關聯。例如,戒律禁止人們輕慢地說起上帝,可能一部分是因為“上帝”是一個極具意義的名字,這個詞應該在使用者的心靈中引起激蕩。這個詞一旦降低為可隨意使用的象徵,“上帝”一詞就會為人迴圈利用,在這樣的使用過程中,這個詞就會喪失不少引起敬畏的魔力。這個詞還會進而被人亂用,人為擴大那些凡人瑣事的意義。
再現的形象也同樣起到平整劃一的作用。本傑明在其經典之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中描述了機械複製的藝術品如何失卻了“靈氣”或聖潔。看過《蒙娜麗莎》或《泛舟午宴》的印刷畫的人也會熟悉這種效果——不管印刷畫如何忠於原作,仍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作的感染力。如果我們在幾個不同場合看這種印刷品,每次新的接觸都會減少原作在多次複印中殘剩的體驗感染力。這是一種交換:更多的人可以體驗到原畫傳達的某些內涵——事實上是相當多的一部分內涵——但是,看印刷畫的體驗與看原畫的體驗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一旦人類採用某一技術來調解自己對世界的體驗,就會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力量,但也會失去某些東西。例如,工廠的組裝線效率日益提高,它要求許多雇員不斷重複同樣的工作,最終,這些人喪失與創造過程有關的任何感覺——隨之也失去了目的感。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們與自然的關係之中。我們日益依賴技術來仲介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我們也日益遇上同樣的交換:我們具有更大的能力,能更容易地為更多的人向自然索取,用來製造我們需要的東西,但是,過去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所具有的那種敬畏感常常被置諸腦後了。現在許多人視自然界為資源的集合體,這就是主要的原因。確實,對某些人來說,自然有如一個他們可隨意操縱的大資料庫。然而,這種觀念的代價是昂貴的。人類拯救全球生態系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對環境的新的尊崇,將環境當作整體而不是部分給予尊崇。
不過,太多的人只對資訊和分析表示了尊崇。環境危機就是這樣的例子:許多人拒絕認真對待它,這僅僅因為他們對人類應對任何挑戰的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只要能弄清問題所在,收集有關的大量資訊,把問題分解成可操作的部分,最後就能解決問題。然而,我們將可能採取什麼辦法來完成這樣一種工作呢?現在有關環境危機的信息量(及多餘信息量)是如此之巨大龐雜,就事論事的常規辦法完全行不通了。此外,我們一直在鼓勵我們最好的思想家在分析微觀部分上殫精竭慮,而不是努力理解宏觀整體。
儘管在這個所謂的資訊時代,或許正是因為在這個所謂資訊時代,現在所需要的是傑弗遜式的對待環境的辦法。和同時代的其他大思想家一樣,傑弗遜追求一種對知識整體的領悟。他和他的同事在費城著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憲政民治政府,他們把對人性的出色領悟與對法學、政治、歷史、哲學和牛頓物理學的充分把握結合起來。現在,全世界來到了一個分水嶺前,其狀況與200多年前美國的創建者所面對的挑戰有幾分可比之處。當時,13個殖民地面臨的工作是確定聯合其共同利益和認同的框架。而現在,所有國家的人民己開始感到,他們是一種真正全球文明的一部分,他們被共同的利益和關心聯繫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拯救我們的環境。如果我們想得到成功,我們必須防止如潮的資訊淹沒我們,必須不再把自然界僅僅視為一個方便的資源和編碼資訊的倉庫。我們必須具有足夠的勇氣採用傑弗遜式的方法,力求把對文明性質的概括理解和對環境運行方式的全面把握結合起來。
當然,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遠不止於對資訊處理方法的影響。事實上,科技革命幾乎完全改變了人與地球關係的客觀現實。新的工具、技術和工藝流程層出不窮,我們從而延伸了自己的感受力,擴大了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現在,我們能夠看見土星的光環,分子中的原子,人體心臟的瓣膜,在月球地平線上升起的整個地球。我們能夠聽見早已去世者的講話錄音,聽見深海鯨魚的樂譜,聽見一千英里外墜入廢井的嬰兒的啼哭。我們能在以兩倍音速飛行的飛機座艙的過道上行走,能在午飯時離開歐洲,同一天可到紐約吃晚些的早餐。我們能抓住大起重機的把杆,像阿特拉斯神一樣舉起千人的重量。
依然在加速的科技革命正擴大著地球上55億人的力量,使他們能按照其意願再創客觀世界。在人類心中迴響的每一種志向、渴求、欲望、恐驚和希望現在都對外部世界有更有力的影響。古代的思維習慣現在有了新的意義,因為我們的力量可將最大膽的想法化為行動。然而,我們有些像魔術師的學徒,正在學習如何任意支配無生命的物體,同時,我們也啟動了比所預料的更為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已比開頭時更難阻遏。
在科技革命產生的諸多問題中,核武器對戰爭觀念的影響須單獨加以深入的審視。核武器構成了一種明顯而致命的威脅,過去45年中,成百萬的人抗議說,只要這種技術能在戰爭中應用,我們的世界就是不安全的。但是,核武器已大大改變了我們的戰爭概念,這從長期看可能是有益的。美蘇之間漫長的冷戰畢竟沒有導致直接的武裝衝突,其部分原因是,兩國都注意到了核時代戰爭的難以想像的可怕後果。蘇聯和所有東歐國家後來從共產主義轉向民主和資本主義,基本上沒有暴力出現,在有關戰爭可否接受的觀念出現變化之前,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
數千年來,戰爭是文明的一部分,同樣,我們為生存、為食物、水、房舍、衣服和其他生活需求而掠奪地球的古老行為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多年來,特別是在本世紀,科學技術給了我們成千上萬種新工具,擴大了我們為了自己的所需,或僅僅為了自己的所欲而向地球索取的能力。所有這些新技術自身並不能與核武器的意義相比,但把它們加在一起,其對地球自然系統的綜合影響卻使得無節制掠奪的後果和全面核戰爭的後果同樣不可估測。
認識到奧本海默博士的原子彈和諾貝爾博士的炸藥在性質上的天壤之別並非很困難的事,其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種突出的技術上。與之相比,把所有影響人類與地球關係的強大新技術與人類試圖通過這些技術來滿足的種種需求與欲望加以綜合考慮卻是極為困難的事。這些技術的積累效應與以往技術的積累效應,在質上是不同的。但是,由於這些技術數量極多,大多數技術完成的工作與人類生活己息息相關,因此,人們很難意識到這種環境上的重大變化是改變人與地球關係的歷史性事件。
我們成為某種技術自大狂的犧牲品,這種心態誘使我們相信自己的新力量是無限的。我們大膽設想,所有技術引起的問題均可以通過技術來解決。文明似乎已對自己的技術偉力敬若神明,為這種做夢也想不到的神奇而陌生的力量所折服。在希臘神話的現代版本中,我們的自大狂誘使我們自私地盜用了可怕的力量,不是從諸神那裏,而是從科學技術那裏盜用了這種力量,誘使我們向自然要求神一樣的特權以滿足自身無度的奢欲。技術自大狂誘使我們看不見自己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自以為什麼都能心想事成。
我們對技術的癡迷取代了往昔對自然奇跡的癡迷,這已成為屢見不鮮之事了。就像小孩子會認為麵包是從商店貨架上長出來的,我們開始忘記技術只有應用於自然界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隨著人口的增加,隨著我們更高消費要求的繼續增長,我們向文明索取想要的一切,卻忽略了造成所有自然系統結構破裂的緊張和拉力。在感性上,我們離超級市場更近,而不是麥田,我們對包面包的五彩塑膠紙給予更多的關注,卻較少關心小麥田表土的流失。於是,我們越來越關注用技術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我們與自然界相聯繫的感受力卻變得麻木不仁了。
當我們力求人為擴大從地球索取所需的能力時,我們常常因此直接損害了地球自然地向我們提供所求的能力。例如,我們使用造成表土流失的技術來增加農業產量,我們同時就損害了土地未來生長更多糧食的能力。我們時常忽略了技術煉金術對自然進程的影響,因此,我們製造了成百萬台內燃機,使氧氣自動轉化為二氧化碳和其他氣體,我們同時就干擾了地球從大氣中正常排除雜質的自淨能力。
為了改變當前人與環境關係的破壞性模式,我們必須發展一種對技術作用的新理解:有些欲望和行為從前曾是良性的,但技術會放大這些事情的有害後果。在很多情況下,技術本身也需要改變。例如,繼續生產20英里耗油1加侖、同時向大氣排出19磅二氧化碳的汽車和卡車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事實上,我們需要做出加速某些新技術發展的戰略決定,如太陽能電力生產,這種方式對環境的有害影響較少。但在所有情況下,要取得成功,我們就必須慎重關注我們是怎樣通過技術與環境相聯繫的,而且尤其必須關注重大技術對這種聯繫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有時,從一種技術向另一種技術的轉變會改變既有的模式。例如,對政府和政治而言,印刷媒體的發明導致了全新的方式。印刷媒體使共同觀念和價值(通常通過共同語言)得以廣泛傳播,在這一基礎上才能建立某一類型的國家。一些現代國家只是在印刷媒體問世後才形成的。許多歷史學家說,沒有潘恩所著《常識》一類印刷冊子和論文傳播了美國新國家的觀念,美國革命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任何時代的主導技術常常對可信可能之事形成不言而喻的設定。例如,憲法建立了政府三權制衡系統,其中每一權力分枝被設定為其他兩種權力分支的平等機構。但是,憲法的作者們認為,每一權力分支應主要通過印刷物與人民相聯繫。在20世紀中葉,電信廣播取代報紙成了主導的大眾傳播手段,起碼在老百姓的眼裏,政府的三個分支機搆的相對突出性發生了變化。和國會與法院不同,總統可以在電臺講話,電視出現之後,他的形象和氣質又可以顯現在幾乎每個美國家庭的客廳裏。參眾兩院和最高法院的成員在這些媒體得不到露面講話的機會——只是在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時,他們作為鼓掌者才會顯形。因為在民主國家中,真正的權力來自人民,這樣,總統相對政府其他分支機搆的突顯地位很快就相當於通過技術而造就了某種憲法修正。
再看一看另一種影響政府制度的技術。現在的戰爭技術不再是大規模的陸海軍,需幾個月的時間來集結和投入行動,而是洲際彈道導彈,它會在國會湊齊法定人數之前就擊中目標。這難道不會構成消除國會的宣戰權的威脅嗎?這又一次表明,技術幾乎己修改了憲法。這也再次表明,就技術與政府系統的相互關聯而言,新技術比老技術有著非常不同的技術係數(“技術係數”指一種技術對其應用範圍發生影響的獨特方式。——譯注)。
即使新技術的採用也出於同樣的基本目的,只要它取代了另一種技術,就會深刻改變一個系統內不同組成成份的關係。此外,當前新一代技術問世的速度極快,技術的替換有時突如其來,異軍突起。這也對人與環境的關係帶來問題。在美國有個著名的有害化學廢物堆放地洛夫運河。讓我們以這條運河的起源為例。在本世紀初,在愛迪生發現電能控制方法之後不久,新的化學加工工業因可以依賴大量電力而應運而生,當時,化學工業在尼亞加拉瀑布一類水電站附近建立工廠,越近越好。愛迪生採取的辦法是出售所謂直流電。直流電在遠端傳送中要損失大部分電能。這樣,靠近尼亞加拉大瀑布附近的優良工業建設用地很快供不應求。
一個叫C.W.洛夫的企業家突發奇想,要在尼亞加拉河上游數英里處挖一條運河,河流在此處彎過一座山邊流向瀑布,河本身折了一個大彎。洛夫意識到,用一條運河將尼亞加拉河的兩側彎流聯結起來,可形成一個能用於發電的人工瀑布。他希望以此吸引新的化學工廠到新運河兩側來落戶。然而,在洛夫開始運河工程後不久,他得知一個名叫N.特斯拉的俄國移民發明了一種使用所謂交流電的新辦法,可以進行較遠端的輸送而損失較少的電能。
化學工廠突然不再需要靠近發電機了,尼亞加拉瀑布的電能被輸送到若干英里外興建的新工廠中。當這些工廠想找個地方堆放化學廢物時,他們發現了一條只挖了一部分的廢棄運河。這條運河被填滿後,又在上面覆蓋了泥土。許多年後,人們沿運河兩岸修建了住宅小區,在運河中間是一所小學校,學校的孩子們從來不知道洛夫運河的來歷,直到化學物從操場逸出,他們才明白了一切。
我們能夠看到一些類同的情況。我們的社會聽任內城區成為犯罪、吸毒、貧困、愚昧和絕望的有毒垃圾場。在這一情況中也存在一種轉變,但這不是單一技術的轉變,而是工業時代自身的轉變——這個時代促使工廠房屋等集中於港口一帶擁有大量煤炭、原材料和工人的地區。在其後的後工業時代中,家庭遷居到郊區,人們找到了新的工作,建立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們遺棄的內城區便對有效的生產活動無關緊要了,多多少少成為舊時生活的遺棄物。
有時,並不是技術而是應用技術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例如在肯雅,一個氏族曾在裏夫特山谷的高地上通過一種成功的技術墾殖種糧,這個氏族後來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遷移到低地地區。然而在新地區,由於雨水更多,土質不同,過去世代採用的有效的農業技術導致了災難性的水土流失。同樣,把在富裕發達國家中有效的工業文化移植到社會條件不同的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恐怕也是很不適宜的。
多種重大技術的相互作用也能使人與技術的關係複雜化。我們都會時而見到藥方上的警告,提醒我們注意藥物可能的相互反應:兩種藥分開服用時效果良好,但一起服用時則產生非常有害的反應。對於技術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我時常猜想,電視和印刷技術同時存在,在傳播以及組織政治思想方面互相競爭,有可能導致了美國政治文化中某種類似的不良反應。人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對一個事件或思想的說法,它們與在晚間電視新聞中看到的同一事件和思想大相徑庭,印象完全不同。每一種媒體都有創造自己的思想方式的傾向,都傾向于使對方受挫。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作為整體似乎不能確定自己的目標,更不用說能團結一致地走向這些目標了。
作家O.帕斯在不同的情況下也觀察到這一現象,他認為,印度似乎存在著社會癱瘓,其部分原因是世界上最嚴格的一神教體系伊斯蘭教與世界最精緻的多神教印度教的共存。同樣,我懷疑,美國的政治癱瘓可能部分出於在傳播政治思想上兩個強大而衝突的媒體的共存。
在考察科學與技術如何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對“技術”的定義予以精確化似乎是有益的。除了工具和發明設計之外,我們還應加上組織系統和方式,它也能增加我們征服世界的能力。凡是能產生新的方式擴大人類能力或促進完成某些工作的過程整體均可被視為技術。甚至像市場經濟學或民主一類宏大的新思想系統也可被視為產生一定結果的發明,它們有時有難以預期的後果。
如按這種廣義的定義,人體也能被視為一種技術。我們思考環境的方式無疑是從我們體驗地球的方式開始的。我們與地球的主要接觸是通過五種感覺進行的。然而,儘管大多數人將此視為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就提供有關世界的資訊而言,我們的感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五官給了我們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初步感覺,儘管如此,它們還是限制了我們的體驗,並把我們的體驗導入一種只反映五官所能接受和加工的資訊的模式。其結果是我們開始相信,我們接受的有限資訊代表著實際存在的一切。所以,當我們發現我們見不到的某些東西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當它構成我們必須回應的嚴重威脅時,我們常常很驚奇。
例如,摧毀臭氧層的化學物氯氟烴是無嗅無味無色的。換言之,我們的感官如無外部幫助,這種化學物對它們來說就不存在。同樣,過去幾十年中,二氧化碳又在大氣層中大量集聚,如果不使用精巧手段加以測試,我們也見不到這種情況。此外,太陽光線中有一種特別的紅外線,它為過多的二氧化碳和氯氟烴所阻留,它也屬於光譜中人眼看不見的那部分射線。事實上,人類回應生態危機的難處部分在於,生態危機的徵兆尚不能通過味覺視覺嗅覺和觸覺提出直接的警告。在過去幾年中,許多人注意到夏天變得更熱了,乾旱時間更長了,如果說,這種全球變暖的明顯證據已使人們更嚴肅地對待這一問題,那麼,如果我們能感到氯氟烴的味道或看見二氧化碳,生態危機將會顯得何等緊迫!
如此說來,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很難說是完美的技術。在感受世界的方式上,性別的作用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心理分析學專家E.艾裏克森的一個著名試驗說明了這一點。40年前,艾裏克森給一群孩子一些積木,仔細觀察他們搭建的形狀與結構。女孩子們更願意搭出在內部保留空間的結構。男孩們則相反,更願意搭建從底座向外和向上伸展、佔據四周空間的建築結構。
這似乎正是我們的整個文明與環境相聯繫的方式,其特點是拼命向自然擴展,而很少強調可以保存、保護和養育環境的模式。按照這一觀點,在過去幾千年中,西方文明一直強調一種非常男性化的對待世界的方式,並以一種貶低女性化生活態度的哲學結構來組構其文明。例如,當科學技術革命加速之時,我們似乎更為強調延伸和擴大能力的技術,諸如人類的作戰技術——這在歷史上與男性而非與女性有更多的關聯。與此同時,減少可悲的嬰兒高死亡率的新方法卻很少為人關注。確實,我們對技術本身的態度也是依據同樣的視角形成的:重視發明設計而輕視系統考慮,重視主宰自然的方法而忽視與自然協調的方式。歸根結蒂,環境危機的解決將部分取決於我們能否在兩性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對女性體驗世界的方式予以更合理的尊重,以此影響占主導地位的男性觀點。
和性別的情況一樣,人生的不同階段也對個人與世界的關聯方式有深刻的影響。例如,少男少女們有一種永生不死之感,這鈍化了他們對某些物質危險的感知。另一方面,人到中年,感情上成熟之後,就會自然感到一種欲望,想在艾裏克森所謂的“繁衍生計”上多花些時間和努力:這是一項思長慮遠之計。這種隱喻是難以抗拒的:一種文明曾像青少年一樣獲得了新的力量,但不成熟,不會明智地使用這種力量,它有一種不現實的永生不死之感,對嚴重的危險麻木不仁。同樣,作為一種文明,我們的希望可能完全取決於我們能否調適出一種作為真正全球文明的健康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具有成熟的責任感,致力於在人類與地球之間創造一種新的、生生不息的關係。
我們肉體存在的另一個特點也塑造我們的生活體驗,雖然我們視之為天生當然之事,幾乎不加注意。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基本人體構架,它在身體兩側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半部,如鏡子一樣將我們的身體一分為二。我們身體的這種鏡映式特徵被稱為雙邊對稱,對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我們在世上做些什麼,我們差不多總把它從觀念上一分為二——固定和操縱,讓我們身體機器的對應兩側各負其責。今天吃早飯時,我用左手按住柚子,讓它在盤子中不動,然後用右手來操縱它,先是用刀把整個抽子切成片,然後用勺子把小片送入嘴中。當我和孩子玩抓球游戲時,我先用戴了手套的手把壘球握定,然後伸過另一隻手抓起球,扔給一個孩子。
我們也運用大腦的兩半以不同方式與世界發生聯繫:一半善於保持順序感和空間比例,另一半則善於邏輯之類的思想運作。有些語言學家認為,在幾乎所有的語言中,唯一的共同特點是離不開主謂二分法。確實,本頁中的每一句子都以名詞開頭,並通過一個動詞移向句尾。我們一直在強調改造世界,強調行動,但依T.貝裏神父的話說:“世界是主語的共聚,不是賓語的複合。”
這一關於雙邊對稱的說法聽起來也許有點模糊,但我認為,這也許是現代技術扭曲人類與地球之關係的一種最危險的方式,因為技術已大大擴張了人類駕馭自然的種種能力。迄今為止,它卻遠沒有同樣擴大人類保存和保護自然的能力。現在,我們有一千種無比強大的新方法來操縱和改造脆弱地球的自然系統,但在如何鞏固和保護環境免遭不測之災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仍是原始的。我們對自然的無情操縱非常可能導致災難性的連帶傷害,這正是因為我們未能考慮怎樣保障自然環境的穩定性與連續性。
當技術被人輕率地運用時,就可能破壞世界的生態平衡,同樣,運用於人類體驗世界方法上的一些技術也可能破壞生態平衡。技術可能僅僅增強人的某些感知力,僅僅擴大人的某些能力,僅僅提升人的某些潛能,而不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質。這樣,技術就能深刻地改變人觀察和體驗世界的方式,從而也改變了人與世界的關系模式。例如,在本世紀的後半葉,我們以前所未聞的方式操縱自然,每當出現了問題,我們就條件反射一般尋找更多的操縱自然的辦法,希望以此補救以前的干預行為造成的損害。
在討論溫室效應時,我確實聽到過老成的科學家建議說,在地球軌道上放置數十億錫片,可以把射來的陽光反射回去,以此平衡現在大氣層中截留的大量熱量。我還聽到過其他人認真地提出了一個龐大的計畫,要向海洋施用含鐵肥料,以刺激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這也許能吸收一些人類造成的過多溫室氣體。這兩種建議都出自這樣一種衝動,即為了抵銷以往操縱自然造成的後果而再度操縱自然。我們似乎認為制定這樣的浮躁計畫倒更容易些,不肯思索一下似乎更為困難的事,即對以往操縱方式明智與否做一番反思,注意到過去的操縱方式似乎未能與環境保持一種健康關系,因為它們正在摧毀環境。
就最深層的意義而言,關心全球生態的環境主義正在一部分人之中勃然興起。這些人頭腦較為清楚,他們知道,在人類無可挽回地操縱和改變自然萬物之前,必須鞏固、保護和保存這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