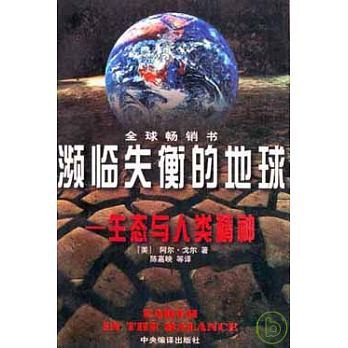【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1)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1)
《第二部分-尋求平衡》第十章 生態經濟學:真相與後果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或許是人類文明史上所使用過的最有力的工具。作為一種制度,它分配資源、勞動力、資金和稅收,決定社會物品的生產和流通,以及財富的消費。古典經濟學在指導我們生活的近乎各個方面的決策上占絕對主導地位。因為古典經濟學的規則如此有說服力,我們通常把它當成不言自明的真理,就像在科技革命之初由牛頓所定義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僅僅幾十年之後亞當·斯密制訂了經濟學的基本原則,至今仍是經濟學的基石。
市場經濟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我們這些堅信資本主義的人因此應當更加有所作為,而不是僅僅沉涸於自我喝彩。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的勝利意味著世界上其他國家將更有可能採納我們的制度,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更加深層次的課題,即糾正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缺點。
事實是我們的經濟體制只看見某些東西而對另一些東西視而不見。它仔細地衡量記錄對於買者和賣者而言最重要的東西如食物、衣物、製成品、工作和金錢本身的價值等。然而這種精密的計算方法常常完全忽略了那些難以用買和賣衡量的東西的價值,如新鮮的淡水,清新的空氣,美麗的群山,森林中豐茂的生物。事實上,我們現行的經濟制度存在的這個問題是導致全球環境問題的不合理決策的最主要原因。
幸運的是,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雖然解決起來困難重重。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像其他工具一樣,經濟學雖然賦予我們嶄新的力量,它卻扭曲了我們和世界的關係。由於我們變得完全依賴於我們經濟制度所具有的能力,我們的思維亦與之相適應,並開始認為這種經濟理論能夠就我們希望它解釋的一切問題提供全面的分析。
然而,就如同人類的眼睛只能看到光譜的一小部分一樣,我們的經濟學無法看到,更無法衡量我們世界主要部分的全部價值。相對於我們的經濟決策所帶來的總體代價和全部利益來說,我們看到的,衡量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視覺上和在經濟學上一樣,我們看不到的也就想不到。
很多我們沒有看到的經濟學問題加速了環境惡化。許多暢銷的經濟理論書籍甚至沒有提及諸如污染或自然資源匱乏等經濟決策上的基本問題。雖然許多微觀經濟學家在特定的前提條件下已經研究過這些問題,它們在總體上沒有融入經濟理論之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H.戴利是這一問題的主要研究者,他說:“宏觀經濟學和環境之間至今沒有建立起聯繫。”
看看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運作的最基本的尺度——國民生產總值(GNP)。在計算GNP時沒有計算自然資源的消耗。建築、廠房會貶值,如同機器設備和車輛會貶值一樣。因此,由於草率的農業耕作方式削弱了土壤表層抵禦風雨侵蝕的能力,導致了依阿華州的表土流失到密西西比河之中,難道它不貶值嗎?為什麼這種損失不能算作我們去年種植穀物的花費呢?如果表土一年之中流失極為嚴重,即使把穀物價值計算在內,國家也會變窮。而我們的經濟統計會使我們相信因種植了穀物而變富。實際上我們變富是因為沒有花必要的錢來保護環境,不使水土流失。這已不僅僅是經濟理論問題了。我們已失去了依阿華州一半以上的表土,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以適合環境保護的方式種植穀物的價值。
類似的例子成千上萬。這就是其中一例:大量使用殺蟲劑會確保我們種植的穀物獲得最高的短期收益,但這樣草率地過度使用殺蟲劑污染了農田底下的地下蓄水層。當我們在計算種植穀物的花費和收益時,水資源的損失被忽略了,我們沒有考慮到乾淨的地下水的價值。我們已經因殺蟲劑和其他有毒的化學藥劑的無法被清除,污染了美國一半以上的地下水,而這些有毒的藥劑實際是無法清除的。
讓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發生在美國之外的例子。某個發展中國家一年內砍掉100萬公頃熱帶雨林,賣木材所得的錢會算作那個國家本年內的收入的一部分,一年內鋸子和運輸木材車輛的損耗會歸入總賬的消費之列,而熱帶雨林的“損耗”卻沒有計算進去。事實上,這個國家GNP的計算過程沒有一處能反映100萬公頃的雨林己被砍伐的事實。這應該讓人感到震驚甚至荒謬。然而,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區域性開發銀行以及國家信貸機構決定給世界各個國家以什麼樣的貸款和資金援助的時候,它們考慮的是什麼樣的貸款會如何改善一國的經濟運行。對所有這些信貸機構來說,衡量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尺碼是一國GNP的增減。出於所有實用的目的,GNP把對環境的這種快速而且不顧後果的破壞看作一件好事!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經濟學家R.羅佩托曾經帶領一個小組研究國民收入統計的變化對印尼發展模式的影響。這個國家森林資源的淨損失現已超過了出售木材所得的收入:大量表土的流失使得出售木材所得的純收入銳減了40%,然而當這個經濟悲劇正在上演而印尼正在走向懸崖邊的時候,所有官方的報告都展示了一幅經濟平穩發展的喜人景象。
最近,我問聯合國負責定期修改GNP定義的官員,為什麼計算GNP時這種只見益處不考慮危害性的現象依然存在?每隔20年,在聯合國的主持下,世界有關組織會重新審議GNP和其他衡量經濟運行的重要標準的定義。許多經濟學家,如戴利和羅佩托,以及馬里蘭大學的R.康斯坦查很久以前都曾經敦促修改GNP的定義。這也正是我所建議的。當時這些官員們剛開始進行20年一輪的審議。他們也建議進行修改——這是明智的做法——但又認為那樣做很困難,現在進行不合適。他們說:“可能在下一次審議的時候會修改。”而那又將是20年以後了。
我們的經濟體制在與馬列主義進行鬥爭時,顯示了十分強大的威力,而它卻沒有重視到水污染、空氣污染,以及每年幾萬種生物滅絕等環境問題。我們每天做出幾億個經濟決策,其後果卻是使我們逐步走向環境失衡的邊緣。
古典經濟學家通常會說,所有參與供求這一矛盾中的人都會佔有“完全的資訊”,即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每個作經濟決策的人能預先知道與他們將要決策的問題有關的所有事實,再做出決策,雖然允許有少許的判斷失誤。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體制有一種市場清理功能,而且這種功能是充分的,“完全的資訊”是這一假設的符合邏輯的推論。一個人所共知的小故事最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個老人和他的孫女在街邊散步。小女孩看到路邊有一張20美元的鈔票,她剛想把它揀起來,老人說:“不要拾它。如果路邊有張20美元的鈔票,早就被人揀走了,那不可能是真的。”
古典經濟學家自視高明,把話說過了頭。特別是考慮到古典經濟學家並未重視自然資源流失的代價這個問題。正像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對於人們的實際可得的資訊做出各種可笑的、不合實際的判斷一樣,古典經濟學也堅持另一同樣可笑的觀點,即自然資源是用不完的“免費商品”。
這種觀點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國民收入計算體制是由凱恩斯在殖民時代末期提出來的,當時自然資源的供應看起來確實是源源不斷的。事實上,如今那些擺脫殖民統治達一代人之久的國家環境污染最嚴重,這並不完全是巧合。對環境的過度開發的勢頭很難遏制,特別是如果這些流行的經濟觀點是由那些首先對從這些國家掠走自然資源感興趣的人所提出的。
然而這種計算方面的盲目性不僅是在計算產品價值上。根據能量轉換和守恆定律,物質和能量既不會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因而自然資源就轉變成有用的物品和有害的副產品,後者包括我們有時所說的污染物。我們的經濟制度以一種更注重我們生產的好產品而不是壞產品的方式衡量生產的效率,即“生產力”,這就不足為奇了。每種生產程式都會產生廢物,為什麼這不算進去?如果一個國家生產大量的鋁,為什麼氟化鈣這種可避免的“副產品”不計算進去呢?
生產力的提高——這個衡量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尺度——如今被另一個荒謬理論方法衡量著,即如果一項新技術有好壞兩方面的作用,在某種條件下就可以只考慮該技術的好作用而忽視壞作用。通常,某個聰明人找到了一種更好的方法用同等數量的勞動、原材料和資金來生產更大數量的產品,人們就說生產力提高了。但是如果這種聰明的新方法不僅導致生產的增長,而且會產生更多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難道不該被考慮在內嗎?事實上我們最終可能要花很多錢來消除這種影響。
然而荒謬之處不僅於此。清除污染所需的費用通常被列入國家支出。換句話說,我們造成的污染越多,我們對國家支出做出的貢獻就越大。例如埃克松·瓦爾德茲號油輪在威廉王子灣發生石油溢漏之後,清除海水中溢漏石油的一系列努力實際上都增加了我們GNP的總量。
古典經濟學也沒有能夠正確地計算與消費相連的一切花費。我們每次消費都會產生一些廢物,而古典經濟學家乾脆忽視這一點。我們每年消耗數百億噸的氯氟烴,它們真的被消耗盡了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是什麼導致臭氧層出現漏洞?我們每天消耗1400萬噸煤,6400萬桶石油,它們真的被消耗盡了嗎?果真如此,大氣層中那麼多超量的二氧化碳從何而來?
所有這些暗含的消費都沒被正確計算。實際上,我們的經濟體制衡量生產力的方式,即使是在這個體制本身的邏輯範圍之內也不能自圓其說。古典經濟理論的超級理智的經濟人假說差不多就像相信魔法一樣。如果我們利用自然資源生產商品而這種自然資源因為取之不竭而永不貶值,如果生產過程中又不會產生任何我們所不需要的廢物,如果產品被消費後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我們確實是在目睹魔力之神奇。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坐在我父親的辦公室裏,聽到一位表面看上去很正常的人詳細地解釋他製造的一台機器,據說這台機器能把鉛變成金子。我猜想我父親表現得那麼和藹而有耐心,是想給我一個機會看一看地球上最後一個煉金師。事實上,煉金師大有人在。因為我們想著在消費商品和資源時,實際上是在把這些東西變成不同的化學和物理物質。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工業性煉金術,並且在某個時候,人類將為這種“煉金術”所隱含的費用付出代價。
古典經濟學對生產力的定義很狹隘,並且鼓勵我們把生產力的發展等同於經濟的發展。但是發展的魅力是如此誘人,以至於經濟學家傾向于忽略那些伴而發展的不利副作用。當然問題是二者總是相伴而行。聰明的做法是權衡利弊再決定總體的效應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如果我們計算我們行為的價值而一直不考慮重要的負面影響,那麼我們將不斷遇到令人不愉快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當新的環境污染被發現了,我們回顧過去,常可以發現那是由幾千個看似明智實則拙劣的決定累積的後果。而這些決定都是遵照標準做出的。然而權衡它們的利弊之後,就會發現這些標準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為什麼不事先考慮這些決定可能會造成的後果呢?答案在於我們的經濟制度能夠掩飾許多決定的不良影響。這是通過給這些不良影響貼上“外部效應”的標籤這種“聰明”的做法來實現的。
當經濟學家衡量積極因素並試圖忽視負面作用時,他們宣稱負面作用難於被歸入他們的計算整體之中。壞事物通常不能推銷給任何人,而處理其後果的責任卻推給了其他的人。因此,既然對負面作用的權衡會使對積極因素的衡量複雜化,負面作用就簡單地被認為是程式之外的事物,被稱為“外部效應”。
這種通過主觀臆斷的定義把不利的事實排除在對總體的衡量之外的習慣做法是一種不誠實的表現。這在某些方面與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分子所表現出的無視道德規範的做法相似,他們也利用武斷的定義來為他們在評判善惡時將劣跡排除在考慮之外的做法辯護。例如,一個種族主義者可以在其自身及其同種族人的周圍劃定一個圈,目的在於排擠異族。種族主義者然後總是做些抉擇,通過貶低圈外之人來人為地提高其自身的價值。這就經常造成圈內人的地位提高與圈外人的地位降低。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制就是這一現象的兩個例子。
同樣,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在人類文明決定加以衡量觀察的事物周圍主觀地劃一個價值圈。然後我們發現人為地提高圈內事物價值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貶低圈外事物的價值。這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傾入河中的廢物越多,污染製造者及其股東所得的短期利潤就越高;熱帶雨林被焚燒得越快,牛就能越快地吃到更多草地上的草,牛肉也就能越快地被做成漢堡包。我們未能將環境因素考慮在內,這一失誤實際上是忽視了破壞環境的政治代價,其後果不堪設想。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數學家C.科拉克曾這樣說過:“許多經濟顯著增長的結論都是在沒有考慮自然資源損耗的情況下得出的,因此可能只是一種錯覺。”
他建議我們認真地研究任何生產帶來的有利與不利的產物,並且注意兩類產物的變化,然後再計算生產力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例如,一個熱電廠既發電又造成大量的空氣污染。電力可以出售,因此很容易計算它的經濟效益,但計算出哪怕是部分廢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可能的。各種硫氧化物導致工廠下風頭田地裏的作物減產,還造成各種污染,能見度降低,為治療呼吸困難還需花醫療費。為了弄清在空氣中每多排放一噸硫氧化物廢氣所要付出的代價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當然,迄今為止,問題的答案還遠不如電力的價格那樣明瞭。然而,這種困難不應該作為一種將這種代價視為零的藉口。現已有一個大家所公認的標準,該標准內的某些數值可以並應該用來計算燃燒一噸煤的收益和代價。
熱電廠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當一項新的法律——如要求降低空氣中二氧化硫含量的清潔空氣法——生效之後,我們就會聽到熱電廠的發電能力將下降的說法。這種說法根據的計算方法只計算燃燒每噸煤所造成的污染的代價而根本沒有計算由於降低煤的消耗所帶來的經費節省。即使我們稍加改變衡量生產力的方法,把那些已有公認的代價標準的污染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包括進來,我們也會大大地接近真正的得與失的準確定義。
然而,超過一定的限度就不再可能給我們的經濟抉擇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定價。新鮮的空氣,清潔的水源,在山中湖面的濛濛晨霧中升起的太陽,陸地上天空上海洋裏自由繁榮的生命,所有這些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如果因為這些寶貴的財富沒有標價,就有理由認為這些財富沒有價值並基於這種觀點來做各種決定,那可真是心腸冷硬了,就像王爾德所言:“心腸冷硬的人知道每件事物的價格卻不知道它們的價值。”
如果我們只考慮我們認為足以衡量經濟系統的那些重要價值,這樣不僅會排除對環境而言很重要的許多東西,而且是在歧視我們的後代。傳統的經濟分析的公式對未來價值的看法不僅目光短淺,而且恐怕頗不合邏輯。尤其是,在評估自然資源的使用與開發所造成的成本效益流動的時候,標準的“貼現率”通常假定所有的資源都屬於當今的一代人。我們以現在就耗盡全部資源為准來計算其價值,於是,任何對後代人可能有價值的資源都大大“貶值”了。其結果是以犧牲後代人的方式來擴大這一代人的權力。用戴利的話來說:“以破產清算的方式來對待地球,這樣做是完錯誤的。”
1972年聯合國成立了布倫特蘭委員會(即由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女士任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譯注),宗旨是考察經濟發展和環保這兩者間的關係。它使我們注意到“世代間平等”這一問題,即現代人在做決定之時要考慮到這些決定對後人產生的影響。雖然這個說法在討論環境保護事務時已成為成說,但並未在我們的經濟體制對我們所做決策的後果進行評估的方式上有所反映。結果我們在有生之年繼續盡可能地消耗更多的自然資源,似乎這樣做沒有任何不妥。
目前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爭論建立在一個共識的基礎之上,即像世界銀行這樣較大的金融機構的許多投資通過鼓勵第三世界國家短期開發自然資源而刺激了它們的經濟發展,從而以犧牲長期、可持續增長為代價來換取短期資金流量。這種模式之所以盛行是因為我們貶低了自然資源的未來價值,還因為我們沒有正確地計算現在用掉的自然資源的價值。
我們衡量現行決策對自然界的影響之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做法也是妨礙我們對戰略性的環境問題做出正確抉擇的主要障礙。通常,我們只誇大地計算改變現行政策所需的預算開支,而從不分析如果什麼都不做會在處理環境問題上花多少錢。
例如,一些氣候學家很早就預言全球變暖將導致加利福尼亞空氣濕度每年降低75%,但因為這個問題很大,沒有人考慮將解決加州水資源短缺的費用納入遏制全球變暖計畫的收益計算中。我們還應該考慮若不採取任何措施將付出多少代價,因為加州7年的乾旱後果已是對我們的當頭棒喝,並且今後還會更糟。當我任參議院負責監督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時,另一個涉及費用的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正好說明了我的觀點。早在1991年國家航空航天局就宣佈加州的乾旱使深層地下水幹涸,其位置在太空飛船返回地球時用作著陸地點的幹湖床下的深處。如果乾湖床表面出人意外地出現的一個6尺深的裂隙將最終給這一著陸帶造成危險。另建一個新的著陸帶就要花許多錢。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措施來消除全球變暖所造成的後果,看來只有把建設新著陸帶的費用計入不採取任何措施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所導致的開支才合適。(當我向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建議把這筆開支計入分析報告時,他們對我說:“你別開玩笑。”我回答說:“不全是玩笑。”)
但是問題遠不止加州的乾旱。從許多方面來說,布希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方式存在的問題明顯反映了他們不能認識環境危機的嚴重性。至今為止,政府不清楚保護環境的真正價值,卻又像王爾德所說的冷硬心腸那樣,對開展環保工作所需的費用卻很清楚。1990年春,布希祝賀一個國際環境大會的召開。他的助手為與會者準備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一個圖示,說明政府如何平衡短期財政收入及長期環境惡化。圖示中,幾根金條放在天平的一個盤子上,天平另一個盤子上放的是地球及其全部自然系統,似乎後者的重要性和價值與6根金條相等。一位科學家,或者一位經濟學家,正在她的本上記錄著這個平衡刻度。雖然一些國家的代表私下裏說該圖示似乎在反諷布希對待危機的態度,而總統和他的助手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把整個地球放在天平一端的做法是多麼荒謬。
美國一些最好的公司正創造性地對危機做出反應,比政府做得好得多。那些為保護環境做出承諾的人驚奇地發現,當他們開始正視污染問題並尋求將污染降至最低限度的時候,他們開始找到了一些新方法來減少使用昂貴的原材料,並能在生產過程的幾乎所有程式上提高效率。一些公司還發現仔細審查每道生產程式能大大提高產品的品質。例如,三M公司污染預防支付計畫就使其利潤有了很大提高。施樂等其他一些公司也是這樣。
一些公司正力圖判斷公眾新的環境意識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例如造紙廠在為提高生產能力進行新一輪投資時,要考慮公眾當前對使用再生紙的熱情能保持多久才能決定大規模投資再生紙生產廠是否有利可圖。當然,這些預測一般來說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政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可惜的是,政府常常未能這樣做。布希政府大談自由市場自己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但是我們的許多市場是受到嚴格調控的,並且常以隱蔽的方式受到調控。就拿造紙廠來說吧,納稅人目前實際上是在補貼造紙廠利用原始森林中的木材製造紙張,因為他們不僅是最大的買主,而且我們用稅收來資助工廠把運輸木材的道路修到國家森林裏去。此外,聯邦政府負擔管理整個森林系統的費用,而其中有些只對木材工業有利。所有這些政策都鼓勵對這種重要的自然資源進行進一步破壞。
布希政府以及整個美國政界都應該意識到良好的環境作為一項基礎設施對於提高未來社會生產力的經濟作用。如果環境遭到破壞,許多現在就已岌岌可危的工作將不復存在。太平洋西岸木材加工的從業人員和熱衷於保護金錢貓頭鷹的環保主義者之間進行的激烈爭論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這場爭論被稱為就業與環境之間的衝突。但若真像木材加工業者所希望的那樣,把僅剩的10%的原始大樹砍伐掉,人們最終還是會失掉工作。問題在於是現在就開始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還是等所有的樹木被砍光之後再開始。
當今政府還應該在鼓勵人們採用合理技術方面更加努力,因為合理技術帶來的收益可以被用來抵消環境惡化給我們造成的代價。日本已經開始實施一項宏偉的計畫,為可再生能源新技術和有利環保的新工藝培養一個巨大的全球市場。可悲的是,美國自從研製出第一代利用風力和太陽能的技術之後,再無建樹,如今已成為此類新技術的純進口國。
現在我們進行經濟分析的方式含有不切實際的成分。我們無視當前的經濟決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瘋狂的投機,企業合併風潮,資產重組和其他在很大程度上與提供有競爭力的商品和服務無關的行為上。如此下去,其結果不僅僅削弱了美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更無法創造性地、有效地解決環境危機。
要想免遭這種危機最不利的影響,現在行動還為時不晚。並且,美國應該成為行動的主導者。我們的光榮歷史應該使我們充滿信心,並肩負強烈的責任感去迎接挑戰。我們必須糾正一些規章和程式的不足。這些規章和程式指導著每天被實施的幾百萬個決策,而這些決策構成了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我們必須改正對什麼是進步,什麼是退步的定義。
某些改革執行起來相對比較簡單,另外一些相對而言難一些。但所有的改革都要求我們具備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欺騙自己。我們要訓練自己及時察覺哪些時候愚蠢的行為代替了嚴謹的分析。例如在1989年,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得出結論說:“為了降低溫室效應、減少廢氣排放量而在經濟上付出重大代價是沒有道理的。”這個論述的部分理由是:“紐約和亞特蘭大兩地的平均溫差相當於所預測的全球變暖後最大的溫差,然而沒有跡象表明,亞特蘭大較為溫暖的天氣比紐約的天氣對健康造成更多危害。”但是如果紐約像亞特蘭大那麼熱,亞特蘭大將會變成什麼樣呢?南加利福尼亞州又將怎樣呢?中西部的乾旱又將如何呢?全球氣候型態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問題及其它許多類似的問題都想當然地被等同於政治上的“外在事物”而被忽視。
若干年後,如果遵照現任政府的政策,不認真採取措施而聽任全球變暖,對全球環境造成極大的危害,布希政府成員一定會後悔莫及。決策者這種只顧眼前利益而無視其對未來發展責任的做法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是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最有遠見的一位領導者那裏尋求某種靈感。
1936年11月12日,邱吉爾對於英國防範希特勒的進攻一直不能做好準備實在忍無可忍,他在下院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到:“政府根本就下不了決心,或者它不能讓首相下定決心,於是就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做出的決定有名無實,想下決心卻又優柔寡斷,立場看似堅定實則遊移不定,看似強大實則不堪一擊……這個時代因循守舊,半心半意,哄騙迷惑,權宜拖拉。這個時代該結束啦。取而代之,我們正進入一個行必有果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