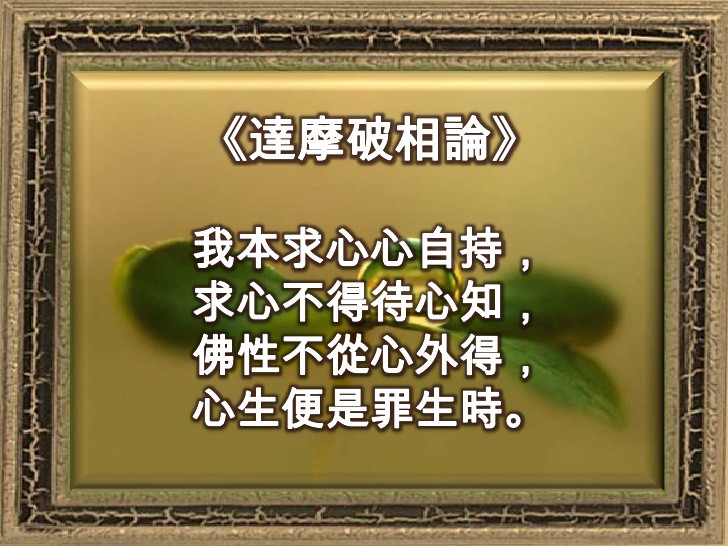禪詩、禪偈、禪心.....
禪詩,具有“禪”與“詩”的兩重性。禪詩以其禪味寓其理,以其詩味耐人吟詠,更是以其直指而令人醒悟,禪是難以言說而又可以言說的。表達禪的可以言說的最好語言,莫過於詩。因為通過詩的含蓄,詩的雋永,詩的韻味,詩的非邏輯思維,在細細的咀嚼回味中漸次進入佳境,並由此而窺視到禪的關照,禪的明淨,禪的超脫,禪的穿透。
禪詩,顧名思義,是指與念佛、參禪相關的詩,應是富含禪理禪意的詩詞作品。如佛祖的四言禪詩《誕生偈》:“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六祖惠能大師的五言禪詩《無相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都應是禪詩的傑出代表作。
禪詩大體可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禪理詩,內有一般的佛理詩,還有中國佛教禪宗特有的示法詩、開悟詩和傾古詩等等。這部分禪詩的特色是富於哲理和智慧,有深刻的辨證思維。
另一部分則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生活的詩,諸如山居詩、佛寺詩和游方詩等。表現空澄靜寂聖潔的禪境和心境是這部分禪詩的主要特色。這些詩多寫佛寺山居,多描寫幽深峭曲、潔淨無塵、超凡脫俗的山林風光勝景,多表現僧人或文人空諸所有、萬慮全消、淡泊寧靜的心境。
禪宗的理論核心是"見性"說,即眾生的自性本淨,圓滿具足;間自本性,直了成佛;只需"自身自性自度",不需向外馳求。這是自部派佛教"心性本淨"說和大乘佛教"悉有佛性"論及"如來藏"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佛家心性學說與中國傳統的人性論(主要是儒家的"性善論")相融合的產物。禪宗的這一理論思想必然與文學結下不解的淵源。
正如後人常說的"詩禪一致,等無差別"。詩情、詩思與禪趣、禪機本來就容易交融。特別是到我國唐代時期,受社會詩歌繁榮風氣的影響,禪僧們在開悟、示法以及一般商量問答時都常用詩偈。這就更進一步說明了禪與文學的緊密聯繫。從詩歌創作上看傳統上的"詩言志","詩緣情而綺靡"。但不論是言志還是緣情,都用的是心靈的語言,因而從一種意義上說,禪宗"見性"理論必然影響到詩壇。
唐代創作自出唐到盛唐逐步繁榮,形成了百花竟盛的局面,這與禪宗的發展暗相呼應,表明二者在思想背景上有共同之處。盛唐詩人中熱衷於禪的不在少數,如王維、杜甫、李白等。他們無論是在詩人習禪還是從詩禪結合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當然他們的表現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唐詩人楊巨源的詩中說:
扣寂由來在淵思,搜奇本自通禪智。
王維證時符水月,杜甫狂處遺天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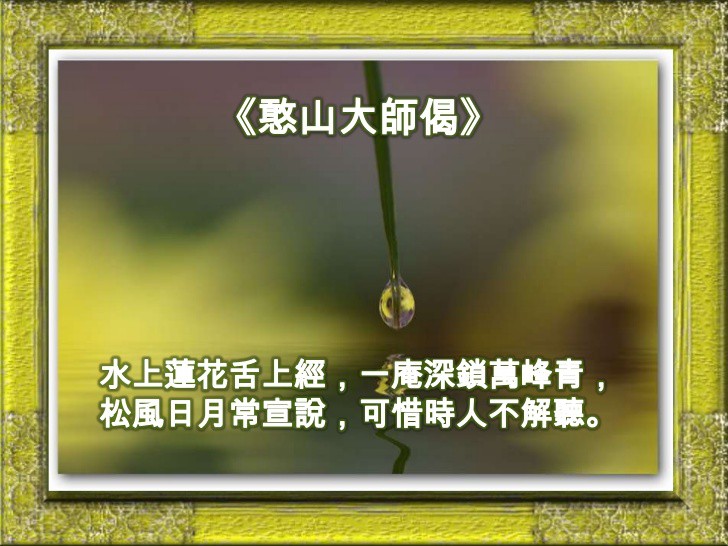
唐人早已看到了禪對於王維、杜甫創作的巨大影響。在中國詩史上,王維是以"詩佛"著稱在他生前,友人就評價他"當代詩匠,又精禪理"。"似禪"、"入禪"乃是後人評價他的詩歌的話頭。在盛唐繁榮的詩壇上,王維詩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藝術特色而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對當時及後代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王維熱心習禪,與他的個人遭際和個性都有關係。他生逢"開元之治",和當時的讀書人一樣,有志於一自己的政能才幹效力於當時。這種豪情壯志,在他早年寫的意氣風發的作品中時有展現。但他的仕途很不順利,特別是對他有提拔知遇之恩的著名宰相張九齡的罷相(開元二十四年736),給他很大的打擊。他"中歲頗好道"(《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王維四十多歲後熱衷於參禪習佛。他表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歎白髮》),到空門去尋求寄託。他的性格又比較軟弱,不那麼堅定的執著於原則,後半生選擇了亦官亦隱的道路。其實,他取號"摩詰",顯然是表示對維摩詰居士敬仰。
悟道偈 宋‧柴陵郁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柴陵郁禪師亦稱茶陵郁禪師,宋朝衛州(今衛輝)人 。生平不詳,約在西元十一世紀在世。他是白雲守端禪師的受業老師,白雲守端是西元1025-1072年在世。
一日乘驢渡橋,不小心墜落而大悟,得一首十分有名的《悟道詩》,明珠,象徵每一個人本具的光明佛性,代表我們都有解脫煩惱、活得自在的成長空間。
換一個方式說∶眾生皆有趨樂避苦的本能,這就預示了解脫煩惱纏縛、追求永恆快樂的可能性,只不過,眾生往往是以錯誤方式來獲取快樂,未能洞悉世間苦樂的無常性,以致更加貪執、放不下。
其實,真實的安樂永遠來自解脫貪嗔癡後的內心寂靜,清淨光明的佛性則是我們解脫自在的源頭活水。雖然這顆明珠暫時被各式煩惱塵勞所遮掩,卻絲毫不減它圓潤無瑕的本質,只待「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這是柴陵郁禪師摔跤悟道所作的偈子。禪師的禪風非常靈巧活潑,但是他座下的弟子白雲守端禪師,治學呆板,時常持誦上面這首詩,卻始終無法參透其中的禪趣。後來白雲禪師因為一個機緣,跟隨楊岐方會禪師學道,但是仍然不能開悟。有一天方會禪師問白雲禪師說:「據說你師父在摔跤的時候悟了道,並且作了一首詩偈,你記得嗎?」白雲禪師於是趕忙把上面那首詩念給他聽,方會禪師聽了之後就哈哈大笑起來,不發一語走開了。
這一笑把白雲禪師的困惑笑出來了,第二天就問方會禪師,是不是說錯了什麼?禪師回答說:「你見過廟前玩把戲的小丑嗎?他們做出種種唬人的動作,無非想博人一笑,觀眾笑得越大聲,他們就越開心。怎麼?我只不過輕輕笑你,就放不下了,豈不是比不上那些小丑嗎?」白雲禪師如夢初醒,遂放下長久以來的執著而開悟了。
這首偈子告訴我們,學佛要開放,要活潑,不要太呆板,太呆板就會失去宇宙奧妙的禪趣,禪是活活潑潑的,一揚眉一瞬目,一投足一言笑,都充滿禪的風光,以一顆靈巧的心才能與禪相應。這首詩更告訴我們不要被外境所轉,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把握住自己的立場,認清自己的價值,世間的毀譽得失都無法影響我們,笑駡由他笑駡,好比去除灰塵的明珠,光照萬里,我們在這動盪的時代裏,要能鎮定自己,鞏固自己,這才是自救救人之道。
禪偈是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一顆耀眼的明珠,璀璨迷人。
禪偈之於禪─
是一種工具─乃師父向弟子傳達心要。
是一種怡情─乃禪師借此表達自己的感受。
明禪意,方能修得禪心。
拈花一笑,便能依破塵埃,禪心如水,亦如是。人的一生,再是浪漫輝煌,終會有落櫻繽紛,殘紅散落。本來是燦爛過的,因此不怕被遺忘;本來是熱烈過的,因此甘於安守,一份不可言喻的靜默。就這樣,把一生的光陰,凝成時光長河中那一瓣恒久的心香,淡淡的,一體青凝不染塵。笑靨如是,真情如是,希望如是,生命亦如是。
遠離了喧囂繁雜,空谷晨鐘不是自耳畔響起,而是自心田深處某個被遺忘的角落。
青青一線,暗香浮動。一切如花,花如一切。
佛祖拈花而迦葉微笑,這一笑,便是整個世界。有時,參禪,只在一瞬間,一杯茶,一葉草,一尾魚,一粒沙,一株桃花,看一個繁雜的世界。世有千態,心有萬言,便可從中拾得一顆澄明無物的禪心。
一切有為法,盡是因緣和合,緣起時起,緣盡還無,不外如是。
緣起緣滅皆有因緣,就如花開花謝皆有定數,勘破自得清歡。花開花謝有定時,為何花開人喜,花落人悲?開到葳靡時,心中的寂落,又是為的那般?
蘇軾有言:“人間有味是清歡。”
塵世曖曖,何以得淡淡清歡?淡看緣來緣去,此中亦如是。《問佛》中言:“笑著面對,不去埋怨。悠然,隨心,隨性,隨緣。註定讓一生改變的,只在百年後,那一朵花開的時間。”
每一朵花開的時間不過刹那,破顏為笑是佛祖為其指明的處世之道─紅塵芸芸,頓悟人生。終於明白,有些路,只能一個人走!那些相約好,要一起同行的人,一起奔赴雨季,走過年華,但有一天,終究會在某個地方自散。
陌上流年,且吟且行,莫執紛擾,莫憂明朝。
山和水可以彼此相忘,星與月可以流光相皎。一個人也可以去看細水長流,待到蓮花開盡後,得一世清歡。
佛禪有三境界,勘破、放下、開悟。
不爭,不憂,不求,留得靜靜歡喜。人活一世,其實,有些東西,要學會思而勿亂;有些情感,要懂得痛而莫恨;有些追逐,要捨得持中有棄;有些浮相,要甘於塵而不染。
坐亦禪,行亦禪,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春來花自青,秋至葉飄零,無窮般若心自在。
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人生百年,都應盡情淺笑,留得款款清歡。許多紛紛擾擾,在茶靡之前,不妨飲一香茗,得幾縷清雅,讓世間的微塵與污垢都埋葬在日落的餘暉裡。
看碌碌塵世,有那麼多撼天動地的事,到最後也不過天地蒼茫中的幾粒微塵,經歷過的所有劫難和困頓,當年老時,再回首,不過那麼簡單。
生死,愛欲,不過是零星的瑣事。不如,不念,不如,不求。不去在意因緣,放下一切執念,心淨無塵不染,禪心如雪晶瑩。此中,自有大道,通向三千。
禪心之中何處有恨?
太遙的,不是煙霞,不是明月,是人心。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一鳥一天堂,生命若弦,雙手彈指之間,處處是禪意。
禪月不語,於是得亂世清幽。
禪心悠然,於是得一世清閒。
參禪默默,如花開輕輕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