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話頭的禪源及工夫處】
【參話頭的禪源及工夫處】
話頭裏起疑情
照顧話頭─返聞自性
在“誰”字上─起大疑情!起大參究!
*幻羽*題
過去坐禪其實是沒有什麼話頭,沒有什麼疑情的。但是隨著眾生心中的貪嗔癡煩惱越來越重,我們沒辦法自己靜下心來禪修了,因此祖師在沒辦法中找了個辦法,這個辦法是假的,辦法是虛妄的,但是沒有辦法給你好像找不到路,所以你要知道,用話頭提起疑情來作為修行的鑰匙、修行的拐杖、修行的橋樑、修行的方法和措施。你有修行的目的,但是沒有方法的話,就達不到最後的成果。
現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充斥著貪心、嗔心、癡心種種不良的心理狀態,有的甚至情緒暴動,沒有一天甚至一時一刻的安祥,這是我們現代人的情況。過去也有這樣的特點,只要是人就有貪嗔癡的根本煩惱,只不過是程度的厚薄有所不同。所以祖師大德教導我們參究話頭,用疑情來打開我們開悟的門。
那麼什麼是話頭呢?虛雲老和尚說:『前一念已經落下,後一念將生起來的時候,這中間就叫話頭。』行者們明白嗎?就是前念已去,後念未生之際,就是話頭,那裏面有空性,但是我們卻還未看到這個。為什麼?因念頭非常兇猛,這“念”跑得非常快,所以你沒有覺察到這個話頭,心一下子都不能停下來。只有當“心”在寂靜時,才觸覺到了這個話頭中的“空性”處,這個話頭的“真如”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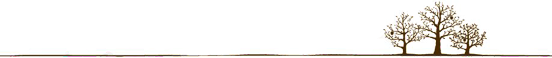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大慧宗杲提倡所謂的話頭禪(又稱看話禪),要人參趙州禪師的無字話頭。他鼓勵學者起疑情,以疑情參究公案,而得到開悟。宗杲認為,修行必須在生活之中,反對遠離塵世,獨自修行。因此,他大力排斥當時流行的默照邪禪,認為它會造成學者終日只知靜坐,是在「斷佛慧命」、「墮在黑山下鬼窟裡」,有默無照,是邪禪。禪宗楊岐派在他手上推至最高峰,他的禪法,對後世禪宗形成深遠的影響。南宋理學也深受他的影響。
大慧宗杲是中國禪宗史上第一個大力提倡參話頭的人。大慧觀察北宋末、南宋初之禪風,批評道:「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
另有一種「默照邪禪」,只教人靜坐稱之為默照而不求妙悟,這類禪師是「教中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大慧對多學言句和靜坐默照都不表贊同,處處批駁。
大慧認為參話頭才是最佳參禪途徑,所謂「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大慧教人參趙州狗子無佛性之無字話頭,「只這一(無)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個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為避免落入默照的窠臼,和禪宗大量的語言文字海中,參無字話頭給人一個新的方向,和有效的入道途徑。
若不能參無字話頭,則用力多而易入歧途,大慧自信其參話頭 「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得力處。」 後世如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是誰?」係由大慧之禪法中發展而成,其方法對中國宋朝以後禪宗之發展有鉅大之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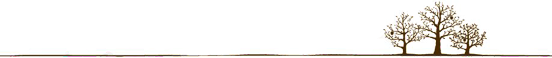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從六祖慧能立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以來,經南嶽、青原兩大師,至馬祖、石頭諸大師之努力弘化,禪宗就像一位天才畫家筆下的新世界,隨意一抹,都有不可言宣的新意;簡單兩筆,都是淋漓盡致的創意。活力充沛的禪師們,薪盡火傳地留下令人景仰的典範。
然而隨著大唐的沒落,禪宗亦面臨生機不再的命運。從清涼文益(八八五—九五八,唐末至後周年間)的「宗門十規論」中,可以看出當時禪門之弊病有十項之多不分溈仰、 雲門、曹洞、臨濟,這些弊病蔓延在各宗派間,清涼文益於痛陳十病後,發出「像季之時,魔強法弱,假如來之法服,盜國王之恩威;口談解脫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既無愧恥,寧避罪僭。今乃歷敘此徒,須警來者」的嚴重警告。
總之,禪的弊病是因欠缺創造力,因循苟且累積而成。早期禪師們在山野水邊,奮其赤手搏虎的勇氣,對無始來的無明習氣,展開生死立判的戰鬥。擺在禪師眼前的只有解脫或輪迴。若無生死以之的態度,只有入驢胎馬腹的命運。然而這些精神,似乎在光陰之流中被沖淡了,參禪學道不再是一種生命的挑戰,無怪乎有大見識的文益要發出如此沈重的呼籲。
再者,法無強弱,因人不同,五家之分,亦不過祖師們之個人氣力和創造性而異。若拾人牙慧,專務師說,則只有徒增門戶之貢高我慢,文益稱此病為「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禪若非有所得,而從自己胸襟中一一流出,則捏拳豎拂,談心說性,都不干自己生死大事。
有僧問五祖法演禪師(不詳—一一○四) 「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學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鑠。學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學云: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僧禮,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學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犯夜。乃云:會即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
其弟子圓悟克勤禪師亦謂:「自曹溪散席以來,數百年間列剎相望,各各握靈蛇珠,人人抱荊山璧,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提振向上宗風,傳持正法眼藏,要且百川異流,同歸大海,千種百匝無出一源。」在第一流之法演、圓悟禪師眼中,五家之分,不過教人手段,若達真際,豈有二途?
指月錄載大慧禪師 「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麼有許多門庭?」又 「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聖首座,師週旋於三公會下甚多,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師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遍歷諸方。」由此可看出五家說法在北宋時,已極普遍,若非穎悟之士,自挺於時倫之外,只有依樣畫葫蘆,迷糊於五家宗旨而忘卻自家重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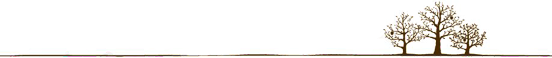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禪從慧能「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以下,就給人一新耳目之感,牛行虎視的馬祖道一奮其獅虎般的威力,泉湧般的智慧,將慧能播下之禪法的種子,栽培灌溉而得在中土開花結果。其後諸祖師之學禪開悟弘揚,都在一種最深刻的教育中鍛鍊出來,禪的生命在大禪師的生命過程中,可以得到最佳的說明。
甚至除了直接面對禪師的生命過程,我們很難再用其他方法,恰當地了解什麼是禪。然而,這些活生生的證悟過程,在語言文字的大量流傳中,逐漸失去了個別、具體的生命衝力。有人借用他人開悟的文字,作為自己的開悟;有人將他人的開悟,當作一種幻境來欣賞,而不知自己該如何開悟。
大慧曾剴切地指出:「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禪若不作為一種生命的挑戰,則言句均將失去光采,成為自欺欺人的把戲。
不幸的是,在大慧的時代裏,學禪者正步入這種險境。碧巖錄一書三教老人序中(元大德八年,一○三四)謂大慧曾焚棄其師圓悟克勤所述之碧巖集,惟碧巖錄仍續流傳,此亦為時勢所趨。大慧本人於屏居衡陽時,亦取古德機語加以拈提,編為「正法眼藏」三卷。惟是書,大慧自謂:「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則有其特殊立場。
與大慧同時之天童正覺亦有「頌古」之作。總之,一方面由於參禪成風,大僧團中,禪眾事實上無法與大禪師起居相共,一般在家居士,更無此可能。另一方面,由於祖師語錄之增加,類似判教之工作,事實上也需要加以整理說明,以維繫宗風。因此,文字之普遍應用,竟成為「不立文字」之禪門裏一特殊現象。
更有甚者,從不識字之六祖開始,早期禪師們均在山邊林下或獨自修行,或聚眾勞動自養,只要機緣巧合,露柱、爐火、鋤地均可作為悟道之接引手段。縱使使用語言文字,也是一般生活用語,樸質無華。然至唐末,在禪師的「頌古」中,可以見到如文學般用字典雅的詩偈了。
大禪師住在敕住的名山首剎中,和朝庭中的名公鉅卿往還,給一向山野叢林中的禪,變成帶有富貴氣息的禪,這種轉變確是一值得注意的蛻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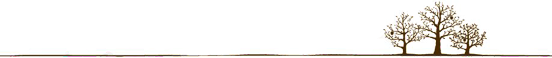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按狗子無佛性之話頭,五祖法演禪師即曾特別提出,觀法演禪師語錄卷下載:「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師云:大眾爾諸人,尋常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爾若透得這一個字,天下人不奈爾何。爾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出來道看。我也不要爾道有,也不要爾道無,也不要爾道不有不無,爾作麼生道?珍重!」
這是一個奇怪的話頭,不能答有,不能答無,也不能答不有不無,其意何在?如何參這話頭,據大慧的看法:「看時不用搏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卻是個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
此一大段,似有解說,又似未解說。總之,大慧對此話頭極具興趣,除此話頭本身具有直參本源心地之重大意義外,大慧更在當時混亂的禪門裏,開拓了一新的途徑。所謂:「從上諸聖,無言語傳授,只說以心傳心而已,今時多是師承學解,背卻此心,以語言傳授,謂之宗旨。為人師者,眼既不正,而學者又無決定志,急欲會禪,圖口不空,有可說耳。欲得心地開通,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
參禪學道,原為解脫。尤其是禪門心法,不在言語,然而一般參禪者,尤其是知識分子,探究祖師語錄,在當時為一普遍現象。如大慧本人「十七落髮,即喜宗門中事,編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文偃)、睦州(陳道明尊宿)語 。」著名之「景德傳燈錄」,約早於大慧百年也流行於世,如五祖法演弟子清遠佛眼 「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許曰:「深深撥, 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灶墮因緣,忽然大悟。」
祖師語錄似已成為參禪者的教科書,尤其士大夫學禪又 「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者來,與一頓飯喫卻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卻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爾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
只在語言上逞小慧,不肯老實修行。大慧警告此等學人「莫愛諸方奇言妙句,宗師各自主張,密室傳授底,古人公案之類,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中,劫劫生生取不出,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日用亦被此障礙,道眼不得明徹。」士大夫平時博覽群書,好作意解,對佛法亦作相同看待,對祖師語錄則要在字句上、意思上去分析解說。
對此現象,大慧歎道:「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卻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個無字,分曉不分嘵,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個道理也。」大慧洞曉其中因由,斷然采取參狗子無佛性之話頭以為對治。
參禪學道就為解脫,非為章句記誦,固為一般人所明知。然而在學習過程中,面對各種經論,若不能時時提醒自己是為解脫而來,則反有落入文字障,而忘卻最終目標之虞。如溈山靈祐禪師對香嚴智閑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典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使香嚴因之盡焚所集諸方語句而後入道。
至宋禪機流行,五祖法演對弟子南堂元靜亦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擊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技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禪宗血脈所在。
第一等的禪師「有時拈一莖草作六丈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卻作一莖草」,任運自在,具有無窮的創造力。若不能直下參透自己的本源心性,徹底掃盡無始來的無明習氣,單只記得經上文字,識得禪門技倆,都是身外邊事。
如何重新提振學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恢復日漸消失的禪門活力,正是大慧所關心的,參趙州狗子無佛性這個話頭,就是大慧提出的答案。這是大慧在禪宗教學史上的一大見識。五祖法演的特識在其徒孫輩的大慧身上,得到最大的發揮。
凡人呱呱落地,帶著無始時來的習氣,隨著知識經驗的熏染,貪瞋癡三毒惡業,就如影隨形。只要這個雜染的心識在,任何角度的燈光,投射在這個心識上,都會產生黑暗的影子。要使燈光晶瑩,只有破除這個雜染心。
大慧之參話頭,就是要一舉擊碎它。將我們的整個生命力量凝聚在這一疑情上──狗子無佛性,這是一個不能答有不能答無,用語言可以解答的問題,只有將所有的精神力量,時時刻刻緊抓不放,排遣所有想象思辨,以意志代替思考,「只這一(無)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個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所有的疑問,根源只有一個,若能掌握住則「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恰如庖丁解牛,游刃有餘了。
將全副意志集中在一無字上,這是一個多麼便捷的方法,然而一般人卻「為利根聰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捷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外馳求。」因此大慧時時以「立決定志」提醒學人,凝聚精神,勿再於文字上計較思量,須立時展開解脫輪迴之對決。
太虛大師曾說:「從參話頭言,禪宗徹頭徹尾就是一個大話頭。」然而大慧卻是第一個大力提倡參話頭為參禪方法的人,此後如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是誰?」均是同一作用。大慧面對「過頭禪」、「口鼓子禪」 、「廝禪」、「默照邪禪」之歪風,以參“無”字一句話頭,掃除葛籐,直透本心!歇即菩提!

參話頭是禪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門,自北宋末年的大慧宗皋禪師大力提倡以來,幾乎成為禪宗的代名詞。千年來,在話頭下參悟的祖師不計其數;而由於祖師的親身履踐,也使參話頭這一法,淬礪得更加善巧與精緻。
參話頭廣受中國佛子歡迎的原因,在於它的入手處極為簡易,但卻開悟速捷,只要靠住一個話頭,起疑情、參到底,就可以了脫生死。可惜的是,宗師隱沒之後,參話頭的運心方法沒有完全傳承下來,致使佛弟子或眩惑於祖師的機鋒、公案、家風,而成為口頭禪;或鄙於宗門知見渾沌的流弊,而棄如蔽屣。但其實在祖師語錄中,保留了非常多實際用功的資料可供我們重新去認識它,只是一般人不太了解。
參話頭的運心方法
「參話頭」這一方法,不了解的人,總以為很玄奧,其實說破了,卻極為平常。它的巧妙,就在「話頭──疑情──參」一句話上。
所謂「話頭」,是在自己心頭上提一句問話,如「念佛的是誰?」、「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一個疑問句!所以當我們提話頭時,絕對不要動第二念去想,而是當下、直接去體會它本身所帶起的那份疑問的感覺。那種沒有辦法解答、不知道答案的「疑問」,就是「疑情」。疑問的感覺保持住以後,我們會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這時在疑情之上,要提攝一種要去看透、追究的覺知照了的力量(近似於永嘉禪法「看」的感覺、「惺惺」的作用),是一種沒有妄念下的覺知力。這股覺照力,因為疑情的推動,一直衝向心源深處去追究答案,這就是「參」。所以參話頭的巧妙,完全表現在疑情使覺照力向心源推動的作用上。
而如何從話頭起疑情而參究,以下舉兩個實際的話頭為例來說明:
一、拖死屍的是誰?
活著的人可以跑、跳、說話,但是一旦死了,就是一具屍體,一動也不動。想想看,活著時候的這個色身,跟死了以後的死屍,不是同一具色身嗎?我現在這個身體,也是一具死屍,只不過它會走、會動。那麼,問題是──現在是誰在讓這個身體動呢?是誰在拖著這個死屍呢?「拖死屍的是….誰~~?」
當「誰」字被提出來的時候,心就定在「誰?」字上不動,保持住「誰?」,當下會有一種疑問的感覺。在疑情當下,絕對不要動念去思維答案;妄想來了,就再把「誰?」的感覺提起,昏沉來了,也只是專注在「誰?」的疑問上。然後在「誰?」的疑問上,心不動的惺惺地著意去看照、追究,這就是「參」。其它像「念佛是誰?」、「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都有類似的作用,都是在追究「誰?」。
剛開始用功時妄想多,疑問的感覺很容易就跟著妄想打掉了;慢慢的,話頭提穩了、綿密了,妄想不容易打進來,疑問的感覺也就能持續,參的力量就會慢慢增長。
參話頭就只是這麼參,這麼簡單!沒有深奧的理論、沒有曲折的過程,參到疑情打破,就開悟了脫生死。高明的禪法就是如此,簡單而有力量,愈簡單就愈好用,最好是每個人都可以用,這就是它可貴的地方。
二、趙州為什麼說狗子無佛性?
禪門中有名的趙州和尚,當人問他:「狗子有沒有佛性?」他說:「無。」我們都知道,佛說:「眾生皆有佛性」,狗也是眾生,當然也有佛性!螞蟻、蚯蚓都有佛性,連鬼神也有佛性,狗當然也有佛性!可是為什麼趙州說狗沒有佛性呢?這不是違背佛陀的教法了嗎?
所以當我們問:趙州為什麼說「無?」的時候,念頭就停在這「無~~?」上產生疑問──「為什麼無?」可是心不准動念,連個「為什麼」都不要,只是「無?」;甚至連「無」字也不要,就只有疑。能夠一直疑下去,那就是「參」。
功夫上路以後,只要「無?」的念頭一提起來,一切念頭就被掃蕩盡淨,只有「無?」的疑情停在那裡,再進一步,就只有疑,一提就是疑惑的感覺,整個身心就在疑情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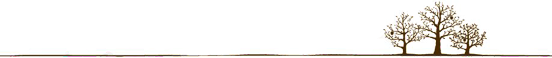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參話頭三要
一、大信心:
首先,要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佛性,信自己決定可以成佛;其次,要相信參話頭這個方法,決定可以引導我們開悟,不管他人說其它法門有多好,絕對不絲毫移易。
二、大憤志:
相信之後,就要很努力,放下一切的參下去。也就是要有一決生死的承擔力。常將「生死大事」放在胸中提撕,疑情參不破,如無常殺鬼守在門口,故要有「蚊子鑽鐵牛」、「擔雪填井」般的死志,愈參不破,愈要參去!
三、大疑情:
(一)疑以信為體、悟以疑為用──參話頭的善巧,就在於「疑情」上,古人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正說明了疑情對於開悟的推進作用。但疑情的發起,必須建立在對法門的信心上,相信就這麼起疑參究去,決定可以了脫生死。所以高峰禪師說:「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
(二)惺惺著意疑──所謂惺惺著意疑,其實就是參的狀態。「惺惺」是指警醒、覺明的照了。對於話頭上的疑情,要一直去覺了、推溯,但卻不是牽動心意識的「想」,而是一種「離心意識參」的惺惺照了。
(三)只就一個話頭上起疑──祖師說,古人也疑,只是不假話頭,只疑自己的生死。後人不懂得疑,妄想也多,才給話頭當柺杖、敲門磚。所以儘管話頭很多,契機也有不同,但疑情只是一個,因此,要大家只在一個話頭上起疑;一個話頭上疑破,千疑萬疑都破。否則東疑西疑,終不得成就。
參話頭可能面臨的身心變化
一、頭脹、胸悶:參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強勁的覺觀力,初參的人,對方法不熟悉,加上妄想多,要想掌握這股覺觀力,不自覺的就會費很大心力,心太躁進,影響氣脈不調,容易有頭脹、胸悶的現象。這時只要將功夫稍微舒緩一下,慢慢熟練之後,就可以改善。
二、睡眠減省:由於覺照力強,只要參究的力量在,可以一直保持醒覺,可能晚上會睡不著,或似睡非睡。只要色身承受得了,可以一直用功,不必強迫入睡,等身體累了,想睡再睡。
三、分別心減弱:參話頭的覺照力,是針對疑情的。也就是說,它只專注在疑情上,而不旁騖其它。所以當疑情大到籠罩整個身心,對外界的反應,就顯得遲滯,亦不想去攀緣、計較,分別心自然減弱,這是用功得力的正常反應,應自我策勉,更綿密的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