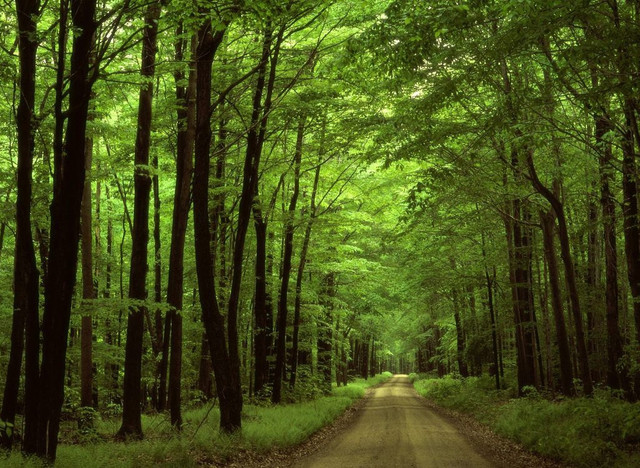工夫理論與境界哲學─禪宗功夫哲學的方法檢討(上) *杜保瑞*教授
工夫理論與境界哲學─禪宗功夫哲學的方法檢討(上) *杜保瑞*教授
本文對禪宗哲學的討論,是在一個中國哲學整體研究的方法檢討的進路中來進行的,是對於中國哲學的功夫理論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方法的使用嘗試,期望由功夫理論的問題意識的揭露與追問,嘗試提出解讀禪宗哲學的新的工作眼光。
一、禪宗功夫哲學的三種研究層面
二、禪宗是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
三、同時在宇宙論與本體論觀念中來理解的功夫理論
四檢別儒佛得由世界觀之別異為路徑
五、禪門公案中接引活動的境界調升法是壇經風格的真實把捉
六、制式性方法建構的知解趣味是悖離門功夫修持的
七、大珠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的功夫哲學
一、禪宗功夫哲學的三種研究層面
禪宗宗門的理論與實踐,從達摩以降的楞伽師到南能北秀以至南宗禪五家七宗的多方分化,其實顯現了理論與實踐活動的多種風貌,雖然我們總提地以功夫哲學說之,但仍得作出內在的區分,才能顯其義理的精確。
首先,我們要先定位中國禪宗在佛教史上及中國哲學史上的理論特徵的方法,就是指出「禪宗是以強調做功夫及其功夫方法的特色而為其特徵的,禪宗的強調做功夫,反映出了佛學理論整個的是一個解決人生問題的功夫理論的實際,這是同於中國哲學儒道兩家作為哲學理論型態的共同特徵的一面。但是禪宗宗師們所作的功夫就大大地與儒道兩家路數不同了的,這個路數的不同就要藉由其功夫理論的研究進路中來檢索了。
禪門宗師們為了強調做功夫所發展的功夫理論,基本上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就為這種型態的功夫實踐的理論基礎作觀念的建構,而他們所提出的就是一套以心性功夫為宗本的功夫理論,我們則將以「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稱說之。但是由於禪宗宗師自達摩以降就是以強調實作功夫為主的宗派,所以他們的心性本體功夫的觀念建構在整個大乘佛學的哲理開發上,談不上有什麼創建,基本上可以說只是將大乘佛教的本體論哲學的基本命題轉換為是功夫理論的基本哲學問題中的命題主張而已,其中有精彩之處,是對這種心性功夫的信念所顯現的功夫氣魄,如黃檗希運禪師說:「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至於他們的功夫理論的真有創獲之處,應是在於這種功夫心法的實際操持中的真實意境之展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二種層次的文字記錄所顯現的理論型態特徵之重點。那就是禪門師弟子間彼此印心接引的公案內容,但是公案永遠必須是當機的,因為它本來就是接引印心的活動,只不過被記錄了下來,是故一落入研究的話就是離了題的。當然如果要對公案進行研究。也就產生了第三種禪門功夫哲學的研究進路,亦即制式性接引機制的探討,此即臨濟宗的「四料簡」、「四賓主」、「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說」、等,這是一種純粹思辨性的形式哲學,它當然也還是禪門功夫哲學,只不過就禪宗宗派立場而言,我們認為它是最遠離達摩、慧能精神的一種進路。以下我們先從第一個層次的禪宗功夫哲學開始討論。
二、禪宗是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
禪宗師門的這種大乘佛學型態的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此處我們認為有兩個重點是要說明的,第一,為什麼是心性論中心的。第二,如何地與儒道功夫做區別。我們曾經指出,功夫理論的義理根據在於表述在形上學世界觀中的觀點,它可以有兩種主要的論述型態,其一為宇宙論進路的、其二為本體論進路的。
我們就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角度來看,禪宗哲學作為中國哲學的特質即在於它的主要形式是一種功夫哲學的中心,當然任何的功夫哲學都不能是空頭的功夫哲學,它其實是併合於形上學的一組整體表現形態之一個角度,是由存有者功夫活動的進程去彰顯哲學體系的基蘊的進路,而禪宗功夫哲學的立足點則是形上學問題中的本體論哲學,亦即是一種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哲學。向來討論禪宗功夫理論的重點是以「心性說」來稱述,例如大陸社科院哲學所蒙培元教授即說:「中國佛教的真正代表是禪宗,中國佛教心性論最後完成於禪宗。它在中國心性史上的影響,遠非其他各宗所及。」。以下我們就要討論如何以「心性說」的理解來建立禪宗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哲學。
首先,「心與性」這兩個哲學概念範疇本來就是人存有者的本體概念,所以也有賴永海教授以「本體功夫」稱說之道:
「隨著大乘佛教把真如、實相、如來藏、佛性我本體化,本體論的思維方法逐漸成為大乘佛教一種最基本的思維方法。……中國佛教就思維方法說,主要是大乘佛教的思維 方法,亦即本體論的思維方法。」
「如果說,中國禪宗的思想大要可以用「即心即佛、頓悟見性八個字加以概括的話,那麼,不論是「即心即佛,還是「頓悟見性,都是以「本體論的思維模式為其最後的根據。」
賴教授提出「本體論的思維方法」,我們認為這對中國哲學基本問題意識或基本概念範疇的釐清是極有貢獻的,而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大乘佛教整個的是一個「修行理論」,所以說它是「本體論的思維方法」時,更可以說它是個「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這就是把以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為重心的研究方法融貫地運用了起來。
由於「本體論思維方式」的認識範疇之提出,使得賴教授得以特出地獲得討論陽明功夫學與禪宗功夫學的新眼光。其言:
「王陽明的修養方法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深受禪宗修行方法的影響,此中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兩種修行方法都是建立在本體論的基礎之上。而 「本體功夫:正如王陽明所說的:「一悟盡透。這句話可視為是對於兩修行方法的點睛之筆。」
王陽明所受的禪宗影響是明確的,但陽明不即為禪,這是因為陽明仍是儒家的世界觀,即使兩者都是本體功夫,但這只是功夫形式的相同,至於功夫的內容,也就是本體的義涵,卻是差異的,這是儒禪之別,我們後文將再提到。
「本體功夫」以我們的語言就稱之為「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這樣的工作方式,就是我們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方法所提出的一個「哲學基本範疇」的轉向,我們是以一個「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認識進路」來取代「以哲學概念範疇為主的認識進路」,在這個理解進路的轉向之後,則更易於我們解讀禪宗功夫哲學的型態特殊性。那就是必須要將「基本哲學問題意識中的宇宙論哲學與本體論哲學」的觀念建構,匯入功夫理論的研究進路中,來並同地認識這禪宗哲學的研究進程。
所謂的「心性說」即是對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哲學概念範疇為主的認識進路」,這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意義乃是在於提出一個傳統哲學理論建構的問題意識的概念範疇。學術界發現,當秦漢時代的理論思維集中在「天、地、宇宙」的哲學問題意識中,而魏晉隋唐的理論家們則集中在「本體」的哲學問題意識中來討論時,原來先秦也罷、貫串兩漢隋唐也罷、更且是在宋元明代之中,中國哲學原來都是一個最終歸向關於心與性的問題意識的探討跟發言的哲學活動,心性說才是中國哲學真精神的結穴地,這就是「心性說」的思維要點。而我們認為「心性說」的提出在哲學研究方法的眼光中來看,就是一種「概念範疇的研究進路」,而我們所說的「哲學基本範疇的轉向」,即是在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上企圖將「概念範疇」的理解方式轉向成為「基本哲學問題」的理解方式。我們認為,心與性是人存有者的活動主體──心,及本質屬性──性,不論是從人存有者的本質屬性的角度言談他的活動蘄向──以性說心,或是從他的活動方式去意識他的性格定位──以心說性,這兩路的理論進程都是關於功夫活動的理論建構,它們都是人存有者的活動,都是人的修養活動,我們把它放在一個基本哲學問題意識中來詮解時,就是「功夫理論」,而且是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因為它是合性說心,性是本體,所以是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如果是合氣說心的話,那就是宇宙論進路的功夫理論。
基於上述所說,我們即將指出,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工作方式中,中國禪宗心性說的義理建構,是以「概念範疇」研究法下的認識進路,而我們要提出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的認識進路即將禪宗心性說置入「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哲學」的架構中來認識,而這樣的詮釋方式,將有助於我們將禪宗哲學置於一個更廣大的中國哲學的視野中來研究予認識,這當然是一個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思考,我們認為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進程而言,將是更有發展潛力的作法。
三、同時在宇宙論與本體論觀念中來理解的功夫理論
中國哲學的功夫活動的理論建構不一定都只是「心性說」為中心的,也就是說功夫理論不一定都只是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我們認為談功夫理論是中國哲學的上下縱貫的問題主軸,但談心性論,也就是談本體論進路的功夫理論卻不一定是主軸。當然,我們絕對認為禪宗哲學確實是談心性論的,不過是它在談本體功夫時早已預設了整個佛教哲學的世界觀,所以一個五蘊積聚的存有者在功夫發用過程中的宇宙論進路意義的功夫理論之存在,更是一個理論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說,因為佛教哲學尚有宇宙論進路的功夫活動在,所以禪宗的本體功夫其實已預設著宇宙論進路的功夫意義在。只要功夫操作者用對了本體功夫,那個宇宙論進路的功夫效用自然是存在的。
說它是心性論中心是說這個功夫主要是做在心上的,說它是本體論進路的是說它是以持守般若智慧為修持內容的功夫法門,這就是為什麼禪宗的功夫會是心性論中心的。一個心性論中心的功夫理論,它還是可以顯現為極多差異各別的理論型態的,這就要從它的心性本體的內涵中去追究了,也就是它的本體論哲學體系中去追究的,但是,哲學理論中並沒有獨立的本體論,因為本體論與宇宙論兩者都是形上學世界觀中的最基本型態的哲學問題,都是任何一套哲學理論要追究的問題,所以一個本體論命題的建立必然是預設在一定的宇宙論觀點之內的義理建構。所以一套以心性本體為進路的功夫理論是一定要交代其身體宇宙在功夫操作中的理論意義的,所以那個為慧能所強調為不是根本路數的禪定活動,便又因為它是任何禪師修行功夫中的真實活動,而成為禪宗功夫哲學中必然要追究的問題了。這時候,心性功夫的實義就要同時在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基本命題中來了解的,也就是要以整個哲學理論的形上學世界觀來了解的,而就在這個認識的進路中,一個心性主體所開顯的自我境界狀態就充滿了分別其功夫路數的要緊地了。
四、檢別儒佛得由世界觀之別異為路徑
就禪宗哲學而言,這個世界觀的預設從達摩「二入四行說」中的「隨緣行、報冤行」等觀念中即得見出,其說顯現了佛教因果輪迴世界觀中人存有者的生命活動如何緊受著業力的牽引拘束,因而欲追求理想的人生便必須將生命的業力因緣予以了結,隨緣即報冤即此了結的法門,這個功夫的法門首先是一種心理的態度,其次進入內在心性的功夫修為,實對著生活週遭的林林總總,展現在人際情境的真實對待中,最終產生種種世界互動的現實效果,終於整體地改變而提昇了人存有者的生命境界,這已經是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共同效果了。我們由此亦得見出,禪宗絕對是一個完整意義的佛教世界觀下的功夫哲學系統,也就是預設了生死輪迴的生命宇宙觀的哲學系統,因此它的功夫思想就是一個面對緣起的世界及輪迴的生命的解脫的修行活動。參見其言:
「云何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那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
而儒者則是面對一個道德理性的世界及實踐君子人格的修養論功夫系統,這個道德理性的世界是不論此世彼世、天上地下、生前死後,世界就是一個有道德理性的意義世界,人存有者是這個理性的天命產物,因此顯現了強烈的目的性世界觀,人的一生修養活動之意義在於彰顯這個道德理性的生命於全福的家國天下之中,二合一地整體置入以達天人合一之效,於是人與天地參,天地人三才皆為其所點化而成為道德的理性世界,此中有功夫,確是心性論中心,而不論生死,因此缺乏各種關於它在世界及身體形氣的宇宙論的討論。
而佛教的世界觀則有六道四聖、有生死輪迴、有重重無盡的緣起世界,而其宇宙本體的觀點卻因見其緣起而領悟性空,性空則無目的,故非道德,它的修持活動的現世性,不過是大乘佛教六度法門中的表現方法,現世界也不過是修行活動中的一個切近的世界,並非對此一世界有一個目的性的確定。佛教修行理論由小乘轉成大乘的過程,可謂其看清了原來只求自度的修行結果,發覺只求自度則將所度未盡淨,原來要所有的眾生都得度之後,才有真正的絕對的盡淨,所以大乘佛教的菩薩的概念都是要「覺有情」的理想性存有者,都是要幫助他人共同修行的存有者,只有在所有的存有者都進入了清淨的境界之後,才有一個自我的絕對清淨境界。這就顯示了佛教的功夫思維是主客一境的義涵,沒有任何一個清淨的存有者不同時具備清淨的國土世間的,所以會有因無限的禪定功深而無窮地開發的世界層級,此其得有繁複的世界觀天地說之緣由。而其每一個修行活動下所成就的世界都交給了共同的修行成就的存有者存在及活動,所以佛教哲學中是有可能發展出追求淨土的思想,雖然禪宗哲學強調隨其心淨即國土淨的思想,但這種說法是從功夫下手的角度說的,是從當下境界的角度言說的,並非禪門功夫即能否定淨土世界之存在者,佛教哲學中有清淨國土的觀念者是必須視為其宇宙論知識系統中的真實對象,而不是畫餅充飢的虛妄對象,否則淨土宗人終生甚而歷劫的修行活動便毫無意義可言。大和尚們自稱是大丈夫,且非帝王將相所可差比者即在此一世界觀的差別上,否則儒者承擔天下修齊治平的事業,為何有自稱是大丈夫的人可以枉視。
我們從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的角度來看,欲準確理解禪宗本體功夫的特質,就應先理解佛教修行哲學的基調,而這個基調,則是人生哲學本位的中國哲學的共同基調,所以我們的中國哲學的研究工作是不能不正視宇宙論世界觀的課題,儒佛之間不可能因為都談「心性論」即同一,心與性只是哲學範疇,是概念,甚至只是字,儒佛兩門各自的廣大心靈、複雜理論、深刻功夫,怎能因為共用了心和性這兩個中國字就一樣了呢?他們剛好就是要從這個心和性這兩個中國字上下手而說出極為不一樣的天地的。「本體」亦然,「本體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哲學主題、哲學題目、基本哲學問題,儒釋道對於本體這個題目都是要發表觀點的,大家的本體的答案是不同的,主張是不一樣的,本體是任何哲學體系中探討整體存在界的根本意義性的問題的那個絕對的對象,是那個真相那個實相,也即是體系中的最高概念範疇、絕對範疇,這個最高絕對範疇則還是功夫的蘄向與終竟,所以佛家有實相禪的修行法門,不過就是般若的功夫,因為佛教的世界實相就是般若的義涵,它不是儒家的本體觀念,諸如「誠者天之道」的誠本體,或是「天尊地卑乾坤定已的乾坤陰陽甚至太極」的作用本體,這是儒門的本體的內容,這是儒門的性、儒門的心、儒門的體,在功夫中進行著這樣的盡心知性知天的進程,儒者的整個人生活動因此就在頭上的天、腳下的地、崇德廣業的君子人格中開展,宋儒再怎麼談心談性,也不會談到彼岸世界去的,再怎麼談本體功夫、功夫本體,也不會離開君王天下鄰里鄉黨的這一現世社會的,而禪師家再怎麼入世地人間淨土,都還是念茲在茲地默契著佛菩薩的召喚,他們可能正默默在實踐著地藏王菩薩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行願,或是一個老實的隨緣行報冤行的謹受奉行,原來如此地入世的大乘行門是要把這個社會中的人存有者在死亡之後帶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去的,而不是如易傳中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如宋儒言「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的作法,這是把它在世界存在者的概念予以抽象理性化而解消它在世界的存在問題的作法。
關於禪儒的關係問題,賴永海教授言:
「禪宗不但中國化色彩濃,而且本身就是一種中國化的佛教。它受儒家心性學說的影響亦最深、最烈。禪宗祖師提倡『即心即佛』、『明心見性』,其所說的『心』就接近於儒家所說的作為道德主體的『人心』,而與傳統佛教所說的作為抽象本體的『真心』不盡相同。其所說的『性』,也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的色彩,是有情眾生之人性,而不同於傳統佛教所說的作為一切諸法抽象本體的『真如佛性』。實際上,祖師禪的強調心性及其對心性內涵的改變,即把原來作為抽象本體的心性人心化人性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其佛性學說和修行理論只能主張『眾生有性』和注重『道由心悟』。到了唐末五代之後,這種情況開始有所變化。由於儒家的復興,特別到了宋代,由於新儒學的出現,隋唐佛教從儒家那裡吸收來的思想,又被新儒學攝取去,佛教的地盤大大地縮小,新儒學則上升為顯學。而就心性理論說,它原就是儒家的道傳,此時之佛教如果繼續在心性問題上與儒家糾纏,就很難顯出自家之特色,因此,宋元之後的禪宗,在思維方式上便掉頭一轉,向道家靠攏,由注重人心一變而崇尚『自然』,倡『性自天然』、『不加造作』。」
又言:
「從理論思維的角度說,佛儒在修行方法上的差異,是由二者思維模式的不同造成的,而隨著佛儒二家在思維模式、思想內容等方面的相互浸透、相互吸收,隋唐之後的儒學逐漸朝著本體論的思維模式方向發展,而隋唐以降的佛教也大量吸收了儒家人性、心性論的思想內容,這就導致了儒佛在修行方法上的相互靠攏,佛教的反本歸極,逐漸變成禪宗的『明心見性』,而儒家的『修心養性』也逐漸發展為『復性』、『明誠』。
我們以為這樣的理解眼光是有些不恰當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以概念範疇研究哲學觀念」的研究方法之論理性的不足之處,這樣的儒佛交涉的研究觀點是被心性概念的同時使用所迷惑的結果,任何哲學體系都必須在文化氛圍中發言,因此不能擺脫文化氛圍中的字詞概念之使用,但是字詞概念之使用是一回事,字詞概念本身在觀念世界中的脈絡意義是另一回事,儒佛皆使用心性概念表述理論、儒佛皆發展了今人所謂的心性說哲學,這都只是中國文化氛圍內的事,這樣的接近實與各個體系內部的特殊型態無涉,我們如果從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進路來看待哲學範疇的使用時,便能發現特定的字詞使用背後反映著特定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基調在,心性概念即反映出人存有者的功夫活動的哲學問題意識在,儒佛皆論心性是因為儒佛皆有功夫活動,但是儒佛又各有其形上學世界觀,形上學世界觀和功夫活動在理論世界中是緊密地綰合的同體型態,強調了心性概念只是強調了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哲學,只是顯現了理論建構的一個特定哲學問題的共同關切,也就是說大家都有了共同的哲學問題必須去建構,以強化其理論體系內的基本哲學問題架構的完整性,也就是說從其形上學世界觀的觀念內涵中勢必要發展出功夫理論也勢必要強調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哲學,於是儒佛皆發展了心性範疇的哲學建構,這絕不表示儒佛皆主張了心性說,因為心性說是個有歧義的概念,嚴格說來,心性說不是一說,從基本哲學研究法的角度看來,心性說只是心性進路的功夫哲學,甚至是心性範疇的本體論哲學,這是一個題目,不是一個主張,當然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理論上爭辨的課題,亦即心性功夫優位的主張,但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層次的理論問題了,心性功夫優位的哲學主張在一定的脈絡下事實上儒釋道亦皆可以有此主張,如此一來是不是儒釋道又即同一了呢?是不是儒釋道即三教合一了呢?仍然不是的。論中說到佛教哲學因為心性說是儒門本來的哲理且已被豐富地建構,因此必須轉向道家的自然範疇,這更是一個理論的錯置,佛教哲理建構也可以強調自然,但這個自然之本然的情狀仍然要回到佛教哲學本體論建構自身之內來,是佛法般若本體的自然自性自在之自然,而不是道家之自然,道家之自然蘊含著道家的世界觀,佛教的自然蘊含著佛教的形上學,這又是一個「概念範疇研究進路」之理論性不足的工作結果。這樣的工作方式亦見於詮解三教異同的問題上,洪修平和吳永和教授亦言:
「明末清初的元賢禪師提出的「理外無教教必歸理」可說是反應了禪玄入理和佛道歸儒的基本現實。……這種諸教歸理的思想,顯然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明理學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後,佛教禪學等各種思想學說對宋明理學的迎合。」
這也是我們反對的觀點。永覺元賢禪師的原文如后:
「問:先覺多言三教一理,是不?曰教既分三,強同之者妄也;理實唯強異之者迷也。故就其異者而言之,則非獨三教不同,即同一佛教,而大小不同,即同一大乘,而權實不同。蓋機既萬殊,故教非一端。若就其同者而言之,則非獨三教是一,即一切魔外,以及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蓋理外無教,故教必歸理,如此方儒教,乃是此中眾生,形生神發,日趨於欲,不約而防之,何所底止!故聖人因時勢,察人情,為之說仁義,立紀綱,化之以禮樂,束之以刑罰,使不亂也。即使佛處震旦國,說經世法,又豈過於周公、孔子哉!然眾生既束於儒典,執著名相,則名相之區,翻為桎梏之地,豈儒家聖人之意哉?由是老莊出,而說虛無自然之道,使聞者閑曠超越,不為物累,庶幾為人道之方便。至於我佛所說,則超人越天之實法,而窮理盡性之實學也。
「昔夫子所謂予欲無言,而端木氏所謂聞於文章之外者,又豈有異於是哉!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嘗不一。彼執異執同者,皆戲論也。」
永覺元賢禪師說從教言三家不同,從理言理實唯一,但這個理卻決不是宋明儒的理,不是仁義禮智的理,而是般若波羅蜜多之理。永覺元賢禪師固然說道「理實唯一」,然其所謂一者是在一個佛教哲學的世界觀本體論的架構內的一,三教之一是一於佛教而不是三教皆使用了理概念範疇即三教之理的內涵即已為一,且禪師認為儒道兩家的義理是更有深蘊,至於這個深蘊是什麼呢,那自然是我佛所說的超人越天窮理盡性的實法實學,可見禪師家亦不自認為此儒道之學即已全福彰顯真理底蘊,唯其真理底蘊之深透之後必然不悖佛法而已,然而就是這樣的論斷在儒道兩家的立場而言亦恐未必即能同意,因此儒釋道教的同異問題之辨,不能僅只是在概念範疇的同異之間了事,而必須進入基本哲學問題的全面體系內來追究才能解明,亦即必須整體地將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哲學主張全體涉入才有同異之明辨。
以上我們集中地討論了作為功夫哲學中心的禪宗哲學之義理型態的諸種問題,這是針對禪宗心性說的提倡所引發的理論性格定位的問題討論,禪宗心性說的提出是禪宗功夫哲學有以貢獻於中國大乘佛學及在中國哲學史義理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出表現型態,它雖然是禪宗哲學的特色,但是它更是大乘佛學的內部理論問題以及它是中國哲學特有的理論型態的問題,因此是一個中國哲學方法論上的突出表現體系,更直得放在一個中國哲學方法論的進程內來探討。以下我們將進行另外兩層的禪宗功夫特色的觀念探討,以下這兩層的探討就更多的是禪宗自身的特色,是只有在禪門內部才得發生的義理型態,而不再地具有那麼多的義理形式之共通性在。(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