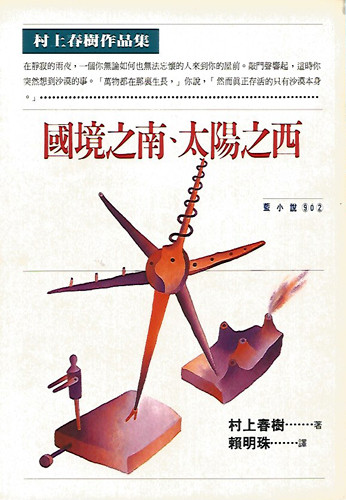《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所謂的「什麼東西」(修訂)
村上春樹早期作品的「個人性」是很重的,這不僅是就他的敘事風格而言,也包括他小說中的主題、人物、對白的同質性,無論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性別、年紀或身處的環境,通常都呈現出相似的思考內容以及生活品味,以致在對白上、對於「物」的描述上,以及比喻的修辭上,經常出現大同小異的情形;再加上村上春樹提到過的小說的「挖井」功能,更讓人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很容易聯想到作者本人,Susan Sontag在《重點所在》裡提到:「好多第一人稱敘述者都被賦予一定的特性使之跟他們的作者有相似之處,作者本人樂於接受這種相似之處」,《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小說裡的主角阿始的文化品味、酒店經營經歷等等,更使得這本小說散發出一種這是作者個人本身經歷(改寫)的味道。
這種「作者本身經歷(改寫)」的感覺,正是作為第一人稱敘事的回顧性作品的特點之一。而且,這種回顧經常帶著一種懺悔的味道:它總描述出過往的錯誤,再透過故事中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敘事者在情節發展的同時逐步的省思與成長,最後(無聲地)尋求來自讀者的諒解,甚至敘事者對自己的開脫。然而,這種懺悔有時既是真摯的,同時卻又是虛偽的:真摯指的是敘述者的確透過反省與提問來承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與造成的傷害;虛偽則是指在這些過錯與傷害的反省之後經常伴隨著一個自我解釋:時間的(因為年少無知)、共犯結構式的(很多人也是如此)等等的解釋。
此外,第一人稱敘事者還會希冀能在回憶過程中釐清或找到當年不解之事的答案,以村上自己的術語來說,就是「挖井」、「穿牆」。男主角阿始的「井」,就是書中一再出現的那個「什麼東西」。
在Milan Kundera的第一部小說《玩笑》裡,同樣也有一位不在卻又無所不在的女主角(島本的「無所不在」在前半部,露茜則是在後半部),她的經歷對男主角而言,一直到故事結束,都是一個謎。在敘事手法上,Milan Kundera是透過四個不同人的第一人稱敘事的「復調」方式來營造出露茜的「神秘感」,村上春樹則是透過一個陌生的男子以及一包裝有十萬圓信封的得而復失來呈現島本存在的「虛實」。
這種缺乏真相(或所謂留下懸念),也是第一人稱敘事的另一特點,因為它不像第三人稱敘事那般擁有全知的能力,不論作者本身有沒有答案,他都可以使敘事者讓真相懸而不明,使讀者產生縈繞於心的效果。另一方面,在面對這類「作者本身經歷(改寫)」的第一人稱敘事故事時,讀者必須保持清醒的是,記憶化為文字必然要經過篩選的過程,也就是說,讀者知道的真相是敘述者篩選之後想要讓讀者知道的真相,儘管讀者也預設敘述者所講的事情是「真的」,但那些被捨棄掉而沒有被講述出來的「事實」,是不是就不具意義與價值呢?也就是說,作者沒有說出來的是什麼?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的內容,簡單來說,就是尋找這個沒有明確說出來的「什麼東西」的過程。作者採用「視線同化」的方式,讓「讀者也以第一人稱的觀點,亦即以和『我』同化的形式,目擊出現在眼前的事物,並一一體驗」(村上春樹語,《『《1Q84》之後~』特集》)。
小說從一開始,敘事者阿始就告訴讀者,自童年對島本的初戀結束後,他心理上就一直有著一種欠缺感,他總是覺得「欠缺了什麼」;故事最後,他又告訴我們,最終不但那個「什麼東西」沒有了,連所謂「我」這樣的存在也消滅了、溶化了,這一表述,似乎充滿著「存在」的味道,然而,實際上,所謂的「什麼東西」在他與初戀的情人島本相逢之後的做愛場景裡已經明確地表達出來:它既不是什麼形而上的純純之愛,也不是愛與慾的靈肉合一,它實際上就僅僅只是對「性」的追逐。
表面上,阿始對島本的感情,透過都是獨生子的連結而開始產生一種初戀情愫,之後透過不斷對島本的回憶,使讀者(甚至敘事者本身)都以為對島本的懷想是一種對真愛的追尋,但在第一章結束時,阿始說:
和她見面的那時候,我才十二歲,還沒有所謂正確意義上的性慾。雖然對她隆起的胸部,她裙子下面所有的東西似乎擁有模糊的興趣。但並不知道那具體上有什麼含意,也不知道那會具體地把我引導到什麼地點去。我只是靜靜地傾聽、閉上眼睛,想像那地方應該會有什麼而已。那當然是不完全的風景。在那裡的一切事物都像被一層霞光籠罩著一樣朦朧,輪廓模糊不清。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那風景之中,潛藏著某種對自己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一段的思考當然不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當時的講述,而是已經步入中年的阿始對當時心境的回想。這一長段的回想的重點,其實就在「風景」這兩個字上,這個風景便是,在島本「隆起的胸部」和「裙子下面」應該會有什麼。而所謂的霞光一樣的朦朧、模糊不清的輪廓等等,只是在「性」這個風景周圍刻意營造的氤氳。
在這裡,小說的主調便被定了下來,之後整個故事的展開,其實就是去追尋並得到這個隱藏在裙子下面的「什麼東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無性的泉、完全只有性的泉的表姊、兼具性與婚姻的有紀子,以及擁有這個裙子的主人島本,然後故事在主角阿始終於得到了這個他夢寐以求卻再度失去的裙子下面的「什麼東西」之後結束。
小學畢業後,阿始選擇了與島本漸行漸遠,這一選擇從後來與泉的交往看來,是具有關鍵性的。
高中時的阿始對泉的感情,實際上只是著眼在「性」這方面。小說的第二章與第三章完全著重在阿始如何想盡辦法要得到泉的童貞,最終,阿始還是失敗了,再一次,透過回想,阿始又提到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困惑而失望的是,不管經過多久我都沒辦法在泉身上發現「為我存在的東西」這一點。我可以把她的優點條列出來,而且那項目絕對比缺點多得多。……但她卻缺少了決定性的什麼東西。如果我能從她身上找到那個「什麼」的話,我想我一定已經和她睡過了。我恐怕絕對無法忍耐吧。……我當然只不過是一個滿腦子性慾和好奇心的十七、八歲不懂事的少年而已。
當泉好不容易答應與阿始袒裎相對,卻被阿姨的到訪破壞後,泉向阿始問到兩人感情以後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時,阿始其實是很清楚他跟泉實際上日後是不會繼續在一起的。
我說我喜歡妳,不會那麼容易就忘記妳。不過說真的,我並沒有那麼肯定。有時候光是場所改變,時間和情感的流動就會完全改變。我想起和島本離開時的事。即使兩個人都感覺那樣親密,可是一旦上了中學,搬到別的鎮上時,我和她就分別走上不同的路了。我曾經那麼喜歡過她,她也叫我去玩。但是結果我卻不再去了。
「我曾經那麼喜歡過她,她也叫我去玩。但是結果我卻不再去了」,這句話正道出了阿始的感情,對島本也好、對泉也好,始終是擺在他的「自我」之下的,這個「自我」──自私──正是貫穿整部小說的主要精神。正是在這裡,阿始透露出了,即使是對島本有這麼深的感情,但在沒有得到他所要的「什麼東西」的情況下,他選擇的方式是「離開」。從故事後來的發展回頭看,正是他的這一態度,造成島本日後謎一樣並顯得不幸的生活的主要原因,因此說,阿始從一開始選擇不再去找他自以為是摯愛的島本這件事是關鍵性的。
這個無法在泉身上得到的「什麼東西」,後來在泉的表姊身上得到發洩,然而阿始性慾的發洩,最終對泉造成無法挽救的二次傷害(第一次傷害是阿始自始至終只是喜歡泉[以及她的肉體],但並沒有愛)。可注意的是,阿始用了「損壞了」這樣的字眼來表達他對泉的傷害:通常人們將「損壞」這樣的字眼用在「物」的方面,而不是用在「人」的身上,在表達一個行為對人所造成的後果時,人們通常使用的是「傷害」,因此,「損壞了」這個詞也許在(無意中)更加表明了他將泉視為「性物」的心態。
泉的表姊,作為故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她卻是無名的,這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阿始的解釋是他已經忘記她的名字了,但一個長時間又是猛烈激情維持性愛關係的對象,這個「忘記」的藉口反倒顯得很可疑!
在電影「巴黎的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裡,當Jeanne問Paul的過去時,Paul拒絕了,同時也不想知道Jeanne的一切,他只想要純粹的做愛而不涉及感情,以致當電影結束,Jeanne槍殺Paul之後,仍然不知道他的姓名。

在一間房間裡,沒有個人的歷史,沒有多餘的言語,有的只是「腦漿都快溶掉似的激烈做愛」。對兩人來說,在屬人的這一面,透過不斷的進出動作與高潮,得到了所謂的「存在感」,在屬獸的這一面,則是用身分、過去與語言的剝離,回到了動物性的生理衝動的發洩。
在這裡,「什麼東西」又再出現:
正確地說,我並不愛她。她也當然並不愛我。但是不是愛對方,那時候對我並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自己現在,正被「什麼東西」激烈地捲進去,而那「什麼東西」之中應該含有對我很重要的東西,這回事。我想要知道那是什麼。非常想知道。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想把手插進她肉體裡面,直接接觸那「什麼東西」。
而這個「什麼東西」卻是泉所無法給予的。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每一段的感情關係後面,敘事者阿始始終會向過去發生的事情提出關於「什麼東西」的反思,透過反思的形式,賦予了小說一種形上學高度的假象,但所謂島本的「風景」,所謂泉身上(這裡的身上明確指的是物質性的肉體)無法找到的「什麼東西」,所謂的「把手伸進她肉體裡面」,一再表明,所謂的「什麼東西」,僅僅是對「性」的追求。
真正衝破這個「什麼東西」的形上學假象的正是阿始最終與島本的結合。首先,在兩人重逢後的一次談話裡,阿始很老實地表示,37歲的他仍舊會有想把手伸進女孩子裙子下面的想法。其次,當最終阿始可以得到他夢寐以求、念念不忘的「什麼東西」前,島本向阿始提出了她的要求:
……對我來說中間性的東西是不存在的。在我裡面中間性的東西不存在,在中間性的東西不存在的地方,中間也不存在。所以你要嘛就全部接受我,或者不要我,只能有其中之一。這是基本原則。……如果你不願意我再離開的話。你必須要我的全部。我的事情從頭到尾全部接受。我跛著的腳,我所包含的東西的全部。而且我可能也要你的全部。全部噢。這點你瞭解嗎?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阿始也表達了他願捨棄一切跟島本在一起的想法,這一段話表面上似乎便是所謂「什麼東西」的最終註解了:
我是愛她們,非常愛,而且非常珍惜,正如妳所說的。不過我知道──這樣是不夠的。我有家庭,有工作。我對兩方面都沒有不滿,到目前為止,我想兩方面都很順利。我想甚至也可以說我很幸福。不過,只是這樣還不夠。我知道。自從一年前遇到妳之後,我變得非常清楚。島本,最大的問題是我欠缺了什麼。我這樣一個人,我的人生,空空的缺少了什麼,失去了什麼,而那個部分一直飢餓著、乾渴著。那個部分不是妻子,也不是孩子能夠填滿的。這個世界上只有妳一個人能夠做到這個。跟妳在一起,我才感覺到那個部分滿足了。而且滿足之後,我才第一次發現,過去的漫長歲月,自己是多麼飢餓、多麼乾渴。我再也沒辦法回到那樣的世界去了。
這段註解乍看之下,似乎是對上面提到所謂「什麼東西」就是「性」這個解讀的反證。當然,阿始對島本的「愛」,從小說一開始就不斷地被傳達出來,在小說末尾島本失蹤之後阿始的失魂落魄,也的確同樣表現了阿始的「愛」,依此,將整部小說視為阿始由「性」到「愛」的追求,而將所謂的「什麼東西」解讀成「靈肉合一」,似乎較符合故事發展的脈絡。
然而,即使是這個「愛的表白」,阿始接下來的(生理)反應卻是奇怪的:在這樣凝重的氣氛下,阿始的性器竟是已經「勃起得又硬又大」了。此外,揆諸阿始在上面提到的幾處關於「什麼東西」的回想中,都是處在「性」的處境下,而且這個「什麼東西」是僅為阿始而存在的:泉當然沒辦法給阿始這個「什麼東西」、泉的表姊的肉體則將他捲入「含有對我很重要的東西」,而跟島本的做愛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這個「什麼東西」是他從12歲開始便有的慾望,就如島本所說的,這個對「什麼東西」的滿足更多地只是具有一種「儀式性」的功能,如果再對比阿始可以從泉的表姊肉體上得到的「對我很重要的東西」來看,那麼,將「什麼東西」解讀為「性」,似乎就不是一種「誤讀」了。
而且,阿始的「愛」似乎也顯得「廉價」:在男女之間的愛方面,除了島本之外,所有的女性人物(甚至包括有紀子)有的只是阿始的「喜愛(歡)」而不是「愛情」,甚至對島本這麼濃烈的「愛」,也只是被動地等待島本的出現,沒有主動去追求,而且島本一旦消失,他便馬上回到了妻子身邊;在親子的愛方面,儘管阿始說愛自己的妻子、孩子,也說非常珍惜他們,但是在島本面前,這些卻都是可以捨棄的──既想捨棄,何來的珍惜!
當最終島本離開了,阿始回到他一度想捨棄的妻兒身邊(雖然他也自知愧疚)時,泉已經被「損壞了」、表姊去世了、有紀子默默承擔了自己的先生外遇的痛苦,並且知道他心裡永遠想著另一個女人,卻還要回過頭來安慰他,而島本又回去過那神秘而似乎是不幸的生活了(這個不幸的生活發生的原因,如上所述,很可能就在於小學畢業後阿始「遺棄」了她)。
阿始呢?在他傷害了這麼多女人之後,想的仍舊只是自己像身體被拔掉栓子般的「空虛」。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不同於所謂的「成長小說」。「成長小說」的其中一種類型是小說主角在故事開端時屬於某種負面性的人物,然後在故事的推進中逐漸得到成長,最後成為(令讀者喜愛)的正面人物。例如Jane Austen《愛瑪》裡的Emma,因為喜歡當紅娘,亂點鴛鴦譜,造成了身邊的人的傷害;又如Henry Fielding《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裡的湯姆.瓊斯,由於年少輕狂犯了錯誤,但這些作者利用寫作技巧(「內心獨白」)或透過情節安排(「真相大白」)的方式,使讀者感受到主角內心的良善以及結局的完滿,來讓讀者原諒主角所做的過錯以及所造成的傷害,進而接受小說主角的缺點,甚至喜愛這樣的人物。
這些主角之所以能夠成長,都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因素,那便是對自己行為的反省,以及進而予以改善或補救的行動。但在《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裡,我們看不到作為主角的阿始的成長,有的只是一再重複發生的、因為對性的追求而對女性的傷害。他始終是一個「被寵壞的」、「任性得可怕的」人(小說一開始以及結束時,阿始自己都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性格的),儘管小說中充滿了反省、悔恨的說詞,使用一些像是「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中間性」、「沙漠」、「無」這樣抽象的字眼來營造一種形上學的帷幕,來掩蓋他形而下的肉體追逐,然而到了故事結局時,他仍然沒有做出任何的努力來改善自己,也沒有嘗試對所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他想到的始終只是他自己的「欲求未滿」,以及「欲求未滿」所帶來的「空」。
這是一個任性的中產階級男人在傷害了許多女人之後,以貌似懺悔的姿態,用「強說愁」似的語調回想、述說的一個追求「性慾」的故事。如果對照他最後描述自己心境的那些文字,與那些受到他傷害的女性的遭遇,令人不禁懷疑,這樣的故事若是改由這些被他傷害的女人──島本、有紀子,以及傷害最重的泉──的角度來述說,那將會是怎樣的姿態、怎樣的語調呢?
儘管阿始作為一部小說的主角,但是,如同Milan Kundera的《玩笑》一樣,《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講的其實是關於島本的故事。
2018.6.10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