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7 04:00:00阿楨
狄金森:世界百大作家54
埃米莉•狄更生

大約於1846年到1847年間所照
埃米莉•伊莉莎白•狄更生(英文: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又譯艾彌莉‧狄瑾蓀或艾米莉•狄金森,1830年12月10日-1886年5月15日),美國詩人。詩風凝煉,比喻尖新,常置格律以至語法於不顧。生前只發表過10首詩,默默無聞,死後近70年開始得到文學界的認真關注,被現代派詩人追認為先驅。與同時代的惠特曼,一同被奉為美國最偉大詩人,後世對她的詩藝、戀愛生活、性傾向多有揣測。
狄更生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安默斯特頗具影響力的一個顯赫家族,性格內向,不愛露面。年輕時,她曾在安默斯特學院學習了七年,此後,又在曼荷蓮女子學院度過了一段短暫的時光,最終返回到位於安默斯特的家中。當地人認為她似乎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她偏愛白色衣著,不願見客,晚年時甚至不願邁出自己房間一步。因此她與大多數朋友的友情都靠通信維繫。
作為一位高產卻孤僻的詩人,狄更生的1800多首詩歌作品僅有十幾首在她在世時得到出版。[1]這些在她生前出版的作品常常會被出版商大肆修改,以符合當時傳統的詩歌規則。在狄更生所處的時代里,她的詩歌是獨特的。她的詩歌包含短句,略去標題,韻腳不齊,並且還有反常規的大寫字母和標點符號。[2] 她的許多詩歌探討死亡和永生,這兩個主題也反覆出現在她寄給朋友的信里。
儘管大多數狄更生的朋友可能都意識到她的寫作異於常人,但是直到1886年她去世這年,她的妹妹拉維尼亞發現了她藏匿的作品,狄更生大量的作品才為人所知。她的第一本詩歌作品集在1890年由私人好友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森和梅布爾•托特出版,他們二人都對作品內容進行了重大修改。直至1955年,學者托馬斯•H•詹森出版了《埃米莉•狄更生詩集》,這是狄更生作品首度完整出版,幾乎沒有任何修改。儘管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這段時間裡,有人批評並質疑狄更生的文學功力,當今的評論家卻認為狄更生算得上是美國一位重要的詩人。[3]
家庭
1830年12月10日,埃米莉•伊莉莎白•狄更生出生在位於麻薩諸塞州西部的安默斯特的農莊中,一個聲望很高但並不富裕的家庭。[4]兩百年前,在清教徒大遷移中,狄更生家族就來到日後使他們興旺發達的新大陸。[5]
埃米莉•狄更生的曾祖父為安默斯特學院的創辦人之一。祖父塞繆爾狄更生幾乎憑藉一己之力創辦了安默斯特學院。[6]在1813年,他建造了自己的宅第,位於市中心主幹道的大宅第,這也成為狄更生家族在那個世紀最好階段的象徵。[7]塞繆爾狄更生的大兒子,埃米莉的父親愛德華父親為有名望的律師,擔任安默斯特學院的司庫接近40年,也曾供職麻州普通法院,以及擔任許多屆麻州參議院、美國眾議院議員,並且代表漢普郡區出席了美國代表議會。
1828年5月6日,愛德華迎娶了來在蒙森的埃米莉諾克羅斯。他們有3個孩子:
被稱為奧斯丁的威廉奧斯丁(1829-1895);埃米莉伊莉莎白和被稱為拉維尼亞或溫妮的拉維尼亞諾克羅斯(1833-1899)。[8]
埃米莉有一兄一妹,年輕時跟兄長奧斯汀的感情尤篤,二人都特立獨行,愛好文學,奧斯汀後來繼承父業,當上律師。
童年生活

這是一張埃米莉•狄更生年輕時的畫像,當時她九歲。這幅肖像畫出自一張對孩童時的埃米莉、奧斯丁和拉維尼亞的特寫。
狄更生從小接受良好教育。據大家所說,年輕的埃米莉是一個行為端莊的女孩。在她兩歲去蒙森走親戚時,埃米莉的舅母對艾米莉的評價是非常滿意的,她是一個很乖的小孩,一點也不亂動。[9]埃米莉的舅母也指出這個女孩對音樂的喜愛,尤其在鋼琴方面極具天賦,她將此稱之為「駝鹿般的」(the moosic)。[10]
狄更生在位於普萊森特街(Pleasant Street)的一座兩層小樓里讀完了小學。[11] 她接受的教育「對於一個維多利亞女孩來說過分的傳統」。[12] 他的父親希望他的孩子們能接受好的教育,即使是在出差的時候,也關注他們的學習進展。在埃米莉七歲時,他的父親寫信回家提醒他們兄弟姐妹「繼續讀書、學習,當我回家時,告訴我,你們都學了哪些新知識」。[13]埃米莉一直以一種溫和的手法描繪他的父親,而從她的信件里可以看出她的母親是冷漠的。在一封給知己的信中,埃米莉寫到「在孩提時代,當發生事情時,我經常跑回家找奧斯丁。儘管他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但是我喜歡他勝過任何一個。」[14]
1840年9月7日,狄更生和她的妹妹拉維尼亞一起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書,這所學院僅在兩年前才開始招收女性學生,在此之前只招收男性學生。[11]大約在同一時間,她父親在被愉快街道購買了一座房子。[15]艾米莉的哥哥奧斯丁後來描述他們大的新家如同公寓,當他們的父母不在時,他和艾米莉就是這兒的君主和夫人。[16]從房子中可以看到安默斯特公墓,當地的一位行政長官認為這兒既沒有樹木又讓人毛骨悚然。[15]
青少年時期
他們把我禁錮在散文中 –
彷彿當我是少女時
被放入壁櫥中 –
因為,因為他們喜歡我「平靜」 –
平靜!那他們豈不要窺視 –
看見我的思緒 – 迴環繚繞 –
真聰明,他們也許早已禁錮小鳥 –
因為它會逃離 – 那鎖著的牢籠 –
埃米莉•狄更生,約1862年[17]
狄更生年輕時曾隨家人到費城、華盛頓等地探親,17歲進入女子大學。她在學院求學七年,課程包括英語和古典文學、拉丁語、植物學、地質學、歷史、「精神哲學」及算術。[18]有幾個學期她因病輟學:其中最長的時間段是從1845年到1846年,那段時間裡她總共才上了11周的課。[19]
健康

2000年發現的一張照片,據說埃米莉為人所知僅有兩張照片的其中之一。購買者在eBay購得,據推測攝於1848─53年。假如照片為真[20],就可看到狄更生健康時的樣子。
狄更生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受到來自死亡「不斷加深的威脅」,特別是那些與她最親近的人之死。當她表姐妹兼密友索菲婭•霍蘭德(Sophia Holland)患斑疹傷寒症並最終死於1844年四月時,埃米莉崩潰了。[21]兩年後,當她回憶起密友之死,埃米莉寫到「似乎當時我也應該隨她而去,因為我不能照顧她,甚至就這麼看著她。」[22]隨後她患了憂鬱症,她父母只將她送回波士頓的家中療養。[23]當埃米莉身心恢復後,她立刻回到了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Academy)繼續她的學業。[24]這段時期里她首次結交了終生摯友及通信往來的朋友,如亞比亞•魯特(Abiah Root)、艾比•伍德(Abby Wood)、簡•漢弗萊(Jane Humphrey)以及蘇珊•亨廷頓•吉爾伯特(Susan Huntington Gilbert)。
性傾向
蘇珊是埃米莉年輕時的密友,後來更嫁給了埃米莉的哥哥奧斯丁,成了狄更生的嫂子。婚後,蘇珊跟狄更生為鄰,但二人常以便條通信。狄更生許多詩作的第一個讀者(超過250首)就是蘇珊,而且常因蘇珊的意見而修改詩作。狄更生現存的書信,致蘇珊的也佔最多。曾說:「成為蘇珊就是想像」(To be Susan is Imagination),[25]狄更生對蘇珊的強烈感情是否為同性戀傾慕,成了不少學者爭論的題目。
信仰
1845年,在安默斯特興起了宗教復興,狄更生的46位同僚都做了信仰宣言。[26]來年,狄更生給她朋友寫到:「我從未如此享受完美的祥和與快樂,好像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我找到了我的救世主。」[27]她接著寫到,她「非常高興獨自與上帝交談,似乎上帝正在聆聽我的禱告」。[27]這一景象並沒持續太久:狄更生從未做過正式的信仰宣言,做禮拜也只堅持了幾年時間。[28]大約1852年,也就是她不再做禮拜之後,埃米莉寫了一首詩,開頭是:「有人堅持,在安息日去教堂做禮拜─/但是我卻堅持,安息日在家中度過」。[29]
埃米莉在學院最後一年間與廣受歡迎的年輕校長倫納德•漢弗萊(Leonard Humphrey)成為好友。1847年8月10日,埃米莉結束了自己在安默斯特學院的學習,並進入位於南海德利(South Hadley)的曼荷蓮女子神學院(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隨後改名為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求學,距離安默斯特大約16公里。[30]她只在神學院上了10個月的課。雖然她喜歡曼荷蓮學院的女孩子們,但是狄更生在學校從未結交永遠的朋友。[31]至於埃米莉在曼荷蓮學院求學經歷如此之短的原因,現在是眾說紛紜:有說是她身體欠佳的,有說她父親想留她在家中的。也有說人說,是因為埃米莉對學校的宗教氛圍非常反感,或者是她不喜歡嚴於紀律的老師。也有人認為是埃米莉的思鄉之情在作怪。[32]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埃米莉離開了女子學院,她的兄弟奧斯丁在1848年3月25日突然出現,「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埃米莉帶回了家」。[33]回到安默斯特,狄更生就做些日常活動打發時間。[34]她會為家裡做些糕點,也會經常在她家鄉──發展中的大學城參加一些當地舉辦的活動。[35]
隱居
1860-65這幾年,是狄更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同時開始隱居,有時甚至拒見來客。對時事坦白地缺乏興趣,包括美國內戰。後世猜測,狄更生因戀愛失敗而離群索居,但並無有力證據支持這一點。[36]
其實狄更生隱居後,依然跟許多人通信(已知的通信者有99人,包括一些有名望的文人),在寫詩、管家之餘,精神上並不孤單。1862年,寫信給當時著名的雜誌編輯希金生(Thomas W. Higginson),請他品評自己的詩作。希金生看到狄更生的天才,但由於她的詩風異於同時,始終沒有鼓勵她出版。雖然狄更生沒有正式出版她的詩,但常在書信中附上詩歌,令其詩開始在親友中流傳。
晚年及身後
埃米莉跟妹妹文妮一樣,終生未婚,替多病的母親管理家事(埃米莉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家中渡過)。55歲病逝,據診斷是死於布賴特氏病(Bright's disease)(一種腎病)。

埃米莉•狄更生自留地上的墓碑
狄更生死後,文妮發現其姊留下的詩歌(共有40本詩稿,以及若干散軼的手稿)。蘇珊嘗試助她整理出版,不果。手稿落在奧斯汀的情婦托德(Mabel Loomis Todd)手上,她與希金生最終合力讓狄更生的詩歌面世。後來,狄更生的姪女瑪撒(Martha Dickinson Bianchi),即蘇珊的女兒,也出版了狄更生的部分詩歌與書信。1955年,首部未經竄改的狄更生詩全集出版,引起文學界的關注,開始對其人其詩作全新的評估。
創作歷程
早期
埃米莉•狄更生年輕時的社交生活跟一般少女無異,且好作諧詩。未能確定狄更生何時開始認真做詩。她十八歲時,狄更生一家結識了一位叫班傑明•富蘭克林•牛頓的年輕律師。在一封牛頓死後狄更生所寫的書信中,狄更生寫道,他曾經「在去伍斯特求學之前和我的父親一起工作過兩年,並且是我們的家庭中重要的朋友」。[37]儘管他們之間可能並不是戀人關係,牛頓對狄更生的影響卻很重大,在狄更生所提到過的一系列年長男士中,就像是她的老師,導師,或者師傅一般,牛頓排在第二位(僅次於亨弗瑞)。[38]
牛頓極有可能給她介紹過威廉.渥茲華斯的作品,他將拉爾夫.華爾多.愛默生的第一部詩集作為禮物送給狄更生,對她以後的創作起到了良好的開頭。狄更生之後寫道,「他是以我父親的法學學生的名義教授我,碰觸到了文思泉湧的秘密」。[39]牛頓很重視她,深信她,甚至已經將她看做一位詩人。在他深受肺結核的病痛困擾時,他寫信給她,並且說他想要活著見到狄更生實現他所預言的成就。[39]傳記作家們認為狄更生在1862年的聲明──「當我還是小女孩時,我有一位朋友,他教會了我不朽的精神,但是他自己卻冒險太近了,以至於他再也沒有回來」就是指的是牛頓。[40]
狄更生不但熟記聖經,而且也諳熟當代通俗文學。[41]她可能受到莉迪亞•瑪麗亞•蔡爾德寄自紐約的信件,這是牛頓給狄更生的另一份禮物。[21](讀過之後,她熱情洋溢的寫道,這些可以成為一部著作,甚至還有更多的可以這樣認為![21])1849年後期,狄更生的兄弟給她偷偷帶了一份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的《卡文那》的抄本(因為他們的父親可能會不贊同)[42]而且一個朋友借給她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43] 《簡愛》的影響難以估計,不過狄更生得到她的第一隻也是唯一一隻狗時,她將這隻紐芬蘭犬取名為「卡羅」,這個名字來自於書中角色約翰 李弗斯教士的狗。[43]威廉•莎士比亞對狄更生一生也有著潛在的影響。關於他的戲劇,她給一位朋友寫道「為什麼緊扣手掌?」,而對另一位朋友寫道,「為何需要其他任何一本書?」[44]
隱居期
隨著埃米莉越來越遠離外面的世界,從1858年夏天開始,她開始回顧、篩選自己之前的作品,並將它們製作成副本,小心整理成「詩稿」(fascicle)。這些可能是她最後的遺作[45]1858年到1865年期間,她創作了40部詩稿,裡面最終包括將近800首詩歌。[45]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在她在世的時候注意到這些作品。
在19世紀50年代晚期,狄更生與塞繆爾•博爾斯(斯普林菲爾德共和報的所有人、主編輯)及其妻子瑪麗成為朋友。[46]多年來,他們堅持定期看望狄更生。在此期間,艾米莉寄給博爾斯三十幾封信件和將近50篇的詩歌。[47]與塞穆爾的友誼更加鼓舞了狄更生的創作熱情,同時塞穆爾在其期刊上也發表了她的幾篇詩歌。[48]人們相信在1858年到1861年期間,狄更生創作了被稱為「致主人書」三卷本書信,這三組書信都是寫給一名不知名的男子,只是簡單的署名為「主人」,而這些也成為學者們一直思考爭論的話題。[49]
19世紀60年代上半葉艾米莉進一步遠離塵世,[50]這一時期也被證明是她的最多產的階段。[51]
後期
與19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狄更生表現出的泉涌似的多產完全相反,1866年她出了相當少的詩篇。[52]情感創傷和幫傭的離開讓狄更生囿於內宅,有可能是成日去解決這些麻煩使她無暇維持原來的創作水平。[53]因為這個時候,相伴16年的卡羅去世了,自此狄更生再沒有養第二隻狗。同年,幫傭9年的家僕結婚並離開了莊園,但直到1869年她們家才再次僱傭一位終身制家僕替代曾經那位。[54]因此艾米莉再次包攬家務,包括她擅長的烤麵包。
艾米莉•狄更生的最後幾年依然堅持寫作,但那時,她已不再編輯、組織其詩句了。她甚至要求妹妹拉維尼亞(Lavinia Dickinson)立誓燒掉她的書信。
作品風格及特色
狄更生的詩作現存一千七百多首,但很難定出實際數字,因為1860年代起狄更生的書信開始「詩化」,有時候很難界定她寫的是散文還是詩(蘇珊稱為「信詩」(letter poem))。狄更生不是個出版的詩人,因此留下的大部分詩作只能看作詩稿,完篇的很少,有句無篇的佔大多數。
狄更生的詩歌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時期,每一時期的作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第一時期為1861年以前,這一時期狄更生的作品風格傳統,感情自然流入。在狄更生死後,出版了她的作品的托馬斯H.詹森,只能給狄更生創作於1858年以前的作品中的五部鑒定年份。
第二時期為1861年—1865年,這是狄更生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她的詩歌在這一時期更具有活力與激情。據詹森估計,狄更生在1861年創造了86首詩,1862年366首,1863年141首,1864年174首。同時,他認為在這一時期,狄更生充分表達了永生和死亡這一主題。
第三時期為1866年之後,據估計,所有的狄更生詩集中有2/3寫於該年之前。
狄更生的詩採用一般教會讚美詩的格律:每節四句,第一、三句八音節,第二、四句六音節,音步是最簡單的「輕、重」,第二、四句押韻。例如: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詩的篇幅短小,多數只有兩至五節,經常破格,常押所謂「半韻」(half rhyme);放棄傳統的標點,多用破折號;名詞多用大寫(但這個習慣在當時很平常);常省略句子成分,有時甚至連動詞也省掉;句法多倒裝,有學者指這是受拉丁文詞序的影響。
狄更生的詩富於睿智,新奇的比喻隨手拋擲,順心驅使各個領域的辭彙(家常或文學的,科學或宗教的),舊字新用,自鑄偉詞。喜歡在詩中扮演不同角色,有時是新娘,有時是小男孩,尤其喜歡用已死者的身分說話。狄更生描寫大自然的詩篇在美國家喻戶曉,常被選入童蒙課本。痛苦與狂喜,死亡與永生,都是狄更生詩歌的重要主題。
狄更生詩作的音樂性和圖象性,成了近年批評家關注的題目。其詩用的破折號,時長時短,有時向上翹,有時向下彎,有批評家指這些是音樂記號,代表吟詠或歌唱那首詩時的高低抑揚;其詩的詩行往往不是一寫到尾,有時一句詩行會分開兩、三行寫(即是說每行只有兩三個字),有學者認為這是刻意的安排,跟詩意大有關係(另外,狄更生有時會在寄給朋友的詩裡會附上「插圖」)。因此,有人主張要研究狄更生的詩,必須以她的手稿(或手稿的影印本)為文本,才不致扭曲詩意。
結構和語法

狄更生詩作"Wild Nights – Wild Nights!"手稿
狄更生在「狂風雨夜—狂風雨夜」的手稿中,運用了大量的破折號,不規範的大寫,以及獨特的文字和意象。這些元素的運用,使她的行文結構在文體和形式上,比傳統規範更多樣化。在韻律方面,她從不採用韻律格五音步(百年來英語詩歌創作的傳統手法),她甚至不用五音步的詩句。她運用的詩句長度不一,從四音節兩音步通常到八音節四音步。
自作品自出版以來,她在文中經常使用的 「半韻」或鄰韻,就倍受爭議。作品的開頭很有特色,第一行往往是一個聲明或說明(人間即天堂」),第二行則對第一行的內容提出了質疑(不管此天堂是不是彼天堂)。由於大量的押韻和自由的詩體,狄更生的詩歌很容易配樂。而詩句主要採用普通格律(四行一節)或民謠格律,相同的韻律格四音步和三音步相間的詩詞,也可把她的詩譜成歌。(這樣的歌中大家熟悉的有「伯利恆小鎮」和「奇恩異典」)學者安東尼•海克特發現,這種行文特點不僅存在於歌曲中,也存在於聖歌和謎語中。下面引用了一個例子: 「誰是東方?/金黃之人/他也許是紫紅之人/攜日而出 誰是西方?/紫紅之人/他也許是金黃之人/帶日而落」
20世紀晚期的學者對狄更生所使用的極具個人色彩的標點符號和詩詞句法深感興趣(句長和斷句)。在她生前出版的屈指可數的幾首詩中,「一個瘦長的傢伙在草地」,共和報刊登時又名「蛇」— 對於共和報版本,狄更生抱怨道修改後的標點符號(逗號和句號代替了原文中的破折號)改變了整篇詩歌的意思。
原文為: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Occasionally rides –
You may have met Him – did you not
His notice sudden is –
共和報版本為: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Occasionally rides –
You may have met Him – did you not,
His notice sudden is.
正如法爾所指出的,「蛇突然出現在你面前」,狄更生的版本抓住了相遇時那「窒息的一瞬間」。而再版中的標點符號則 「使她的詩句相對就顯得普通了」隨著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逐漸認為狄更生的詩句結構和語法「建立在美學基礎之上」。
在研究狄更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1955年版詩集,雖然相對忠實於原文,但後來的學者指出該版本在文體和布局上偏離了原來的文稿。他們斷言,明顯的區別可以從不同的破折號的長度和頁面排版中得知。
有幾冊詩集,人們在印刷時使用了大量不同長度和角度的印刷符號,試圖保留狄更生手稿中破折號的特點。1988年W.富蘭克林註解版詩集,在更忠實於原文的基礎上,給喬納森選擇的詩集提供了可用的措辭。同時,富蘭克林通過對不同長度的破折號進行排版,使其更接近於手寫稿中的破折號。
主要思想
狄更生沒有對其審美意向做出任何正式的評價,因為她作品的主題種類多樣,她的作品也不僅僅局限於一個範圍內。她同埃莫森(一位她所敬仰的詩人)一樣,被視為先驗論者。但法爾則不同意社會對狄更森的評價,他不同意「狄更生固執的思想阻礙了先驗論的進步」的說法。除下面所討論的主要思想之外,狄更森的詩歌還大量運用幽默,雙關,反諷和諷刺等手法。
題材
花與園
法爾發現狄更生的詩和信幾乎都是關於花的,花園通常被形容成「想像的世界,在那,花朵通常象徵著行動與情感」。在她筆下,有的花與年輕和謙遜相聯,比如說龍膽和銀蓮,有的與謹慎和頓悟相聯。她通常附上信和花束把詩送給朋友。法爾注意到,狄更生早期的一首詩,大概寫於1895年,好像自然地融入了花中:我的花為俘虜/那期待已久的雙目/手指拒絕採摘/細心至極/如果它們可以輕聲細語/從早晨到荒野/沒有其他的差事/這也是我唯一的祈禱
給「君」的詩
狄更生的很多代表詩都以「閣下」「先生」「君」作為稱呼,「君」被視作狄更生永久的愛人。這些懺悔詩經常「灼燒於自我質問」並「令讀者通心」,其隱喻體來自狄更生所處年代的文章和繪畫。狄更生的家人認為這些詩是寫給實實在在的人,但學者們卻不這樣認為。比如說,法爾認為君是平常人無法達到的一種混合形象,是「具有鮮明個性的人,但卻像上帝一樣神聖」,他還猜測君可能是「一種基督教的意象」。
病態
狄更生的詩反映了她年輕時便受到疾病、垂死和死亡的困擾,並長期處於這種狀態。她的詩中提到過很多死亡的方法:「釘死,淹死,絞死,憋死,凍死,因早產而死,槍擊,刀割,以及砍頭」,這會令新英格蘭的傳統婦女大吃一驚。她保持著對「依上帝旨意的死亡」和對「頭腦的葬禮」的犀利見解,並用乾渴和飢餓的意象來加強效果。研究狄更生的學者維維安 波拉克把這些引用視作狄更生映射自己的潦倒生活的一種自傳方式,一種對她矮小、貧困的形象的外在表達。狄更生的一首在心理活動上最複雜的詩揭露了這樣一個主題:失去了對生活的渴望會導致自我的死亡,她也視之為謀殺與自殺的結合。
福音詩
狄更生一生寫的很多詩是關於全心領悟基督耶穌的教誨的,實際上,很多是寫給基督的。她強調了福音書的當代內容並進行了重造,通常是用「風趣的語言和美國的口語」。學者多羅西奧博發現「貫穿於基督詩歌的主要特點是對耶穌生活的敬仰,他還認為狄更生的內心世界可以讓她與霍普金斯、埃利奧特、奧登相提並論,排入「奉獻於基督教的傳統詩人」行列。在一首講述誕生的詩中,她結合了愉快和風趣,重現了一個古老的主題「上帝定是/一位易被馴服的紳士/在這麼冷的天氣,走了這麼久的路/僅為幾個人/通向伯利恆的路上/我和他都只是孩子/得到了提升/崎嶇的一億里程。
未發現的大陸
學者蘇珊尤霍死認為狄更生把頭腦和精神看作實實在在的領域,她大部分之前都居住於此。這個極其私人的地方通常被稱為「未發現的大陸」以及「精神的家園」,並被自然景觀所美化。其他時候,這一景觀變得黑暗且令人生畏—城堡和監獄,到處充斥著走廊與房間──構造了一個「我」和「不同的我」共同居住的地方。一個把這些思想融為一體的例子為:我內心的自己—被放逐/經過裝飾/我的堡壘已無法攻破/直到所有的心──/可我──攻擊了自己/這怎麼辦/除了放棄──/我—屬於我?
認同

1880年,狄更生創作了詩歌(「消失的道路」),並將其寄給托馬斯•金森。
這首詩第一次被公佈於眾是在狄更生去世之後出版的詩集中。在金森的支持以及哈珀雜誌編輯威廉•迪安•豪厄爾斯為這首詩添加了激賞的注釋的情況下,這首詩在1980年首次出版後,大眾對此褒貶不一。金森在狄更生的詩集首次出版時,為其作序,他在序中寫道,這些詩「具有非凡的力量和見解」。曾任「獨立」雜誌文學編輯12年的莫里斯•湯普森,在1891年寫道,狄更生的詩歌是「難得的個性和獨創的混合物」。一些批評家熱情洋溢的稱頌狄更生的詩歌,但卻對其不同尋常的非傳統風格提出批評意見。英國作家安德魯•朗對狄更生的作品嗤之以鼻,他說道「詩歌存在之根本在於,它應該遵守一定的形式和語法,並且在該押韻的時候就得押韻。歲月的智慧和人類的天性也堅持該如此」。詩人兼小說家托馬斯•貝利•奧德爾里奇同樣對狄更生的是個提出了技術性批評,他在1892年1月的亞特蘭大月刊上寫道:「很明顯,狄更生女士擁有一種非傳統的怪誕的幻想。她深受布萊克的神秘主義以及艾默生過分獨特的風格的影響……但是她的不協調以及毫無章法可言的——姑且稱之為短句是災難性的……偏遠的新英格蘭鄉村(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古怪,夢幻般半隱居並不能使的她的那些違反常理的詩歌免收批評」。
1897年至1920年早期,評論界對狄更生的詩歌關注不足。直至20世紀初,對狄更生詩歌的關注變得廣泛起來,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狄更生的詩歌體現了現代詩的本質。現代評論家傾向於認為狄更生的那些毫無章法可言的詩句是自覺的藝術,而非缺乏只是和技巧的結果。伊莉莎白•謝普利•薩金特在1915年的一篇散文中將詩人的靈感稱為「富有冒險精神的」,並且稱詩人為「新英格蘭貧瘠的土地上開出的最珍貴的花朵」。隨著20世紀20年代現代詩的風行,狄更生的那些不遵循19世紀詩體的詩歌不再那麼驚世駭俗,並且被新一代的讀者所接受。狄更生突然間被評論家們稱為偉大的女詩人,她的詩歌也成為文學界競相熱捧的對象。R.P•布萊克莫曾經試圖總結和明確外界對於狄更生的評論,他在1973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文章中寫道:「……她是一個小我的作家,她不知疲倦的創作著,正如一些婦女不知疲倦的編織和烹調。她的語言天賦和他所處的時代都驅使著她進行詩歌創作和不是反屠殺……正如泰特先生所說,她處在那種先鋒的,古怪的詩歌創作的當年。」
第二輪婦女權運動使得作為女性詩人的狄更生受到了更多的文學方面的支持。從女性視角來看第一部收集了狄更生主要作品的文集的話,狄更生被認為是英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女詩人。以往的傳記作家和理論家們傾向於將狄更生女性的角色和其實人的角色分開。例如,1952年,喬治•惠徹在其《這是位詩人:埃米莉•狄更生的批判傳記》中寫道,「也許作為一位詩人【狄更生】可以彌補作為一個女人所不能得到的缺憾。」另一方面,女權主義的批評者認為狄更生作在為一個詩人和作為一個女人之間,存在著必要以及強有力的聯繫。阿德里安•瑞奇在「美國的維蘇威:埃米莉•狄更生的力量」(1976)一文中表示,狄更生女性詩人的身分帶給她力量,使得她「既不古怪,也不離奇;她註定會生存下來,運用她的力量,書寫她自己的「經濟學原理」。」同樣的,一些學者質疑狄更生的性傾向,他們引證埃米莉•狄更生寫給蘇珊•吉爾伯特•狄更生大量的詩歌和書信,暗示詩人有一段同性戀的感情,並且推論這段感情會對她的詩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諸如約翰•科迪,麗蓮•費得曼,薇薇安•R•波拉克,保拉•本內特,朱迪•法爾,艾倫•路易斯•哈特以及瑪莎•內爾•史密斯認為,蘇珊是狄金一生中情愛的中心。
評價
狄更生的詩集在1890年代面世時,普遍受到讀者的歡迎。[55]批評家大都承認狄更生的天才,但只把她看成「怪才」、「鬼才」、「偏才」(情況有點像中國的李賀),而非大詩人。狄更生的詩常常不押韻,格律不齊,被多數論者看作是「無能為力」,都覺得她才氣有餘,但詩藝還未到家。對於狄更生其人,只看作一個戀愛失敗、自我封閉的脆弱女子。
往後數十年,狄更生都保有讀者,但文學地位並沒有提高。到了現代派掘起,狄更生那種聲調不諧、句法支離的詩歌開始被看重,認為能夠代表現代人的感受。1950年代,首部未經竄改的狄更生詩全集出版,使人看到其詩的全貌、真貌,從此狄更生的文學地位被重新評估,已進入所謂「西方正典」。傳記作者也開始強調狄更生獨立、堅強的個性(不一定跟女性主義的興起有關),甚至有人稱狄更生為「阿默斯特的薩德侯爵」,[56]強調她個性中乖僻的一面。
曾在阿默斯特學院任教的詩人佛羅斯特(Robert Frost)談到狄更生的詩風:「她一落筆就是『我來了!』然後一頭跳進去,往往無暇照顧格律、韻腳。」(When she started a poem, it was 'Here I come!' and she came plunging through. The meter and rhyme often had to take care of itself.)[57]
錢鍾書談到一個狄更生詩中常見的主題:「……如願償欲必致失望生憎……美國女詩人埃米莉‧狄更生所謂『缺乏中生出豐裕來』(a sumptous Destitution)者是……眼饞滋慕,腹果乏味,其詩中長言永歎焉……」[58]
出版
生前

短詩《在他們的石膏房安然無恙》(Safe in their Alabaster Chambers –)被加上《睡眠》(The Sleeping)這個標題,於1862年在《斯普林菲爾德共和日報》上發表。
1858年至1868年間,狄更生有少量詩歌刊登在由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創辦的《斯普林菲爾德共和日報》上。這些作品刊出時並未署名,而且被大量修改,加上符合常規的標點和標題。其中的第一首詩《無人認識這枝小玫瑰》(Nobody knows this little rose),發表時可能未經狄更生本人同意。《共和日報》還發表了她的另外幾首詩,以《蛇》(The Snake)為題發表的《一位瘦長的君子在草地》(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以《睡眠》為題發表的《在他們的石膏房安然無恙》,以《日落》(Sunset)為題發表的《在金色中閃耀在紫色中熄滅》(Blazing in the Gold and quenching in Purple)。以詩歌《我品嘗未釀之酒》(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的改編版為例,第一節最後兩行為了押韻被完全改寫了。
原文: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
From Tankards scooped in Pearl –
Not all the Frankfort Berries
Yield such an Alcohol!
共和日報版本: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
From Tankards scooped in Pearl –
Not Frankfort Berries yield the sense
Such a delirious whirl!
1864年,狄更生的幾首詩歌被改編後發表在《擊鼓》上,用來籌集醫療資金,以支持戰爭(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聯邦軍隊。另有一首詩於同年四月發表在《布魯克林聯合日報》上。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希金斯將狄更生的詩歌推薦給海倫•亨特•傑克遜(Helen Hunt Jackson),巧合的是傑克遜年輕時曾與狄更生就讀同一所私立學校。當時傑克遜已經是出版界的資深人士,她說服狄更生將其詩歌《成功被認為最甜美》(Success is counted sweetest)不具名地發表在一個名為《詩人們的假面舞會》(The Masque of Poets)的系列作品中。然而,這首詩仍然被編者按照當時的審美觀作了修改。它也是狄更生在世時發表的最後一首詩。
列表
| 詩歌首行 | 出版者加的詩題 | 出版年分 | 附註 |
|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 A Valentine | 1852 | 一首夾雜拉丁文的諧詩 |
| Nobody knows this little rose | To Mrs.——, with a rose | 1858 | 此詩的出版,並沒有得到狄更生的首肯 |
|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 The May-Wine | 1861 | |
| Safe in their alabaster chambers | The Sleeping | 1862 | 狄更生對此詩作過多次修改,是她最有名的詩之一 |
| Flowers - Well - if anybody | Flowers | 1864 | |
| These are the days when birds came back | October | 1864 | |
| Some keep the Sabbath going to church | My Sabbath | 1864 | |
| Blazing in gold and quenching in purple | Sunset | 1864 | |
| Success is counted sweetest | Success | 1864, 1878 | 初次出版時沒有詩題 |
|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 The Snake | 1866 |
逝世後
狄更生逝世後,拉維尼婭•狄更生(Lavinia Dickinson)遵守諾言將狄更生的大部分書信焚毀。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狄更生將她的四十本詩稿和一些散佚的手稿封存在箱中,卻沒有留下任何指示。拉維尼婭認識到這些詩稿的價值並且一心期待著將其出版。她先是求助於她兄弟的妻子,後又轉向其情人梅布爾•盧米斯•托德(Mabel Loomis Todd)。經過一場紛爭,部分詩稿落入托德手中,致使狄更生的詩歌全集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才得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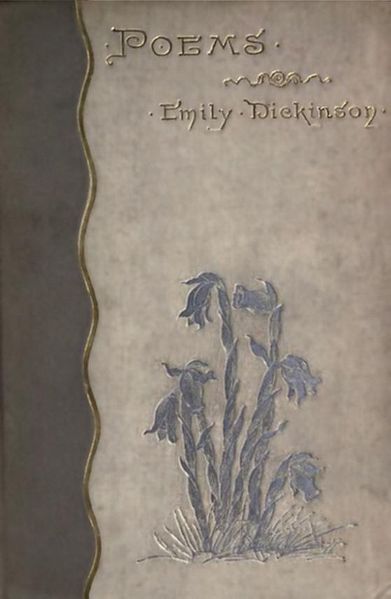
Poems第一版封面,1890年出版
由梅布爾•盧米斯•托德(Mabel Loomis Todd)和希金森(T. W. Higginson)共同主編的《狄更生詩集》第一輯與1890年11月出版。儘管托德聲稱只做了必要的改動,但大部分詩歌的標點和大寫字母部分都依照 19世紀晚期的標準作了修改,還做了少量措辭上的修改來減少狄更生的不規範用詞。最初出版的115首詩在評論界和市場銷售上都大獲成功,兩年內印刷了十一次。《狄更生詩集——第二輯》(Poems: Second Series)隨即於1892年出版,至1893年已再版五次;第三輯於1896年面市。1892年時評論如此寫道:「整個世界都撥不急待地期待著狄更生的所有作品的出版,她的文字,書信,她的一切文學作品。」兩年後,狄更生的兩部書信集出版,同樣被大量修改。同時,蘇珊•狄更生(Susan Dickinson)將狄更生的幾首詩歌發表在文學雜誌上,如《斯克裡布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和《獨立》(The Independent)。
1914年至1929年間,狄更生的侄女瑪莎•狄更生•比安奇(Martha Dickinson Bianchi)出版了一個新的系列詩集,其中包含了許多之前從未公開發表的詩歌,同樣對標點和大寫字母作了規範化的修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托德和比安奇編輯出版了另外幾卷詩集,逐漸地將更多先前未能發表的詩歌公開發行。
1955年,托馬斯•詹森(Thomas H. Johnson)主編的一個全新的三卷本詩集出版,這是第一個狄更生作品的學術性版本。它為狄更生及其作品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些詩歌首次以最接近狄更生原稿的方式印製出來。這些詩歌沒有標題,只是大致按照時間順序編了號,大量運用破折號和不規範的大寫字母,而且經常出現極其晦澀難懂的詞句。三年後詹森和多拉•沃德(Theodora Ward)共同編輯出版了完整的狄更生書信集。
其他專長
園藝
狄更生精通園藝,愛培植奇花異卉。學者朱迪•法爾指出:比起詩人,狄更生生前更多的是以園藝愛好者為人所知。[59]狄更生九歲的時候,開始與妹妹一起學習植物學並照管家中的花園。[59]她曾將壓花收集到一本66頁的皮製封面的標本集中。它包含了她收集,根據林奈體系分類並標記的424種壓花標本。[60]
狄更生大宅(Dickinson Homestead)內有她自己的花園,其父甚至特別為她興建了一個溫室。當時,其家庭花園在當地很有名,並得到了人們的讚賞。標本集沒有保存下來,狄更生沒有保留任何園藝筆記或是植物名錄,但是從其朋友及家人的信件與回憶中,人們可以清楚了解到這一情況。狄更生的侄女,瑪莎•狄更生•比安奇回憶道「鈴蘭、三色堇鋪成一條條地毯,一排排的甜豌豆、風信子,還只是三月,但蜜蜂採的蜜到夏天也吃不完。適逢花期,籬笆上纏滿的芍藥像是縷縷綵帶,另有大片黃水仙,大叢金盞菊讓人心馳神往。這簡直是蝴蝶的樂園。」[61]
特別的是,狄更生培育有香味的異國花朵,她寫道自己:「可以在餐廳與懸掛著盛放植物的籃子的暖房間種植香料群島上的香料」。狄更生常常送花束給朋友,附上詩句,但是「他們珍視花朵勝過詩句」。[61]
烹飪
狄更生也擅長烹飪,常用籃子將焗好的麵包、曲奇餅從她房間的窗子吊下,送贈鄰居、親友;1856年,她的麵包更在當地農業博覽會的比賽中取得二等獎。下面是她存世的薑餅食譜:[62]
一誇脫(美製)麵粉、二分一杯牛油、二分一杯奶油、一湯匙薑、一湯匙蘇打、一湯匙鹽,另加糖漿。
遺產

迪金森莊園今貌。2003年,它被改建成了艾米莉•迪金森博物館(Emily Dickinson Museum)。
參考資料
詩集、書信版本
Poems by Emily Dickinson. Ed. Mabel Loomis Todd and T.W. Higginson.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90).第一本狄更生詩集,經竄改(改成傳統的標點,也將少數詩歌改成押韻)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Ed. Thomas H. Johns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55).首部未經竄改的狄更生詩全集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including variant readings critically compared with all known manuscripts. Ed. Thomas H. Johns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58).三卷本詩全集,連異文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Ed. Thomas H. Johnson and Theodora War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58).三卷本的書信集
The Manuscript Books of Emily Dickinson. Ed. R.W. Frank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81).手稿影印本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Variorum Edition. Ed. R.W. Frank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98).較新的異文版本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Ed. R.W. Frank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99).較新的詩全集,部分詩歌經重新編年
Open Me Carefully: Emily Dickinson's Intimate Letters to Susan Huntington Dickinson. Ed. Ellen Louise Hart and Martha Nell Smith. (Ashfield, MA: Paris Press, 1998).致蘇珊的書信,部分書信依照原稿的文字排列來排印
評論、傳記
M. T. Bingham. This Was a Poe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早期狄更生傳記的代表作
Charles R. Anderson.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Stairway Of Suspense.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1960).
Richard B. Sewall. The Life of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4).較詳細的傳記
Cristanne Miller. Emily Dickinson: A Poet's Grammar. (Harvard UP, 1989).
Judith Farr with a chapter by Louise Carter. The Gardens of Emily Dickinson. (Harvard UP, 2004).有關狄更生的園藝與其詩歌的關係
外部連接
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艾彌莉‧迪更生
網上版詩全集
狄更生國際學會
注釋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84%E9%87%91%E6%A3%AE
狄更生(Emily Dickinson)詩選


狄更生(1830-1886),20歲開始寫詩,早期的詩大都已散失。1858年後閉門不出,70年代後幾乎不出房門,文學史上稱她為“阿默斯特的女尼”。她在孤獨中埋頭寫詩,留下詩稿 1,775首。在她生前只有 7首詩被朋友從她的信件中抄錄出發表。她的詩在形式上富於獨創性,大多使用17世紀英國宗教聖歌作者以撒•沃茨的傳統格律形式,但又作了許多變化,例如在詩句中使用許多短破折號,既可代替標點,又使正常的抑揚格音步節奏產生突兀的起伏跳動。她的詩大多押半韻。狄更生於1886年 5月15日逝世。她的親友曾選編她的遺詩,于19世紀末印出 3集,但逐漸為人忘卻。直到美國現代詩興起,她才作為現代詩的先驅者得到熱烈歡迎,對她的研究成了美國現代文學批評中的熱門。
這是鳥兒們回來的日子
這是鳥兒們回來的日子——
零零落落——一隻或兩隻——
仿佛是依依不捨。
這是天空重新明亮的日子——
似乎六月的魔術未曾離去——
蕩漾著藍色和金色。
你的詭詐不可能瞞過蜜蜂——
但你這逼真的障眼法
幾乎讓我深信不疑。
甚至那些種子都在為你作證——
趁著暖意,溫柔地送出
一片怯生生的葉子。
啊,繁華夏日的美麗慶典,
啊,秋日霧靄裡的最後聖餐——
請牽住一個孩子的手。
讓她分享你神聖的符號——
讓她領受你神聖的麵包
和你永生的葡萄酒!
(靈石 譯)
風暴之夜——激情之夜!
風暴之夜——激情之夜!
若能和你一起
風暴之夜就會讓我們
沉醉無極!
風,徒然地呼嘯——
心,已在港口的懷抱——
指南針,不需要——
航海圖,不需要!
劃槳,在伊甸園——
啊,海的起伏!
要是我能停泊——今夜——
在你的深處!
(靈石 譯)
我覺得腦子裡有一場葬禮
我覺得腦子裡有一場葬禮,
往來的悼念者腳步雜遝,
踩啊——踩啊——到了後來
所有感覺仿佛慢慢坍塌——
等到所有客人都已就坐,
儀式開始了,像有一面鼓——
敲啊——敲啊——到了後來
我的心仿佛已漸漸麻木——
接著我聽到他們扛起棺材,
在我的靈魂裡緩緩穿行,
那些鉛做的靴子吱嘎作響,
然後,空間裡灌滿了鐘聲——
仿佛一切星球都變成了喪鐘,
存在本身淪為了一隻耳朵,
而我,還有某種詭譎的寂靜
卻在這裡面,痛苦,落寞——
然後,意識裡的木板突然斷裂,
我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往下掉——
掉一層就撞上一個新的世界,
然後,我就不再知曉——然後——
(靈石 譯)
至少——還可以——還可以——禱告——
至少——還可以——還可以——禱告——
啊,耶穌——在縹緲的空中——
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間屋子——
我四處敲著門——一片迷茫——
你喚起了地震,在南國——
喚起了漩渦,在海洋——
說啊,拿撒勒的耶穌基督——
難道你沒有伸向我的臂膀?
(靈石 譯)
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
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
那將是生命本身——
而生命在那邊——
櫥櫃的後面——
鑰匙在教堂司事的手裡——
他把我倆的生命——
他的瓷器——放在高處——
像一隻茶瓶——
被主婦棄置——
模樣古怪——或是有些殘缺——
新的法國餐具更討人歡心——
舊的那些遲早會碎裂——
我不能死去——和你一起——
因為我倆必須有一人——
等著合上另一人的眼睛——
你——不能——
而我——我能忍心在一旁——
看著你——慢慢凍僵——
我自己卻得不到死神的恩賜——
領受他的寒霜——
我也不能復活——和你一起——
因為你的面容——
將會蓋過耶穌的面容——
那種新的光芒——
將清晰——而陌生地——
照在我懷鄉的眼睛上——
只不過是你,而不是他——
閃耀在我身旁——
他們會審判我們——怎樣——
因為你——曾是天堂的僕人——
你知道——或者那是你的願望——
我,不能——
你佔據了我的一切視覺——
我沒有多餘的眼睛——
不會把污穢的神聖——
當作樂園的風景——
如果你下地獄,我也去——
即使我的名字——
響亮地在天堂回蕩——
尊榮無比——
如果你——被神拯救——
而我——卻受咒詛——
必須去沒有你的地方——
那我自己——就是我的地獄——
所以,我倆只能望著對方——
你那裡——我——這裡——
隔著一扇虛掩的門——
海一樣深——只剩禱告——
和那白色的食糧——
絕望——
(靈石 譯)
因為我不能等待死亡——
因為我不能等待死亡——
他體貼地停下來等我——
馬車只載著我們兩個——
還有永生。
我們慢慢行進——他從不著急
我放下了我的工作,
我的閒暇,
為了他的善意。
我們路過學校,孩子們
在操場上——遊戲——
我們路過凝視的麥田——
我們路過西沉的落日——
毋寧說,落日路過我們——
露水讓我直打寒顫——
我只穿了一件絲衣——
和薄紗的披肩——
我們在一間房子前停下
像是地上的小丘——
屋頂幾乎看不見——
泥土——快蓋過了簷口——
許多世紀——過去了——可是——
感覺比一天還短——
我這才懷疑我們到達的
是無限的時間——
(靈石 譯)
說出全部真理,但別太直接——
說出全部真理,但別太直接——
迂回的路才引向終點
真理的驚喜太明亮,太強烈
我們不敢和它面對面
就像雷聲中惶恐不安的孩子
需要溫和安慰的話
真理的光也只能慢慢地透射
否則人人都會變瞎——
(靈石 譯)
沒有一朵快樂的花
沒有一朵快樂的花
似乎感到任何驚詫
寒霜讓它們屍首分離——
權力的無心遊戲——
金色的殺手無動於衷——
太陽依然穿行在天空,
為許可這一切的上帝
量度著又一個日子。
(靈石 譯)
我的生命曾兩度終止
我的生命曾兩度終止,
在終止之前;它仍在等待,
看第三次苦難的秘密
是否會被時間的手揭開。
如此巨大,如此難於想像,
就像曾經的兩次,令我昏厥。
我們只能一次次告別天堂,
一次次夢想著與地獄告別。
(靈石 譯)
最淒涼的聲音,最甜蜜的聲音
最淒涼的聲音,最甜蜜的聲音,
最瘋狂的聲音,越來越清晰——
那是春天鳥兒們的歌唱,
在那美麗的時刻,當夜將消逝。
在三月和四月之間——
一旦越過那奇妙的邊界,
猶疑的夏天就像天堂一樣,
幾乎伸手便可採擷。
它讓我們想起所有的死者,
他們曾和我們在此漫步,
彼此隔絕,卻更加渴念,
這是別離的殘忍法術。
它讓我們想起曾擁有的一切,
現在卻只剩下感傷的回憶。
我們幾乎希望這些可愛的塞壬
能遠遠飛走,留一片靜寂。
耳朵也能刺穿一顆心,
就像長矛一樣迅速,
但願世間沒有一顆心
與危險的耳朵比鄰而居。
(靈石 譯)
夏之逃逸
不知不覺地,有如憂傷,
夏日竟然消逝了,
如此地難以覺察,簡直
不像是有意潛逃。
向晚的微光很早便開始,
沉澱出一片寂靜,
不然便是消瘦的四野
將下午深深幽禁。
黃昏比往日來得更早,
清晨的光彩已陌生——
一種拘禮而惱人的風度,
像即欲離開的客人。
就像如此,也不用翅膀,
也不勞小舟相送,
我們的夏日輕逸地逃去,
沒入了美的境中。
餘光中譯
蟲鳴
在夏日眾禽的啁啾之外,
悽楚地起自草底,
有一個較小的國度舉行
它那寧靜的贊禮。
我看不見有任何儀式,
禱詞是如此舒緩,
它要變成一種沉思的風俗,
擴大了寂寞之感。
日午時最感到了古意悠揚,
當八月焚燒了殘燼,
遂喚起這幽靈似的音樂,
作為安息的象徵。
迄今盛況猶未見減色,
光彩也未顯皺紋,
但是一種神奇的變化,
已侵入自然本身。
餘光中譯
某個陽光斜射的時刻
某個陽光斜射的時刻
在冬日的下午——
讓人抑鬱,像沉重的
教堂的旋律——
玄妙地傷害我們——
沒有任何傷口和血跡
卻在意義隱居的深處
留下記憶——
沒有人能夠傳達——任何人——
它是絕望的印章——
不可抗拒的折磨
來自虛空——
當它來時,一切都側耳傾聽——
影子——屏住了呼吸
當它去時,就像死神臉上
遙遠的謎——
靈石 譯
我從來沒覺得這是家——
我從來沒覺得這是家——
在這塵世——在美麗的天空
我也不會自在——我知道——
我不喜歡樂園——
因為那兒是星期天——永遠都是
休憩的時刻——從不降臨——
伊甸園會多麼冷寂
在明媚的星期三下午——
如果上帝也會外出——
或者打盹兒——
這樣就看不見我們——然而他們說——
他自己——就是一部望遠鏡
千萬年地監視著我們——
我就會逃亡,遠遠地
離開他——和聖靈——和一切——
可是還有“最後審判日”!
靈石 譯
我聽到蒼蠅的嗡嗡聲——當我死時
我聽到蒼蠅的嗡嗡聲——當我死時
房間裡,一片沉寂
就像空氣突然平靜下來——
在風暴的間隙
注視我的眼睛——淚水已經流盡——
我的呼吸正漸漸變緊
等待最後的時刻——上帝在房間裡
現身的時刻——降臨
我已經簽好遺囑——分掉了
我所有可以分掉的
東西——然後我就看見了
一隻蒼蠅——
藍色的——微妙起伏的嗡嗡聲
在我——和光——之間
然後窗戶關閉——然後
我眼前漆黑一片——
靈石 譯
但願我是,你的夏季
但願我是,你的夏季,
當夏季的日子插翅飛去!
我依舊是你耳邊的音樂,
當夜鶯和黃鸝精疲力竭。
為你開花,逃出墓地,
讓我的花開得成行成列!
請採擷我吧—秋牡丹——
你的花—永遠是你的!
江楓 譯
有人說,有一個字
有人說,有一個字
一經說出,也就
死去。
我卻說,它的生命
從那一天起
才開始。
江楓 譯
愛,先於生命
愛,先於生命
後於,死亡
是創造的起點
世界的原型
如果記住就是忘卻
如果記住就是忘卻
我將不再回憶,
如果忘卻就是記住
我多麼接近於忘卻。
如果相思,是娛樂,
而哀悼,是喜悅,
那些手指何等歡快,今天,
採擷到了這些。
江楓 譯
心啊,我們把他忘記
心啊,我們把他忘記!
我和你——今夜!
你可以忘掉他給的溫暖——
我要把光忘卻!
當你忘畢,請給個信息,
好讓我立即開始!
快!免得當你遷延——
我又把他想起!
我們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們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們有一份黎明—
我們有一份歡樂的空白要填充—
我們有一份憎恨—
這裡一顆星那裡一顆星,
有些,迷了方向!
這裡一團霧那裡一團霧,
然後,陽光!
江楓 譯
為什麼,他把我關在天堂門外
為什麼,他把我關在天堂門外?
是我唱得,歌聲太高?
但是,我也能降低音調
畏怯有如小鳥!
但願天使們能讓我再試一試——
僅僅,試這一次——
僅僅,看我,是否打攪他們——
卻不要,把門緊閉!
哦,如果我是那一位
穿“白袍”的紳士——
他們,是那敲門的,小手——
我是否會禁止?
江楓 譯
如果你能在秋季來到
如果你能在秋季來到,
我會用撣子把夏季撣掉,
一半輕蔑,一半含笑,
象管家婦把蒼蠅趕跑。
如果一年後能夠見你,
我將把月份纏繞成團——
分別存放在不同的抽屜,
免得,混淆了日期——
如果只耽擱幾個世紀,
我會用我的手算計——
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
全部倒伏在亡人國裡。
如果確知,聚會在生命——
你的和我的生命,結束時——
我願意把生命拋棄——
如同拋棄一片果皮——
但是現在難以確知
相隔還有多長時日——
這狀況刺痛我有如妖蜂——
秘而不宣,是那毒刺。
江楓 譯
美,不能造作,它自生
美,不能造作,它自生——
刻意追求,便消失——
聽任自然,它留存——
當清風吹過草地——
風的手指把草地撫弄——
要追趕上綠色波紋——
上帝會設法制止——
使你,永不能完成——
江楓 譯
你無法撲滅一種火
你無法撲滅一種火——
有一種能夠發火之物
能夠自燃,無需人點——
當漫長的黑夜剛過——
你無法把洪水包裹起來——
放在一個抽屜裡邊——
因為風會把它找到——
再告訴你的松木地板——
江楓 譯
我一直在愛
我一直在愛
我可以向你證明
直到我開始愛
我從未活得充分——
我將永遠愛下去
也可以向你論證
愛就是生命
生命有不休的特性
如果,親愛的,
對此也抱懷疑
我就無從舉證,
除了,骷髏地——
江楓 譯
詩人,照我算計
詩人,照我算計——
該列第一,然後,太陽——
然後,夏季,然後,上帝的天堂——
在就是全部名單——
但是,再看一遍,第一
似已包括全體——
其餘,都不必出現——
所以我寫,詩人,一切——
他們的夏季,常年留駐——
他們給得出的太陽——
東方會認為奢侈——
如果,那更遠的天堂——
象他們為他們的崇拜者
是準備的那樣美
在情理上就太難證明——
有必要為做夢而入睡——
江楓 譯
我們曾在一個夏季結婚
我們曾在一個夏季結婚,親愛的——
你最美的時刻,在六月——
在你短促的壽命結束以後——
我對我的,也感到厭倦——
在黑夜裡被你趕上——
你讓我躺下——
一旁有人手持燭火——
我,也接受超度亡魂的祝福。
是的,我們的未來不同——
你的茅屋面向太陽——
我的四周,必然是——
海洋,和北方——
是的,你的園花首先開放——
而我的,播種在嚴寒——
然而有一個夏季我們曾是女王——
但是你,在六月加冕——
江楓 譯
頭腦,比天空遼闊
頭腦,比天空遼闊——
因為,把他們放在一起——
一個能包含另一個
輕易,而且,還能容你——
頭腦,比海洋更深——
因為,對比他們,藍對藍——
一個能吸收另一個
象水桶,也象,海綿——
頭腦,和上帝相等——
因為,稱一稱,一磅對一磅——
他們,如果有區別——
就象音節,不同於音響——
江楓 譯
http://www.shigeku.org/shiku/ws/wg/dickinson.htm
林德爾戈登對艾米麗狄金森的終極解讀 2011-02-20
我的生命是一支上了膛的槍:艾米麗-迪金遜的家族糾葛 作者:林德爾-戈登
近200多年,艾米麗-狄金森來一直是個迷。她生性孤僻避世,在她度過一生的家鄉麻塞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鎮子上的人們都稱她為“謎團”,仿佛她是否存在過都是個問題。沒幾個人見過她一身白衣的身影——成年的她只穿白色的衣服——她生平只發表過10首詩。1886年她去世以後,人們在一個木匣子中發現了她成百上千的詩作,一個新的傳奇就這樣誕生了,她那病態的甜美對於這個世界太過脆弱,這使得她對愛情心灰意冷。
然而艾米麗的神秘詩總是與甜美相去甚遠。詩中令人咋舌的暴力色彩和奇怪的停頓——也就是作為狄金森商標式的標點破折號——似乎暗示著一個秘密, 既準確無疑又不可捉摸。艾米麗的思想正進行一些變化,“我的腦海中有一場葬禮”像是火山爆發般的“劇痛”。“我的生命是一支上了膛的槍”這本書2月份在英國出版現在美國相繼發行,作者林德爾-戈登是出生于南非的文學傳記作家和學者,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頗令人信服的新的證據,解釋了詩人與世隔絕背後一個與傷感主義無關的原因:在她的詩中那個神秘的“它”是先天性癲癇這種病,她的堂妹和外甥也經受著一樣的病痛折磨,在19世紀,患有癲癇被視為是一種恥辱。
大家公認狄金森受到某種疾病的折磨,戈登女士展示了醫生給狄金森的治療癲癇發作的藥方。這位詩人很少出門,因為癲癇很可能隨時發作。她放棄正常生活而過得像個修女一般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關,在美國,有些州禁止癲癇患者結婚。
似乎狄金森的詩中那些神秘的頓悟與超驗的體驗是來源於她的疾病這一事實。可是癲癇並不是她創作和反傳統的觀念的所有來源。她思想的驚人的獨立早在犯病前就形成了,在她小的時候,她拒絕向奮興運動的宗教同齡人卑躬屈膝。詩歌成為她應對萬變的方法,幫助她與少數分享她的作品的人之間交流經驗。
如果詩人那聞名的靈性實際上植根於她的肉體,那麼,如戈登女士所揭示的,她的家庭生活,也是由肉欲所支配,而且遠遠出乎人們一貫的猜測。虔誠、受人尊敬且睿智的狄金森一家人在阿姆赫斯特是首屈一指的大族。但是深鎖的庭院後,正演繹著一場放縱不羈的性欲和遺毒不淺的通姦之故事,這將對詩人死後的名譽有很大的影響。
艾米麗-狄金森和未婚的妹妹拉維尼亞住在一座優雅的叫做霍姆斯特德的宅子裡。 住在隔壁Evergreens的是她的哥哥奧斯丁一家;她的妻子Sue是艾米麗的閨中密友,艾米麗把自己寫的大部分詩都寄給她看。但是他們相對平靜的生活卻因為一個年輕的教員的妻子瑪佩爾-陶德的到來而被摧毀。瑪佩爾擅長音樂和美術,而且野心勃勃冷酷無情,她處心積慮地融入了誒迷離艾米麗的生活。1882年,她與艾米麗的哥哥奧斯丁開始暗度陳倉,為了確保陶德先生的默許,艾米麗的哥哥答應促進他學術事業發展。這對情人認為他們之間的愛情是如此的特別以至於常規對他們來說並不適用。而被他哥哥拋棄的妻子Sue十分的悲傷,因而發生的家族仇恨纏繞了幾代人。
對於瑪佩爾來說,佔有奧斯丁是不夠的。她還想得到這個遁世的天才艾米麗。令人驚訝的是,她從未與艾米麗碰面,因為每一次瑪佩爾到霍姆斯特德來時,艾米麗就會溜走。這樣的事情頻頻發生,這對情人每次都在在客廳約會,在黑色的馬鬃沙發上纏綿2、3個小時。艾米麗被迫離開她習慣寫作的房間,躲到樓上去,樓下發生的事情她總是聽的一清二楚。瑪佩爾的後代宣揚他與奧斯丁之間美麗的羅曼史,但對於艾米麗的耳朵來時,那是在算不上是崇高的愛情。她一直躲著瑪佩爾,但是她的詩歌和筆記處處提到莎士比亞悲劇中那種毀滅性的性愛迷戀。
瑪佩爾成功的毀掉了狄金森家。但是諷刺的是,她是艾米麗一生中為數不多肯定她創作和智慧的人之一。艾米麗去世後,瑪佩爾下定決心要讓世人讀一讀艾米麗的詩,並且致力於編輯、出版和推銷那些詩歌。在此過程中,她壓抑了一些詩歌的獨創性,將艾米麗奇怪的斷句修改的符合傳統認識。她還杜撰了一個多愁善感的神話般的女詩人及其生平,而在戈登女士的這本傳記裡,那些謊言都被戳破了。
對於一個文學傳記作家來說,重新改寫一個被人們所熟知的詩人的歷史並不多見。這本用常識與憐憫著成的驚世駭俗的書,在未來幾年,對於人們認識狄金森是一次革命性的貢獻。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658747/
為詩而生 2011-02-28
艾米莉•狄金森與惠特曼被稱為美國詩壇的雙子星,幾乎在任何一部美國詩文選集中,她的詩都佔有顯著的地位。她生前卻默默無聞,大部分時間在麻薩諸塞州的艾默斯特小鎮閉門獨居。她20歲左右開始寫詩,到五十六歲去世寫了近一千八百首,生前只有十首發表。
她的詩追求簡煉、生動、準確,用最少的詞彙表達最真實的情感、最迅捷的想像。她總是把尖銳的措辭建立在一種堅固的形式之上。這種形式就是四行一組,單行八音節,雙行六音節的長短句,此形式之於詩就像道德之於她的生活,不僅左右了她的靈感,還疏導她的心境,只要能自如地運用這種形式,她就牢牢操住生活的舵。那些脫離了形式的詩不是她內心受到強烈的顛簸,就是情感上急需一些放縱。
這個四百頁的譯本中容納其中的六百多首,只占她全集的三分之一,但已經像一個袖珍的書櫃。譯者在編輯方面下了一翻功夫,把狄金森的詩分為七個集合:“人生”“自然”“愛情”“永恆”“靈魂、心理”“信仰”“文藝”。這種編輯方法雖然給詩的主題作了清晰的分類,卻打亂了狄金森小姐生命的韻律,只是幸好保留了詩作的年代和編號,使讀者仍能識別出詩中的生命軌跡。
狄金森小姐仿佛是一個為詩而生的人,靈感還沒出現的時候,詩已在她心裡等候其光臨,1862年她一共寫了三百多首詩,平均每天一首,她如此密集的寫詩,使她的詩集就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從一首詩到另一首詩就像一個波浪引出另一個波浪。波浪之下就是她生活的河床,隨著人生季節的更迭,河面上卷走的落花變成了枯葉,再往後,河床漸趨寬廣,河面也平靜下來,當生命之光逐漸暗淡,死亡之夜來臨,河面就只映出高山和群星這些永恆之物的倒影了。
愛情是狄金森小姐一生不滅的主題。她開始寫詩的時候,正是她人生中的浪漫的愛情季節,所以她是那麼熱愛生活以及那些生活的體驗,她精心地收集聚攏,又用火熱的愛情把它們澆鑄成自己敏感、多情、優雅、驕傲的靈魂。但是隨著愛情的破滅,這個靈魂也像青銅一樣凝固了,那些四處洋溢的激情,被死亡和永恆的沉思所取代,詩意冷峻而剛烈,愛情雖已成空,但仍像倒掛在希望之顛的大鐘,餘音繚繞連綿不絕:/愛開始之日,便是愛結束之時,/聖賢有言。/但是聖賢可知?/真理將你的恩惠延期,/沒有時限。/
由於狄金森在生活中深居簡出,她有兩種特殊的觀察方式,有時候她的觀察極其專注而集中就像要上足勁的時鐘,然後她就可以巧妙地把時間揉進詩意,讓語句在紙面上像噝噝的發條一樣放鬆:
我來告訴你太陽如何升起——
某一時刻只是絲帶一條——
一群尖塔游泳在紫水晶裡——
消息,像松鼠奔向四方——
群山鬆開了自己的帽子——
長刺歌雀開始——登場——
此時此刻我柔聲自語——
“那必定就是太陽!”
另一種情況,她以一種超然的心態遠遠地觀看世俗百相,把這些喧鬧寫得異常靜謐,就像精采的無聲電影:
對面房子裡,近在今天,
有人死亡——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
那些房子總有那種麻木的——面相——
鄰居們進進出出——醫生——架車離去——
一扇窗戶像豆莢般蹦開——
冷不丁——如同機器——
有人扔出一張床墊——
孩子們急忙跑掉——
心裡納悶是否有人就死在——那上面——
我小時候——見過不少——
牧師——僵硬地走了進去——
仿佛那房子就是他的——
他擁有了所有的弔喪者——現在——
而且——還有那些男孩子——
然後就是女帽商人——還有那嚇人的行業的員工——
來估量那座房子的情況——
然後就會有黑色的遊行——
有流蘇——有馬車——很快——
在一個鄉村小鎮——
對這種消息的直覺——
就像招牌一樣從容——
狄金森小姐的詩不好翻譯,英語的詞音節不等,組織在句子中具有自己獨特的韻律。翻成漢語以後,一個詞對應另一個詞,音節數不能全都相等,原詩的韻律譯不來,詩的形式也不再那麼嚴整,變成了自由體。不過,本書譯者蒲隆先生儘量遵重其形式,使其中的長短句的節奏還保留其痕跡。只是譯作由於過於追求簡捷或為了湊音步的目的使語句有點踉蹌跌撞,對原作的典雅從容有所損失。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712777/
江楓:艾米莉•狄金森——美國詩歌的新紀元 《中華讀書報》第328期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於1830年12月10日將近午夜出生在美國麻塞諸塞州當時還是個小鎮的艾默斯特。到1886年5月15日黃昏在昏迷中離去,她已給人間留下了自成一格、獨放異彩、數量可觀的篇什。而在她有生之年,公開發表過的詩作只有12首。
除了20世紀30年代由於評論界的派別之見一度有過分歧之外,狄金森作為對美國文學作出了重大獨創性貢獻的偉大詩人地位已經牢固確立。有人斷言,她是自西元前7世紀古希臘薩福以來西方最傑出的女詩人;有人就駕馭語言的能力和對人性的探究而言,甚至把她與莎士比亞和但丁相提並論。由於詩作被譯成了各種文字,狄金森可以說是世界上影響最大、擁有讀者和研究者最多的女詩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
她的詩作,和惠特曼的一樣,已被公認為標誌著美國詩歌新紀元的里程碑。他們對詩歌的傳統規範都表現了不馴的姿態。有人說,“惠特曼和狄金森寫詩,都好像從不曾有人寫過詩似的。”但是他們風格迥異,各趨一極。惠特曼的藝術境界是宏觀的、外向的;狄金森則傾向於微觀、內省。如果能用“豪放”表述惠特曼詩風的主要特徵,也許可以說狄金森的藝術氣質近乎“婉約”。
他們所處的時代,在社會思想上是清教主義影響日趨衰微而餘威猶在,文藝領域內後期浪漫主義已經氣息奄奄卻又無以為繼,但是在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統治,加強了中央權力,並且在經濟上解除了蓄奴制枷鎖,工商業得以迅猛發展,甚至,已經開始向外擴張,日益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一種新的民族感情已經覺醒,而且正在加強。在文化上認為舊大陸月亮比新大陸月亮圓的時代也在成為過去,曾經作為前宗主國英國文學支流而存在的美國文學,現在,強烈要求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特徵,總之,要求有自己的個性。
狄金森和惠特曼在思想感情上,都和時代精神相通。詩,在美國,從什麼時候獲得“現代”面貌,從什麼時候有了美國氣派?這兩位詩人,是並立的分水嶺。
從20歲起,她已經在寫詩。1862年,她32歲那一年,為了寫詩而寫信求教于湯瑪斯•溫特沃斯•希金森。但是希金森不是發現新星的伯樂。對於她的詩,他建議“推遲發表”。而她,竟把發表推遲到了身後。
詩如其人;詩,即其人。狄金森的詩充分反映了她的獨特個性。但是,只有個性,既不會有詩,也不會有詩人。詩的創作源泉,只能來自生活。狄金森自有狄金森的生活,雖然閱歷不廣,但是體驗較深;雖然曾被接觸不多的部分人稱為“修女”,卻除了終身未嫁和不曾生育,像任何一個正常的女性,也嘗味過愛的甜蜜和酸辛。經過狄金森學者細緻入微的研究,加上她自己措辭隱晦卻仍可解讀的詩篇,她的感情生活已無隱私可言。她告訴我們:
我啜飲過生活的芳醇 —
付出了什麼,告訴你吧 —
不多不少,整整一生 —
她寫愛的萌動、愛的燃燒、愛的消失,有甜而不膩的喜悅、熾烈而蘊藉的吐露、苦而不酸的沉痛、綿綿難絕的長恨。愛,是她詩歌題材的重心,寫來清新、別致。例如《“為什麼我愛”你,先生》,她甚至能夠寫出難得有幾個女詩人寫得出的一個女人只能意會的感受: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靈魂
像琴師撫弄琴鍵
然後,正式奏樂 —
他使你逐漸暈眩 —
使你脆弱的心靈準備好
迎接那神奇的一擊 —
以隱約的敲叩,由遠而近 —
然後,十分徐緩,容你
有時間,舒一口氣 —
你的頭腦,泛起清涼的泡 —
再發出,莊嚴的,一聲,霹靂 —
把你赤裸靈魂的頭皮,剝掉 —
颶風的指掌抱握住森林 —
整個宇宙,一派寧靜 —
她熱愛自然,寫自然如寫家園,她對自然界的一切“住戶”,“叢林中美麗的居民”無不滿懷親切柔情,而且觀察仔細,常有精緻入微、準確生動的真切描繪。她堅持真實,對真實有一種不妥協的忠誠。她確信:“真與美是一體”。有些平凡的景象在她筆下寫來,時而驚心動魄,時而悅目怡神。其魅力就在於總能使人感受到一種無可置疑、確實存在,卻又是從不曾被意識到的美。日出,是像宇宙本身一樣古老的題材,她卻寫得仿佛是嶄新的最新發現,而且,有極其濃郁的“現代”感:
太陽出來了
它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
車輛來去匆匆,像報信的使者
昨天已經古老!
她愛生活和生命,她試圖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地探索、解釋和表達生的意義。她的詩裡還有引人注目的大量死亡,因為在她所接觸的狹小天地裡,有許多親友鄰人由於疾病、戰爭(內戰和外戰)或貧困,先她而相繼凋零。和死神打交道多了,以致連死也使她覺得“彬彬有禮”,而且“親切”。由於人世間有比死更可怕、更難忍受的事,所以,她並不畏死。
她寫死亡,不同凡響,尤其和流行的感傷濫調大異其趣。既然生開始,死也就開始,她“並不害怕知道”,她視死如歸。1886年5月她臨終前留給兩個“小表妹”的最後一封遺書,只寫了兩個詞構成的短促的一句:“歸”(Called back)。—— 今天,我們在艾默斯特西墓園狄金森墓碑上看到的就只有她的“生年”、“歸年”,而沒有“卒年”。
她的死亡詩很有點一生死、齊彭殤的味道,卻又不完全是,因為她雖不畏死,卻更眷戀生活,一想到生活,就使她“心醉神迷”。她寫死亡,甚至寫死後的“體驗”,往往是幽默和詼諧壓倒了感傷。
她的思辨能力和想像力一樣強,她寫哲理,精闢深邃,耐人尋味,警句連篇。她主張:
要說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說
成功之道,在迂回
……
真理的強光必須逐漸釋放,
否則,人們會失明 —
一般情況下,她的理念總是帶有可感知的特徵,總是以有尺寸、有音響、有色彩、有質感的形體出現。例如:“希望是個有羽毛的東西”,會飛,會唱,有體溫,棲息在人們心底。但也有些詩,幾乎就是赤裸的理念本體。在這類詩中,有更可愛、更耐人咀嚼的:
籬笆那邊 —
有草莓,長著 —
我知道,如果我願 —
我可以爬過 —
草莓,真甜!
可是,髒了圍裙 —
上帝一定要罵我!
哦,親愛的,我猜,如果他也是個孩子 —
他也會爬過去,如果,他能爬過!
另一類,談得較多的是上帝、天堂、永恆、不朽和信仰。這固然是她自身文化背景的某種反映——她畢竟是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下成長起來的;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她常常是借宗教聖壇上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用《聖經》的詞彙和傳教士的口吻發表她對人生的觀感。
她追求“活的”、“能呼吸”、“有生命”的詩。從什麼時候起,她決心寫這樣的詩,立志當這樣的詩人,準確的年月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1862年是她創作欲最旺盛的一年,這一年她寫了366首。她棄絕社交的理由,除了與愛情受挫有關,至少有一個,是為了寫詩。通讀全集,不能不讚歎她在有限天地裡的廣闊視野。她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直接經驗,她接觸到和接觸過的一切,她無不採擷入詩。家務勞動可以提供素材,學校生活是另一個源泉,以至她會寫出上帝“在天上那漂亮的教室裡”之類的句子。她以豐富的書本知識和特異的想像力來彌補閱歷:
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隻蜂,
一株苜蓿,一隻蜂,
再加上白日夢。
有白日夢也就夠了,
如果找不到蜂。
她的視線並未局限於她自我禁閉的象牙之塔和狹隘的自我探索。雖然應該承認,她果然是描繪靈魂世界風景畫的丹青妙手:人類靈魂裡應有的,她的筆下幾乎盡有。通過閱讀報刊,她也關懷家院以外的天地,而不乏刺時之作。她曾在一封信裡寫道:“請原諒我在一個瘋狂世界裡的清醒”。
她抨擊“議會是根沒有骨髓的骨頭”;她嘲諷“真知灼見”服從“僵化的癡癲”。她也關心國家命運,甚至議論國際糾紛。她有一首詩譏評“大不列顛不喜歡那些星星”。
狄金森的創作盛期恰與南北戰爭同時,有800首是在這場以廢除蓄奴制告終的內戰進行期間寫成的。她沒有正面寫她不熟悉的戰爭,但也不回避戰爭。“成功的滋味最甜”、“勝利到來已晚”,顯然有戰火的烙印。
狄金森之所以會被她死後將近30年才出現的意象派詩人視為先驅,是因為她的詩,應該說是到那時已經公開發表的那一部分,較之意象派共同信條起草人的作品更符合他們的信條。她的詩,如前所述,大多使用意象語言。她所塑造的意象,有一部分,可以認為堅實而清晰,較之後來一些意象派詩人完全排斥理念的“意象”更有深度而且豐滿。狄金森和惠特曼,上承浪漫主義餘緒,在他們不少作品中的表現毋庸諱言;下開現代主義先河,已經得到一致公認。
到1998年R•W•佛蘭克林經過進一步的編年考證編訂的《艾米莉•狄金森詩集》問世,人們所知的狄金森詩,共有1789 首。而所增加的數量,並不是1789首與1775首之間的簡單差額,而是由於佛蘭克林根據自己的考證,把他認為以前是拼接錯了的拆開,把誤收的剔除,未收的收入。
我們現在知道,狄金森曾有“艾默斯特修女”之稱,只是部分人的片面印象和個別人的渲染,像她妹妹一樣,錯過了婚嫁好芳華,都是由於父親太愛女兒,看不上登門求婚的年輕人,姐妹倆終老獨身,卻並未妨礙她們體驗正常女人所能體驗的全部生命過程。1932年,艾米莉的侄女瑪莎在《面對面》一書中初次透露她姑姑和有婦之夫曾有過秘密戀情,晚年,和年長二十多歲、喪妻不久的洛德法官從交換情書開始,也有過一段甜蜜的准婚姻生活。事實上,她也留下了一些涉及性愛歡樂和男女調笑的詩篇:
羞,不必畏縮著
在我們這樣的世界裡
羞,挺直了站起來
這宇宙,是你的
世界上居然有人批評狄金森放蕩,那是洛德法官僅有的晚輩——他的侄女,唯恐洛德再婚影響她可能的遺產繼承。
2008年10月,我訪問了艾默斯特,艾默斯特學院是東道主,他們好心把我的住處安排在正街(Main Street)東端南側的“艾默斯特客棧”(Amherst Inn),正好和狄金森家的“家宅”(Homestead)和“長青居”(Evergreens)隔街相望。“家宅”已經被設置成“狄金森博物館”,相鄰的“長青居”,現今,估計也已作為博物館的一部分對外開放。果然,正像王蒙告訴我的,我的中文譯本《狄金森詩選》陳列在眾多文種譯本的中央。應館長之請,我在譯本上簽了名。
此行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艾默斯特的書店。從那裡出售的有關於狄金森的傳記、論著、資料和文學創作種類之繁、數量之多可以看到,狄金森研究在美國的聲勢及研究成果的豐碩。其共同的特點是,多為獨創性成果,沒有一部是人云亦云的合成品。當你見到《狄金森:意想不到的佛家》,作者還在序言中稱她為“艾默斯特的菩薩”,一定奇怪,但是,讀過,你會承認,不無道理,成一家言。
讀到觀點各不相同的論著,不能不驚歎狄金森其人精神境界的淵深、其詩內涵的豐富,經得起多種理論、多種角度的探究和解讀。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92132/
上一篇:佩特拉克:世界百大作家53
下一篇:愛倫坡:世界百大作家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