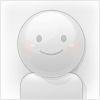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傻瓜才信:經濟學人唱衰中共 2023-08-29 銘傳大學副教授楊穎超
英國《經濟學人》近日發表「中國經濟何以救不起來」,指出,日益獨裁的中共政府正做出種種錯誤決定。這不是經濟學人首次唱衰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他們認為中共是「脆弱的強權」,甚至只是GDP成長率沒達到一定數字,社會就會開始動亂。
回應
西方主導世界知識領域已超過200年,世人失去審辨真相的能力久矣。
可以說西方不了解中共,斬釘截鐵的結論出意外不意外.
以美為首的所謂民主世界都是靠抹黑、造謠來打擊對手
西方惡霸從中共改革開放一直唱衰到現在, 現在更糾集各方惡霸一起圍毆中國,台灣更是幸災樂禍, 真是無知到極點啦!
美歐為什麼不想學中文了?--經濟學人
2016年國際調查,當時選學中文的主要原因是讓就業的路更寬廣。過去十年,比起國際關係與安全學生,學中文的商學院學生減少了。西方國家的學生對於與中國生意往來的想法或許也走味了,新疆與香港人權問題經廣泛報導,富國對中國的負面觀點攀上最高點或逼近高點。同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也愈來愈緊張。不過,依然有許多西方國家政府表達,他們其實還是需要更多精通中文的人才。中央情報局(CIA)正尋求把中文人才增加一倍。
但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中文學習趨勢似乎是上揚的,2018年有超過8萬1000名非洲學生前往中國留學。中國的孔子學院也有幫助,既教導中文,也教導其他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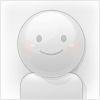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英】馬丁•雅克:西方可以從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學到什麼 2023-02/07 環球時報
第一,共識。在當今全球發生劇變時代,事實證明,一黨制國家比西方多黨制國家更善於達成共識。
第二,參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陳腐的。主要模式是選舉,選舉週期之外幾乎沒有民眾的參與。在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有許多不同形式:選舉、持續的協商過程、自治、民眾參與立法以及制訂五年計劃,等等。
第三,長期。西方民主政府更替不利於連續性,不利於追求長期目標。政黨制度強調贏得下一次選舉,而很少關注未來十年。在中國不斷地進行長期思考,無論是五年計劃還是2035年遠景目標,短、中、長期之間產生非常動態和創造性的關係。這是現代社會實現深刻變革的唯一途徑。中國對“長期”的偏好深深植根於這個國家的基因中,長城和大運河就是其象徵。
第四,專業知識。一位中國共產黨員幹部在政治層級中上升的唯一途徑,升職時,他們已經積累了如何管理的大量知識。西方模式的政治人士主要技能是說話,而中國是做事。
第五,實效。西方認為民主的意義在於民主本身。其實民主的意義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改善經濟和社會。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已全球2大經濟體。使近8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的抗疫表現遠遠優於西方。它對未來有清晰的認識。
西方能否展示智慧和謙遜,從自身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治理中學習呢?挑戰不是在於要採用中國的政治制度:那將是一項既不可能又無望的事業,它們的歷史和文化截然不同;挑戰在於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並找到將其應用于西方民主的方法。(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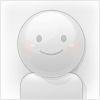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英】馬丁•雅克:西方可以從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學到什麼 2023-02/07 環球時報
第一,共識。在當今全球發生劇變時代,事實證明,一黨制國家比西方多黨制國家更善於達成共識。
第二,參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陳腐的。主要模式是選舉,選舉週期之外幾乎沒有民眾的參與。在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有許多不同形式:選舉、持續的協商過程、自治、民眾參與立法以及制訂五年計劃,等等。
第三,長期。西方民主政府更替不利於連續性,不利於追求長期目標。政黨制度強調贏得下一次選舉,而很少關注未來十年。在中國不斷地進行長期思考,無論是五年計劃還是2035年遠景目標,短、中、長期之間產生非常動態和創造性的關係。這是現代社會實現深刻變革的唯一途徑。中國對“長期”的偏好深深植根於這個國家的基因中,長城和大運河就是其象徵。
第四,專業知識。一位中國共產黨員幹部在政治層級中上升的唯一途徑,升職時,他們已經積累了如何管理的大量知識。西方模式的政治人士主要技能是說話,而中國是做事。
第五,實效。西方認為民主的意義在於民主本身。其實民主的意義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改善經濟和社會。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已全球2大經濟體。使近8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的抗疫表現遠遠優於西方。它對未來有清晰的認識。
西方能否展示智慧和謙遜,從自身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治理中學習呢?挑戰不是在於要採用中國的政治制度:那將是一項既不可能又無望的事業,它們的歷史和文化截然不同;挑戰在於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並找到將其應用于西方民主的方法。(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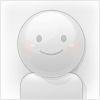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時論廣場》民主與民本 誰以蒼生為念 2023/01/20 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黃光國
中國式的「民本主義」,講究的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方法是「民主協商」,而不是西方所謂的「民主投票」。3月4日,大陸將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新華社指出,對全國政協委員人選將「逐個審核把關」,嚴把人選的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
這當然不是賴清德主席心目中的「民主」,也不是五四青年夢寐以求的「洋菩薩」或「德先生」。我想請教賴主席的是:經過「民主投票」選出的貴黨前主席蔡英文,在「徵召」各種選舉候選人的時候,大權獨攬,有沒有像大陸這樣的「把關」?……
認定明清“閉關鎖國”的人,你們才是“閉觀鎖國” 2023-01-16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修木
1683年三藩之亂平定,臺灣收復,清朝坐穩,康熙下詔重新開海,不是以前的三年一貢的朝貢關係,歐洲帆船每年都可來廣州,還可建倉庫。康熙開海,並不是為了照顧歐洲人。中國有最大市場,而中國的瓷器、絲綢又是品質最好的。18世紀是康乾盛世,天下大致安定,而且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由此也帶來消費需求的急速增長。
回應
清朝賣出貨物,收穫白銀,基本是單方面的,中國怎能是閉關鎖國?
在客觀歷史上,清朝確實沒有閉關鎖國;但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清朝必須是閉關鎖國的,只有這樣,西方的殖民史觀才是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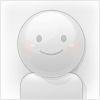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陸版誠品「被關門」官方稱違建 其實原因是… 2019-11-07 聯合報
有北京最美書店之稱的老書蟲(The Bookworm)5日在其官方微信上宣佈,因大陸政府整頓違章建築的關係,書店將被迫結束營業。老書蟲曾被世界知名旅遊指南叢書「孤獨星球」評為世界十大書店,自2005年開始營業,起源是一個私人借閱圖書館。當時來自英國的Alexandra Pearson來到北京生活,他在其參與營運的餐廳組織各類主題的專家講座,包含文藝講座、脫口秀、電影放映、音樂沙龍等等,在這裡可以談女權主義、中美貿易戰等時下議題。
講座太「自由」 上海書店也關門
事實上,去年上海獨立書店季風書園致力於「獨立的文化立場,自由的思想表達」價值追求,也會不定期舉辦沙龍座談。儘管當時房東告訴場地無法續租的理由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不過就該書店瞭解,不再續租的原因,與官方認為書店舉辦的講座活動會帶來風險有關。
回應
接下來「新文化大革命」就要發生了!中共國說要書店關門就關門,根本不需理由的!
內文不看就急著發文,這種1450的行為不要學。
就是違建,要遷址重開,這麼簡單的事也要扯政治意識形態?難怪台灣難以進步,太多井底之蛙。
半年沒吃豬肉?陸婚宴豬蹄膀一上餐桌 立刻秒殺搶光 2019-11-07 世界日報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中國普遍生豬短缺,豬肉價格居高不下,民眾慨歎「吃不起」。近日網上一段視頻引爆一眾網民的討論與「垂涎」。該段視頻據指拍攝自河南洛陽一場婚宴上,賓客桌上才剛上了一盤「豬蹄膀」,就立馬被「秒殺」。
回應
豬價都回跌好一陣子了,何來沒吃豬肉?人家就是在找梗玩... 結果到了台灣政治豬眼裡變了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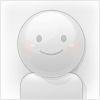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從中國外交慣用辭彙 看中國外交 2019/08/06
多年前我看過一則挖苦西方漢學家的笑話,說有位博士,其博士論文是「孔雀東南飛」。考試委員問:「為何孔雀要向東南飛,而不向西北飛?」,博士回答:「因為西北有長城」,這充份說明了西方政客對中國永遠也弄不清楚,其實正是緣於半吊子中國通的緣故。
這種情形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前幾天自由報的一位美國中國通易思安寫了一篇文章,就說明了半吊子的狀況。易說:【中國的政府文件及宣傳廣播非常難以解讀,挑戰性很高。這些官樣文章以中共版的雙言巧語寫成,往往意在言外、故弄玄虛,並引用冷僻的歷史事件、採取拐彎抹角的敘述方式,還會利用列寧主義者隱晦又自相矛盾的修辭扭曲邏輯】。
中國由於文化關係,本來就不喜歡直來直往,把話說清楚,所以必須了解話後面的意義。半吊子感覺非常之拐彎抹角,這是工夫不到家的緣故。今次我稍微收集了一些中共外交用語,可以大略領會一、二。
1.表面意義:坦率交談。實質意義:分歧很大,無法溝通。
2.雙方交換了意見:各說各話,無法達成協議。
3.充分交換了意見:雙方吵的非常厲害。
4.增進了雙方的了解:雙方分歧很大。
5.會談是有益的:雙方相距甚遠,能坐下來談就不錯了。
6.我們持保留態度:我們絕不同意。
7.尊重:不完全同意。
8.讚賞:不盡同意。
9.遺憾:不滿。
10.不愉快:激烈衝突。
11.極大的遺憾:我們對你們沒有辦法。
12.嚴重關切:可能要干預。
13.不能置之不理:即將干預。
14.保留進一步的反應權力:我們將報復。
15.勿謂言之不預:即將開打。
16.將重新考慮此一問題的立場:將改變原來好的政策。
17.拭目以待:最後警告。
18.請於某日以前答覆:在某日前,雙方處於非和平狀態。
19.由於此事引發的結果,將由貴方負責:可能我方將實施武力。
20.這是我方不能容忍的:戰爭在即。
21.這是不友好的行動:這種敵意的行為,可能引發戰爭。
22.具有高效及建設性:會談時間很短,所以必須高效,且對此次談判,不存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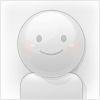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論中共的一黨專政 2019/03/11 筍子
我是政治的現實主義者,我反對絕對主義,因為世間沒有非黑即白的絕對真理,一切都是相對的。
中國比起30年前,絕對是大大的進步。如果30年前,中共即採取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那麼結果就是今日之台灣。當然,臺式民主,有言論的自由,但若給乞丐言論自由,我認為他寧願多要一碗飯比較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西方一神教徒,容易受到絕對主義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在斷頭臺上就說:「自由、自由、多少人為你而死」。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則沒有這一套,是講相對思維的。
中國人只有在沒有飯吃,而非在思想受到壓制時,才會推翻暴政。黃花崗72烈士死難時,當時大多數人民是不表同情的。為了思想或宗教而革命是傻瓜才會幹的。
維吾爾是中國的隱患,西藏則不然,主因就在伊斯蘭教與佛教,其絕對與相對的思維是不同的。搞政治評論的,務必要考慮民族特性,照般西方思維,是抓不到癢處的。
釋道儒三家,都沒有絕對思維,中共的思想更是無神論,所以中國無法產生非要如何如何的絕對一神思維,不會因著思想上的被壓制,而產生非要革命不可的文化背景。
在不餓肚子的大原則下,思想上面的壓制,多數人民是願意忍受的,中共對此是非常清楚的。西方人以西方思維,堅定的認為中共一定瓦解,一定大卸八塊等等,但喊了70年後才發現中共及中國人民完全不是他們想像的,九千萬黨員組成的一黨專政,不是隨便就可以唬弄的。
 圖博館
圖博館
那種高污染、腐敗嚴重、低俗現象氾濫的GDP運動是中國老百姓想要的嗎?大多數人的回答顯然是“不”。這幾年中國的調整是全面的,既是經濟上的,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今天中國經濟增速換擋了,我們對這個數字不習慣,但是政府清明了,社會風氣清朗了,公平增加了,土壤、水和空氣的清潔都在恢復,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嗎?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理念、新路徑和新動力都在逐漸形成,過去的發展成績巨大,但說實話有些粗糙,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在以往成就的基礎上進行轉變。我們無法一蹴而就,但中國新舊轉換的設計是邊行進邊完成。
歷史上一些大調整往往是通過各種“休克療法”實現的,比如斷崖式的經濟危機。中國是迄今唯一沒有出現過嚴重硬著陸危機的高增長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調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貿易戰的疊加衝擊,增加了複雜度。但是中國能夠有序對抗這些負面影響,錘煉了中國經濟的承受力。2018年6.6%的增長率裡面包含了中國體制所貢獻的特殊定力和成熟。
西方一些分析人士表達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態度,但他們的分析僅僅停留在資料的最表層,而沒有沉下去。
中國2018年依然貢獻了全世界約30%的經濟增量,繼續排第一。我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市場資源擴張的前景是全球最被看好的。中國經濟總實力和綜合國力都保持著逐年上升態勢,6.6%這一增長率低點對這些趨勢都不構成打斷,而且它所提供的有效能量並不比過去的時候少。
中國經濟當然有自身的問題,邊發展邊調結構,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大國,不熟悉就足以讓我們交一部分學費。但是中國的大方向顯然找對了,它得益於我們對國家重大經濟挑戰的客觀判斷和實事求是的解決態度,還有執政黨的領導力。
外界的各種聲音都值得我們兼聽,然而過去的情況已經表明,外界的分析和支招經常有些偏,遠不及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的研判準確。這說明外界總的來說沒有摸准中國發展的脈絡和邏輯,他們的視角常有新穎之處,材料的發現也對我們構成補充,但他們就是容易被立場和價值觀帶歪,得出偏離中國現實的結論。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遠比西方人想的充足,駕馭力則比他們想的強大、有效。我們的問題的確多得數不過來,但在這個龐大、厚實的國家裡,沒有哪個問題能夠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對抗。這聽上去有點虛,但它就是中國真實且最為強大的時代公式。
 圖博館
圖博館
6.6%這一“最低增長率”並非中國經濟正在走向斷崖式危機的徵兆,而是中國解決尖銳問題、控制嚴重風險後實現軟著陸的過程。當然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率能夠再高一點會更好,但是能夠一邊大幅調整,一邊保持這一中高速的增長水準,已經證明了中國站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時的穩健和韌性。
世界輿論都提到一點,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中國沒有採取10年前4萬億元基建投資的強刺激。這不僅反映出中國政府對經濟基本面良好頗有信心,還因為這10年間中國經濟的結構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當時中國不得已,只有增加基建一條路,而2018年時,中國可以承接溫和刺激政策的經濟運行面和點要豐富得多。
如果中國的治理模式像美歐那樣,在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幾十年後,一定會有一場美國1929年式的經濟危機,這也是西方一些人鼓噪中國崩潰論的經驗依據。然而中國的體制優勢使得我們能夠主動化解積累起來的風險,讓前進與解決問題有效結合成同一個宏觀政策。
這不是哲學和詭辯,而是中國經濟活生生的現實。2018年6.6%的增長率對應了遠超過十多年前10%以上的實際經濟增長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比當時清潔了許多,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邁過從遭到破壞到走向修復的轉捩點。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瞄準經濟發展的“以人為本”原則,食品安全、教育、醫療、養老、宜居、旅遊等高度涉及民生的領域更多成為投資的方向。
中美貿易戰發生在2018年,它顯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種負面影響無疑要比它一旦發生在十幾年前小得多。今天的影響也是大的,但它是中國能夠不以“傷筋動骨”的方式承受得了的。
社評:重回高增長不難,但時代不會回頭 2019-01-23 環球時報
中國2018年GDP增長6.6%,創28年來最低年度增幅,引起諸多議論。其實如果中國想高一點,我們迅速沖到8%,未必是件很難的事。
中國最近幾年大量去產能,高污染的企業受到嚴重限制。華北地區的霧霾天數明顯在減少,很多河流的污染情況得到好轉。只要稍微放鬆一點調結構針對治理污染的努力,就能恢復不小的一塊GDP。但是大家願意嗎?
這幾年不健康(楨:?)的娛樂業(相關新聞:阻礙「中國夢」 娘炮與佛系被央媒點名指導)、尤其是色情業受到嚴厲管制,公款消費也是這幾年GDP中頗具分量的一塊損失,如果恢復這一切,GDP馬上可以點燃一部分動力。
 圖博館
圖博館
美國在高速增長
你在搞笑?美國GDP同比2.5%, 4.1%是假的是環比,中國用的同比。
經濟增長了,人民得到多少實惠?高房價,看不起病,上個好點學校上不起,工作八對八,每週休三四天。實惠在哪?
大學公立本科一年學費幾千元/大學宿舍住宿費一年1200元的白菜價/高鐵平均1公里0.36元的客運價,鐵路平均1公里不到0.1元的客運價/城市地鐵幾元錢可以環遊半個城市——你以為是市場價?戈壁山區手機信號都能滿格/哪怕不到100人的偏遠村莊都給你開山架橋通電通水/一個村莊建一個4G基站最後收取的通訊費還不夠基站的電費/發生火災或者險情你一個電話消防官兵就迅速趕到而且免費服務/發生天災軍隊3小時就立即出動不顧危險迅速救援——你以為全世界都這樣?城市晚上10點之後你仍然可以喝酒K歌亂串亂逛/最好的醫院都是國家公立醫院都對最貧窮的民眾敞開大門/政府官員直接入住貧困家庭,挖空心思幫助貧困人群脫貧致富——你以為是理所當然?
環球時報社評:如何看經濟下行中6.6%的年增速
國家統計局2019-01-21公佈,中國2018年GDP總值達到900309億元,增長6.6%,第四季度增長6.4%。這是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踏上90萬億元人民幣的臺階,但從增長率看,6.6%又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速,6.4%是2009年一季度以來最低的季度增速。
如何看中國的經濟形勢呢?外媒的最初評論大多集中在了“中國GDP28年增速最低”上,強調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這些都是事實,必須正視。然而僅僅從“最低增速”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又很容易誤讀它。
人們都還記得,在早些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兩位數的時候,我們經常談要控制經濟增速。為什麼?因為中國當時的增長高度粗放,而且對出口依賴度太高,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生態成本,而創造的財富卻沒能充分地轉化為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優化。直到2014年,中國生產的鋼筋水泥和煤炭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再不轉型,這個國家已經承受不了。
 圖博館
圖博館
外媒稱中國GDP增速實際只有4.1% 發改委回應
2019-01-22,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佈會。有記者提問:昨天統計局公佈了內地的經濟增速是6.6%,但外媒有的認為實際增長只有4.1%,有的認為甚至更低。對此,有何評論?
新聞發言人孟瑋:
首先,從實物量資料看。2018年全社會用電量6.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8.5%,這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增幅;煤炭在嚴控新增消費的情況下,消費仍增加1.5億噸左右,天然氣更是大幅增長400多億方、增速17%以上;全年全社會貨運量增長7%左右,其中鐵路貨運量增長9.1%。實物量指標是經濟增長最直接的反映,這些實物量資料可以有力支撐全年經濟增長資料。
第二,從關聯資料看。看三大產業,2018年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2%,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7.7%,一產增加值增長3.5%。看三大需求,2018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9%,且在四季度逐月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全年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增長9.7%。看就業和收入,全年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61萬人,比上年多增10萬人。前11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5%,而且這是在全年減稅降費規模達到1.3萬億元的條件下實現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1.8%。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5%。無論按照GDP核算三種方法的哪一種看,支撐6.5%左右增速的資料都是匹配的。
第三,從國際組織預測看。今年1月初,世界銀行發佈最新一期的《全球經濟展望》,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等對中國2018年GDP增速的預測值為6.5%—6.6%。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中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健康穩定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支持高品質發展的生產要素條件沒有改變,長期穩中向好的總體勢頭沒有改變。我們不追求高速度,更加注重高品質發展,但中國經濟完全有條件、有潛力、有能力保持合理區間的增長。
相關新聞
IMF將2019年世界增速預期下調至3.5% 發達國家將僅為2%
回應
這是西方人慣用的伎倆打壓不了中國就唱衰中國。西方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
西方唱衰中國也不是最近這一兩年了,我們也應該見怪不怪。我們應該抱著一個平常心,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對於別人的說三道四,我們只當刮了一個耳旁風!
去年82萬億,今年90萬億,不是增長9.26%嗎?
扣除物價上漲按可比價格算6.6%
 圖博館
圖博館
媒體:首席經濟學家要珍惜自己的聲譽
2018-11-19,《證券日報》發表《首席經濟學家要珍惜自己的聲譽》一文稱,在金融圈中,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機構研究實力和品牌的標誌之一,如果不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只是一味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觀點、言論,就算是頂著“首席”的光環,也終將會被市場、被投資者拋棄。
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16日發佈消息,為進一步發揮好首席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和公信力,維護行業聲譽,更好服務資本市場和國家經濟建設,近日證券基金行業首席經濟學家簽署《首席經濟學家自律倡議書》。原文如下:
其一,是遵守《證券法》等規定,恪盡職守,勤勉盡責,認真做好經濟金融研究和諮詢服務工作,樹立廉潔從業良好形象。
其二,愛惜在行業形成的良好聲譽,客觀、專業、審慎發表研究觀點,積極傳遞正能量。
其三,加強政策法規和專業理論學習,不斷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為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為引導市場預期貢獻積極力量。
在金融圈中,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機構研究實力和品牌的標誌之一。
從普通研究員到首席經濟學家不易,一方面,他們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供就職單位使用,另一方面,還要經常通過各種管道,將自己的觀點和聲音傳播出去,並得到市場的認可。而他們的觀點,代表的是所就職單位的觀點。他們是否具有強大的研究實力,對事件的判斷是否準確,對於提升所在機構的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以,對首席經濟學家而言,必須要客觀、專業、審慎的發表研究觀點,推出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報告;要對自己負責、對就職的機構負責,更要對投資者負責、對市場負責。如果不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只是一味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觀點、言論,就算是頂著“首席”的光環,也終將會被市場、被投資者拋棄。這一點,在任何一個研究員身上,應該都適用。
回應
不知道多少個首席說過中國崩潰論了,也不見一個辭職
首席?西方經濟學的鸚鵡和傀儡而已
研究中國經濟、政治的西方學說,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巫術;那些人,與其說是專家,不如說是巫婆神漢;他們說的,與其說書預測,不如說是嘲笑和詛咒。這批人往往產生於以下三個領域:1.媒體2.經濟學3.律師.
 圖博館
圖博館
西裡塞納上臺之後,為了平衡中印關係,曾經採取措施提升與印度的合作,並對中資項目進行重新審查。然而後續的財務危機迫使斯裡蘭卡不得不繼續依靠中國的支持,從總體上看,斯國政府都必須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換句話說,前後兩任總統其實都致力於加強與中國的關係,雖然過程中有批評也有修正,但大方向上卻沒有多少分歧,台灣輿論如果只抓住一些批判言論,就認為該國政策上的根本轉變,無異於用幻想來代替現實。
當然,友中政策當然也並非全貌,這次被取而代之的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就是斯國內部的傳統親印派代表人物。按照該國的憲政體制,總理也有相當大的實權,所以維克勒馬辛哈一直想要將西裡塞納變成傀儡,只是後者不甘心受人擺布,所以才與之展開政治鬥爭,而雙方最終翻臉就出於對一個港口應否租於印度產生分歧。而現在的結果就是,親印派失勢。
黑中言論影響政策
這一局面顯然又與台灣獨派的想像背道而馳,他們自從注意到印中矛盾之後,就致力於通過新南向政策,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對美國提出的印臺戰略也樂此不疲,如今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印度在印度洋區域的準霸權,其實是周邊國家最為擔憂的常態問題,而中國的加入,從長期來看是平衡。國際局勢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它不會按照獨派的自我想像去運作,但蔡政府的政策卻可能按照這種想像去制定,這自然會構成想像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圖博館
圖博館
勿陷大陸遍地烽火想像 2018-10-31 旺報特約主筆 王欽
最近這兩年,大陸的國際處境看起來並不樂觀,許多已開發國家都站出來抨擊大陸,一帶一路沿線的合作項目也經常遭遇挫折,大有遍地烽火之兆,這與大陸崛起及其國際影響力躍升的大方向,看起來有些背道而馳。
親中派並未失勢
對獨派來說,這種局面當然是進行政治操作的大好機會,正好可以對內宣傳大陸崛起的「虛幻」,他們擷取眾多案例來證明,大陸崛起不過是一種新形式的「擴張」,而現在不僅遭到已開發國家的警覺,而且已經在開發中國家中受到質疑乃至糾正。也恰好在此時,從斯裡蘭卡開始,再到馬來西亞,甚至到馬爾地夫,這些國家內部的政黨輪替,都被拿來解讀成當地親中派的失勢,而反對黨贏得選舉,都是因為反中立場鮮明。
這種分析視角不僅昧於事實,其實也在不自覺中陷入一種邏輯陷阱,因為如果他們說的為真,那等於證明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已經大到足以左右各國的國內政局。現實顯然並非如此,中國或許正在積極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並透過各類大型公共建設來深化雙邊合作,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已經可以對各國內政指手畫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內政複雜度,遠超過獨派的想像,單一視角下的中國影響論或者反抗中國論,都無助於台灣社會更清楚的瞭解當今的國際大勢。就以這一輪「黑中」言論的起點斯裡蘭卡為例,即可知道台灣獨派的虛妄認知。這幾天的南亞新聞無疑被斯裡蘭卡內部「準政變」搶了頭條,該國總統西裡塞納決定罷免現任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其政黨也退出現正執政的聯盟,而轉而任命前總統拉賈派克薩出任總理,後者剛在今年2月的地方選舉中獲勝。
不意外的是,台灣的獨派輿論又抓住拉賈派克薩在選舉過程中曾經對現政府的一些抨擊言論,認為現政府的親中立場受到質疑,這才讓反對黨有了上臺之機。但這未免又陷入一個悖論,因為拉賈派克薩擔任總統的時候,正是中斯關係最好的時候,前總統本人也被視為該國最大的親華派,而當初西裡塞納之所以能夠戰勝他,也是因為反對他的單邊親華立場。
 圖博館
圖博館
美媒:中國經濟不是“正常”狀態?NO!
美國《紐約時報》2018.3.13:中國經濟不是“正常”狀態,它不需要這樣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催生出了兩大分析流派:一個學派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注定要征服世界;另一個學派認為中國經濟扭曲太嚴重了,會走向崩潰或者至少會退回到中值水平。這兩種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
首先,中國從來就沒被歸列為“正常”經濟體:該國近40年來平均增長率接近10%,創了紀錄;是躋身世界強國的第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此說來,中國為什麼就不能繼續藐視一些人的預測,繼續走它自己的路呢?
事實上,一些人所認為的中國經濟弱點恰恰是其強項。不均衡的發展不是風險逼近的證據,而是工業化取得成功的一個跡象。猛增的債務水平是金融深化的一個標誌,而非揮霍無度的開支。至少到目前為止,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是否繼續混淆被要求遵守的規範,而是中國政府是否能在國家干預和市場力量之間取得平衡。擁有強力的中央政府有其好處,包括有能力快速撥正航向。這使中國的領導人在近幾年來將中國經濟轉換到了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
對中國未來持懷疑立場的人通常指出該國不斷膨脹的債務。中國的債務總額和GDP之比超過了250%,但這是一個相當平均的水平:比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高,但比大多數高收入國家低。為什麼中國就與眾不同呢?一個理由是並不是所有的債務都是平等的。一些樂觀人士指出,中國的債務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這意味著風險主要由財力更加雄厚的國家來承擔。借貸更多是在國內進行的,而不是從外部借的。儘管抵押貸款出現了井噴,但與其他地方相比,中國家庭總體債務負擔較低。
一些中國觀察家還擔心中國的高速增長不能得到維持,除非消費代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事實上,即使消費在GDP中所佔的份額下降,中國的個人消費增長速度也比其他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快好幾倍。最終,中國經濟將變得更加平衡,中國政府非常清楚這一點。或許中國經濟的瘋狂時代即將結束,但是即使今後10年維持6%的增長率也將是了不起的。在筆者看來,中國直到今天取得的顯著成就應歸功於中國領導人追求務實主義的意願。(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陳一譯)
 圖博館
圖博館
外國專家:中國過去五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2018-03-09 新華網
五年成就獲得世界點贊
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名譽教授凌星光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政府工作報告以客觀而有說服力的數字闡述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事實。特別是五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比重上升,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經濟社會充滿活力、欣欣向榮的面貌。
阿根廷《二十一世紀美洲》雜誌主編路易斯·畢爾巴鄂說,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82.7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7.1%……中國過去五年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可藉鑑的經驗,更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活力與信心。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客座教授施永豐評價說,中國過去五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在民生髮展方面,惠民政策力度不斷加大;在綜合交通建設方面,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運行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鐵路網絡;在創新就業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舉措。
歐洲學院中歐研究中心主任門靜認為,在過去五年中,中國經濟發展更加註重質量,穩中求進。與此同時,創新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動力,投資力度明顯加大,整體創新能力顯著提高。國家鼓勵創新的舉措與“中國製造2025”發展規劃相呼應,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鋪路。
外國專家:中國仍然致力於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2018-03-09 新華網
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漢學家巴利·拉姆·迪帕克(中文名狄伯傑)說,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中國仍然致力於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將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
談及報告中對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凌星光說,其內容幾乎每項都涉及人民生活,令人讚嘆。比如明顯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專線使用費,取消流量“漫遊”費;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等。
緬甸資深媒體人、《北極光》雜誌總編輯吳溫丁說,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國今年各領域工作都做了具體部署,有助於各項政策順利落實。中國政府將加大精準脫貧力度、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平等。這些保障民生的舉措必定會讓民眾感到踏實和滿意。
 圖博館
圖博館
僅2票反對...大陸超高票通過修憲 習近平可再延任2018-03-11聯合報
大陸全國人大會議昨天表決以超過九成九的比率,通過中共修憲案,將習近平思想、國家監察委員會等內容入憲;修憲同時通過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規定,習近平可望延任到二○二三年之後。
16人缺席 2票反對 3票棄權
會議應到人數兩千九百八十人,實到兩千九百六十四人,缺席十六人。廿分鐘投票結束。結果贊成票兩千九百五十八票、反對票兩票、棄權票三票、無效票一票。
這次最受關注的是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首度公開表態,「完全贊同憲法修正案草案」。習近平還說,憲法修正草案在形成過程中「充分發揚了民主,集中了各方面智慧,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倒退到文革時代?外媒強烈關切
沈春耀說,「你提問中設想、推測和延伸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對於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其他機關是否也有相同考慮?總書記任期限制應寫入黨章,而不是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沈春耀都未回應。
人大宣稱:修憲健全國家領導體制
沈春耀強調,這次修憲是健全國家領導體制的重要舉措,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位一體」符合國情與實際需求,這是長期實踐探索總結的成功經驗,在黨內外、全國上下具有高度共識。
回應
德國默克爾當四任總理,美國小羅斯福當了四任總統,沒有開倒車?
相關新聞
憲法修正案草案表決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人民日報社論:為民族復興提供有力憲法保障
環球時報:中國修憲無須與西方政治體制“對錶”
強人政治興起…習延任 各國緘口 外媒質疑
中共修憲 內有紛紜 外有物議
回應
聯合報記者李春的這篇"中共修憲 內有紛紜 外有物議"足證台灣記者的腦殘無知,就是一個長期受妖魔化中共醜化中國人洗腦教育下長大的人。修憲是人大投票表決,人大又不見是中共,看這標題"中共修憲",真是腦殘無知,難怪會練肖話三位一體,改掉國家主席任期稱之為"習近平稱帝"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自古以來,除了台灣地區,從未實現過具有實際意義的一把手任期制。權力應如何更迭,一直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最大政治問題之一。台灣近二十年來,堪稱和平地移轉了政權數次,惟因執政利益所趨,政客們不惜耍弄選民;台灣正朝向以民粹取代民主的三流政體奔去。值得玩味的是,民眾並不總是糊塗,實施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在逝世三十年後的聲望,仍然壓倒性的超過歷任台灣民選總統。
從孫中山、毛澤東以降,任期制在中國從未發生過西方式體制之作用。在當今之中國,取消任期制,反有實事求是之意味,名實相符,誰掌權,誰負責!此外,取消任期制,並不代表就此能夠自動的無限期續任。出任國家主席、副主席,仍須全國人大代表同意。管見以為,此次修憲,仍有未竟事項:其一,人大代表應通過真正意義的普選產生;其二,人大議決事項之具體機制,應提升至憲法規範層級。世間本無萬全之策,求其得在平穩中探索進步之道路耳。中央有顧慮,可考慮試點行之。
中國人走自己的路
筆者從未敢輕忽西方現代化法律對人類文明之貢獻;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亦深受其益。然五四以來,不知有多少高手期盼中國能朝此轉變,之所以未能成功,正是因為國情不同。湯姆漢克與梅莉史翠普所演的電影《郵報‧密戰》(The Post),尤其能讓媒體人與法律人熱淚盈眶;但是走出戲院,我們當冷靜的認識到,中國人有自己的路要走。王滬寧曾言:「中國的民主模式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為基礎,能有效地保證政治體制的效率,保障政治體制一體化和社會穩定的發展,同時必須能夠適應中國歷史—社會—文化條件。」這番話正可為本文之註解。(作者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圖博館
圖博館
實事求是看中共修憲2018.3.7旺報 王冠璽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目光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之規定」、「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等。
此一修憲建議稿,除了大陸官媒以外,境外媒體有的疑慮,有的批評;境內亦不乏反對聲浪。凡評價某事,必有基準,首要關鍵非在條文本身,而在於論者對評價對象與基準均能有深刻認識。此次修憲持不同意見者,其判斷基準多來自西方。的確,憲法傳自西方;西方人對法律有信仰,西方的大法官們對法律的解釋有定紛止爭,一槌定音之效。
別持西方標準批判
西力東漸以後,非西方國家效法西方國家制憲;然環顧宇內,並無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該國之法律地位能達到西方國家之位置。原因很簡單,就是國情不同。論者切莫輕忽「國情不同」四字,華人世界之政爭,多起因於私利;袞袞諸公藏身於法律之後,道貌岸然,法律經常淪為黨同伐異之工具。對此修憲案持反對意見者,不妨捫心自問,月旦他人容易,涉及自己或所屬黨派切身利益時,又有多少人願意按「西方法律標準」辦事?
對中國有成熟認識者當能同意,以黨國體制形容中國都不算準確;當今中國所實踐之體制,乃是披著政黨外衣的傳統官僚體系。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無從區分。之所以「治」國必先「治」黨,係因從嚴治黨的目的不在「黨」,而在提振執政水平。中央權威如不能保證,執政團隊(黨)如不能確保廉潔高效,令出不行,上下敷衍,則政治何以清明,全國百姓如何邁向小康?於此所謂之「治」,與西方的「法治國」根本是兩回事。故此,「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誠為實際情況之描述;而監察體系之設置,乃為加強「治」「黨」的應有環節。
 圖博館
圖博館
14億人的治理規模是人類歷史之最,這樣的規模別說台灣的領導人,就連美國也可以站一邊了,因為單單是讓14億人吃飽,所涉及的挑戰之大、之複雜,就遠非他人所能想像。正如習近平在2009年一場演講中指出,中國能夠基本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大的貢獻。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別人,大家還有什麼好說的。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演講中提到2020要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台灣有人批評簡直是吹牛。老實說,這確實是個艱鉅困難的使命,讓14億人全面脫貧,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做到過。然而,有努力的目標勝過沒有,如此理想就是再打個5折,一樣很驚人。
中國大陸問題當然很多,但誰又不是呢?希望大陸一路以來的努力,至少能讓持中國崩潰論者能稍為謙遜一些,甚至務實一些。畢竟,如果中國夢失敗,對大家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夢礙你什麼了2018.2.27彭蕙仙
日前中共《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建議刪除國家主席及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規定。這個建議被外界認為是為習近平在2023年後的連任掃除障礙。對此,美國白宮的回應是「這是中國政府的內部事務」,他們會予以尊重。
然台灣有不少人以「威權」、「極權」乃至於「習皇帝」譏諷之、批判之。不過,這些人大概忘了,中共似乎並未像某些政黨,一方面愛強調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聯盟」,另一方面卻做盡掠人資產、卡人校長之類的惡事。
還有些人喜歡恥笑習近平的中國夢,或是以看好戲的心情等著中國夢碎。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殘忍。任何一個民族或是國家懷抱復興光榮、飛躍成長的夢想,都是值得祝福、鼓勵和幫助的,更何況有著這樣夢想的這群人,從歷史、地理、文化到種族,都跟在台灣的我們關係如此密切。從某一個角度來說,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也是屬於台灣的,也可以是屬於台灣的,甚至,也應該是屬於台灣的。
至少我對中國夢就非常感動,甚願百年來受盡欺凌與羞辱的中國人可以走出歷史的晦暗記憶、走出民族的幽禁心靈。這個世界上多一個有自信心、追求榮譽感的民族總是好事,特別是這個民族的人口是如此眾多。在我們的地球上,每5個人就有1個是中國人,你能想像中國不好、不健康、不繁榮,會對人類造成什麼樣的壓力嗎?
說到大陸的人口,這又是另一個讓我感慨的事。台灣常有人喜歡對大陸的體制、治理說三道四,下指導棋,這些人簡直是井底之蛙到了極點。2300萬人與14億人的治理規格,相差太多了,很多事根本無法直接比擬、適用。
 圖博館
圖博館
...
白俄羅斯: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標準普爾為B,相差3級;
觀察者網此前報導,2013年5月,由中國投資50億美元的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獲得白俄羅斯政府的批准。這座佔地約80平方公里中白工業園,總投資約56億美元,距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市僅25公里,總規劃面積約91.5平方公里。
......
結語:
數據圖像化以後,小編也粗略總結了一些規律。總體上,對於東半球、大公國際評級略高,標準普爾略低;西半球則反過來。對於大陸國家,大公國際評級略高,標準普爾略低;海洋國家則反過來。
對於兩種評級方式的差異原因,小編在上面列出了一些關聯新聞,更多的數據解析,請讀者出手。
回應
噫,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的一大票金融機構都是3A,當時中國主權應該是A-吧。雷曼兄弟可以發賀電問候下了。2002至2007年,相關評級機構將絕大多數的美國房貸抵押債券評為最高級別AAA,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閉前,相關評級機構依然給予其A級以上的評級。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第二天評級機構才倉促將其評級下調至D級,即破產級。
看了半天,麼是評級,就是國家意志。現在美國強就標普是通行標準,哪一天種花家強了就是大公無敵。
西方三大評級是為西方金融霸權服務的,你想要幾級?得我說了算!哪天西方金融霸權倒台了,這三大評級也就完蛋了
給出評級只是第一步。美國的大銀行都有硬性規定的製度,必須買一些國債,而且國債持有量必須隨著評級的變化而增減。既然中國有了自己的評級,是不是也應該規定國有銀行這樣做?比如,前段時間調降了美國政府的評級,中國的各大銀行就應該同步拋售美國國債;如果調高了俄羅斯的評級,就應該同步增持他們的國債。這樣你在國際上才有說服力(楨:?) 。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087
 圖博館
圖博館
4 排個隊
阿曼: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為BB,相差8級;
美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B+,標準普爾為AA+,相差6級;
1月18日,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把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由A-下調至BBB+。
對此,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作出解釋:“美國政治生態和信用生態對經濟基礎的長期負面影響導致中央政府償債來源持續惡化,這一狀態將會長期存在。大規模減稅直接減少中央政府償債來源,進一步削弱政府償債基礎。用增加債務收入彌補減稅帶來的財政缺口勢必加劇中央政府信用風險。美國債務經濟模式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持續下降。”
巴林: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B,標準普爾為B+,相差5級;
巴林是首個步入後石油經濟的波斯灣國家,目前經濟並不依賴石油。自20世紀後期,巴林已投入巨資在銀行和旅遊事業。該國首都麥納麥是國內外大型金融機構所在地。2017年12月5日,歐盟宣布巴林列入避稅天堂黑名單。
觀察者網注意到,中國已於2016年成為9個阿拉伯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中東投資貿易促進中心副總裁孔軍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在巴林的兌換所可以拿人民幣直接兌換巴林當地貨幣第納爾,這顯示出人民幣在巴林乃至海灣國家的認可度已經比較高。建立人民幣清算中心無疑將會提高貿易的便利程度,從而加速雙方貿易發展。”
俄羅斯: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標準普爾為BBB-,相差4級;
2014年4月,標準普爾將俄羅斯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BBB-,前景展望保持“負面”。理由是俄羅斯經濟已經遭到本幣貶值和資本外逃的衝擊,而烏克蘭出現的危機令俄羅斯經濟的風險進一步加大。
當年10月,標準普爾確認了這一評級。理由是由於俄羅斯經濟依賴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經濟存在結構性弱點。
雖然該機構於2016年9月上調俄羅斯的“垃圾級”(BB+)長期外幣主權評級的前景,原因是該機構預測二十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俄羅斯經濟衰退時期已接近終結。但並未對本幣評級進行調整。
阿聯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標準普爾為AA,相差4級;
中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為A+,相差3級;
 圖博館
圖博館
大公和標普眼中的兩個世界2018-01-25 觀察者網
最近,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把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由A-下調至BBB+,而此前兩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下調了中國的信用等級。圍觀評級機構“互相傷害”之餘,小編不由得好奇——中西評級體係到底有多大差異?
帶著這份好奇心,觀網小編整理了標普和大公評級對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打分”,並以圖像形式呈現。其中頗有耐人尋味之處:
說明
兩家機構均以A、B、C代表投資級別,信用等級從高到低依次為:A>B>C。其中,A級代表信用質量高、投資品質優良,共分7級,從高到低依次為:AAA、AA+、AA、AA-、A+、A、A-;B級代表信用一般、投資品質不穩定,共分9級,從高到低依次為:BBB+、BBB、BBB-、BB+、BB、BB-、B+、B、B-;C級為劣質債券、有可能或已經出現違約,共分6級,從高到低依次為:CCC+、CCC、CCC-、CC+、CC、C。以下皆為長期本幣主權信用等級:.....
在整理了兩家機構的“打分”後,小編將兩家機構的評分進行對比,製作了第三張圖,分別用暖色和冷色表示大公國際與標準普爾的評級差異,並用深淺表示評級差異強弱。即暖色是大公更高,冷色是標普更高。顏色越深,說明差距越大。
1 最驚訝
位於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納是“二戰”後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曾是世界上25個最貧窮國家之一。目前,大公國際給出博茨瓦納的主權信用評級為A,高於其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BBB+兩級。
2 最反差
兩家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差異最大的國家是阿曼,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給出的評級為BB,相差8級。
觀察者網關注到,早在2016年5月23日,阿曼與中國企業簽署了一項建設杜古姆港(Doqm)工業區的投資協議,總規模達10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1.22億元)。而此前一年,即2015年,阿曼國內生產總值僅為270.1億里亞爾(1里亞爾約合2.6美元),約702多億美元。中國企業的這一項目約佔2015年阿曼GDP的1/7。
3 最接近
除了差異外,兩家評級機構對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給出相同的評級,包括瑞典(AAA)、盧森堡(AAA)、瑞士(AAA)、挪威(AAA)、新加坡(AAA)、澳大利亞(AAA) 、奧地利(AA+)、新西蘭(AA+)、芬蘭(AA+)、科威特(AA)、中國台灣(AA-)、智利(AA-)、卡塔爾(AA-)、西班牙(BBB+)、羅馬尼亞(BBB-) 、印度尼西亞(BBB-)、摩洛哥(BBB-)、格魯吉亞(BB-)、約旦(B+)、斯里蘭卡(B+)、波黑(B)、厄瓜多爾(B-)、埃及(B-)、加納(B -)。
 圖博館
圖博館
如果中國都應該被看空,被做空,那麼歐美日諸國早就應該掉到十九層地獄里永不翻身。
簡單說,就是自己裝完B自己信了唄?!自己把自己忽悠瘸了。開始是意識形態不同,為了證明西方的意識形態正確,就得證明自己標榜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正確。那麼中國的意識形態必然邪惡,中國的政治制度就必然失敗。那麼中國的政治制度怎麼失敗呢?找幫專家論證一下吧。專家給出結論,政治制度失敗,那就得體現在經濟失敗啊。 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嗖嗖滴啊,那怎麼辦啊?專家繼續論證出一個,你別看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那必然是有毛病滴。有啥毛病?經濟專家上來一桶論證,他們有負債,必然有隱患,要硬著路!得,結論出來了,中國要崩潰! 中國這邊呢?一邊自己印錢借給政府建基礎設施,一邊自己印錢借企業發展!然後目瞪口呆的看西方的各種專家戲精似的表演。愣是把政治正確發展出一個經濟結論,然後自己信了去投資了!
中國建國69年,西方哪天看多過?中國就是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成長壯大的,中國崛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8_01_24_444409.shtml
 圖博館
圖博館
在談及中國經濟為什麼始終沒有發生崩盤時,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基金經理邁克爾·戈麥斯(Michael Gomez)說:做空中國的人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有意願,也有財力來應對問題。
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就投資於中國的對沖基金老將馬克·金登(Mark Kingdon)表示,許多看空中國的人士只是誤解了這個國家,“在所有這些噪音下,人們有時候很容易忘記中國是一個有管理的經濟體,他們所有的債務都是自己欠自己的,他們還有數万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關注中國很多年了,他們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
《金融時報》還說,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正在著手解決信貸熱潮問題。
摩根士丹利估計,2017年前9個月,中國總體債務與GDP之比僅上升4個百分點,這與2015年至2016年上升42個百分點相比是一個“顯著改善”。摩根大估計,去年第二季度債務與GDP之比下降,這是自2011年以來首次出現絕對值下降。
........
回應
做空的再加把勁,還有二十來天中國就要崩潰了,工廠歇業,車少人稀,人們無所事事,甚至孩子們都挨家挨戶上門要錢......
放眼全球,只有中國真真正正,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地在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看空中國的不是壞就是蠢。
這裡一定要說下咱們制度的優越性:沒有黨的堅強領導,改革真的無從談起。
其實出現這個巨大的偏差根源在於中西社會結構不同,中國自古就是中央集權性質的國家,共和國成立後,政權甚至可以直接進入最基層的單位,這在西方分權制社會是無法想像的,西方社會普遍是金權集權、行政司法立法分權、多黨輪流執政、選民普選或代議制的社會模式,這與中國一黨執政、政治集權、內部分權監督的模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對於社會問題的控制力差異巨大,很多事情在西方社會的體制下無法解決,會形成巨大的各種風險,但在中國卻可以實現可控狀態。
說白了,做空中國失敗的基金經理意識形態太重,思維僵化,與羅傑斯等頂級投資人完全不是一個層次。
 圖博館
圖博館
英媒:看空中國的人已被迫嚥下苦果,他們誤解了這個國家
2018.1.21,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眼下,看多中國的人擊敗了看空者》的文章。文章稱,2018年,看空中國的人大多已被迫嚥下苦果。
《金融時報》說,2009年,首批意識到安然公司(Enron)騙局的基金公司創始人詹姆斯·夏諾斯(James Chanos)在聽過一個分析師的報告後,認為中國經濟將會迎來“硬著陸”,並毅然決然開始做空中國的公司,到處宣稱中國債台高築的經濟中潛藏著危險。
夏諾斯曾在2009年對美國財經媒體CNBC說,中國經濟存在巨大泡沫,理由是中國存在著規模龐大的過度信貸,“眼下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加信貸過度”。
受到夏諾斯的召喚,一群在媒體上頗具知名度的對沖基金經理很快跟進,浩浩蕩盪地開始做空中國。
但時間來到2018年,看空中國的人大多已被迫嚥下苦果。很多基金經理賠到傾家蕩產,有些基金經理開始轉為看多中國,一些人甚至關閉了自己的基金生意。去年,做空中國者遭受了尤為沈重的打擊。
根據紐約數據提供商S3 Partners的數據,2017年,做空在香港或者中國內地上市的中資公司的投資者遭受了逾350億美元的損失,幾乎是他們賭注的一半。
僅僅計算做空排名前三的中國公司,大空頭們的損失就高達185億美元。
其中,阿里巴巴是今年被做空最多的中資股,賣空金額高達233億;但自2017年年初至2017年11月,阿里巴巴的股價上漲108%,做空者按市值計算的累計虧損為122億美元。
中國平安保險,賣空金額為133億美元;2017年前11個月股價攀升82%,賣空者虧損達39億美元。
騰訊,賣空金額為51億美元;2017年前11個月股價大漲94%,賣空者虧損達24億美元。
另外,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稱,在做空恆大和融創這兩家以“高槓桿”而聞名的公司時,做空機構也遭到了重大損失。
《金融時報》說,儘管中國經濟已從10年前的兩位數增速放緩,而且在2015年和2016年都曾遭遇顛簸,但每一次顛簸最終都平息了下來。許多人當初預測的債務危機和匯率崩盤都沒有成真。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6.9%,這是兩年來最快的增速。
而據觀察者網此前報導,由海外上市中資股組成的MSCI明晟中國指數今年以來攀升約48%,在這家全球指數公司所追踪的任何國家指數中表現最佳。
 圖博館
圖博館
文化包含多個層面,當一個文化體跟另外一個文化體碰撞時,就會有強勢弱勢的差別,其決定因素在於經濟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基礎完全有可能不斷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識地實踐、倡導,中國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倫理價值取向,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行上層建築的創新。
今天,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地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係。除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6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有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條件相似,來自於中國復興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回應
林毅夫是比較早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理論不適合解釋中國發展的人,在國內一大幫經濟學家指責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要學習西方徹底私有化時,林就是提出不同意見的少數人。現在,好多經濟學家跟著人云亦云,因為事態明顯了,中國完全走的是適合自己的道路
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現象。然後他們會說:統計數據是假的。
所以林毅夫永遠都不可能獲得諾獎,但是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將永遠記入人類歷史,他自己明白,西方人也明白。
但這反而大大加強了林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中國的道路太超前了,這也證明了西方文明所謂的包容性多元性都是假的。
 圖博館
圖博館
西方主流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完全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必然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在現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照搬發達國家的道路、理論、文化亦不可行,學習參考他人要建立在對自己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礎上。
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自信,它意味著文化的綿延不斷。中國文化何以幾千年綿延不絕?首先,需清楚何為文化。我傾向於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即生產、生活工具;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倫理、價值取向,等等。五千年來,器物層次和組織層次的中國文化都在發生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體系始終綿延不斷。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都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延續的體現。
面向未來,伴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不斷釋放,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統之一的中華文化,能否與經濟基礎發展相適應並不斷演進,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精神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答案是肯定的。當西方還是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而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也頗為活躍。可以說,中華文化以及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係是共容的。
從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既能適應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實質,並以相應形式與變化相呼應。以儒家為例,孔子所以被稱為“聖之時者”,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他把過去的經典按照時代需要給予了創新性整理和詮釋,正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後儒家文化吸納了佛家文化的內涵,發展為宋明“理學”和“心學”,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承內容的中華文化有能力隨著時代而調整、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共中共19大新核心2017-10-26名單出爐「留二(習近平、李克強)進五(栗戰書接任人大主席、汪洋接任政協主席、王滬寧接任中央書記處、趙樂際接任中紀委、韓正.)」學界、媒體和兩岸關係研究圈猜測的名單和風聲卻大多「失準」:
英國BBC中文網(7中5),命中率71.4%
香港明報(7中5),命中率71.4%
美國馬可波羅智庫智庫(5中3),命中率60%
日本讀賣新聞(5中3),命中率60%
政大國關中心模型(5中3),命中率60%
調查局(9中5),命中率55.6%
英國路透社(6中3),命中率50%
中央社(7中3),命中率42.9%
國安局(2中0),命中率0%
回應
中共研究方法「失準」
別說「中共研究方法」、就連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洋學(邪?)者為典範!
林毅夫:西方國家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奇蹟2017.10.27人民日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學會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拿來推行,就能夠取得發展和轉型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幾十年的實踐證明, 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蹟。
以我的專業領域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自主追求現代化之需,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以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二戰結束至今已70餘年,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所推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結構主義角度來看恰恰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我國改革開放以後以漸進雙軌方式轉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如果從新自由主義視角來看卻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衰退:慢慢陷入倒塌式的惡性循環
作者: 金偉倫
出版社:領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31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真將陷入蕭條?
資金非法流出中國居榜首
江下習上李嘉誠加速撤離
信心動搖,老百姓不敢花錢了
習近平掌控經濟的信心動搖
中國經濟要跌回全球平均值
中國真的進入通貨緊縮時代了嗎?
新年經濟增長靠什麼?
巨龍減速,亞洲準備好了?
中國恐將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李嘉誠新年加速撤離再放危險信號
跨國企業爭相向中國快速投降
城市大躍進造就諸多“鬼城”
中國“超越”市場的改革之路
報告首長:東北經濟告急!
各地市長傻眼,43號文件或改變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談大數據
王岐山老伙計的肺腑之言
防火牆把中國科學從巨人肩膀上拉下來
焦慮的中國人
作者: 茅于軾
出版社:天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8/15
內容簡介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繼續30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
中國晉身經濟巨人,為何民怨卻與日俱增?
深層次矛盾不解決,將引爆政經大變局?
經濟學界良心、「佛利民自由獎」得主茅于軾,直面中國改革頑症、貧富皆怨之危,把脈下藥的敢言之作!
中國社會矛盾日深,未來步向崩潰,還是延續輝煌?
大國已經崛起,中國人卻充滿怨氣。焦慮根源不僅是貧富懸殊或貪污腐化,而是社會不公義,官員不講理。追求GDP卻犧牲人民幸福,甚至引來「中國崩潰論」之說,預言巨變一觸即發。
站在發展路口,中國下一步應如何走?如何在大危局尋求化解的機遇?被喻為「經濟學界良心」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直搗改革開放的弱點,指出社會及政治危機與經濟問題一脈相承,只有建立保護財富的體系,順應市場和公正的洪流,中國才能在改革頑症中扭轉乾坤。
目錄
前言 正視社會不公
第一章 蝸居在中國
第二章 窮人為何貧窮
第三章 富人如何致富
第四章 消除貧富分化
第五章 人權與中國社會
第六章 人民和國家利益
第七章 自由市場必勝
第八章 未來世界如何
8.1 中國人口隱憂
8.2 尋找「人間天堂」
 圖博館
圖博館
為什麼中國經濟走向崩壞:大國空巢下的危機與出路
The Road to Ruin
作者: 李國平
出版社:有意思
內容簡介
2010年初,美國《新聞》周刊將「中國經濟的崩潰」列為「2010年十大世界預測」第二位。同年,《紐約時報》以「做空中國」的大標題發表了對華爾街空頭大師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的採訪。中國過多的貨幣造就了房地產泡沫,一旦其經濟體系無法繼續支撐新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的經濟增長程度勢必大幅放緩,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崩潰。
實際上,除了通貨膨脹接近5%外,中國經濟算是平安度過了2010年,而且增長率還達到9.7%。在中國政府推出房產限構的禁令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沒有下跌,更沒有泡沫行將破裂的跡象,「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似乎已經不攻自破。
然而,中國經濟沒有在2010年崩潰,並不意味以後就不會崩潰,因為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那些問題並沒有隨著2010年的過去而消失。
數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的「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日趨惡化的跡象。在繁榮的表面之下,中國經濟仍然效率低下,缺乏創新能力,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而且,貧富分化極端。
目錄
第一章 效率低下的經濟增長
第二章 沒有消費的經濟增長
第三章 沒有創造力的經濟增長
第四章 脆弱而效率低下的金融體系
第五章 特權集團壟斷國家經濟
第六章 三大差距危機
一、全球最嚴重的貧富差距
二、農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苦?
三、東部六省市占了中國富豪的一半
第七章 資源與環境危機
第八章 人口危機
第九章 出路在哪裡?
一、停止「GDP崇拜」
二、「王者富民」
三、民進國退
四、約束政府權力
結語 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公平中國
作者: 王福重
出版社:中華
出版日期:2014/07/25
內容簡介
公平是未來很長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本書論述了其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個問題:農村、義務教育、高考、大學、養老、醫療、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稅、公共預算、央企、外匯儲備、計劃生育。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需要以公平為準繩,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這樣才能走向一個和諧的社會。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失控中:大陸的機會和危險都失控,有人套利、也有人心血落空,你得先認清哪些現實
「中国の夢」は100年たっても実現しない
作者: 山田順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27
內容簡介
權威機構一直在替中國背書、按讚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測,2060年,中國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
4.0%,美國為2.1%,中國將成為全球之首。
將成為全球之首
◎高盛集團繼金磚四國之後,提出中美逆轉論:中國成為經濟的世界第一大國。
◎北京政府宣布,2020年中國人將登上月球(月亮將成為超級核彈基地)。
但住在大陸的人,會告訴你:
◎中國的水和油都遭到汙染,食材再好也枉然。
◎從農村到城市各省都有癌症村: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罹癌。
◎每天都有爆炸案,大工廠會爆、連番茄西瓜也會爆!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高居世界第一。
郎咸平說──中國進入從亂局到變局關鍵十年!:金融、樓市、食安、教育等改革,重裝上陣!
內容簡介
► 中國金融「一身病」:中國股市先天不足、實體經濟萎靡;保險業停留在美國一百年前水準,還在靠欺詐賺錢;再加上國有銀行壟斷,最終導致「負利率」,中國金融圈,亂!
► 貪腐除不盡,春風吹又生:賣官鬻爵,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審批制更是腐敗的「源泉」。想用高薪養廉與運動式反腐止貪,難!
► 霾害愈演愈烈五十年:霧霾籠罩七分之一國土,然政府始終無作為。唯有讓PM2.5和政績考核掛鉤,霧霾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 新型城鎮化引發「逆城鎮化」危機:農民工數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設「大躍進」無人埋單,製造更多「空城」。「逆城鎮化」則導致有效勞動人口減少,地方財政負擔更沉重。
► 詭異瘋漲的樓市:通膨,讓老百姓把錢投入房地產;製造業利潤下滑,令企業家把錢投入房地產。這兩股熱流,讓中國房價一發不可收拾地瘋狂上漲。
► 房產稅壓垮房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地方政府無地可賣,製造業低迷難收稅的情況下,房產稅成為支撐地方財政的新稅源,完全背離了原本的「均富貴」初衷!
目錄
序言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第一篇 中國改革重裝上陣
第二篇 經濟弊病無處遁形
第三篇 金融變局迫在眉睫
第四篇 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經濟底氣
作者: 陳琳琳
出版社:財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9
內容簡介
每當中國經濟遇到困境,中國崩潰的論斷便被提出來。然而,中國崩潰論的預言一次次的落空。“中國崩潰論”預言的落空,激發了它的對立面“中國模式論”的流行。
專制窮國可能停滯發展幾十年,卻並不發生政治崩潰。真正的問題是,領導階層願不願意降低增長目標,讓增長更能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還是會覺得有責任繼續堅持那些居高不下的增長目標?
自改革開放國策被確立30 多年來,“社會主義威權政體”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因沒有實施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使得一個能夠對經濟發展施加主導掌控力的“有為政府”成為可能;其次“有為政府”選擇了正確的發揮比較優勢的經濟戰略。
不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依賴於政府主導的巨量投資不可持續下去,已經到了盡頭。目前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精英集團,是否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和緊迫?
赤色浪潮:Made in China蘊含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 高先民, 張凱華
出版社:上奇資訊
出版日期:2015/11/30
內容簡介
曾經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現今Owned by China,中國擁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造訪英國,大把的中國訂單為這次訪英行程鋪好了紅地毯。BBC中文網直指,中國正用人民幣買下英國。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文字,精闢分析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世界地位,涵蓋中國經濟發展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各個領域。
2010年,Google正式關閉中國版搜尋引擎,高調退出中國市場。
然而,中國網路產業發展急劇增長,現今全球網路公司市值最高十強,亞洲占了4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及京東,全來自中國。
面對看得到卻吃不到的中國市場,美國科技大腕怎能不著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臉書執行長祖克伯的互動,尤其引人好奇。
不論「Google重返中國」「2016中國對臉書解禁」的傳聞真偽,都直指一個不可擋的趨勢──.CN時代正在來臨。
目錄
1.「中國製造」-新「世界工廠」正在崛起
2.「13億」-充滿無盡想像的大市場
3.「人民幣」-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金融符號
4.「A股」-全球資本市場的奇蹟
5.「.CN」-中國的互聯網世界第一
6.「改革開放」-中國符號的前行動力
 圖博館
圖博館
從世界工廠變世界市場,中國13億人的驚人消費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場,然而許多外資卻也發現,他們在中國生存日益艱難。全球頂尖的中國商業經營個案分析團隊,從歷史、政治、企業管理三大面向,深入淺出剖析當前中國政府的實力和目的,大膽直陳中國經濟成長的關卡與在中國做生意的陷阱。所有現在或未來打算在中國投資經商者,來往兩岸的跨國企業經理人、上班族,都應該一讀。
目錄
推薦序 放不下的第六力——不確定性的根源 馬紹章
導論 重新檢視中國經濟奇蹟
第一章 迷思與現代中國之形成
第二章 黨公司:中國紅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侷限
第三章 工程國家:路的盡頭
第四章 計劃革新?
第五章 在中國獲致商業成功
第六章 全球中國:權力的極限
第七章 中國2034
2016年中國難題
作者: 劉金山
出版社:外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5
內容簡介
在美國智庫的報告中,中國被列為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中國股市今年開門大黑,已經反映中國人自己深深的憂慮。但是,這不僅僅是溫家寶濫發貨幣的遺禍,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已將獲利空間榨乾,現在已經到了結構性的銅牆鐵壁面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回到幾年前的黃金時代。
在內政上,民眾將權貴集團譏諷為「趙家人」,但沒有人找到辦法緩解他們與平民的對立情緒。幸而,一般百姓只是將怨氣宣洩在口頭上,新疆人卻是以命相爭。中國立出《反恐法》,也就將分離分子當作恐怖分子予以摧毀。只是生死恩怨已經深根了。
在外交上,「擻幣」很多國家還是頗有效果的,但並非萬能,南海島權之爭沒有顯示出和解的前景。中國是否真有打算硬拼一場?也許這就套住了中國雄心。
 圖博館
圖博館
「+」指的是「連接」,即連接傳統各行各業;「跨界融合」是全書的主要概念,也是書中諸位倡導者不斷強調的重點。
本書從理論層面、實踐經驗等多角度切入,全方面闡述互聯網結合各產業的趨勢,推薦給關心傳統產業轉型、互聯網新經濟等具備前瞻性思維的讀者。
目錄
第一篇 「互聯網+」成為國家戰略之因
第一章|「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
第二章|「互聯網+」時代的六大特徵
第三章|順勢而為,勢是什麼
第二篇 「互聯網+」連接一切
第四章|互聯網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
第五章|用「互聯網+」連接未來
第六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1) 眾創空間
第七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2) 微信
第八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3) 泛娛樂
第九章|連接社交網路
第十章|連接數位鴻溝
第三篇|「互聯網+」行動計畫
第十一章|行動計畫導引
第十二章|互聯網+工業
第十三章|互聯網+金融
第十四章|互聯網+能源
第十五章|互聯網+健康、教育
第十六章|互聯網+智慧生活
第十七章|互聯網+X
第十八章|時代的風口
強國不強?:中國國力與經濟成長的極限
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
作者: 雷影娜, 柯偉林, 沃倫‧麥克法蘭
原文作者:Regina M. Abrami,William Kirby,F. Warren McFarla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6/06/29
內容簡介
哈佛商學院、華頓商學院著名中國通最新力作!哈佛商學院熱門課程菁華!
面對中國空前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又是如何與全球競爭?
從傳統製造業到網路電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無所不在,外資企業的機會又在哪?
到中國經商,技術早晚會被轉移或偷走,你能保護自己維持領先嗎?
公司的中國風險組合有適當的避險安排嗎?
以黨領政下,為什麼中共依然沒有安全感?國內維穩、國防事務仍然占極高預算比例?
 圖博館
圖博館
◎第二章 一種深厚的文化價值觀
約翰‧奈斯比及夫人:中國是蘋果,美國是橘子
約瑟夫‧奈伊:在曲阜感悟中國軟實力
勞倫斯‧庫恩:中國夢並非模糊空洞的口號
趙錫成、趙小蘭父女:中國夢意義深遠
沙學文:將中國夢注入中國製造
凱瑞‧布朗:中國歷史應是西方的必修課
彼得‧聖吉:中國包容文化將重獲新生
柯偉林:中國很強大,但還不夠自信
◎第三章 一種獨特的政黨制度
約瑟夫‧奈伊:反腐就是增加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
皮特‧鮑泰利:民主的要義是為人民負責
貝淡寧:當代賢能政治是中國的大進步
大衛‧麥克萊倫:高效是中國體制的巨大優勢
廖燃:腐敗與政治制度無關
托尼‧賽奇:學美國沒什麼意思
◎第四章 一種成功的經濟模式
斯蒂芬‧羅奇:戰略思維是中國發展奇蹟的精髓
吉姆‧奧尼爾:中國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規
米夏埃爾‧普法費爾:德國對中國企業沒有偏見
馬西莫‧羅依:中國房地產不是華爾街式泡沫
理查‧福爾德:中國經濟不會有「雷曼時刻」
蓋爾‧拉夫特:中國不必為減排「忙於招架」
◎第五章 一種中國式的和平崛起
包道格:中國崩潰論已成笑料
季塔連科等:中國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
塔德烏什‧霍米茨基:中國發展有利於全世界
艾瑞克‧霍布斯邦:中國降低了全球戰爭的危險
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中國為非洲打開了一扇門
傑克‧斯奈德:中國離過度擴張還很遠
愛德華‧N‧魯瓦克: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恐慌在加劇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美國沒有能力阻止中國崛起
古斯塔夫‧格拉茨:歐洲的抱怨上不了臺面
馬丁‧雅克:西方年輕人在思考,為什麼中國做的好
拉納‧米特:作為二戰盟友的中國,不該被遺忘
互聯網+:中國經濟成長新引擎
作者: 馬化騰、張曉峰 等著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30
內容簡介
騰訊官方唯一正版授權
瞭解中國國家級戰略「互聯網+」權威讀本
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最新指標政策
中國傳統企業正在飛速轉型!
當「互聯網+」的革新如大潮來襲 台灣勢必得站在浪頭上
跨界融合,連接未來無限可能
「互聯網+」是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的新常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認為據此發展順勢而為,將能提升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的水準。
 圖博館
圖博館
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
作者: 季辛吉, 約瑟夫‧奈伊, 大前研一, 法蘭西斯‧福山, 約翰‧奈斯比 等著
出版社:風雲時代
出版日期:2015/07/21
內容簡介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
到底是誰要崩潰?誰才是最大威脅?
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中國模式」是什麼?
中國的「軟實力」又是什麼、表現在何處?
誰才是當今世界真正的超級強權?
不能小看的中國實力,你該了解的中國真相!
本書集結了《環球時報》記者於二○○九至二○一四年對西方政要、學者的部分專訪,採訪對象包括季辛吉、法蘭西斯‧福山、約瑟夫‧奈伊、美國前總統卡特等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作為西方長期深研中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智庫成員,他們不僅曾經銳利地對中國提出批評,也具有面對中國崛起而承認現實、自我糾錯的勇氣。本書所集結的文章反映了他們對西方種種「誤解」的最新認識,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對中國文化、現實與趨勢的重新認知和判斷。
目錄
序言一 請不要誤判中國 張維為
序言二 瞭解中國很難,但必須瞭解 金燦榮
◎第一章 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
季辛吉:中美有責任建新型大國關係
約瑟夫‧奈伊:中國變富,中美都會受益
法蘭西斯‧福山:中國崛起對我的理論形成挑戰
卡特:美中合作既是機遇也是責任
布里辛斯基:美民間對華批評源於無知或焦慮
大前研一: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
桑德施奈德:中國就像一面遠方的鏡子
恩道爾:中美關係的不利因素在美國
斯蒂芬‧佩里:國際權力偏移中國讓西方不爽
米爾斯海默:我希望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
道格‧班道:現在是美國真正改變其對外政策的時候
休‧懷特:澳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促進中美平等對話
 圖博館
圖博館
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圖博館
圖博館
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圖博館
圖博館
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圖博館
圖博館
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圖博館
圖博館
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圖博館
圖博館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圖博館
圖博館
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
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
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
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
 圖博館
圖博館
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禀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
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避免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台,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
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
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
 圖博館
圖博館
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禀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禀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禀賦結構的狀況。
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禀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鬚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
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製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
 圖博館
圖博館
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
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
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
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圖博館
圖博館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圖博館
圖博館
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
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了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藉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藉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1988年我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
 圖博館
圖博館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
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了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像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
 圖博館
圖博館
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
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
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圖博館
圖博館
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資本密集。後來了解到,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複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而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
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圖博館
圖博館
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了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
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
 圖博館
圖博館
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乾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
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圖博館
圖博館
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2017-5月13-14日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號】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
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複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圖博館
圖博館
印媒:印度小地方意識到中國影響但對中國了解少
印度 Scroll網站2017.1.24文章,原題:印度小地方意識到中國影響,但對中國了解很少馬哈拉施特拉邦索勒布爾一所夜大的教授莫漢最近招收到一名博士新生:正在該校做兼職的某中學教師班達里。他們在準備應對相當陌生的課題:中國。
如今,中國投資者和官員正走遍印度內地以尋找投資機遇。但在印度的小地方,當地官員直到最近尚無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也無可供諮詢的專家。中國是印度最大貿易夥伴,但印度對中國的了解僅限於學術圈:德里的小型智庫以及西孟加拉邦和南印度的某些大學。
“對中國研究的大力投資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位於德里的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阿爾卡•阿查里雅說,“我們需要在大都市以外地區培養更多人才,使他們能夠直面中國在就業及經濟機遇乃至社會交往領域的存在。”在印度,研究中國的學術會議已從大都市擴展至南部和東北部的大學。但分析人士稱,長期參與該“小眾”領域研究的新人仍微乎其微,各研究中心也不具備在印度各地培養此類學者的實力。
相關新聞
印媒:被遙遙領先!印度旅遊業遠遜於中國的5個原因2017-01-24
英媒:中國對出口依賴將低於印度可抵禦特朗普任內貿易緊張2017-01-23
印媒:2017年,印度應擁抱中國而非美國!2016-12-27
印媒:印度乘客愛上中國低價航班世界航空面臨挑戰2016-12-26
回應
印度當年在錯誤的觀念下跟中國打了一仗,不從自己角度分析,吸取教訓;此外對中國對中華民族了解相當膚淺,誤以為中國跟那些老牌或者新興的殖民地國家一樣,一直對中國懷有不正確的想法,不肯與中國真誠合作,不願意接受中國的援助。可以說這是它的致命傷。日寇也罷,美國也罷,是不可能真誠幫助它的。
這個國家依然沉浸在大英帝國殖民的輝煌記憶中,對東方龍的騰躍視若無睹。
就像越南對中國愛恨交加一樣,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印度必須接納中國經濟的春風……其實隨著中國川藏鐵路的施工,中國內地鐵路從西藏經尼泊爾到印度也就是十年多一點的事,就怕印度小雞肚腸……
印度從西方學了不少殖民主義的流氓伎倆。
阿三仍活在狹隘夜郎自大的思想裡
 圖博館
圖博館
羅思義:IMF調高中國GDP預測,為何?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IMF在2016年10月發布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將美國2016年增長率下調至1.6%,即從2015年2.6%的增長率基礎上嚴重減速。與此同時,IMF預測中國2016年增長率從6.3%上調到6.6%。
分析這些也有助於弄清,IMF一直以來所做的錯誤預測只不過是為了唱衰中國、唱多美國,跟彭博和其他西方媒體沒什麼兩樣。
IMF的錯誤只是其長期的錯誤預測模式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有必要對IMF就中美經濟趨勢所作的錯誤預測做一番總結。
IMF去年的預測嚴重失誤不得不做出調整
增幅大幅放緩的是美國而非中國
IMF的錯誤預測對中國的誤導
IMF的公信力危機
從長期角度來看,IMF的整體戰略分析顯然也是錯誤的。正如拙文《世行數據中隱藏著一個秘密》的詳細分析,數十年來,效仿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經濟體的表現,遠優於效仿IMF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經濟體。............
首先,媒體為IMF錯誤預測做吹鼓手,可能阻止一些潛在的外國對華投資。其次,IMF具有誤導性的預測可用於扭曲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討論,進而主張制定一些危害中國的政策。
一個結論顯而易見:IMF的政策幾乎沒有公信力,這可以幫助我們盡量減少破壞性的政策對中國的不良影響;試圖借IMF的“權威性”預測唱衰中國不再具有可信性。
回應
老羅才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然而即使是西方人,說中國好話是拿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按林毅夫說的那樣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一群學術近親繁殖的小圈子自嗨,比的是誰學生多。
羅思義總讓人想起楚國國籍的秦國謀士李斯,張儀,魏國國籍的秦國謀士商鞅,范雎。祝愿今天的中國像當年的秦國一樣積累上百年的強盛國力,一統天下。
老羅啊,你讓一些中國的媒體偽經濟學家都沒臉在中國待下去了!
老羅啊,你讓一些中國公知大V噴子的媒體偽經濟學家都沒臉在中國待下去了!
這個你放心,國內的那些媒體人及偽經濟學家臉皮之厚遠超你的想像,更何況他們若不待在國內,你認為還會有人給他們發狗糧嗎?
國內有很多經濟學家,都接受美國那套經濟學,被人家洗腦了。說白了,這些經濟學家無意間成為美國的間諜,潛伏在中國經濟界裡,蓄意搞破壞
 圖博館
圖博館
接班人 傳習近平已有中意人選 2016-10-09世界日報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引述專家和政界內部人士表示,推遲的做法可為習近平贏得更多的時間,來提拔和考驗他中意的候選人,並防止自己的影響力漸漸轉移到繼任者身上。但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在一群有抱負的幹部競爭最高領導人職位時出現的數年內耗,以及一種令人不安的不確定性,即習是否想超出黨總書記通常的兩屆任期,繼續把持權力。
據報導,不具名人士透露,習要等到他中意的人選有了更多的經驗,經過了更多考驗之後,才會做出決定。還有專家認為,推遲選擇繼任者可以給習中意的人選提供時間,讓他們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忠誠度。有了忠誠的繼任者,習就可以在離任之後繼續在幕後行使權力。
不過報導指出,幾名專家表示,黨的上層發生內鬥的風險,以及來自其他高級官員和已退休的領導者的要求,可能仍會迫使習在明年釋放出誰是自己繼任者的信號。如果他被迫指定一名繼任者的話,像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那樣的年輕政治局委員,可能會得到黨內的支持。
然而,報導引述幾名專家及與高級官員有往來的人士說,習也面臨著困境,明年那輪退休之後,最高層留下來的政客中,沒有長期與習共事的經驗,也沒有在省級和中央政府的適當位置上工作過。那些據認與習關係最密切的、處於上升期的省級領導幹部缺乏經驗,難以讓人將他們作為待任的國家領導人來認真對待。
此前,外界諸多猜測指向,習在2022年第二個任期結束後,將繼續把持權力。雖然憲法要求他在國家主席的位置上擔任兩個任期之後退休,但對權力更大的黨總書記的職位沒有任期的限制。
美智庫:習近平可能延遲挑選繼任人選 2016-10-08 中央社
中共18屆六中全會24日起將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是決定明年中共19大人事布局和權力再分配的關鍵一役。一般相信,明年春天人大開會前,官方不太可能做出任何決定,不過隨著黨內競爭加劇,內部派系紛爭勢必更加尖銳。
紐約外交關係協會(CFR)在綜合整理「解析亞洲」(Asia Unbound)部落格文章提及,習上任後推動的反貪腐運動已讓他在黨內取得空前無比的地位,外界謠傳他一直有意以其反貪腐左右手王岐山取代現任總理李克強。
回應
又鬼扯蛋!低劣媒體事前大炒特炒事後當成沒事。然後另起話題再繼續灑狗血,周而復始,一點徵兆或根據都沒有天天鬼扯
 圖博館
圖博館
“一帶一路”之所以受歡迎,關鍵還是在於符合了各國的需要。中國推進基礎設施投資,“要致富,先修路”,這句最樸素的中國發展經驗,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發展共識。中國推進投資走出去,正在成為全球第三大的對外投資國,五年內很有可能躍升為全球第一大對外投資國,誰能拒絕中國的“投資”呢?中國還是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與“一帶一路”的貿易額年增長20%左右。更重要的是,每年中國有1億多遊客到海外旅遊與消費,相當大的增量都在“一帶一路”地區。去年,中國赴土耳其、伊朗的遊客增長了30%以上,哈薩克斯坦等國也在與中國談如何放開旅遊簽證。大家想一想,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力啊?
可見,“一帶一路”重塑了中國崛起的路徑,也讓中國可持續發展越越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設立的兩條傳統路徑,重寫了未來的國際發展與大國崛起歷史,呈現了第三條大國崛起的道路。
當然,這不等於“一帶一路”沒有風險,也不是說“一帶一路”目前不存在問題。一年前,我訪問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官員問,中國沒有正視“一帶一路”恐怖主義、政局不穩、主權債務高風險等問題,“一帶一路”不可能成功。當時,我非常真摯地告訴美國官員,與中國合作搞“一帶一路”,美國不會虧的。
現在,美國官員與智庫專家都很後悔,都認為美國沒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戰略錯誤。今年4月18日,人大重陽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合作辦了第一次公開的“中美一帶一路智庫對話”,來了許多美國專家、官員。他們向中方傳遞的信息是,美國人已開始認真地考慮“一帶一路”了,並尋找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
我想,現在還不晚。今天在場有10多位政要,一定要告訴本國人民,千萬不要錯過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機遇。
謝謝。
回應
有美國參加,一帶一路就不會成功!這是基本常識!
這個第三個不說的還太早,首先中國崛起本身就是在這個不平等的國際舊秩序裡,而且中國的一部分資本家在非洲拉美的表現,和100年前的西方殖民者也沒有太大區別
我們殺人放火了還是販賣人口逼良為娼了
西方殖民者是靠著奴隸貿易起家的。
講真的,每次看到這個頭像,看到這個名字,點踩八成沒錯
 圖博館
圖博館
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威脅論”,還是“中國崩潰論”,都失敗了。去年,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巴伯到人大重陽訪問,我對他說,未來的國際媒體人和讀者們會感到奇怪,21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即中國崛起的偉大故事,所有的西方媒體裡都找不到歷史的真實紀錄。因為你們的報導中,大多數是中國的負面內容,或者是惡意的威脅揣測。難道你們西方媒體人對此不感到羞愧嗎?
很多歐美學者說,時間還太短了,不足以證明“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是錯誤的。他們會說,看,南海、釣魚島,中國多大的威脅啊!看,中國的地方債、中國經濟下行,中國一定會崩潰啊!
我常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常以這種“自我應驗的預言(fullfilling prophecy)”來觀察中國,那你們永遠都不可能看準中國的未來。你們錯了20多年,還想繼續錯下去嗎?我建議你們多研究研究“一帶一路”。
現在,“一帶一路”已是中國最大的外交政策,是中國崛起後給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是使中國得以超越“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關鍵戰略,也將使中國成為第一個不依靠戰爭、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金融和經濟體係而成功崛起的大國。“一帶一路”使中國走上了大國崛起的第三條道路。
因為“一帶一路”沒有輸出戰爭、沒有到國外去殖民、沒有在“一帶一路”的各個國家建立不平等的貿易經濟和金融體系,而是貿易合作、金融合作、基礎設施合作等共贏的合作,將城市與城市之間連接起來,將國家與國家連接起來,真正既使中國走上了可持續的道路,也讓各國搭上中國崛起的順風車。
過去兩年多,國內外有許多人都錯估了“一帶一路”的前景。一年多前,我曾寫過一篇《“一帶一路”的風險被誇大》的文章,引起了不少關注。現在看來,各種觀點仍有效。“一帶一路”沒有受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是受到了未曾想到的歡迎。
我與人大重陽的同事近年來去了40多個國家調研,真切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受歡迎程度。近30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協議、70多個國家公開宣稱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還與中國逐漸展開各個項目的合作,至少有九個國家設立了類似“絲路特使”、“絲綢之路大使”等專門職位,負責與中國的戰略對接。
 圖博館
圖博館
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威脅論”,還是“中國崩潰論”,都失敗了。去年,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巴伯到人大重陽訪問,我對他說,未來的國際媒體人和讀者們會感到奇怪,21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即中國崛起的偉大故事,所有的西方媒體裡都找不到歷史的真實紀錄。因為你們的報導中,大多數是中國的負面內容,或者是惡意的威脅揣測。難道你們西方媒體人對此不感到羞愧嗎?
很多歐美學者說,時間還太短了,不足以證明“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是錯誤的。他們會說,看,南海、釣魚島,中國多大的威脅啊!看,中國的地方債、中國經濟下行,中國一定會崩潰啊!
我常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常以這種“自我應驗的預言(fullfilling prophecy)”來觀察中國,那你們永遠都不可能看準中國的未來。你們錯了20多年,還想繼續錯下去嗎?我建議你們多研究研究“一帶一路”。
現在,“一帶一路”已是中國最大的外交政策,是中國崛起後給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是使中國得以超越“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關鍵戰略,也將使中國成為第一個不依靠戰爭、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金融和經濟體係而成功崛起的大國。“一帶一路”使中國走上了大國崛起的第三條道路。
因為“一帶一路”沒有輸出戰爭、沒有到國外去殖民、沒有在“一帶一路”的各個國家建立不平等的貿易經濟和金融體系,而是貿易合作、金融合作、基礎設施合作等共贏的合作,將城市與城市之間連接起來,將國家與國家連接起來,真正既使中國走上了可持續的道路,也讓各國搭上中國崛起的順風車。
過去兩年多,國內外有許多人都錯估了“一帶一路”的前景。一年多前,我曾寫過一篇《“一帶一路”的風險被誇大》的文章,引起了不少關注。現在看來,各種觀點仍有效。“一帶一路”沒有受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是受到了未曾想到的歡迎。
我與人大重陽的同事近年來去了40多個國家調研,真切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受歡迎程度。近30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協議、70多個國家公開宣稱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還與中國逐漸展開各個項目的合作,至少有九個國家設立了類似“絲路特使”、“絲綢之路大使”等專門職位,負責與中國的戰略對接。
 圖博館
圖博館
王文:美國官員曾跟我說,“一帶一路”不可能成功
【2016.5.29,主題為“一帶一路框架下:包容、可持續發展和可抵御風險的城市”的從都國際論壇在廣州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中國對外友協會長李小林,拉脫維亞前總統、世界領袖聯盟主席弗賴貝加,尼日利亞前總統奧巴桑喬等10多位國家前政要參加了會議。觀察者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在第一天全場討論會中主旨發言,同場討論的還有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坦桑尼亞前總統姆卡帕、韓國前總理韓昇洙等。本文是作者應約就討論核心內容補充完成的專欄文章。】
潘德里歐前總理、姆卡帕前總統、韓昇洙前總理還有場內的各位政要、各位專家:
感謝主辦方的邀請,感謝主持人楊潔勉教授。今天我們談“一帶一路”,最大的背景是中國崛起。所以,我的發言從大國崛起講起。
過去兩百年,西方的大國崛起都只有兩條選擇,一是崛起失敗,有的淪為全球二等強國,有的國家崩潰或解體,19世紀的法國、20世紀初的德國、20世紀下半葉的蘇聯和日本都是“失敗的大國崛起”的典型。二是成為現存霸權國的重大威脅,並通過戰爭的方式成功崛起,如18、19世紀的英國,分別戰勝了原有的“海上馬車夫”西班牙和通過拿破崙時期的法國,成為“日不落帝國”;20世紀的美國,通過1898年美西戰爭與抓住了一戰、二戰國際機遇,造就20世紀的全球霸權。
過去20多年,從1994年美國輿論第一次喊“中國崛起”以來,美國智庫界、媒體界就是基於自己的歷史經驗,大體對中國崛起進行了鐘擺式、兩分法的“預測”。一種是“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會發動一場或幾場戰爭,自從美國海軍學院揣測“2015年中美海戰”落空以來,最近美國國防部長、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又開始基於南海爭端,預測中國下一次軍事行動,甚至把中國視為像蘇聯那樣假想敵;另一種論調是“中國崩潰論”,除了章家敦、克魯格曼之後,去年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教授又發了《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文章。過去一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速變緩,關於“中國崩潰”的輿論又開始多起來。
 圖博館
圖博館
回應
羅思義有此體會與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他不是書齋裡的經濟學家,而是在倫敦擔任過主管經濟的高官的經濟學家,他從中西兩種不同機制的對比中看到了孰優孰劣。另外,他是英國左翼人士,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同時他又熟悉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這也使他在不同理論的對比中看到哪種理論更有道理。現在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即使不帶意識形態偏見,也總是誤判中國,就與他們缺少羅思義這樣的經歷有關。
任何制度都是有生命週期的。因為製度本身在一定時期內是固定的,穩定的,而社會本身則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一項製度在其初創期,是符合社會發展現狀的。而當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與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而 製度本身不變。就會導致制度紅利慢慢消退,消失,乃至變成阻礙社會進步的製度。此時,如果想要讓經濟社會繼續增長,就需要進行改革。....... 現在,對於中美兩國,事實上都走到了一個改革的關鍵節點。中國的問題是必須通過全面的經濟社會改革使得經濟發展模式得以轉變,以適應產業升級。而美國的問題則在於經濟的過度金融化,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現在看中國的改革雖然艱難,但卻在穩步推進,而美國的改革根本不存在。看的出美國的國運已經開始轉向。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蘇俄與中共 )
 圖博館
圖博館
1996年,運用同樣的經濟理論框架,我在題為《論歐洲單一貨幣的基本經濟意義》(英文請點擊)的文章中(中文版請點擊),準確地預測到歐元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我可以肯定,這種創建單一貨幣體系的方式,會導致加入歐盟的相當一部分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將會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具體體現為經濟蕭條、失業、貧困、福利制度崩潰、工會被削弱,以及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犯罪等現象增加。結局要么是一場經濟災難,要么是歐盟史上最大的危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今,我的分析得到了證實:希臘等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法國“國民陣線”等極右勢力和排外黨派崛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 )稱,“美國將是第一個從這場危機中復甦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將是最後一個。”我則認為,中國將會繼續以遠快於美國和任何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增長。事實再次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至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8% ,中國則增長80%——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10倍。
任何理論能否通過檢驗,是看其能否準確預測事實。事實證明,我對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經濟災難、歐元創建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等過去20年最重要的國際經濟事件的預測分析,都是正確的,西方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測則是錯誤的。這說明,作為外國人,我有可能為中國智庫做出一些自己的貢獻。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凡事要尊重事實,要“實事求是”。這些重大事件驗證了源自於中國的經濟理論,在涉及中國自身乃至全球重大發展事件中的正確性。
與中國經濟的最早淵源
但應該說明的是,我作出這些正確分析的原因,並非基於個人視角或者自身優勢。並非因為我三十多年前就多麼了解中國。我的初步結論是根據經濟理論得來的。我最初的研究領域就是國際經濟,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曾學習蘇聯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圖博館
圖博館
羅思義:我為什麼對中國經濟如此痴迷? 2016-04-29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羅思義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發布之際,他首次對三十年個人經歷、學術生涯,以及對中國經濟思想認識來了一次大梳理。文中談及他如何對中國經濟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及他在任倫敦“副市長”時與中國的交往,在中國智庫工作7年關於中國經濟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經濟思想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做出獨特的歸納分析,既有感性流露又有理智分析。羅思義獨家賜稿觀察者網發布。】
我研究中國經濟三十多年,從撰寫第一篇中國經濟的文章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中國不僅取得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而且逐漸形成了世界最先進的經濟思想。
我的說法並沒有誇大其辭,具體原因在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有詳述。而且,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持此看法了。當時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詳細闡述了我的這一觀點。
作為外國人,用西方經濟學術語,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輕鬆闡述中國的經濟政策成為我的優勢。如《一盤大棋》所示,我用這兩種理論體系,分析了中國經濟制度具有優越性的原因。
上世紀90年代,我就曾預測到中國經濟改革將會取得成功,以及西方倡導的“休克療法”將會讓俄羅斯遭受災難性的失敗,而當時和我持同樣看法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是極少數。
1992年,我撰寫過文章《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觀點如題,一目了然。
當時討論的陣營涇渭分明:研究前蘇聯經濟形勢的絕大部分(約佔90%)的西方經濟學家支持“休克療法”,只有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內的少數人反對“休克療法”,但後者也未預測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取得成功。只有極少數(大概不到1%)的西方經濟學家,也同我一樣預測中國的模式會取得成功、西方的“休克療法”模式會造成災難性後果。
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可謂是天壤之別: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俄羅斯則遭受了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
 圖博館
圖博館
【英】羅思義:中國經濟硬著陸預言為何總失敗2016-03-18 環球時報
日前,美國一些對沖基金又在鼓吹中國經濟將“硬著陸”,這一論調在部分國際媒體得到響應。1978年中國開啟經濟改革,此後幾十年,這種歪曲預言總是周期性出現。此前西方預言,如果不能實現公司私有化,不採取俄羅斯和東歐經歷的所謂“休克療法”,中國就將陷入經濟停滯。然而,1978年至2015年,中國年均GDP到9.6%,這是人類歷史上主要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
最近對此論調叫囂最甚的是海曼資本管理公司,其創始人巴斯稱,這場危機的規模“遠大於美國的次貸危機”。他認為,人民幣貶值幅度將達到40%。如果巴斯堅持這一立場,他將損失大量財富。
索羅斯最近也稱“中國硬著陸難以避免”。但索羅斯在中俄兩國的投資記錄堪稱災難,他投資俄羅斯國有電信公司損失約10億美元。
對沖基金經理們鼓吹人民幣將大幅貶值這種顯然不靠譜的信息,是因為他們想要從散佈“末日論”中牟利,而這類觀點最終總是被證偽。
2002年,章家敦寫了《中國即將崩潰》,並因此被西方媒體吹捧為“中國專家”。這本書的結論是:“5年前,中國領導人有真正的選擇,但如今沒有了,他們已經沒時間了。”十年多過去,中國依然沒崩潰。儘管如此,章家敦仍繼續作為“中國專家”在彭博電視台出鏡。
彭博社最近也發表了類似言論,聲稱中國經濟陷入了類似希臘的危機之中。2007年至2014年間,希臘經濟負增長26%,而中國經濟同期增長81%。將兩者進行類比簡直荒謬。
“中國經濟硬著陸”論調將毫無例外地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並非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並不了解這一事實所帶來的影響。在發生硬著陸的經濟體內,大公司為私人所有,政府沒有能力阻止投資衰退,而投資衰退最終導致了經濟“硬著陸”。
以美日兩國為例。2007年之後的大衰退,美國家庭消費下降了3%,但私人投資下降了23%。1990年後,日本陷入連續25年的硬著陸中,GDP年均增長率不足1%。然而,1990年至2013年間,家庭消費增長了31%,但固定投資則下降了16%。美日的經濟完全是由於投資衰退所造成的。
與美日兩國相比,2007年至2014年,中國的固定投資增長了105%,創造了81%的經濟增長,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擁有大量國有企業。中國不會陷入硬著陸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而非資本主義經濟體。(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由王曉雄翻譯)
 圖博館
圖博館
現在不但強硬派在北京政府的決策圈當道,而且是中國地緣戰略思想的主流,他們很少公開說話,一旦公開站出來說話,就代表了決策者真實的聲音。
民進黨2012年敗選,記取「最後一哩路教訓」開始勤跑大陸,與台辦、涉台智庫及財經研究單位多所接觸,可能也與特定官方人士建立某種聯繫管道。不過,我們可以推測,大陸不會容許他們與軍方、外交圈或黨的宣傳單位有任何交往,綠營人士接觸的對象應局限於統戰、財經及涉台領域。其結果是,局部的接觸與訊息得到局部的訊息理解,很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我們非常憂心,民進黨決策人士因偏聽而對大陸產生誤判,甚至對大陸所謂「鴿派」有錯誤的期待。
民進黨不能對北京有錯誤的想像,以為520後就算不承認九二共識,或不與大陸就兩岸政治基礎達成基本共識,兩岸能「馬照跑、舞照跳」;更不能誤以為美、中兩國因南海問題交惡,台灣問題就能成為美國戰略利益的核心而取代美中關係,甚至冀望華府會倒向台北來和北京對抗。事實上,一旦面臨到國家核心利益,無論北京或美國,都沒有鴿鷹之分。尤其大陸,一旦涉及主權和反台獨大前題,無論鴿派或鷹派都寸步不讓,誰當最高領導人都一樣。
只有透過對話和合作,才能讓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的溫和主張抬頭,讓分歧有效控管,讓爭端危害極小化。要達到三贏,三方都必須採取降低衝突、尋求對話、達成協議,而非反向而行,讓爭端更難化解,民進黨政府是其中重要因素。
新政府應立足於兩岸現狀,看清北京當局目前的政治氣候,創造能讓兩岸溫和派握手的條件,而不是冒險製造讓鷹派抬頭、強硬派文攻武嚇主張當道的機會。
回應
其實就是一言堂與百家齊放的較量。中國只有ㄧ派,台灣每個人都是一派,沒有說服大多數人,不管官員屬於那一派,四年後就下臺.
中國5000年來都是人治的地方~ 十足的屁國家ㄧ個!
像我們恐龍法治才好
鹰和鸽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没什么派分,就一个目标,军政一把手哪来的派系之分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國時報社論-沒有鴿沒有鷹 對台只有習核心2016.2.21
長期以來,媒體評論或專家解析大陸對台政策,經常以「鴿派」或「鷹派」分類北京對台兩種不同的策略或手段,甚至定位涉台單位或官員、學者。但所謂鴿、鷹,只是北京在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基本方針前提下,針對台灣不同群體、或不同時期所採取的不同策略。北京從來都是鴿、鷹兩手抓,有時一手用力些,另一手放鬆些,有時相反。
一般稱鴿派路線,主要以國台辦及上海、廈門台研智庫為代表。鴿派希望透過擴大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逐步深化成文化、媒體、教育等全方位的交流合作,最終實現兩岸中止敵對,再進展到完成和平統一。這個路線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馬英九總統去年12月實現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後,達到階段性的高峰。
所謂鷹派,通常指的是軍方、外交部門和立論強硬的官媒。鷹派強調嚴肅看待國家主權利益,高舉民族復興和愛國主義傳統。落實在具體對台政策上就是台灣一般稱的外交封鎖和文攻武嚇。這個路線在1995、1996年台海飛彈軍演危機、2000年兩國論和2005年大陸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期間,都曾出現。
無獨有偶,華府研究中國事務圈內也有紅與藍或鴿與鷹之分。主張透過積極交流以促成中國民主演變的鴿派,和主張強勢圍堵、逼中國從內部瓦解的鷹派,長期爭論不休,近年又形成既交流又圍堵、既圍堵又交流的折衷派。而北京和華府間鴿鷹派的浮沉,不但方向高度連動,而且有軌跡可循。當中美關係和緩,鴿派就有出頭的機會;反之,如果雙方關係起了重大爭執,鴿派就會被打擊,鷹派重新抬頭。
中國自大量青壯「海歸派」回國後,經濟發展成就和軍事力量飛躍成長,讓中國的民族自信和自尊不但空前,而且具有厚實的民意基礎,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無法違逆百年來的「中國夢」,也是以習近平在十八大所揭示的政治目標。也因為中國大陸正處於近代中國遭受百年列強侵侮之後的重新崛起,外交、軍事作為轉趨強勢,不再韜光養晦,甚至在釣島爭議和南海問題上,經常選擇性「亮劍」。
不過,中國大陸體制和美國與台灣不同,不能用美國的鷹派與鴿派來理解大陸的鴿與鷹。曾任美國防部助理副部長、長期擔任美國國防政策顧問的白邦瑞去年出版新作《百年馬拉松》中,直言美國溫和派長期以來認為大陸鷹派言論只是邊緣主張、民族主義不是主流,這是嚴重的錯誤。
 圖博館
圖博館
其實,“中國拖累世界經濟”的誤讀,照見的不僅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偏見,更是“如何認識中國”知識譜系的不足。中國已經進入經濟新常態,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是經濟的主旋律。一味盯著鋼煤產量、房地產開發投資額等舊指標,而忽略結構優化、動力多元、效益提升等新趨勢,只談風險、不談機遇,只看困難、不看成績,自然只會陷入“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的困境。
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奇蹟百思不得其解,不僅因為中國的崛起因素無比複雜,更因為中國人的勁頭和決心絕非一兩個經濟模型就能輕易解釋。看看街邊的紅薯攤都開始推出微信支付,就能感受得到“互聯網+”的強勁脈搏;在自貿區走上一圈,就能體會到簡政放權帶來的各種便利;深入了解東部沿海正在上演的“機器換人”產業革命,就能理解“中國製造”的勢不可擋。
除了理論和數據,有經濟學家還給出過第三種研究方法——歷史。就在春節期間,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的最新文章在題目中設問《本世紀仍屬於中國嗎?》並在文尾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對比當今中國的崛起和上個世紀美國的崛起,中國所遇到的都不是什麼新問題,而恰恰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面臨的極其典型的問題,而且完全可以解決”。
認識中國,認識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真實關係,首先應該看到中國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發現的一片片“藍海”。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所指出的,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進行認真係統的調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觀點”。“以中國為方法”,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跟上中國轉型的步伐,這恐怕才是認識中國和把握自身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相關新聞
【美】斯蒂芬·羅奇:世界經濟大範圍染上“日本病”2016-02-19 環球時報
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日筷箭之爭 對中貨幣戰 中國製造業 《中共研究方法論》中國經濟成長之謎 《中國即將崩潰》
 圖博館
圖博館
人民日報:中國拖累世界經濟論可休矣 2016.2.19
在世界經濟遭遇困頓的這段時間,正值全民“歸鄉團圓”、歡度傳統佳節的中國,所顯示的強勁經濟活力,給世界增添了不少正能量.
猴年新春,就在中國人忙著“搶紅包”之際,全球股市卻遭遇了“黑色一周”,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下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委員會等紛紛下調經濟增速預期。同時,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速低於預期,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負增長”。
每當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總會有人把禍水往中國引,釋放“下一個全球衰退將由中國引起”的奇談怪論。前段時間,中國股市春節“休市”,人民幣匯率也未有異常波動,世界經濟卻依然在經歷震盪和下滑,可見中國經濟這艘大船,根本沒有“拖累世界”。相反,在世界經濟遭遇困頓的這段時間,正值全民“歸鄉團圓”、歡度傳統佳節的中國,所顯示的強勁經濟活力,倒是給世界增添了不少正能量。
春節期間,走進餐館,預定爆滿、一座難求的現象四處可見;放眼影院,更是人流湧動、摩肩接踵。據統計,僅正月初一至初六這6天,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就實現銷售額約7540億元,比去年增長了11.2%;春節電影票房更是同比勁增近七成,順利突破30億元,被稱為“史上最強春節檔”。而在一個電商平台,5天的“年貨節”竟賣出了21億件年貨,相當於全國人民每人買了1.5件。在全球經濟踉踉蹌蹌前行的路上,這樣一份紅火的數據,映襯的是中國經濟亮點頻出、活力充沛、韌性十足。
從消費數據來看,中國非但不是最近世界經濟的風險之源,反而是熱力之源。“一個繁榮的中國使世界受益”生動地體現在不少國家的“春節大作戰”之中。這個春節,近600萬中國出境游客,能“刷出”大約900億元人民幣的境外消費額度。中國人光顧的免稅店和大商場,堪比國內春運火車站,“取貨處排隊排到沒脾氣”;在德國,馬克思、恩格斯的出生地打出“紅色旅遊線路”,招徠中國遊客……“和中國人一起過年”,共同分享“春節紅利”,消費市場的情真意切,已超越了很多“黑板經濟學”的估量。
 圖博館
圖博館
中時短評-美國的夥伴: 歐巴馬日前讚揚普丁為解決敘利亞危機所付出的努力,還形容俄是「具有建設性的夥伴」。就在歐巴馬說這番話之前一個多月,美國才批評俄羅斯在敘利亞的空襲行動是「短視、犯了戰略錯誤」。歐之所以出現重大轉折,是因為俄最近開始轟炸IS目標。美對俄態度如此,誰曉得哪一天,中國又會成為美國口裡「具有建設性的夥伴」?
美油2016-1-13 盤中跌破30美元/桶 多家投行預測進一步跌至20
油價重挫 中國2016年戰略儲油採購量倍增至7-9,000萬桶
中國儲油空間近乎滿載!大型油輪運費暴跌至13個月來新低
中國戰略石油三期儲備三期能力為2.32億桶 相當於37天進口量: 中國目前的石油儲備相當於大約30天的進口量,政府尋求到2020年提高至100天。一期4個儲備基地儲備原油9,100萬桶,二期7個1.68億桶。
沙特上調國內油價,土豪過年也難? 2016-01-02王晉 以色列海法大學博士生
這次發改委沒降油價,我帶頭鼓掌2015-12-17 張捷 政法大學金融研究院主任
英媒:汽油廉價推動SUV銷售美氣候目標面臨風險
低油價打趴美國頁岩氣 中油進場撿便宜 抱330億要獵美頁岩氣2016.1.7
中石化在重慶涪陵建成首個國家級年產50億立方米頁岩氣示範區 2015.12.25
中石化擬提高重慶頁岩氣項目年產能一倍12.28
頁岩氣銷售受阻「兩桶油」壓縮目標產量12.8
發改委下調成品油價並宣布低於40美元國內不降價
另詳參【圖博館】:習李三中全會 中國大戰略 《絲路文化海上卷》 《中共研究方法論》 民主形式萬歲 假民主自由之名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民主的類型》 中共為何反維權 中國的國際責任 中國與非洲 中國與中亞 中日釣島之爭 中艦南海逼退美艦 中國與韓朝 中國與東協 袈裟革命? 中國與印度 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 《中國模式》 中國石油大戰略 《石油世紀》 中日高鐵之爭 拉美向左轉 俄烏戰爭 中國熊報? 俄羅斯經濟 《俄羅斯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 金磚褪色為土磚 天下民主一般黑 民主偽形(二) 《歐洲新霸權》 歐豬四國 《德國與日本的省思》 恐怖攻擊本土化 美伊與中東 美以伊朗 波灣世紀來臨? 伊斯蘭革命
 圖博館
圖博館
法国不能一个人战斗 俄媒:建立国际反恐联盟时刻到
外媒:法俄反IS同盟不太可能 西方不会解除制裁
對俄制裁延長半年為烏克蘭選舉護航2015-11-22
多国舰机密集搜索俄潜艇 俄回应:这是反俄大合唱
美法俄圍殲IS 說比做容易?
IS仍有生命力 因:1、單靠空襲難以解決。美主導的國際聯盟,各有各的打算,行動虛多實少,空襲次數不少,命中率不高;2、不派地面部隊,僅靠訓練伊拉克政府軍、庫爾德武裝和敘利亞溫和反對派武裝很不理想。。3、排斥異己,不與伊朗和敘利亞合作。4、IS仍有生命力。目前,伊、敘亂局正是該極端組織生存的土壤和空間。它可利用教派矛盾、權力之爭、群雄割據,擴充兵員,增強實力,甚至招募世界多國極端份子,前來參加聖戰,據報導來自世界104個國家的大約3萬人參加了IS。
利比亞警營2010.1.7遇襲致70餘死 石油命脈遭IS攻擊
非洲警察法國與非洲糾纏半世紀 恐怖組織眼中釘:巴黎恐怖攻擊才剛屆滿一周,法國昔日在非洲的殖民地馬利就發生首都五星級「麗笙酒店」170人遭挾至少27死,不是意外,更非巧合.
中國駐馬里大使館:襲擊事件中3名中國公民遇難 2015-11-20
新疆打掉一境外組織指揮暴恐團伙殲滅28人 2015-11-20
法國《新觀察家》駐華記者高潔(Ursula Gauthier,郭玉)未獲續籤2016.1.1離境 郭曾撰文攻擊中國反恐政策,被斥“政治偏見和雙重標準”
殺害中國人質是IS對華的陰險策略:中國千萬別上當(回應:煽動中國出兵的都是美國的陰謀)
美专家:没看出中国有向海外派兵打算 他们不好这口
中國赴馬里維和部隊為何不能救人質:無法理權限
法国在马里给自己挖好大一个坑:法国收获的苦果大部分是自己种下的(回應:还是中国够机智)
巴黎恐袭应该让西方看清自己的衰落 by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奥巴马公开拉拢台 台湾网民:怕引火烧身
台灣被IS點名 國防部:妥慎因應 練新戰技
 圖博館
圖博館
巴黎11.13爆炸案 專題
http://news.sina.com.cn/w/z/Parisqjjbzsj2015/
IS週四揚言讓俄國、歐洲血流成河
苗柔柔:民主还是安定,也许是法国人民选择的时候了
巴黎恐袭事件后第二次全球反恐或将到来(回應:越反越恐)
巴黎恐袭比利时成后方基地 外媒:比利时怎么就成了“贼窝”?
巴黎爆炸後謠言四起 中國媒體躺槍(回應:公知真是不擇手段!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比賣國為榮)
恐怖主义是现代人类社会之癌
“阿拉伯之春”,歷史不賣後悔藥
突尼斯总统卫队2015-11-24遇IS袭 阿拉伯之春昙花一现恶果凸现
「阿拉伯之春」再起 突尼西亞宵禁
巴黎恐袭,西方的失败还是恐怖主义的成功
阿拉伯之春第五年 突尼斯多地爆發衝突 抗議青年失業率高
中國強勢崛起 以美為首的民主制度仍是最好選擇嗎?by湯錦台(台灣史學家)
沙特邊境被也門攻破 戰力太渣 已經失去一個省 (沙特國王該考慮一下自己盲目出兵的後果了,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美式裝備堆積的沙特陸軍。)
沙特在也門最高指揮官陣亡2015-12-14 疑遭胡塞武裝導彈(中國M-7)襲擊
占豪:沙特要玩一票大的了?事實上,沙特組建35國聯盟,其根本目的和白宮借打擊IS推翻敘利亞政府一樣,是要藉打擊IS之名進一步擠壓什葉派勢力。之前,沙特為首的12國聯軍打了大半年實際效果如何?連王室最帥的那個王子戰死了,就在前兩天最高指揮官又被胡塞武裝的導彈給炸死了。就現在的狀況看,35國聯軍也就那麼回事,大部分是濫竽充數。
沙特2016.1.3與伊朗斷交 :沙特2日以恐怖主義罪名處決了包括知名什葉派教士尼米爾在內的47人。2日晚,伊朗示威者衝擊沙特駐伊朗大使館。伊朗總統魯哈尼3日譴責焚燒沙特大使館的行為,表示伊朗當局將保障外國使領館安全,伊警方逮捕了40抗議者。尼是2011年沙特東部爆發的反政府示威抗議活動的支持者,當地的什葉派穆斯林長期以來一直抗議被邊緣化對待。沙特政府處死尼的最主要罪名是里通外國。尼被處決後,引起中東乃至全球什葉派穆斯林的抗議浪潮,也點燃了遜尼派主導的沙特和什葉派主導的伊朗這對中東宿敵的口水戰。沙特執行死刑人數之多經常受到國際人權組織批評。鑑於沙特是重要的產油大國,沙特的重要盟友美國一直迴避對其實施制裁,不過即使如此,美國也對沙特頗有微詞。(回應:美國佬怎麼不在沙特推銷它們的價值觀? 沙特後面的美國人才是真正的劍子手。 )
沙伊斷交凸顯美中東控制力減弱
中東風雨逐漸吹到沙特身上
 圖博館
圖博館
俄戰機被擊落對中國有何警示: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中,也存在自己的戰機或艦船被潛在對手擊落或擊傷的威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遇到對方挑釁的情況,我們必須提前做好就地反擊的準備,但是更需要判斷出對方的挑釁是不是一個圈套。如果對方的挑釁是為了惡化中國周邊的投資環境,有意逼你動手,一旦上套,就等於幫助對手惡化我們的周邊環境,有助於對方謀劃全球資本從中國周邊撤出意圖的達成。土擊落俄戰機一事,導致了歐洲股市大跌,以及土耳其里拉的貶值和俄羅斯股市的下挫,也就是說使大量的資金撤出了當地資本市場。這一結果最有利於美國,因為與此同時,美聯儲加息預期正吸引著國際資本流向美國。
中國反恐分三步 出兵中東是下策 美將抽身巡航南海 : 第一步,國內強勢反恐,對國際反恐道義或者物質支持。第二步,實在熬不住,向西“一帶一路”的中亞反恐。 第三步,增強實力後,全球反恐。 如果直接一步到位,痛快固然也痛快,“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國內估計也會有一些喝彩聲。但這其實正中西方國家下懷。別忘了,中東是一個無底洞,已經吞噬得美國苦不堪言(所以奧巴馬反復強調不會派地面部隊),俄羅斯可能也不知會如何收場(俄客機爆炸、與土耳其摩擦,都是警訊)。
美俄在敘拉鋸對中國最有利:當今世界三足鼎立。一足過強,必然影響世界的平衡。如果中國從經濟上上積極支援俄羅斯,使俄羅斯有能力在敘利亞與美國長期拉鋸,必將極大削弱俄羅斯和美國的力量。這顯然對中國有利。俄羅斯依賴中國的支持,必然要給予中國相應的好處。美國要中國削減對俄羅斯的援助,也要拿出交換條件。這樣的交換條件,顯然應該在第一島鏈一線向中國做出必要的讓步。中國在經濟上支援俄羅斯的一個聲明,即可能對美國在敘利亞的政策產生巨大的影響,讓美國重新考慮中美利益博弈關係。這樣的好事,何樂不為?
美稱中國海軍繞道西太赴南海大練兵欲敲打美國(回應:大國博奕就是這樣針鋒相對,好得很!這些大動作可以理解為中國在下一盤大棋,目的是在南海拖住美國,同時俄國在中東開闢新戰場,遙相呼應,讓它深陷泥沼不能自拔。)
 圖博館
圖博館
土耳其对驻叙俄军有压倒优势 俄机一起飞就被发现 俄对北约摊牌力不从心:当然,如果有需要,俄完全能用不对称战术抵消土耳其的空军优势。(回應:没钱就没志气了,俄现在就剩下个空壳,真打起来外强中干更难看。 金钱不能决定一切,但启着重要作用,现在我国还是发展经济还是重之重,美国现在挑衅,还得忍,经济再强大些,美国也得忍。)
惹了俄羅斯又闖伊拉克 土耳其高調背後有三大目標 : 一是蒐集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的戰場情報。第二是培訓親土耳其的地區力量。第三是加強土耳其-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邊界管控,防止可能出現的難民潮。
奧巴馬終於出手普京在中東遇5大麻煩:一、俄在中東的戰線在被迫拉長,戰爭時間也在被拉長,俄有陷入戰爭泥潭的危險。二、俄在東歐面臨美方的反擊。三、美國與沙特繼續聯手打壓石油將會給俄經濟繼續帶來巨大壓力。四、美空襲敘利亞政府軍,將會使中東局勢陷入更加膠著的狀態。五、俄土關係惡化,俄羅斯在敘利亞港口的補給正遇到麻煩。
為何總是贏在北京 : 當大災難發生時,一個國家的態度最能反應這個國家的國格和國品,不得不佩服我們的北京,無論哪裡起風雲,它總是能恰到好處地成為贏家。從2001紐約9.11,美國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2015巴黎11.13恐怖之夜.
当IS/反政府武装攻击西方/俄国時,中国仍在崛起 (回應:IS/反政府武装报仇来了! 肢解土鸡。 键盘侠头脑一定要清醒,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我们国内千万不能瞎折腾,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强大国防。 其實,普京的戰略基本失敗了,普京的戰略目的是控製石油價格,即使保住巴沙爾政權,只要沙特等產油國維持低價,普京即使滅了IS,也是然並卵。美帝看準這一點,挖了大坑。 鄧小平打越南,計劃就打十幾天就收兵,這是深通兵法的大師的做法。兵貴勝不貴久,長期用兵,亡國之道。我們希望俄再撐十年,如果明年,後年倒了,土共的壓力山大。)
土軍進伊拉克要斷俄後路中國出手援俄可獲3大收益:一是俄改變中東格局就是改變世界格局,這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重組有好處,而重組加快正是中國所需要的。 二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將美國、歐盟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中東,這對中國經略周邊、非洲、拉美都有好處。 三是俄對中國越依賴,歐盟越感覺到自己的風險,不但越有利於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還有利於加快中國與俄、歐合作的步伐。
中国为何对俄土争端沉默不语 俄媒称因为有智慧
西方深陷中东 中国是唯一没犯错的大国
 圖博館
圖博館
俄軍介入敘利亞局勢 專題
http://mil.news.sina.com.cn/nz/eluosijrxly/
相關新聞
IS聲稱擊落俄羅斯A321客機 飛機墜毀於交戰區
俄航委會10.31失事客機空中解體
BBC:俄客機墜毀前曾試圖迫降 升空23分後突然減速
埃及總統稱可能要數月時間查明空難原因
俄媒公布俄客机残骸可疑弹孔照 或为炸弹爆炸 俄或进行重大报复
黑盒子錄到爆炸聲 失事俄機顯示被裝炸彈
俄客机坠毁水落石出 普京会尽量拖延公布
俄客机坠毁埃及超一周找到黑匣子为何还没有答案
俄客机坠毁系恐怖袭击 普京:恐怖分子无论在哪儿都将把他找到
埃及逮捕17名俄航空難嫌疑人 2人疑協助炸毀客機
IS:用汽水炸彈炸俄客機
俄客机坠毁背后的大国较量:美给俄设了个大圈套
美副国务卿:俄军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陷入泥潭(回應:美就没陷入?)
俄媒稱敘軍在俄空襲配合下擴大戰果解放8個村鎮
德媒称叙军无能拖累俄军 损失24辆坦克突进半米
叙政府军大反攻已经快2周:为何前进还不到1公里
美國2015.12.16接受俄立場稱不求敘政權更迭阿薩德熬出頭
俄軍轟炸IS往往一刀切缺準頭 敘總統正輸掉戰爭
俄轟炸IS每日花費250萬-1億美元
俄经济濒临崩溃 普京倒回苏联模式
俄石油收到中国972.6亿预付款 美媒:雪中送炭
獨聯體國家貨幣兩年來大幅貶值:盧布兌美元貶值超50% 受油價大跌、俄羅斯經濟衰退,以及美聯儲加息等因素影響。
敘利亞和談前夕 IS襲擊敘首都大馬士革 歐盟:欲破壞朝野和談
聯合國特使:敘利亞和談正式展開2016.2.1
敘利亞內戰和談登場 情勢悲觀 俄稱繼續空襲直到擊敗恐怖組織
美国防部确认土耳其F-16击落俄SU-24战机前曾10次警告 2015.11.24
土总统:击落侵犯土领空的俄军机符合规则
土总统:俄根本没反恐,炸的都是我们亲人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土库曼人
俄寻找苏-24的米-8直升机被叙反政府武装用陶氏反坦克导弹击落
土总统拒绝向普京道歉赔偿 俄才该道歉俄 驳斥与IS石油交易: 俄媒曝光土总统之子与IS头目合影,参与IS的石油走私(回應:照片上的两名蓄须男子是土当地的餐厅老板,被误认为恐怖分子。)
俄:空袭了叙土边境的运油车队 土:是救援车队!
俄全面制裁土 略谈苏俄对外“报复”史
俄对土经济制裁会有何效果:俄GDP萎缩比韩国还低
普京執政16年不能成中國也該成阿聯酋 結果卻很悲劇
 圖博館
圖博館
朝鮮牡丹峰樂團演出因工作層面間溝通銜接原因 2015-12-12取消 (回應:這是因為本來就不是一場單純的文藝演出,而是有重要政治目的的政治活動,政治目的沒達到,演出自然也就進行不下去了。 來演出是為金三胖訪華做鋪墊的吧,也可說是文藝外交了,但出了一出朝鮮有了氫彈的消息,TG也不會含糊吧,取消演出就不奇怪了。 看來分歧不小 半島無核化對中國也是意義重大,這事中國不會含糊 鬧妖娥子。鬧吧,折騰一次,好感下降一點。)
中国驻朝使馆:“朝鲜当局逮捕百余华侨”报道子虚乌有
外媒:朝鮮脫北者自殺率高受不了在韓當下層人
30年,沒人能攔住朝鮮核試驗
美國稱中國對朝政策已不管用 中方:關鍵不在中國
朝鮮2016.1.6進行氫彈試驗 專題
http://news.sina.com.cn/w/zx/2016-01-06/doc-ifxneefu2310218.shtml
朝鮮春節發射「衛星」或為遠程導彈
為何印、巴、以可以擁核而朝鮮不可以? 一直以來胖粉們都忿忿不平,為何你們中、美、英、法、俄、印、巴、以可以擁核,而我們社會主義強盛大國朝鮮卻不可以擁核?首先說說中、美、英、法、俄。我們知道這五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合法擁核的國家,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五個國家就是國際秩序的領導者、就是國際社會的當家大哥。做為領導者當然就要有領導者的特權,而擁核就是特權之一。 再說說印度。一是因為印度的體量太大,這一切使國際的製裁都難以奏效。 巴以原因有三。一、這兩個國家的核武不能威脅到當家大哥的安全。二、這兩個國家服從當家大哥的戰略利益。三、這兩個國家保持低調不給當家大哥找麻煩。 綜上所述,這個世界上除了五大流氓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合法擁核,想體制外擁核原本就是萬里挑一的事,多少國家想體制外擁核都失敗了,日本、韓國、南非、巴西.....,特殊機緣造就你體制外擁核了,就要學會順勢而為、學會乖巧、學會八面玲瓏,狂妄無知、招搖過市只能招致全世界的聲討,到頭來手裡的核彈非但成不了自己的護身符反倒成了自己的上吊繩。(回應:以、印、巴可以有核武器,朝鮮為什麼不行?美國人能說出理由嗎? 美國是世界霸主,他想給誰權利就是合法,還說朝鮮是流氓國家,但是美國尿泡尿照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朝鮮可以,這都是美國逼的。伊朗十年後再看吧,波斯人早晚會有原子彈的。 都是美國逼得,所以,中國就冷處理,中越/中朝關係一樣,正常對待,不再援助,一切都歸於貿易,走互利關係道路。)
 圖博館
圖博館
占豪:中國高鐵在印度輸給日本是壞消息嗎?一、中國戰略投資重點現階段應放在汎亞鐵路、中巴經濟走廊。二、讓日本適度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有利無害,因為這種投資終歸是推動亞洲國家互聯互通的。三、中印合作穩中求進推動更為合適。印度也不可能將自己的所有高鐵訂單給日本,這不僅僅是因為日本的高鐵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印度也想拿到中國投資。另外,以印度效率看,日印度的合作恐怕並不高,未來印度還會有高鐵線路給中國做,到底誰先修通運行這事還真難說,我們拭目以待。
印度二手航母开进斯里兰卡港口
印度反對斯里蘭卡被迫棄買梟龍?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抵達斯里蘭卡訪問
斯里兰卡宁弃印度4亿美元援助也要买枭龙 拒购印度瘸腿战机
港媒:中國如何在尼泊爾打敗印度?西方很關注
印媒:尼泊爾總理或首訪中國向印度施壓
中國與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成為「一帶一路」推進焦點地區和優先區域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抵達巴基斯坦訪問
印度擬在越南設衛星站合作監視中國與南海 料將激怒中國
越共總書記之爭 親中派1.26打垮總理
越南政壇巨變 親美派阮晉勇出局 對抗中國戰略不會改
老撾1.25被指對美承諾打擊中國南海立場 媒體稱美國自吹
克里拉柬埔寨攪局南海遭當面拒絕 柬方表態打美國臉
印度海軍的作戰實力會超過中國海軍嗎?
印度神盾艦全面落後於中華神盾艦
印度海軍膽真肥!科欽船廠造不好油輪竟敢讓它造航母
新印度快報 感慨印度浪費十年:中國武器進口減半印翻番
中國市場見頂蘋果轉攻印度 暫難取代中國
鴻海生產重心正移轉?捨棄中國,傳印度建全球最大代工廠
印度製造能取代中國製造?太天真了
莫迪顧問:印度最佳選擇是模仿中國
英媒:「印度龜」將超越「中國兔」
英媒評論"印度龜將勝中國兔"觀點
獨家揭秘所謂資本主義如何毀了印度?
中國成就多個世界第一:莫迪慌忙對印度下新命令
印度擬五管齊下 抗衡中國經濟影響力
五理由力證:已錯過起飛機遇印度只能做阿三
印媒:中國曾強大數個世紀世界應習慣其崛起
 圖博館
圖博館
中国要担心缅甸投向美国怀抱吗?
纽约时报2016.1.24称昂山素季向中国靠拢 中缅将有更多合作
中企2015.12.30中標“一帶一路”緬甸皎漂經濟特區深水港工業園(回應: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港、緬甸港,孟加拉港...阿三又要睡不著了。注意防範各種不利因素,吸取密松。水電站經驗教訓,不要再重蹈覆轍。中國是緬甸搬不走的鄰居,素雞都已承認了,即便民主派上台執政,發展還是離不開中國。)
投资缅甸经济特区风险莫测
中國企業主導緬甸西部經濟特區開發
中国能建承建缅首个世行贷款 11.9万千瓦EPC电厂项目
中国产新客运列车在缅甸投入运营
美媒称中国对缅甸北方领土影响巨大
美國《外交政策》2016-01-12緬甸為何必須重啟與華關係?首先,緬甸應率先制定振興經濟所需的基礎設施發展計劃,邀請和鼓勵中國發揮重要作用。其次,緬甸領導人必須認識到,搞發展不能以損害和平為代價。此外,緬甸的和平進程應該是全球合作而非無謂的競爭,可以通過中國也參加的聯合國相關機制進行。
緬甸執政黨 只能靠憲法續命
從偶像變為領導人的昂山,能治理好國家嗎
缅甸能走出一条新路吗?
緬甸民選國會開議翁山蘇姬時代來臨
緬甸軍方學泰國翁山蘇姬頭痛
維持緬甸安定翁山蘇姬不尋求立即修憲 爭取修憲拚明年當總統
斯里蘭卡清除所有障礙 中國承建科倫坡港有望復工
斯里蘭卡欲與中國修好 尋求投資扭轉經濟下滑
斯里蘭卡財長:懇請中國拋去不快幫助我們
美媒稱斯里蘭卡因欠中國巨額外債試圖修復對華關係 (回應:別看外國那些反對黨們沒上位時個個反中,一但上位了他媽比前任更親中。放眼全球,還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政府更有錢?前段時間的斯里蘭卡不就是這樣嗎?一上台馬上停掉中企承建的科倫坡港口建設,還沒有一年吧,當初的藉口環評也過關了,還賠中企一年的損失。看看西方領導默克爾,薩爾科奇,奧巴馬上台前哪個不反中?後來不是一樣愉快的玩耍。)
德媒:中國沒有對斯里蘭卡耿耿於懷 美印很嫉妒(回應:自個是漲臉了,老百姓呢? 這不是長不長臉的事,中國已經長大,但不用美國那一套,美國那一套高軍事聯盟已經過時了,互利的經濟聯繫才是最核心的,高層比你想得遠。)
 圖博館
圖博館
暴政仍然持續埃及醞釀再革命?
埃及投票率惨淡——选民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
埃及黑市匯率1美元兌8.6埃及鎊
阿拉伯之春五年埃及經濟為何無起色?
阿拉伯之春5週年埃及嚴防抗議活動2016.1.24
埃及革命5周年:推翻獨裁政權,卻換來鐵腕政府?
希臘2016.1.21批准中國中遠集團4億美元購買比雷埃夫斯港67%股權
希臘危機和中國的一帶一路
中國要趁希臘危機入市?
中國會從金融崩潰中解救希臘嗎
趁債務危機中國銀彈佔領希臘?
希臘債務難民悲劇和歐盟危機的迷思
希臘島嶼外海移民船翻覆增至24死
歐盟指責希臘「嚴重忽略」控制邊界義務
堵截難民不力或被踢出申根希臘罵歐盟「騙子」
左翼齐普拉斯微弱领先 将与希腊极右翼组联合政府 希臘人:誰上台都一樣
委內瑞拉將親美?中國已經做了準備 : 2014年,中委雙邊貿易額169.8億,中方進口113.2億,出口56.6億,主要進口原油、成品油、鐵礦砂及其精礦等。2007年以來,中已向委發放逾500億貸款,其中超過一半已經償還,仍有約200億未還。不過,中對委債務違約的風險並非毫無準備。路透社援引委《官方公報》7月報導稱,委中修訂了兩國的石油換貸款融資協議,對之前沒有設定償付時間框架的貸款設定了三年償還期。
拉美左翼倒下第二塊骨牌?委反對派控制議會
環球時報社評:委內瑞拉很難回到傳統資本主義 在委政局出現變化後,中國對委擁有債權是否安全,多名學者表示這種委對華惡意賴賬的可能性很小。
油价暴跌危机深重委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开始清算?委反对派调查中国贷款
油價暴跌加劇委債務違約擔憂
巴克萊:委拉或將重組中國石油債務,不然就無法對其他國際債權方要求
2015阿根廷向中國出口大豆943.84萬噸同比增長57.19%創歷史最高紀錄
阿根廷天氣擔憂CBOT黃豆玉米上漲
大豆期货下跌因中国经济忧虑和阿根廷天气改善
解除4年外匯管制阿根廷披索狂貶30%
阿根廷新政府宣布取消外匯管制披索狂貶30% 將把部分人民幣換成美元用於與華貿易和對外融資。(回應:取消外匯管制等於束手就擒,任人魚肉. 看這心操的。 確實,取消外匯管制,能進去的也不是只有美國,中國也可以啊.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新總統比前總統好多了。尤其是取消限制工業產品進口簡直就是……幾十年來,我國和世界各國打交道,就怕對方是個左派逗逼,下手、捅刀子都不太方便。)
 圖博館
圖博館
習1.19-23出訪中東三國 專題
http://news.sina.com.cn/c/z/xjpcfzdsg/
習近平訪中東 撒550億美元
中國伊朗簽署核能 17項合作,10年內使雙邊貿易規模達到6000億美元
國際社會投資伊朗的熱情強烈“多數美國公司只能靠邊站了”
伊朗總統訪法砸8千多億購118架空巴
伊朗增產石油法、希、義買單
核子協議後...伊朗無人機飛越美國航母
伊朗市場難經營
美打破中東平衡致沙特伊朗對峙 中國為何要當調解人
中東多國受西方欺騙內部混亂崩潰 齊倒向中國
土媒:中國不干涉內政 易被阿拉伯國家接受
中時社評-習近平訪中東 中國走自己的路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球覆蓋:習總上任三年來,外交佈局有氣勢,一招一式都是奔著全球謀劃的。先是跟俄美等大國接上頭,接著訪問非洲重點國家,然後密集的中亞東南亞南亞周邊行,從14年初開始,歐洲也接連走起,拉美也氣勢恢宏地開了新局,中間還密集穿插著多邊舞台上的縱橫捭闔和直來直去只訪一國的點穴式外交。轉著地球儀看來看去,哎,就差踏上中東的土地了!
習文《讓中阿友誼如尼羅河水奔湧向前》:中阿關係呈現蓬勃生機,迄今為止,已有埃及、阿爾及利亞、沙特、阿聯酋、卡塔爾、蘇丹、約旦、伊拉克等8個國家同中國建立或提升了雙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4年,中阿貿易額突破2511億美元,中國從阿進口原油1.46億噸,成為阿第二大貿易夥伴。7個阿國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60年來,中國累計向阿提供了254億元人民幣經濟援助,培訓了2萬多名各類人員,向8個國家派遣援外醫療隊。11個阿國成為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目的地國,中阿每週往來航班達183架次,每年往來人員達102萬人次。
埃媒2016-1-4中企將幫埃及建設能居住500萬人的新行政首都,該項目將在今後5年至7年執行,預計耗資450億美元。之所以計劃建新行政首都,是因為開羅人口將在40年裡翻一番。據稱,開羅現人口有1800萬,2050年將增至4000萬。(回應: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希望國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當心像利比亞那樣,政權更替了,我們投入的一切都煙消雲散。中國的眼光是把世界當成試煉場,做一切可做的生意,交一切可交的朋友,國外國內一樣重要,唯有這樣才符合中國夢強軍夢.)
習訪埃簽巨額經貿協議
振興觀光埃及積極拉攏陸客
埃及紅海酒店遭IS襲擊3名外國遊客受傷
埃及吉薩金字塔區穆斯林兄弟會恐攻 警方中計遭炸至少6死
 阿楨
阿楨
民主的烏坎之路
旣然炒作中國的維和救災軍售軍費不能阻止中國崛起,炒作美國自己的頁岩氣和製造業是種泡沫,中國的製造業又如此堅強,那就發揮美國的柔軟戰力6,對中國展開貨幣戰爭!
可惜中共土匪、匪性堅強、軟硬都不吃,不只對人民幣,對所有金融炒作如影子銀行、第三方支付和比特幣等都強控!
敬酒不吃,就聯合全球對中國展開貿易戰爭、那知老共更會玩,於是改玩網絡/信息/宣傳/心理戰。
美人全球監(奸)控別人,憑啥玩網絡/信息/宣傳/心理戰。
民主是普世價值,老美又是老牌的民主國家,美人總可用民主玩華人了吧!
天下民主一般黑、多會變民粹,不只發生在亞非拉美歐,連被反中者捧為民主樣板的「烏坎」民主之路、也變調成烏漆麻黑的坎坷之路!
這沒啥,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研究、不用政治巫師預言,便能預測到烏坎民主會變成「宗族角力場」,這早在本館前評已指出大陸學者《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下篇便提出<宗族及惡勢力對鄉村關系的制約>,相反、海外學者三冊一套的《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則捧民貶官!
烏坎「民主」變調 選舉變宗族角力場2014-3-13聯合
廣東陸豐縣烏坎村二○一二年一人一票選村官,被稱為是開啟大陸農村民主新紀元,但兩年過去,取回被貪官私賣的土地毫無進展。村委會換屆選舉前天再度啟動,有村民表示,烏坎村委黨委重組後,成員中出現二○一二年選舉前的村委成員,村民並無太大反彈,這反映村民對新村委的失望與無助。他表示,加入老村委是理智的選擇,因為新村委年少不作為,老村委個別是有權威,且做事穩重。也有村民表示,與兩年前相較,本次選舉已變成宗族勢力的角力場,村民對下一屆的村委會已無信心。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9924458
 阿楨
阿楨
中艦南海逼退美艦
中國軍艦敢在南海逼退美艦?
有何不敢?來而不往非禮也,那天中艦中機也該到美岸逛逛!
快了,2013年中國新艦數量世界第一
相關新聞
南海對峙內幕:美國導彈巡洋艦「考朋斯號」(Cowpens)2013年12月初強闖航母內防區美媒稱考本斯號巡洋艦若碰撞中國坦克登陸艦吃虧大中國軍艦 南海逼退美艦 陸網民:顯示習李時代的強硬
南海對峙事件後 陸前進環太軍演
美國防官員:中國軍艦極具侵略性(楨:的相反!) 陸官媒:竟先告狀
美高官評中美軍艦對峙:中方經驗不足英語不好(回應: 哈哈,笑死了,美國佬,出了問題,怪別人不會講你們的話,丟人!)
美國《海軍新聞》網站2014-6-10美軍考彭斯號艦長Gregory Gombert被解職
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
2009年3月的無瑕號事件
2009年6月麥凱恩號驅逐艦撞船事件
2013年12月中艦南海逼退美艦事件
中與越菲日島礁之爭
相關新聞
菲律賓抓扣11名中國漁民
菲軍強登仁愛礁
中國擴建南沙赤瓜礁
中國南海981深海鑽油平台
越南暴動2014-5-13砸搶 500台商 盛傳默許暴民發洩3天
中越南海紛爭影響越南經濟2014-5-8股市暴跌超過6%
東協峰會緬甸登場 聚焦區域穩定2014.5.11閉幕絕口不提陸
東盟首腦峰會成果未提及南海 菲南海企圖再落空
日本放棄武器出口三原則 引起中韓密切警惕
安倍2014-7-1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 孤注一擲為參戰鬆綁
安倍拉攏菲越聯手對付華或激怒中國 但美歡迎(楨:集體自慰權?玩3P?)
習近平 普丁揭幕 中俄5.20-25東海軍演
習近平會見普京:決不允許軍國主義侵略悲劇重演
日戰機曾監視中方軍機近半小時 最近距離僅10米
美環太平洋軍演 中2014.6.9首度參加
美日vs.中俄 雙方「鬥而不破」
亞信峰會 中俄通氣制衡美 中俄要將美踢出亞太
中女將軍香格里拉會議(2014第13屆亞洲安全會議)連發四問 美防長避重就輕
梅克爾訪陸 適逢七七事變77週年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774885
 阿楨
阿楨
文革電影:名導演79
《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禁映
《楓》1980年 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鄭義、導演:張一、演員:徐楓(飾盧丹楓)、王爾利(飾李紅鋼)。
《戴手銬的旅客》1980年 導演:于洋 編劇:紀明 馬林 演員:于洋、邵萬林,趙子岳,馬樹超,葛存壯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電影公司(台灣)出品,演員有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
《小街》1981年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徐銀華 導演:楊延晉 攝影:應福康、鄭宏 美術:劉藩 作曲:徐景新 演員:郭凱敏(飾夏)、張瑜(飾俞)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李碧華、蘆葦編劇,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兇猛》),夏雨、寧靜主演)
《天浴》(1998年,陳冲導演,陳冲、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年,法國籍的華人戴思傑執導之電影,由周迅、劉燁和陳坤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張藝謀導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編劇,周冬雨、竇驍主演)
張藝謀《回歸》(2014)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449701
 阿楨
阿楨
中FK-1000仿自俄96K6-S1?
《簡氏防務週刊》憑啥說「中國的FK-1000新防空系統仿自俄軍96K6-S1炮彈合一防空系統」?
憑啥啊?憑它倆都有8×8輪式越野車、12枚地對空導彈、單管機關炮。而且仿的更差,機關炮由30毫米變23毫米!
果然如前評<中國防空武器虎頭蛇尾?>1對詹氏磚家之評:不只兩岸多軍事磚家2,全球的學者專家教授、若不依理性專業事實評論、多會變邪者磚家叫獸,尤其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中共的話3、解放軍武器甚至中國產品全成了山寨貨!
所言極是!二者射程均達廿公里、能對抗AH-64E直升機4,但FK-1000是整合式箱型、96K6-S1是分離式圓桶!至於機關炮的口徑與防空/反彈能力之關係不大(美國密集陣才20毫米),重要的是防空導彈能在敵導彈射程外將載具打下,等敵彈逼近、單管機關炮已沒多大作用、除非將多管機關炮升級到能反彈的C-RAM系統5!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259572
 阿楨
阿楨
中國防空武器虎頭蛇尾?
<中國防空武器虎頭蛇尾>是全球軍武權威期刊《詹氏:空射武器》的編輯休森之專家大作嗎?由下圖或下文1可知是「中國各軍工企業不斷推陳出新完善之作」!休森怎會說:「中國的國防工業部門通常不會善始善終地完成開發和生產工作,如果沒有國外購買者立刻訂購的話,那麼一種設計方案就會很快被另外的方案取代,從此煙消雲散,而這種替代方案可能同樣也是短命的。」
這個嘛!不只兩岸多軍事磚家2,全球的學者專家教授、若不依理性專業事實評論、多會變邪者磚家叫獸,尤其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中共的話3!
所言極是!中西軍工軍武的研發採購制度本異,很難說誰優誰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軍就憑其中國特色的制度養活了眾多軍工企業和效費比/性價比高4之軍武,不只能滿足各軍種軍區的軍武所需,還能針對各國推銷不同產品、比如中國的肩式對空導彈就已經出口到印尼(QW-3)緬甸(HY-6)泰國 (QW-18) !
相關資料
1. 以上詳參【圖博館】:中國防空導彈 中國四款近程機動防空導彈系統 天劍2上艦?
2.以上詳參【圖博館】:兩岸軍事磚家
3. 以上詳參【圖博館】:《中共研究方法論》
4. 以上詳參【圖博館】:CP值與小確幸 中國軍工
前衛1→前衛2→前衛3
獵手1→獵手2→地空-10防空飛彈
紅旗6/7→LY-60/FM-80(FM-90)
KS-1→KS-1A→KF-3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179993
 阿楨
阿楨
俄烏戰爭
館長真是先知,不只預知俄國普亭不再柔性吞併南奧塞1而會合法合併克里米亞,還預知俄烏難免一戰!
館長又非政軍巫師2,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的方法論研究3再加了解蘇俄歷史4,便能預測普亭5的決策!
原來普亭早就看穿、美國和歐盟北約會假反恐/人權6之名、計謀推翻烏克蘭民選總統,普亭於是將計就計、合併克里米亞、裂解東西烏克蘭!
普丁果然是有吞併他國野心的大帝!
少來了,普亭只不過模仿西方在東歐7南斯拉夫8拉美9伊斯蘭10等世界幹過的丑事!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7667497
 阿楨
阿楨
習李三中全會
境外的媒體名手名嘴政客民眾/學者專家教授,為何會再次誤判習李的三中全會?
不依理性專業事實、只依反共意識形態之中共研究1,理盲濫情的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誤判中共是正常、正判反而是反常,中國崩潰論2即是明証!
問題是會前中共大力強調改革之重要、又傳出有啥「383」改革方案,結果卻只是會後的新設國安會和改革小組而已,沒啥具體方案。難怪境外的評論者,會從原先的「雷聲大雨點小」、到《決定》文件的60個具體方案出來的「改革超過預期」,有人又放馬後炮似的說啥「誤判、驚訝與懸念」。
自己不去了解知內情的真正專家,早已言:「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改革深度廣度 三中歷來最大」,怎能怪中共沒講清楚?
問題是中共太威權了,不像民主國家要經過各種公開的辯論才形成透明的決策!
問題是大多民主國家含美日台(德除外)的辯論似「便」論、常便秘沒效率吧!怎能反怪中共(含新加坡) 的威權太有效率呢?
民主「便」論豈只沒效率,還常假民主之名3、相互噴糞4成民粹5。
民粹又怎樣,反正一句「不民主」便能否定中共的一切改革。
那就讓反共者盲目地隨便否定唄,自以為閉著眼睛,中共的一切改革都不存在,包括不在改革方案中的軍事改革「修正大陸軍主義增加海空軍」5「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6等.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7167270
 阿楨
阿楨
當年在戰俘營 反共派殺親共派 分屍裝糞桶【聯合晚報2014.01.11
韓戰老兵身上的刺青,未必全是自願。報系資料照
韓戰結束後,一萬多名反共義士來到台灣。國史館完成部分反共義士的口述歷史,這些反共義士都已年邁,他們回憶當時,在戰俘營裡區分親共與反共兩派,反共派居多,戰俘身上刺青反共字眼,有些是被迫表態,不完全是自願的,有的人沒有支持反共派,就被反共派打死。台灣當時透過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邵毓麟,動員戰俘營中文翻譯員,進行戰俘策反,後改派國民黨中央黨部六組副主任陳建中,以大使館陸軍副武官身分,化名陳志清,在韓國發展戰俘營的反共組織。軍方後來派賴名湯、王昇等協助戰俘返台,楊亭雲也曾參與。
根據調查,一萬多名反共義士當中,四川籍4449人最多,山東籍次之。原國府官兵有9234人。反共義士85%都只在共軍服役三年以下,擔任共軍10年以上僅兩人。曾參加共黨組織有3948人,但有人隱匿經歷。經宣導後,願意辦理脫離共黨組織者有4410人,後來再推動匪諜自首,有609人自首,其中15人情節嚴重送感訓。
反共義士回憶,戰俘營裡打死人是常態,美軍也不會管。反共派殺親共戰俘,還將屍體支解,裝進糞桶裡,隔天扔到海裡,或者是燒掉,也有就直接埋在營區裡面。
幾位反共義士都指稱,有位林學圃,英文不錯,卻被其他人認為沒有明顯表達反共態度,就被活活打死,這人死前還高喊毛澤東萬歲。反共派懷疑他是共產黨故意派來滲透戰俘營,分化戰俘。
韓戰義士控訴 美違日內瓦公約【聯合晚報2014.01.11
1月23日,是紀念韓戰反共義士重獲自由的世界自由日,根據國史館出版的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多位當年來台的反共義士宣稱,被美軍俘虜後,美國違反日內瓦公約,強迫他們擔任美國間諜,透過海陸空的運輸方式,滲透到共軍戰線後方,為美軍收集情報,不配合的人,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韓戰 詳參【圖博館】:《孤獨里橋之役》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1162108
白色恐怖的真相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290589633
 阿楨
阿楨
果然是疆獨幹的
疆獨1組織「東伊運」2終於承認犯下「天安門火燒車」反中恐攻行為,「山西太原116爆炸案」也破案証實是偷竊犯的反社會行為。看看當時條件反射式、指責中共「官逼民反」的、島內外媒體名手名嘴政客民眾/學者專家教授,如何自處和交待?
理盲濫情的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會有啥交待?再怎麽抹黑共匪也處之泰然!說你裁贓維族、打壓弱勢、你就是裁贓打壓,誰叫你是中國共產主義黨,即使國內外環境再怎麼穩定發展,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也會被擴大成「中國崛起」3變「中國威脅」4、「中國夢」5碎成「中國崩潰」6。相反的,美台等資本主義黨,國內外環境再怎麼恐怖攻擊7、校園鎗擊8、政黨惡鬥9,只要享有民主自由之美名10,也會被美化合理化成「正義之師」、「柔軟戰力」、「民意流水」。
如此理盲濫情啊,難怪老是測不準中共的變展11,即使中共再怎麼優待藏12維族也會被反中者嫌、再怎麼改善人民生活再怎麼也會被反共者啐。
有啥辦法,這是所有威權政權在取得成就時、常要付出的代價,別太難過,贈詩四首以慰之!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543898
 阿楨
阿楨
美自誇 兩軍對戰 陸1分內就掛2012-12-04 旺報
美國防務分析家錯估中國?對於中國人在追求成為武器強國過程中所展現的雄心、水準和膽量?關注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西方專家們是否正在誤讀和低估?中國的新航母跟美國海軍艦隊較量挺不過1分鐘?美國《防務新聞》雜誌文章如此報導中國軍力的增長。
戰機起降 專家閉嘴
過去不少西方軍事專業媒體,一次又一次的表示,中國的戰機研發落後美國許多年。報導還指稱,中國新航母跟美國海軍艦隊較量挺不過1分鐘。
他們還說,中國尚需數年才能實現戰機著艦航母。但現在中國已有兩款新型隱形戰機。當照片剛開始亮相時,外界說那是合成的。當殲─15還沒試飛而出現在甲板末端時,好事者說那可能是木製模型。不過所有的一切,都在殲─15著艦後,「專家」的嘴巴全部同時間閉了起來。當隱形戰機飛行現身時,這些專家又不以為然地說,那是絕不會投入量產的原型機。
中國在軍事發展上確實還存在著缺點,特別是在發動機研製上,但其進步也是顯著的。在珠海航展,中國軍方就推出了兩款自製發動機,雖還不能跟西方和俄羅斯相比,但發動機發展在中國似乎有了眉目。11月分就有多個例子,說明中國似乎比計畫提前數年,而非許多西方分析家所宣稱的落後數年。
訓練表現 超乎預期
英國分析家加里·李說:「如果談論的是,中國獲得像美國海軍一樣強大的航母能力,那麼答案是否定。若美國分析家是以他們對海軍力量發展的瞭解和美國海軍的經驗來看,那中國顯然還不具備。可是,中國人現在搞的不是這一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海上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山姆·貝特曼說,「最近中國航母的航空作戰訓練表現,解放軍海軍發展航母作戰能力的速度遠遠超過許多西方觀察家的預期。」貝特曼對此並不吃驚,「我一直認為,北京感覺戰略環境惡化,加上中國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技術進步,只要給予高度重視,中國的航母就能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
詳參【圖博館】:中國航母
 阿楨
阿楨
OECD預言:中國經濟 2016稱霸全球【經濟日報 2012.11.10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9日發布預測說,全球經濟勢力在未來半個世紀會出現大洗牌,中國最快將在2016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2025年前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產值合計可能超越7大工業國(G7)的總和,並在2060年前超越所有已開發國家加總。
與霍布斯邦談共產主義2012-11-11 中時 江靜玲(另參本館:《革命的年代》)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今年十月一日在倫敦辭世。
猶太裔的霍布斯邦十四歲參加共產黨,十六歲跟著叔父逃避納粹,從柏林輾轉到倫敦,在劍橋大學完成歷史學業後一直在倫敦的柏貝克大學任教,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即使在一九九一年英國共產黨解散後,他仍堅持自己是一名獨立共產黨員,「那是我的少年夢,我想保留著它。」
中共十八大本週在北京揭幕,當年訪談中,霍布斯邦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有成為世界強權潛能的講述分析,再次在我腦海中迴盪,昨日重看訪談筆記,益發懷念並佩服這位史學大師。
他指出,在廿世紀中,俄共垮台,歐洲共產國家也瓦解了,中國共產黨已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之初的政策大不相同,「因此,我不相信這個企圖改變社會的運動是成功的。」但是,霍布斯邦對此解析又十分清楚,他把以「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為根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與共產主義執政質變聯在一起,「當『共產主義』演變成為『政府』的那一刻開始,共產主義已完全變質了。」
霍布斯邦指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可以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政府」闡釋得更好,「我們應該把共產主義做為一個社會解放、民族解放,或混合兩者的解放運動,興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嚴格區分開來。」
霍布斯邦早已預言,中國具有成為世界強權的潛能,甚至可能與美國競逐世界超強地位。在那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急速發展,一直到廿世紀未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中國將會很快的邁向先進國家,「中國在廿世紀,建立了強烈的國家定位和民族主義,甚至可說,是一種強權式的民族主義,因此,我認為,中國有極大的可能在未來發展為世界主要強權。」霍布斯邦並指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勤奮和才能各界有目共睹,「我不相信,也不同意一些人的主張,即中國將會開始分裂的說法。」
版主回應
社論-言過其實的「做空中國」論調 2013-05-04 工商時報
大陸主流媒體最近熱烈討論外資正在「做空中國」的話題,擔憂以索羅斯等為主的外資大鱷,正在製造一場以中國為主角的金融危機。大陸媒體的疑慮並非空穴來風,「做空中國」將成為今年第2季國際金融市場不可忽視的議題,雖然離真正的風暴還有很長的距離,卻值得關心兩岸經濟發展的各界人士持續關注。
包括新華社、中國證券報以及大量的平面與網路媒體,最近都持續報導紐約掛牌的安碩富時中國25指數基金(FXI)做空股數飆升的現象。安碩富時是目前規模最大的大陸股市ETF(開放式股市指數基金),到3月底為止,FXI的空頭部位已經升高到4,860萬股,放空比例3.2%,創下2007年以來的高峰。統計資料還顯示,投資者在3月份撤出FXI金額達8.24億美元,4月至23日為止又撤走了2.56億美元,兩個月合計減少超過10億美元。FXI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也誘發海外資金售出香港A股,造成4月份A股欲振乏力的走勢。
除了整體資金流動之外,曾因為揭發安隆(Enron)假帳弊案、放空安隆股票而聲名大噪的對沖基金經理人查諾斯(Jim Chanos),在4月5日一場投資說明會上,提出一份短短19頁的簡報檔案,聲稱中國金融危機的骨牌似乎已經開始倒塌,他認為大陸發生一定程度的金融危機已經存在相當的必然性。
接著4月8日在大陸舉行的博鰲論壇,索羅斯也於演講中公開表示,大陸的影子銀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及房地產融資飆升,這些發展都與美國金融危機前的次貸風險具有類似之處,大陸經濟潛藏硬著陸的風險。
日前本報大陸財經版也報導了大陸上市公司盈餘集中在金融業的現象。依最近公布的今年第1季財報,大陸五大銀行創下2,349億元(人民幣,下同)淨利的新高數字,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就貢獻了688億元;深滬股市上市的16家銀行股,合計的獲利更高達3,091億元。
銀行獲利雖然持續創造新高,不良放款卻同步升高。中國銀監會統計到今年3月底,大陸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增加到5,243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了2成。從2011年第4季以來,大陸的不良貸款餘額就呈現逐季增長的趨勢。雖然整體的逾期放款比率仍低,但是增長的趨勢卻值得重視。
另外,具有爭議性的標準普爾、穆迪以及惠譽三家國際評等公司,陸續對中國經濟前景表達憂慮。動作最大的惠譽將中國的長期本幣信用評級,從AA-調降一級至A+,這是大陸的主權信用評等從1999年以來,首度遭到三大國際評等公司降級;穆迪也將大陸政府債券的評等展望,從「正面」,下調為「穩定」。
外資基金經理人對於大陸經濟前景看壞,幾乎已經獲得共識。美林證券在4月中旬發布對於全球基金經理人的調查,看壞中國經濟前景的比重,竟然高達91%,這又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數字。這些訊號應該可以說明,在日本、歐洲與美國股市聯袂走高的國際趨勢下,大陸股市為何停滯不前。即使政府持續發布政策利多,市場都只能出現短期反應,市場人心不安的氣氛,的確受到外資看空的影響。
雖然「做空中國」的報導看似怵目驚心,但是我們認為,大陸股市過去兩年表現並不亮眼,整體股市位在長期趨勢線的低點,在這樣的基礎上,並不存在爆發泡沫危機的條件。加上大陸資本管制並未開放,近日雖然逐漸放寬QFII的額度,相對於整體市場,外資規模仍然有限,放空的對沖基金要在大陸股市或外匯市場大進大出,實質上並無法操作;外資在ETF市場放空的金額,相對於整體股市也不具實質影響力,我們並不需要因為少數經理人的放話而過度擔憂。
大陸領導階層在習近平與李克強接班之後,面臨全球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以及大陸內部的經濟增長減緩,期待甚殷的國內需求又遲遲無法展現成長力道,的確需要時間與更強大的政策力度,設法提振經濟繼續成長的動能。但此時預言大陸走向「空頭」,明顯欠缺說服力。
外資「做空中國」的論調雖然嚇人,卻也提醒大陸執政當局,應該對已經存在的地方債務平台、過度增長的銀行信貸,儘快加速進行有效的整理。不必刻意追求成長,而是藉著經濟增長逐漸緩和的趨勢,擠掉泡沫,調整經濟結構,同時深化市場化、法制化的政策。那麼經過沉澱之後的大陸經濟,仍會朝向2030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繼續邁進。
 阿楨
阿楨
看懂中共十八大眉角 2012-11-09 旺報短評
中共十八大昨開幕,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為未來路向定了調。他強調「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革易幟的邪路。」既不左也不右;但是他也明確回應了社會對於政治改革的呼聲,獲得5次熱烈的掌聲。可以看出,未來中國將在平穩的道路上逐步推進體制改革。
薄熙來唱紅打黑曾一度蔚為風潮,薄熙來去職,象徵黨中央揚棄文革思想,黨內左右兩派路線歧異似乎隱隱浮現,各界充滿好奇。但十八大會議不但沒有揚棄毛思想,相反的,胡錦濤兩度提及毛主席,而且在提及「科學發展觀」理論時,仍然重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江澤民「三個代表」,強調「這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顯示中共建政60年後,雖然不會再回到僵化的過去,但歷史的傳承不能中斷。
不左不右並不代表不知改革,針對經濟發展後衍生的種種社會矛盾現象,胡錦濤提出明確的政治改革方針。在民主方面,要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在法治方面,要深化司法改革,「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在權力運作方面,要公開化、規範化,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
現代化民主國家體制應有的規範,幾乎已全數納入胡錦濤的政改報告中,但仍需要有完善的規畫、認真的執行才能奏效,才能回應中產階級參與權力的需求、舒緩社會的集體壓力,平安度過國家轉型的挑戰。
胡錦濤這項報告,既總結了十七大以來所完成的歷史使命,也為十八大後的政治定出了路向,在這個平穩的大方向之下,「胡溫體制」順利交棒「習李體制」後,如何落實政治改革將是習近平的課題。
相關新聞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胡八個堅持
政改列專章 胡推行陽光政治
黨代會常任制 擴大基層民主
場邊觀察-不要期待「中國曼德拉」大刀闊斧
新聞分析-政改 正面訊號成亮點
中共元老出席 突顯影響力
習近平謹慎低調 老低頭看報告
缺奧援 習近平前路多風險(楨:?)
8年建成小康社會 GDP翻倍
觀察站/向盲目追求GDP 說拜拜
周小川:大陸經濟 緩中趨穩
大陸CPI控制在4% 今年安啦
大陸自主品牌練功 苦盡甘來
版主回應
胡錦濤:堅持一國尊重兩制 防外力干預港澳
胡錦濤:兩岸應啟動政治對話 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
台灣回應》馬:時機未到 不會邀習訪台
觀家觀點-軍事互信機制倡議 我方宜正面回應
馬英九:簽和平協議 待商榷
綠營談十八大:對台態度相同
綠:胡提「特殊情況」 展現善意
國民黨中央電賀中共十八大
2050中國可能成唯一強權 2012-11-09 旺報
美國《僑報》11月5日文章,釣魚台形勢正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但現在還不是中國攤牌之時,原因與台灣問題類似,因為二者背後都有美國的勢力,而中國還不具備與超級強國美國攤牌的實力。
過去10年,中國最大的收穫,就是被譽為「全球最成功的國家」。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2經濟體的中國,事實上在積累著解決台灣,和釣魚台問題的實力。世界銀行曾預測,估計中國GDP在2020年左右趕上美國,2020年以後差距進一步拉大,到2050年中國GDP將超過7萬億美元,接近美國的一倍,屆時中國GDP將占世界的40%,成為唯一超級強國。「時間是站在中國這一邊」,當中國真如世界銀行所言成為「唯一超級強國」時,台灣、釣魚台問題之於中國將會成為「不是問題的問題」。
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待釣魚台糾紛,需要將中日島爭盡可能納入和平解決中,不讓局勢惡化,尤其是防止戰爭,因為戰爭會擾亂中國的和平崛起,讓美國得到圍堵中國的口實。
回應
中國的問題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如果還是維持一黨專制的政治,是否能持續成長進而超越美國,令人不敢樂觀;相反的,進行政治改革,同樣有動盪的風險。
人類至今尚未發明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有優劣點,不能盲目的站在歐美立場把一黨專政說的一文不值,起碼,對經濟而言是有利的,你把一黨專政和經濟不振畫上等號是大錯。
1 堅持主權 擱置爭議 2 看 誰先動手 先動手必輸 3 看 誰能等待 日本的極右派必定按捺不住
分裂的美國靠什麼維繫團結?【聯合晚報社論 2012.11.08
歐巴馬一人之力,難以扭轉多年累積而且愈演愈烈的兩黨對立狀況,但他勢必得想出方法和國會中的反對黨溝通,和社會上接近半數人口的共和黨支持者溝通,否則他將很快就陷入跛鴨的困境,也會使美國亟需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停滯,這當然是個巨大的考驗。
不過換另個方向看,美國畢竟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許多基本的政治運作機制,還是有助於修復社會和諧。選戰的激烈程度無以復加,但沒有人會擔心美國因此而動亂不安,尤其政治人物深明社會分裂的潛在破壞力,因此一選完就主打「團結」牌。
這令人更加體會民主之可貴,以及民主機制之迫切必要。台灣很多社會亂象被歸咎於「太民主」,但多半是誤用民主精神所致。民主仍然是人類組織社會,解決彼此差異衝突,最安全的一種制度。美國大選落幕,緊接著中國共產黨的接班大戲就要上演,十八大會議所在的北京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城市風采。沒有民主,沒有開放的程序,沒有透明的資訊,領導人的更替就充滿了神秘與危機的色彩。這樣的政治制度,要如何扮演創造社會共識、解決社會緊張的角色呢?
分裂的社會可以在民主原則下繼續運作,倒過來,不民主的社會卻不斷升高內在的分裂。從美國看到中國大陸,這樣的歷史教訓再清楚不過了!
相關新聞
美國源自國內的外交挑戰…聯合報副總編輯郭崇倫
美媒洛杉磯時報:中國經濟政治危機比美國更嚴重
回應
憑空想像, 不知所云.
美式民主,社會分裂,是必然的事,台灣是最佳示範
美國投票行為看似分裂也不是一天了,遠的看林肯當選時的投票行為,近的小布希鬧了一個月才底定,都沒有怎麼樣嘛 (楨:造成:南北戰爭/如今之分裂!)
對中國社會與政治情勢缺乏深刻了解分析,只會幼稚地套上美國式民主的八股論調,這種人有甚麼資格寫社論!?
靠印美元營造"普世價值"來維持團結, 就這麼一回事. 沒錢了, 富人跑了,一樣怨聲載道,.
靠強大的軍警情治力量呀!! 不然你們以為美國靠什麼維持聯邦制...
北京警衛森嚴和民主不民主沒有必然關係. 開票當晚, 羅姆尼把競選總部設在波士頓的會議中心, 一樣是警衛森嚴, 沒有邀請函不得接近, 因為有可能幾個小時後, 他就變成美國的下一任總統, 維安系統疏忽不得. 此刻全中國的政治菁英都在北京, 警衛能不森嚴嗎? 我們批評人家, 要批評的有道理. 不要凡事想當然爾.
(詳參【圖博館】:中共十七大 《和諧社會導論》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國崛起(二) G2 歐巴馬 《分裂的一代》)
 阿楨
阿楨
中共中央2012.09.27開除薄熙來黨籍公職 新華網
經查,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利用職權爲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利用職權、薄谷開來利用薄熙來的職務影響爲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系;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此外,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薄熙來的行爲造成了嚴重後果,極大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國內外産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
薄「雙開」 網民評價兩極 2012-09-29 中國時報
一名自稱施威博士的網民說,薄案「終於劃上句號,一代梟雄就此退出歷史舞台。」不少網民慶幸,「黑打領袖終於玩慘了,差點再推向文革,等待他的會是法律制裁。」
不過,也有網民力挺薄熙來,呼籲民眾簽名支持薄熙來,並對中共「違法」拘禁薄熙來的行動提出抗議。這批網民稱,薄熙來注重民生民權的「重慶模式」有一定的民意基礎,擁有高人氣,導致北京擔心並除之而後快。
相關新聞
陸2重大宣布:薄熙來「雙開」 11月8日十八大
胡溫習李聯手大勝 接班障礙已除
薄熙來「雙開」 未從輕發落
十八大後薄熙來料判20年
大陸甩「政」盪 穩住經濟大勢
薄熙來一家累積大筆財富 其他領導人的家人呢
民眾感念薄熙來 把重慶變美女
重慶百姓仍挺薄 張德江施政謹慎 難全切割
中共官方《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薄熙來下場 證明文革是死路
(楨:未審先判的文革式鬥薄,除非有直接證據,不然民主化後「唱紅打黑」式左派民粹終將起!)
薄熙來遭「雙開」 陸媒掀起「批薄風」
北京倒薄 汪洋率2012.09.30先表態「擁護」
薄瓜瓜2012.09.29網路貼文 為父辯護
薄瓜瓜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劃清界線 薄熙來長子斥父:毀我一生(楨:打著文革反文革!)
詳參【圖博館】:沒直接證據又如何 民主與民粹 別侮辱民眾智商 中共十七大 《中共研究方法論》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中共為何反維權 《天安門一九八九》《謠言》
版主回應
法院:薄谷開來悔罪並提供他人違法違紀線索 2012-8-21 北京晨報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薄谷開來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曉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楨:故非反中霉體造謠的洗錢/情殺!)
相關新聞
王立軍2012-09-23一審獲刑15年 徇私枉法7年 叛逃2年 濫用職權2年 受賄9年 法院解釋輕判原因:叛逃後自首並揭發他人犯罪線索
陳長文評谷案:陸比以前進步
谷案宣判暴露中共在司法與政治的雙輸2012.08.21聯合報社論
(回應:聯合報胡說八道,突顯臺灣落後.是殺人案,薄是政治路線鬥爭. 法院將證據陳現,被告均已認罪,就不需要浪費資源了.不要老是用過去的眼光或是思維,一句專制政體就推論大陸不會依法行政.美國時常在起訴中,採用認罪協商,減刑處理,為何就一定認為是依法行政呢? 台灣以民粹治國, 美國以利益治國(或世界); 所以沒什麼好說的.)
平反六四 考驗「習李體制」(楨:活該!反中者趁薄案加大六四23周年反中力道!)
遭坦克輾斷腿學生出席 18萬港人 燭光悼亡靈
溫家寶文革悲劇說 黨內抨擊
薄案保守派反撲 老幹部聯名上書 罷免溫家寶
薄去職_胡溫趁勢推溫和政改
右派疾呼:不政改會再現薄熙來
中共:政改絕不照搬西方模式
涉台學者:陸未必能套用台民主
陸在意統一願景 冷對民主
守衛倒水十秒 中國維權律師陳光誠2012-4-26翻牆逃入北京大使館(楨:打薄下王叛逃錯誤示範之報應!)
美:陳未向美提政治庇護 表明想待陸
美庇護維權盲律師陳光誠 陸要求道歉 斥美干涉內政
向外媒控訴 陳:感覺被騙 盼搭希拉蕊專機赴美
駱家輝:陳自行選擇離開使館
大陸鬆口:陳光誠可出國留學
陳光誠澄清:未要求政治避難 自願走出美使館
學者:大陸政府寧可把陳送出國
陳光誠事件 從三贏到三輸
北京在陳光誠風波中的寬容表現
安逸紐約 消沉的開始?
陳光誠對外聯繫 受制公關公司
綠委赴美想邀陳光誠訪台 美盼陳光誠 持續學術研究2012.08.31
艾未未欠稅千萬案2012-9-28二審敗訴 艾未未稱不再繳納剩餘罰款 恐再入獄
中共2012-9-30吊銷艾未未公司的商業執照
(楨:以下反映出反中者對中共研究之無知:中共視軍政為機密(其利:知己知彼/其蔽:不利監督),而外媒好揭密(其利:民有知權/其蔽:八卦謠言)!
相關新聞
薄案牽動軍警?多為小說情節
新華社:外媒造謠 別有用心
英媒:北京用八卦抹黑薄熙來
(楨:以上皆共犯!)
習近平「失蹤」十多個版本和來源 每個謠言都難以自圓其說 2012-09-12
1.路透社:療養 游泳受傷可能性大
2.紐約時報:運動引起輕微心臟病
3.博訊:準備十八大過於繁忙 需要就醫修養 無礙
4.博訊:被薄派車禍行刺
5.大陸網帖:曾慶紅的運作下,元老們不讓習近平見美國國務卿
6.蘋果日報:無法接班 改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頂上,總理之位由王岐山代替。
7.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不滿胡錦濤不裸退 十八大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太多團派
8.江系明鏡網和多維論壇和博客:急病 中風 家族病史 腰間盤突出
9《德國之聲》:得罪大佬 被蘋果日報總結為不勝權鬥辭職
10.美國之音:秘密南下處理香港政治危機
11.日本讀賣新聞:游泳受傷手臂無法舉起
12.華爾街日報:運動背部受傷
13.日媒時事通信社:習近平動肝腫瘤手術
相關新聞
接班前夕習近平神隱不利中共穩定 吹皺接班春水
英媒BBC:聯想到林彪事件
看習近平神隱 兩岸更隔閡…【聯合報/季節/研究生 (回應:你教授請假3天沒交代詳細過程 使你們師生之間加深隔閡? 看台籍慰安妇媚日反中,兩岸更隔閡!)
習近平2012.09.15露面 嘴能講、腳能走、手能牽 粉碎疑慮 18大接班軌道不變
BBC:習近平現身 媒體空猜一場 難堪?(回應:媒體的宣傳手法啦!)
習近平12-09-19見美國防部長:日上演鬧劇 盼美勿介入 (回應:習同志能說善道,立場鮮明堅定。看好並期待他將會表現的比胡同志強得多。)
美國防部長2012-09-20:日勿仗安保 為所欲為
日相2012-09-20坦承失算 盡速派特使赴中
習近平2012-09-23強調中國需要周邊穩定 永不爭霸稱霸(詳參【圖博館】:中共唱黑白臉? 美對台的兩手 保釣再起? )
 阿楨
阿楨
中國模式 _百度百科
中國模式的實質,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走出的一條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這是一條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爲實踐基礎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爲奮鬥旗幟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爲指導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現代化道路。
目錄
簡介
淵源與發展
産生的背景和條件
基本特征從經濟體制上看
從經濟結構上看
從經濟增長方式上看
從經濟發展戰略上看
內在規定性獨立自主
改革創新
實踐本位
以人爲本
和而不同
成功經驗
不足和完善
政治智慧
經濟模式
社會變革
文化模式
發展方向
影響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3982.htm#8
中國模式 维基百科
中國模式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自改革開放開始,尤其是在六四事件後,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權力與市場的結盟為特徵,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既得利益集團幾乎壟斷了中國所有重要行業。
正面評價
有評論家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西方國家狀況不佳,應對措施緩慢低效。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人權狀況較差,但經濟穩定發展,前途更為光明。西方注重人權,但自由的模式已失去活力,一個新的北京共識正在成形。
負面評價
經濟問題掩蓋了的政治問題,如中國的經濟性質以及所有權的體制問題等。中國模式」的另外一個弊端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帶動為主。
(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大戰略 中國崛起)
中國模式: 贊成與反對 (丁學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1)
本書將作者一系列的演講和回應整理成文,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公共政策層次的探討和相關思路之理順。作者以中立的態度剖析「中國模式」現象,通過公共辯論啟動思路,以求達到共識。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陳志武 八旗文化 2010)
版主回應
(楨:
同屬儒教文化圈,為何只准「日本第一」「四小龍」不許「中國模式」呢?
(共)匪類不配同一標準唄!只配與同類蘇俄比啦!
另參本館:《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 (鄭永年 揚智 2011)
內容簡介
中國模式是媒體與社會傳播中耳熟能詳的詞彙,然而中國的高速發展能否持續、中國共產黨如何成功轉型、政治體制的改革又該何去何從?以及中國如何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何發展,而各國又該如何看待中國的民族主義等等,這些都是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書為讀者解析何謂中國模式,並為讀者詳述中國模式如何發展而來、未來會如何發展,進行深入而透徹的系統研究。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術背景、獨到的眼光、精闢的批判手法,自紛繁的表象裡超越各種主義的紛爭,對於諸多重要的政治社會問題給予了冷靜、公平與有力的解釋。
作者簡介
鄭永年 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先後出版專書達十四本,由其主編的學術著作也有十二本。此外,更經常在報刊及其它媒體發表評論,為香港《信報》1997至2006年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撰寫專欄。多年來其深入而精闢的中國研究以及視野獨到的專欄文章,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且廣泛的影響。
目錄
前言: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 5
第一講 國際發展視野中的中國經驗 13
引言 14
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 15
社會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17
透過政治與行政手段保護產權 17
社會正義是持續發展的前提 19
社會多元促進政制改革 21
第二講 中國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25
引言:余英時vs.姜義華 26
西方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 28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演變及其與自由主義的關係 34
經濟發展和民族國家建設 43
中國民族主義的未來 47
第三講 政治改革與中國國家建設 53
引言 54
國家與民主 55
國家、民主和開發中國家 63
國家建設和中國的民主化 66
第四講 人本社會主義、政黨的轉型和中國模式 81
引言 82
政黨、國家建設和民主 83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轉型 91
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與黨的第二次轉型 107
第五講 民主化的中國模式 117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118
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 122
中國的漸進民主化 128
第六講 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模式 133
金融危機和中國模式 134
中國的複合經濟模式 137
社會改革和中國模式的改進 146
第七講 國家權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
中央地方關係問題 154
現象的根源 158
現代國家權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161
國家權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166
選擇性集權、國家權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173
第八講 放權改革:中國的中央、地方與公民社會 181
引言 182
兩種分權概念 183
政府間放權如何造就經濟的高速成長 186
政府間放權的負面後果與重新收權 190
國家—社會放權的舉步維艱 194
結論:進一步實行國家—社會分權 206
第九講 必須保衛社會: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政策
發展動力與社會後果 216
曼庫爾.奧爾森和卡爾.波蘭尼 218
開放與市場發展 223
開放政策不均衡的影響 225
政治改革和利益代表 230
社會開放和不均等的政策參與 233
為什麼必須保衛社會? 237
第十講 鄉村民主和中國政治歷程 245
引言 246
農民與民主 246
中國農民的新特質 248
中國農村基層組織形式 251
鄉村民主與民族國家的建設 254
結論 260
第十一講 農民與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視的關鍵點 265
引言 266
作為一門顯學的農民民主 266
理論認識的進步和現狀 268
現存理論的批判 275
農民與民主關係的再思考 279
結論 284
第十二講 中國要從新加坡模式學習些什麼 287
新加坡能不能學 288
權力的有效集中 290
融政黨於社會 291
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295
反對黨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標誌 298
領袖的作用 301
新加坡模式與中國政改前景 303
結語:中國模式與思想解放 309
 阿楨
阿楨
英國媒體稱中國軍力至少在30年內仍是“紙龍” 2012-04-08 環球時報
“一艘插著中國國旗的潛艇浮出水面,壓在潛艇上的明黃色大字寫著:中國軍事崛起。”這是7日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的封面,內頁文章的標題則透著聳動———“龍的新牙”。就在兩天前,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布報告,稱過去10年來,在中國的“戰略性欺騙”下,美國“非常錯誤地”低估了中國的軍事發展。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曾預測,到2020年中國就能阻止美國進入“第一島鏈”。《經濟學家》則說,至少30年內,中國軍力還都是條“紙龍”。這是西方輿論場內的典型圖景,對中國軍力的“高估”和“低估”同時存在,但對于哪個更接近真實,卻沒人說得清。日本學者仲村澄世用“沒有人會踢一條死狗”解釋中國的遭遇,他說,如果中國仍像過去一樣貧窮落後,就不用承受這麽多懷疑和指責。法國《回聲報》6日勸告西方,不要將每個安全問題都化作對中國善意的考驗。因爲如果中國不能在自由世界秩序內追求其利益,它會變得棘手甚至好戰。
美國“檢討”低估中國軍事發展
“10年了,現在很清楚的是,新世紀以來關于中國的許多傳統看法被證明非常錯誤。”5日,這段聽上去有些“痛心疾首”的話出現在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網站上。該委員會起草的一份報告稱,上世紀90年代末一些美國專家曾言之鑿鑿,認爲中國在軍事上永遠不可能超越美國,且爲了發展經濟,絕不會優先考慮發展國防工業,但如今看來,美國低估了中國軍事發展。
這一結論來自對中國4項尖端武器系統的分析。“美國之音”稱,它們的共同點是讓美國情報官員和中國問題專家“大吃一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說,2011年1月中國公開試飛殲-20,此前15個月,時任國防部長蓋茨關于“中國還要10年才能發展與F-22同級別戰鬥機”的判斷猶在耳畔。“美國之音”稱,美國沒能預測到2004年中國海軍推出“元”級潛艇,更沒料到這種潛艇還可能使用不依賴空氣的動力系統。此外,雖然對中國反衛星系統和反艦彈道導彈非常敏感,美國卻錯誤地估算了中國自主研發的速度。
德國新聞電視臺6日將這份報告解讀爲“美國人的擔心”。德國《明鏡》周刊則援引柏林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專家的話說,這意味著美國正把中國視作最可能的敵人。
版主回應
《印度教徒報》評論說,在中國迅速崛起的20年中,中國官員往往將一句箴言作爲外交方略指南,那就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過現在有觀點認爲,鄧的這個外交遺産正迅速褪色。
“新炮艦外交”,這是英國《經濟學家》對中國軍力發展的最新總結。該雜志7日的封面文章稱,龐大軍費改變了解放軍戰鬥的方式:20年前,中國軍隊靠人海戰術和肉搏攻城。而現在,美國五角大樓認爲中國正在掌握所謂“反介入”和“區域阻絕”能力。在西太平洋,這意味著中國能威脅美國航母編隊或設在日本沖繩、韓國乃至關島的空軍基地。這將令美國爲盟友提供保護的說法變得難以讓人信服。
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預測了中國軍力今後10年的發展,這個“藍圖”包括中國將擁有60多艘隱形常規潛艇、至少6艘核潛艇、隱形載人戰鬥機和無人戰鬥機、像美國一樣以航母爲主的海上力量,以及太空戰和網絡戰實力。該中心認爲,到2020年,中國將擁有不讓美國航母和戰機在“第一島鏈”以內行動的威懾力。
“如果當時美國專家裏有更多懂中文的人,他們完全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國軍事發展的實際情況。”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這樣“檢討”對中國軍力發展的誤判。但“美國之音”說,是中國的“戰略性欺騙”誤導了外國觀察家。報告認爲,中國對很多軍事活動保密,或有意發出錯誤和誤導信息,中國國家安全決策過程也難以理解。同時,美國低估了北京感到威脅的程度———中國領導人將美國看作對中國安全的根本威脅。
中國軍力:被低估還是被高估?
雖然英國《經濟學家》將中國軍事發展形容爲“龍的新牙”,但它認爲,至少在30年內,中國軍力還都是一條“紙龍”。文章說,亞洲軍備競賽前景令人驚悚,但對中國軍事發展的關切不應陷入歇斯底裏,(上接第一版)至少目前中國遠非雙方鷹派所言的那麽可怕:其軍隊30多年來未有真正作戰經驗,而美國一直在戰鬥和學習;中國可怕的導彈和潛艇部隊將對美國航母戰鬥群構成威脅,但不是在遠洋。中國海軍遠洋行動僅限于印度洋反海盜巡邏以及疏散在利比亞的中國工人;中國也許不久會部署兩三艘航母,但學習使用航母尚需多年。
以上還只是限制中國軍力發展的因素之一。《經濟學家》稱,“像其他所有大國一樣,中國面臨在槍炮和拐棍(指養老)之間做選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進一步放緩後,其高投入發展軍力將迎來真正考驗。因爲中國與前蘇聯不同,保持國際經濟體系穩定符合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
這種和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報告相反的結論,不禁讓人發問,西方對中國軍力到底是“低估”了還是“高估”了?事實上,這樣的矛盾情況一點都不少見。去年10月,法國《費加羅報》在重要版面刊出題爲“中國軍隊大躍進”的文章,3名特派記者在參觀中國軍營後說,所到之處都能看到中國爲成爲世界之最而不惜付出代價。有趣的是今年3月,法國《當今價值》周刊上一篇同樣以此爲題的文章稱,外界或許無須對中國軍力發展太多擔心,因爲對這個擁有漫長陸地邊界和海岸線的國家而言,國土安全仍是軍隊的首要任務。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從過去30年來看,美國對中國短期和中長期軍力發展的評估預測,總的來說都是“高估”大大多于“低估”。但不論是“高估”還是“低估”,事實是美國對中國軍力相當了解。這從美國每年發布各種有關中國軍力報告就可見一斑。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沈丁立說,比較有名的是美國藍德公司發布的年度中國軍費報告。而實際上,美國政府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獨立的情報判斷部門。
隱藏在這種或高或低的評估背後的則是不同利益。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說,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在美國立場偏右,代表的利益集團是美國大型軍工企業,常常通過渲染中國軍力爲相關企業說話。時殷弘稱,中國軍力已經成爲西方的周期性話題。
“從無稽之談到事實”。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周刊總結這一過程說,一個說法是,中國宣稱新型武器裝備數量微不足道,是爲了以後放開手腳;另外一個說法是,中國新武器裝備的質量非常低劣,根本無法對抗俄羅斯和西方裝備。這些說法都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卻被大衆在潛移默化中接受。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中國軍事科學院少將姚雲竹的一段話被外媒引用。她說,我們做的多受批評,做的少也受批評。西方應該明確自己到底想要什麽。國際軍事秩序由美國主導,在軍事領域中國沒辦法參加類似世貿組織這樣的機制。
沒有人會踢一條死狗
……………
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4-08/1011686978.html
另參本館:《中共研究方法論》中國軍力
 阿楨
阿楨
薄熙來還會回來嗎? by李飛 尖端科技軍事雜誌2012-4
……………
薄熙來是當下中國最耀眼的政治達人,處事果斷,厲行「打黑除惡」,其政治魄力在中共高層無人能與之比肩,堪稱「中國大陸版普亭」,受到各界矚目,美國CNN也曾作過大篇幅相關報導。近5年來,重慶市的經濟發展與民生利益保障(包括住房、醫療、教育以及對農民的保障)始終排在全國首位,整個中國大陸都被薄熙來帶著向左轉,「全國學重慶,到處唱紅歌」,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重慶市調研時,對重慶市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理想信念教育及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予以高度肯定。正由於如此,薄熙來失事如同十級強烈地震,會令今秋中共18大領導層換班變得更加複雜,引發了中共內部對中國大陸未來走向的激烈爭論。
「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民情激憤,左右兩派觀點尖銳對立,各種離奇的臆測和謠言滿天飛,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令人瞠目結舌,接應不暇。3月18日上午,有重慶民眾在朝天門廣場自發聚會,打出「薄書記,重慶人民愛戴您」的橫幅,即刻被便衣員警強行帶走。目前中共中央對薄熙來的處置仍不明朗,人們尚無法知曉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到底做了什麼?薄熙來是否有政治之外的其他問題?中共高層因王立軍事件而引發的政治角力還在繼續延伸,事態仍在進一步發展,關鍵還是要看主流民意的訴求。
日前,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發起了《未來十年10個最嚴峻挑戰》問卷調查,位居前三位的挑戰依次是:
1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2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
3社會福利與人民要求相差甚遠。
人民日報據此得出結論:中國官場腐敗已經超出老百姓能夠容忍的底線,政府不但要做大蛋糕,更應該公平分蛋糕!
如今,中國大陸再次處於波詭雲譎的十字路口,但願薄熙來事件最終能夠完滿解決,以免留下嚴重的政治後遺症;這與文革期間的鬥爭模式相對而言,18大之後,中共領導層順利換班完成,站在「惜才」的角度,薄熙來重返政壇佔一席之地,也下不無可能?不論何種結局,都會波及或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對內、對外政策,甚至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
http://www.dtmonline.com/
版主回應
挺薄熙來 「烏有之鄉」網站遭封【聯合報2012.04.07
支持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最力的大陸知名左翼網站「烏有之鄉」,昨天遭到北京當局查封。該網站負責人表示,已接到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和北京市網管等部門通知,網站從六日中午開始,關閉整改一個月。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報導,「烏有之鄉」網站負責人表示,六日,接到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北京市網管和公安部門的通知,要求這個網站從當日中午開始關閉整改一個月。
與此同時,毛澤東旗幟網、四月青年社區以及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等網站,也都不能正常訪問。
「烏有之鄉」負責人透露,他們的網站遭到關閉的理由是,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妄議中共十八大的文章」。
這位負責人稱,「烏有之鄉」的確發表過不點名批評中共領導人的文章,也發布過有關中共十八大的評論和看法,但是所有議論都在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內。
報導稱,中共當局撤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兼任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後,大陸一些左翼學者公開發表支持薄熙來的言論,似乎讓中共最高層感到憤怒。
評論人士指出,大陸總理溫家寶此前曾發表談話表示擔心文革重新發生,但是當局目前採取的封殺異己言論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文革遺風。
 阿楨
阿楨
蓋洛普:台灣媒體自由全球17 中央社 2012-03-29 (楨:自由亂評!)
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Gallup)今天公布的2011年全球媒體自由度調查報告,台灣全球排名第17,被認為是有媒體自由的國家,遠高於中國大陸和新加坡。
台灣排名也高過法國、西班牙和日本。排行前3名的國家為芬蘭、荷蘭與澳洲。在這3個國家,超過9成受訪者認為當地媒體有充份報導自由。
調查指出,86%受訪台灣民眾認為當地媒體擁有高度自由,只有9%受訪者認為台灣媒體缺乏自由。
這項針對全球133個國家進行的抽樣調查中,58%的中國大陸受訪者認為大陸媒體有報導的自由,14%認為沒有,25%說不清楚。
55%的新加坡受訪者認為新加坡媒體有報導自由,但39%說沒有。新加坡的媒體自由度排在中國大陸之後,兩國皆被這份報告評為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
香港排名第19,85%的港人認為媒體有報導自由,14%認為沒有。香港被列為擁有部份新聞自由的地區。
劉屏專欄-薄案是權鬥 不是改革 2012-03-29 中國時報
中國大陸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突然下台,舉世關注。有人認為這是及時撲滅了文革的火種,及早挽中國於潛在威脅,代表著改革派占了上風,是好消息。但真是如此嗎?很多人對薄熙來深惡痛絕,聽說他下台,額手稱慶。然而胡耀邦、趙紫揚,不也是這樣說垮就垮?
今天打倒薄熙來,這與一九八九年打倒趙紫陽,一九八七年打倒胡耀邦,文革時期打倒劉少奇,一九五九年打倒彭德懷,一九五四年打倒高崗、饒漱石,在本質上究竟有什麼不同?
有美國媒體問道,薄熙來下台,真的是因為唱紅、太左,導致路線之爭?還是因為他得到很多人支持,導致黨內高層忌恨?說的更真切些,第一,是否因為他的唱紅其實反映了億萬人民對貪腐的痛恨,不利於黨中央一心一意的「維穩」?第二,是否因為他的人氣太旺,違背了「權為上所授」的定律?
版主回應
英媒:薄熙來友人指薄遭抹黑丟官 2012-03-30 旺報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這位薄熙來的好友要求匿名。他說,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在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前幾天,與薄熙來的關係「正常」,王立軍還向薄熙來保證他的忠誠。
這位消息人士進一步指出,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數年前是很成功的執業律師,「當她的律師事務所逐漸擴大事業,快速起飛成長時,她結束了律師事務所的業務」。
對外界指稱,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稱頌「文化大革命」,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在薄熙來被革職前1天,間接批評薄熙來。
薄熙來的這位友人說,「任何指稱薄熙來想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說法,都是錯的,更何況他本人還在那期間坐了牢」。
去年11月英國商人海伍德在重慶死亡,他生前據說是薄熙來的好友,受訪的消息來源說,海伍德與薄熙來並沒有任何的商業交易。
薄下台後 烏有之鄉兩派決裂 2012-03-30 旺報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後,挺紅網站「烏有之鄉」隨著大陸政治氛圍改變,造成網站創辦人之一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與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兩人因論述不同而公然決裂。
據大陸《時代周報》報導,楊帆說:「我是烏有之鄉的創始人之一,我現在目標就是要封掉烏有之鄉,把張宏良送進監獄。」
楊帆在微博上指出,張宏良等人的行為「已經觸犯法律,必須嚴懲」。他還指責張宏良奪了烏有之鄉網站的權,用極端思想綁架了他們這群人。
與楊帆的激憤相比,張宏良相對「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轉載別人對他的負面評論。分析認為,這場罵戰是政治氣候變化背景下,聚集在烏有之鄉的部分知識界人士分化與潰敗的縮影。
3月15日,新華網發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消息後,烏有之鄉網站突然不能正常登錄,引起「有人受打壓」的猜測。有分析認為,一些知識分子害怕受牽連,急於與其原來所屬的團體作出切割、劃清界線。
現任「烏有之鄉」經理的范景剛認為,「楊帆的說法嚴重背離事實。」「張宏良2006年開始在烏有之鄉網站發文,他運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普通公眾不易理解的專業問題講述明白,獲得廣泛認同。」
 阿楨
阿楨
孔慶東公開挺薄 節目遭停播 2012-03-21 旺報
香港《明報》報導,薄熙來上周四(15日)被免職後,孔慶東便在第一視頻網的《孔慶東有話說》節目中宣稱罷黜薄是「反革命政變」,還呼籲民眾要挺身「維權」抗「黑暗」。
不料,第一視頻19日發表通告稱,由於進行設備升級,部分節目暫停播出。該網雖仍可重溫《孔慶東有話說》,但上周四挺薄的一段節目被刪除。
重慶「變天」後,大陸多個左派網站連日無法登入,其中「烏有之鄉」在19日重開,但網站內的熱點專題「重慶經驗」標題下卻一片空白。
景山公園禁掛毛肖像
至於薄熙來一手主導的唱紅歌,在薄被免職後,活動也遭到打壓。有重慶「紅歌角」之稱的人民廣場,在15日薄遭撤換當天,突然豎出告示牌禁止民眾唱歌跳舞,由於告示牌是綠色,有網民調侃,「重慶由紅色轉深綠了。」在北京,持續多年的景山公園紅歌會18日亦受限制,當局以影響環境為由,禁止懸掛毛澤東肖像和相關布條。薄熙來○八年六月展開「唱讀講傳」活動以來,在大陸各地推廣的紅歌傳唱活動累計十八萬場以上,參與民眾逾一億一千萬人次,驚人的動員能量令人不敢小覦。
薄熙來被免職後,外界高度關注其動向。網上消息指,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姐姐谷丹,日前偕丈夫李小雪出席大陸著名學者鄧英淘喪禮時,首度開口談及薄熙來的近況,證實薄熙來去職後在其北京寓所,指「薄在家平靜坦蕩」。
相關新聞
左派網站被封鎖 鼓吹改革聲響亮
英國金融時報:薄熙來遭軟禁 妻被調查
學者看王立軍案 中央要阻薄熙來進十八大
王立軍調查薄妻谷開來 薄反目成仇
薄熙來下台 禍起王立軍竊聽風暴
王立軍查案涉及薄熙來親屬? 傳美方智庫刻意介入
網路爆料/薄瓜瓜保母海伍德死 王立軍查薄熙來妻
英國每日郵報:薄熙來之子 生活如花花公子
薄瓜瓜多日無音訊 傳在學校失蹤
金融時報:傳溫家寶3提平反“六四” 薄熙來等激烈反對
相關人士:胡溫當局平反六四不太可能
《澳門每日時報》爆料薄熙來涉澳門黑幫黑幕
據法輪功大紀元報道薄熙來、王立軍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人體實驗
版主回應
「倒薄」陰謀論 傳美智庫介入 2012-03-19中國時報
據「博訊」指稱,中共曾在通報事件時說,王立軍曾向薄通報下屬對薄家人進行調查,因辦不下去辭職,薄對王的處置相當震怒,決定調離他的公安局長職務;薄並開始整頓王立軍周遭核心幹部,秘書司機十餘人都被抓,王因擔心受害決定赴美國總領事館避難。
近日網路還流傳一份「解密」稱,美方智庫曾對白宮建議如何應對薄熙來的內容。華府多家智庫曾祕密建言,應設法運用一切政治資源,在中國製造不利於薄的負面新聞云云。 智庫建議官方應介入「倒薄集團」,激化中共競爭對手之間的對立。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海外即流傳一份所謂《王立軍告白》,刻意突出薄藉「唱紅打黑」圖謀大位的意圖,是地方挑戰中央的「逼宮」。
相關新聞
美國之音:薄熙來聯手周永康 打擊習近平
薄熙來想「謀反」 勝算有多大?
習近平不會相助 薄熙來無能力兵變
王立軍案 美國務院配合國會查
周永康力保薄熙來激怒胡溫內幕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缺席上海政法會議 引揣測
周永康會見印尼外長稱願加強同印執法部門合作
周永康驚現央視專家分析「被露面」
公開透明才能終結謠言 2012-03-24旺報短評
王立軍外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事件,發生至今月餘,官方只說他正在接受調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到免職,迄今未見公開活動,海內外傳出不少內幕,有的傳言非常聳動。日前《解放軍報》逐一駁斥了外界不實的傳言,卻未能產生平息之效。
美方握有王立軍提供的情資,西方報刊陸續引述美官員的爆料,內容相當聳動。美國國會日前進行王案調查,並準備舉行聽證會,屆時將會有大量中共權力鬥爭內幕曝光。
與其被動因應,大陸有關部門應主動出擊,盡快結束這場風波。結束風波最佳手段就是公開透明。
相關新聞
真相不明導致政變謠言漫天飛
黨媒《環球時報》:中國不應是謠言共和國
王立軍事件 兩會政協會議發言人趙啟正批媒體荒唐
華文外媒寄兩會厚望 分配反腐成焦點
陸民忍受腐敗 已到了臨界點
兩中將貪腐落馬 胡疾呼倡廉
溫家寶:中共最大危險是腐敗
陸下修經濟成長目標 不再保八
陸GDP 7.5% 學者說合理
外媒掌聲多於質疑聲
今年不保八 透露轉型難題
解讀中國調降經濟成長目標
經濟 不是這樣推測的 2012/03/02 尹啟銘
自由時報社論「中國經濟危機四伏 台灣豈可飛蛾撲火」
全球每一個經濟體在其結構層面都有各自的問題,中國大陸亦然。2011年3月中國大陸開始實施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在改變發展模式和調整經濟結構,追求經濟的永續成長,能不能落實改革、再創轉折而上的另一高峰,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http://blog.udn.com/cmyiin/6166077
外媒認薄下台缺民主程序 2012-03-18 旺報
中央社報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作者麥克雷倫(A. McLaren)分析,大陸號稱「講民主」不犯法,薄熙來也常把民主掛在嘴邊,但他說得太響亮,走民粹路線,結果卻「功高震主」,最後只能下台一鞠躬。文章中也指出,西方政壇觀察薄熙來過去的行事風格,彷彿體現大陸是真的民主國家,但最後卻發現在大陸「黨才是代表一切,黨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相關新聞
中國民調:一半不反對西式民主但不現實 1/3傾向革命 令人憂心
李侃如:中國民主非美外交核心(楨:民不民主西/奴說得算!另參本館:民主偽形 《美國人權外交政策》)
汪洋:烏坎選舉沒有任何創新 只是落實《選舉法》
薄熙來重慶模式 敗給汪洋廣東模式
胡錦濤出手 平衡太子黨與團派【聯合報記者賴錦宏 2012.03.19
「太子黨」是指是一群與中共「元老」、「高幹」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紅朝權貴子弟。在中共官場上,這群人以「革命血統」為主要的政治資本,憑藉父輩關係結黨,靠相互提攜升官。 遠的不說,才結束的中共全國「兩會」,就有以下的「太子黨」參與,包括李鵬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鄧小平子鄧朴方女兒鄧楠、朱德孫朱和平等人,連習近平、薄熙來都算。
「共青團」或「團派」則指一群曾經在共青團系統任職,出身自中國共青團的幹部,與胡錦濤有門生之情,成為中共當今重要的「派系」。胡錦濤、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汪洋、周強都屬團派。
預計十八大的中央委員陣容中,團派可望占上多數,這不僅可穩住胡錦濤的聲勢,讓團派達到權力頂峰,也可以說胡錦濤即使交棒給了「太子黨」的習近平,仍能牢牢掌握局面。習近平接班後,也必須搞「平衡」,不會也不能搞「太子黨」一言堂。預計「太子黨」依舊會掌握煤、電、石油、電信等部門。 但「太子黨」要真正接班,恐怕還得等習近平完全掌握住軍權。
 阿楨
阿楨
(楨:薄熙來雖因以似毛之「矯往必過正」鄧「改革開放」之弊、有違胡「和諧社會」而遭貶,純屬假反文革左派復辟之名、透過媒體謠言、行權力鬥爭之實,若薄真貪腐、胡溫大可依法判薄刑、不必訴諸有爭議的路線之爭,此乃歷史常見之受害者變迫害者如文革/屠猶!但薄「唱紅打黑」之「均富肅貪」本質、是人民對任何政體要求「廉能」之普世價值,若民主選舉、薄將似俄普丁以民粹勝選。故薄不必學宋權謀,宜暫退出黨政,深入民間,或有再起之日!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和諧社會導論》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 《中國多黨合作制》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式媒體監督 《德國與日本的省思》 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與總統職權 民粹亡臺 別侮辱民眾智商 自作孽的親民黨 )
記者會直言 薄熙來:有人給我潑髒水 2012-03-10中國時報
今年大陸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焦點人物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昨上午出席重慶團記者會,薄熙來面對媒體提問答稱,我們敢打黑,就像古人說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要這種精神,「但是他出走這個事情,我就完全沒有想到!」
薄還要求在場媒體完整報導說:「出了這個問題,我很痛心,我感覺到我用人失察,要認真反思和總結」。而重慶市長黃奇帆也當場證實說,他二月七日確實去了美國駐重慶總領事館,和王立軍談了兩個小時、瞭解情況,但外傳有十幾輛車陪著,「這是子虛烏有的事!」
外媒對薄的妻子與兒子「奢華」生活頗多質疑,薄熙來語帶憤怒地說,「也有不少人給重慶潑髒水,給我本人給家庭潑髒水,甚至說我兒子在外邊學習,開紅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氣憤!」語畢氣不過,薄又補一次:「一派胡言!」薄熙來澄清說,兒子讀國外名校,「是拿全額獎學金」,妻子早是司法部認可的律師,原在大連開設律師事務所也很成功,後來怕外界造謠,廿年前就全關了,「就幾乎在家裡做些家務,我對她做出的犧牲很感動。」
相關新聞
記者會高調逼宮 成壓垮薄的最後稻草?
溫家寶撂重話 要薄熙來反思
中共解除 薄熙來重慶市委職務
高層堅決反左 對薄下重手
溫家寶兩提決議 擔憂文革復辟
誰人卡我比?薄熙來能學宋楚瑜屢仆屢起?
大陸的宋楚瑜
高層共識:不會對薄熙來趕盡殺絕
常委成幻影 薄可能依楊白冰模式淡出政壇
薄可能遭「處理」 另傳任政協副主席
學者:薄能告老還鄉已萬幸
薄熙來遭軟禁? 謠言滿天飛
版主回應
薄熙來事件簿【聯合晚報社論2012.03.17
王立軍事件後,眾人還在疑惑著薄熙來究竟將是「死去」或能否「活來」之時,他就被迅速拔除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他的政治墜落,被普遍描述成「左右路線之爭」,亦即是左派敗北、右派勝出。這個解讀法只是淺層的表象,「薄熙來事件簿」應更有深義。
這次鬥爭最確切的涵義,可謂權貴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目前是以前者勝、後者敗為結局。但薄熙來之前何以能夠創造「唱紅打黑」的高潮?難道薄熙來一人之力,就能橫空拉出全重慶、全中國的巨幅紅幕?
他創造的重慶模式,簡言之即「唱紅打黑重民生」。「紅」未必可逕解為「左」,它其實順勢借助了老百姓對「服務人民大眾」的純淨目標的嚮往與回歸;「黑」亦非「黑社會」而已,而多少有遙指「權貴」之意,打黑意在打權貴;而「民生」則是配房、均貧富,就是所謂分蛋糕論。這些無不扣合了民眾的深層心理。
相關新聞
薄熙來: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僅僅少數人富有,就會落到資本主義,我們就失敗了
中共要給左派生存提供合理合法的空間 2012-03-19美國世界日報社論
自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解職後,中國的所謂(楨:所謂即假反文革左派復辟之名、行權力鬥爭之實)左派勢力遭遇沉重的打擊。事實上,目前中國的改革,正在遭遇「極左」(文革)和「極右」(利益集團)的兩面夾擊。如今,「左」的旗幟已經倒下,但人民要求清廉反貪,要求公平正義,要求反利益集團的訴求,依然是合理的。因此,反文革回潮,切忌走向極端,把健康的左翼聲音一併反掉,讓利益集團更加暢通無阻。
相關新聞
薄看不出是左派… 陸媒:左右之爭 言之過早
人民日報頭版再讚薄熙來政績 2012-01-10 旺報
身為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言論的一舉一動,都透露著中共黨內的風向。隨著「十八大」換屆的臨近,《人民日報》竟在3個月內2度以頭版篇幅,宣揚重慶的施政作為。外界分析臆測,《人民日報》此舉說明中共黨內肯定重慶模式,將重慶文化建設樹立為全中國的標竿。似乎也在助長薄熙來聲勢,支持他力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文中,重慶官方多次提及胡錦濤訂定的科學發展觀、和諧論,向黨中央效忠的味道不言可喻。
近3年重慶經濟增速連續保持中國前3位。初步統計,2011年經濟成長16.5%,增幅躍居中國第一。《人民日報》通篇報導充滿對重慶的溢美之詞。
薄熙來重慶經濟模式曾震動海內外
相關新聞
薄熙來談重慶模式稱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
薄熙來談打黑稱涉及重要幹部都上報中紀委
無關唱紅 薄熙來去職因違反黨風 2012-03-19 旺報 徐尚禮
連日來,海外媒體甚至大陸報刊對薄熙來下台有各種推論,有指中共黨內再掀路線鬥爭、反左的政改將啟航。其實,前述推論是霧裡看花,悖離中南海政局形勢。
記者近日和正在台北參訪的大陸、香港媒體總編談薄去職事件,他們共同看法是:薄被免去書記僅僅是因王立軍外逃事件,中央如何處置薄,現在說不準。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媒體有些捕風捉影。
也就是說,外界不能把薄下台和溫講話,解讀成中共要反左、要反毛、決心推政改。
中共中央認定薄的「嚴重政治影響」,不是唱紅有錯,打黑更是無罪,而是他大樹個人權威。薄錯在個人作風問題,他結合自身政治企圖的「唱紅打黑」運動違反了黨風。
相關新聞
薄熙來下台:違反低調的潛規則
重慶政壇風波 媒體進退失據
(楨:反中外媒更甚!呆歹彎的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忽而以民粹強逼哥不可依法行政當法匠;忽而以民主罵薄的(嚴刑峻罰)打黑(分配正義)唱紅!)
 阿楨
阿楨
北韓:別妄想我們會改變【聯合報2011.12.31
北韓30日警告全世界,不要期待新領導人金正恩改變政策,並控訴南韓政府在北韓國喪期間的反應侮辱了已故領導人金正日,揚言報復。
這是北韓結束13天哀悼期、官方媒體首度稱金正恩為「黨、政、軍最高領袖」後,北韓官方首度對外釋放訊息。
北韓最高統治機構國防委員會透過發表聲明說:「我們要對全球愚蠢政客,包括南韓傀儡在內,嚴正並自豪地宣示,他們不應期待我們會有任何改變。」
聲明中又說:「北韓絕不會跟(南韓總統)李明博的叛徒集團往來,廣大軍民將把淚水化為報復之火,燒光所有叛徒。」
首爾東國大學教授金容鉉分析,這份聲明措辭嚴厲,但不表示北韓會與外界斷絕關係,他預測北韓反而會跟美國改善關係。這份聲明是在強烈要求南韓改變強硬的對北韓政策,同時凝聚北韓內部向心力。
北韓以驚人速度 鞏固金正恩體制? 2011-12-31 中廣(楨:猜錯後又唱衰!)
根據南韓「朝鮮日報」一篇「展望朝鮮半島未來走向、面臨的三大變數」的分析報導指出,預計新的一年的朝鮮半島,將有三個不確定變數相互作用,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情況。首先是「北韓變數」。鐵腕統治北韓三十年的金正日突然去世後,他的小兒子金正恩成為北韓最高領導人,但他的權力基礎非常脆弱。南韓國防和統一部長,最近都強調了北韓內部的不確定性。
其次是,南韓將於明年四月十一號舉行國會議員選舉,並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總統選舉。南韓朝野政黨和保守與進步陣營,必將發生劇烈衝突。屆時北韓新體制,有可能趁此機會煽風點火,大做文章。有人指出,北韓有可能透過第三次核子試驗、試射「大浦洞飛彈」等意想不到的軍事挑釁方式,促進內部團結。
該報分析指出,「金正日死後百日、是北韓命運的關鍵時刻」。二十多歲的金正恩,就站在北韓權力中心,這種以驚人速度,繼承金正日大部分職務的金正恩,表面看來,似乎掌握了所有權力。但實際上,他掌握的權力不太可能達到父親金正日的程度。
就「金正恩體制」能否順利領導北韓這一問題,南韓政府外交和安全部門官員大都認為:「需要進一步觀察,但不太容易」。政府的一位高層人士表示:「至少還要觀望三至六個月」。政府內部有人認為,如果金正恩體制早期不能發揮領導力,發生其他事變的可能性將變大,甚至會出現嚴重的權力分裂局面。
版主回應
美華裔作家 再賭中共2012垮 2011.12.31 中央社(另參本館:經濟巫師)
曾預言中共政權將在2011年垮台的美籍華裔作家章家敦,昨天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承認預測錯誤,但他仍認為,共產黨會在2012年垮台。
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出版「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預言中共政權將於10年內垮台。10年過去,他的預言顯然未實現。
2011年結束前夕,章家敦昨天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再度發表「2012年版中國即將崩潰」文章解釋,預言未實現,是因中共保護國內市場,拒絕國外競爭所致。
章家敦說,當年預測中共10年內垮台,是根據中國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放市場所做的推論。中共未垮,和北京當局規避世貿法規,拒絕開放市場,國際社會對大陸忍氣吞聲所致。
章家敦從經濟角度分析,北京當局保護國內市場,拒絕競爭者,加速出口政策,在1990年代,保持兩位數高速經濟成長,但好日子已經過去。
雖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預言,未來20年中國大陸經濟將一路保8,國際貨幣基金(IMF)也預測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但章家敦說,不要相信這些推論。
章家敦分析,中國大陸過去30年的成長首先歸功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當年幸運遇上冷戰結束,中國大陸得以規避政治阻撓進入全球貿易體系,另外大量勞動人口也功不可沒。
不過,章家敦說,這些正面的時代背景都將改變。共產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改變經濟政策,2008年起,再將企業國有化,壓縮外資空間;為扶植本土製造業,拒絕外資併購與增加限制。中國國企成為民族榮耀的象徵,胡錦濤揚棄令中國成功的經濟典範。
章家敦接著指出,全球經濟榮景在2008年告終,各國自顧不暇,並急著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因此容忍中國的外貿政策。現在各國急於向外推銷產品,中國靠外銷推動成長的策略難再奏效,中國將是歐債危機最大的受害者。
再者,中國勞動人口在2014年開始遞減,勞工問題已陸續浮現。工資上揚終究將使中國失去競爭力,影響經濟成長。
另外,北京當局從2008年起大量注資經濟體系,引發資產泡沫化與通貨膨脹,從9月開始,用電量、工業訂單、外銷成長、汽車銷售、房產價格等指標都出現警示,外資從10月開始撤出中國大陸,種種問題都將使中國大陸經濟出現日本式的停滯甚至崩潰。
章家敦指出,去年中國出現28萬次各種「意外」,近期出現的示威與動亂,暴力成分增加,中共官方將無力協調社會不安。短期而言,官方可以鎮壓動亂,但長期來說,民眾認為一黨專政不適用於中國,官方將無法控制現代社會的思潮。
 阿楨
阿楨
金正日遽逝 專題
http://news.sina.com.cn/z/jzrss/index.shtml
白宮首次稱金正恩為接班人 2011-12-23 旺報(另參本館:中國與韓朝 天安艦事件
外界盛傳金正日死後,北韓將進入集體領導,但這項說法被美國白宮修改。白宮發言人卡尼一改先前使用新領導班子的措詞,首次稱金正恩為「接班人」,並稱迄今未有任何變化跡象。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表示朝鮮半島情勢平靜,國務院則稱與北韓駐聯合國外交官通話,進行「電話外交」。
金正日死了,北韓會有內亂外患嗎?
金正日的死何以會引起周圍的戒備?北韓內部會出現震蕩嗎?會不會發生北韓為轉移國內矛盾、而發生的戰爭?或者有沒有國家在此時趁火打劫、試圖顛覆北韓政權?
……………
綜上所述,無論從外部還是內部,金正日之死,盡管會增加北韓政局的不穩定性,但因為支持和反對北韓的力量,暫時還沒有打破平衡的條件和機會,所以短期內都不會導致北韓大規模內亂或者是周邊的戰爭。但意識形態的不同,和北韓對外一貫的作風,會讓周邊國家的戒備至少要保持一段時間,則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http://blog.udn.com/xinluzhiyin/5947761?f_ORDER_BY=ASC&
相關新聞
後金正日時代 傳改為集體領導
美軍:北韓軍隊無異動
金正日遽逝 東北亞警戒
「偉大的接班人」 金正恩 似大權在握
金正日死前 金正恩已掌軍權
北京致電弔唁 肯定金正恩接班
老臣第二代 金正恩拉攏效忠
缺乏權力基礎 各方勢力覬覦金正恩接班埋變數
姑丈攝政 推手還是對手?
張成澤攝政姑丈攀巔峰 讓不讓權?
金氏世襲體制成敗 繫乎軍方
29歲金正恩接班 「垂簾聽政」在所難免
北韓恐進入3年悼喪期 陸擔心穩定度
學者:北韓內部 恐現歧異
英法德視為北韓改變契機
不看好金正恩能hold住 陸學者:北韓必現動盪
美智庫:新領導人可能製造危機
版主回應
公布才知已死 南韓情報網破大洞
韓媒:金正日逝世前 視察超市
金正日死亡 日情蒐慢
南韓人:震驚,憂引發戰爭
青瓦台戒慎 軍方提升警戒狀態
情報大漏洞…金正日歿 美日南韓狀況外
謎樣平壤 韓美情報 瞎子摸象
韓媒:金正日死亡當天 中國就知
中共挺金正恩 重振北韓控制權
金正日逝 南韓股匯重挫、亞股大跌(另參本館:台股 全球股災
大陸支持金正恩 市場將回穩
國安會緊急因應 馬:台灣相對穩定 不須恐慌
台灣學者:朝鮮半島衝突機率不高
北韓空襲 衝擊最多一周
謝國忠:觀察北韓體制是否崩盤
南韓退休基金護盤 股匯市止跌回升
口水護盤成功 台股飆漲303點
國安基金 首日未進場
政府基金:輪不到我們出手
慎用國安基金
外資看護盤 用錢少效果大
短期止跌回穩 但難保不陷長期抗戰
台股一日行情? 3大名師說NO
法人:補量才能上攻
本周台股大漲4.8% 每位股民扳回10萬
擴大公共建設 3千億拚經濟
外資收假 啟動1,200 億攻擊量
外資:先蹲後跳 明年衝8,000
耶誕買氣引爆 概念股暖了
北韓神秘 還是陌生而仇視?【聯合報 卓亞雄 資深媒體人2011.12.21(另參本館:《中共研究方法論》
三十多年的新聞工作資歷,「前進現場」是筆者被教導且奉行的最高準則。很遺憾,北韓領導人金正日過世的消息,各報都只有一則直接出自平壤的消息:北韓「人民播音員」李春姬哽咽播出金正日的死訊。不管是美、日或南韓的所謂北韓事務專家分析,幾乎都沒去過北韓,隔靴搔癢,擴張既定認知,無助世界瞭解北韓。
筆者在一九九四年七月金日成過世後即致力探訪這個神秘國度,七個月申請很痛苦,隔年二月十四日終於得以在平壤順安機場入境,兩天後,是金正日的五十三歲生日,也是金日成過世七個月後北韓第一個假日,平壤超過百萬民眾盛裝到金日成廣場追悼「國父」。
為期七天的北韓觀察,遭遇不少麻煩,但感覺相當深刻,值得。
踏上平壤土地後,目擊北韓,強烈感受到與之前西方世界的定調的北韓形象差異極大,或許不是西方世界因為不瞭解的刻意醜化,但與北韓二千四百萬民眾的生活現況、國家認同、領袖崇拜確實有極值得討論的空間;更讓人深思的是,北韓人民可不可以決定國家樣貌?一定要西方世界定調的才是對的?
看到CNN稍早訪問曾赴北韓人士,只是一位曾有旅遊經驗的人,並不是長居或曾赴平壤的「北韓學」研究者,不禁慨嘆,這不止反映出美國媒體不瞭解北韓,學界一樣陌生;一些西方所謂的「北韓研究者」,竟然都沒去過北韓,不貼近現場,怎能判斷?
到底是北韓神秘,還是西方世界對北韓因陌生而仇視?關心北朝鮮與世局的人,都該拋棄之前印象好好想想。
無知又無感的國際觀【聯合晚報社論2011.12.20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逝世,台灣竟有電子媒體在晚間正規的新聞節目裡,出現記者穿上韓服模仿北韓主播李春姬報新聞,讓觀眾以為看到了Kuso版的娛樂節目。
觀眾喜歡看「春姬」? 2011-12-23 中時 劉屏(另參本館:別再比較兩岸了 《中國電視產業的危機與轉機》)
看台灣的電視新聞,北京的領導人應該非常高興。因為從新聞的內容與走向,看到台灣恰恰是個「地方」而不是國家。這回掀起軒然大波的「梁春姬」,正印證了台灣電視新聞窄化、搞笑、綜藝化,失去了新聞應有的深度、廣度與莊重。
相關新聞
才為「梁春姬」道歉 新聞又搞戲謔
NCC批糟糕 要華視自行懲處
學者:新聞娛樂化 貶低專業
 阿楨
阿楨
18大前 薄熙來、汪洋營造和諧【聯合報2011.12.13
被視為下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熱門人選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從私下的暗自較勁,到日前檯面上演出攜手合作一幕,喊出「渝粵合作,十分愉悅」的口號,營造明年十八大前的和諧氣氛;兩位政治明星的互動,與背後各自代表的政治集團和利益間的角力,都是鎂光燈的焦點。
廣東和重慶、廣西壯族自治區前天在北京分別簽署戰略合作架構協議,薄熙來和汪洋並舉行座談;南方日報和廣州日報昨天都報導了這次座談,強調雙方合作愉快,大陸各媒體紛紛轉載,不過這次兩人會面的相關照片皆未披露。
薄熙來和汪洋目前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外界普遍看好兩人未來的政治前景,明年都可望躋身中共政權最高核心─政治局常委會。薄熙來是「太子黨」代表人物,他的父親是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汪洋則是共青團「團派」要角,早年頗受前領導人鄧小平提拔。
薄熙來近年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不但讓他成為左派領頭羊,也將重慶塑造成著名的「紅色之都」;幾場打黑行動,讓他贏得為民除害的好名聲,更被視為針對汪洋而來的行動,暗諷汪洋在主政重慶時管理不善。
相較堅持左派路線的薄熙來,以親民作風聞名的汪洋主張「實用主義」,他認為緬懷馬列主義、歌頌毛澤東,絕對沒有比發展重要,即做大蛋糕勝過平分蛋糕。有觀察家認為,兩人的瑜亮之爭演化成「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是中共黨內長久以來兩條路線鬥爭的延續。
重慶與廣東在二○○九年已簽訂兩地全面合作協議,前天簽署的合作架構協議,希望共同建構合作與發展新格局。
汪洋在周日北京的座談會上指出,廣東與重慶近年交流密切,去年廣東在重慶投資超過一千項,實際投入金額達人民幣四百卅億元;廣東盼與重慶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原則,積極推進各項合作,使粵渝合作成為中國大陸東西部合作的典範。
薄熙來則對廣東提出「建設幸福廣東」目標給予肯定,也認同汪洋有關加強兩省市合作的意見和建議,盼雙方以這次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為契機,完善、提升合作層次,「使渝粵合作更加愉悅」。
版主回應
社評-中共發展之謎 2011-12-13 旺報
2004年底英國人庫柏雷默提出「北京共識」,解釋中共是如何領導一個有90年歷史、執政超過60年、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依然能充滿生機和活力。不過北京對此說法態度保留。
最近在中國大陸有一本書十分流行,全書回答了15個問題,在這本中共中宣部推薦的圖書中,中共自己對這個問題作了問答。其中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答如:為什麼曾經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為什麼中共沒有像蘇聯與東歐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為什麼能成功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為什麼能管理好近8000萬黨員。最後一段,作者回答了中共能否「成功應對面臨的挑戰」的問題。當然回答十分制式,有些答案甚至與事實有出入,譬如「民族和睦相處」、「凝聚人心」等等。從外界來看,似乎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中共持續發展90年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或外部環境等各個領域都曾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也是眾所周知,但最終並未造成政權瓦解。
過去我們很常用「民主」、「專制」二分法理解中共的治理方式,也常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預測其發展,然而,外界的預測都不準確。特別是我們依據科學的數據,作出負面的預測時,最後預言都會落空。更有趣的是中共在解釋其發展的動力時,使用的也是西方理論,譬如作者說:「扭住經濟發展不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科技教育作為支點」、「行動口號喚起民眾」、「優秀文化與文藝作品照亮人心」、「暢通思想溝通未雨綢繆」;唯一特殊的是「深入各個階層、領域的黨組織」「思想理論建設」,而這些正是外界所撻伐的。那麼何以中國大陸發展的結果,既不是蘇聯式的瓦解,也不是中南美的「拉美化」,林毅夫甚至樂觀預測,中國經濟最終將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何在?
我們以為,有3個常常為外界所不願意承認,或至少是忽視的因素,可能是中共不斷發展的原動力所在。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創新:許多國家從事發展時,基本上是被迫抄襲或全盤接受「華盛頓共識」,以社會革命方式推動改革,換取暫時的經濟發展,社會制度與結構並未改變,經濟發展成果只能曇花一現。而中共的改革是從調整意識型態入手,30年前的改革是先破除「兩個凡是」,再號召「思想解放」,才逐步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作法是在每一次前進的道路上,都立足於既有意識型態的改良,而非否定過去的基礎上,這就有效地延續了社會的主要價值觀,降低了被改革者的空虛和失落,自然也就降低了反對和反彈的力道,為改革前進注入新的動能。這一部分是以往討論中國大陸改革成功與否時,甚少觸及的角度。如今,中國大陸在意識型態方面,注入了「後社會主義階段」理論,強調要從社會主義立場,有序吸收西方社會有益於中國大陸發展的任何理論和方法,用大陸的術語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一口號本身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同時展現了靈活性和保守性。
第二是鳥籠式政治改革:這是中國大陸內外在爭論大陸改革中爭議最大的議題,究竟中國大陸們改革是否包括了政治改革?如果是否定的,則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如何做到?如果是肯定的,何以中國大陸現今的表現似乎越來越不穩?也有人認為大陸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其實,中國大陸今天正在從有限的「行政改革」,逐步轉向「有序民主」的「政治改革」過程中。中共為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改革初期是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但隨著社會的複雜化與改革的推進,行政體制和官員作風也不可能不調整。
進入21世紀,「行政改革」的速度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因此,模仿當代西方制度的民主改革已經悄然起動,如中共中央大肆宣傳中國大陸的地方換屆選舉,上個月底,〈北京日報〉發表文章〈「參與式民主」是中國式民主的實現形式〉,〈環球時報〉社評提出〈民主,僅靠革命遠遠不夠〉,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撰文〈推進憲政民主應是中共執政使命〉等等,看得出來中共中央有意在「政治改革」方面作文章,不過如果以西方民主的標準去期待,必然又要落空,因為中共希望的「政治改革」是「有序民主」的逐步作為。
第三是學習型的政黨:最近有不少海外的華人開始評估「胡、溫」體制的歷史定位,雖然不少人認為「胡、溫」體制的建樹有限,然而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台海的和平發展以及學習型政黨的推動,不能不歸功於「胡、溫」體制。尤其「學習型政黨」的建立更是不容易,從毛時代開始,中共已成為一個反智主義的政黨,如今卻已調整成為每個黨員平均每40天必須學習一次的政黨。執政團隊因而可以不斷吸收新生事物,不斷自我調整,在改革的行動上,雖然保守平實,然而在觀念上不會自我僵化,這就有足夠的智慧去因應外界的挑戰了。
 阿楨
阿楨
江澤民生死 左右未來誰掌權 朝鮮日報2011/07/15
「江澤民去世傳聞」終以一次烏龍報導告一段落。本月6日,伺服器設在美國的中文網站「博訊網」和香港ATV陸續發出有關新聞後,使「江澤民去世謠言」傳遍全球。這一傳聞在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7日予以否認後,暫時告一段落。
媒體對江澤民健康狀況如此敏感,是因為他健在與否會對明年年底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巨大影響。在明年舉行的十八大上,以胡錦濤、溫家寶為代表的第四代領導班子將會下台,取而代之的將是習近平、李克強領導的第五代領導班子。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目前由九人組成,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其餘七人都將到退休年齡68歲。另外,包括常務委員在內的25名政治局委員中,也有14人到了退休年齡。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由誰來接替退休的人坐上這些位置。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派系之間現在正就這一問題展開激烈的暗鬥。
從表面上看,中國共產黨以「集體領導體制」為本表現出非常團結的面貌,但內部大體上分為兩派,相互對立。九名常委中,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三人被列為「改革派」或「共青團派」。因為胡錦濤的權力基礎是共青團。而二把手吳邦國以及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周永康六人則被稱為「泛上海派」。其中還包括指代共產黨高層幹部子女的「紅二代」。
這兩個派系在政治傾向和經濟路線方面有很大差異。就像溫家寶總理去年多次強調的那樣,改革派主張,中國若想持續發展,就必須擴大國民的參政權、實現黨內民主化、擴大媒體自由、優先開發中西部落後地區、杜絕腐敗等。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就是包括這些內容的詞語。相反,泛上海派則提倡堅持共產黨一黨路線、回避西方政治改革模式、控制媒體、優先發展沿海地區等。
在2007年年底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泛上海派戰勝了共青團派。當時,前主席江澤民和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支持的習近平在黨內的權力排名比胡錦濤等人推舉的李克強靠前。接著,習近平在去年10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被增補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從而鞏固了接替胡錦濤成為第五代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泛上海派的教父級人物江澤民去世,中國政界可能會掀起一陣政治旋風。
(楨:上下皆反中者之偏見而已!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中共研究方法論》)。
版主回應
爭權爭路線 汪洋、薄熙來仙拚仙 2011-07-16 旺報記者何明國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7月14日到佛山市順德區調研時強調,實行大部制必須建設「小政府」、「大社會」。以目前汪洋在中共政壇動見觀瞻,這一席話可謂隱含可觀的想像空間。
大部制是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改革思路。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範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達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標。汪洋則提出,實施大部制,必須建設「小政府」、「大社會」這樣的理念。
以汪洋的政治角色,提出這樣的理念背後有太多想像空間。眾所周知,汪洋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中共政壇當今兩位耀眼明星,都是明年秋天18大擠入9名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而且已多次公開進行較勁。不僅如此,汪、薄兩人在18大的權位之爭,同時也被視為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背後各有高層支持。
外界一般認為,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得到北京的支持,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國家副主席也就是未來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都公開相挺,加上薄一直受到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提攜,薄在重慶走的路線,應有習、吳、江等高層的支持。薄和習都是太子黨,同樣受到江澤民的提拔,路線上應是異曲同工。
汪洋在廣東探索公民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得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支持,而汪洋又是團派人馬,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相挺,他的作為多少反映出胡、溫的心聲。
薄熙來大張旗鼓在重慶唱紅(歌)打黑(道),汪洋則嗆說,「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唱歌頌輝煌更重要」。
汪洋說,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要繼續牢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要做大蛋糕」為重點,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薄熙來則說,蛋糕要先分得公平,才能做大,亦即要先將蛋糕分好,再做大。因此薄在重慶大建公租房照顧基層民眾。
汪、薄兩人的路線之爭其實反映出大陸經濟改革30年來出現的諸多矛盾和問題,貧富差距嚴重、社會失諧矛盾叢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考驗。薄認為應多一點社會主義,先做好分配,才可能把經濟的大餅再做大;汪則認為,要再多一點市場經濟先把餅再做大,再講分配。這當中當然也隱含著沿海和內陸之爭,沿海已經先富了,那內陸呢?
對於社會的矛盾和失諧問題,薄主張唱紅歌,走革命老路線,用意識型態那一套來鼓舞淨化人心,化解矛盾。汪則主張探索公民社會,簡政放權,積極培育社會組織,並通過法治手段加以規範,實現社會事務社會管,也就是他的「小政府」、「大社會」理念。
簡言之,面對當前大陸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薄傾向多下一點社會主義的藥,那麼政改的空間就窄一點,汪主張多下一點市場經濟的藥,那麼政改的空間就多一點。汪、薄兩人仙拚仙,既有18大權力排名之爭,同時也在打一場黨內路線之爭的代理戰。
回應
台灣往往汙名化大陸的‘鬥爭’,其實所謂的鬥爭是一種不定時的選舉。經由鬥爭來檢驗一個人的能力,能力或品德不夠的人,馬上淘汰;但在台灣,無論能力和品德多麼的差,都有4年的任期保障。阿扁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傷害,就是因他有4年的任期保障。台灣很多地方不見得比大陸好,只有經由二蔣和民進黨的洗腦宣傳,台灣人還以為大陸差台灣甚多,悲哀啊.....
 阿楨
阿楨
保障房每週觀察:房企缺位保障房 薄利難為藉口2011-07-04 張達智/整理
今年大陸將開工建設保障性安居住房1000萬套,目前半年已過,從部分省市看來保障房開工情況看,情況並不樂觀,開工率較低,房企參與熱情不高,最近調查顯示,百強房企參建保障房建設的僅為三成。除土地、資金是困擾保障房建設的難題之外,顯然,房企缺位也是當前保障房建設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大陸中新網報導,房企對保障房建設受益有所顧慮是必然,較之商品房30%以上的利潤,保障房3%-10%的利潤確實非常微薄,開發週期長,資金回籠慢,不能上市交易影響利潤空間,都是房企對參建保障房的熱情低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時也應看到,保障房建設雖然利潤率低,但是建設規模卻非常之大,量的優勢帶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利潤的損失。保障房的建設和銷售還具有穩定性強,市場風險小的特點,在商品房成交持續低迷的當下,參建保障房也不失為房企度過難關的一種好選擇。
更重要的是,國家對參建保障房建設的企業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資金方面,融資機制的創新,地方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等方式籌措資金,吸引各方面資金投入,在完成保障房建設任務後,企業可以為其他項目融資;部分省市出臺土地優惠政策,比如土地出讓金優惠,審批支持、稅費減免,確保保障房用地優先供應。另外,參建保障房可以密切開發商與政府的關係,提升企業形象,這對企業是個極大的利好。
保障房建設是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不僅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房地產企業切身參與建設、完成建設計畫。開發商追逐利益雖無可厚非,但在任何市場情況下,積極回應國家規定和政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和榮譽感的提升,將為企業帶來的巨大潛在力量也不容小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導、開發商實體積極參與建設下,保障房建設任務的圓滿完成值得期待。
版主回應
今年下半年保障房開工建設將提速 2011-07-06 張達智/整理
2011年7月6日獲悉,自今年5月起,大陸相繼出臺政策積極建設保障房,增加計畫用地及融資支持。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大陸計畫供應7.74萬公頃,占住房用地供應計畫的35.5%,與2010年實際供地3.24萬公頃相比,增幅達138.9%;同時融資支援政策下半年有望出臺,由此保障房開工建設將提速。
保障房用地難題有解 2011-07-06 鉅亨網新
市場一度擔心,在地方政府動力缺乏、資金缺口巨大、土地難以落實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提出的2011年1000萬套、“十二五”期間3600萬套的保障房建設目標難度不小。從我們調研的保障房建設實質推進情況來看,雖然問題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已經無暇在“建不建”做選擇,而是將重點由“口號”快速走向“落實”。從最新情況來看,多元化融資渠道逐步形成,其中發改委明確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可申請發行企業債,募集資金優先用於保障房。財政部明確地方債主要支持保障房,今年首期504億將於近期推出,全年發行規模2000億。總體上,融資難題逐步破解,各地保障房提速,并進入“黃金開工期”,并在11月底實現全開工,建成或基本建成50%。從這個角度講,保障房的對沖功能或者投資“紅利效應”將在三季度集中釋放。
相關新聞
上半年甘肅全省保障房建設開工10萬多套 開工率近七成
武漢159個保障房項目半數已開工
山西保障房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開工率高于全國水平
遼寧保障房開工率91.1%
貴陽"十二五"將有30萬中低收入家庭納入住房保障范圍
南京保障房32種戶型方案,請市民評議
太原:新建住房項目按比例配建公租房
社科院:未來保障房不會閒置
閻慶民:嚴防平臺貸款風險
中銀監:嚴控信貸資金支持地方融資新平台上新項目 - 經濟通
銀監會︰嚴控信貸資金支持平台貸上新項目 - 財華網
保障房債或將使地方政府債務惡化 2011-7-5 華爾街日報(楨:老外老誤判!另參本館:《中共研究方法論》 經濟巫師 中國房地產 )
《新世紀》週刊週一援引行業人士及政府官員的話報導﹐中國大多數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資金鏈已緊繃到極致﹐為保障房住房建設融資發行的企業債券是一根新的救命稻草。
然而報導稱﹐如果缺乏適當的監管機制﹐保障房債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一些新問題。
報導稱﹐許多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公司開始聞風而動﹐打算借保障房的政策東風發債融資。
作為遏制房地產價格飆升的一種措施﹐中國政府一直試圖保障房的建設。中國政府已表示希望年內啟動1,000萬套低成本住房的建設﹐但也承認由於地方政府籌資困難﹐保障房的建設遠遠落後於計劃。新華社近期報導﹐截至5月份﹐僅有30%的保障房得以開工。
保障房建設預計將耗資約人民幣1.3萬億元﹐其中約5,000億元由政府提供﹐其餘則來自企業、居民及其他渠道。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6月末宣佈﹐為鼓勵其他投資者參與保障房項目的建設﹐其將允許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及其他滿足特定條件的企業發行債券﹐以為保障房建設籌集資金。
不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的不斷增加已引發外界對潛在不良貸款的擔憂。
據中國審計署表示﹐截至去年末﹐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了人民幣10.7萬億元(合1.65萬億美元)。一些經濟學家表示﹐這個數據仍然低估了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
 阿楨
阿楨
中聯辦譴責 亞視為誤報致歉2011-07-08 旺報
亞視6日晚間播出江澤民過世消息,引發全球媒體跟進,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社和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天雙雙否認。大陸駐港中聯辦也批評,「香港亞洲電視台的報導毫無事實依據、純屬造謠,對香港亞洲電視台這種嚴重違反新聞職業操守的行為『表示極大憤慨』。」
亞視隨即發表致歉聲明:「亞洲電視注意到新華社今日中午發出的報導,撤回於昨晚有關江澤民先生逝世報導,謹向觀眾、江澤民先生及其家人致歉。」
對於香港中聯辦的批評,王征拒絕評論,他認為,在香港這個地方發生這種事,可能很難避免,同行不應該過度反應。
產經新聞電子版 驚人號外 2011-07-08 旺報
《產經新聞》7日上午9點43分以「江澤民前國家主席去世,或影響今後日中關係」為題,於其網路版發布有關報導。其中指根據中日兩方消息來源,江澤民於6日晚間在北京辭世,目前遺體於北京市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報導並指有關人士表示江為「腦死」。
《產經新聞》接著發布電子「號外」,並刊登相關報導指江澤民後的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將白熱化,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副主席習近平間或出現「直接對決」。同時指出,江澤民的反日色彩濃厚,因此,日本方面將十分關切江澤民辭世後,日中關係如何演變。
新華社否認江澤民死 民意盼死引深思
【新唐人亞太台2011年7月7日訊】即便中共官方否認江澤民的死訊,還是有網民留言,說“新華社消息純屬謠言”。
雖然新華社時隔將近一天之後,才為江死亡一事避謠,但很多消息指,江澤民已經腦死亡。儘管中共瘋狂封網,不少民眾公開慶祝,並燒鞭炮盼江澤民死亡。
http://ap.ntdtv.com/b5/20110707/video/67203.html
(楨:上下皆法輪功之造新聞!)
胡錦濤控制局面 江澤民大勢已去
【人民報/大紀元記者駱亞、吳偉林2010年5月4日採訪報導】“世博會開幕式,他出來不出來很關鍵。如果他不出來,基本上是出不來了。”對於江澤民沒有出席世博會開幕式,大陸學者、中國二戰史研究會會員呂加平分析,胡錦濤抓到了問題的突破口,已基本上把江澤民拿住了。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0/5/4/52460b.html
版主回應
生死成謎 江澤民「被失蹤」2011/07/07美國之音 (楨:反中者「被失智」吧!另參本館:《謠言》 中共十七大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式媒體監督)
在當今中國,「被失蹤」已經變成了一個常用詞。人權活動家、人權律師、異議人士常常遭遇「被失蹤」的命運。所謂的「被失蹤」就是被當局秘密抓捕,人間蒸發,家屬得不到被抓捕的人的任何資訊。
如今,中國執政黨退休的首腦、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也遇到了一種「被失蹤」的麻煩。
美國《時代》雜誌7月6日網路版發表記者漢娜‧比奇的報導,題目是「中國前領導人江澤民死了嗎?中國的網際網路資訊審查機構不讓人猜測。」 報導説:「他到底是死沒死呀?在7月5日夜間大約11點,中國的網際網路開始流傳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已死的傳聞。到了午夜時分,這成為中國的網際網路非常熱門的搜索話題。但是,在半個小時之內,中國網際網路資訊審查機構使出了重手。人們用中文搜索跟死有關的話題,即使是不搭配江澤民的名字,也會得到奧威爾(所描寫的資訊全面控制的集權專制國家)式的資訊:『根據相關的政策和法律,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資深外交事務記者詹姆斯‧法洛斯美國東部時間上午10點發出報導,題目是「江澤民死了嗎?中國在實時演示新聞封鎖控制。」 報導説:「在過去的24個多小時裏,任何一個追蹤社交媒體有關中國消息的人都看到了有關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可能已死的謠傳,然後是官方的否認,然後是沉默……
中國的網路資訊審查封鎖,在中國幾億網民那裏是家常便飯,是他們每日每時都必須面對的現實生活。但江澤民去世謠傳的傳播,以及中國當局隨後的網路刪貼,大大方便了外界記者的工作,使他們原本可能是沉重乏味的報導一下子增添了豐富的戲劇性。
《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實時報"記者Josh Chin在7月6日中國時間晚上發出報導,題目是「江澤民死亡的謠傳出現,中國的江河失蹤。」 報導説:「今年夏天,中國出現大洪水。最長的河流長江洪水尤甚,導致幾十人死亡,毀壞了成千上萬畝的農田。但對中國一個最有人氣的社交媒體網站的用戶來説,長江已經消失了。
「星期三,在新浪網的微網誌那裏搜索『長江』,人們得不到搜索結果。搜索其他的江,會得到該網站標準的資訊封鎖通知:『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江河為什麼突然遭白眼了呢?最可能的解釋是,自星期二以來,網路間流傳大量的謠傳,説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病重,或者已經死去。江澤民姓『江』(由此連帶江河遭殃)。」
「但是,一個很尋常的字眼星期三加入了敏感詞的單子。這個詞是『江』」。
「突然之間,凡是帶有『長江』字眼的有關長江一帶洪水的帖子,得到跟提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帖子一樣的對待。這樣的帖子上網就消失。其他提到別的江的帖子也是一樣。在微網誌搜索那些江,會得到司空見慣的回應:『根據相關政策和法律,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其他消失的字眼是『心臟病突發』和『總書記』以及『301醫院』。有人説,江澤民已經在那所設在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醫院去世。」
美國之音在中國時間7月6日半夜時分獲得的最新消息是,新浪微網誌搜索功能以及轉發功能出現罕見的失靈,不能進行任何搜索或資訊轉發。新浪微網誌發出公告説:「由於系統維護,微群內的轉發功能和搜索功能暫時關閉,對給您帶來的不便深表抱歉。」
外界以及中國網民現在不清楚這是新浪正常系統維護的一部分,還是中國當局封鎖資訊行動的一部分。
官方資訊的稀缺和不透明,也使先前的舊消息獲得了新的意義。日本主要報紙《每日新聞》在日本時間7月7日淩晨0點,也就是北京時間6日夜間11點發出駐北京記者工藤哲的報導説:「在中共創立90年慶祝大會之後,江澤民病重的説法通過微網誌、推特等開始悄悄流傳開來。在7月5日中國外交部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人提出了相關問題。新聞司副司長洪磊聽到這樣的問題,顯得有些吃驚,並予以否定,説『我沒有聽到這種消息。』新華通訊社等國營媒體從6日到現在也沒有有關江澤民健康狀況的資訊報導。」
江澤民在中共成立90年紀念活動中沒有露面,成為他病重或死去的謠傳的來龍。現在,中國的網民和國際媒體在繼續追蹤其去脈。
 阿楨
阿楨
渣打:陸經濟Q3非常軟的著陸2011-06-30 旺報記者韓化宇
大陸經濟將「硬著陸」或「軟著陸」?近期爭論不休。渣打銀行最新研究報告表示,大陸經濟有望第3季「非常軟的著陸」。
同時,在今年的下半年宏觀經濟基調將從注重通膨,轉為同時強調「經濟平穩快速成長」和「保持溫和通膨」,意味緊縮政策落幕。
不過,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師梁兆基昨日表示,不要對下半年貨幣政策放鬆「存有幻想」。因為當前實質利率仍為負,投資仍偏高,通膨不會馬上回落。
渣打報告稱,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進一步調高存款準備率或升息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只要通膨降溫,即代表本輪緊縮政策已過關,整體經濟活動良好加上通膨受控制,都為大陸經濟「軟著陸」創造條件。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表示,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很難控制在4%以下,但有信心維持在5%以內。
他並還強調,大陸抑制通膨「已取得明顯成效」。
渣打報告指出,大陸經濟成長可能持續減緩,但「硬著陸」風險非常低。
報告還稱,北京中央將於7月前兩周舉行小型經濟工作會議,調整下半年宏觀經濟重點,預計「經濟平穩快速成長」和「保持溫和通膨」將並重,而非只強調通膨目標。
梁兆基認為,北京中央可能擔心升息會戳破房地產泡沫,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因此對升息保持審慎。
預計今年至少升息2次,大型銀行存準率有可能升至23%。
(楨:以下在唱衰中國!另參本館:經濟巫師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崛起(二) 中國振興方案(二) 中國經濟成長之謎 大陸經濟 國際金融新體制(一) 中國地方經濟 )
相關新聞
大陸經濟危機顯現
二次金融危機?羅比尼:2013「完美風暴」來襲!
完美風暴裡的中國氣旋
賀鏗:大陸經濟出現滯脹跡象
經濟硬著陸 索羅斯唱衰大陸
瑞穗:陸信貸泡沫和希臘差不多
戳泡沫 對沖基金放空人民幣
地方債危機 滬城投傳無力償貸
小企錢荒 銀行建議給專項信貸
中國土地財政失靈
中國的人口負債
版主回應
溫家寶:今年通膨5%以下 GDP保八
溫家寶:大陸成功抑制通膨
李克強:通膨在全球蔓延
溫家寶今抵英國 「對歐元有信心」
扮演救世主 陸外儲增持歐債
溫訪歐扮救星?歐學者:別想太多
中德磋商 簽署逾150億美元合同
不顧風險 陸有戰略經濟考量
溫家寶訪英 帶來大筆生意
歐債危機 中國出手救援
中國全球經濟貢獻 最大
中國趕超美國 長路漫漫
飛龍與巨象 中印角力競合
中國崛起 桃太郎苦抉擇
(楨:此次歐債危機有美法之陰謀!另參本館:《歐洲新霸權》 《歐洲共同市場》 歐豬四國 法總統能改革嗎)
IMF換帥即改口 陰謀論再起2011-07-02 明報專訊
5月14日中午在曼哈頓酒店套房發生的懸案,把卡恩由天堂推至地獄。案件雖未開審,但控方及美國傳媒一口咬定卡恩有罪,卡恩被迫辭去IMF總裁一職。但就在法國財長拉加德接掌IMF總裁不久,美國檢察官卻突然改稱可能撤銷對卡恩的性侵控罪,這戲劇性發展,難免令陰謀論再度熾熱起來,例如是否有人(楨:沙克吉啦)想阻止他選總統,還是有人(楨:美國啦)想逼他交出IMF權柄?
美殭屍消費者 拖累全球經濟 2011-06-22 工商時報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非執行董事長羅奇(Stephen Roach)指出,迫於高失業與高負債而緊縮開支的緣故,美國消費者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成了名副其實的「殭屍(zombies)」,全球經濟恐受到這群美國殭屍消費者的拖累,建議亞洲經濟重心及時轉向內需,方可維持成長動能。
政府撙節惹民怨 變天潮恐襲歐 2011-06-18 中時
歐洲債信危機野火燎原,不少國家政府被迫推行財政撙節方案,但也引發民怨沸騰。繼希臘之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十六日也有逾一萬名憤怒群眾走上街頭,參加「小丑大遊行」。
相關新聞
卡恩性侵案 女侍疑想撈一筆
IMF前總裁史特勞斯卡恩 有限度恢復自由
卡恩性侵案 原告被爆是妓女
IMF前總裁的下一步 告檢警?
卡恩案大轉折 青天霹靂撼法國
卡恩的總統夢…回溫中
史特勞斯‧卡恩逆轉勝?
“性侵門”曝陰謀論卡恩掌握美黃金儲備秘密?
「誰陷害卡恩?」 支持者深信陰謀論
卡恩性醜聞扯上“陰謀論” 法民眾疑美設陷阱
薩科奇三線作戰可能以轉移國內困境視線為目的(另參本館:伊斯蘭革命
卡恩愛女人 法支持民眾不嫌
拉加德掌IMF 面臨重重挑戰
拉加德上火線 點名先救希臘
希臘危機暫解 美股收紅
希臘撙節案過關 歐股勁揚
希債危機暫解 銅漲金跌
油價攀抵2週高點
120億歐元希臘紓困金將到手
希臘悲劇?鬧劇?
希臘爆大罷工
希臘賣祖產籌錢 乏人問津
希臘通過撙節案 激化警民衝突
條件太苛 希臘新撙節案惹民怨
歐元區的赤壁之戰
經濟比爛 歐元對美元續堅挺
東歐 看破統一大夢
國家倒債…早有前例
認清希臘將倒債的事實吧
主權債信風險 希葡登雙高
防債務危機 義將撙節支出
IMF:西班牙恐陷經濟危機
歐債危機新爆點 穆迪擬降義大利信評
西比義 恐捲入風暴
憂鬱的世界:四速變失速?
歐美經濟 烏雲籠罩
新經濟危機烏雲 籠罩全球
謝國忠:下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即將來臨
「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三個麻煩
 阿楨
阿楨
古巴首提任期制 卡斯楚時代幾年內落幕【聯合報2011.04.18
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16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主持14年來首次古巴共黨代表大會,他表示古巴幾個最高領導職務應該建立任期制,限當2任共10年。這項宣示如果真的實施,堪稱古巴1959年共黨革命以來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卡斯楚兄弟檔統治古巴52年的情況不會再出現,卡斯楚時代也將在幾年內落幕。
勞爾表示,古巴共黨領導階層必須換血,同時接受嚴格的自我批判。他並說,任期限制適用於他本人與古巴各部會首長。在共黨當家的古巴,這種提議前所未有。勞爾現年79歲,6月滿80歲。
勞爾表示,古巴人必須克服「精神惰性」,而唯一足以威脅古巴革命的因素是「我們未能主動糾正錯誤」。
84歲的前古巴領導人卡斯楚與胞弟勞爾聯手統治古巴長達52年,卡斯楚出現嚴重健康問題後,2008年由勞爾接任總統。
卡斯楚並未親自出席此次為期4天的黨代表大會,他上個月聲稱他已不再是古巴共黨領導人。
如果勞爾具體落實政治職務任期限制的構想,他最快2013年、最遲2018年就會交出權力。勞爾的談話意味,卡斯楚兄弟共攬大權的時代即將結束。
這是古巴共黨的第6屆黨代表大會,共有1000人與會。他們將在會中表決勞爾擘畫的經改方案,正式解除卡斯楚的黨最高領導人之職,同時改選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等重要機構的成員。
勞爾的經改方案將廢除基本物資大規模配給制度,將社會福利支出「合理化」,維持健保和免費就學,不過不會實施類似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改革。
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以及國際糖價暴跌,對古巴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目前全球號稱為共產主義國家只剩5個,包括中國大陸、越南、寮國、古巴和北韓,中、越、寮都已建立領導人任期制,並規定最多只能連任1次,古巴實施類似改革後,只剩北韓領導人能終身執政。
版主回應
中共內部鬥爭激2011-05-26 旺報
內外交迫,中紀委祭出霹靂手段。昨透過《人民日報》向黨員發出警告,要求謹守黨的政治紀律。綜觀過去中共發展歷程,中紀委通令黨員尊法守紀並不罕見
今年,中共在目睹中亞、北非的社會動盪;中共四級黨委領導班子處於換屆的重要時機,中紀委祭出「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的尚方寶劍,格外引人矚目。
對於中共的統治,大陸社會其實早已醞釀某種程度的怨懟。尤其最近部分指標性人物還「大鳴大放」,針對中共過去的錯誤行為不假辭色攻擊,在在挑戰中共容忍所及的那道紅線。
社評-評中國特色接班人制度2011-05-26 旺報
在神祕色彩壟罩下,大陸高層人事更替一直是海內外專家、學者和媒體關心的話題,特別是中國已經崛起,換代換屆的「十八大」人事變動,不但將影響中國的命運,對全球政經情勢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因而備受矚目。總體而言,外界對中共人事變遷的判斷,比上個世紀要準確得多,但仍難以避免若干猜測。
大陸政治體制雖然並未出現根本性變化,但今天大陸高層接班問題已與毛澤東時代不同,毛時代的接班問題具有兩大特點:一是毛一人定奪,二是獨裁接班,接班無法經由制度、規範決定,而以毛的意志為主;同時接獨裁者的班,接班者可以集一切權力於一身,這就註定了接班的鬥爭是攸關個人生死的鬥爭,贏者通贏,輸者輸掉一切。
鄧小平處理交班問題時,只有權威而無權位。權威無法繼承,接班人對他不會構成威脅,於是在處理權位繼承問題上,鄧小平可以為共黨政權的存續而選人。
當年鄧擬出培養幹部的條件: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原則,也建立「梯隊接班」制度,將培養成熟的幹部選入領導階層歷練。後來,鄧小平又開創「集體領導」模式,所以有「江核心」的提法,使得接班鬥爭從權力的鬥爭轉向職位的鬥爭,大大趨緩鬥爭的衝突性。
到江、胡時代,特別是胡錦濤,他是「梯隊接班」制度受益者,也是「集體領導」運行者,經過從「十五大」到「十七大」的運作,江、胡都為接班訂定許多新的規則,這一套規範漸漸成為中共黨內的鐵律。
胡錦濤應提拔誰來接班,在江澤民時代並沒有解決,胡自知無法單獨指定接班人,所以有了「民主測評」辦法,由黨內精英共同承擔選拔接斑人的責任,使新的接班團隊在黨的精英階級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換言之,胡在接班人的問題上主要考量是如何保持共黨繼績執政。
胡在「十七大」的「梯隊接班」中安排了兩個人:習近平、李克強,習為總書記,李為國務院總理,一般稱之為「雙接班」制,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但是無論如何按中共黨內的政治文化,除非中共內部或大陸社會出現重大問題,否則這兩個人的接班應該己經無需討論,需要討論的是,另外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及分工。
鄧小平以來這一套接班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接班制度,具備4項持點:
第一、強化政權穩定性:在梯隊接班的安排下,接班人預先進入執政核心中,他們雖不能主導,但也承擔部分責任,從而得到相互磨合的機會,經過5年歷練,正式接班後,無論在工作方法、決策風格上都已相互熟悉,勿須摸索學習,可以直接上路。
第二、強大的政策延續性:在梯隊接班制度下,接班人常常承擔跨屆工作計畫或文件負責人,例如,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報告人是江澤民,起草小組負責人是胡錦濤,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的政治路線就不會有重大改變;同理,中共的「十二五規畫」綱要起草小組副小組長是李克強,未來「十二五」的執行,就不致於出現「人走茶涼」現象
第三、削弱政治鬥爭衝突性:權力鬥爭是政治行為的共通性,權位越高鬥爭越激烈,所以西方就提出了以「數人頭」取代「打破頭」的選舉制度來緩和衝突。中共則以集體領導來因應,中共中央9位常委,各有分工,每個「常委」都負責一個領域的工作,統管全大陸該領域所有工作,因而有人稱大陸有「九個總統」。在此制度下,勿需爭第一或唯一。最近傳出王岐山負責中美談判,因應經濟危機頗受肯定,有可能超越李克強,其實王岐山未來最可能是常委兼常務副總理,分管財經工作;在此制度下總書記是班長,負最終總責任,但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尤其是那些非總書記直接分管的工作。如此一來,大陸政治鬥爭的手段、方式、激烈程度都大大不同以往。
第四、失敗者也有保障:政治鬥爭最終必有失敗者,這一部分也和毛澤東時代不同,失敗者不再被打倒在地。只要沒有政治問題,沒有法律問題,失敗者基本生活待遇仍有保障,和緩了政治鬥爭的衝突性。
但最後還是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何在,大陸人民會永遠認可嗎?(楨:制度那來永恆?民主形式也不可能萬萬歲!另參本館:民主形式萬歲 《中共研究方法論》)
 阿楨
阿楨
聯合筆記/艾未未仰空長嘆【聯合報╱陳東旭2011.04.10
國際天文學會去年底,將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艾未未星」,以表彰艾未未在藝術領域的成就。不過,艾還來不及看到這顆星星,就被中共以「涉嫌經濟犯罪」逮捕拘留。
從北京奧運後,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縮與網路的監控日益嚴重。社會活動家胡佳入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重判,多名被指散布茉莉花革命的社會人士被逮捕;接著在上周,擁有國際知名度的艾未未也落難。
這一連串的行動,說明中共改革愈開放、經濟愈發展,對維護自身利益、對維護「改革來之不易的局面」也更堅決,對異議人士也就更無法包容;對任何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引起政治動盪的源頭,更是要堅決打掉。
而網路快速傳播的特性,個別人士利用網路傳遞訊息、「散播謠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成為中共首先要預防的對象。
於是,在大陸,臉書不能上;各西方國家主流媒體網站不能上;有關對大陸的網路負面評論幾乎都被刪除。
美國年度人權國別報告,今年仍把中共批評一番,批評語氣比往年加重,國務卿希拉蕊更以「不安」來形容中共侵犯公民的網路、言論、集會自由,以及鎮壓社會活動人士的趨勢有增無減。
然而,西方國家再怎麼批評,中共似乎依然不為所動,按照自己的發展道路前進;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似乎事不關己(或者說根本使不上力),祇忙著發展經濟、忙著賺錢。
版主回應
福山的新政治制度2011-04-12 中國時報 【郭崇倫專欄】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瓦解前夕,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正好把右派知識分子想講卻不知如何措辭的概念,以黑格爾歷史目的論的方式呈現,一出版,立即洛陽紙貴,華府有些書報攤,刊載論文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期刊,比色情雜誌還暢銷。
福山那時還不到四十歲,搖身一變,成為最為人知的學術人物,整日演講邀約不斷,活躍在權力核心內,福山是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大師,在小布希當政時,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盛極一時,他們主張民主沒有例外,駁斥其他文明產生不了民主之說,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入侵伊拉克,希望建立穆斯林世界的新民主典範。
但研究革命的人多對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嗤之以鼻,哈佛大學女教授Theda Skocpol 專研法國、俄羅斯與中國三大革命,就對福山過於簡化的論點,強烈批評,但是最切中要害的,卻來自他在哈佛的恩師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他一九九三年發表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反對冷戰後的價值將定於一尊,相反的,他認為,衝突將來自更古老的文明衝突。
杭亭頓的看法,隨後受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印證,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後來雖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是等茉莉革命一起,整個論點又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福山的看法再度勝出。
期間他也寫過其他的著作,如《信任》等,但都沒有像第一本這麼轟動,現在廿年後,福山又要出書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卷一(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十二日上市,佳評如潮,福山又回到他所擅長的大歷史哲學論述。
寫這本書其實是個偶然,恩師杭亭頓二○○八年過世後,他一九六八年的經典「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要重印,大弟子福山被要求寫篇導言,重看後,觸發福山靈感。
在他定義下,好的政治制度包括三方面:國家執行力、全體接受的法治、以及統治者為行為負責,他想要研究,在不同於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環境裡,像是印度、中國與穆斯林世界,政治體制是如何形成的;福山的新想法裡,中國最近十年的飛躍式表現,尤其占有一個典範地位。
中國也很注意他的看法,尤其是一月在胡錦濤訪問美國時,他在金融時報發表了「美國民主沒有什麼好教中國的」,三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是下一個(革命)嗎?」;三月底,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邀請,訪問北京,由副局長俞可平與他做了一場對談。
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的智庫,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問題的釐清,俞可平問的問題當中,有些反映出中共目前的困惑與不安;譬如中國目前的制度是「姓社」還是「姓資」,這是中國學者爭論的問題,對福山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現在全世界,已經不存在純粹的資本主義,或純粹的社會主義,而是政府以不同程度介入經濟活動,來促進社會平等。
但是福山到哪裡都會被問到的,就是「歷史終結」之後,「新的歷史是什麼?」福山以市場民主與政治民主,做為歷史發展的終點,指的僅是人類發展的方向,已經確定;但是最近有人提出,類似中國的「威權政府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不是新的選項?歷史新的方向?
福山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模式的確是非常有趣,但是其他國家未必能夠複製,而且中國模式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也是個問題,他提出未來將面臨的兩個挑戰;其一是,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美國金融危機後,消費模式不再,中國必須開始擴大內需,轉向為平衡的發展模式;其二是,在政治權力集中的體制下,中國如何能維持高品質的治理水準。
但福山的兩個挑戰其實是蘊含在他對中國的假設前提中的,他認為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夠繼續維持,有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是中產階級,願意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前提下,以有效集權的政府,換取政治上的民主參與;其二是,由於高度集權,中下階層官員的腐化,可以經過由上而下的懲處,但是如果最高層是腐化的,就會陷入中國傳統「壞皇帝」的困境,就像中共自己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從福山的標準來看,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雖然國家有效能,但是底下人民的不滿,要靠上面的人抒解民怨,不是上面的人為此去職負責,這離民主還是很遠,不過對福山來說,這樣的政治制度還是令人滿意的。從這點來看,他不愧是杭亭頓的弟子,政治穩定還是有最優先的價值。
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中國宣言(館長代胡擬)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共研究方法論》 民主形式萬歲 《歷史的終結》 《文明衝突》
 阿楨
阿楨
民主制度選出的無厘頭總統2010-12-18 中時 梁東屏
亞洲的民主制度這些年來頗精彩,選出了一些無厘頭總統。
最出名的是已經過世、雙眼幾乎全盲的印尼總統瓦希德。
被暱稱為「古斯度爾」的瓦希德在印尼民間聲望很高,主要的原因是他擔任印尼最大回教組織「回教教士聯合會」主席,但是更大的原因是他玩世不恭、愛講笑話。
第二位無厘頭總統是緊接著瓦希德的美嘉華蒂,她是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長女,基本上是家庭主婦,靠著父蔭以「公主復仇」之姿當上總統。
不過現在倒是出了個後起之秀--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
如所周知,艾奎諾三世之所以會當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母、已逝菲律賓前總統科拉蓉的庇蔭,他本人一直是位表現平庸甚至根本沒表現的參議員。
今年八月,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生香港康泰旅遊團巴士遭槍手挾持,菲國軍、警處理危機荒腔走板,造成人質多達八人死亡的慘案,引起全球對菲國軍、警匪夷所思素質的批評。
結果,艾奎諾三世的表現更讓人下巴脫臼。
他不但拒接香港特首曾蔭權的電話,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第二天更讓人瞠目結舌地發表了一個面帶微笑的記者會,遭到批評之後居然說「微笑」是一種表達悲傷的方式。繼則又以總統之尊跑到出事現場,煞有介事地穿著便服、端著槍,模擬軍、警當時的攻堅處理,似乎想證明遭全世界訕笑的軍、警並未作錯。
最近,艾奎諾三世出面解釋為何菲律賓沒有派遣代表出席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的本屆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地表示,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影響到該國營救在中國遭判死刑五名毒販的努力。
台灣也對自己的民主制度頗為驕傲,是啦,是沒選出什麼「無厘頭」總統,只曾經選出了位「有搞頭」的總統--陳水扁,還讓他搞了八年。
留言:
民主制度就是自做自受的制度,運氣好選出好的人,運氣不好選出爛的人。但總比專制制度(像中國大陸)好,因為下次選舉就有機會讓爛傢伙落選。但是台灣比較特殊,因為藍綠對抗太嚴重,深藍和深綠只認顏色,不管候選人本身的素質,這是台灣的最大隱憂。(楨:迷信者之言!)
版主回應
中國經濟會硬著陸嗎?【經濟日報社論 2011.04.26(楨:又一經濟巫師?另參本館:經濟巫師 《中共研究方法論》)
準確預測美國房市泡沫及隨後全球信貸危機而聲名大噪的著名經濟學家、被封為「末日博士」的紐約大學教授羅比尼(Nouriel Roubini),這回看上了中國大陸,最近他預測2013年後中國大陸經濟將會出現硬著陸。
英國《金融時報》針對羅比尼的論點有評論指出,羅比尼有夠勇敢,敢於預測中國經濟崩潰,甚至還敢預測時間。評論指出,在過去20年中,許多人都曾嘗試過同樣的事情,結果無一例外,全都遭到慘敗。但這次不同,這次的鐵嘴畢竟是世界第一鐵嘴的「末日博士」。羅比尼這次為什麼將他一世英名押在了中國大陸身上?
經濟邏輯其實並不複雜。羅比尼最近先後兩次訪問中國大陸,他看到了嚴重的過度投資及產能過剩的現象。面對2008年9月世紀金融海嘯的衝擊,大陸當局以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兩年合計約人民幣18兆元的新增貸款)及極為擴張的財政政策(兩年合計人民幣4兆元的財政支出),通過公部門爆發性的固定資產投資(將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從原就偏高的42%拉高到近50%)因應。這劑猛藥雖然使中國大陸避免了金融海嘯後一般國家所遭遇到的嚴重經濟衰退,但也造成了當前在中國大陸觸目可見的投資與建設的氾濫現象:亮麗光鮮的機場及高鐵列車中旅客寥寥,通往偏僻地區的高速公路空蕩蕩,各地政府高大的辦公大樓數以千計,一座座空無一人的新城區,以及汽車、鋼鐵、水泥、鋁等產業的巨大過剩產能,還有無法精確統計但肯定偏高的空屋率等。歷史經驗證明,這樣的過度投資與過剩產能,很難不以一場金融危機及長期的低成長或衰退作為結束,中國大陸也不會例外。
為什麼是2013──以後?這就要見識到羅比尼這個「老外」的厲害之處了。換屆!中國大陸領導層在2012至2013年之間換屆;換屆之前,中國大陸的政策部門總會繼續在罔顧未來巨大成本下維持一個高成長率。這個政治經濟學,羅比尼懂得。
作為一個出色的經濟學家,羅比尼的分析與預測相當靠譜,近乎無懈可擊,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學畢竟比較特殊複雜;以下幾個方面,也許是羅比尼沒有看到的,但很關鍵:
一、一般情況下,產能過剩與過度投資到了這個地步,一定會因為銀行金融資產惡化(呆帳增加)而引發金融危機,但在中國大陸,卻未必。因為政府總是可以將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剝離,然後再編列預算成立不良資產處理公司,購買這些不良資產並加以處理。簡單說,就是由全體老百姓埋單。
二、過去20年,為什麼幾乎每次看衰中國經濟的專家都摃龜?那是因為他們每次看到的過剩供給產能,總是很快地被快速增長的需求追趕上來,消化吸收。
大陸巨大的人口規模及其所擁有的巨大需求潛能,經常超過經濟學家的理論理解及經驗認知。過去都如此,從今年開局的「十二五規劃」,重點放在民生產業,其所能釋放的需求潛能之大,恐怕更要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三、還有一點,可稱之為「品質的弔詭」。大陸各種建設與工程品質普遍有低劣現象,所以一般國家可以用上50年或更長久的基礎設施,在大陸10年或20年內就不得不推倒重建。這或許是一種另類的「凱因斯政策」,但卻是事實。
大陸經濟會不會硬著陸,儘管存在著不同角度的分析判斷,但羅比尼之言,仍有其理論參考價值,大陸當局幸勿以河漢之言視之。
 阿楨
阿楨
(楨:以下全為反中的霉體邪者磚家叫獸之偏見!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共研究方法論》)
習近平上台後 恐終結技術官僚 2011-03-27 旺報
中共「十八大」將在明年10月召開,宣告新一代領導人將正式接班。身為中共太子黨的一員,現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接棒也為過去20多年來的技術官僚統治時代,暫時劃下休止符。
政治大學昨日舉行「中共十八大政治繼承」研討會,對於十八大的意義和趨勢,與會來賓多聚焦在中共新統治階層如何處理中國未來的深層矛盾上。
技術官僚難克服現狀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由冀認為,「習近平的上台,很可能是過去20多年來技術官僚統治時代的終結,而是以政治家或政客方式來治國」。
他指出,改革開放後將近30年的積累,中國的深層次矛盾已到達一般技術官僚無法克服的程度,必須交由政治手段來解決,特別處理利益集團的問題。
不像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上台前已在中共黨內形成高度共識,由冀說,習近平的上台具有高度爭議性。因此,未來習的統治必須有一強力集團作為支持,而軍隊就是他權力的主要基礎來源。
得透過軍隊推動政治
他認為,若習近平是政治家或政客,勢必透過軍隊勢力來推動政治目標。過去10多年來,黨內平緩有序的軍政關係的制度化,可能會因他為了要推動政治目標而有所改變。是好是壞,不得而知。
對於十八大後中共的前景,香港科技大學終身教授丁學良則提出共黨永久執政、具有中共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和政府操控的市場經濟等鐵三角作為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模式會在十八大後有明顯調整,但社會控制系統轉變的可能性則比經濟調整還低。
他說,胡錦濤提出「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系統」,代表並非放棄社會控制系統手段,而是增加補償,「用人民幣解決內部矛盾」。
但丁學良認為,應該要把補償的制度化,法律系統的相對獨立要增強一點,儘管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控制」。
至於政治改革是否會有驚天動地的大轉變,丁學良則抱持悲觀態度說,「政治重大意義的改變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只能期待「兩會」功能的提升和黨內民主化推進。
版主回應
中共黨員結構 已現分化矛盾 2011-03-27 旺報
中國改革開放33年,大陸年輕人參與中共的入黨動機,已不再唯理念是從,反而更側重在有助於個人的職業發展和提高社會位等目標上。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唐文方指出,知識水平高的實用型黨員,擁有較高的政治不服從度,已在中共黨內形成傳統型和實用型的分化矛盾局面。
在政大舉辦的「中共十八大的政治繼承」研討會中,唐文方指出,中共本質上是一個菁英政黨,從教育程度、收入和城市化等指標分析,中共黨員都比一般民眾明顯來得更高。
對於黨員和非黨員的政治態度,唐文方從對政府滿意度、民族主義、社會容忍度、民主支持度、不服從程度、政治參與、政治效能感等方面調查發現,黨員對民族主義、政權的服從度和滿意度都明顯偏高,這對中國民主化似乎沒有促進力量。
但另方面,黨員卻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效能感上,又比一般民眾更強勢,說明他們比一般民眾更能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這種前後選項的結果,看起來頗為矛盾。
唐文方解釋,這與中共推行黨內民主,促成黨員政治參與和政治效能感增強有關。
他也發現,在中共內部,比起傳統型中共黨員,越年輕、教育程度越高的黨員,越偏向「實用型」的入黨動機。
唐文方說,這些「實用型黨員」正在擺脫意識型態束縛,在政治上也較為獨立,對權威不會輕易服從。他們同時也把入黨做為自我實現的工具,這種入黨為「公」和入黨為「私」的分化,在中共內部越來越明顯。
他警告,這種黨內兩代群體的分化和矛盾,若處理不好,恐將削弱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推黨內民主? 學者:為取代人民民主2011-03-27 旺報
在「中共十八大政治繼承」研討會中,中共黨員對中國民主化和黨內民主的影響,引起各方熱議。中研院政治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徐斯儉直指,中共近年來推行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是一個悖論」。中共希望透過黨內民主,來取代人民民主給他們的壓力。
「黨員的政治參與度高和政治效能感高,不見得是支持民主」,徐斯儉說,黨內民主本質上是不同派系力量的平衡作用,而非讓民眾廣泛參與。他認為,黨內民主並非一般民主,「黨內民主是一個形容詞而非名詞」。黨員自我感覺良好,是因他們社經地位和一般老百姓差距拉大。
徐斯儉表示,由於黨員比一般民眾享有更多的特權地位,這勢必面臨一個困境:黨員越要維持這個特殊地位,越要支持政權,黨員就越不想改變。
至於黨內民主能否成功,徐斯儉並不抱持太正面的態度。他認為,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其實是一個悖論」。
但他也說,從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的效應來看,會讓一個政權倒台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問題,這才是關鍵的,「中共政權尚未發生大變化前,是非常穩定。但若出現大變化,同樣也非常脆弱」。
 阿楨
阿楨
挑戰美霸主? 大陸軍力評估兩極2011-01-07 中時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將於九日訪問中國,為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行暖身的同時,並試圖修復因對台軍售一度茍延殘喘的軍事交流。然而,外界更關注的,其實是美國如何面對,中國頻繁釋出的軍事重大突破,包括可迫使美國海軍退回第二島鏈的中程反艦彈道導彈(東風21D)、以及首架自行研發的隱形戰機。
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副助卿薛瑞福認為,中方或意在顯示有能力克服任何軍事技術發展困難。對此,美國國防部官員目前為止仍認為中國還需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相關測試與海空部署,甚而運用戰場與之匹敵。
但《紐約時報》昨日專文認為,透過這些進展,中國至少非常清楚的傳達:中國在快速發展抵禦或威懾能力,以鎮守自己(或視為自己)的領域,包括美國承諾協防的台灣在內。大陸官方也不諱言擔心,美國要聯合亞洲鄰國,遏抑中國的發展與影響力。
對中共軍事發展成果存疑也大有人在,或認為發布成果過於片面,或認個別研發並不具實際戰鬥力,就連北京大學學者朱鋒也認為,大量如高額軍購等相關軍事報導的背後,更多是無謂的浪費與自我膨脹,所謂「軍事發展」其實意在維護其他計畫的影響力。
真相究竟如何?大家只能用猜的。西方多數媒體認為,中國的軍事高層,鮮少透露國家軍事的長期發展策略,只是埋頭不斷發展軍力。
蓋茨的前任幕僚鄧馬克便說,中國的軍力發展,明顯針對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部署,但動機非常模糊,大家很難瞭解這些高度現代化的軍力會用於何圖。
美軍情報部門承認低估中國殲-20研制速度(楨:J-10/J-11/高鐵/超級電腦……等即已如此!老依西驗,不準!另參本館:《中共研究方法論》兩岸高鐵 超級電腦 PLA四代機之爭)
東方網2011年1月7日消息:美國華盛頓時報6日報道稱,美國海軍情報負責人5日向媒體承認,盡管美國對中國J-20隱形戰機的出現並不驚訝,但其進展確實超過了此前的預期。這是美軍情報界繼低估中國元級潛艇後再次對中國重大武器進展出現研判失誤。美國軍事專家費舍爾稱,中國J-20戰機的出現將對美國空軍戰略構成全面挑戰。
……………
更多殲-20新聞
美國媒體擔心殲20會對美航母構成威脅(圖)
英媒稱中國殲20及反艦導彈將打破東亞軍事平衡
美稱中國瓦良格搭載艦載機性能將超過美軍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1-07/0925627275.html
版主回應
亞洲新軍備競賽 2011-03-27工商時報(另參本館:《海權論》 中國軍力 中國軍工 中國軍費 中國軍售
中國軍事力量迅速壯大,美國介入地區性衝突的能力及意願降低,使亞太國家認為必須自求多福,競相擴張軍備。
亞太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美蘇冷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同步建置先進武器競賽,中印、印巴、中越、兩韓之間長期來存在疆界上的糾紛,正升高這個地區爆發戰端的可能性。
澳洲國防事務智庫科克達基金會(Kokoda)發表研究報告,將這場軍備競爭賽歸因於中國軍力迅速壯大。美國國防部的新「國家軍事戰略」報告中,也表示「關切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程度及戰略意圖,及中國在太空、虛擬空間、黃海、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的展現自信。」
澳洲智庫及美國國防部的報告,都特別關切:軍事電腦系統遭中國從虛擬空間發動攻擊的脆弱性。
中國當局則一再強調,其軍事現代化並沒有針對任何外國,其軍事花費也遠低於美國。
華爾街日報援引官方資料指出,中國2010年總國防支出是780億美元,2001年時僅170億美元。西方國防官員認為這些金額並不包含進口武器的支出。美國國防部估計,中國2009年的軍事總支出為1,500億美元。
中國第1艘航母 將服役
中國第1艘航母(柴油動力)預期今年或明年服役,最新殲-20戰機的原型機也在1月首度試飛。
日本在2010年12月全面檢討國防方針,列出新武器採購清單,包括5艘潛艦、3艘驅逐艦、12架噴射戰機、10架巡邏機、39架直升機等,並要求部署更多美國愛國者飛彈。估計在2011年到2015年,將投注多達2,840億美元於國防自衛隊現代化上。
南韓在2006年訂出為期15年的軍事現代化方案,計劃花費約5,500億美元,其中約三分之一用於軍購。據悉南韓去年遭北韓砲擊後,已修改這項方案,將加碼購買潛艦、驅逐艦、F-15及甚至F-35戰機等傳統武器。
越南也有意購買潛艦,除大舉擴建軍力外,還開放金蘭灣深水港,吸引他國艦艇進入,成為越南的軍事屏障。
新加坡現已躍居全球前10大軍火進口國之一,正計畫購買2艘潛艦。
澳洲擴軍 二戰後最大規模
澳洲計劃未來20年花費多達2,790億美元,購買新的潛艦、驅逐艦及戰機。這將是澳洲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擴展軍備行動。
印度迄今年3月底止年度的國防支出約320億美元,等於過去10年來成長151%,預期未來幾年每年將成長逾8%。2009年向波音購買8架海上偵查機及反潛機,最近又通過加買4架。印度擬議中的126架戰機採購案,總金額高達約105億美元,堪稱該國歷來最大筆的國防訂單,引起國際各大軍機製造商競相逐鹿。
購買潛艦蔚為亞太國家這波軍備競賽中的風潮。相較於航母或驅逐艦,潛艦較為便宜,能發揮很大威嚇作用,更是反制其他潛艦的最佳武器。
據估計,中國現約有62艘潛艦,未來幾年將再增加15艘;印度、南韓及越南在2020年前將共買6艘潛艦;澳洲未來20年計劃增加12艘;新加城、印尼及馬來西亞將各增加2艘。
軍武市場研究機構AMI國際公司估計,未來20年,亞太國家加起來將購買多達111艘潛艦,是自冷戰初期以來最大規模的潛艦建軍行動。
 阿楨
阿楨
中國崩潰、美國分裂?專家預言大錯 ‧朝鮮日報中文網 2010/12/23
全球知名投資戰略大師麥嘉華(Marc Faber)今年5月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曾預測說:「2010年中國股市將暴跌,經濟走向崩潰(crash)。」在美國活動的瑞士投資大師麥嘉華因成功預測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而聞名於世。但中國在2010年實現的高度增長徹底粉碎了他的預言。
「中國經濟恐崩潰」
錯誤預測中國經濟的不僅僅是麥嘉華一個人。《外交政策》報導說:「過去30年預測中國經濟將崩潰的人沒有一個人猜對。」
「希臘和愛爾蘭不需要外部資金」
今年2月,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ios Papandreou)面對國家破產危機依然沈著冷靜地表示:「經濟陷入了困境,但不需要外部資金的支援,因為首次碰到這種情況,感到有些陌生。」但兩個月後,帕潘德里歐親自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盟(EU)請求金融救濟。愛爾蘭總理布賴恩‧考恩(Brian Cowen)也在11月15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愛爾蘭經濟能夠自救,不需要金融救濟。」但僅過一周他就向歐盟請求幫助。
「查維斯被驅逐出境,卡斯楚逝世」
美國時事雜誌《新聞週刊》在去年年底發表的《2010年世界展望》中預言:「委內瑞拉軍事勢力將發動政變,驅逐支持率較低的查維斯(Hugo Chavez)總統,恢復秩序。」查維斯稱《新聞週刊》是「充斥著帝國主義憎惡的媒體」,並在9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獲勝。《新聞週刊》還預測,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斯楚因健康惡化,將在今年去世。但《外交政策》報導說,在今年剩下的幾天裡,卡斯楚病逝的可能性不大。
「美國將分裂成6塊?」
去年3月,在俄羅斯外交部下屬外交學院供職的伊戈爾‧帕納林(Igor N. Panarin)預言:「由於未能成功克服金融危機,美國在移民者問題和道德墮落等諸多問題的作用下,將在2010年7月左右分裂成6個小國。」但如今到了12月,美國依然是世界超強大國。
此外,錯誤預言還有,駐阿富汗美軍司令麥克裡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在今年2月說的「塔利班佔領的馬爾紮被攻陷僅僅是時間問題,阿富汗文民政府已做好了接管準備」、美國總統歐巴馬說的「將在今年年內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美國副總統拜登說的「美國經濟將從今年夏天開始復甦」等。
版主回應
旺報社評-西方需要全面地認識中國 2010-12-25(另參本館:中國崛起 G2 《強國之鑑》
去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對中國大陸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歐巴馬就任總統後的首次中國大陸行,也是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第三度雙邊會晤。
當月17日,中美發表聯合聲明,聲明中指出「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而「美方重申,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中方則表示,「歡迎美國作為一個亞太國家為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努力」。雙方重申,「致力於建設二十一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並將採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
歐巴馬的中國行讓中美共生共存共榮的蜜月氛圍,成了國際上熱門的話題,「G2」和「中美國」這個前兩年就已經出現的新詞,一時之間甚囂塵上,許多觀察家也解讀出此份聯合聲明中透露的不尋常訊息。
2009年,的確是中國崛起,積極而順利展開大國外交的一年,連超強美國的元首都考慮中國因素而推遲對台軍售、拒見達賴喇嘛。但正在中國和平崛起形勢一片樂觀的時候,2009年終、2010年年初,掌握國際脈動的人們就敏感地發現,局勢正悄悄發生變化。
創造「中美國」一詞的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尼爾.弗格森在2009年12月發表《中美國的終結》一文,指出「經過2007年至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已開始離婚之旅。」
2010年1月中,谷歌宣布退出中國內地,當時就有國際觀察家指出這件事預示著「2010年中美關係會充滿坎坷」,「中美蜜月期可能結束」。2010年事態的發展,證實了這樣的預言。
這一年,從谷歌、天安艦事件、南海問題、人民幣匯率、中日釣魚台爭端,再到北韓核武與兩韓軍事對峙,一連串的事件與爭議,讓中國彷彿真的陷入某些人渲染的「C型包圍圈」中,東北亞一時之間看似戰雲密布,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擺的那張空椅子,不但加劇了中西方的意識型態對立,也讓中國大陸內部「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的拮抗更加升溫。
又到了歲末年終,在此時,許多國際觀察家正在進行一年的總結。英國《經濟學人》文章的標題頗為醒目:〈崛起中國之威脅〉(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最近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國的關鍵詞,往往採用「自信」(assertiveness)、「進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脅」(threat)等負面語彙。《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則在文章中,把「皺眉外交」(frown diplomacy)列為2010年中國「七大印記」之一,他認為「在這一年,中國區域性的微笑外交變成了皺眉外交」。
短短一兩年內,在國際主流論述中,中國的形象從「和美國一同經營地球村」、和西方世界「利益密切相關」的大國,迅速變成了「拒絕承擔國際責任」的負面角色。
到底,那個面孔才是真正的中國呢?或許,西方世界首先要做的,不是輕易地在兩個結論中擇一,而是應該全面、準確的認識中國。
其實,西方世界讀不懂、測不準中國,已是長久以來的大問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才指出:「過去30年預測中國經濟將崩潰的人沒有一個人猜對」,而最新的例子則是全球知名投資戰略大師麥嘉華在今年5月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所預測的:「2010年中國股市將暴跌,經濟走向崩潰」。
經濟方面如此,政治社會上亦然。觀察中國政治動向的人們應該要清楚:大陸當局最大的特點不在於堅持意識型態教條,而在於徹底的「實用(實利)主義」。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與西方世界的交往,甚至是在處理內部的政治社會矛盾上,所秉持的都是這樣的思維。從這點出發,我們方能理解大陸當局在諸多議題上的擺蕩、矛盾與權變。
前述英國《經濟學人》文章中,正確的指出:「將中國變成敵人的最佳方法就是將中國看做敵人」。當西方主流輿論「將中國看做敵人」,很可能只起著「為淵驅魚」的效果,讓中國大陸的鷹派更為抬頭,獲得更多的支持者。
 阿楨
阿楨
俄媒體稱錯估中國是西方近20年重大戰略失誤2010-04-01 新華網
俄羅斯《專家》周刊3月29日一期文章 原題:全速前進
沒有正確地評估中國的潛力和野心,這恐怕是西方近20年來所犯的重大戰略失誤。
多年來,西方重要戰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國很重要嗎?”——這是1999年美國著名雜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其作者是被公認爲“中國通”的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專家傑拉爾德?西格爾。因此,他對“中國仍將是普通大國”的預測讓華盛頓很受用。然而,中國在應對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了超乎想像的堅決和深思熟慮。
值得一提的是,西格爾在1994年發表在《外交》雜志上的《中國正在轉型》一文中寫道:“如果能給香港和中國南部的經濟造成損失,從而迫使中國改變有關軍火貿易和人權的政策,那就這麽幹吧。”許多專家將這篇文章視爲西方投機客在亞洲危機期間攻擊香港的理論基礎。但最終,中國戰勝了包括喬治?索羅斯在內的所有投機客,西方期待的“政策變化”沒有實現。中國沒有淪爲“不團結的王國”,相反,她在危機後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
美國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國仍然不太強,她永遠不會成爲世界大國。但10年過去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中國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GDP從1999年的4.8萬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8.8萬億美元。中國以最小的損失挺過了2007至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而且並不打算停下發展的腳步。
據美國估計,她能在戰爭中打贏中國的最後期限是2017年。況且,如今美國根本不想與中國交戰。同時,她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國。
中國在10至20年後會成爲全球領導者嗎?她到底有多強大?她的弱點又在哪兒呢?
盡管經濟實力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國目前仍是一個相當貧窮的國家。2009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GDP爲6500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127位。中國的人均GDP不到墨西哥的一半,更不及美國的七分之一。這麽低的人均産值卻伴隨著嚴重的分配不均。
此外,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總之,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依然不高。這樣的社會結構對人口資本的發展産生諸多限制,從而妨礙了中國向獨立的創新經濟增長模式轉型。
版主回應
目前中國依然是一個技術欠發達的國家。在諸如汽車制造等基礎行業上,中國可以勉強進入世界領先行列。但她與德國的水平還相差甚遠。即使是韓國的水平也不是一年就能趕上的。在全球20強企業中只有兩家是中國公司,而美國有12家。中國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天河一號”是在西方技術的基礎上制造出來的。
中國的某種經濟缺陷和發展不均衡要求北京走強硬的政治路線。否則,國內積累的諸多矛盾將會爆發。
由于存在這些因素,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將是一個極其艱巨、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應該對中國精英的智慧和責任心抱有一定信心。更何況世界其它地方的問題也不少,美國還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其現有地位。
不論是歐盟還是美國,西方文明地區的沒落將使中國更有機會在近30年內成爲無可爭議的世界領袖。但對這一點妄加猜測是沒有意義的,眼下中國還需要好好努力。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4-01/0757588932.html
 阿楨
阿楨
中國軍力突飛猛進 美情報失算2009-10-23 中時 劉屏
新上任的太平洋美軍司令威勒上將表示,中共軍力發展之速,史無前例,令美國的情報部門幾乎全盤失算,所以美國應該擴大與中國交往,以增進瞭解。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也指出,美國應竭盡所能擴大與中共的軍事關係,以避免誤判情勢。五角大廈網站廿一日刊登美國軍事新聞社發的專題報導,標題是《蓋茨、威勒尋求擴大與中國交往》。
威勒上將 尋求擴大與中國交往
威勒是在十九日接任新職,當天就與蓋茨飛往南韓。威勒在南韓首都首爾指出,中共過去十年的軍力發展,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增長,美國大部分的情報機構都低估了。共軍已有若干「非對稱戰力」,也有若干阻絕能力,令周邊國家關切。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即將訪問華府,是雙邊軍事交流的重大項目。不過威勒希望有多一點較低階層的軍事交流,以逐步建立互信,消除因為中國軍事現代化而引發的疑慮。他說,不只美國感到不安,區域內其他美國的盟邦也多少感到不安,因此他的責任就是尋求與中國建立更佳關係,促進相互理解,對彼此的軍事發展、意圖多一分認識。
加強對話 盼中貢獻建設性力量
中美兩國今春發生船艦對峙事件,美國認為是在公海合法作業,中方則認為美船是在中國的二百浬專屬經濟海域非法作業。威勒說,兩國對於海事法有不同詮釋,如能加強對話,當有助於釐清歧見。不過威勒也強調美國不會退縮,因為美國在相關海域作業已一百五十年,一定要維護軍艦商船的國際水域行駛權。
威勒表示,兩國可藉對話尋求共同利益,例如中國已參與的人道救援、反制海盜、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美國不把中國視為敵人,而是希望與中國推展建設性的關係,也希望中國貢獻建設性的力量。
增進瞭解 防誤判鼓勵國際維安
蓋茨則在另一個場合指出,擴大與中國交往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尤其是藉由對話,美國可進一步瞭解中共的軍事現代化,防範誤判,這也就是美國一再主張的「透明化」。
因此蓋茨強調要竭盡所能擴大中美軍事關係,不但交換意見,也可合作面對各種安全議題。他說,中國在北韓核武六方會談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有關預防區域動盪,中美有類似的利益,因此美國鼓勵中國擴大參與國際間維持安定的活動。
另參本館:《強國之鑑》 《當代中國》 《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中國崛起 G2
版主回應
崛起經濟 規模空前 課本失靈【聯合報╱林中斌 10.03.10(楨:林多前論亦然
07年二月倫敦經濟學人編輯Z先生來台請我用餐。我說:「1998年十月底貴刊封面故事說中國經濟將崩潰,而且廣徵博引專書。我現在仍在等待預言實現。」他答:「不好意思,那是我寫的。」
我解釋:「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經歷如此大規模的經濟快速崛起。所以教科書恐怕不再全然適用。」四月,他寄來新出的雜誌,金龍封面,附紙條說「我們已修正看法了。」
中國經濟復甦
08年八月底,世界金融風暴衝擊,大陸經濟已連五季度下滑。前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大陸經濟奧運泡沫破…未來十二個月出口可能會繼續下降。」相當悲觀!我說:「大陸經濟會下滑,但不致太糟。」(聯合新聞網08/8/25)
之後,大陸經濟再連續下滑三季度。09年五月,大陸出口開始回升。第二季度GDP成長百分之7.9,由第一季度百分之6.2谷底彈起。第三及第四季度,持續回升,分別為百分之9.1、百分之10.7。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首先從金融風暴脫困。
質疑假造論點
質疑北京假造數據的論點開始出現。簡述如下:一、汽車狂賣,中國汽車消費量成為世界第一,而汽油消耗量卻持平,數據矛盾。二、失業人口兩千萬,失業率卻在百分之五以下。三、民間消費增加百分之16,消費者物價卻下跌百分之0.7。所以,09年全年成長百分之8.7,還領先世界大國,不可信。
這些論點應有所本。但是,即使把百分之8.7成長打八折,仍有百分之七,遙遙領先美國的百分之0.3,日本的百分之0.6,歐盟的百分之0.5。比印度的百分之6.7,毫不遜色。
今年三月一日國際先鋒論壇報:「最近中國勞工短缺,工廠工資已上升百分之廿。廣東的短期仲介公司,已把工資由春節前的一小時人民幣七元五調至八元,而兩年前工資是五元五。金融風暴之前的勞工短缺又再浮現。因為,中國政府沒有及時公布就業數據,所以工資是最好的就業狀況指標。」這項非官方、非大陸的報導應為中國經濟復甦作了很難推翻的肯定。
中國經濟規模巨大,可以吸收衝擊,孕育潛能。金融風暴期間,沿海企業明顯困難,但內陸發展不大受影響。經濟改革在沿海遭遇到問題,可以推給內陸。等到內陸問題要爆發時,沿海已平穩了。
第二大經濟體
09年十月,中國外匯存底,本來已居世界之冠,再創新高達美元2.27兆。兩個月之後,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09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汽車、發電風車、太陽能面板製造國,並擁有最快高速鐵路。
國家經濟力量也來自人們對它的認知。卅年來人才外流最近起了變化。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教授施一公,不久前剛得到美元一千萬元的研究獎金,今年一月突然宣布辭職,回國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饒毅07年已回國帶領北大生命科學研究。
今年一月,曾預測安隆公司倒閉的投資專家查諾斯說中國經濟將崩潰。他應不知道倫敦經濟學人十多年來的學習歷程,因為他也承認從09年夏天才開始研究中國問題。之後,名政論家佛里曼回應寫道,他不曉得全世界不找中國投資要找誰,至少它的外匯存底是最大的。
台灣經濟發展很難自外於大陸,但在它政治改革之前,我政治把關、軍事嚇阻仍不可缺。 (作者獲UCLA企管碩士後曾任美國Manville公司兼任財務分析師,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傻瓜才信:經濟學人唱衰中共 2023-08-29 銘傳大學副教授楊穎超
英國《經濟學人》近日發表「中國經濟何以救不起來」,指出,日益獨裁的中共政府正做出種種錯誤決定。這不是經濟學人首次唱衰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他們認為中共是「脆弱的強權」,甚至只是GDP成長率沒達到一定數字,社會就會開始動亂。
回應
西方主導世界知識領域已超過200年,世人失去審辨真相的能力久矣。
可以說西方不了解中共,斬釘截鐵的結論出意外不意外.
以美為首的所謂民主世界都是靠抹黑、造謠來打擊對手
西方惡霸從中共改革開放一直唱衰到現在, 現在更糾集各方惡霸一起圍毆中國,台灣更是幸災樂禍, 真是無知到極點啦!
美歐為什麼不想學中文了?--經濟學人
2016年國際調查,當時選學中文的主要原因是讓就業的路更寬廣。過去十年,比起國際關係與安全學生,學中文的商學院學生減少了。西方國家的學生對於與中國生意往來的想法或許也走味了,新疆與香港人權問題經廣泛報導,富國對中國的負面觀點攀上最高點或逼近高點。同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也愈來愈緊張。不過,依然有許多西方國家政府表達,他們其實還是需要更多精通中文的人才。中央情報局(CIA)正尋求把中文人才增加一倍。
但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中文學習趨勢似乎是上揚的,2018年有超過8萬1000名非洲學生前往中國留學。中國的孔子學院也有幫助,既教導中文,也教導其他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