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遇見民俗》
林瑤棋的《醫學遇見民俗》(大康,2004)旣不是介紹民俗療法,也不是醫療人類學,倒像是用西醫在檢視台語的民俗。
只不過它的併音怪怪的,你比如「瘦田肴吸水,瘦狗公上枵鬼」(san2 chan5 gau5 su8 tsui2 ,san2 kau2 kan sion7 yao Qui2)意指:「貧瘠的田地須要較多的水灌溉,瘦公狗(喻瘦男人)性能力比較強…是否真的如此,依醫學上的統計報告,人的性慾確實隨著體重增加而減退…女的豐胸男的高瘦是現在青年男女的最愛…所以台灣人選『狗公腰』的女婿與醫學研究報告吻合…(雖然)影响男人性功能除了體型之外,還有好因素…除非有特殊情況,這句台灣俗語確實是一句名言。」(p.43)
那是大陸的漢語併音,阿拉伯數字代表聲調的平仄,比起ㄅㄆㄇㄈ、羅馬或通用併音,不但能通行全球也能通用各方言,只有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旣科學又易學。
照你這麼說,漢語併音不只可用來併中國各民族的上百種語言,也應用來併全世界各民族的所有語言,是真正的世界語,應當聯合國的唯一官方語言!
哎啊!別爭語言政治學的難題,回到書評,相關俗語還有「怨妒別人大尻川肴生囝」意思是「嫉妒別人的媳屁股大,能多生男孩子。」作者認為「從醫學立場來看,那是無稽之談…儘管大尻川不是多產或生男的因素,但屁股大,產道寬廣,生產較容易。」(p.144)
這還差不多,不過作者對「尻川幾枝毛知知咧」的過度引申就尚待考察。
不會啊!他解釋的通:「肛門長幾根毛,雖然穿著褲子看不到,可是黃種人都長得稀疏人盡皆知,吹牛也沒用。」(p.236)
可是他以下說法就有點種族問題:「上帝把我們黄種人的密疏度設計得很少,甚至只是『會陰毛』的延續而已,可以緩衝肛門周圍皮膚的磨擦傷,又可以用衛生紙把大便擦乾淨,不像中東人的肛門毛,長得又長又密,必須用水沖洗。」(p.237)
林醫生的生物學也有問題,他在解釋「台灣牛牽到北京嘛是牛」時竟然說:「人類的遺傳因子不單是指疾病,人的性格也不能例外,維京人的冒險犯難、台灣人的奴隸性、日本人的狡滑機警…等等都與此有密切關聯。」(p.189)
太扯了!別說不合生物演化論,連演化醫學也不是。
連文化類型學也不再如是說,林醫生是1936年生的老人,有些看法很LKK很奇怪,比如他說日本沙西米之父是鄭芝龍:
「傳說,有一次鄭芝龍親自出馬,帶領船隊到呂宋走私,返航途中遇到強烈颱風,在海上漂流了十幾天,連糧食也中斷,船員只好抓魚生吃,問大王要吃幾『麵』(閩南語片之意),問随便答『三、四麵』…也許都鄭當時餓,把七片生魚片全都吃光,當船抵達九州基地時,沙西米的吃法就傳遍全日本。」(p.121)
太好笑的台灣人精神勝利(日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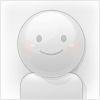 阿楨
阿楨
胎盤已被全世界人民吃出花樣,但這可能是有害的 2019-08-13 新浪科技
2017年,美國出現了一例可怕的病例報告:
寶寶的媽媽告訴醫生,在生完寶寶後,就委託了一家公司將自己的胎盤製成膠囊,然後堅持每天3次,每次2粒服用。
但寶寶的媽媽沒有想到,自己每天吃的胎盤膠囊就是將寶寶送進重症監護室的“罪魁禍首”。因為胎盤膠囊裡不僅帶有胎盤粉末還帶有B型鏈球菌GBS。
不過,幸好寶寶感染發現的還算及時,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關於這點,科學家早就指出,對人類而言,很少有證據表明吃胎盤對人類健康有益,胎盤不可以隨便吃。但現實卻正好相反,人們不但沒有放棄吃胎盤,反倒在這事上吃出了花樣。
根據16世紀中國醫學文本《本草綱目》上面的記載,胎盤是一種中藥,又名紫河車。
另一篇中國醫學文獻《大藥典》中,也曾記錄將胎盤與人乳混合有治療貧血、緩解疲憊等功效。可見,胎盤在古代的藥用地位。
除了中國有食用胎盤的習慣外,西方也有。18世紀,歐洲也出現了吃胎盤的零星記載,將胎盤乾燥食用可能能治療疾病。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研究中醫的美國助產士Raven Lang的推廣下,“吃胎盤”在西方世界也大肆流行開來。
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的文化裡,胎盤不是以一種中藥身份出現,而是被做成了各式各樣的飯菜,炒、燉、煮應有盡有。另外,每個地方對於吃胎盤這事能夠帶來的好處的解釋也不盡相同。
比如,在阿根廷,人們會將胎盤曬乾、磨碎然後保存起來,等孩子生病的時候拿出來給他們服用;在牙買加,人們會把胎盤膜放入給孩子喝的茶中,防止抽搐;在非洲東部的坦噶尼喀,人們會將胎盤晾乾,磨成粉末,做成粥,給家裡的老人和小孩喝,延續他們的生命;在越南的一些文化中,胎盤被視為一種賦予生命的力量,所以食用胎盤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能量和活力。甚至,在歐洲的某些國家,胎盤還被用來治療燒傷和罕見的遺傳病等等。
甚至在歐洲,人們還在化妝品中發現了“胎盤提取物”的商業用途。例如,面霜。
除了女人吃,男人也吃。
很多吃過胎盤的媽媽都表示,吃胎盤可以改善她們的產後健康。
其中一個說法是提高母乳量。
另一種說法是吃胎盤可以改善產後心情,增加活力。
還有一個最常見的解釋是可以緩解疼痛。
儘管吃胎盤的好處有很多軼事證據,但科學的研究結論是,食用胎盤對媽媽的健康有益的證據不足。
 圖博館
圖博館
通過對西醫訴訟檔案文本的解讀,可以看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醫醫訟的“盛產”,確實與當時西醫所大力建構的現代醫療模式以及對新式醫療器械的使用與中國的本土傳統存有很大張力有關。面對西醫基於西方醫學倫理而展開的對國人的規訓,在本土傳統的影響下,國人有意無意地採取了形式多樣的“反抗”,表達了自身對西醫的部分看法和態度。醫訟案中病人及其家屬的發聲,便集中體現了國人對西醫的一般感受與想法。當對療效不滿後,病家的疑慮、焦灼、想像、恐懼,諸多情感交錯雜陳,在訴訟狀中得到了強烈的爆發。當然,事實證明,這些“反抗”最後都在擁有強勢話語權的西醫面前以失敗告終。本土的醫療傳統,最終讓位於西醫的專業權威。在某種意義上說,西醫訟案中醫病之間的這些較量,也便成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角力的一個縮影。
 圖博館
圖博館
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如若醫師並無醫療過失,即便醫病雙方因故未在之前簽字,“亦不能遽責以手續不完,便令負何責任”。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世人不察,有以事發不得簽字引為口實而起無謂之糾紛者”。
由此一來,許多醫師被迫捲入醫訟之中,不但名譽受損,一些“忠厚畏事之醫者”不得不委曲求全,“賠償來纏者以若干之願”。 ……
關於醫師在症起倉促時的顧慮,瞿紹衡講述了兩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例。一則發生在1937年,一男子陪同產婦入住醫院待產。男子在簽署住院保單並交納住院費用後離去。不想產婦夜間“劇痛,至午夜忽起變化,勢非施行手術不可”。瞿紹衡急忙讓院役按照保單上的地址去找簽保單的男子,然而卻並無此人。當時產婦“時勢益危”,瞿紹衡百般無奈下只得在街上叫來一名安南巡捕,在後者同意做證人的前提下為產婦實施了手術。瞿紹衡所講述的另一則事例,發生在1937年12月的一個深夜。一“其狀非常狼狽”的婦人扣門求診,當其進門後“嗚嗚不能言,腹痛不能步,腰彎不能支”。待將婦人抬入產室,褪去衣褲時才發現嬰兒已“露頂矣”。這一突發事件,著實讓瞿紹衡頗費躊躇。在良心的驅使下,瞿紹衡最後還是為產婦進行了接生。儘管產婦順利產下嬰兒,但也著實令瞿紹衡異常擔心,“倘或不測,早步杭州某醫師之後塵矣”。
從瞿紹衡的文章中,我們約略可以看出,當時的國人對於醫療協議書的認識,的確不是很清晰。在醫師看來,本來用以表現穩妥慎重的行為,最後竟然會成為病人家屬舉控的理由,難免讓人心寒。不過,從病人家屬的角度來看,協議的簽訂,多是在遇有危險的診療之時。病人一旦發生變故或者身死,病人家屬心中本就無法釋然。因此,對協議書的再三強調,更會讓病人家屬產生醫師在推卸責任的看法。
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西醫的在華傳播與中國本土傳統產生了諸多疏離和緊張。而通過對這些疏離與緊張的深入探討,往往會讓人們別有收穫。如上所述,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醫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已然站穩腳跟。中醫界通過積極革新也取得不小進展,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的名醫也開始樹立起了專業權威。西醫以及新中醫對現代醫療模式的強調,顯然讓依然抱持傳統醫療觀念的國人不易接受,進而給現實中的醫病關係帶來了深刻影響。就在醫病雙方圍繞現代醫療模式的磨合中,摩擦與齟齬也在所難免。特別是對於西醫來說,醫病之間的緊張關係尤為明顯。
 圖博館
圖博館
彼等深知蹉跎再四,挽救已遲,深恐庸醫殺人,論法應負全責,為諉卸其怠忽業務之罪,乘自訴人驚惶失措之際,迫簽生死各由天命字樣,以自掩其責。……庸醫徒知法螺,對案務完全怠忽,以至於死。且醫院純以科學治病,而乃責人簽立生死由天之據,尤屬荒謬絕倫。其毫無醫學常識,誤人性命,可為明證。
從沈文達的《刑事自訴狀》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醫療協議的簽訂,沈文達認為是“尤屬荒謬絕倫”的事,完全持否定態度。同樣,在葛成慧醫師所遭遇的另一起醫療訟案中,當病患家屬李石林對尚賢堂婦孺醫院的診療完全失去信心後,要求將妻子從醫院中遷回家中醫治。出於對醫院權益的考慮,婦孺醫院要求李石林必須先簽訂自願出院書,李石林認為此舉顯然是院方日後為了推卸責任,因此十分憤怒。
自訴人知病勢凶險,留院無益,決擬遷回家中醫治,求最後之一線希望,而該醫院乘機迫令在鉛字印就之自願出院書上簽名,為日後圖卸責任之計,可惡尤極。
再來看一下江明醫師訟案。在這起訟案之中,14歲的貧農之子餘年福患咽鼻部纖維瘤,“大如鵝卵”。在其父餘以海的陪同下,送往南昌醫院求治。江明醫師在為病患診視後,認為只有將瘤割除,否則終將身死。在徵得病家的同意後,按照南昌醫院的規則,病家需具結覓保。由於餘以海不識字,載有“倘有不測,各安天命,與貴院及各醫生毫無干涉”字樣的甘結,只得由余年福的母舅劉靜山簽署,病人餘年福在甘結上按了手押。
江明醫師的手術並不順利,餘年福在實施麻藥的過程中身死。簽訂甘結一事,成為醫病雙方爭論的焦點。醫院方認為病者在入院之初即已簽訂甘結,在醫師無醫療過失的情況下身死,自然與醫院和醫師沒有乾系。然而,即使醫院方面出具了當初入院時所簽押的甘結,但餘以海卻矢口否認有簽押甘結之事,並聲言江明醫師也從未向其說起過“割治危險之厲害” ,“他如說危險,當然不肯割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昌地方法院認為,儘管在入院時簽有甘結,但仍不能免除醫師治斃病人的責任,一審判決江明醫師有罪。
頗為有趣的是,儘管民國時期的國人對醫療協議書多持抵觸心理,但在有些情況下,如不簽訂醫療協議書往往也會被病家利用,並成為引發訴訟的理由。在《醫病簽字之檢討》一文中,西醫瞿紹衡便曾指出,只有醫師在實施危險性的診治(如手術)時,出於慎重才會採取簽訂協議書。目的是萬一發生不測時,“免病家之誤會,或聽信旁人之慫恿,而滋枝節”。
 圖博館
圖博館
第二天,張二毛被送到仁濟醫院求診,“口吐黃血水甚多,未及治療,即告死亡”。張洪源見兒子慘死,便將謝夏氏告上法庭。有意思的是,張洪源後來又將梅、俞二位醫師也一同告上了法庭。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與張洪源的對答,充分體現出了張洪源對於兒子之死的懷疑以及對兩位醫師的氣憤。
(檢察官)問:你兒子被燙死了,不是已經起訴了嗎? (張洪源)答:是的。 問:你怎麼又告誰了? 答:告醫生等打針後就不能開口說話了。 問:你現在是何意思? 答:我的兒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我要伸冤。 問:你認識字嗎? 答:我僅會寫我自己的名字。 問:關於謝夏氏部分已經起訴了,你還告他嗎? 答:我現在告兩個醫生。 問:你告醫生何事? 答:醫生打針後就不能開口,一句話也不說就死了。是俞醫生叫看護打的針。 問:你因何告俞醫生呢? 答:我見兒子死了在那裡哭,梅醫生說哭也沒用,你去告我好了,因此才告他。 問:你告醫生何罪? 答:針打多了。……
國人對器械的疑懼,還表現在如若病人不治後,病人家屬會結合病狀形成某種聯想或想像,並據以作為控訴醫師的理由。這在當時的訟案中亦為數不少。如在沈克非醫師訟案中,病人陳允之因患急性盲腸炎在南京中央醫院割治身死。關於死因,院方認為“酷似肺動脈栓塞”。江寧地方法院檢察處起訴主治醫師沈克非的理由有兩條,一為對死者施雙重麻醉而侵害心臟提出質疑;另一條理由則為,術後縫結腸部時,“未將血塊或脂肪揀淨,以致血塊由割口入血液,將血管栓塞”。
第二條理由的提出,頗為有趣。因為從醫理上講,這顯然不能成立。但病家卻以此舉控,明顯是以“栓塞”而“想像”出來的結果。由於對西醫的不了解,以至檢察官都確信不疑。另外,在俞松筠醫師訟案中,也有一條理由與此相類。那就是田鶴鳴之妻因產後便秘,俞松筠為其用皮帶灌腸。而此後,產婦腹瀉不止。於是,田鶴鳴認為,顯係“灌腸之皮帶,染有病菌灌入腸中所致”。
2.因醫療協議的模糊認識而產生的糾紛
醫療協議書的使用,是現代西醫的一個重要特徵。大量事例表明,近現代國人在醫療協議接受上,內心也是頗為複雜的。從這一時期的醫療訟案來看,但凡涉訟的病家,多數對醫療協議書的簽訂持有不同程度的抵觸心理。比如,在葛成慧、朱昌亞兩醫師訟案中,原告沈文達在《刑事自訴狀》中,對於醫病雙方的簽字是這樣認識的。
 圖博館
圖博館
為了較為清晰地考察現代醫療模式的建構為醫病糾紛的發生所帶來的影響,我從1930年代發生的醫訟案件中,擷取了幾則較為典型的訴訟案件進行分析論說,希望能夠具體地呈現出醫病之間的這種緊張與衝突。
1.因對醫療器械的恐懼而產生的糾紛
對冰囊的疑懼與排斥,在民國時期的一般民眾中確實形成了一個“準共識”。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訴訟案中,但凡醫師曾用過冰囊,一般均會被作為控訴理由。比如,俞松筠醫師訟案,便是如此。在這起訟案中,病家田鶴鳴之妻在上海中德產科醫院生育後,出現乳脹的症狀。於是,俞松筠乃用冰袋冰敷產婦乳房用以消脹。後來,產婦接連腹瀉,最終身死。於是,田鶴鳴不禁將冰袋的使用與腹瀉聯繫起來,“產婦最忌受寒,被告更不應令產婦於睡眠中用冰袋,且腹瀉隨冰袋而發生,足見冰袋可使產婦受寒,並減低其抵抗力而利痢菌之繁殖”。
除去冰囊之外,國人對注射器、手術刀具等也有很大的排斥心理。因此,當用注射器注射、用刀具切割身體而終使病人於不救時,部分病人家屬也會據此而作為興訟的理由。這在鄧青山醫師訟案中,便有著集中體現。彭武揚之妻胡爾欣因咽喉痛,前往九江牯嶺醫院求診。醫師鄧青山認為病人所患為白喉,乃以醫院尚存過期不久的血清為病者註射於手臂。然而,就在註射後不久,病人病情忽然大變,“兩手震動,氣喘,遍發紅點”。鄧醫師一見不妙,立即進行搶救,“持病者兩手上下搖動,以助呼吸”,复“將病人注射處,用刀劃開,用兩手擠出黑血兩點”,“見病者呼吸更微,乃向病者胸膛复打一針”。可惜,這些舉措都未能見效。病人最終身死。從病人注射血清後的反應來看,應屬於對血清的過敏不適應症狀。而鄧醫師的搶救方式,在諳熟西醫知識的人來說,可能也不會感到訝異。但在胡氏的家屬看來,顯然不能接受。於是,彭武揚以鄧青山圖利,“復加殘忍行為”而致病人於死為由,將鄧青山醫師控告於九江地方法院。
再來看一則案例。這一訟案發生在1948年12月2日。上海市民張洪源8歲的兒子張二毛中午放學回家,在路過華興路時,不幸被謝夏氏用熱水瓶燙傷背部,被北站警官孫菊林緊急送往西藏北路上海濟民醫院醫治。在濟民醫院,經梅姓醫師和俞姓醫師為張二毛檢查傷勢後,由俞醫生為傷者“注射一藥水針”。孰料,在打過針後,張二毛旋即“閉口不能言語,面目及口舌發白,全體抖動,閉目暈沉,不省人事,疼痛失去知覺”。
 圖博館
圖博館
再以手術為例,范守淵便曾指出,一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國內行醫的醫師們“時常會得碰到害怕開刀的病家”。
這一類病家,因為對於這“開刀”二字,有了先入之見的害怕心理,於是自己或家族一旦遇到有需用於開刀的毛病,他們總想盡種種方法來反對:對於年紀輕的小孩子,不消說,拿“年紀太輕吃勿消!”的理由來反對;歲數太大的老人家,又拿“年齡太大不相宜!”的理由來抵拒;不大不小的中年人,說不定,又會想出百般反對的理由,以達到不要開刀的目的。
對於病人害怕開刀這一現象,范守淵認為,這主要與開刀本身所具有的危險性,及其對身體造成的疼痛息息相關。
他們所以害怕開刀的原因,揣摩起來,不外於這麼二點:1.視“開刀”這項手術療法,是一種很危險,而非安全的辦法;2.以“開刀”為十分痛楚,而非王道的治療方法。……
西醫是“靈不靈當場出彩”的,他會在你大腿上刺一針,叫你如殺豬一般的叫起來;你腦袋覺得燙,他就給你兩個冰袋;你身子怕冷,他就替你生火;肚裡難過吃藥水,也許生個熱癤會挖掉一塊肉。說者謂這樣似乎太欠忠厚,然而“死去”“活來”倒也不失為“直截了當”。……
現代醫療模式的踐行與醫病糾紛的發生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已然可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醫病互動的大體特徵進行一初步的概括與總結。一方面,西醫與部分新式中醫基於新式的醫業倫理,試圖對國人重新進行規訓與形塑;另一方面,國人特別是在大都市中越來越關注自身身體的人們,由於受到傳統醫療文化的影響,依然對醫生抱持不信任的態度。特別是對於西醫,國人的信仰力尤為不足。如此一來,在醫病雙方之間,特別是西醫與國人之間,明顯地形成了不易調和的緊張與矛盾,從而也為醫病糾紛的產生帶來了重要影響。也便基於此,雷祥麟指出,正是由於醫病雙方在建構新型的醫病模式中的相互摸索和彼此衝突,“造成了三十年代盛產的醫訟”。應當說,這種識見是非常到位的。
 圖博館
圖博館
同樣,在1930年代初期,一位顯然頗為認可現代醫療模式的醫師,結合自身的日常診療經歷,對國人的醫療觀念進行過非常形像地記錄。個中頗體現著醫病雙方各自所秉持的一套迥然有異的醫學知識體系,在彼此遭遇之時所產生的內在張力。他寫道:
對於來就醫的病人,照例我是要先問他:“某先生,您是怎麼呢?”或是說:“您是哪裡不舒服呢?”我總也不問:“您得的甚麼病? ”但是許多的病人卻回答說:“大夫,我有胃病。”有的說:“我有肺病。”有的說:“我受了濕氣。”有的說:“我上焦有火啊。”有的說:“我這病是由氣上得的,我這人肝火太旺。”……前幾天有一位朋友來求我給他的母親看一看病,他說:“家母這病橫豎是由氣上得的。”病狀是發熱,腹痛,噁心,水洩,不思飲食,四肢酸痛。我診視以後就安慰病人幾句話說:“我想您這病就是平常的痢疾,不要緊的,要好好的調養。”病人卻呻吟著表示反對說:“我這不是痢疾。”我心裡說:“她看不起我麼?不信任我麼?”然而,她確是以為她自己比我這個醫生更明白她自己的病。
“得病亂投醫”雖是一句俗話,實際上這種現象,也真不少,就是知識階級,也常免不了。至於愚夫愚婦,對於處治病人,更根本不懂。談到衛生,他們更聞所未聞了。所以他們一遇有病人發生,必先求神問卜,試偏方,或到藥店藥房問病買藥。親戚說甲種的藥有效,就吃點甲種藥;鄰居說乙種藥好,就又吃乙種藥。像這樣處治病人,病哪能好呢?等到第三步才去求醫,但是求醫又不去請正當的醫家,專好去找那些近於神怪的江湖騙子,不但病沒有治好,反耽誤了治療的時間。金錢損失,還是另一個問題。等到覺悟了之後,再送入醫院,可是已經病入膏肓,大半已難醫治有效了。因為這種衛生常識缺乏而致死亡的,實不在少數;又因亂投醫的結果,受社會上江湖醫生的詐騙,也是常有所聞。尤其是熱鬧的都市,真是無奇不有。……
西醫的東傳,不僅帶來了迥異於中醫的新式醫療模式,而且在診斷與操作上也為國人帶來了許多新奇的醫療器械。新式器械的應用,在使國人大開眼界、感歎其奏效迅捷的同時,亦不免令國人多少抱持恐懼與拒斥之心。西醫動輒用刀切割身體或以針管將藥液注射的行為,畢竟與國人傳統的身體認知理念相左。 ……
 圖博館
圖博館
馬金生|西醫東傳與醫病糾紛的發生2016-10-24
“特別是對於西醫,國人的信仰力尤為不足。如此一來,在醫病雙方之間,特別是西醫與國人之間,明顯地形成了不易調和的緊張與矛盾,從而也為醫病糾紛的產生帶來了重要影響。”作者在文中擷取了較為典型的訴訟案件來論說西醫東傳和現代醫療模式的建構給醫病糾紛的發生帶來的影響。本文出自《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有刪節。馬金生,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傳統觀念與現代醫療模式的緊張
在傳統中醫文化影響之下,民國時期的國人特別是對身體越發關注的城市人群,無疑是積極推行現代醫療模式的西醫師所不易應對的。在傳統中醫文化的影響下,國人漸漸形成了一系列用以感知和表達自身狀態的概念和語言。諸如上火、體虛、受寒等疾病概念,時常被國人掛在嘴邊用來描述自身的不適感覺。一直到今天,這種影響仍在延續。病人的這些不可名狀的“身體感覺”,是很難用現代科學通過數據加以精確量化與清晰界定的。換句話說,受傳統醫學影響下的國人對於疾病和身體的認知,在相當程度上與現代西醫知識是鑿枘不通的。然而,正是這套與西方醫學彼此相異的身體觀念與醫療知識,卻在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當深受此種影響的病人與標榜科學的現代西醫師遭遇時,兩者之間的緊張也就在所難免。從病人方面來看,當自己的身體感覺與疾病認知遭到醫生的質疑或被視如敝屣的時候,那種與醫生的疏離和不信任感可能便會油然而生。同樣,當每天都要面對這些根本不識現代醫學為何物的病人時,民國時期西醫的那份不滿與無奈也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20年代末,曾經留洋日本、後回上海行醫的西醫余云岫,便曾對中國病人在診病過程中的“自以為是”頗多抱怨。
餘懸壺滬上,十年於茲矣。遇有善怒多倦不眠虛怯之病人,彼必先自述曰:我肝火也。若為之匡其謬誤曰:肝無火也。真肝之病,不如是也,此乃精神衰弱也。則漠然不應,雖為之詳細解說,以至舌敝唇焦,又切實疑信參半。若直應之曰:唯唯,此誠肝火也。則如土委地,歡喜欣受而去者,比比然也。如之何醫者不樂行此耶?是以今世新醫,亦有隻按脈處方者矣,以為對付不徹底之社會,如實而已足也。
胎盤已被全世界人民吃出花樣,但這可能是有害的 2019-08-13 新浪科技
2017年,美國出現了一例可怕的病例報告:
寶寶的媽媽告訴醫生,在生完寶寶後,就委託了一家公司將自己的胎盤製成膠囊,然後堅持每天3次,每次2粒服用。
但寶寶的媽媽沒有想到,自己每天吃的胎盤膠囊就是將寶寶送進重症監護室的“罪魁禍首”。因為胎盤膠囊裡不僅帶有胎盤粉末還帶有B型鏈球菌GBS。
不過,幸好寶寶感染發現的還算及時,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關於這點,科學家早就指出,對人類而言,很少有證據表明吃胎盤對人類健康有益,胎盤不可以隨便吃。但現實卻正好相反,人們不但沒有放棄吃胎盤,反倒在這事上吃出了花樣。
根據16世紀中國醫學文本《本草綱目》上面的記載,胎盤是一種中藥,又名紫河車。
另一篇中國醫學文獻《大藥典》中,也曾記錄將胎盤與人乳混合有治療貧血、緩解疲憊等功效。可見,胎盤在古代的藥用地位。
除了中國有食用胎盤的習慣外,西方也有。18世紀,歐洲也出現了吃胎盤的零星記載,將胎盤乾燥食用可能能治療疾病。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研究中醫的美國助產士Raven Lang的推廣下,“吃胎盤”在西方世界也大肆流行開來。
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的文化裡,胎盤不是以一種中藥身份出現,而是被做成了各式各樣的飯菜,炒、燉、煮應有盡有。另外,每個地方對於吃胎盤這事能夠帶來的好處的解釋也不盡相同。
比如,在阿根廷,人們會將胎盤曬乾、磨碎然後保存起來,等孩子生病的時候拿出來給他們服用;在牙買加,人們會把胎盤膜放入給孩子喝的茶中,防止抽搐;在非洲東部的坦噶尼喀,人們會將胎盤晾乾,磨成粉末,做成粥,給家裡的老人和小孩喝,延續他們的生命;在越南的一些文化中,胎盤被視為一種賦予生命的力量,所以食用胎盤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能量和活力。甚至,在歐洲的某些國家,胎盤還被用來治療燒傷和罕見的遺傳病等等。
甚至在歐洲,人們還在化妝品中發現了“胎盤提取物”的商業用途。例如,面霜。
除了女人吃,男人也吃。
很多吃過胎盤的媽媽都表示,吃胎盤可以改善她們的產後健康。
其中一個說法是提高母乳量。
另一種說法是吃胎盤可以改善產後心情,增加活力。
還有一個最常見的解釋是可以緩解疼痛。
儘管吃胎盤的好處有很多軼事證據,但科學的研究結論是,食用胎盤對媽媽的健康有益的證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