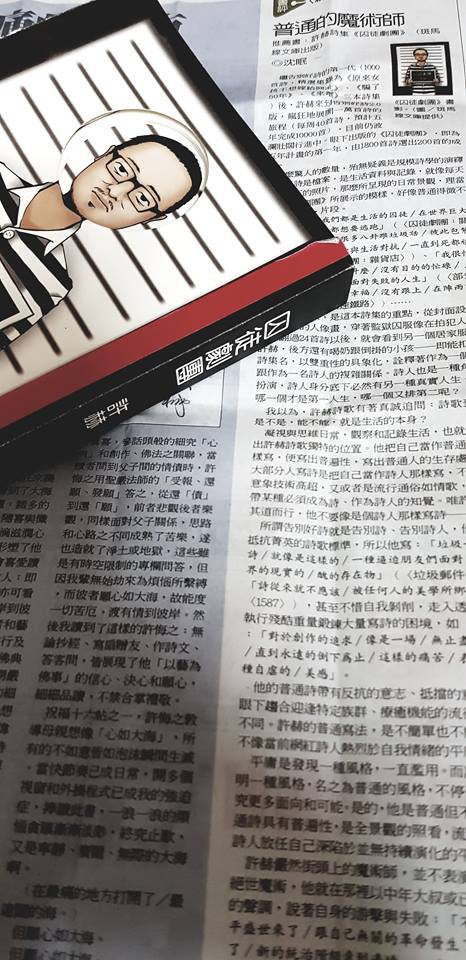〈普通的魔術師──閱讀許赫詩集《囚徒劇團》〉
沈眠/寫
繼告別好詩的第一代(1000首詩,精選集錄為《原來女孩不想嫁給阿北》、《騙了50年》、《來電》三本詩集)後,許赫來到告別好詩2.0版,瘋狂地展開一萬首詩的旅程(每週40首詩,預計五年完成10000首),目前仍波瀾壯闊行進中。眼下出版的《囚徒劇團》,即為五年計畫的第一年,由1800首詩選出200首的成品。
這麼驚人的數量,殆無疑義是規模詩學的演繹。如果詩是檔案,是生活資料與記錄,就像每天手機拍下的照片,那麼所呈現的日常景觀,理當是《囚徒劇團》所展示的模樣,好像普通得微不足道,即時,片段。
許赫寫:「我們都是生活的囚徒/在世界巨大的牢裡/每一天都想要逃跑」(〈囚徒劇團:關於〉)、「他們講很多八卦跟垃圾話/彼此包紮傷口/他們很強悍的與生活對抗/一直到死都頑強無比」(〈囚徒劇團:雜貨店〉)、「我很忙/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目的的忙碌//也許只是因為/無法面對失敗的人生」(〈部分09〉)、「但是你的幸福/沒有跟上/在陣雨中千瘡百孔」(〈高速鐵路〉)、……
囚禁與解放,是這本詩集的重點,從封面設計──許赫的人像畫,穿著監獄囚服像在拍犯人照,但翻過24首詩以後,就會看到另一個居家服的許赫,後方還有喝奶跟倒掛的小孩──即能扣合詩集名,以雙重性的具象化,詮釋著作為一個人跟作為一名詩人的複雜關係。詩人也是一種角色扮演,詩人身份底下必然有另一種真實人生。而哪一個才是第一人生,哪一個又排第二呢?
我以為,許赫詩歌有著真誠追問:詩歌到底是不是,能不能,就是生活的本身?
凝視與思維日常,觀察和記錄生活,也就形塑出許赫詩歌獨特的位置。他把自己當作普通人那樣寫,便寫出普遍性,寫出普通人的生存處境。大部分人寫詩是把自己當作詩人那樣寫,不管是意象技術高超,又或者是流行通俗如情歌,都夾帶某種必須成為詩、作為詩人的知覺。唯許赫反其道而行,他不要像是個詩人那樣寫詩──
所謂告別好詩就是告別詩、告別詩人,他想要抵抗菁英的詩歌標準,所以他寫:「垃圾一般的詩/就像是這樣的/一種逼迫朋友們面對/這世界的現實的/醜的存在物」(〈垃圾郵件〉)、「詩從來就不應該/被任何人的美學所綁架」(〈1587〉),甚至不惜自我剝削,走入透支肌肉執行殘酷重量鍛鍊大量寫詩的困境,如〈1510〉:「對於創作的追求/像是一場/無止盡的戰爭/直到永遠的倒下為止/這樣的痛苦/表達成一種自虐的/美感」。
他的普通詩帶有反抗的意志、抵擋的意圖,跟眼下趨合迎逢特定族群、療癒機能的流行詩大為不同。許赫的普通寫法,是不簡單也不簡化的,不像當前網紅詩人熱烈於自我情緒的平庸重複。
平庸是發現一種風格,一直濫用。而許赫是發明一種風格,名之為普通的風格,不停深化,探究更多面向和可能。是的,他是普通但不平庸。普通詩具有普遍性,是全景觀的照看,流行詩則是詩人放任自己深陷於並無持續演化的平庸狀態。
許赫儼然街頭上的魔術師,並不表演華麗劇場絕世魔術,他就在那裡以中年大叔或已瀕臨阿北的聲調,說著自身的游擊與失敗:「不知不覺太平盛世來了/跟自己無關的革命發生了/也結束了/新的統治階級來到邊境……這一切的失敗/只是證實了自己/是一個失敗的人而已」(〈跋──措手不及的太平盛世〉),節制清醒的憂傷,而那樣的真誠與美好。
本文發表於《聯合報:聯副•周末書房》2018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