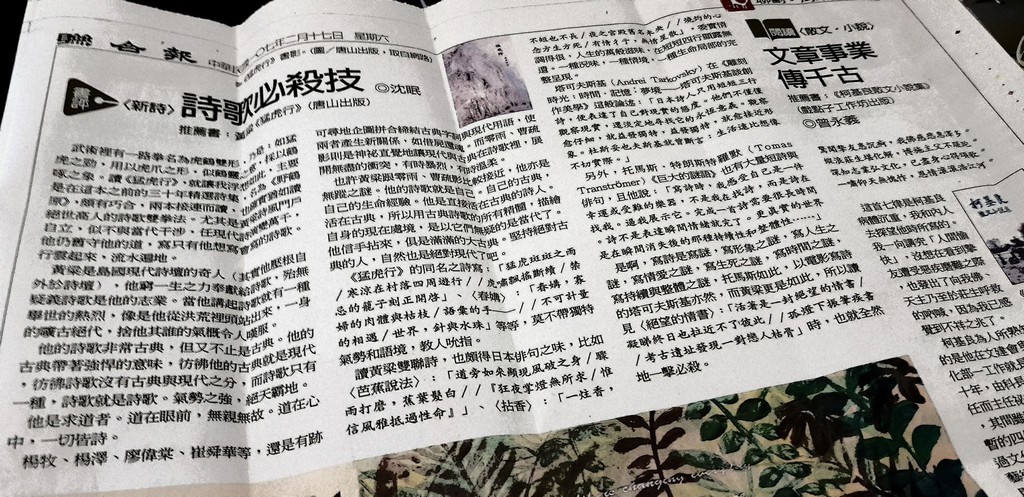〈詩歌必殺技──閱讀黃梁歌詩《猛虎行》〉
沈眠/寫
武術裡有一路拳名為虎鶴雙形,乃是:如猛虎之勁,用以虎爪之形,似鶴靈之意,採以鶴啄之象。讀《猛虎行》,就讓我浮想如此,主要是在這本之前的三十年精選詩集,名為《野鶴原》,頗有巧合,兩本接連而讀,也確實猶如讀絕世高人的詩歌雙拳法。尤其是黃梁詩風門戶自立,似不與當代干涉,任現代詩演變萬千,他仍舊守他的道,寫只有他想寫會寫的詩歌。行雲起來,流水遍地。
黃梁是島國現代詩壇的奇人(其實他壓根自外於詩壇),他窮一生之力奉獻給詩歌,殆無疑義詩歌是他的志業。當他講起詩歌就有一種舉世的熱烈,像是他從洪荒裡頭站出來,一身的曠古絕代,捨他其誰的氣概令人嘆服。
他的詩歌非常古典,但又不止是古典。他的古典帶著強悍的意味,彷彿他的古典就是現代,彷彿詩歌沒有古典與現代之分,而詩歌只有一種,詩歌就是詩歌。氣勢之強,絕天霸地。
他是求道者。道在眼前,無親無故。道在心中,一切皆詩。
楊牧、楊澤、廖偉棠、崔舜華等,還是有跡可尋地企圖拼合締結古典字詞與現代用語,使兩者產生新關係,如借屍還魂。而零雨、曹疏影則是神祕直覺地讓現代與古典在詩歌裡,展開無盡的衝突,有時暴烈,有時溫柔。
也許黃梁跟零雨、曹疏影比較接近,他亦是無蹤之謎。他的詩歌就是自己。自己的古典,自己的生命經驗。他是直接活在古典的詩人。活在古典,所以用古典詩歌的所有精髓,描繪自身的現在處境,是以它們無疑的是當代了。他信手拈來,俱是滿滿的大古典。堅持絕對古典的人,自然也是絕對現代了吧。
《猛虎行》的同名之詩寫:「猛虎斑斑之雨/寒涼在村落四周遊行//虎嘯飄搖斷續/禁忌的籠子刻正開啟」、〈春媾〉:「春媾,寡婦的肉體與枯枝/語彙的手──//不可計量的相遇/世界,針與水珠」等等,莫不帶獨特氣勢和語境,教人吮指。
讀黃梁雙聯詩,也頗得日本徘句之味,比如〈芭蕉說法〉:「道旁如來顯現風破之身/驟雨打磨,蕉葉髮白//『狂夜掌燈無所求/惟信風雅抵過性命』」、〈拈香〉:「一炷香,不短也不長/夜之宮殿舊名未央//燒灼的心念方生方死/有情彳亍,無情星散」,委實情調得很,人生的萬般滋味,在短短四行顯露無遺。一種況味,一種情境,一種生命局部的完整呈現。
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雕刻時光:時間.記憶.夢境──塔可夫斯基談創作美學》這般論述:「日本詩人只用短短三行詩,便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的態度。他們不僅僅觀察現實,還淡定地尋找它的永恆意義。觀察愈仔細,就益發獨特,益發獨特,就愈接近形象。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曾斷言:生活遠比想像不切實際。」
另外,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巨大的謎語》也有大量短詩與徘句,且他說:「寫詩時,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詩需要很長時間。詩不是表達瞬間情緒就完了。更真實的世界是在瞬間消失後的那種持續性和整體性……」
是啊,寫詩是寫謎,寫形象之謎,寫人生之謎,寫情愛之謎,寫生死之謎,寫時間之謎,寫持續與整體之謎,托馬斯如此,以電影寫詩的塔可夫斯基亦然,而黃梁更是如此,所以讀見〈絕望的情書〉:「活著是一封絕望的情書/凝睇終日也拉近不了彼此//孤燈下振筆疾書/考古遺址發現一對戀人枯骨」時,也就全然地一擊必殺。
本文發表於《聯合報:聯副•周末書房》2018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