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1 18:38:24來自星星的喵
我的老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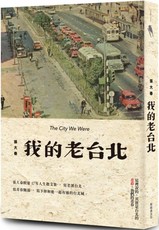
我的老台北
作者:張大春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2-30 00:00:00
<內容簡介>
這裡說的,其實是台北的青春,我們的青春。--張大春
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標,
它就在那兒──
在遼寧街116巷的公共電話亭旁
在漢中街博愛路的相機行外
在安和路麥田咖啡眾人作著夢的時光裡
在如今只剩片段記憶,卻難以忘懷我的老台北故事中
張大春繼《聆聽父親》後,睽違17年的深情散文
以此書交代了一代人從家族遷徙、漂離到落定,最終將台北視為家的感情。
周華健、詹宏志、楊澤、趙少康、王偉忠、李壽全、劉克襄、姚任祥、馬世芳……老台北人齊聲推薦
★目錄:
自序 看見那一片寂靜
1遼寧街116巷的三輪車和電話
2新家舊家回家
3父親與我的年節儀式
4成功高中101班
5台大門前,榜單之外
6電影街與公車起站
7再春游泳池,波光粼粼的一汪池水
8紅土丘下的網球兄弟們
9一車倆驢和我哥
10菜園外的吉普墳場
11屬於夏天的小說--老先覺與通信兵
12麥田咖啡,安和路,還有那些剛起步的人
13那些數不完的第一次--漢中街幼獅、沅陵街思蜜、梅村,還有博愛路相機行
14 我們的賭徒生涯 --歷史小說家高陽、副刊主編高信疆、哲學家勞思光還有我
15 台北神話,想起那個對的名字
16台大醫院和麗水街那件染血的毛背心
17無照駕駛--從新莊中正路510號,到溫州街18巷6號
18打表妹、電影畫報和武俠電影裡的大時代
19富錦街的招待所--一個計程車司機之死
附錄 查他、途死、拖拉、如是說
<作者簡介>
張大春
1957年台北出生。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碩士。早期作品著力跳脫日常語言慣性,捕捉80年代台灣社會的動態。張大春的小說充斥著現實的謊言與虛構的魅力,除了時事與魔幻寫實、更以文字顛覆政治,90年代以《大頭春生活周記》《我妹妹》等寫下暢銷紀錄,千禧年後重返華語敘事傳統,先推出武俠小說《城邦暴力團》,繼之又出版《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將其敘事風格結合文化傳承,走上自我追索傳統的道路,並以《大唐李白》系列向書場敘事及中國詩歌致意,近年出版《文章自在》《見字如來》,顯示其對教育系統中語文教養侷限的不耐。
《聆聽父親》入選中國「2008年度十大好書」,《認得幾個字》再次入選「2009年度十大好書」,成為唯一連續兩年獲此殊榮的作家。近作為《送給孩子的字》、大唐李白系列《少年遊》、《鳳凰臺》、《將進酒》,以及《文章自在》《見字如來》等。
★內文試閱:
遼寧街116巷的三輪車和電話
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標,它就在那兒──
有三輪車行經一人高的郵筒和鐵框玻璃電話亭的那個年代是其中之一。
三輪車要到1960年九月才會逐漸消失在台北街頭。三輪車伕報繳了車,可以領三千塊錢現金。最早一批車的解體儀式公開盛大,一百輛三輪兒堆擠在中山堂前的廣場上,居然也有一種壯大的聲勢。接著,你聽到不知何處一聲令下,公開拆毀。外縣市拆三輪兒的工作似乎推宕得很晚,一直到八十年代,透露著那種無聲無息便再也看不見的況味。而我印象中最後一次乘坐三輪車是四歲鬧肺炎的時候。
那時我住的國防部復華新村在遼寧街116巷,距離每天早晚要到街口去打針的松本西藥房,了不起兩、三百步的距離。可那是一個颱風天,天上潑大水。慢說是走,用我媽的話說:雨大得都看不見鼻頭了。可偏偏這時門外來了一輛三輪兒,車伕原本大約也沒有料到可以做成生意,騎過家門口的時候一按鈴,我媽就衝出去,叫住那車。從此說好了:只要是下大雨,這車一早一晚地就來門口接我去打針。我那場肺炎起碼鬧了一個月,早早晚晚打消炎針的日子還真碰上不只一個颱風,到後來和那車伕都熟了起來。大風大雨之中,上車才要坐定,就聽見他隔著油布車蓬問道:「太太啊!孩子好些了嗎?」
那車伕姓郭,後來我才知道:他和咱村辦公室的工友老孟是一對不知怎麼樣交好的朋友,倆人都是大清朝年間出生的四川老鄉,經常在遼寧街靠近12路公車起站的小麵館門口的長凳上喝太白酒,一面看瘸子老闆在大鋁盆裡刷碗。彷彿那樣刷碗是個下酒的娛樂節目似的。老孟喝著酒,還會在作廢的日曆紙背面塗塗畫畫,在咱們村口上開著雜貨鋪的村幹事徐伯伯看見了,總會咧起嘴笑著說:「老孟,認字兒啦?」
至於瘸子麵館,據說是方圓多少里以內最便宜的麵食鋪子,牛肉麵五塊錢、排骨麵五塊錢,當時我都還沒吃上。我爸說:咱們吃不起,俺一個月的薪水湊足了讓全家吃八十碗,別的幹甚麼都不能再花錢了,沒有了,光蛋了。這是我爸的原話。
老郭和老孟有些時候會蹲在村辦公室的小院子裡乘涼或曬太陽,而且悉心防範著村裡的孩子們去玩電話。村辦公是一戶寬窄的一間通聽,當間兒拼湊著幾張方桌,鋪著灰不灰、藍不藍的大桌布,那是全村開動員月會的地方,至於甚麼是動員月會,我到今天都不太清楚。而這辦公室根本沒有人辦公,室內永遠瀰漫著一種發霉的、或者是蜜餞的氣味。拼起來的大會議桌上甚麼也不許擱,此外就是一個報紙架子,和一具手搖電話機。人說老孟住在「後頭」,還說老孟在「後頭」藏了一把刀,他用那把刀趕過好幾回小偷。
村裡沒有哪個孩子不想去搖通那一具電話的,然而老孟看管得極嚴密,沒見誰得逞過──頂多頂多,有人能蹭到話機旁邊,伸手搖那曲柄幾下。老孟不喝酒的時候,除了看管電話、不讓孩子們接近之外,似乎只有兩件事可做,其一就是到了每隔週週末下午,他便搖著串鈴,走在棋盤格子似的巷弄裡、挨家挨戶門外喊報:「看電影嘍!看電影嘍!」意思是說:當天晚上龍江街封街,跨馬路張掛起大白布幕,全村甚至村外的人都可以搬把小椅子、小凳子,坐在布幕的兩邊看免費電影。
搖鈴之餘,老孟會幹的另一件事,就是當他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拿一隻毛筆蘸著黃銅盒裡的墨絲,在舊報紙上塗抹些橫線、直線、斜線、大圈兒帶小圈兒……直到把一整張報紙圖畫得密密麻麻,才作勢吹吹乾,折疊成巴掌大小的方塊,收拾到「後頭」去。
就我來說,畢竟還是那一具黑得發亮,始終放在崁入牆身的木架之上的電話,是最有趣的東西。在當時,那話機是一個極豐富的象徵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等待著被揭發或啟動禁忌的密碼,也是陌生遠方鋪向腳下的門徑,甚至──在某種被催化和誇飾了的想像力鼓盪之下,它還會帶來令人不安甚或危險的消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當反攻的號角響起──」我總是幻想著:那號角必定是在老孟的串鈴襯托之下,打從話機之中傳來的。
我的肺炎痊癒之後不多久,老郭的三輪車報廢了,但是老郭並沒有消失,他不但領了一筆補償金,還轉業成了水肥隊裡的一員。只不過從此以後出入復華新村就不走前門巷子了,也不踩車子了。他頭上多了一頂竹條箬業編成的斗笠,手上多了一根長柄鐵杓,肩膀上多了一根扁擔,扁擔兩頭各有一隻木桶。隔三岔五的,老郭就這麼打扮著從我家後門更窄小的巷子裡鑽進鑽出,挑大糞。
有一天我聽見他和我爸隔著後紗門聊起來,聽見老郭說:「我這是神聖的一票啊,當然要投給周百煉的。」我爸後來老是跟朋友說起這事:「挑水肥的都說要選周百煉,可是選出來的還是高玉樹。」那是我平生第一堂政治課,我爸的結論是:「無論選甚麼舉,千萬別問人投甚麼票。」選高玉樹有甚麼不好呢?十多年之後,這個無黨無派的政治菁英不就成了深受執政黨倚重的閣員嗎?
那些年,投開票都在臨龍江街的復華幼稚園裡。高玉樹當選的時候,我已經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了。選後沒有多久的一個週日,我在幼稚園的蹺蹺板底下撿到一個五毛錢,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當下搋起那銅板,經過村辦公室,我往裡看一眼,暗道:「你那電話有甚麼好稀奇的呢?」這是想說給老孟聽的。再往遼寧街走,看見了牛肉麵店,暗道:「還是吃不起你。」這是想說給瘸子老闆聽的。可是我知道我有五毛錢,而且我也決定了我可以用它來找個甚麼樂子──
從遼寧街右轉,直走到南京東路上,我拍打了一下那一座鑄鐵的綠色大郵筒,看看四下無人,搶步衝進行人道邊上的公用電話亭。我翻開黃色(特別強調:不是白色)紙頁的那一本號碼簿,找著了分類項目標註肉著肉脯店的欄位,隨便點了一家,撥號。
「喂?」
「豬肉店嗎?」
「是,請問找哪位?」
「你有豬頭嗎?」
「有啊。」
「那就趕快把帽子戴起來,不要讓別人看到了呀!」
我若無其事地掛回話筒,從原路往回走,發現松本西藥房對面新開了一家冷熱飲店,正在販賣一種我想都沒有想過的食物,叫芝麻糊,一碗也要五塊錢。「反正就是吃不起你」我跟自己說。一分鐘之後,我還沒走到村辦公室門口,發現前面兩個巷口都是警察。這一下我慌了,那惡作劇電話才掛下,就被發現了嗎?我猛轉身繞上遼寧街,往長春路狂奔了幾個巷口,再從光復東村那一頭繞回來。到家的時候發現我爸也像是剛從外頭回來的模樣。他往衣架上掛了西服外套,沉著一張臉對我說:「老孟拿菜刀把自己劈了。」
這件事應該還有些後來,像是鄰里間的少不了的閒話甚麼的。只不過我都不記得了。唯一有印象的是:據說南京東路電話亭旁邊那個大郵筒裡,老是被人塞進去一堆一堆的廢紙,只不過形式奇特。廢紙都有信封裝裹,裡頭放的則是墨染淋漓的舊報紙。寄件人、收件人、信件內容都像是鬼畫符。然而,知道這件事的人在老孟自殺之後到「後頭」去看過,發現老孟床下都是那樣不成字跡的書信。
也算是惡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