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1 18:38:04來自星星的喵
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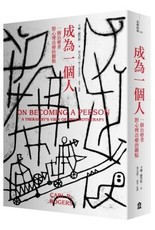
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作者:卡爾.羅哲斯 出版社:左岸 出版日期:2014-10-08 00:00:00
這不是一本勸善文,也不是一本勵志文集,也不是一本自助手冊。
本書的目的,是要拿我這個人的某些部分來與你分享。
這是我在現代生活的叢林中所體驗到的一些東西;
這是我所看到的;這是我終於相信的;
這也是我所面對的困惑、疑難、關懷和不確定。
但願在這分享的過程中,你會發現,有些東西正是針對著你而說的。
──羅哲斯
*********************
《成為一個人》在1961年的出版,為羅哲斯帶來了全國的知名度。身為研究者和治療者的羅哲斯原本認為這本書是寫給心理治療者看的,但是在銷售超過百萬冊之後,他才發現他是為一般人寫的:看護、家庭主婦、商界人士、牧師、傳教士、老師和年輕人。接下來的十年間,羅哲斯成了大寫的「美國心理學家」(the Psychologist of America),他的很多想法得到廣泛的採用,成了主流心理學的一部分,以致到了現在,我們都已經忘了那些想法在當時是多麼地新穎、多麼地具有革命性。
羅哲斯重視治療者與案主之間所建立的關係。他相信案主需要一種能夠被接納的關係,而他所使用的技巧叫做「同理心」和「無條件的正面關懷」。羅哲斯用一句話來描述他的核心假設:「如果我能夠提供某種型態的關係,那麼案主就可以在他自身中找到一種能力,從而在這種關係當中開始成長、改變與進行個人發展。」
全書由二十一篇個別發表的文章集結而成,但貫穿其間予以統整的正是羅哲斯溫暖、熱切、自信與關懷的語調。我們看到一個人,不斷耐心嘗試,並善用所有資源,以傾聽他人與他自己。如此細細的聆聽,既是為了那個前來求助的個人,也是為了尋索那個大哉問:究竟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人?
★內文試閱:
‧譯者導讀
宋文里
一、
一個驟然興起的專門職業中,許多從事者們急切想要建立他的專業身份,他所憑恃的常是那些較易於為人所知的外顯行為,譬如說:執行的技術,而不是內在的專業理念。這是「心理治療」【註1】這門專業的現況,同時也是問題之所在。當然,這並不是說,現今心理治療的工作者們對於心理治療的理念——即哲學、理論或基本假設——都一無所知。事實上,正因為所有的心理治療技術都由理念所孳生並且也由理念指引方向,因此,若對理念無知便實際上無法執行技術。然而我們目前的問題是:自從心理治療這門專業輸入國內並漸成氣候以來,雖然有了些關於心理治療的組織、做法、期望的成果等參考讀物(其實大部分仍是節譯或編譯的介紹性作品)出現,但基本的理論原著卻仍然罕見。心理治療工作者在養成教育的階段所閱讀的「理論性著作」也泰半是些大綱或摘要,對於經典原著的閱讀則常因資料來源的匱乏,或時間經濟的問題,甚至因為無法瞭解其必要性,而被省略了。
理論的摘要不能代替原著本身,其理安在?
作為一個專業心理治療者,光是「聽說」或「知道」一些關於理論的說法,對自己的專業工作是毫無助益的。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須以他的全部存在沉潛於某種理論之中,直到理論浹洽內涵成為他的一部分為止——這個說法和閱讀理論大綱時的那種含糊籠統、事不關己的態度實在是南轅北轍。簡單地說,「沉潛」就是羅哲斯﹝或其他關切存在(existential)問題的思想家們﹞所說的「成為」(becoming),而決不是許多初學者所誤信的「聽說」、「看過」云云。
心理治療的工作者除了用他所學到的一些專業技術(譬如心理測驗、評量、或心理治療的晤談和組織運作方式)之外,能使心理治療具有真實成效的東西,竟是心理治療者自己的人格!正因為我們不假設心理治療的人格會從天而降,反而認定:在人間,我們可以用人自身的力量培養出適當的人,來擔任心理治療工作,所以,我們也可用不帶神秘色彩的方式,來看看這種培養應如何才能成功。
羅哲斯的《成為一個人》這本書,假如讀者們也能認真理解的話,應很容易發現:重要的不在於如何安排一些程序步驟,或使用一些方法技術來操弄求助的案主,讓他去成為一個(心理治療者心目中的)人;相反的;羅哲斯反覆再三地說明,成人的過程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才有以發生,而發生此一過程的動力有兩重,其一在於心理治療者以自身為本而創造出某些條件,其二則是當案主感受到這些條件後,加強了改變的意願;於是,在兩重動力的交互合作之中﹝羅哲斯所謂的「關係」(relationship)即此之謂也﹞,心理治療就會以一個動態過程而往目標邁去。
話說回來,這就是羅哲斯寫成一些理論著作時,常有的本意——在閱讀之中,羅哲斯本人(如同一個心理治療者)與讀者(如同一個案主)以文字訊息為媒介而產生一個交互合作的動態過程。在本書中,羅哲斯提到一個案例,讀者閱讀羅氏的原著而獲得相似於心理治療的效果(十六章,原文pp.325–6),而所謂心理治療的「效果」(也就是漢語「療癒」一詞中的「癒」)也者,正是指:讓人格變化的過程得以發動起來。心理治療者在學習的階段先經發動,然後有案主加入,然後再以雙方合作的方式繼續進行此一動態過程。所以說,心理治療者所運用的工作法則並不將他自己摒除於外,他不能抽離於治療關係之外,他不能袖手旁觀,或僅僅以「後座司機」的身份來指點案主應該何去何從。簡而言之,心理治療者的學習過程和案主是一樣的;如果他沒有機會進入實際的治療關係;那麼,他至少應進入一種能引發變化過程的閱讀和啟蒙。
事實上,除了少數的專家之外,大多數身負心理治療之責的人都沒有機會以案主的身份進入實際的治療關係,因為一方面只有專業訓練的課程中才會包含這種課目,另方面,這種課目和真正的治療關係一樣,總是得延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大約一年到兩年),因此,目前在台灣並不是每一位心理治療工作者都能接受這樣的訓練。我們總是用比較簡便的方式來開始,因此,那就非閱讀莫屬了。也許,我們會由此而比較容易瞭解,為什麼不能只讀教科書式的大綱和摘要,而必須讀到真正可能引發交互關係的原著了。
二、
羅哲斯的心理治療取向,有過三種名稱。最初叫做「非指導」(nondirective)治療法,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以案主為中心的治療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時,已被揚棄,其理由是要將「強調的重點從負面的、狹隘的語詞……轉成較正面的、針對案主個人自身所能產生成長的因素」(Meador and Rogers, 1984: 150),但在一九七四年,羅哲斯和他的同僚們又把「以案主為中心」的名稱改換成「以(個)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相信這個名稱,更能充分描述人在其工作的方式中所涵攝的價值」(Meador and Rogers, 1984: 142n)。
這一段「正名」的過程,對於瞭解羅哲斯和他的心理治療理念而言,頗有意義。在台灣,我們常見到「當事人中心」、「個人中心」這樣的譯名。本書中,將前者改譯為「以案主為中心」,至於後者,雖然在本書出版時尚未出現,但對於「person」那個核心字眼的翻譯,則從本書的書名起,直到最後一頁,都無法迴避翻譯上的尷尬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裡討論。
在此首先要談的是「當事人」或「案主」的問題。原文中的「client」一字,最初由羅哲斯啟用,以代替過去慣用的「病人」(patient),或「被分析者」(analysand)、「受諮商者」(counselee)之名。「Client」是什麼意思呢?在法律事務上,僱請或委託代理人的那位主顧,就叫做「client」。漢語的法定譯名一般叫做「當事人」。不過,client這個字的字根原義是「聽」,也就是說,被僱請或委託的人通常是個專家,所以那個出錢的主顧還必須聽他的意見。以此而言,用「client」來代替「patient」,用意在使案主不再被視為一個有病的病號,也不再接受病患般的處置。不過,這是不是說,他真的「反客(體)為主」了呢?原文中雖給了他一個「中心」的名號,但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中心呢?
由本書所輯錄的二十一篇文章來看,羅哲斯的心理治療理論幾乎毫無例外地,是從治療者開始談起的。首先是有個人前來向治療者求助,然後兩個人接觸了。由於案主處在焦慮、脆弱、紊亂的狀態中,使得治療者必須對他提供一種特殊的協助。而後,理論的核心於焉展開——治療者應具備的條件是什麼?哪些條件可以有效地幫忙案主,使他卸除防衛之心,而開始和真實的自己鉤連?——如果沒有治療者的發動,則案主的困難狀態簡直毫無改變的契機。他將會帶著焦慮前來,也帶著焦慮回去。所以,治療者乃是這場引發改變的關係中,居於結構性關鍵地位的人物。就此而言,他和醫師、律師的關鍵性毫無二致。但是,話說回來,這位治療者是怎樣運用他的關鍵地位呢?這就涉及了羅哲斯正名過程的第一層次考慮——治療者究竟要不要指導前來求助的人?你到底該不該叫他去做這、做那?羅哲斯的回答是「不必」。因為求助的關係已經帶有形式結構上的引導性,案主已經進入了一個很特殊的引導性關係之中,而這種結構上的引導性已經很夠了,不必再加上別的引導——何況,羅哲斯在晚期的著作中還強調了:在案主那個人的整個存在中,還分受了一種來自宇宙天地的自然結構,動力豐沛,躍躍欲出,只等著由治療者釋放而已,哪還需要什麼命令、催促式的指導呢?(Rogers, 1981)這個想法看似幾近神秘,但羅哲斯曾特別為此作了闡說:大自然的世界中富含形成的趨勢(formative tendency),即使生物學家、化學家也可在演化的進程,或物質的結晶法則中看出此一趨勢的存在,所以並非神秘主義者的妄作主張(Rogers, 1981: vii-x)。由於懷有這樣的信念、所以,「非指導」的治療法可以義無反顧地推出,但是,我們不可被字面意義所惑,因為「nondirective」(非指導)並不意味著「no direction」(無方向),「非指導」並不是「沒有引導」。至少,不談自然所引導的方向吧,在結構關係中的引導之責仍然一分不少地落在治療者的肩上。因此,這個治療者既然身負重任,羅哲斯就必然要先把他所應具備的條件指明。然而,在關係中如此重要的人,為什麼反而不是中心,卻讓另一個人變成了中心?這是怎麼說的?
事實上,這種令人困惑的問題胥來自於翻譯的語義。當我們說「案主中心」或「個人中心」時,原本是一種相互關係的心理治療結構,竟只凸顯了一個人,而讓另一個關鍵人物隱沒不見了。這是翻譯者的矯枉過正,因為,在原文中,不論「client-centered」或「person-centered」的語詞都含有「被…造成」、「因…而然」的含義,而這樣的被動態自然蘊涵了一個主動者在內。我認為,這就是方才提到的「結構性」之主動──誰主動?不是別人,正是治療者,以及他所代表的治療體制。是這主動者使案主變成治療關係的中心,或焦點,但,我們永遠不應忘記:焦點的背後必然有個聚焦的裝置,或調整焦距的人存在。
談到這裡,才可以回過頭來說明:為什麼我寧願使用「以案主為中心」的冗長譯名。我不願把「以…為」兩字省掉,是為了讓結構性的主動者重新回到它的涵義中。其次,我把「當事人」換成了「案主」,則是因為「當事人」一詞即使在法律意味之中,也並未真正顯出「主動性」的意思——他仍然是個委託專家替他辦事的人。反正我們的漢語中沒有一個在意義上完全相當的字眼,不如就直接以實際的求助情形來給他一個名稱也罷。他來尋求的是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而由於本地已經有個通用來稱呼以上兩者的名詞——「心理輔導」——我們就說他是個「由心理輔導體制所接案的人」,簡稱作「案主」,於是,我們的「以案主為中心」的譯名乃於焉構成。
至於到「以(個)人為中心」的階段,事實上,羅哲斯已經很明顯地放棄了偏袒一方而讓另一方隱在背後的做法。他使用了「person」一字,用以指稱關係雙方的兩個個人。史畢哥勃(Herbert Spiegelberg, 1972: 154)在分析羅哲斯的現象學觀點時說得好,他說:「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就得說:這種理論已經不是只以案主為中心,而是雙中心(bi-centered);或是兩極(bipolar)的了……。」兩極互動,或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也可譯作「交互主觀」,其實才是羅哲斯所謂的「關係」之本色。
三、
接著要談「person」的問題。我把「On Becoming a Person」譯作「成為一個人」,是利用「一個」的量詞和「人」接在一起,一方面使「人」不會成為集合名詞;另方面也避免了用「個人」來譯「person」的困境。「person」當然是指單數的人,但它不等於「個人」(individual)——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他和羅哲斯的對話中很堅持這種分野。他說:「我反對individuals而贊成persons。」(Buber, 1965: 184)至於布伯的堅持究竟有什麼道理?我想,也許應該先從我們自己的語言,來看看我們的意義系統中潛伏的一個基本難題。在漢語的語法中,「人」這個字雖是個單數人的造形,但它?絕少有「個人」的涵義。在古漢語中的「人」甚至常用來指「他人」,譬如在「利己利人」、「推己及人」等等詞句中,「人」是用來與「己」對立的。而在俗語中的「人家」、「不像人」等說法,則用「人」來泛指集體而不指特定的人。另外只在「人家我要去…。」或「氣死人」等語句中,才用來指外化的「我」。不過,以上這幾種用法,都不同於羅哲斯所特意標舉(或布伯所堅持)的「person」。
布伯對於「person」的說明是:「一個person……乃是一個個人而實實在在地與世界生活在一起(an individual living really with the world)。而所謂與世界在一起(with the world),並不意指他只在世界之內(in the world)——而是他和世界有真實的接觸,有真實的相互性,且是在世界之能與人相遇的各點上,皆能如此……這才是我所謂的a person……」(Buber, 1965: 184)。「A person」是個可以數的、具體存在的人,但他既不是囿於一己之內而與世界(社會)分別、對立的個人,也不是被世界所吞噬,被群體所範限而至失去各別性的「一般人」。與此相較的話,羅哲斯的用法比較不作嚴格的區分——他以「individual」和「person」作可以互換的使用,但很明顯的,他的「individual」一字承襲了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用法,不是指私心濃重、與人有別的個人,而更為接近布伯所稱的「person」之義。
由於「person」一字在漢語裡譯作「個人」或「人」都不很貼切,加上它在西方的語言體系中確實有相當複雜的脈絡,【註2】所以台灣的神學、哲學界常另採用「位格」的譯名,也就是以新語詞來刷新它在漢語裡的舊涵義。這個辦法,我也無法採用,因為羅哲斯所稱的「person」雖也用來指稱一個哲學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它常常與量詞、冠詞連用(persons, a person, the person)而用以指稱「具體存在的個人」。若譯作「一個位格」,無人能解,所以,我仍然想辦法依照文脈,使用具體字眼去翻譯它——有時作「個人」,有時作「人」,有時作「我個人」,只有在不指各別而具體的人時,才稱作「人格」,但,我一定要提醒讀者:對於「person」這個關鍵字眼,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更進一步說:每當羅哲斯提到人、個人、我、自我之類字眼時,他所指的,幾乎都是他的哲學中所欲重建的那種人。我們必須洗掉我們舊有的語言習慣,否則將無法接收他的意思。對於「人」,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賦予它更多新義的時候。俗話中有種種與「人」有關的常用語詞,譬如「人權」、「人性」、「注重人而不注重物質」等等,都不見得超脫得了傳統語義的窠臼,換句話說:僅僅一個「人本主義」的新口號,也不見得能表示任何嶄新的反省。我們很需要跳進另一個意義系統的水庫中,才能汲得新的理解。羅哲斯至少是那個意義系統中的一個鮮活樣本,值得我們浸潤於其中。
四、
羅哲斯在他有生之年,對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地區的心理治療已造成廣泛的影響,有人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理論「簡單、易懂」,換言之,他是個很適合大眾傳播(甚至報紙的家庭版與休閒生活版)口味的人。這種說法似乎正是大眾傳播式的論調——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報導中變得「簡單、易懂」。但在本質上,羅哲斯有個無比艱難的層面。從理論和方法的關聯上,對羅哲斯重新加以思索,就會發現,其實他一點也不簡單。
羅哲斯和存在主義哲學以及現象學的關係相當微妙。他未嘗以「學術性的閱讀」,或其他學術活動(如研討會、辯論會等等)的方式直接參與現象學界以及存在主義哲學。他自承自己在那方面「不是一個學者」,只是偶爾讀到幾本別人寫的書,而「確認了我自己當時所作的嘗試性思考。」(Rogers, 1980: 63)。他所指的書包括了齊克果、布伯、以及博蘭霓(Michael Polanyi)等人的著作。而在本書中,羅哲斯確曾七度提及齊克果的名字。我們只能說,他獨立發展自己的哲學,但?與存在主義者們遙相呼應。至於現象學,羅哲斯的工作證明了他在此有某方面的參與及貢獻。史畢哥勃指出:「羅哲斯對於人格與行為的最後理論更明顯地表示:現象域(phenomenal field)乃是人格結構中的一個基要部分……現象學的世界不僅是人的行為之主要原因(causal factor),也是治療過程中主要的攻擊點(point of attack)。」(Spiegelberg, 1972: 152)雖然羅哲斯的工作同僚中就有現象學者(譬如Arthur Comb, Eugene Gendlin等),但他從未明顯引述現象學著作,譬如最後一章所談的主觀性,在胡賽爾的《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Husserl, 1936/1992)一書中早已說得非常透徹,而羅哲斯只是一直以他自己的「現象學方法」呈現了案主和心理治療者的主觀體驗。這樣的工作實際上就是他一生事業的主要內容。
對於現象學,或存在主義哲學都還相當陌生的知識界(譬如當時的美國,或甚至當今的漢語世界),提及現象學方法,以及存在主義的「本體論」時,幾乎都難以開始討論。尤其對存在現象學的術語,連最接近於此的心理學界仍多無法接受,因此,很自然的,這種溝通無從發生,只能留下一些「簡單、易懂」的部分,聊資茶餘酒後閒話一番而已。
再談到方法的問題(專業工作者事實上都應從這裡開始談起才對)。羅哲斯所稱的真誠(genuineness)﹝或稱「合一」(congruence)﹞、同理心(empathy)【註3】、無條件的積極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等,在方法的運作上是極其困難的過程。首先,就概念的界定,或性質的指認來說,就會引發非常複雜的問題。羅哲斯對於這些概念都用體驗描述的方式來說明它們的性質,然後用交互主觀認定的方式,來確認它們的存在。接著,放在專業訓練的脈絡中,更為困難的則是;如何引發、如何修正、如何維持的問題——對接受專業訓練的準心理治療者,和對案主而言,都一樣不容易。沒有人能期盼它「天生註定」或「生而有之」,我們必須以整套的培養、實習及核驗的方法,來引發並鞏固理論的主張。就培養和實習的部分而言:羅哲斯學派(The Rogerian Schoo1)事實上發展出很多方法,而且也廣泛地被專業訓練機構採用。以一份調查資料來看,當可見其一斑——Heesacker, Heppenr, & Rogers(1982)對諮商心理學的經典之作,用引述(citation)次數的多寡為標準,計算了三種主要學術期刊(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Personnel and Guidance Journa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在一九七九、一九八○兩整年內所有文章所引述的著作,結果發現:自從一九五七年以來、排名前九名的著作中,有四本受到羅哲斯的直接影響,並且都以說明專業訓練方法為其主要內容﹝這四本著作是:Carkhuff (1969), Truax & Carkhuff (1967), Ivey (1971), Egan (1975)﹞。再就核驗的部分來說,羅哲斯更以大量的精力投入於各種實徵研究。本書十一、十二兩章對這段研究過程及結果作了清楚的報告。總之,理論本身涉及複雜的訓練方法及核驗方法,而這些都是羅哲斯理論的實質內容。對這些方法未曾親歷或未嘗清晰理解的人,都不應說是「知道了」羅哲斯,而只能算是道聽塗說。很可借,一直到今天,在台灣號稱為心理治療「專業訓練機構」的地方,都還明顯地缺乏對理論的深入討論,以及,更嚴重的是,幾乎沒有認真的專業養成訓練——沒有完整的訓練制度與課程,甚至沒有充分的訓練設備。在這種情形下,難怪會稀釋了羅哲斯的份量,也使得心理治療的理念縮水淡化,不知所云。
五、
另外兩個問題也必須在此澄清一下,就是關於羅哲斯和精神分析理論及治療法的關係,以及羅哲斯與行為主義者之間的爭論。
羅哲斯本人相當堅信他的主張是反佛洛伊德的。在本書中(第五章),他指出:佛洛伊德及其後繼者認為,人的本能衝動若不加以管制則必導致亂倫、謀殺等行為,人的本質是非理性、非社會性、損人害己的。這種態度,經過二十年也似乎沒有改變(Rogers, 1980: 201)。但是,羅哲斯並不知道他犯了相當嚴重的「稻草人式」謬誤——他所說的佛洛伊德不是佛洛伊德的原義,充其量只是一些來自二手著作的意見,或甚至是觀察到不入流的精神分析師之工作而產生的成見而已。
佛洛伊德創造了心理治療的基本型式,而他所創用的幾種觀念,譬如:無意識(the unconscious)、自我防衛(ego defense)、傳移(transference)【註4】等等,幾乎已成了心理治療學所不自覺的通用概念。羅哲斯無疑的也落在這種觀念系統中。認真檢查羅哲斯的想法,可以找出他和精神分析有許多相通之處。譬如本書第六章,談到人的意識知覺與有機體官能和體驗的關係,他說:「當意識不再戰戰兢兢地執行看管任務的時候,人的所有官能都會善為自律……」(p.119)在此,他的「意識」與「官能」間的關係,可說是佛洛伊德「自我」(ego)與「它」(id)【註5】關係的複本。換言之,知覺與體驗之可以併存,或根本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都接近於佛洛伊德的主張。更明顯的證據,莫過於本書十七章中的一段話:「一個精神官能症患者(the “neurotic”),在自己的意識裡有個常被稱為無意識的部分,這些部分由於受到壓抑或否認,以致造成了知覺上的障礙。使得這些部分的訊息無法向意識,或向他自己的主宰部分傳遞。」(p.330)——這個說法,如果不特別標明的話,幾乎會被認為出自精神分析的官方文件。更有甚者,羅哲斯在早年的工作經驗中雖然有「棄絕精神分析模式」的階段(本書第一章,關於羅徹斯特那幾年的工作經驗),但他也接觸了另一種精神分析學者的治療法,就是巒克(Otto Rank)的「意志治療法」(will therapy)或「關係治療法」(relationship therapy),並且頗受影響(Rogers, 1980: 37)。巒克的治療法導源於佛洛伊德所發現的傳移現象。不論巒克對佛洛伊德有多少修正的意見,他仍是屬於精神分析傳統的。佛洛伊德的後繼者,乃至其他的批評者,在羅哲斯盛年之時的美國,由於《佛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4)尚未出版,因此很少人看到了佛洛伊德的全貌;更有甚者,由於訛傳、誤譯之故,更嚴重地扭曲了精神分析的原旨。貝托海(Bruno Bettelheim, 1982)曾提出許多嚴肅的說明,希望糾正這數十年來的錯誤。他在書名頁之前,引了佛洛伊德致榮格(Carl Jung)信函中的一句話:「精神分析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透過愛的治療。」(“Psychoanalysis is in essence a cure through love.”)——這不也正是羅哲斯的根本信念嗎?以此而進一步再尋找羅哲斯與佛洛伊德的相容,或相匯(而非對立)之處,不是很有可能嗎?
羅哲斯沒有機會碰到佛洛伊德,但是他碰到了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學的史金納(B. F. Skinner)。他們真的對上了。一九五六年九月,羅、史二人在明尼蘇達大學(杜魯曰校區)作了一場長達九小時的辯論,其辯論內容被廣播出來,並摘要節錄於《科學》雜誌,但羅哲斯原本希望全部內容,甚至原始錄音都能全部公開,卻因史金納事後拒絕同意,而使此事未能如其所願。羅哲斯對此耿耿於懷,他的強烈不滿表現於1980年的回顧中,他說:「我覺得(我們)這整個專業都被(他)欺騙了。」(1980: 56)
究竟羅哲斯和史金納的爭論焦點何在?羅哲斯表示那是基本哲學之間的對立,自由對控制,人本主義對環境決定論。但史金納在辯論中堅認:人本主義者所主張的自由抉擇,最後都擺脫不掉控制的成份——在心理治療中,不論案主如何被允許、鼓勵去作自由抉擇,他仍是在治療者所提供的護持之中才能如此。史金納的回顧說得非常乾脆:「一個人可用安排環境的方式來協助另一個人,然而他所安排的環境就施行了控制。如果我沒說錯的話,一個人不可能不作此安排而竟能有助於人。所謂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是在控制著人的,如果他們所做的事情真的有效的話。」(Skinner, 1974: 186 )羅哲斯在本書中很清楚地提出行為主義的缺陷,但,史金納的答辯不是也頗有道理嗎?所以,到底他們在爭什麼?
如果他們的爭論不只是因為「控制」這個字眼的同名異指,那麼,也許羅、史二人的主張是分立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上。羅哲斯強調人的價值判斷和目的選擇的基本歷程,而史金納則把焦點放在人際互動的實際行為,以及該行為的結構涵義上(我在譯序第二節中對此作過說明)。史金納並不是個贊成恐怖控制的人,相反的,他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乃是用小說的形式來表現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他想使人的精力不浪費於維持不人道的「尊嚴」;他所嚮往的是一個能以有效安排行為和賞罰的前後關係而建立的秩序世界,藉此避免濫施懲罰的「社會化」過程——他又是哪裡逸出了人本的關懷之外?史金納的本體論不在他自己的方法論之中,但我們卻可以在他的研究和著作事業上,清楚地看出他的價值觀。所以,羅哲斯才會說:「我們(的想法)儘管截然不同,但這仍不會傷害我對他的尊敬。」(Rogers, 1980: 56)行為主義當然可以衍生很多機械論、決定論式的枝節末流,但當我們弄清楚它和人本主義的層次關聯後,就不難理解:它們之間仍可以有結構性的相容關係,羅哲斯在本書第三章中也實際上表示了這種看法。行為主義的心理學衍生出行為改變技術(behavior modification)和行為治療法(behavior therapy),但誰說它不能被人本主義者使用呢?誰又能說一個行為治療者不能懷有羅哲斯的價值觀呢?
羅哲斯實在不是讓我們用來反精神分析或反行為主義的藉口。這就是我要強調的意思。我們閱讀羅哲斯的目的,是在於達成融匯——存在的本體之融匯——而不是在製造「說說嘴」式的衝突。這就是我真正應該表達出來的意思。
六、
我在一九八六年裡開始動手迻譯這本書、到一九八九年它才得以出版,距原文首版的時間(一九六一年),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這是不是正表示了:即便在號稱為「已經現代化」的台灣,我們對具體存在之人的關懷,在起點上也比羅哲斯所處的世界落後了至少二十七年——或,再過十四年,到了二○一三年,還是需要修訂再版一次──所以我們真的不知該如何計算時間的距離。在此之外,更有意味的學問距離竟是:即連美國本身,人文的心理學也並未在羅哲斯那一代的幾位「人文主義者」叱吒風雲之後,就開顯出人文心理學的另類主流,相反地,這曾經被名為「第三勢力」的心理學,在學院中竟然隨著一代風雲的退休潮之後,就沒再來潮,而是改頭換面地以另一種方式,在一九八○年代末重新漲潮,那就是「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但其中蘊含的思想背景已經和羅哲斯等人的主張有很複雜的差異,我們在此無法詳論。【註6】只不過,成為一個人的路程,在個人的世界中,已有羅哲斯這類的人物以其經典(也堪稱古典)的現身說法而為我們指出一個必然不可或缺的方向,只是在文化全面的意義上,還要看我們自己能不能測量這段路程的距離,以便能夠勇於開拔而走上其道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
寫于新竹清華大學
二○一三年四月
改寫於輔仁大學
隨頁註
【1】目前在台灣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以及一些精神科醫師在從事這個專業。但這些領域區分並非必要(譬如在美國的證照制度中就無此區分),而在羅哲斯的討論中,就都可涵蓋於「心理治療」的範圍內。
【2】參見關子尹在卡西勒(Ernst Cassirer)所著《人文科學的邏輯》一書中的譯註,頁九○~九二,台北:聯經。
【3】「Empathy」目前通用的譯名是「同理心」,但這樣的漢語語詞是很有問題的。「同理心」這個語詞的核心是「同理」,原本有個來源,就是王陽明哲學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簡化成「同理心」之後,「心」就落到語意的邊緣上(這種語詞構成的原則,請參閱徐通鏘,二○○五,《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譯者目前不打算推翻這種「同理」而不一定「同心」的譯名,只是要提醒讀者,使用翻譯名詞時,常要有這樣的警覺:不可望文生義。
【4】「Transference」一詞,目前坊間有些精神分析著作的翻譯本都譯為「移情」,這會造成學術上的混淆,因為「移情」一詞早就在朱光潛(一九三六)的《文藝心理學》(台北:開明,一九六三)及其他翻譯的美學作品中用以作為「empathy」(德文einfühlung)的譯名。目前漢語的美學對此詞的譯法都是依照朱光潛的譯法,因此,在漢語中較晚出現的「transference」譯名不應僭奪美學既有的術語。目前注意到此一問題的精神分析學者已經改用「傳移」來作為「transference」的譯名。
【5】「Id」在過去的漢語文本中一直被翻譯為「原我」或「本我」,這就是下文中的貝托海所要批評的一個重點。佛洛伊德對此概念的原文(德文)是「das Es」,英文應該譯為「the It」,所以貝托海批評英譯者選用的「id」不知所云。在漢語中,譯為「原我」或「本我」則都犯了另一種錯誤──把「不知的他者」強名為「已知的客體或本體」。但願讀者可以接受最接近原意的「它」這種譯法。
【6】讀者可以參看以下幾本書:Jahoda, G. (1993). Crossroads between culture and mind: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 M. (1996). Cultural psychology : A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 A., Harré, R. and van Langenhove, L. (eds.) (1995). Rethinking psychology. London: Sage; Valsiner, J. (Ed.)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上一篇:中國贏了嗎?挑戰美國的強權領導
下一篇:做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