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3-12 00:06:25太皮
心之禁室:憂鬱懸掛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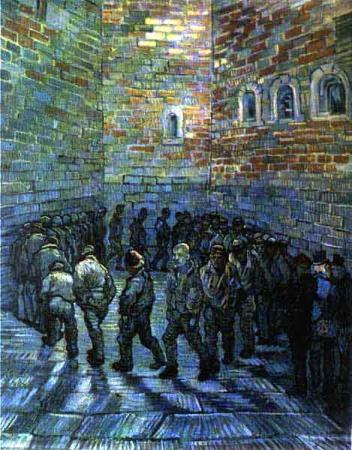
“真的要記得,自己曾經是如何堅定地愛著他的……”小秋沉吟著,望著高士德馬路上空的雨發呆。不知道為甚麼,每逢寫一些關於憂鬱的東西時,我總會不期然想到高士德天空上的雨。到底是甚麼記憶觸動我呢?是小時候和弟弟站在麥當努門前,一邊避雨一邊分享一份薯條的記憶呢?還是中學時代那些愁人的下雨天,我都要守候著巴士的角落與全車乘客一起沉默地在這條馬路上等待的記憶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小秋就是在一個下雨的傍晚,靜悄悄地從這條馬路上其中一棵榕樹的樹葉間爬下來的,我知道,她是一隻精靈,因為只有這樣說,才可以解釋她為甚麼如此輕盈和漂亮。那時她就靜靜地站巴士站旁兩部自動櫃員機中間,沒有說話,雙手下垂,十指交纏著,頭髮和白色連衣裙都是濕的。人來人往,沒有人真的注意她。我那時盤算著她歸家的時間,因為她是逃跑出來的精靈,總要回家的。
然而任憑我怎樣想像,小秋仍然擺脫不了命題的限制,這個命題就是澳門,一個小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其實她只是作者筆下的意像,而我自己是否受到了澳門這個命題的限制呢?也許。我敢說,很多澳門人都受到這個命題的限制了:短視、狹隘、緩慢、缺乏浪慢;當然,我列舉的只是壞的一面,澳門人還有很多好得沒話說的品格,好到成為了別人評論澳門人時的陳詞濫調,作為西里的我,是不會再說的。
小秋已經第十天站在同一個位置等待同一個男孩子了,那男孩子本來是她的男朋友,他在半個月前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告訴小秋,他已經愛上了第二個女孩。小秋十分傷心,將自己關在房間裡一個星期,學也不上,飯也不吃,瘦得十分厲害。
那時,在兩部櫃員機中,她想起了和男友相處的種種,快樂、悲傷、憎恨和原諒就像池裡爭吃的錦鯉一樣,擁到了一處。眼淚模糊了她的視線,她見到自己的憂鬱正往上飄、往上飄,結集成烏厚的雲。
“你為甚麼要離開我?”小秋喃喃自語,抬眼望前。那時我坐的巴士正好駛到站上,我在看她,以為跟她目光相觸了,但其實她一無所見。
寫下上一段文字的時候,我就罵小秋了,罵她為甚麼問這麼傻的問題。離開,又怎麼需要理由和解釋呢?我們需要的只是包容和接受。為了讓她明白,我安排了一輛粉紅色的私家車在我所乘搭的巴士後面,而那輛車正開盡喇叭播放著Beatles的《Yesterday》,在如此嚴重的塞車情況下,小秋有幸聽完了這整首歌。
為甚麼她一定要離開?
我不知道,她不會說,
我想一定是有些事情出錯了,
我如今只渴望回到昨日。
小秋哭了,我陪著她哭了。巴士上年少的我在哭,剛寫下這段文字的我也在哭。只有莫名其妙失去某樣東西的人,才能深刻體會那些歌詞的份量。
是甚麼事情影響著我的內心呢?我的心態越來越朝著糟糕的方向轉變,每天面對著社會上發生的大小事情,都無法使我動容,我發覺澳門的小,已到了一個失控的地步,這地方太缺乏想像力了。當然,小並非藉口,想像力不能欠缺的是內心的純真。澳門能生大事嗎?不知道,或者看你衡量事情的標準,但命題決定了大事也不能大到哪裡去。那麼,在這三個小島上的詩人,靠甚麼來激活、來超生?所以,當我每天看到在澳門發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也不過爾爾時,我就會躲到自己幻想的角度裡去,幻想,絕對比現實美麗,至少小秋會這樣想。
她有預感,這傍晚一定可以看到他。她摸了一下放在袋裡的彈弓刀,幽幽地說:“一切就此了結吧……”
一切就此了結吧。少年時代,我常常都十分希望了結自己,因為我發現理想與現實的不協調、個人與群體的不協調。但這個了結自己的想法已多時沒出現在我心間了,表明了甚麼?表明了我越來越沒有理想,越來越妥協了。我想,唯一不協調的時候,應該是我偽裝成太皮的時候吧,而太皮又常常偽裝成各種各樣的人物。
最近有幾天十分寒冷,而且下著綿綿細雨。小秋突然間也感到了十分寒凍,她抱起了雙手。從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太多小秋的過去,只知道她被男朋友拋棄了(也許我不該用“拋棄”這個詞)。作者無需為故事的人物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你們要知道的,就是小秋只是我一個情感的反射。因為太皮已經江郞才盡了,寫東西不得不取巧。其實為甚麼,每一文學作品幾乎都避免不了愛情命題呢?說穿了,愛情只是一個夢,只是性交的偽裝。然而人是虛偽的,絕對不會撕破愛情這個漂亮的外衣,反而會好好地保護著。
但小秋認為愛情是人生中至高無上的情感,沒有愛情,人活了也是白活;至於性交,只是愛情的一個過程,並非目標。“那麼愛情的目標呢?”一把聲音在她心靈裡響起。愛情的目標?她疑慮起來,自己問自己:愛情的目標?……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她捂住雙耳,尖聲大叫!她的叫聲充斥了整條馬路,但無論她怎樣喊叫,始終沒有人理會她,只有我在巴士上如看電影般默默地看著她。
我們每天都在喊叫,但沒有人理會我們。
那是一個十分寒冷、下著大雨的深夜,和同事吃完宵夜,我冒雨駕著電單車回家,在三角花園旁的行人天橋下因紅燈而停了下來。一陣淒厲的的狗叫聲在不遠處傳過來,我透過刺眼的雨珠,看到一隻黃狗趴在天橋下安全島的草地上,我估計牠一定渾身濕透,凍得要死了。牠不停地仰頭嚎叫,一次又一次,聞者動容。
我沒有理會牠,綠燈,開著車趕緊回家,實在冷得可怕。這些天來澳門和國際上發生過甚麼大事,我幾乎都忘了,但那隻狗的嚎叫,卻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腦子裡。
我回過神來,再看小秋時,她已經倒在血泊中。她了結了自己,看得清楚,彈弓刀還插在她的小肚上。
外傳
SK,很久沒有碰到妳了,那天在高士德我見到了妳。我遠遠地看著妳,像看著一尊神聖的雕像,妳還是那麼清秀而美麗,很少有人穿裙子穿得像妳這麼漂亮的了。妳那若有若無的眼神,不知是否看到我了?上一次在板樟堂,我還敢叫妳一聲,今次在高士德,我連那一丁點兒勇氣都蕩然無存了,不知為何,在妳這女神面前,我總感到十分自卑。妳知道的,我不是沒有被妳迷倒,沉默只因高攀不起。
2004/3/7
註:題目為陸奧雷在我新聞台的留言。
如果我沒有記錯,小秋就是在一個下雨的傍晚,靜悄悄地從這條馬路上其中一棵榕樹的樹葉間爬下來的,我知道,她是一隻精靈,因為只有這樣說,才可以解釋她為甚麼如此輕盈和漂亮。那時她就靜靜地站巴士站旁兩部自動櫃員機中間,沒有說話,雙手下垂,十指交纏著,頭髮和白色連衣裙都是濕的。人來人往,沒有人真的注意她。我那時盤算著她歸家的時間,因為她是逃跑出來的精靈,總要回家的。
然而任憑我怎樣想像,小秋仍然擺脫不了命題的限制,這個命題就是澳門,一個小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其實她只是作者筆下的意像,而我自己是否受到了澳門這個命題的限制呢?也許。我敢說,很多澳門人都受到這個命題的限制了:短視、狹隘、緩慢、缺乏浪慢;當然,我列舉的只是壞的一面,澳門人還有很多好得沒話說的品格,好到成為了別人評論澳門人時的陳詞濫調,作為西里的我,是不會再說的。
小秋已經第十天站在同一個位置等待同一個男孩子了,那男孩子本來是她的男朋友,他在半個月前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告訴小秋,他已經愛上了第二個女孩。小秋十分傷心,將自己關在房間裡一個星期,學也不上,飯也不吃,瘦得十分厲害。
那時,在兩部櫃員機中,她想起了和男友相處的種種,快樂、悲傷、憎恨和原諒就像池裡爭吃的錦鯉一樣,擁到了一處。眼淚模糊了她的視線,她見到自己的憂鬱正往上飄、往上飄,結集成烏厚的雲。
“你為甚麼要離開我?”小秋喃喃自語,抬眼望前。那時我坐的巴士正好駛到站上,我在看她,以為跟她目光相觸了,但其實她一無所見。
寫下上一段文字的時候,我就罵小秋了,罵她為甚麼問這麼傻的問題。離開,又怎麼需要理由和解釋呢?我們需要的只是包容和接受。為了讓她明白,我安排了一輛粉紅色的私家車在我所乘搭的巴士後面,而那輛車正開盡喇叭播放著Beatles的《Yesterday》,在如此嚴重的塞車情況下,小秋有幸聽完了這整首歌。
為甚麼她一定要離開?
我不知道,她不會說,
我想一定是有些事情出錯了,
我如今只渴望回到昨日。
小秋哭了,我陪著她哭了。巴士上年少的我在哭,剛寫下這段文字的我也在哭。只有莫名其妙失去某樣東西的人,才能深刻體會那些歌詞的份量。
是甚麼事情影響著我的內心呢?我的心態越來越朝著糟糕的方向轉變,每天面對著社會上發生的大小事情,都無法使我動容,我發覺澳門的小,已到了一個失控的地步,這地方太缺乏想像力了。當然,小並非藉口,想像力不能欠缺的是內心的純真。澳門能生大事嗎?不知道,或者看你衡量事情的標準,但命題決定了大事也不能大到哪裡去。那麼,在這三個小島上的詩人,靠甚麼來激活、來超生?所以,當我每天看到在澳門發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也不過爾爾時,我就會躲到自己幻想的角度裡去,幻想,絕對比現實美麗,至少小秋會這樣想。
她有預感,這傍晚一定可以看到他。她摸了一下放在袋裡的彈弓刀,幽幽地說:“一切就此了結吧……”
一切就此了結吧。少年時代,我常常都十分希望了結自己,因為我發現理想與現實的不協調、個人與群體的不協調。但這個了結自己的想法已多時沒出現在我心間了,表明了甚麼?表明了我越來越沒有理想,越來越妥協了。我想,唯一不協調的時候,應該是我偽裝成太皮的時候吧,而太皮又常常偽裝成各種各樣的人物。
最近有幾天十分寒冷,而且下著綿綿細雨。小秋突然間也感到了十分寒凍,她抱起了雙手。從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太多小秋的過去,只知道她被男朋友拋棄了(也許我不該用“拋棄”這個詞)。作者無需為故事的人物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你們要知道的,就是小秋只是我一個情感的反射。因為太皮已經江郞才盡了,寫東西不得不取巧。其實為甚麼,每一文學作品幾乎都避免不了愛情命題呢?說穿了,愛情只是一個夢,只是性交的偽裝。然而人是虛偽的,絕對不會撕破愛情這個漂亮的外衣,反而會好好地保護著。
但小秋認為愛情是人生中至高無上的情感,沒有愛情,人活了也是白活;至於性交,只是愛情的一個過程,並非目標。“那麼愛情的目標呢?”一把聲音在她心靈裡響起。愛情的目標?她疑慮起來,自己問自己:愛情的目標?……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她捂住雙耳,尖聲大叫!她的叫聲充斥了整條馬路,但無論她怎樣喊叫,始終沒有人理會她,只有我在巴士上如看電影般默默地看著她。
我們每天都在喊叫,但沒有人理會我們。
那是一個十分寒冷、下著大雨的深夜,和同事吃完宵夜,我冒雨駕著電單車回家,在三角花園旁的行人天橋下因紅燈而停了下來。一陣淒厲的的狗叫聲在不遠處傳過來,我透過刺眼的雨珠,看到一隻黃狗趴在天橋下安全島的草地上,我估計牠一定渾身濕透,凍得要死了。牠不停地仰頭嚎叫,一次又一次,聞者動容。
我沒有理會牠,綠燈,開著車趕緊回家,實在冷得可怕。這些天來澳門和國際上發生過甚麼大事,我幾乎都忘了,但那隻狗的嚎叫,卻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腦子裡。
我回過神來,再看小秋時,她已經倒在血泊中。她了結了自己,看得清楚,彈弓刀還插在她的小肚上。
外傳
SK,很久沒有碰到妳了,那天在高士德我見到了妳。我遠遠地看著妳,像看著一尊神聖的雕像,妳還是那麼清秀而美麗,很少有人穿裙子穿得像妳這麼漂亮的了。妳那若有若無的眼神,不知是否看到我了?上一次在板樟堂,我還敢叫妳一聲,今次在高士德,我連那一丁點兒勇氣都蕩然無存了,不知為何,在妳這女神面前,我總感到十分自卑。妳知道的,我不是沒有被妳迷倒,沉默只因高攀不起。
2004/3/7
註:題目為陸奧雷在我新聞台的留言。
上一篇:吹水:死神與太皮
下一篇:心之禁室:四年前的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