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案...粗糙卻可判人死刑的刑事司法制度(美國死刑改革研究)

蘇案...粗糙卻可判人死刑的刑事司法制度
—也介紹一個美國的死刑改革研究
蘇建和等三人「又」被判了死刑。為什麼蘇案能惹起這麼多的聲援與注目?因為它像一面照妖鏡,清清楚楚顯示出我們的刑事司法離「現代」的距離還有多遠!
蘇案更讓「台灣應否維持死刑」的辯論,從「壞人該不該死」的道德或哲學爭議,來到「如何確定該死壞人是誰」的制度與法律爭點。即使是支持死刑與應報的人,應該也同意「不錯殺好人」吧。就算是對壞人毫無同情心的人,大概也不會認為,國家可以在證據可疑的情況下把任何人定位為「該死的壞人」。
偏偏,這似乎就是蘇案。這也是我們的司法制度—由一堆徹頭徹尾不相信「推定無罪」,而且連表面遵守「推定無罪」也不願意的司法人員所組成的審判制度。
那麼,如果堅持維持死刑,要怎樣確保司法制度不草菅人命呢?
在2003年,美國麻州州長Romney邀集各界專家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研究「死刑配套措施」。由於麻州有可能恢復死刑,但近年來美國的死刑制度卻也被揭露有諸多問題,因此這個研究委員會的主旨,是探討:如果麻州要恢復死刑,該有什麼樣的制度設計來配合?
Romney州長的目標有二:第一,在實體上,死刑應該限縮於某些子類型的「一級謀殺」行為,已確保被處罰的謀殺行為與謀殺犯都一定是「至惡中的最惡」(worst of the worst) 。第二,在程序上,應以科學證明方法,盡可能確保無辜之人(包括未犯罪者,以及罪不致死者)不會被判處死刑。
委員會的成員共有十一人,主要是由法界與鑑識科學人士組成。主席是印第安那大學法學院的Joseph L. Hoffmann教授與哈佛大學病理學系的Frederick R. Bieber教授擔任。其他包括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刑事警察實驗室主任等。李昌鈺也是其中一員。
研究委員會在2004年五月提出報告,內容中包括十點建議,認為這些制度是麻州恢復死刑的前提條件。這份報告也成為美國近年來討論「死刑改革」的重要文獻。
要怎樣才能實施一個較為公正的死刑制度呢?這十點建議分別為:
(一) 嚴格限縮得判死刑的謀殺行為類型(A Narrowly Defined List of Death-Eligible Murders)。
(二) 適度控制潛在死刑案件中,檢察官的起訴(求刑)裁量權(Appropriate Controls Over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
(三) 確保潛在死刑案件中,被告擁有高品質辯護律師的制度(A System to Ensure High-Quality Defense Representation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
(四) 以新審判程序避免同一陪審團審理兩階段死刑案審判程序所生的問題(New Trial Procedures to Avoi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se of the Same Jury for Both Stages of a Bifurcated Capital Trial)。
(五) 法官對陪審團以人證定罪應為特別之指示(Special Jury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Human Evidence to Establish the Defendant’s Guilt)。
(六) 應有科學證據支持被告之犯罪(A Requirement of Scientific Evidence to Corroborate the Defendant’s Guilt)。
(七) 提高證明標準以提升陪審團的決定正確性(A Heightened Burden of Proof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Jury Decision-Making)。
(八) 對於科學證據的蒐集、分析與呈現,進行獨立的科學審查(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view of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九) 賦予事實審法院與上訴法院撤銷錯誤死刑判決的廣泛權限(Broad Authority for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 to Set Aside Wrongful Death Sentences)。
(十) 創設一個死刑審查委員會以審查有關實體錯誤的申訴案件並研究此等錯誤之原因(The Creation of a Death-Penalty Review Commission to Review Claims of Substantive Error and Study the Causes of Such Error)。
簡單介紹一下這十點建議。
(一) 嚴格限縮得判死刑的謀殺行為類型(A Narrowly Defined List of Death-Eligible Murders)。
研究報告挑出六種「得判死刑」的一級謀殺:基於政治恐怖主義而為之謀殺、意圖妨害司法的一級謀殺(例如,謀殺對己不利的證人)、刻意折磨被害人的謀殺、一次殺害多人的謀殺、多次殺害多人的謀殺,以及已被判決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而服刑中所為之謀殺。這些可謂「至惡中的最惡」,且除死刑外別無其他有威嚇力的刑罰。
研究報告嚴格限縮得判死刑之謀殺行為類型,也是為了減少種族或階級歧視。美國的死刑被抨擊的原因之一,常常在於它「執行上」的不公平—同樣或相似的罪行中,黑人、窮人特別容易被判死刑。研究報告則認為,嚴格限縮死刑的範圍,減少檢察官、陪審團與法官的裁量,是一個重要的步驟。試想,如果條文僅曰「一級謀殺得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麼在這個種族主義充斥的國家,往往被判死刑的人不見得是「最惡質的謀殺者」,而是「黑膚色的謀殺者」。
但若法律條文已經將「最惡」的謀殺類型具體挑出,就可以減少這個問題—不要全讓有偏見的司法人員與陪審團決定「誰是最壞的」。
(二) 適度控制潛在死刑案件中,檢察官的起訴(求刑)裁量權(Appropriate Controls Over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
這個建議與美國特殊的檢察官制度有密切關聯,但對我國也有啟發餘地。
麻州(與美國多數州相似)的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以及各地的檢察長(District Attorney)均為民選,且在追訴、求刑上均有相當大的裁量權。這種向各地方選民負責的追訴裁量,可以依據地方觀念,修正、微調刑法的解釋與適用,是美國的重要傳統。
可是,也正在這樣的制度下,同樣的罪行可能在不同地方被求處不同的刑度。民選的檢察長在治安的壓力下,就可能(不必要地)求處死刑,以塑造「對罪犯絕不手軟」的形象。
為了克制濫行求處死刑的實務,研究報告建議,一方面採取「由下而上」的策略,由各地檢察長簽署協議,統合協調「求處死刑」的標準;另一方面則由州檢察總長實質審查每一個求處死刑的起訴案。
(三) 確保潛在死刑案件中,被告擁有高品質辯護律師的制度(A System to Ensure High-Quality Defense Representation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
美國憲法與判例承認,政府有義務提供貧窮被告辯護律師。理論上,涉及死刑案件的被告,在人命關天的情況下,應該有最優質、認真的律師來辯護。但事實上相反,鮮少有優秀律師(即使是法院指派的)會全力為死刑犯辯護。死刑犯的辯護律師素質通常是很差的。
研究報告因此建議麻州最高法院應該要訂定標準,並且列出合格的「死刑案件辯護律師名單」。這些標準相當嚴格,包括(但不限於):刑事案件的辯護經驗、處理科學證據的經驗、受過挑戰人證的訓練、受過處理證人偏見的訓練等等。唯有符合這些標準,才有資格列在名單內為死刑犯辯護。
研究報告也同意,短期內可能根本湊不出足夠的名單。但這是恢復死刑必須要做的準備,即便因此暫時無法求處死刑也在所不惜。
(四) 以新審判程序避免同一陪審團審理兩階段死刑案審判程序所生的問題(New Trial Procedures to Avoi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se of the Same Jury for Both Stages of a Bifurcated Capital Trial)。
死刑的審判程序通常分成兩階段:(1)有罪與否的審判,以及(2)是否判處死刑的審判。被告若在第一階段被定罪(確實符合構成要件),仍可在第二階段爭論其是否有足以判處死刑之事由(是否有悔改實據...)。
但若兩階段均由同一批陪審員擔任,很可能會傷害被告憲法上的辯護權—第一階段努力「否認犯罪」,第二階段就很難期待陪審員「從寬量刑」。因此研究報告建議,被告有權在第二階段要求由新的陪審團審理。以避免第一階段的印象影響其量刑。
(五) 法官對陪審團以人證定罪應為特別之指示(Special Jury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Human Evidence to Establish the Defendant’s Guilt)。
許多謀殺罪都是由於他人的自白或目擊證人而判定。但這些人證從鑑識科學來說,是非常不可靠的。法官對於某些類型的人證,應該要指示陪審團特別謹慎判斷,因為它們的可靠度十分可疑。例如:
(1)目擊證人,尤其是在熱門案件—即便證人本身的可信度無可置疑,仍然需謹慎而不宜太過信賴。
(2)跨種族的目擊證人(如:白人目擊黑人殺人)特別不可靠。
(3)在警方拘禁中之被告所為的證詞,未必可靠,必須更加謹慎判斷。
(4)在警方拘禁中之被告所為證詞,而無同步錄音或錄影紀錄者,應該存疑。
(5)共同被告或線人所為之陳述,特別是在他們與檢警有某種利益交換(如:作證交換檢型)時,應特別謹慎。
(六)應有科學證據支持被告之犯罪(A Requirement of Scientific Evidence to Corroborate the Defendant’s Guilt)。
要判處死刑,必須有確定性與可靠性相當高的科學證據(須為physical or associative evidence),能夠連結被告與犯罪現場、凶器,或屍體等。例如,DNA、指紋、錄音或錄影、彈道比對、鞋印、輪胎印等。
無此等客觀科學證據,不得判處死刑。
(七) 提高證明標準以提升陪審團的決定正確性(A Heightened Burden of Proof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Jury Decision-Making)。
眾所周知,刑事案件定罪的證明標準,是「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這已經是相當高的標準。但研究報告建議,在死刑案的量刑階段,必須要到達更高級的「無疑」(no doubt)才能夠判處死刑。陪審團必須對被告之罪行已無任何殘存的懷疑(residual or lingering doubt),方可判處死刑。否則頂多只能判處無期徒刑。
(八) 對於科學證據的蒐集、分析與呈現,進行獨立的科學審查(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view of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研究報告建議,麻州最高法院應該發展出一套規則,建立一個委員會來認證麻州乃至全國的鑑識單位。並且在被告判處死刑後,由委員會指派一個小組來檢驗系爭案件的科學證據是否充分足夠。這個小組與委員會的成員,不能是刑事警察局或其他政府的人員。
(九) 賦予事實審法院與上訴法院撤銷錯誤死刑判決的廣泛權限(Broad Authority for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 to Set Aside Wrongful Death Sentences)。
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陪審團所做的評決(verdict),以及一審法院所為的判決,原則上都會受到尊重。事實審法官只有在極為例外的情況,才會推翻陪審團的決定。上級審更只有在事實審的認定「明顯錯誤」時,才會撤銷判決。審查法官基本上不能以「見解不同」而撤銷陪審團或事實審的事實認定。
但研究報告建議,在死刑案中,法官對陪審團決定的審查權,以及上級法院對事實審法院的審查權,均應擴張。只要審查法官「自己認為」陪審團或下級判決有誤,就可以逕行予以撤銷。
(十) 創設一個死刑審查委員會以審查有關實體錯誤的申訴案件並研究此等錯誤之原因(The Creation of a Death-Penalty Review Commission to Review Claims of Substantive Error and Study the Causes of Such Error)。
最後,研究報告建議仿效英國與其他國家,設置一個在司法程序之外的審查委員會,專門調查死刑案件的可能錯誤。如果調查出問題,委員會有權將案件交由司法機關重審。

坦白說,如果真的要嚴格依據這個報告的建議,要恢復死刑是很困難的。但這份報告確實是針對美國的死刑實務具體問題,所提出的改革。它不只處理了死刑,其實也碰觸了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過份依賴人證、輿論與情緒影響檢方及法院、科學證據不足等)。不過「從死刑案開始」修正刑事訴訟制度,誰曰不宜?
換另一個角度,在死刑案件中,主張如此高度的證據標準與鑑定程序,又有誰能反對?
研究報告也指出,他們就是要提出一套「多層次審查」(multi-layered review),使得「死刑案」的成立特別嚴謹,也特別困難。這實際上當然有一個誘因引導效果:減少檢察官求處死刑的動機。在這套機制下,普通的一級謀殺,可以照正常的程序跑。但只要檢察官以得判死刑的重罪起訴,又求處死刑,那麼又要州檢察總長審查,又要遵守各管轄區的協定、又要特別高素質的辯護人、又要兩階段不同的陪審團、人證方面會被特別挑剔、科學證據的舉證責任提高、證明標準變成幾乎不可能成功的「無疑」、科學證據要被獨立檢驗、評決與判決被撤銷的可能性提高,甚至還有司法外的審查委員會來攪局...沒有強烈的把握與必要,檢察官是不會求處死刑的。
回到蘇案與我國的司法改革以及死刑廢除運動,我認為這份研究報告提醒我們: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到底有沒有資格判人死刑?雖然我們是由職業法官而非沒法律知識的陪審團裁判,但職業法官(與檢察官)是因此更加公正客觀,還是反而更帶有職業偏見—被告幾乎都是有罪的?蘇案的法官們都敢說檢警的證據已經無懈可擊到「超越合理懷疑」甚或「無疑」了嗎?系爭的「科學」證據與被告有什麼「關聯」?該被質疑的「共同被告自白」是不反而被賦予過高的評價?
如果前述研究報告的建議,我們通統做不到,真的有資格將人處死嗎?如果真是如此,那刑事訴訟與憲法正當程序所要求的什麼無罪推定、有效充分辯護權等原則,還有什麼意義?
第二,廢除死刑運動除了道德與價值層次的辯論外,也應該有務實策略的途徑。Hoffmann教授除了在這份報告擔任主席外,也在伊利諾州等地參與「死刑改革」。他不去挑戰「該有死刑」這個前提,但強烈質疑現行制度下的死刑,會有多麼惡劣的效果!(這也是美國近十年來一波批評死刑浪潮的主要論述)
事實上,死刑往往成為一個「信仰」問題。「國家是否有權殺人」或「壞人是否該死」,對於不同立場的人來說,是很難妥協的。台灣與美國同樣民粹,少數人權主張者的菁英主義不容易貫徹,因此「發展一套不冤枉人的死刑(或刑事訴訟)制度」,是不是會更務實?
誠如報告中所云,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寧可選擇「錯放」而非「錯殺」(如果不能百分之百「毋枉毋縱」,而一定會有錯誤)。從這個角度來看,強化審理程序的精確,誰能拒絕?我們的司法人員,如果有機會瞧瞧這份報告,是否也可自己反思一下自己敢不敢在現行制度下判人死刑?
第三,台灣在討論死刑或是刑事訴訟專業問題時,刑法或法律圈的人參與太多,鑑識科學的意見太少。麻州的這份報告中,鑑識科學與法界約各佔一半,法律學者更是只有一人。這樣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訴訟過程中的「證據認定」問題有多麼嚴重。
當然,這也許跟我國欠缺官方以外的刑事鑑識單位有關。美國可以找出一拖拉庫的鑑識實驗室或研究單位,並在某些案例(通常也是有錢的被告...)與官方對抗並找出官方證據之不足。但我國動輒說「要相信刑事局」...被告為什麼該相信刑事警察局的鑑識?事實上,如果依照前述的研究報告,「欠缺獨立於刑事局以外的鑑識單位以進行獨立審查」的事實本身,恐怕就構成「不可判處死刑」的前提了。
無罪推定在台灣其實還是很遙遠的。即使是「優秀公正」的刑庭法官,在證據模糊不清時,往往還要繼續調查,而不是逕行判決無罪。像蘇案法官這樣公然說「找不到無罪的理由,所以判處有罪」的,恐怕也多有所在。
如果法官一直這麼幹,那檢警也就永遠會這樣辦案。
妳我隨時都可能是檢警院聯手打擊的犧牲者...因為沒有任何有效的制衡與「多層」審查。
**********
以上麻州的死刑研究報告,可以在
http://www.law.indiana.edu/ilj/volumes/v80/no1/report.pdf 下載全文。
印第安那大學法學院以這份研究為主軸,辦了一場研討會(
http://www.law.indiana.edu/ilj/volumes/v80/no1/index.shtml),論文收錄於Indiana Law Journal,全文pdf檔可於
http://www.law.indiana.edu/ilj/volumes/v80/no1/80_01.pdf 下載。
該報告的主席Hoffmann教授,是我的口試委員之一,也是成大李佳玟教授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今年九月將應政大邀請,來台參加法學教育改革的研討會,或許屆時也可以邀請他順便就這份研究發表意見。

補充:
哈佛大學政府學院的Sheila Jasanoff教授撰寫了一篇論文「正義的證據:科學在法律程序中的侷限」(”Just Evidence: 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the Legal Process”),針對「科學可以確保死刑正確性」的前提,以科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批判。
這篇論文不只適用在死刑,也可以用來挑戰所有「科學(技)萬能」的迷思。特別是在法律方面。「科學」所要求的「真實」,與「法律」所期待的「真實」往往會有落差。而且,人類行為永遠牽涉在科技與法律的適用上。從而,先進的科學未必能夠真正解決法律上的問題;有時反而造成問題。(例如,指紋曾經是最好、最科學的證據,於是最熱心的警探遂積極地偽造指紋)
這篇論文刊登在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summer 2006。我手頭有PDF檔案,有興趣而又找不到原文者,歡迎來信。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6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6
「起訴狀一本」主張不應將檢察官所偵查全部訊息提供法院,致使法官受起訴卷證影響,形成有罪預斷,但此與「證據開示」防止突襲審判要求有違,不利於被告律師訴訟防禦權之行使,因檢察官於窮盡一切力量以單方之強勢處分所取得證據資料,應能同樣使被告得以充分獲得被訴相關資訊及所訴是否有理,足以充分提出防禦,如此亦得使檢察官面對律師挑戰而可以加強充實其控訴證據內容及理由,以保障被告人權不受匆促起訴而受到侵害。為防止法院產生預斷,應是陪審團而不是法官,陪審團應該是維持客觀不受起訴卷證資料影響下,完全以法庭內所見所聞提供其心證供法院審判參考。
被告屬於證據方法之一,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告設有保護措施,但卻容忍可以使用傳聞證據,違反直接審理主義。刑事訴訟法對於傳聞證據例外可採為證據之情形過於寬鬆,實影響當事人有受法院正確判斷之正當法律程序。無異使偵查庭取代了審判庭一切作為。因此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規定所有被告自白均不得作為證據,審判庭必須充分告知被告接受訊問之法律上權利,並經法庭上詰問程序,始能成為法院論罪證據,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使檢察官拋棄只要自白,不要其他證據可能。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5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5
引入陪審制必須注意事項:
陪審團成員所需具備資格條件,不僅社會形像要清新,操守必須純正廉潔,思慮必須冷靜理性,且擁有高度社會公信力,才能確保客觀及專業要求。人數必需多而普遍,並且來至各階層,平時即要有法律上基本訓練,遇到案件馬上就可勝任工作。
陪審團遴選及運作,必須嚴守秘密原則,選擇參與個案人員須秘密,通知時要秘密,表決時更要秘密。選擇必須有妥適抽樣法則,抽樣結果應有保密措施,參與案件內容必須保密,除了到庭時間、連絡人及電話外,其餘均不須記載以確保秘密不洩漏,出庭之日法院才告訴庭別。表決時要保密,不得討論,正反意見必須保密並陳,供法官評議參考,判決理由由法官評議提出。
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之人數不到二分之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法院應為無罪之認定(仍有合理懷疑),陪審團一致認定被告有罪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法院應為有罪之認定(已超越合理懷疑)。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之人數超過到二分之一,但非一致認定被告有罪,其有罪無罪,由法院本於確信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認定之(雖達二分之一以上,但法院綜合一切情況,顯然證據證明力不足以認定有罪,利益應歸於被告)。法官指揮訴訟進行,應時時提醒陪審團法律對於證據之規定,雙方當事人對於他方違反法律規定,應提出於法庭,由法官裁定,不適宜作為證據者應於準備程序時即應排除以免影響陪審團心證。法官對於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之人數不到二分之一或一致認定被告有罪者,得不提出此部分之判決理由。上級審對於下級審,及陪審團之有罪無罪認定得依法律予以審查。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4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4
為建立第一審堅強事實審不妨引入陪審制,陪審制優點為具客觀性免以專斷,缺點是專業性不足,容易誤斷,又台灣民情具有濃厚道德意識,有過度道德化風險。
故引入陪審制必須限制在下列條件下:
1.限於刑事案件。
2.限於最輕本刑10年以上案件。
3.應屬輔助法官認定事實,而非取代法官認定事實職權。
4.在充實法官對於依「經驗法則」認定事實,得以形成正確「自由心證」。
5.第二審對於陪審團在「經驗法則」認定上,在特定情形下得有審查餘地(例如:人員組成適當與否……)。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3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3
因此凡是當事人上訴第三審應該具體指出「過去」法院已作成未成為判例之判決(不論哪一審級,只要未經修法變更者皆適用)意見或第二審判決如何違背判例(判例得由第三審內部修正或透過大法官解釋),敘明第二審判決如何不適當,如何判決才是正確法律見解,由第三審作正確判斷,未指出「過去」法院已作成未成為判例之判決或第二審判決如何違背判例,即不應受理。至於純屬法律上不同意見,而事實認定無誤,應由第三審發回第二審針對法律意見上審查。如果關於事實認定之法律見解不同,因涉及事實正確發現,由被告向第三審提出上訴(即第二審認定第一審判決被告有罪為正確)為有理由,應該由第三審(代替第二審)發交第一審法院重新審理。如果關於事實認定之法律見解不同,因涉及事實正確發現,由檢察官向第三審提出上訴(即第二審認定第一審判決被告無罪為正確)為有理由,應該由第三審(代替第二審)發交第一審法院重新審理。第三審對於同一上訴案件有不同法律見解,應交由內部所成立審查單位對不同見解做出統一解釋,得成為「判例」者應對外公布,變更時亦同。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2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2
如何做到使案件不流轉於法院,如何使不成熟或顯然不能成罪或證據不足或證據取得違法等各種缺失,檔在法院外,如果已進入法院也可以迅速回歸檢察機關。法院並非不辦事,而是辦他應該辦的事,不進入法院或使案件快速回到檢察單位,並非審判機關推卸責任,而是使檢察單位更堅實做好本身份內工作,確實讓檢察單位認為追訴犯罪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權利,念茲在茲應該是使真正犯罪的人繩之於法,使無辜的人可免於受國家機關對人權無端侵犯所受的恐懼。所以應該把「事實」認定階段放在一審,事實不明或違反嚴格證據法則之案件根本不能進入法院,或進入法院則可以盡速回到檢察機關調查清楚後再進入法院。法院甚至於第二審不該成為事實實質調查及補充證據的「附屬機關」,應該回歸到負行政責任之檢察機關,不應再作補充調查工作,而應該是檢驗檢察機關所提出證據,法院調查範圍只能在當事人所提出內容(被告的權益應該由國家另成立之扶助單位擔任,而不是法院本身,法扶單位建全屬於另一課題)。現行案件在二審及三審間反覆流轉,原則上都是在法院內,而沒有回到偵查機關,所以訴訟資料都是一些已經被炒爛的內容,如果依此發現真實,實無法冀望在二、三審間反覆論證而發現真實,直言之,是緣木求魚。因此要擺脫存在法院間流轉而應回到偵查機關,就要加強第一審事實認定,而且是採取嚴格證據法則,而二審應該做的事不是事實重新或補充調查,因為由二審就事實重新或補充調查只會更加混淆事實無法釐清事實,二審應該做現階段三審的事,而且應該將重點工作放在檢驗一審及檢察機關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法則相關章節規定,而三審工作重點應該是「統一法令見解」,使一般大眾知道法令正確意涵才可以有效規範眾人行為,不致違反法令或得以正確無誤知道國家法令處罰界線。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1
論建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1
民國88年3月29日司法院為加速司法改革,對外公佈司法再造藍圖構思將目前刑事第二審之覆審制改為其他諸如事後審制或續審制,而在一審則建立堅強事實審,冀求解決現階段最大司法問題在於證據取得不足或違失,而妨礙事實發現,導致案件流轉法院而無法了結。所以為解決案件流轉於法院,對於不成熟或顯然不能成罪或證據不足或證據取得違法等各種缺失,就檔在法院外,如果已進入法院也可以迅速回歸檢察機關,使其補充、矯正、充實證據後再進入法院,俾使證據不因「時間因素」更加混沌不清。觀察現行司法運作狀況,因輕易讓不成熟案件在法院流轉,甚至將「審判機關」當成「檢察機關」行「調查」實質責任,完全違背法令或法令自相矛盾,將二機關職權完全混淆,混淆結果「審判機關」變成「檢察機關」之待罪羔羊,備受人民指責,且使法院疲於奔命,無法實現正義。就蘇案來說顯然「審判機關」認為不成立犯罪有相當疑慮,但「檢察機關」根本沒有辦法提供足夠證據足以超越合理懷疑,使得「審判機關」得於正確無誤作成最後判斷,就在有疑中又不能輕縱作用下造成今日結果。嚴格的說蘇案三人當年是否幹了不該幹的事,就法論法,沒有足夠證據就該判定無罪,法院根本不應該有其他選擇,無需把縱放責任背在身上,要論責任應該對於檢警當時在偵查時為何草率到無法讓法院作最正確判斷。因為迷信「自白」所以輕忽其他證據充分取得,以為只要不計一切方法取得「自白」即可大功告成,殊不知為此發生多少冤錯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檢察官負犯罪舉證責任且須提出證明之方法,但同法第163條第2項又認為法院在特定情況下,「應」調查證據,於是把「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權責完成又混淆了,於是第二審變成續行調查單位,而忘了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檢察官的責任,最後「審判機關」承受所有責難,在被害人及嫌疑人間沉重壓力下成為無法解脫夢饜。審判機關是否要承受調查責任,就調查資源及調查受到法令限制之「靈活度」,根本無法做好調查的工作,有的只是他人卸責管道,刑事訴訟法既然已把職權主義改為(改良式)當事人主義,還遺留一個尾巴,認為審判機關還在作追訴犯罪工作而不是一個「仲裁者」。追訴犯罪應該是行政機關的事,要受民意監督和檢驗,法院應該是一個純正中立,依據法律公正裁判的仲裁者,如此才能為全民所信賴。
 補充回復平心而論
補充回復平心而論
...如一審檢察官決定不再上訴或重新起訴,而二審檢察官卻決定上訴,為二審判決為無罪,二審檢察官就要被「扣分」,以此類推
修正為
如一審檢察官決定不再上訴或重新起訴,而二審檢察官卻決定上訴,為二審判決為無罪,二審檢察官經檢討如認為應上訴第三審,應作成意見書,由三審檢察官上訴,三審檢察官同意上訴,上訴為三審法院駁回,就要被「扣分」,以此類推
 回復平心而論
回復平心而論
立法院通過了刑事妥速審判法對於法院反覆發回更審發揮了一些改善功能可謂立意良善,不過刑事政策除必須注意人權維護外,仍然必須顧及到刑事政策為維持社會正義之目的,二者不可偏廢
當然期待一個在不正確起訴之前提下要法院作出正確判斷乃緣木求魚的事情
因此如何維持正義必須從檢察機關上落實,亦就是說檢察機關必須作正確起訴,換言之,就是要讓檢察官找到對的人起訴,有這樣的前提下,才能使法院做到正確判斷,設若檢察官起訴錯了人,送到法院又無法正確而即速作成無罪正確判斷,除不斷使案件在二審及三審間擺盪外,錯失找到該起訴的人,不但無法維持正義,將使無辜之人不斷受到不確定訴訟程序所帶來煎熬
因此刑事案件首重一審程序,當一審判決判斷當事人無罪時,應有讓檢察機關反省及調整偵查'起訴或上訴之制度設計餘地,使舉證不足或起訴錯誤...等等缺失在一審時就檔在檢察機關內部,等檢察機關做過檢討補充證據...等等措施後仍採相同看法時.才能往二審方向前進,以確保真正起訴對人,也才能維持正義,不致於冤枉情事發生,否則經過冗長訴訟程序後發現錯誤,再回頭將使真正該受處罰之人逍遙法外,徒使寶貴司法資源浪費卻達不到效果,更造成社會依亂,導致司法不受信任
檢察機關在收到一審判決無罪判決後,應該讓一審檢察機關自我反省,如認為一審審判正確或證據不夠充足或根本被告另有其人,可以給予二個月或更久補充偵查之制度設計,再決定上訴或重新起訴
如經反省決定上訴或重新起訴(該起訴之人另有他人)應提出意見書送二審檢察機關上訴或不上訴二審法院,二審檢察機關亦可不同意一審檢察機關意見,敘明理由發回一審檢察機關補充偵查或不上訴
為使檢察機關能正視維護正義及人權保障作出正確抉擇,應該結合「計分」及自我反省制度,在一審檢察官送交二審檢察機關上訴,如經二審審查同意上訴,二審檢察官上訴後遭無罪判決一審檢察官就要被「扣分」,反之,一審檢察官即可得到「計分」,如一審檢察官決定不再上訴或重新起訴,而二審檢察官卻決定上訴,為二審判決為無罪,二審檢察官就要被「扣分」,以此類推
在一審檢察官送交二審檢察機關上訴,如二審檢查官審查不同意上訴,該案件即終止或由一審法院另行偵查將真正該起訴之人重新起訴,自不待言
這樣制度推行將可以確保無罪案件進入二,三審,使司法可以達到其真正之功能
 chienwen
chienwen
請問一下最近關於死刑的探討有無新論點來支持台灣廢除死刑,另外可以提供近期關於死刑廢止法律上論證的書籍嗎?中英文皆可
 平心而論
平心而論
3.起訴,但被告經一審判決無罪,僅扣除原「加點」但不「扣點」
修正為
起訴,但被告經一審判決無罪,檢察官不上訴,僅扣除原「加點」但不「扣點」
 平心而論
平心而論
美國的刑事訴訟審判,一審若判無罪,檢察官是不得上訴的。(若判有罪,被告可上訴)而在事實審階段,陪審團若評決無罪,法官也不得推翻(如果評決有罪,而證據明顯不足,法官可以推翻)。
檢察官可以針對無罪或量刑較輕的判決上訴,請求法院判決有罪或是請求更重的刑,是我國訴訟拖延的原因之一。這使得審級制度」不再是一種「救濟」,而是一種折磨。
如果檢察官也來「記點」的話是不是也能有所改善
1.不起訴處分,不加點亦不扣點
2.起訴,加點,但最終判無罪不但原「加點」要扣除,並且要「扣點」
3.起訴,但被告經一審判決無罪,僅扣除原「加點」但不「扣點」
 平心而論
平心而論
對於蘇案而言,不僅要從訴訟制度上改革,更要從人方面來革新。訴訟制度之改革,諸如:強化嚴格證據主義,實行改良式當事人主義,以及採無罪推定等訴訟制度改革已有一定成效。制度改革雖然重要,在相對程度上易較容易,惟制度必須有人施行,故而對人制度的改革恐怕更是重要。司改會長期推動法官法立法工程,也就是對於法官如何產生及如何評鑑,甚至於如何淘汰不適任法官,均有其獨到見解。但是對於人的改革則涉及到一些司法基本核心問題,必須慎思明辨,並非可一蹴可得。司法一方面要達到客觀公正可受公評,故必須獨立不受任何干涉,否則受到外力干涉與控制將淪為政治打手,無法主持正義;另一方面因為獨立自主,又不得不有所監督,否則流於恣意為之,勢必成為怪獸。司法之所以難以處理人的問題就在於前述涉及司法「獨立」與「監督」二難問題上。如何使司法受到監督,而不影響到司法所不可逾越價值-獨立,在分寸拿捏上,必須恰到好處,否則不但無法發揮監督作用,更可能喪失司法最重要價值,一但司法核心崩潰,其弊害可謂無窮。觀司改會之法官法對於法官監督,其嚴格之程度更甚於一般公務員,重重評鑑之監督體制,似乎一心想讓司法脫胎換骨,但可知道司法本身是在做排難解紛,維持正義工作,所以必須有一支判斷是非曲直的尺,而論斷評鑑法官功過是非正是在評判這把尺,問題是誰的尺才是符合標準符合正義的尺,在論斷評鑑法官的同時,如何認定評鑑諸君的尺更值得信賴,因此評鑑諸君本身恐怕也是最應該被評鑑對象,換言之,監督標準應該是什麼?又是誰來定這把尺,而敢說他的最準。因此必須注意過度監督稍有不慎就可能變成一言堂。
現行司法制度採用審級監督,雖不盡使人人滿意,但至少可維持一定程度可接受之公平運作,在獨立與監督的二難中獲的一些必要平衡。例如:不斷發回重審對於當事人身心折磨不可謂不大,但對於「一試定江山」所帶來罔判對於當事人侵害有一定矯正作用,使不當判決有機會可以獲得糾正。當前改革方向敝人的建議是:
1. 減少人為干預:因為誰也無法做上帝,只有對於事理充分論證,用說理方式接受監督,不應該由一堆人靠表決來做任何決定。人為干預意味著靠人之主觀感覺,來對人作任何判斷和決定,包括薪級、升遷、獎懲及考績…….等。
2. 強化審級監督:對於審判品質監督,被發回重審情形越少,意味著審判品質越好,如何能使法官被發回重審機率越低就是最好監督,因此是否可考慮採用「記點」方式來監督。每一個法官有基本點數,而點數代表薪俸,被發回重審情形越多「扣點」越多,代表給予越少;相反的被發回重審情形越少「加點」越多代表給予越多。不同案件難易為示公平可給予不同點數。
3. 為避免見解上不同,上述扣點可以採用最終確定判決來作處理,換言之,被發回更審者如與最終判決之結論相同則加點,如不同則扣點。
4. 同樣的「結案時間」亦可採用上述相同監督,惟一般而言,因最終判決有一段時差,判決品質驗證需要一段時間,但平常之時可以把監督落在結案時間上。惟應注意審判品質與結案時間之間,必須取得一個合理平衡點。
5. 施行監督可能結果,各級法院為能減少發回機率,必將統一共同見解,而此統一共同見解其最大公約數將會確實落在法律正確適用上。
6. 最高法院為最終監督者,而其成員可從歷年獲得點數最多之法官上遴任。
 phil6dog
phil6dog
《 正義的證據:科學在法律程序上的限制 》
Sheila Jasanoff, J.D., Ph.D. 作
〔依靠科學,Romney推動死刑法案〕。這是ㄧ家媒體在2005.4.28的頭條新聞。它報導麻塞諸塞州長Mitt Romney正尋求立法恢復,1984該州最高法院已裁判違憲的死刑制度。其內文明顯表示,科學無疑是州長這一舉措的主要基礎,並引述州長的話〔(這法案)在當今的科學時代,為死刑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標準〕。Romney另稱〔科學不僅能證明人無辜,也能證明人有罪〕。我之後將探討這句話引起的相對性問題。該法案要求科學提出確切的科學證據、多層次的查對方法、無可質疑的新標準去檢驗證據。除了嚴格證據的標準、限縮死刑的範圍,法案還要糾正其它死刑法令的缺失。Romney向媒體談到〔我希望(麻州立法者)看了這法案後,會說“沒錯,它已排除別州死刑法令的主要缺失”。這缺失當然就是無辜者可能被判處死刑。(他加強語調)我們排除這可能性了〕。多數媒體以頭條報導這法案,並說明科學是影響Romny的主要因素,也引述其渴望證據能無可辯駁、確鑿無誤的言談。
州長想完美化死刑制度的理念,反映了當今社會認為,科學能提出無錯誤、由是正義又合法的成果,來補足法律或有的缺失。這理念因此也基於大眾普遍相信,科學界自我糾正錯誤的能力,遠比其它社會體系有效。著名的美國科學社會學家Robert K. Merton於其1942的文章說明,〔組織性的懷疑論〕為科學界的一個特殊規範。科學家以此懷疑論相互檢視;研究成果須符合共同協商過的真實與客觀性標準,才會被大家接受。他解說科學界必需追求高標準的精確度,因為科學家須以同儕的研究當成自己工作的依據。所以在科學家宣佈其研究係可靠、可複製之時,已負擔了集體性的風險。Merton視〔組織性的懷疑論〕,與〔自主自治性〕、〔普遍適用性〕、〔公正無私性〕,為科學界的四大指導準則。
然而,在科學被用於法律目的時,前述準則不必然能實現。科學的脈絡被法律改變了,科學的成果因此不符合大眾原本的期望。法律自身有其需要與約束,主要是確保正義能在各案件裡實現。據此建立的法律程序,所以不必然能區分個別科學見解的良窳,也該重視卻不重視科學界自我糾正錯誤的努力。
美國最高法院1993企圖聚合科學與法律,讓科學專家的證據可以被聯邦法庭接受。在指標性的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案件中,最高法院認定審判法官事實上應作為科學界的代理人,採取科學家評估關聯性與可靠性的同樣標準,去決定某項科學證據可否接受。但情況快速明白的顯示,科學界內部自我糾正錯誤的程序,無法全盤複製在法律環境中。例如最高法院於General Electric Co. v. Joiner一案判決,審判法官對科學證據接受或否的裁定,只能被以濫用裁量權的理由提起上訴。這嚴格的上訴標準符合法律安定性的利益,卻阻隔科學界慣常的同儕懷疑論,不能進入法院。
於是,運用DNA檢測等科學證據在法庭上,有如要目標與規範皆大不相同的兩個體系聯合作業。在它們時起勃谿的相遇裡,兩者皆未完全保留或完全放棄其自主權。科學界無法以追求純科學目的之同樣方式為法律盡力;法律界寄望科學的權威見解,但在其尋求事實精確度之時,從不拋捨自己的核心價值。立法者盼望科學介入、解決法律的缺失,卻未考量雙方體系的機制不同,因此其成效被誇大了(例如,Romney聲稱他的法案能“排除”誤殺的可能性)。就此一點極至而言,將導出可疑的正義。
想建立一個更合理的法律與科學間的關係架構,要先瞭解科學並非以純事實或當今世界真理的形式進入法庭,而是作為證據。意即科學必須作成法庭能接受的某種論點、敘述或實質物件,讓法庭據以判斷何人較為可信。專家證人提出科學與技術上的證據,更應符合法律認知上的一些標準。例如,必須是有關聯的、必須能及時在法庭提出、必須是Daubert判例容許接受的。本文探討科學轉變為法庭證據時的一些爭點,而這也是科學在作為法律用途時,面臨的一些問題。本探討以DNA證據為分析的舉例,雖然它有很多法律依賴科學的意味。 #
 phil6dog
phil6dog
活該我將廖老師講的〔科學+法律〕,聯想到〔星艦迷航記+CSI犯罪現場〕去!
但基於推崇廖老師在學術的夙夜努力、對社會的熱情關懷,感謝他開闢此園地讓我遊玩開心、並懺悔自己小時候不讀書,我翻譯了該PDF的第一節...無怨無悔的。
只是想建請大家,下回當廖老師說“I bet you`ll like it.”時,審酌一下為何我打死不能說那花了多久時間。 #
 布魯斯
布魯斯
哈佛大學政府學院的Sheila Jasanoff教授撰寫了一篇論文「正義的證據:科學在法律程序中的侷限」("Just Evidence: 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the Legal Process"),針對「科學可以確保死刑正確性」的前提,以科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批判。
這篇論文不只適用在死刑,也可以用來挑戰所有「科學(技)萬能」的迷思。特別是在法律方面。「科學」所要求的「真實」,與「法律」所期待的「真實」往往會有落差。而且,人類行為永遠牽涉在科技與法律的適用上。從而,先進的科學未必能夠真正解決法律上的問題;有時反而造成問題。(例如,指紋曾經是最好、最科學的證據,於是最熱心的警探遂積極地偽造指紋)
這篇論文刊登在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summer 2006。我手頭有PDF檔案,有興趣而又找不到原文者,歡迎來信。
 phil6dog
phil6dog
無名氏:
冒昧我猜想您意旨為,
法官審判不應自限於只斟酌
[歷年來的原審判決及本件判決的訴訟資料]。
容或有誤。敬請指證! #
 無名氏
無名氏
如果歷年來的原審判決及本件判決就代表所有的訴訟資料,我想法官很容易當,不用每天喊著被卷壓著跑了...
 陌生人
陌生人
陌生人在此先道歉,之前的po文論及再審與非常上訴的問題,恐有誤導大眾之嫌,很明顯的,我的論述有誤,在非常上訴此點。
sorry~~~
 陌生人
陌生人
台長po出了由台大法律系黃榮堅教授與成大法律系李佳玟教授的合著文章,在此感謝。兩位教授都是刑事法學教授。謝謝廖教授的指出。
不過,我想說的是,我常常在想,刑事法學教授有啥用?我真的很懷疑,最近的例子,是許玉秀大法官再釋字617號鏗鏘有力的不同意見書,寫得真是好,但...那又如何?我個人的感覺是仍難撼動主流思想(這個主流可能是保守的,反動的),面對這群人,鏗鏘有力反倒像是狗吠火車。特別是,許大法官還是刑事法學領域裡的著名教授。
 現代俠盜
現代俠盜
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必須要相當。這是普世標準。
我們就用這個標準,來看看台灣的法官吧!
他的權利一個都沒有少。
他的義務就是給我們一個程序正當的審判。
他的權力很大。座位後面,有國旗,代表國家主權的行使。在法庭內,法官就是國王的使者。
他的責任就是確保這是一個程序正當的審判。
下棋時,也講究程序規則的正當,而且雙方當事人以及裁判都要遵守,這個相同的規則,不會因人而異。否則,這盤棋玩不下去。
裁判負責雙方照著規則玩下去。確保規則能嚴格的執行。
所以法官在程序上,是規則的奴隸。在規則面前,國王也要低頭。不能臨時改變規則,不能說不懂規則,不能有自己的心證,當然只要在座位上,就不能以任何理由來卸責、搪塞。
目前實務上,我們的狀況是,有審級救濟,所以程序上的重大瑕疵,制度允許,如果上級法院已補正,就沒事了。
下級法官就不用負此「失職」的責任。
那麼下級法官的權力與責任,是否相當,合乎標準。是否將會有持無恐,任意踐踏規則,而有權無責,此之謂也。
甚且,上級法院裝聾作啞,官官相護,不認錯,不補正。當事人又奈我何。還會有再審可以補正啊,一個賴一個,一個推一個,怎麼辦。
所以只要是重大程序瑕疵,只要有虧職守,任何法官(包括下級)就應交由外人議處。司法的公信力,自然提高。
這是各行各業的共同標準,核心責任,沒有逃避的理由,也沒有不受監督議處的權利。
為何法官的「程序正當」責任,可以由別人補正而免除(其實,當事人之審級利益已受損),並且不受懲處(包括行政監督)。有無過度保護,就是因為一句獨立審判嗎?
結論是任何人,大權力,大責任。失責,就要付代價,不能沒事。
 現代俠盜
現代俠盜
「此一連署並非是想要在實體上左右法院的判決,而是要求法院重視正當法律程序」終於打到關鍵問題了。
獨立審判的核心價值,是否及於「程序法」(當然不是)。大法官釋字228號,只提到人民要容忍,有審級救濟,也未區分「實體」、「程序」之差別,實在不該,有點為德不卒,不知是故意,還是沒想到。
「實體」有心證的問題,且牽涉廣,法官不一定顧慮周全,人民要容忍,我可以接受。「程序」硬碰硬,專屬法官專業領域,沒有容忍的空間。法官有程序違法,錯就是錯,就要直接嚴懲。
但制度上「實體」、「程序」混在一起。一句獨立審判,好像包括「實體」、「程序」,大家於是碰也不能碰。台灣沒有一條規則,談到法官程序違法,如何救濟或懲處,通通也是一句「審級救濟」,與實體攪和在一起。好像我們法官比上帝還厲害,永不犯「程序」的錯。要不,就是聖人,異於我們凡人,所以程序公正無比,絕對值得信賴。
本盜認為「審級救濟」,只限實體法。重大程序瑕疵,直接嚴懲,一定要與實體分開。如此,司法才是真正獨立,否則是假獨立、真濫權。
問題來了,法官太懂如何操作了,實體不能玩弄,就耍程序。有人抗議,就賴說「獨立審判」,他們永遠對。
本盜手上就有兩件指責法官違法案子,一件該受理,未受理。一件該言詞辯論,未言詞辯論。他們就是混在一起,打濫仗。真是不要臉極了。一件已告至監察院,看他們敢不敢動「法官」。
社會矚目,人命關天案子,尚且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注意,本盜閉著眼睛抽籤,正確率50%,成本很低。蘇案鬧了十幾年,花了這麼多的資源,正確率多少,不知道。
但我們要的就是相信這個法律程序正當,我們喜歡的就是這個調調,汝愛其羊,吾愛其禮。如今「正當法律程序」都遭到刑事法學教授公開質疑,大家還不生氣嗎。
好像台灣所有法律人也是吃稀飯的,沒人敢大聲罵出來。不敢面對此「程序濫權」的問題,有損驕傲似的。
愈說愈生氣,罵你們是「雞X」,看你們「法官」如何回嘴。
 月廬老人
月廬老人
TO 現代俠盜
我可能沒有全面地解釋大陸的司法現狀,因此兄弟對我的觀點可能有些誤解。
我說現在大陸死刑案件,法官會判得很謹慎,並不是說大陸的司法現狀讓人放心,也不說大陸現在的司法很公正。這不是一回事。
總是說來,大陸的司法人員的整體素質很低——當然我不排除上海、北京以及江蘇、廣東的個別的大城市可能司法人員的素質要比全國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多。但是,總體說來,大陸司法人員的素質很低。造成司法人員素質的原因很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十年前,司法機關仍然被當作是專政機關。國家並不重視司法人員的法律素養,而更重視地是要“聽話”,於是司法機關被當作從軍隊轉業下來的人員的就業安置所。這些人在進法院和檢察院前是幾乎一點都不懂法律的。2000年大陸每年舉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只有通過該考試的人員才能被任命為法官和檢察官。因此,從這一年以後,軍隊轉業下來的人員越來越不願意進法院和檢察院工作,因為參加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必須要有法律本科文憑,而且這個考試也很通過,軍隊轉業人員很難被任命為法官和檢察官。當然,大陸的法律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如果要被任命為法院副院長、院長,檢察院副檢察長、副檢察長,則不需要法律本科文憑,並且不需要通過司法考試。於是每年還是有一些在軍隊中級別較高的人員直接轉業到法院和檢察院當領導。
二是法官和檢察官的工資待遇很低,使得這兩個職業的社會地位也很低。同時也很容易誘發腐敗。
三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法院和檢察院雖然在憲法上與行政機關是平級的,但是事實上,法院和檢察院是被當作行政機關的下屬機關進行管理的。比如,臺北地方檢察署,在大陸,會被臺北市政府當作和臺北文化局一樣的部門進行管理,包括法院和檢察院人事權、法院和檢察院財政支出,都是政府掌控。法院和檢察院對於招錄工作人員、平時辦公經費的支出、人員工資的水準都是政府說了算。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我說現在大陸死刑案件,法官判得很謹慎,並等於大陸的司法現狀讓人放心,也不等於大陸現在的司法很公正。原因是:
之所以法官會判得很謹慎,是因為這兩年出現了好多死刑案件的錯案。當然這些錯案大多是十年前的。這十年,大陸的司法狀況進步非常快,用現在的眼光審視十年前的案件,就覺得當時判得太糊塗。全國對死刑案件的公正性一片質疑,於是法官寧願不判死刑,也不想承擔判錯的責任,就是判死刑也是更多地選擇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雖然也是死刑,但是罪犯只要在兩年內不再故意犯罪的,就會直接減刑為無期徒刑),於是造成求得法院的死刑判決現在很難。
法官不願判處死刑(當然暫不考慮死刑的存廢),並不意味著司法公正。應當判處的死刑,法官因為怕承擔責任而不判處死刑,其實也是一種瀆職行為。而且,現在的司法行為越來越趕時髦——不少西方國家視中國的死刑為野蠻的象徵,少判不判死刑自然會被蒙上司法理念先進的外衣,這種即不要承擔責任,又能趕上時髦,法官何樂而不為。這難道是司法公正?
 phil6dog
phil6dog
敬謝啦!大盜兄。
我想再說個看法。
死刑制度自始是/現在是/可見未來裡仍是
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當然也是一個復仇行為。
美國執行死刑應即本於此。
但基於[減少誤殺/降低復仇心態/增加人道色彩],
美國為執行死刑提供了種種[限制條件]。
這包括[繁瑣的程序/嚴格的辨證/長期的徒刑]。 #
 現代俠盜
現代俠盜
但問題一般不在司法追求的目標,
而在其手段過程。
這才是區別文明與否的關鍵重點。
phil6dog 兄的見解太好了。敬表同意。
兩岸的中國人(獨的朋友先別緊張,我指的是文化上),都有個共同毛病,喜歡談大道理,用大帽子壓人。
Hannah的發言已指出「死刑制度是能解決問題的方式,或只是一個復仇行為?美國為執行死刑提供了種種條件,能不能解釋成美國把死刑當成解決問題的方式?」,正巧,也談到此問題。
美國是實用主義國家,著重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老祖宗喜歡「禮教殺人」,所以那麼多人不分青紅皂白,贊成「死刑」。
大陸有「法官法」約束法官,但我不相信如「月庐老人」朋友所說的那麼好,那麼樂觀。黑幕重重,一句話,「悲慘」。
書本上與真實間的差別,太大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唉!海峽兩岸,都須要加油。
 月庐老人
月庐老人
很愿意为这一问题再听听你的意见。我再认真考虑一下,再向你请教。
 phil6dog
phil6dog
陌生人:
我是法律外行,
看了貴文,始驚覺本案可能超過我想像。
因為我很好奇,大法官能怎樣的去解釋/應對,
〔法務部長拒不簽署死刑案〕與〔總統拒不簽署法律案〕。
然而,以下二段的文意應有相當矛盾,我質疑。
-- 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管是再審或非常上訴,都不能暫停執行刑罰。
-- 死刑,應經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令准,於令到三日內執行之。但執行檢察官發見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內電請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再加審核 (刑事訴訟法#461)。 #
 phil6dog
phil6dog
月庐老人:
歡迎您!
我的看法是,
姑先不談司法為統治工具,及司法的手段過程,
起初它追求正義,以平反/報復為目標。
之後文明進步,其報復色彩漸低,甚且講究寬容了。
然而,追求正義/要求平反必須是司法永恆的目標,
其心態由報復趨近寬容,則是文明社會的必然走向。
但問題一般不在司法追求的目標,
而在其手段過程。
這才是區別文明與否的關鍵重點。
這就是本案最可悲嘆之處。 #
 貴仔
貴仔
首先
先感謝anarch幫忙改了錯字
想不到身為法律系還犯這種致命的錯誤= =”
針對anarch提出的疑問:
處罰犯罪者的同時讓「犯罪者擁有作為人的尊嚴」跟讓「無傷天害理的人擁有不受恐懼生活的權力」一定是矛盾、衝突,不能並存的嗎?
先做個說明。
因為自己的跳躍性思考,就直接把結果打上來了。
我的基礎是,可以判處置死刑的人,他的罪行絕對不是偷竊這種小事。她並定是否定了別人的權利,一個別人作為人的權利。當他自己已經先將別人否定了,我們卻仍為他辯護,說他的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用一個犯罪者自己否定的事情來為他辯護,說實在的,我自己覺得這時在是太有趣了。而平民百姓不受危險的威脅,當然也是有我自己的理由,試想一個組織的頭頭他背叛了終身監禁,而在那個國家裡,沒有死刑,最高的就是終身監禁。若我自己身為那個大哥,我會想盡辦法的逃出來,我不會讓自己永遠困在一個不見天地的牢籠裡。那麼,他的身存,永遠就是一個不定時炸彈。惟有一個沒有知覺沒有行為能力的”人”,我才能真正確定他的”存在”是不會威脅人的。因此,兩者比較之下,熟輕熟重呢?
至於
”一個人的權利與眾多人的權利到底孰輕孰重”
這問題,確實是需要許多的理論和現實狀況去論述。但用最基本的想法,現在損失一個生命法益和以後可能會失去更多生命法益來看。我會較偏向前者。
再次感謝anarch的指教,也讓我有個機會能闡述一下我的想法。
也請老師提供一下意見
 陌生人
陌生人
ps:從蘇案來看,審判機關的功能已經崩解,那麼我們也不能忘記蘇案前的他案被判處死刑且已執行以及蘇案後的他案被判處死刑且已執行與未執行者。審判機關的職責是判斷有罪與無罪,有罪者應該有何罪責(刑罰)。除了死刑以外,我們也不得不從蘇案中反省包括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有罪判決。
再者,未免落入司法尊嚴與人性尊嚴(生命)之爭,上述個人所言者,係指蘇案的一來一往,包括:
81.02.18/士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蘇建和等三人死刑
82.01.14/台灣高等法院維持死刑
82.04.29/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
83.03.16/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維持死刑
83.07.07/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
83.10.26/台灣高等法院更二審,維持死刑
84.02.09/最高法院自為判決,三人死刑確定
84.02.20/台灣高等法院駁回再審之聲請,檢察總長提第一次非常上訴
84.03.02/最高法院第一次駁回非常上訴
84.03.11/檢察總長第二次提非常上訴
84.04.12/最高法院第二次駁回非常上訴
84.05.28/法務部請最高檢提第三次非常上訴
84.07.05/最高檢第三次提非常上訴
84.08.17/最高法院第三次駁回非常上訴
84.12.30/台灣高等法院第二次駁回聲請再審
85.03.11/台灣高等法院舉行三死囚記者會
85.06.18/最高法院刑事庭舉行三死囚研討會,對外強調三死囚案確定判決及駁回三次非常上訴判決並無錯誤或違失
89.05.19/新總統就任前一日台灣高等法院以發現足以動搖確定判決的心證據為由裁定再審。
91.01.13/蘇建和三死囚無罪開釋。
96.06.29/台灣高等法院宣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
誰能說這一來一往司法的尊嚴(非法官的尊嚴,也不否定司法人員自己踐踏司法尊嚴)在本案已崩解?
最嚴重的,蘇案至今還沒了結~~~~
 陌生人
陌生人
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管是再審或非常上訴,都不能暫停執行刑罰,身為刑罰執行機關的法務部豈可不知?法部部長不願簽署死刑執行令早己顛覆了所謂的三審定讞;法部部長有沒有權力不簽署恐怕也有疑,如果法務部長可以決定刑罰執不執行恐怕是棄審判機關之建置於不顧,對於判決的確定力與執行力都是大大的打擊,結果是,法務部成為太上審判機關,因為就算是三審定讞的案子在蘇案看來就是尚未定讞,法務部忘記了他的角色是執行刑罰(可以不作為?)以及真認為案情未明也應該是例如請檢察總長申請非常上訴,但不要忘了,就算是非常上訴也不能暫停執行刑罰。
特別是,蘇案的一來一往,早已將司法的尊嚴踐踏的體無完膚,折磨了蘇建和三人,結果是,所有參與審判並判死刑的法官似乎通通都才是真正的罪人,我想,這是蘇案發展下來最荒誕不經的。
 月庐老人
月庐老人
在大陸,由於這幾年接連出現數起死刑判決被證明是錯誤的,使法院承受巨大的壓力。現在死刑案件證明標準很高,去年我們這兒一件搶劫作案五起致二人死亡的案件被判無罪。現在法官對於死刑案件,要求證據必須沒有一點矛盾,必須要有物證的證實,僅有人證,就不會判死刑,怕判錯了承擔責任。
我要請教的是,現在大陸主張廢除一切死刑的學者越來越多,在理論界已經是佔據主流觀念。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認為司法的追求是寬容,而不是報復。不知道您對這一問題是怎麼看的。
 anarch
anarch
個人一點小意見:
從樓上幾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覺的是有太多根本不一定矛盾的情境,被誤導成「非a即b」的對立。
怎麼會輕率問出「一個人的權利與眾多人的權利到底孰輕孰重?」(我改了一下錯字)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群體的利益可以這樣輕易、簡化地論斷衡量計算嗎?
處罰犯罪者的同時讓「犯罪者擁有作為人的尊嚴」跟讓「無傷天害理的人擁有不受恐懼生活的權力」一定是矛盾、衝突,不能並存的嗎?
何況,有哪些證據可以論斷蘇建和三人是「犯罪者」呢?
我更訝然有人會說出「就算當時判錯 ,都要比現在判對來的傷害來的小」這種冷血的話,按照這位eden的看法,當初判死,就應該下個了斷(執行?),以免對所謂司法造成污辱?
到底是司法虛假的尊嚴重要,還是三條被薄弱證據和刑求折磨,加上自由心證判死的人命重要?
 eden
eden
對蘇案個人見解
讓人生不如死 比判死刑還要嚴重
不管現在判無罪 或是死刑 對台灣的司法都是一種污辱 一個早就要下個了斷的事 一托在托讓很多變素都加進來了 這已經很難有一個對錯的分別
就算當時判錯 都要比現在判對來的傷害來的小
版主回應
這個案子對司法的確是一種污辱。
但改編一下周星馳的話:「司法尊嚴當然重要啦! 但有的時候,司法尊嚴...也是自己湊上來...丟的!!」
「抽象」的司法威信,比得上具體案件的人命關天嗎?Absolutely NO!!事實上,許多案件根本不涉及什麼制度尊嚴,而只是維護法院或司法人員的面子。「面子」重要嗎?套句米蘭昆德拉的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
 貴仔
貴仔
在我的認知裡,我覺得國家是用來保衛人民的。在有不同的利益衝突下,國家便可依此做一個適當的裁量。這也是我為什麼以為國家應該有判決死刑的權力。當一個反社會到了極端的人,他的存在其實是影響整體國民的安全。我知道老師是個專為人權伸張正義的人權律師,但我也不禁想請問老師,一個人的權力與眾多人的權利到底熟輕熟重?犯罪者擁有作為人的尊嚴,那無傷天害理的人,是否也應擁有不受恐懼生活的權力?
對於死刑犯的判決,自己也認為應該採行最嚴格的審核標準,畢竟一個人生命是無可取代的。但在一個國家裡,尤其是民主國家裡,一個過於民主,一個過於個人主義的國家裡,死刑,我覺得仍然是有必要的。
版主回應
"國家可依此做一個「適當的裁量」"......
其實憲政主義的前提,就是把某些事項移除於國家機器的政治權衡之外...有些底線是不可以拿來衡量的。
如果有這種底線,那「生命」不正是這種底線之一嗎?何況,一定要有「死刑」才能維護整體國民安全,讓國民不受恐懼生活嗎?「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如何?
先不否定死刑,但如果您也同意死刑「應該採行最嚴格的審核標準」,那麼蘇案實在很難通過「最嚴格的審核標準」。
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不同,它不是一個even的制度。相反地,它強烈要求由檢方證明被告有罪;而不是由被告證明自己有罪。法院的刑事審判,應該是「嚴格、挑剔地檢驗檢方證據」之處所。檢辯雙方如果打平,炸成一團讓人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罪,那就應該判無罪!
台灣有句話說「罪疑為輕」其實不對,應該是「疑則無罪」!
 現代俠盜
現代俠盜
蘇案又一次證明台灣法律不公義
我們對總統實質進攻,想罷免他,法律保障他,在任期內,只能一次。
我們對確定判決進攻,聲請再審,法律保障「法官」,同一事由,也只能一次。
為何?對被告進攻失敗,發回更審,法律卻沒有次數的限制。法律允許一再進攻,死而後已嗎?
是否總統,法官,血統純正,上帝特別眷顧。販夫走卒,賤如敝履,天生的壞痞子,不值得保護。
誰能「經」得起司法「嚴厲」的一再進攻,折磨。
社會上岐視,看不起別人,已經叫人「難過、怨歎」了。
而司法「長期」、公然「質疑」、「否定」一個人,甚至想永久「隔離」,「驅逐」出社會。這也應該要有個「限制」,有個「範圍」吧。
不斷發回更審,就表示有問題,「公權力」如果已經實質的進攻三次,也夠了罷!
三次不成功,也該罷手了吧!
但是,蘇案高院卻實質的進攻了被告五次。,包括第四次再審,還獲判無罪,但至今爭議未息,未獲得大家的口服心服,仍吵著要上訴。而被告「顯然」仍繼續要再被「司法」折磨下去。
到底我們「台灣」什麼地方錯了,這種追求「復仇」正義,有無過當。由於一個不義,換來了另一個不義。
錯就錯在「立法」已經不公平了,再加上長期「司法人員」保障太多,監督太少。寵壞了。任意妄為,已經變成「怪獸」,反咬主人。才有今天這種「世界級」笑話發生。
感謝台長提供進步國家,如何處理這種問題。看完,真教人汗顏,台灣還「驕傲」個屁。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被告如果已經遭到多次進攻、檢驗。就是不公,有權要求「無罪」,應釋放。
那麼,苦主或被害人家屬,則可以「司法無能」要求國家賠償,撫平傷痛。
轟動社會的刑案,悲劇既然已經發生了,就交由國家主持公道,無奈,國家司法機器無能,無力實現正義,對當事的雙方都是不公平,對人民更是無法合理交待。此時,由國家代位賠償,承擔不幸,撫平悲劇。
既然,連銀行發生的呆帳,由於自己經營的不善,政府都會去承擔損失,由全民買單補貼。現在,國家司法機關自己無能,當然應該國家賠償,向人民道歉。
沒錯,死刑廢不廢可以大家再討論,但決不能錯殺人,造成冤枉。「王迎先」的例子,還沒有得到教訓嗎?
蘇等有沒有殺人,該不該死,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司法」真的要再多多加油,向進步國家學習了。
版主回應
俠盜提出的「實質攻擊三次,也夠了吧」確實值得我們反省。
美國的刑事訴訟審判,一審若判無罪,檢察官是不得上訴的。(若判有罪,被告可上訴)而在事實審階段,陪審團若評決無罪,法官也不得推翻(如果評決有罪,而證據明顯不足,法官可以推翻)。
檢察官可以針對無罪或量刑較輕的判決上訴,請求法院判決有罪或是請求更重的刑,是我國訴訟拖延的原因之一。這使得「審級制度」不再是一種「救濟」,而是一種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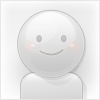 小杜白雲
小杜白雲
不知閣下是否已經審閱過本案所有的訴訟資料?
不然,如何能說的如此斬截?
而確定自己不是人云亦云?
版主回應
ㄟ...不知您所謂「本案『所有』訴訟資料」指的是什麼?我閱讀了前幾天高等法院的判決書全文,以及之前受幾位刑法與犯罪學學者所批評的「前審」判決書。
人是不是他們殺的?從判決書上的證據與認定看來,我認為確有可疑之處,至少絕對無法形成刑事案件應有的 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更遑論 no doubt!
如果我是刑事案件的陪審團,我會投「無罪」票;如果我是法官,碰上這樣除共犯與被告自白外幾乎無其他旁證的案子,也會把它dismiss掉。
 Hannah
Hannah
這篇文章除了讓人就美國的死刑改革制度有更深瞭解外,也使人期待您提到的九月份在政大舉辦的研討會。
但我更好奇老師的想法:您覺得死刑制度是能解決問題的方式,或只是一個復仇行為?美國為執行死刑提供了種種條件,能不能解釋成美國把死刑當成解決問題的方式?
版主回應
Good question!!
我個人是從根本反對死刑的。但我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思考如何與不同意見(可能是多數)的公眾對話。而「死刑改革」或許是一條途徑
「改革死刑」當然也有困境:對主張廢除死刑的人來說,「改革死刑」論形同為死刑背書--只要有嚴謹的程序與科學鑑識,就可以處死人民?而贊同死刑的人,也覺得這套制度其實等於把死刑挖空--那個州的死刑制度經得起麻州這份報告的檢驗?
麻州州長就是以這個研究報告為基礎,向州議會提出法案。也遭到不少抨擊。哈佛政府學院的Shiela Jasanoff教授在一篇名為"Just Evidence: 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Legal Process"就認為科學鑑識不足以正當化麻州州長的死刑恢復論,因為科學上的「真實」與法律上的「真實」其實有很大的不同。(感謝迷走兄提供的論文)
死刑當然具有「復仇」、「應報」的特質,而美國社會民意也強烈支持刑罰應有復仇與應報特性,因此實施死刑也是一種「解決問題」(政治問題)的方式。
對了,Hoffmann教授九月來台的研討會是「法學教育改革」。但我會與他(以及其他單位)協調至少就死刑議題參與一場討論。
「起訴狀一本」主張不應將檢察官所偵查全部訊息提供法院,致使法官受起訴卷證影響,形成有罪預斷,但此與「證據開示」防止突襲審判要求有違,不利於被告律師訴訟防禦權之行使,因檢察官於窮盡一切力量以單方之強勢處分所取得證據資料,應能同樣使被告得以充分獲得被訴相關資訊及所訴是否有理,足以充分提出防禦,如此亦得使檢察官面對律師挑戰而可以加強充實其控訴證據內容及理由,以保障被告人權不受匆促起訴而受到侵害。為防止法院產生預斷,應是陪審團而不是法官,陪審團應該是維持客觀不受起訴卷證資料影響下,完全以法庭內所見所聞提供其心證供法院審判參考。
被告屬於證據方法之一,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告設有保護措施,但卻容忍可以使用傳聞證據,違反直接審理主義。刑事訴訟法對於傳聞證據例外可採為證據之情形過於寬鬆,實影響當事人有受法院正確判斷之正當法律程序。無異使偵查庭取代了審判庭一切作為。因此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規定所有被告自白均不得作為證據,審判庭必須充分告知被告接受訊問之法律上權利,並經法庭上詰問程序,始能成為法院論罪證據,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使檢察官拋棄只要自白,不要其他證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