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7 08:56:30Jonas
學與覺---《春風化雨》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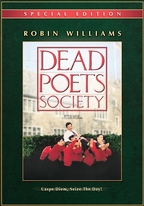
我是誰?我要怎麼樣的人生?
一位高中的國文老師,鼓勵學生去問這樣的問題。十六、七歲,正是開始建立自我的年齡。在充實學識與拓展心靈之間,該學什麼?該教什麼?電影中以四堂課來呈現老師的教育理念。
首先談「無常」。老師在穿廊上課,先讓同學唸了一段詩:「珍惜年少摘下花蕾,因為時光飛逝不回。今日微笑的花,明天即將枯萎。」當學生還在笑笑鬧鬧的氣氛中時,他要全班思考為什麼詩人這麼寫、然後煞有其事的要大家去看一些學長的老照片。他說:「因為世事無常。不論你信不信,在場的每一個人有一天都會停止呼吸、變冷、然後死亡,就像照片中這些學長。他們和各位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的髮型、同樣的全身充滿荷爾蒙。他們也感到天下無敵,好像世界都在手掌中。他們的眼裡充滿希望、相信自己是要做大事的,這和你們現在都一樣,不是嗎?但是,當這些學長真正想要發揮所長時,是不是已經時不我予?各位,他們如今都已入土。不過如果你用心去聽,還是會聽到他們想說的秘密。來,大家靠上去聽。聽到了嗎?」老師說的繪聲繪影,學生也狐疑的湊近去聽,一時鬼氣森森。
這是深刻的啟蒙。歲月盡,才華老。今人古人,同此一悲。老師沒有正襟危坐的在教室裡講「一寸光陰一寸金」、這種聽起來就是老頭子在喟嘆的舊諺,而是帶著學生親眼去看當年和他們同樣青春飛揚的人。這些彷彿只是剛剛走到前方照相的學長,如今安在?老師要同學自己去感慨生命的老死,然後自己去想:我呢,我要什麼?他用這種方式來警醒學生,言微義廣,淺近而深刻。同時,學生也容易感受傳統,接通前人的心靈。容易在嚮往中認識傳統,而非從規範中承擔傳統。他確是善於教學。
接著談「詩教」。老師鼓勵學生撕去教科書上死板的詩論序文。學生又是一片驚愕。老師從這裡解釋:詩的價值是不能用數字、面積去計算測量的。學詩,也不是為了掛在嘴邊清談兩句。他說:「看你們的眼神,好像認為十九世紀的文學和考取商學院或醫學院無關?你們私下都在想,不過是詩嘛,只要草草學個聲韻和格律,然後就趕緊去讀那些能夠實現夢想的正經書。錯了,各位。我們不是因為詩可愛,才來作詩或讀詩的。想讀詩,想作詩,因為我們是人類,而人類是充滿熱情的。醫學、法律、企業、工程,這些都是崇高的職業而且人們賴以維生。但是詩,美麗、浪漫、有愛,這才是人活著的原因。同學們,人類生命的戲劇仍在上演,而你們都能為此獻出一篇詩。你們的詩會是如何?」
老師眼中預見著這群青年的未來。他提醒這些蓄勢待發的佼佼者,不要只顧謀生而錯失人生。不要撇除一切,只為了某個外在事業的發展。因為人們總在事業完成之時,才來惋惜除了事業自己一無所有,甚至覺得沒有活過。
第三堂課談「明辨」,同學輪流站到講桌上面。老師說:「要以不同的方式觀看事物,就像在桌上看的世界是不同的。你們在自以為知道一件事情之後,必須再以另一種角度思考。這雖然可能愚笨,可能錯誤,但必須嘗試。讀書時別只顧著作者的想法,還要釐出自己的想法。去找到自己的聲音,因為你愈猶豫,就愈難找到。梭羅說過:『多數人過著寂靜的絕望生活。』不要被這句話說中。要突破,不要盲從。大膽的獨樹一格,找尋新的視野。」
最後是談「篤行」。全班聚在中庭,由三個學生出來作示範。同學於是看到了一幕有趣的現象:開始時三人本來各有步調,但是彼此看到後就開始懷疑而互相遷就。於是,各自走路變成一齊走路。老師要大家從這裡認識群體對個人的影響。他說:「人需要被認同,因而在他人面前維持自己的信念是困難的。同學們,即使別人認為你奇特、不流行,即使流俗都說你爛,你也應該相信自己的信念,因為那是獨一無二的。羅伯佛洛斯特說過:『樹林裡兩條岔路,我選擇比較少人走的那條,因為那裡有天壤之別。』現在,請試著找到自己走路的樣子。隨意的方向、隨意的漫步,不管你是洋洋得意或是傻裡傻氣。」
這是一位好老師。他有熱情,教法活潑,他珍惜這些青年璞玉。對高中生而言,升學並不輕鬆。因為文明已如巨塔,文學、數學、歷史、化學,每一項科目都有讀不完讀不盡的知識。然而,如果教學中喚不起學生的熱忱與智慧,那麼學校這個偉大的知識殿堂,就會成為一處碑石雜傾的亂葬崗。而其所傳遞的,充其量也僅是知識的鬼火,對人生難有助益。他要學生對傳統、對生命、對自己有感覺,不要麻木不仁。在幾千年幾億人的綿延長流中,要追問我是誰?追問誰是我?這就是教育中所強調的「傳道」,傳一條生命覺醒之路。
不過,教育貴在平和,撕書序的教學方式似乎太過了。以學生當場的反應來看,有人是立刻撕了用嘴咬成一團、有人是遲疑之後小心翼翼的用尺去撕、有人揉成紙團扔著玩、有人笑嘻嘻的起哄。不同的反應,顯示不同的資質和體會。這其中很難知道,如此強大的刺激會不會喧賓奪主?會不會讓學生忽略了老師的本意?會不會只記得獨立,卻不記得思考?這是教育中最難拿捏的分寸。因為當學生的心靈解放,情感隨才華而豁然奔放時,碰到挫折怎麼辦?書序可以撕,現實中的壓力怎麼撕?理性,能不能也在一樣大的刺激中同步成長?老師該怎樣繼續引導學生、解開接下來就要面臨到的困惑呢?這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因而接下來,電影就從查理、尼爾、凱邁倫、塔德四個人身上,進一步來敘述教學所產生的影響和得失。
首先是查理,他性子最衝,最敢於挑戰學校的權威。他利用校對校刊之便,偷加了議論文章,訴求男女合校。還在週會場合上公然開了校長玩笑,引起軒然大波。不過他受罰後,同學卻圍著他,當他是衝撞體制的英雄。這時老師來看他,同學紛紛讓開,等著看老師怎麼說。
「你今天耍的噱頭真是鼈腳。」老師一開口就不以為然。
「什麼?你是站在校長那邊的嗎?」查理顯得訝異,也顯得委屈:「那你上課講的『要把握今天』、『要吸取生命中所有精髓』,這些話都怎麼說?」
「吸取精髓,不表示要被骨頭噎到。人有時要大膽,有時要謹慎。聰明人可以分辨。」
「我以為你會高興?」查理失望的說。
「不。」老師明確的說:「如果你被開除,我一點都不高興。這不叫大膽,而是愚蠢。因為你會失去許多可貴的機會。」
「是嗎?譬如什麼呢?」查理的牛脾氣來了。
「不提別的,譬如,上我的課的機會。」老師微笑著:「聽懂了嗎?好小子。」
查理愣了一下,笑了,然後懂了。
「要冷靜理性一點。」老師回頭對大家說:「其他同學也要記住。」
然後是尼爾,同儕間才情洋溢的意見領袖。他喜歡演戲,但是他父親認定這是不務正業而逼他退出公演。他來找老師訴苦:「演戲是我的一切,可是他不知道。我也明白他的想法。我們不像查理他家是有錢人,他是在替我計畫我的下半輩子。但是他從來不問我『我想要什麼』。」
「這些話你曾對父親說過嗎?你對他談過你對演戲的熱忱嗎?」老師和藹的問。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和他交談。」
「那麼你是在對他演戲,你在演一齣乖兒子的戲。」老師鼓勵他試著和父親溝通:「你記得,這也許很難。但你必須讓他瞭解你是誰,你的心在想什麼?」
「我知道他會說什麼?他會說,演戲只是年少輕狂的一時奇想,我應該算了。他會說,父母對我的期望有多高多高,一切都是為了我好,要我別再想這件事了。」尼爾無奈的說。
「你不是他雇的傭人,也沒有突發奇想。這一點你要用你的信念和熱情證明給他看,讓他知道。如果他仍然不相信,那麼你要等。或者等你畢業,你就可以作自己想做的事。」
「不可能的。」尼爾顯得完全沒有信心:「那這次的演出怎麼辦?明天就要上演了!」
「那你必須在明晚之前找他談。」
「沒有比較容易的方法嗎?」
「沒有。」老師斬釘截鐵的說。
「我被困住了。」
「不,你沒有。」老師又是斬釘截鐵一句。
可惜尼爾終究沒有找父親談,因為他提不起勇氣。演出成功之後,盛怒的父親卻命令他轉學。這更讓他絕望。他自哀自憐,陷入一股不可自拔的挫折和憂傷中。雪夜裡,他還像在舞台上,最後一次感覺生命的寒冷孤寂。他自殺了,逃避一切。生命的浪漫熱情,他不願被銷磨,但也掌控不住。
老師的教誨攔住了查理,卻來不及攔住尼爾。命運就是這樣弄人,如果老師有再多一些時間開導他,如果他爸爸氣憤之餘來找老師,如果他媽媽能安慰他給他支持,如果尼爾能再多想想,如果尼爾還有機會和死黨們聊聊。有太多的如果,卻都沒有發生,事情直衝悲劇而去。
事發之後,全校震驚。校長為了給尼爾父親和輿論一個交代,便設計誣陷老師以減輕校方的責任。這個老校長的作法當然不值一提。他儘可以不同意國文老師的教學方法,儘可以召開教務會議檢討這個事件,然而昧著良心無中生有,用退學威逼學生。甚至運用親情壓力,在學生還傷心不知所措的紊亂中引人犯罪,這是最不可原諒的身教。他未來怎麼在入學典禮上詮釋他口口聲聲標榜的偉大校風?他將憑藉什麼談「傳統」?憑藉什麼談「榮譽」?憑藉什麼談「紀律」?憑藉什麼談「卓越」?學生會從這裡看到什麼,學到什麼,會把什麼帶進他們即將要走入的社會?
凱邁倫可以算是校長影響下的產物。因為擔心學校遷怒,他搶先去檢舉有關詩社的事。而當其他同學質問他背叛時,他反駁:「如果你們還不知道,讓我告訴你們吧!本校有一種叫做『榮譽法』的玩意兒。如果遇到師長查問卻不老實回答的話,就會被開除。聰明點!學校要抓的不是我們,我們是受害者,尼爾和你我都是受害者。學校要抓的是老師,你們不會以為他可以逃避責任吧?尼爾的死,難道要他爸爸負責?難道要學校負責?老師慫恿我們搞這些無聊的事。如果不是他,尼爾現在應該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宿舍裡,唸他的化學,夢想著被人恭恭敬敬的尊稱一聲大夫。隨你們愛怎麼想,總之我已經向學校自白,也簽了名希望老師受到懲處。各位,何必讓他破壞我們的生活?」還沒聽完他的話,查理當面就給他一拳。凱邁倫也給激怒的吼叫起來:「你們要是聰明,作法就會和我一樣,那就是合作。反正現在學校什麼都知道了,你們救不了老師,但是你們可以救自己。」這樣的心機,和老校長如出一轍。而他也是同坐在一間教室、同受一種教育的學生。
同輩之中,塔德一開始是不起眼的,最後卻是亮麗的。他因為哥哥過去在學校表現優異,因而總是害怕自己表現不好。害怕犯錯、害怕參與、甚至害怕大聲說話。但是在循循善誘中,他逐漸能擺脫心中的害怕,甚至能用詩吶喊出他的恐懼。到了最後,雖然不如查理的硬骨氣,但他是第一個向老師道歉,公開為老師澄清,也是第一個站上桌子、以老師所教支持老師的學生。全班二十個學生,尼爾死了,查理因為拒絕簽字而被退學,剩下十八個。十個站上桌子,八個不敢吭氣。而被迫簽下自白文件的學生全站上桌子,除了凱邁倫之外。
這位老師,尊重了每個學生不同的潛能與特質,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盡心盡力之下,二十個學生的發展卻不盡相同,也未必如意。然而為人師表,傳道、授業、解惑的職守,他已經作出最大的努力。老師能啟發學生,能協助每一個生命找到自己,卻無法代替學生為他們的人生負責。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電影最後一個鏡頭,停在老師對塔德的凝視上。對老師而言,班上能教出一個足以堅定自立的學生就殊堪告慰,何況他還鼓舞了這麼多人的覺醒。這些青年依然真情而善良,人格也已經有了立足。縱使沒有他,往後也必能繼續茁壯。師生一場,短短相聚,成果如此,夫復何悲?
只有學生自己能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古人說:「讀書是學做人,學作一個人格。」現代人說:「受教育是學獨立,學過一個人生。」這位國文老師則說:「找到自己的聲音、寫下自己的詩篇、讓你的生命不平凡。」這些,都是儒家教育中講求的「德」的本義。「德」,是心得,不是守則規範,是對於生命有所體會後展現出來的一種個人風格。不斷的反省思考,不斷的發揮潛能。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衝突,有抉擇、有行為能力,讓心靈不斷地向前進步,這就是「立德」。立德的極致,可以使個人的人格與天地同壽,匯入人類不朽的大傳統中。人一生中,如果能遇到好老師,務必珍惜。如果遇不到,也不要放棄,先努力做自己的老師。這種源之於「德」的自信,就是在學校中應該教、應該學的吧。
【影片資料】
英文片名 Dead Poets Society
出品年代 1989年
導演 彼得.威爾(Peter Weir)
原著劇本 湯.舒曼(Tom Schulman)
主要角色 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羅伯.辛.雷歐納(Robert Sean Leonard)伊森.霍克(Ethan Hawke)基爾.漢森(Gale Hansen)戴倫.庫斯曼.(Dylan Kussman) 飾國文老師(John Keating)飾尼爾(Neil Perry)飾塔德(Todd Anderson)飾查理Charlie Dalton飾凱邁倫(Richard Cameron)
其他譯名 死亡詩社、暴雨驕陽
時代背景 1959年.美國Welton Academy
一位高中的國文老師,鼓勵學生去問這樣的問題。十六、七歲,正是開始建立自我的年齡。在充實學識與拓展心靈之間,該學什麼?該教什麼?電影中以四堂課來呈現老師的教育理念。
首先談「無常」。老師在穿廊上課,先讓同學唸了一段詩:「珍惜年少摘下花蕾,因為時光飛逝不回。今日微笑的花,明天即將枯萎。」當學生還在笑笑鬧鬧的氣氛中時,他要全班思考為什麼詩人這麼寫、然後煞有其事的要大家去看一些學長的老照片。他說:「因為世事無常。不論你信不信,在場的每一個人有一天都會停止呼吸、變冷、然後死亡,就像照片中這些學長。他們和各位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的髮型、同樣的全身充滿荷爾蒙。他們也感到天下無敵,好像世界都在手掌中。他們的眼裡充滿希望、相信自己是要做大事的,這和你們現在都一樣,不是嗎?但是,當這些學長真正想要發揮所長時,是不是已經時不我予?各位,他們如今都已入土。不過如果你用心去聽,還是會聽到他們想說的秘密。來,大家靠上去聽。聽到了嗎?」老師說的繪聲繪影,學生也狐疑的湊近去聽,一時鬼氣森森。
這是深刻的啟蒙。歲月盡,才華老。今人古人,同此一悲。老師沒有正襟危坐的在教室裡講「一寸光陰一寸金」、這種聽起來就是老頭子在喟嘆的舊諺,而是帶著學生親眼去看當年和他們同樣青春飛揚的人。這些彷彿只是剛剛走到前方照相的學長,如今安在?老師要同學自己去感慨生命的老死,然後自己去想:我呢,我要什麼?他用這種方式來警醒學生,言微義廣,淺近而深刻。同時,學生也容易感受傳統,接通前人的心靈。容易在嚮往中認識傳統,而非從規範中承擔傳統。他確是善於教學。
接著談「詩教」。老師鼓勵學生撕去教科書上死板的詩論序文。學生又是一片驚愕。老師從這裡解釋:詩的價值是不能用數字、面積去計算測量的。學詩,也不是為了掛在嘴邊清談兩句。他說:「看你們的眼神,好像認為十九世紀的文學和考取商學院或醫學院無關?你們私下都在想,不過是詩嘛,只要草草學個聲韻和格律,然後就趕緊去讀那些能夠實現夢想的正經書。錯了,各位。我們不是因為詩可愛,才來作詩或讀詩的。想讀詩,想作詩,因為我們是人類,而人類是充滿熱情的。醫學、法律、企業、工程,這些都是崇高的職業而且人們賴以維生。但是詩,美麗、浪漫、有愛,這才是人活著的原因。同學們,人類生命的戲劇仍在上演,而你們都能為此獻出一篇詩。你們的詩會是如何?」
老師眼中預見著這群青年的未來。他提醒這些蓄勢待發的佼佼者,不要只顧謀生而錯失人生。不要撇除一切,只為了某個外在事業的發展。因為人們總在事業完成之時,才來惋惜除了事業自己一無所有,甚至覺得沒有活過。
第三堂課談「明辨」,同學輪流站到講桌上面。老師說:「要以不同的方式觀看事物,就像在桌上看的世界是不同的。你們在自以為知道一件事情之後,必須再以另一種角度思考。這雖然可能愚笨,可能錯誤,但必須嘗試。讀書時別只顧著作者的想法,還要釐出自己的想法。去找到自己的聲音,因為你愈猶豫,就愈難找到。梭羅說過:『多數人過著寂靜的絕望生活。』不要被這句話說中。要突破,不要盲從。大膽的獨樹一格,找尋新的視野。」
最後是談「篤行」。全班聚在中庭,由三個學生出來作示範。同學於是看到了一幕有趣的現象:開始時三人本來各有步調,但是彼此看到後就開始懷疑而互相遷就。於是,各自走路變成一齊走路。老師要大家從這裡認識群體對個人的影響。他說:「人需要被認同,因而在他人面前維持自己的信念是困難的。同學們,即使別人認為你奇特、不流行,即使流俗都說你爛,你也應該相信自己的信念,因為那是獨一無二的。羅伯佛洛斯特說過:『樹林裡兩條岔路,我選擇比較少人走的那條,因為那裡有天壤之別。』現在,請試著找到自己走路的樣子。隨意的方向、隨意的漫步,不管你是洋洋得意或是傻裡傻氣。」
這是一位好老師。他有熱情,教法活潑,他珍惜這些青年璞玉。對高中生而言,升學並不輕鬆。因為文明已如巨塔,文學、數學、歷史、化學,每一項科目都有讀不完讀不盡的知識。然而,如果教學中喚不起學生的熱忱與智慧,那麼學校這個偉大的知識殿堂,就會成為一處碑石雜傾的亂葬崗。而其所傳遞的,充其量也僅是知識的鬼火,對人生難有助益。他要學生對傳統、對生命、對自己有感覺,不要麻木不仁。在幾千年幾億人的綿延長流中,要追問我是誰?追問誰是我?這就是教育中所強調的「傳道」,傳一條生命覺醒之路。
不過,教育貴在平和,撕書序的教學方式似乎太過了。以學生當場的反應來看,有人是立刻撕了用嘴咬成一團、有人是遲疑之後小心翼翼的用尺去撕、有人揉成紙團扔著玩、有人笑嘻嘻的起哄。不同的反應,顯示不同的資質和體會。這其中很難知道,如此強大的刺激會不會喧賓奪主?會不會讓學生忽略了老師的本意?會不會只記得獨立,卻不記得思考?這是教育中最難拿捏的分寸。因為當學生的心靈解放,情感隨才華而豁然奔放時,碰到挫折怎麼辦?書序可以撕,現實中的壓力怎麼撕?理性,能不能也在一樣大的刺激中同步成長?老師該怎樣繼續引導學生、解開接下來就要面臨到的困惑呢?這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因而接下來,電影就從查理、尼爾、凱邁倫、塔德四個人身上,進一步來敘述教學所產生的影響和得失。
首先是查理,他性子最衝,最敢於挑戰學校的權威。他利用校對校刊之便,偷加了議論文章,訴求男女合校。還在週會場合上公然開了校長玩笑,引起軒然大波。不過他受罰後,同學卻圍著他,當他是衝撞體制的英雄。這時老師來看他,同學紛紛讓開,等著看老師怎麼說。
「你今天耍的噱頭真是鼈腳。」老師一開口就不以為然。
「什麼?你是站在校長那邊的嗎?」查理顯得訝異,也顯得委屈:「那你上課講的『要把握今天』、『要吸取生命中所有精髓』,這些話都怎麼說?」
「吸取精髓,不表示要被骨頭噎到。人有時要大膽,有時要謹慎。聰明人可以分辨。」
「我以為你會高興?」查理失望的說。
「不。」老師明確的說:「如果你被開除,我一點都不高興。這不叫大膽,而是愚蠢。因為你會失去許多可貴的機會。」
「是嗎?譬如什麼呢?」查理的牛脾氣來了。
「不提別的,譬如,上我的課的機會。」老師微笑著:「聽懂了嗎?好小子。」
查理愣了一下,笑了,然後懂了。
「要冷靜理性一點。」老師回頭對大家說:「其他同學也要記住。」
然後是尼爾,同儕間才情洋溢的意見領袖。他喜歡演戲,但是他父親認定這是不務正業而逼他退出公演。他來找老師訴苦:「演戲是我的一切,可是他不知道。我也明白他的想法。我們不像查理他家是有錢人,他是在替我計畫我的下半輩子。但是他從來不問我『我想要什麼』。」
「這些話你曾對父親說過嗎?你對他談過你對演戲的熱忱嗎?」老師和藹的問。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和他交談。」
「那麼你是在對他演戲,你在演一齣乖兒子的戲。」老師鼓勵他試著和父親溝通:「你記得,這也許很難。但你必須讓他瞭解你是誰,你的心在想什麼?」
「我知道他會說什麼?他會說,演戲只是年少輕狂的一時奇想,我應該算了。他會說,父母對我的期望有多高多高,一切都是為了我好,要我別再想這件事了。」尼爾無奈的說。
「你不是他雇的傭人,也沒有突發奇想。這一點你要用你的信念和熱情證明給他看,讓他知道。如果他仍然不相信,那麼你要等。或者等你畢業,你就可以作自己想做的事。」
「不可能的。」尼爾顯得完全沒有信心:「那這次的演出怎麼辦?明天就要上演了!」
「那你必須在明晚之前找他談。」
「沒有比較容易的方法嗎?」
「沒有。」老師斬釘截鐵的說。
「我被困住了。」
「不,你沒有。」老師又是斬釘截鐵一句。
可惜尼爾終究沒有找父親談,因為他提不起勇氣。演出成功之後,盛怒的父親卻命令他轉學。這更讓他絕望。他自哀自憐,陷入一股不可自拔的挫折和憂傷中。雪夜裡,他還像在舞台上,最後一次感覺生命的寒冷孤寂。他自殺了,逃避一切。生命的浪漫熱情,他不願被銷磨,但也掌控不住。
老師的教誨攔住了查理,卻來不及攔住尼爾。命運就是這樣弄人,如果老師有再多一些時間開導他,如果他爸爸氣憤之餘來找老師,如果他媽媽能安慰他給他支持,如果尼爾能再多想想,如果尼爾還有機會和死黨們聊聊。有太多的如果,卻都沒有發生,事情直衝悲劇而去。
事發之後,全校震驚。校長為了給尼爾父親和輿論一個交代,便設計誣陷老師以減輕校方的責任。這個老校長的作法當然不值一提。他儘可以不同意國文老師的教學方法,儘可以召開教務會議檢討這個事件,然而昧著良心無中生有,用退學威逼學生。甚至運用親情壓力,在學生還傷心不知所措的紊亂中引人犯罪,這是最不可原諒的身教。他未來怎麼在入學典禮上詮釋他口口聲聲標榜的偉大校風?他將憑藉什麼談「傳統」?憑藉什麼談「榮譽」?憑藉什麼談「紀律」?憑藉什麼談「卓越」?學生會從這裡看到什麼,學到什麼,會把什麼帶進他們即將要走入的社會?
凱邁倫可以算是校長影響下的產物。因為擔心學校遷怒,他搶先去檢舉有關詩社的事。而當其他同學質問他背叛時,他反駁:「如果你們還不知道,讓我告訴你們吧!本校有一種叫做『榮譽法』的玩意兒。如果遇到師長查問卻不老實回答的話,就會被開除。聰明點!學校要抓的不是我們,我們是受害者,尼爾和你我都是受害者。學校要抓的是老師,你們不會以為他可以逃避責任吧?尼爾的死,難道要他爸爸負責?難道要學校負責?老師慫恿我們搞這些無聊的事。如果不是他,尼爾現在應該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宿舍裡,唸他的化學,夢想著被人恭恭敬敬的尊稱一聲大夫。隨你們愛怎麼想,總之我已經向學校自白,也簽了名希望老師受到懲處。各位,何必讓他破壞我們的生活?」還沒聽完他的話,查理當面就給他一拳。凱邁倫也給激怒的吼叫起來:「你們要是聰明,作法就會和我一樣,那就是合作。反正現在學校什麼都知道了,你們救不了老師,但是你們可以救自己。」這樣的心機,和老校長如出一轍。而他也是同坐在一間教室、同受一種教育的學生。
同輩之中,塔德一開始是不起眼的,最後卻是亮麗的。他因為哥哥過去在學校表現優異,因而總是害怕自己表現不好。害怕犯錯、害怕參與、甚至害怕大聲說話。但是在循循善誘中,他逐漸能擺脫心中的害怕,甚至能用詩吶喊出他的恐懼。到了最後,雖然不如查理的硬骨氣,但他是第一個向老師道歉,公開為老師澄清,也是第一個站上桌子、以老師所教支持老師的學生。全班二十個學生,尼爾死了,查理因為拒絕簽字而被退學,剩下十八個。十個站上桌子,八個不敢吭氣。而被迫簽下自白文件的學生全站上桌子,除了凱邁倫之外。
這位老師,尊重了每個學生不同的潛能與特質,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盡心盡力之下,二十個學生的發展卻不盡相同,也未必如意。然而為人師表,傳道、授業、解惑的職守,他已經作出最大的努力。老師能啟發學生,能協助每一個生命找到自己,卻無法代替學生為他們的人生負責。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電影最後一個鏡頭,停在老師對塔德的凝視上。對老師而言,班上能教出一個足以堅定自立的學生就殊堪告慰,何況他還鼓舞了這麼多人的覺醒。這些青年依然真情而善良,人格也已經有了立足。縱使沒有他,往後也必能繼續茁壯。師生一場,短短相聚,成果如此,夫復何悲?
只有學生自己能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古人說:「讀書是學做人,學作一個人格。」現代人說:「受教育是學獨立,學過一個人生。」這位國文老師則說:「找到自己的聲音、寫下自己的詩篇、讓你的生命不平凡。」這些,都是儒家教育中講求的「德」的本義。「德」,是心得,不是守則規範,是對於生命有所體會後展現出來的一種個人風格。不斷的反省思考,不斷的發揮潛能。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衝突,有抉擇、有行為能力,讓心靈不斷地向前進步,這就是「立德」。立德的極致,可以使個人的人格與天地同壽,匯入人類不朽的大傳統中。人一生中,如果能遇到好老師,務必珍惜。如果遇不到,也不要放棄,先努力做自己的老師。這種源之於「德」的自信,就是在學校中應該教、應該學的吧。
【影片資料】
英文片名 Dead Poets Society
出品年代 1989年
導演 彼得.威爾(Peter Weir)
原著劇本 湯.舒曼(Tom Schulman)
主要角色 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羅伯.辛.雷歐納(Robert Sean Leonard)伊森.霍克(Ethan Hawke)基爾.漢森(Gale Hansen)戴倫.庫斯曼.(Dylan Kussman) 飾國文老師(John Keating)飾尼爾(Neil Perry)飾塔德(Todd Anderson)飾查理Charlie Dalton飾凱邁倫(Richard Cameron)
其他譯名 死亡詩社、暴雨驕陽
時代背景 1959年.美國Welton Academy
挺好~!
http://www.yyj.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