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逃避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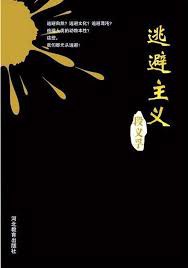
誰不曾有過逃避的想法?但逃避何物,逃向何處?一旦我們來到一個美好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是否就是我們遷移的最後目的地?--段義孚,《 逃避主義 》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 故鄉 》
在運動員的生理體能黃金年齡,三十歲前後加起來將近十年,我都待在一般人喜稱的退休養老理想地,花蓮。在花蓮,反而是我經濟的高峰,工作與生活都最穩定的日子。可同樣的社會身分擺在台北跟花蓮,社會位置完全相反,比如,若同樣從事NGO工作,在台北,簡直要讓人自我感覺是無產階級,在花蓮,卻能做個好好生活,還算光鮮亮麗的中產階級。(但現在都無所謂了,大家都不可能有產了。套句陳界仁用語,我們都被「在地流放」了。)
這塊山海包覆的「台灣最後淨土」退休養老理想地,絕非政治從未侵占的桃花源,反而「地方」才是直接感受、面對政治的一線戰場。過去「地方分權」的台北人自以為的文明理性,也漸漸因為目睹種種各款地方社團之封閉、狹隘、人治,政治主事者之保守、貪婪、暴力再暴力,才體認到此不過贖罪心態罷了。繼而,「社團」盡情包養地方民眾的文藝接受,貫通政治網絡,使得地方文藝的創造性與自主性只能通過民間中的少數,孤立地開展,盡可能延遲夭折的時刻。
但這裡面實存一種可能繞過,甚至擊破既定生產形式的原生力量,現在流行的「共享」、「參與」,不正是源自非都會的產物。可是地方對城市的模仿欲太強,不斷向「外」看,卻無法正視自身的潛在的創造性。都市是國家的幻影,資本的器皿,地方卻通過模仿,自願為奴,以殖為生。彷彿歷史從未終結。
顏崑陽於〈後山的存在意識〉,從台灣拓殖史視角探討花蓮人的精神意識,包括三種向度,空間/由清朝首都北京往台灣看,先看到的是西部(前山);時間/最晚開始開墾,意味經濟、文化建設之落後;雙重邊陲性/台灣是相對於西方的邊陲,花蓮是相對於前山的邊陲。他依此歸結出「後山意識」乃兩種力量之拉扯--孽子情結與希求開發,淨土理想與堅持自然。換句話說,即經濟建設與自然景觀的辯證。
也是在花蓮這些年,因著工作、生活、從旁極稀薄地參與地方上一些反對運動,漸漸發覺了民眾的不可能,當然,更是發覺了自己的不可能。而隨2012年辭去全職工作,我逐漸地又逃回移居花蓮之初以為將漸離漸遠的劇場。對於地方的民間社會(是的,我連「公民社會」都要打上問號)的接觸、參與,日漸陌生,是更稀薄的看客了。但到現在,花蓮的民間團體確實結盟出了越來越強的能量,他們在「後山意識」包覆之下,實踐、相信的是這樣的事吧--
和辻哲郎提到黑格爾對自然類型的劃分,其中一種是「與海直接相連的海岸國土」,其意義是什麼呢:「海岸國家可以作為世界關聯性的表現。沒有比海更適合與將世界連接在一起了,所以商業發達。不過,海的表象是非制約性的,非局限性的,無限的。所以,自己內心感受到這點的人們便培育出超越限制內外拓伸的勇氣,湧現出征服欲、冒險欲。同時,人們也產生了對市民自由的自覺意識。」
他們既相信地方是島嶼的「內部」,亦堅持人們不妨跟隨海洋,拓伸自己的「外部」,如太平洋、如南島、如群島。而不必老在公路坍方時聞縣長的三等縣民愚論起舞,不必老跟著已死氣沉沉的都市後頭走,那是倒退,不是前進。我相信他們這麼相信。
2012年以後,在花蓮的時間越來越少了,除了睡覺,也許在各種交通工具上的時間最多。來回移動之間,卻驚覺花蓮已成我的風土,不由得時而眷戀,也因而對其他地方都還沒完全習慣,但又總要對自己說,應該上路了。定下來,反而是逃避。
可是,風土的花蓮仍然一直教我如何看島嶼的劇場、文化生態;看文化政策實踐上的不可能,看,應該先看「社會」而非「國家」。我的視界很小,不夠海洋,台灣太小,以致人們以為新店到淡水比台北到花蓮快很多。台灣的小,反而讓我們錯認台灣很大,彷彿活在虛胖的地理世界,無形把自己跟土地的距離拉得很遠。台灣一直是座「內部性匱乏」的島嶼。這是我們的過去,也是我們的未來。
去年,難得回花蓮一趟的火車上,臨近上下車數百回的終站,奇異的感覺剎那襲來:一個人要對陌生的地方熟悉很難,要對熟悉的地方陌生卻很容易。
上一篇:【在東岸】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下一篇:記啟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