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整體佛教發展應有的正確觀念~2012-11-27 12:49:00
前言
台灣佛教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已廣獲社會大眾的迴應,不管是傳統寺院專屬的弘法活動也好,抑或學術界熾盛的研究討論風潮也好,在在都顯示著台灣佛教正邁入一個嶄新的紀元。而值此之時,如何攜手共進同創佛教未來的課題,更為每一個佛教弟子所重視著。因此,我們特別採訪甫獲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的惠敏法師,請他來談談台灣佛教發展的契機。
問:台灣佛教近年來學術研究與討論風潮甚熾,學術研究機構現也已頗具規模。然而當年法師所處的學術環境正值草創期間,當時遠赴日本深造,是否遭遇諸多困難?法師您如何克服?又台灣佛教學術研究環境的改善,是否已能彌補當年的缺失與不足?
惠敏法師答:出家以後,主要是在傳統的寺院內修行與學習,然而我卻發覺,既然想要深入佛法,就必須要開拓視野,吸收國內外的研究成果,甚至更應該瞭解國內外從事佛學研究的狀況。不過,要吸收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瞭解別人的研究方法,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譬如說,梵文、藏文、巴利文這類經典語言,若要在寺院中學習恐怕不易。再者諸如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研究用語言,雖然自修還可以增益,不過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去念國內佛研所的一個主要動機,主要還是想吸收和瞭解國內外的佛學研究成果。
當時國內的佛學研究所尚處於草創階段,許多佛學有關課程都還在摸索。譬如說,語言方面特別是梵文、藏文等教學均才起步。但是,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與基礎已近百年,成果豐碩。再者,他們研究與學習已蔚為風氣,學生們自然會主動去學習這方面的語文,因此他們的語文根基甚穩,使用起來就十分「自然」。當初我們在國內學習這類語文,算是頭幾批,周遭環境與教學要求,尚不是那麼地「自然」,所以初到日本,在那種學風及環境下,當然很難跟得上進度。因此我認為目前國內佛學研究所的基礎教育,特別是在語文訓練與文獻學方面,須要再接再厲,精熟再精熟。
我舉一個較具體的例子,我到東京大學後,仍到大學部上梵文文法的課,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及教學的進度,都要比國內高出許多。日本學生碩士班以上大部份都能熟讀幾本梵文原典,有的甚至都能夠背誦,所以進入研究所,在這方面他們就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大體說來,在日本從大學部到碩士班,對於學生的語文訓練及文獻學要求比較徹底,這也是目前國內佛學研究所較弱的一環,也是國內學生到日本較有障礙的地方。
問:從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一年六年的留學生涯,除了取得文學博士外,法師認為在日本還有那些收穫?
惠敏法師答:談到六年留學生涯的收穫,無疑地,上述我所強調的語文及文獻學方面的訓練,是我最大的收穫。因為我在日本就是專攻梵文、藏文及巴利文,至於漢籍佛典的課程,我只在碩士課一年級時選了一門。
笫二個收穫,是在日本拓展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資相當齊備的東京大學,比較能夠迅速獲知一些新的研究動向。大致來說,在東京大學資訊的取得與接觸機會均甚為便捷,而且凡是有國際知名學者路過東京,校方均會自動邀請前來演講,這種面對面的知識傳遞模式,對學生的吸收與剌激,是有其正面效果。
再者,日本與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交流甚為密切,新資訊的取得如此快速,自然拓展研究的視野。以上兩點是我在日本學習上最直接的收穫。間接的收穫是從日本的社會及媒體得到的知識,日本是個先進的國家,舉凡政治、經濟、高科技發展、都會予人很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帶來諸多啟發。當然這一點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留學都能有相同的感受,不一定只在日本。
另外一點,就在六年的留學生活中所建立的人際關係與管道,這也是相當可貴的資產。而這項收穫就如同日本人講話中常用的(plus a),是一種難以估計之附加價值,憑添始料未及的收穫。
問:留學前後,對台灣佛教整體發展的改變,有何感覺?發展的主要因素為何?
惠敏法師答:在我留學期間,不僅是佛教有了很大的改變,整個國家社會的變化也十分快速,因此我想,佛教的發展與整個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有關係,是整個國家在動,整個國家在變,連帶著佛教也動了起來。當然教內的發展也有些前因,就我所知,教內已不像過去定為一處,活動的範圍與空間已擴大許多,且已多元化。我在國外獲知這些消息,常歡喜讚歎,經過國內法師與居士用心的推展,台灣佛教已有長足的進步。
問:聽法師您如此說,是否意味佛教已從傳統的寺院中走出,邁向寺院外(社會大眾)的發展?
惠敏法師答: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因為如此說法容易引人產生錯覺,認為走出寺院是「對」,寺院內就「錯」。整體佛教蓬勃發展,與愈來愈多的青年加入佛教有關,他們為佛教注入一股新血。就拿我這一代來說,當初在學校學佛被認為是少數民族,且為異類,可是現在不一樣,似乎已有不學趕不上時代潮流的趨勢,因此佛教的活動份子愈來愈年輕化,程度也愈來愈高,這自然有助於佛教的發展。
不過,我也感覺到,現在變化的速度要比過去快很多,這或許與資訊的傳遞快速有關,有時更令人眼花撩亂,然而僅管如此,不如將它視為另一種好的轉機,與其驚恐,不如加以期待吧!
問:法師您是宗教師兼學者的身份,日後必大力推展佛教教育與文化的發展。而法師您又甫從日本返國,關於教育文化方面,可否請法師您分析兩國的優劣點?而台灣佛教的發展方向應朝向何方?
惠敏法師答:日本佛教與台灣佛教非常有趣的!她們兩者正好長、短處相反。日本佛教屬橫向關係的發展,而台灣佛教屬於縱向的發展,兩者成為有趣的對比。日本佛教橫向關係的發展,以大本山為中心,寺院與寺院的聯擊力較強,學者之間亦若是,學者之間透過各種學會彼此切磋增長知識。而台灣佛教恰好相反,領導者每天的交流及接觸不是徒弟就是信徒,與同輩間的交流微乎其微,弘法者與弘法者之間鮮有機會互相切磋佛法,個人講個人的經。這種每天面對的上下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很難察覺自己的缺點,師父講的話是對,老師講的法絕對錯不了。因此自成各個封閉的體系,於是就形成各說各話,各講各的「好」,就這一點,與日本不太相同。
再者,除上述之對比之外,「弘法取向」與「學術研究取向」是日本與台灣主要不同之處。日本學術研究很強,第一流人才幾乎全走上佛學研究的路線。因為日本佛教寺院是採世襲?長子繼承,假若長子會念書,他就選擇學者路線專心去當教授,或許就把寺院交給弟弟去執掌。
問:但是,當住持同樣要能專業弘法?
惠敏法師答:基本上他們沒有弘法。現在我要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日本佛教既是學者取向,又是橫向結構,自然寺院與信徒之間的關係就很微弱,可以說日本佛教的住持幾乎不弘法。因為信徒與寺院的關係只建立在納骨塔上面(日本法律禁止土葬,一律火葬),日本人若自稱是佛教徒,並非代表他真正信仰瞭解佛教,只是意味我家的骨塔在寺院內。日本佛教信徒平時去寺院不是向法師請法或去大殿禮佛,只是去掃墓祭祀而已。
台灣的佛教信徒則不然,去寺院有請法師開示的風氣,因此台灣的法師被這些信徒「訓練」的都很會弘法或開示,所以台灣通俗弘法很強。但是日本寺院的住持就不然,他只是專心做「佛事」即可,信徒也無此習慣請法師說法,因此日本寺院住持通俗弘法的刺激幾乎沒有。所以當日本佛教的住持在學校學了幾年的佛法與佛事知識外,長久下來,除了那些與佛事相關的知識外,所有的佛學知識幾乎全用不著,難怪有位日本法師就曾對我說:「用不著,幾乎都忘了!」
所以,在日本討論與研究佛法大多是教授學者,社會與媒體教育有時亦摻入佛學的課程,大多請學者來講,像NHK電視台即有「人生講座」講佛學,或者像「心的時代」也有佛教課程。因此日本人接觸佛法,大多數還是透過媒體及書,另外就是寺院以外專門弘法的組織,所以這也是造成日本新興宗教如雨後替春筍般出現的原因。
因為日本新興宗教的經濟基礎不是建立在納骨塔上,所以他們非得弘法不可,否則無法生存。而傳統寺院以骨塔為其主要經濟來源,且相當優厚,因此他無需靠弘法維生。但是實際上,日本社會仍有強烈的宗教需求,在傳統寺院無法滿足大眾需求時,轉而向新興宗教訴求,造成新興宗教非常興盛,並不是沒有來由的。所以這也是日本與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將來台灣佛教的發展,即然在通俗弘法方面很強,就應該繼續保持不應捨棄。而我們比較弱的一環即是高深的佛學研究,就應該持續加強,當然,這些年來已有改觀,佛教徒正逐漸重視佛學研究的強化工作。
問: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有其優劣,弘法取向與學術研究各有缺失,在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找到平衡點?
惠敏法師答:在日本,學術研究與修行系統並非因橫向發展關係,而達到某種協調的程度,他們幾乎很少交流,說白一點,在談佛學的時候,學者們往往會輕視寺院的僧人,而寺院系統的人認為,既瞧不起我,我也不與你打交道,所以在日本,學者與寺院間並沒有調和得很圓滿。我想將來佛教辦的大學遲早會成立,要成立的話,難免會遭遇這些問題,不過我仍希望是能夠協調比較好。我個人認為,這兩者應該可以互補,應該彼此尊重,各取所需。站在整體佛教的發展來看,兩者均各有其必要性,不是光靠佛學研究或僅遵修行可賴以發展的。兩者理應並重彼比肯價值,各發揮所長,不要彼此否定才好,要知:合者兩利,分則兩敗俱傷。所以整來看,台灣佛教應加強橫向聯繫及重視學術研究的發展,絕不能顧此失彼,反而減緩佛教的發展。
問:與佛教發展有切身關係的人才問題,是否請法師提出您的看法?
惠敏法師答:人才的吸收與培養是佛教要維持穩定成長的重要因素。佛教有兩大培養人才據點:一是寺院,二是寺院外的教育組織。寺院是培育僧才的中樞機構,因此寺院內部如何運作,怎麼把人一、接引,二、培養,三、適得其所的出路,這三個環節做好,是非常重要的。以工廠作譬喻,首先必須先找尋所需的適當原料,這些原料進來後,如何把它加工、製造,而成為有用途之產品。這便是第二個階段須要有完善且健全的培育系統來培養人才,第三階段是,當他完成某種階段的培訓後,是否還有管道使他能更上層樓繼續深造,或者從事他所專精的事務。
嚴格說來,吸收接引、培養訓練及出路這三個階段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夠有問題,不然任何一點堵塞都會造成人才的浪費與流失。所以整體來看,佛教寺院方面應該針對這三部分做一個總檢討。也就是說,如何提高學生的興趣來報考及參與。甚至我們還要能夠主動積極去發掘人才,而不應只是被動等他來報考。人才進入以後,必須給予完善健全的培養,甚至幫他選擇適當的出路,我想唯有這樣,才會使得人才的管理可暢通。佛教所需的人才太多太多了,主動發掘人才,因才施教,因才而用,絕不能認為每個人非得走這一條路不可,因此廣泛培育人才,才是佛教賴以發展的憑藉。
問:法師您將來除了在教內研究教學外,是否另有教職?
惠敏法師答:將來我主要擔任的教職是法光佛學研究所及中華佛研所,另外可能將在國立藝術學院擔任通識教育的課程,除了宗教人生這類的宗教課程外,另外則是我比較專門的「佛教藝術中的思想」課程。但是這些均屬共通課程,與研究所的專精性質不一樣。對我來說,兩邊任教比較平衡一點,通通教太專精的課程,卻忘了一些基本的問題也很不好,所以這正好平衡一下我學佛的感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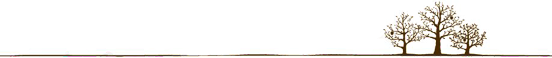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簡介--惠敏法師俗姓郭,名敏芳,台灣省台南市人,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民國六十年畢業於台南第一高級中學,進入台北醫學院攻讀藥學,於大學期間接觸佛法深受法益,遂發心深入法海,於台北醫學院畢業後進入中華佛研所鑽研佛學,又感佛學研究不能侷處一隅,應有開拓之視野,遂即負笈東瀛(民國七十五年),民國七十六年考進東京大學大學院成為正式院生,兩年後以「『聲聞地』種姓論資糧論」論文,取得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同時更上一層進入博士課程,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提出博士論文「『聲聞地』研究序說--瑜伽行所緣中心」,且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正式取得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學博士。惠敏法師現任三峽西蓮淨苑副住持,且執教於國立藝術學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及中華佛研所,臺灣法鼓山佛教學院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