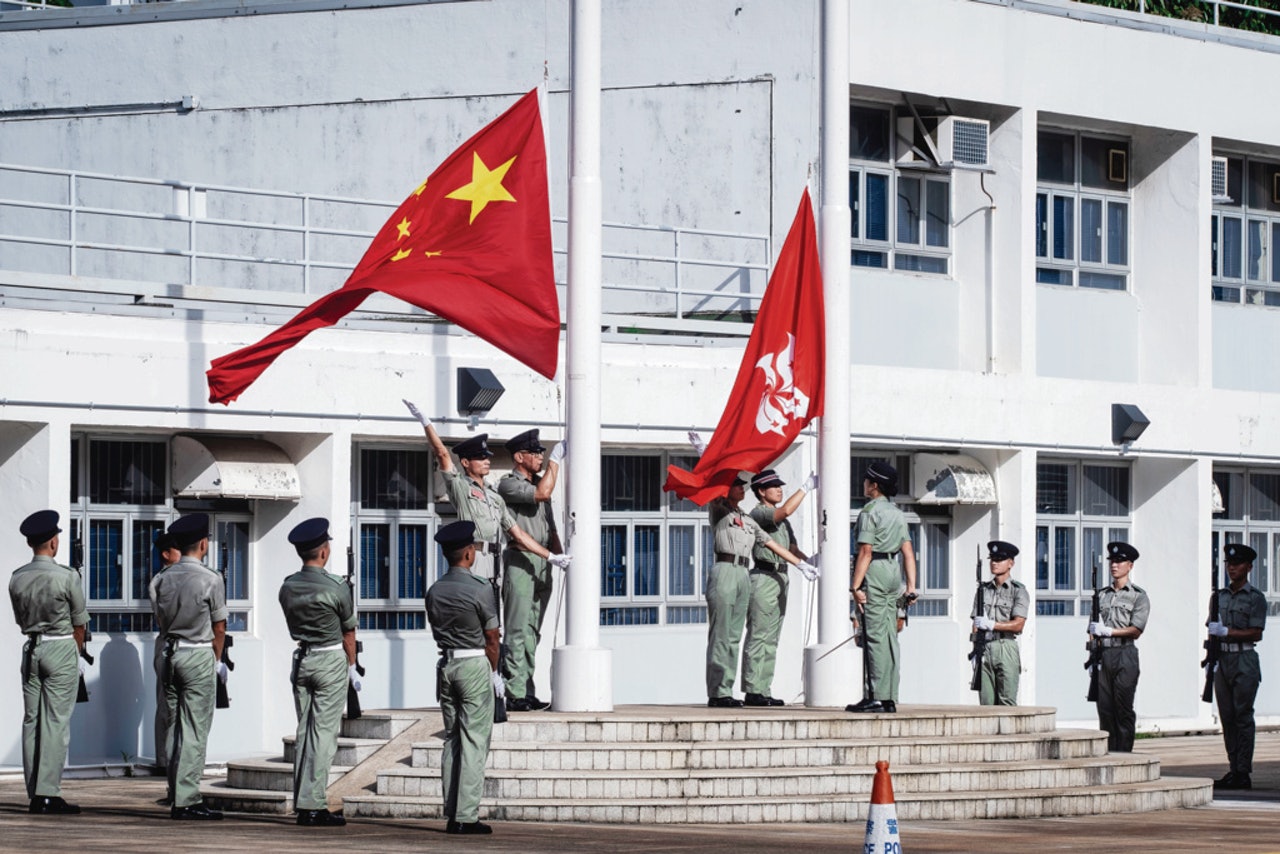【專訪-音樂劇《一水南天》創作者:大時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

【專訪-音樂劇《一水南天》創作者:大時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
周報特約撰稿人 撰文:伍麗薇 2020-06-27 12:00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場白,放在今日的香港毫不過時。這也是音樂劇《一水南天》的命題,主創人員張飛帆及劉穎途以1920至1941年為背景,書寫香港人在大時代下如何抵抗天命,如何在黑暗中展現人性光輝。
歷史不斷重複,看似老土的劇情,正正呼應着當下社會。一整年的反修例運動,疫情下經濟停滯,國安法悄悄到來,大時代下人心惶惶,兩位創作者都希望作品或多或少可以鼓舞人心,甚至為行業帶來一點點改變。
疫情衝擊各行各業,藝文界幾乎停頓,《一水南天》由香港舞蹈團及演戲家族聯合製作,是疫情放緩後本地第一個大型演出,演出規模及資源投放之大都是近年少見的。
故事講述潮州人陳一水在十九世紀末來港,由窮小子一步步打拚成為米行老闆,恰逢時代動盪引發米荒,眼見同行囤積居奇,炒高米價,但百姓卻因戰亂、飢荒苦不堪言,在利益與公義下,陳一水面臨巨大掙扎。

編劇張飛帆(左)和音樂總監劉穎途希望《一水南天》是一個好開始,於港人,於音樂劇界,以及逐漸失去的自由。(黃寶瑩攝)
最壞的時代最美的人性
編劇張飛帆形容《一水南天》是史詩式作品,時間跨度大,中間經歷戰亂、海難、米荒等事件,若要形象化比喻的話,是一部耗資幾億元製作的電影。宏大的背景,訴說的是平凡人的事迹。陳一水代表着上一代的香港人,他勤力,他肯捱,他也很精明,所以能在亂世中發迹。張飛帆用三個詞語概括這一代香港人的特質:出力、搵食、發財。「香港人從來都是要搵食,搵完食下一步便是發財。」
那麼發財之後呢?陳一水將米業經營得有聲有色,在糧食短缺的年代,開米行無異於印銀紙,人人都要開飯,做大米入口的,想賺多少錢就賺多少錢,是賣人血饅頭還是推翻米價,是賺到盡還是與民同行,全在一念之間。 陳一水的選擇,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選擇,在最壞的時代,總能看到人性最好的一面,放在現代香港,也很有共鳴,譬如疫情期間,有人炒口罩,也有人派口罩。
「人性是永恆的,我們並沒有刻意呼應時代,是時代呼應人性,就像莎士比亞的作品,你覺得它們呼應時代,因為人性永恆,歷史也是永恆。」
七年前構思音樂劇時,他們便想寫一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當時有兩個方向,一是寫新聞女郎,講創作自由,一是寫潮州商人在香港發迹,後者最後跑出。「在很多地方我都講過,香港衰不是這幾年的事,香港的風起雲湧,在這十年間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香港有許多艱難的日子,當時寫這個故事,我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香港以前是怎麼走過來的,那我們才會知道怎麼走下去。」
故事很有獅子山下的色彩,堅持便能走過逆境,互相幫忙便能跨越苦難,隱隱帶有樂觀的色彩。但現實是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飛帆不諱言即便處於滿是苦難的大時代中,他依然相信未來會更好。透過《一水南天》,他叩問天命,天命底下人要跪低還是群起反抗?故事結束在香港淪陷的一天,後來我們都知道,香港人捱過日本侵華、天災、瘟疫,最終成了國際都會,回頭再看,未來確是更好。「我很相信的,我信的原因是不能不信,如果我們連希望都沒有,那我們什麼都不會有。」
「戲裏有講,大善到即大惡到,有惡劣的事發生,譬如疫症,死了很多人,但地球的臭氧層修復了,中間有句歌詞令我印象好深刻─『每一個銀分兩邊』,每件事都有兩面,視乎你如何看待。」《一水南天》另一位創作者兼音樂總監劉穎途(阿途)補充道。

以1920至1941年為背景的《一水南天》,書寫港人在大時代下如何抵抗天命,如何在黑暗中展現人性光輝。(受訪者提供)
橫跨七年的創作 半杯水的道理,兩人深有體會。《一水南天》拖拉近七年,最終定在今年6月底演出,本身工作忙碌的兩人,因為突如其來的疫症,所有工作都被叫停,手停口停當然不好受,但他們也慨嘆,若不是有這空閒時間,很難應付這半年來不停改音樂改劇本的生活。
飛帆說,一切都是天意。從2013年開始構思劇本,中間不斷有朋友問他們,作品什麼時候面世,他們都無法說清,都在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機遇。直到2017年,他們出現第一個機會,演戲家族與香港話劇團做了七場圍讀,在話劇團的黑盒劇場進行,有點像外國音樂劇般,想試試市場水溫。這個方式對創作人、投資人而言,是很健康的做法。劇本值不值得投資、有沒有硬傷、觀眾反應如何,都可以一探究竟。當時圍讀的評價大都正面,服裝、燈光、氛圍都不俗,最後作品被香港舞蹈團睇中。
「中間有好多人都感興趣,亦有商業資金投資,但因為種種原因,最後我們與舞蹈團合作。」飛帆指,資源是其中一個考量,因為寫的時候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很重型的演出,沒有實力的大團很難負擔。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楊雲濤亦承認,製作這個音樂劇很吃力,舞蹈團從未試過做這麼大型的演出。
決定了6月27日的公演日子後,大家開始籌備演出,風風火火的,誰也沒想過疫症的出現幾乎推翻一切努力。自2月起,本地表演場地關閉,所有演出暫停,飛帆的另一個作品《大狀王》原定5月底公演,因為場館未開,最終延期。6月1日,場館重開,但只容許工作人員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進入場館工作,關鍵在於6月15日的新指引,即使放寬觀眾入場,人次也與原本的首演有落差。隔開坐,觀眾只剩一半,「天意,我們遇過很多天意,有時我都覺得是否上天在考驗我們。」飛帆苦笑。
但創作上再多的未知數,都比不上香港這個未知數。有段時間,他們情緒甚受影響,阿途說,試過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要寫情歌或開心的歌,很辛苦很困難,只能迫自己去做。飛帆則說,至少創作還是快樂的,在失意時可以透過寫作抒發情感,「我們還有創作,已經比很多人幸福。」

疫情之下,街道、康體設施都顯得十分冷清,也幾乎推翻劇組一切努力。(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做腰馬合一的音樂劇 坐在面前的兩人,一個看起來老成,一個書生感十足,沒想到一唱一和就似多年老友。嚴格來說,《一水南天》是兩人第一個合作的作品,沒想到一拍即合,中途合作了《時光倒流香港地》及《熱鬥獅子球》。老成的飛帆在訪問中常常說很喜歡阿途的音樂,很大器很澎湃很對胃口,「有時,我會說他的音樂好似開外掛般,有四個核彈頭,好勁。」 「一個銀分兩邊,有時太澎湃,事情會變質,我會提醒自己,要拉返來,不要由頭到尾都澎湃。」阿途不好意思地說。
兩人的音樂喜好相近,又特別鍾情音樂劇,七年前朋友介紹下便說不如認真寫一齣劇,再搵劇團來做,最後可能無法成事,但就是想慢工出細貨,能夠將每個細節都做好。阿途表示:「我經歷了很多個音樂劇,三個月寫30首歌,想都沒時間想,便要開始寫,質量連自己都過不了,我覺得很對不起演員,亦於心有愧,聽到他說和我一齊癲,即刻答應。」 三個月做起一齣戲,在香港很常見。香港劇場的生態是,一年前預約場地,構思半年,拍板做的時候只剩下三個月,時間與資源都很緊絀,出來的成品自然不盡如人意。「上年有內地製作人找我,說想做音樂劇,我說最重要的是時間,畀幾多錢都沒用,對方說那再傾。我希望《一水南天》的創作流程可以讓其他人借鏡,從而再思考如何做好的作品。」
音樂劇講求合作性,劇本、音樂、填詞、編舞,如何入歌,跳舞時怎麼入音樂,都需要互相配合,大家舒服才能成事。
飛帆形容,這是一個腰馬合一的過程,「以前做音樂劇,我最憎聽到一句:音樂劇最重要是音樂。當然,音樂很重要,好多人都用這個概念去做,你有沒有看過內地的『印象』系列,真的很賞心悅目,又激光又放煙花,但故事講什麼,可能只是一個男仔喜歡上一個女仔。」
音樂劇的靈魂是以故事推動音樂,歌曲之所以動人,是情節濃度可以發展成音樂唱出來,音樂的唱詞等於戲劇的台詞,男女對唱等同男女對話。「在劇情下唱一段,再由演員演出來,這便是音樂劇腰馬合一的狀態,而我們的粵劇便是這樣。」阿途亦說:「音樂劇最正的地方是,有些台詞未必適合直接說出來,但我們可以唱出來。」

香港舞蹈團及演戲家族聯合製作的《一水南天》是疫情放緩後本地首個大型演出,創作者希望作品可以鼓舞人心,帶來一點點改變。(受訪者提供)
藝術需要自由與氣度
唱唸做打,是傳統戲曲的基本功,音樂劇講求唱跳演,香港有粵劇傳統,理應有先天優勢發展音樂劇,可惜的是,這個優勢沒有被好好把握。目前亞洲做音樂劇最頂尖的地區是韓國,不只是音樂劇,韓國的影視文化在這十多年間快速冒起,已成產業,但在二十多年前,韓國的流行文化養分都從香港而來。飛帆解釋,音樂劇由西方而來,香港發展音樂劇已有二十五至三十年歷史。身處的是華洋雜處、東西匯聚的地方,加上本身有戲曲的底蘊,可說有豐富的土壤去醞釀屬於華人的音樂劇,但這件事並沒有在香港發生,中間曾出現過好的作品,但只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並沒有發展成一個行業或一個時代。
「韓國這些年急起直追,它的電影、劇集、流行音樂,完全打敗我們。它的音樂劇很頂尖,可說是東方的百老匯。當然,韓國也很西化,做很多翻譯作品,背後也在仿效西方,但韓國演員可以跳唱演,打兩個筋斗再唱跳,而且唱得好好聽,仲要靚仔和高。」飛帆說。「最近還做了《英雄本色》,是香港的《英雄本色》。」阿途強調。
工作以外,兩人曾相約到韓國看音樂劇,一口氣看了數個作品,其中曹承佑主演的《變身怪醫》(Jekyll and Hyde),娛樂與質量兼備,演員不斷變身,飛帆大讚水準好到「嚇死人」。「好勁,出來謝幕都要做好型的事,型到女仔不斷尖叫。」 技巧、功架都無可挑剔,作品是賞心悅目的,而且市場推廣很成功,利用偶像化演員吸納年輕觀眾,看音樂劇,原來也可以追星。「靚仔,唱得,仲要技巧好,公平咩?」他們忍不住吐槽。
歸根究柢,韓國影視業搞得有聲有色,主因在於政府願意投放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創作自由。
「韓國的政治好黑暗,但他們的電影好痴線,有暗殺總統、北韓人可以去南韓。香港都有創作自由,但大陸卻要審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電影來來去去都是這樣,反而韓國可以好燦爛。韓國劇集可以搵好多錢,每一件事都計算得很精準,連皇帝都可以玩,像《The King:永遠的君主》,原來有平衡世界,現實是大韓民國,而在平衡世界中有大韓帝國,皇帝過來追女仔,女觀眾當然開心,人家可以這麼大膽。」飛帆指,香港的優勢是有創作自由,但這種自由也開始有不自由之處,因為過於背靠大陸,作品入大陸需要通過審批,有些題材總是不能做。

(《The King:永遠的君主》劇照)
去年,飛帆擔任戲劇文本指導的劇場空間便發生類似事件。其中一個劇場作品《坂本龍馬の背叛!》的一則牆身廣告因繪有蒙面黑衣人撐黃傘,廣告商在自我審查下不批准發布,要臨時抽起廣告。類似的自我審查近年在戲劇界愈來愈常見,「多多少少都遇過,尤其返大陸做的作品,可以突然不做,電影更嚴謹,不是要審查,而是必須審查。」
國安法鬧得沸沸揚揚,兩人都擔心創作自由只會愈來愈少,另一方面也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自設框架,阿途說,《時光倒流香港地》也涉敏感題材,以為做不成,但最後也完成了,說明限制不是來自他人,而是自己。
飛帆亦說:「退一步講,我相信有些事需要氣度,好的作品未必要做些什麼,探討人性而已,就像《一水南天》,你可以有無限想像,它亦呼籲香港人要團結一致去對抗逆境,可以很正面。是社會變,不是我們變,當社會變的時候,你帶着不同的眼光來看,是可以的。藝術就是可以容納不同的看法,這就是自由,而這在創作上是需要的。」
他們希望《一水南天》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於2020年,於香港人,於音樂劇界,以及逐漸失去的創作自由。
*上文節錄於第21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2日)《專訪《一水南天》創作者:大時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