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與如來藏說的交涉─ 文:*賴賢宗* 教授
經教裏的禪法,因它是如來所說,後人因名之為如來禪。至於禪宗中的禪法,因它是祖師所倡,後人因名之為祖師禪。其實祖師禪也是如來所傳,並非祖師所發明,釋尊在靈山會上,把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咐囑摩訶迦葉,便是祖師禪的來源。
─禪與如來藏說的交涉─ 文:*賴賢宗*教授
摘要:
本文對禪宗思想史之中的「禪與如來藏說」的交涉的問題,加以闡明,進行反思。傳說中禪宗達摩祖師以四卷本《楞伽經》為禪悟之教證,《楞伽經》提出著名的「如來禪」,而《楞伽經》倡言「如來藏藏識」,是如來藏說的要典。在早期禪史中,禪法的形成與發展與如來藏說有不絕如縷的關係。考察「如來禪」一語最早即出現於四卷本《楞伽經》,重視「自覺聖智」,依如來藏理對眾生界行不思議禪觀,達摩師弟,遞相傳習此如來清淨禪,終於形成作為如來禪的達摩禪,這是以證悟大乘佛教「如來藏」、「佛性」為根本的如來禪,和當時同時流行的另外兩種 禪法(以數息為主的安般守意小乘禪法,以對治和念佛為主的兼融大小乘的禪法)鼎足為三。「如來藏禪」是印度禪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調「見性」思想,其後並開展出祖師禪「作用見性」的大機大用,這已是經由《涅槃經》「見性」思想的過渡,而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 的文化土壤上所開出的奇葩,而和印度古貌的「如來藏禪」對「信」的強調,二者在修行風格上和哲學型態上有所不同。
導論:
傳說中禪宗祖師達摩以四卷本《楞伽經》為禪悟之教證,四卷本《楞伽經》提出著名的「如來禪」,倡言「如來藏藏識」,是如來藏說的要典。藤田正浩在〈禪宗的見性思想與印度如來藏思想〉一文,闡明了禪宗的 見性思想與印度如來藏說的關係。在早期禪史中,禪法的形成與發展與如來藏說有不絕如縷的關係。印順法師也明確指出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他說:以「楞伽印心」,達摩所傳禪法,本質是「如來藏」法門;「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印順法師又說:印度傳來的達摩禪,從達摩到慧能,方便雖不斷演化,而實質為一貫的如來(藏)禪。因此,從達摩到慧能的禪不僅有「般若禪」的成份,其實也更是「如來藏禪」。在這裡,吾人必須注意下列三點:首先,在達摩禪中,所謂的二入四行是闡明信如來藏理而據以實踐其禪悟的禪法。其次,慧能禪強調「見性」和「本體」,也不能不說除了與《般若經》之外,也與如來藏說有深密的關係。 最後,在如來禪與祖師禪的中華禪宗的早期發展史發展中,也必須以如來藏說為背景,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對於中華禪史和中華禪的思想模式的理解。筆者對前述問題陸續加以論述。本文擬於「如來藏禪」的論理脈絡中,來探討達摩禪〈二入四行〉所蘊涵的「信」與「真性」,從如來藏說史及禪學史的角度,挖深其思想預設,並澄清若干禪學史上的疑點。
本論文分為下列三節:
一、《楞伽經》與如來禪
二、達摩禪〈二入四行〉所蘊涵的如來藏說與信
三、從如來禪的信到祖師禪的作用見性
在本文的第一節「楞伽經與如來禪」,說明如來禪與如來藏說的關係。在印度南北佛學的交流中,信仰如來藏說的著重禪觀的瑜伽師,發展出強調對如來藏理的信的如來禪,這個說法是相當具有可理解性的, 而筆者認為「達摩祖師」可能就是屬於這個系統。
筆者另文〈《寶性論》論信與佛性:如來藏與唯識的交涉中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之交涉〉,曾由對《寶性論》真諦譯《攝大乘論釋》、《佛性論》、《成唯識論》和《寶性論》的信與佛性概念做比較研究,藉此論述了信的三義與三種佛性及二者之內在關係的論述。
由此可以得知:1、如來藏說與瑜伽行的交涉。2、信如來藏理的強調在早期禪宗思想史之中是當時佛教教理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提出「如來禪」一語的四卷 本《楞伽經》之統合「如來藏說」與「禪」,此一統合與達摩〈二入四行〉強調對如來藏理、佛性的信,二者實有其內在理路的根據。
《寶性論》為早期三經一論之「一論」,《佛性論》為其異譯增刪本。《寶性論》、《佛性論》闡明「對如來藏理、佛性的信」,孕育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及其內在關連的論述。由此可見,如來藏、佛性之實有,與信如來藏理之內心心靈程式的相應與交涉此一洞見及論說一直存在於討論如來藏與唯識的交涉的論典中,有其相繼之發展,此一思想氛圍在吾人研究早期禪史文獻之「信如來藏理」,為深值注目之事。在印度南北佛學的交流中,信仰如來藏說的著重禪觀的瑜伽師,發展出強調對如來藏理的信的如來禪,這是相當可以理解的。傳說中的達摩禪或許就是屬於這個「對如來藏理的信的如來禪」的傳統。
本文第二節「達摩禪〈二入四行〉所蘊涵的如來藏說與信」,對達摩的〈二入四行〉做一分析,指出做為「如來禪」的達摩禪是「如來藏禪」,強調了對如來藏理的信是入道之鑰,這個強調一直延續到了傳為中華禪三祖僧燦所作的〈信心銘〉一文之中。筆者將上述論述延伸至對中華禪宗史的反省:「如來藏禪」是印度禪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調「見性」思想,其後並開展出祖師禪「作用見性」的大機大用。這已是經由《涅槃經》的「見性」思想之過渡,而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的文化土壤上所生長與綻放的奇葩,而和印度古貌的「如來藏禪」對「信」的強調,二者在風格上和哲學型態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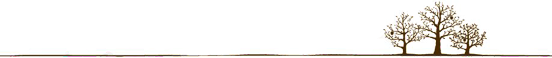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一、《楞伽經》與如來禪
(一)「如來藏」之語源考察
「如來禪」一辭之來源,學界有下列三說:1、「如來禪」起源於《楞伽經》卷二,區分四種禪:「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其中最被肯認者為「如來禪」。2、「如來禪」一語辭起源於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將禪由淺至深,分為五等,即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五種,其最上乘禪又稱如來禪,又認為達摩所傳之禪即此最上乘禪。然後世禪徒卻以宗密之如來禪為五味雜陳之禪,而別立祖師禪,用以稱呼慧能、馬祖的禪法。3、將「祖師禪」與「如來禪」相對而提出,因此有「如來禪」一辭之說法。就此而言,「祖師禪」之稱號或始自仰山慧寂和香嚴智閑關於「祖師禪」的公案,例如《景德傳燈錄》卷十一〈仰山慧寂章〉:「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牟宗三的禪學研究指出:「祖師禪」是將空宗之精神收攝於自心,強調實踐主體之能動性,開出存在地實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的禪法。而「如來禪」則預設一超越的分析(transcendental analysis), 以顯示一超越的真心(transcendental and authentic mind)。筆者認為,在前文上述三種關於「如來禪」一語的提出的脈絡當中,「如來禪」之原始語義當取《楞伽經》卷二之四門判攝,因此,如來禪是以《楞伽經》 所說的「如來藏藏識」為超越的預設,亦即以超越的分析而逼顯出「法界」作為修禪的依據。其次,宗密有禪師和華嚴教學大師的兩重身分,所以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所說之「如來禪」是融合華嚴法界觀而成,走向圓融的論義,不只如《楞伽經》在超越的分析中預設了法界和真心,因此宗密之如來禪亦有落入被批評為五味雜陳之禪的危機。
所謂的宗密的「如來禪」,不只是一般意義的法界的禪,而且是以華嚴法界觀闡明其圓融內涵,和後來的祖師禪強調的「作用見性」有很大的互相融攝的可能性,故後來有「華嚴禪」一流,宗密為「華嚴禪」之祖師。至於祖師禪強調的「作用見性」,在此,「見性」強調的是實踐 主體的能動性,而非一般意義的流於靜態的法界觀。「作用見性」則更強調的是大用現前,離開當下一瞬的主體實踐別無法界可得,因此也和強調靜態三昧的一般意義的法界禪觀,在風貌上有所不同了。祖師禪的「作用見性」強調的是佛性的大用現前,是更為接近「華嚴法界觀」所 說的「事事無礙法界」。相對於此,則可以說「如來禪」乃是「理法界」、 「理事無礙法界」的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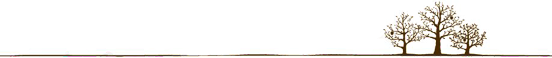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二)四卷本《楞伽經》與十卷本《楞伽經》對比研究
《楞伽經》有三個譯本。一是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的四卷本《楞伽 阿跋多羅寶經》(443 年譯),即傳說達摩以之為心要,並為楞伽師所依的經典。二是北魏菩提流支所譯的十卷本《入楞伽經》(513 年譯)。三 是唐代實叉難陀所譯的七卷本《攝大乘入楞伽經》(700-704 年譯),以 前兩種譯本的影響較大。《楞伽經》處理了如來藏與唯識的交涉的問題。 《楞伽經》的特色在於,它闡釋了佛學史中難以面對的問題:提出「如 來藏藏識」以處理如來藏緣起與阿黎耶緣起的問題(卷四)。以唯識和 唯心的內在銜接發展「三界唯心」的唯識思想(卷四)。以上是關於如 來藏與唯識的交涉,而「如來禪」實為「如來藏禪」。又,《楞伽經》區 分「宗通」與「說通」(卷三),提出「離念」的主張與禪的頓漸問題(卷 一),如來禪的聖智內證的禪觀修行(卷二)。
就其思想的文獻傳播的外部因素而言,達摩採用四卷本《楞伽經》 的理由:四卷本的譯出(西元 443 年出)比十卷本(西元 513 年出)還 要早將近八十年,達摩較早接觸的當是四卷本。從譯出到流通,也還需 要一個過程,因此達摩即使看過十卷本,也在晚年。
據道宣《續高僧傳》的記載,以四卷本《楞伽經》為依據的禪法,是通過達摩而傳到中原一帶的。依據《楞伽師資記》,楞伽師特別指出 要依四卷本《楞伽經》〈一切佛語心品第一〉的品名的解讀,從而重視心,而這個品名在十卷本並未出現。所以,楞伽師認為成佛之要乃在修「心」。所謂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其理據則為《楞伽經》。早期如來 藏說的三經一論中的《不增不減經》,就有「法身=如來藏=眾生界」,而到了四卷本《楞伽經》更塑造了「如來藏藏識」一辭,將如來藏說內塑於「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卷四)的唯識思想,指出藏識即為如來藏、佛性,從而指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理據,而因此四卷本《楞伽經》才為達摩禪所重視。
達摩祖師以四卷本《楞伽經》為心要,達摩禪一流不取十卷本《楞伽經》的另一個思想原因為:雖然四卷本、十卷本《楞伽經》二者都把如來藏和八識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但是「如來藏藏識」之說和「如來藏識不在識藏中」成為四卷本和十卷本的重要區別。四卷本《楞伽經》多次將如來藏、藏識用為一個名詞,認為八識即為如來藏,所謂「名如來藏識」、「名識藏如來藏」、「如來藏名藏識」、「此如來藏藏識」,四卷本《楞伽經》卷四並不區分「八識」與「如來藏」:
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
四卷本《楞伽經》卷四又認為如來藏藏識是轉依,是「善不善依」。又用「大海與波浪」的比喻來說明藏識(八識)與如來藏是同一個相即的實體。因此,禪的解脫是「不離不轉」藏識而即證得如來藏(佛性)的,四卷本《楞伽經》卷四: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為無始虛偽所薰。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清淨畢竟無垢。……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藏識。
而十卷本《楞伽經》則認為八識與如來藏並沒有相即的關係,認為 八識與如來藏有根本區分,是兩個不同的實體。如十卷本《楞伽經》卷七說:
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如來藏識、阿黎耶識境界,我今與汝及諸菩薩甚深智者能了分別此二種法。
因此,雖然四卷本《楞伽經》和十卷本《楞伽經》都把如來藏和八識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但是「如來藏藏識」(《楞伽經》四卷本所主張者)之說和「如來藏識不在識藏中」(《楞伽經》十卷本所主張者)成為四卷本和十卷本的重要區別。前者(四卷本《楞伽經》)主張藏識中,存在 有自性清淨的心,即是如來藏(佛性),因此如來藏(佛性)和藏識相 即為一,而為「如來禪」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理據。後者(十 卷本《楞伽經》)以如來藏為淨心、道心、真心,而又以阿黎耶(阿賴 耶識)為染心、俗心、人心,分列此彼,並認為「如來藏識不在識藏中」, 如來藏識、阿黎耶識是兩種境界,佛與諸菩薩甚深智者「能了分別此二 種法」。因此,十卷本《楞伽經》分列如來藏識為不生不滅,而阿黎耶 識(阿賴耶識)有生有滅,所以乃是走向《攝大乘論》真妄合和的系統,也就不適於達摩據以為如來禪禪法的理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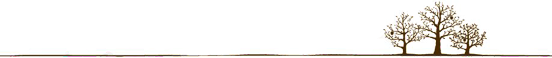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三)《楞伽經》、如來禪與達摩禪
傳說達摩以《楞伽經》為禪之心要。四卷本《楞伽經》確實也區分「凡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楞伽經》卷二: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雲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雲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凡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
此中之「如來禪」根據現代學者研究應即為「如來藏禪」。《楞伽經》在如來藏思想史上乃是屬於中期的經典,四卷本《楞伽經》地位是把早期三經一論的「如來藏三義」的有機構成和「阿賴耶識」唯識系統結合起來,而有「如來藏藏識」一語:
此如來藏藏識,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不見,雖自性淨,客塵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
如來藏系經典與如來禪的成立地點,由於文獻缺乏,實難斷言。而根據印順法師與木村泰賢的研究,吾人可以合理的推想:如來藏系經典初起於南印,後來才流行於罽賓和北印,在此流傳的過程中,一方面和 北印的唯識說合流;二方面與罽賓區的禪法結合,因此產生了《楞伽經》 的「如來藏藏識說」和「如來藏禪」,這在大乘佛學是一相當大的進展。而早期唯心學派的大乘瑜伽師一方面研究如來藏與唯識的交涉,二方面 同時深行禪法,正所以完成了此一進展。而達摩禪就是其中之代表。《續高僧傳》卷十六〈慧可傳〉:
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經》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可見達摩禪以《楞伽經》為經證,以之為心傳旨授。達摩禪〈二入 四行〉之「理入」: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
這裡的「理入」指的就是依如來藏理而入於禪。其中,「藉教悟宗」 之「教」當指《楞伽經》的教法,而「宗」則指「如來藏理」。傳說中 的達摩以《楞伽經》印心,此處乃為經文之相應之處。達摩的〈二入四 行〉此處所說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 可以理解這即前引《楞伽經》:「此如來藏藏識,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不 見,雖自性淨,客塵覆故,猶見不淨」。而對所悟之宗,又強調「信」(深 信含生具有如來藏)。因此,吾人可以說:作為如來禪之達摩禪,以如 來藏說為其教證,而「信」如來藏理又為如來禪入禪之鑰。
二、達摩的〈二入四行〉所蘊涵的如來藏說與信
(一)早期如來藏說與達摩的〈二入四行〉的「信如來藏理」 四卷本《楞伽經》所說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客塵所覆」、「入於一 切眾生身中」,合於初期如來藏說三經一論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以及「眾生界=如來藏=法身」之論理。達摩〈二入四行〉是達摩禪的主要文獻。〈二入四行〉是達摩禪的重要文獻,〈二入四行〉談論入佛道之方,提出理入與行入,理入即本論文所強調的「信如來藏理」之如來禪與如來藏說之交涉之課題,所謂「理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煩惱所覆,不能顯了」,而「行入」則為由信如來藏理, 「凝住壁觀」之後,更相稱而起的行動與倫理,即所謂「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其中,「稱法行」是稱法而起行,即相應於所信之如來藏理而生起行動之意,就禪之無功用行之立場而言,「報怨行、 隨緣行、無所求行」三者即須在如上之「稱法行」之下理解之,研此可見「信如來藏理」並依此而能有無功用之「稱法行」,實為達摩禪之禪 門入途與禪行之心要。達摩〈二入四行〉在此意義下是「如來藏禪」, 且強調對如來藏理(「真信」)的信,此信是其入禪門之鑰。
對「信」的強調,亦同樣見於三祖僧燦的〈信心銘〉之「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早期禪宗發展史之中,例如在達摩〈二入四行〉、四卷本《楞 伽經》和僧燦的〈信心銘〉之中,「信如來藏理」和「心意之轉化之禪行工夫」是彼此相需的,乃至於信如來藏理之信之心行即是如來藏理之開顯,此一課題顯示了如來禪與如來藏理之交涉之取向在早期禪史是相當重要的。
達摩認為應以《楞伽經》為心要,所以達摩系統乃重視《楞伽經》 終於形成「楞伽師」的楞伽講學系統。而考「如來禪」一語最早即出現於四卷本《楞伽經》,重視「自覺聖智」,依如來藏理對眾生界行不思議禪觀,達摩師弟,遞相傳習此如來清淨禪,終於形成作為如來禪的達摩禪,這是以證悟大乘佛教「如來藏」「佛性」為根本的如來禪,和當時同時流行的另外兩種禪法(以數息為主的安般守意小乘禪法,以對治和念佛為主的兼融大小乘的禪法)鼎足為三。淨覺(680-750 A.D.)所撰之《楞伽師資記》,以四卷本《楞伽經》的譯者求那跋陀羅為初祖,以達摩為二祖,混同「楞伽師」與「達摩禪」師承。《楞伽師資記》乃是北宗禪的文獻。呂澂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依北宗的《楞伽師資記》,認為楞伽講學系統的楞伽師與達摩的禪系統 有深密關係。宇井伯壽則辨析此二者的不同。筆者本文研究早期禪宗史,對如來禪與如來藏說的內在關係做出闡釋;並不採取傳統研究楞伽 師與達摩禪師承二者關係的進路,如胡適、呂澂、宇井伯壽。筆者此處亦不採取對敦煌文獻的達摩作品做深度解讀的進路,如關口真大所從事者。而是另闢蹊徑,筆者由達摩〈二入四行〉特重「信」與「真性」出發,在四卷本與十卷本《楞伽經》的對讀中,指出達摩特重四卷本的內在理據之一,乃在於如來藏(佛性)與藏識(八識)的相即為一,對此「真性」的描述,《楞伽經》明言其繼承自《勝鬘經》,為佛與上智菩薩真正能知,其他人只能是「信」人。《寶性論》與《楞伽經》是先後出現的如來藏說的代表性經論。筆者認為《寶性論》和《楞伽經》二者同樣是繼承《勝鬘經》之說,都著重對「如來藏理」的性,而有著「頓悟 漸修」的禪法特徵;由此可解明達摩禪的特徵。也就是說:達摩禪以對如來藏理的信為「理入」之禪悟之鑰,達摩禪以如來藏說為思想預設而提倡對眾生界的不思議禪觀。一般認為以《楞伽經》的教證而認為達摩禪是如來禪,若是以達摩〈二入四行〉為標準,則應該說達摩禪的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
傳統的看法以《楞伽經》提出「如來禪」一辭,而達摩以《楞伽經》為其教證,遂認為達摩禪是如來禪。達摩〈二入四行〉是達摩禪的主要文獻。〈二入四行〉談論入佛道,提出「理入」與「行入」。「理入」是對如來藏理的信(「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行入」則為由信此如來藏理,「凝住壁觀」後,更相稱而起的行動實踐與倫理關懷(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因此,達摩 〈二入四行〉不僅是「般若禪」,也是「如來藏禪」,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如來禪」,而且強調對如來藏理(「真性」)的「信」,是其入禪門之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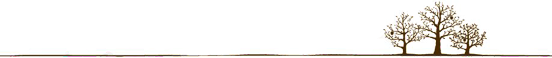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二)達摩的〈二入四行〉的稱法行
許多文本都題為達摩所撰,例如〈絕觀論〉、〈破相論〉、〈悟性論〉、〈血脈論〉等,都統稱為「達摩禪師論」。但根據近代及現代學者的研究,一般認為〈二入四行〉可確定為達摩的代表性的著作。在關口真大的研究中,則強調敦煌出土的寫於 681 A.D.之《達摩禪師論》可代表達摩思想,而強調了《達摩禪師論》在達摩研究上的重要性。19方廣錩整理《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又名《達摩禪師論》,方廣錩認為是中國僧人假託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所撰典籍,著者不詳。在敦煌遺書中,至今已經發現兩種題名為《達摩禪師論》的文獻。其一為日本橋本凝胤所藏, 首殘尾存,尾題作「達摩禪師論」,唐高宗開耀元年(681)所書,這也就是後來被收入關口真大《達摩大師之研究》一書中的文本。第二種是日本田中良昭於法國敦煌特藏中所發現的伯 2039 號(伯希和帶至法國的收藏本)。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北新 1254 號與北新 1255 號其後,經田中良昭先生鑒定,此中的第一個闕名殘文獻即《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的又一個抄本。《達摩禪師論》的部分思想內涵和〈二入四行〉相當一致。例如《達摩禪師論》的「達心門」乃是「由常看守心故,漸達自心,本性清淨,不為一切煩惱諸垢之所染汙,猶如虛空。」〈二 入四行〉之說「客塵妄想」、「真性」都可被了解為「如來藏說」。而吳 汝鈞〈達摩及其早期禪法〉研究《達摩禪師論》也指出後者主張:
以舉眼觀法界眾生,一體一相,平等無二,一等看故一種,皆是 如來藏佛故,以常用一清淨心故,以常乘一理而行故,即是頓入一乘。
又如《達摩禪師論》的「安心門」說「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迷是自心變作,知境界唯是自心作此,觀自然漸合唯識觀智。唯識者,遮詮為義。遮卻雜染虛妄之法,詮取真如佛性者。不去不來,不生不滅,不取不捨,不垢不淨,無為無染,無有自性。」
吳汝鈞〈達摩及其早期禪法〉研究《達摩禪師論》也指出後者主張:
法佛者,本性清淨心,真如本覺,凝然常住,不增不減。
這裡提到「如來藏佛」和「本性清淨心」,因此,《達摩禪師論》的基本觀念是如來藏和自性清淨心。再者,《達摩禪師論》引用了不少如來藏說的經典,如《如來藏經》、《勝鬘經》,也引用了與在義理詮釋上涉及如來藏說的《維摩詰經》、《法華經》,更可見出《達摩禪師論》以如來藏說為教證。而就文獻學而言,《達摩禪師論》所引述原典,其譯文相當古樸而忠於原文,在達摩時代沒有出現過的譯經譯論的文字,和當時未曾運用的語詞,則未出現,可見《達摩禪師論》確實為早期禪宗史的作品。因此一版本的《達摩禪師論》(敦煌出土的寫於 681 A.D.)的 研究,使得達摩禪是「如來藏禪」,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吳汝鈞《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指出,〈二入四行〉計有十一個本子。筆者本文所根據者,乃載於《楞伽經師資記》中,而為柳田聖山《禪の語錄 I 達摩語錄》所採用者。
對應於上節的論述,筆者對達摩禪〈二入四行〉的內涵從事下列分析:「二入」為「理入」與「行入」。首先,「理入」為「信」如來藏理而能入於禪之體性: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兩種。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聖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自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為理入。
信如來藏理,進而對此「信」經過「凝住壁觀」的錘鍊,而達至「與理冥合」也就是修禪者與如來藏理的冥然相應。「理入」思想應為中印思想之合璧。柳田聖山指出:中國佛學中對「理」一詞重視,早出現於《維摩詰經》〈問疾品〉道生注、《涅槃經集解》第一,以及吉藏《淨名玄論》第三。而「理入二行」之說,則已經見於《金剛三昧經》〈入實際品〉。至於〈二入四行〉一文所說的「真性」,則有《莊子》〈漁父〉 所說的「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以及《中庸》「天命之 謂性」,已經存在這些中國心性論的基本命題。
其次:「四行」分為前三後一的兩組,前三是「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後一是「稱法行」。由「將倫理建立於超自然的根源之基礎的非結果論」來研究如來禪的倫理,「稱法行」正所以明示了此性格。而「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則是建立於其上的倫理規範。又,稱法行是相應於不著兩邊之空之佛法而行,「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 取相。此為自行,亦為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
上述所論的「稱法行」,此中有數點值得注意:
(1)此中之「性淨之理」指如來藏理。
(2)此性淨之理一方面「無染、無著、無此、無彼」,二方面「稱化眾生」,亦即:一方面不離法身,同時又不捨眾生界。因此,〈二入四行〉言簡意賅地敘述了如來藏說的「眾生界=如來藏=法身」的論理。
(3)「此為自行,亦為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則是陳述了「眾生界=如來藏=法身」的超越實體當開出利他的倫理規範,是以可以理解它為一「非結果論」的倫理學,在此開為「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三條主要的宗教信念倫理學(Gesinnungsethik)之倫理規範。
三、如來禪的信到祖師禪的作用見性
根據印度佛教發展史的了解,自性清淨心〈「心性本然清淨,但為客塵煩惱所雜染」〉首先出現於部派佛教的文獻,例如《舍利弗阿毘曇》。以後大乘佛教發展中的如來藏思想,將自性清淨心之說予以發揚光大,當然以上兩者對自性清淨心的詮解各有不同,差異甚大。關於對於自性清淨心的詮解,在大乘佛教發展中的如來藏思想,包含了《佛性 論》〈真諦譯〉所示的一套特殊的三種佛性的如來藏構成。
藤田正浩在研究禪宗見性思想與印度如來藏思想時指出:如來藏與佛性可視為同義語,在印度之三經一論使用如來藏一語,《涅槃經》則將之轉變為佛性一詞。根據柳田聖山或田中昭良的研究,南宗禪受《涅 槃經》影響很大,「見性」思想是南宗禪的特色,「見性」就是「見佛性」。藤田正浩指出:buddhadhatu(佛性)一詞中,dhatu 可說具有 hetu(因)之義,因此,在印度 buddhadhatu 是指成佛的可能性。29可是筆者本文對於《寶性論》的「佛性」概念的研究,則指出:《寶性論》的佛性概念,包含了因、德、果三層次,而為《佛性論》三種佛性說所繼承。因此,就印度傳來的佛性說的內面結構而言,佛性、如來藏內含眾生界,以 hetu 解 dhatu,則佛性則是還在因位,在《寶性論》說為「菩提」,在《佛性 論》說為「住自性佛性」。在高崎直道對 dhatu 的研究中,指出「法界」 (dharmadhatu)有兩種意義:(1)「法之全領域」,此用法等同於說「一 切法」。(2)「法出生之因」(dhatu=hetu),亦指一切法的根源、本質。但,漢譯將 buddhadhatu 譯為佛性,則隱含了和中國思想之心性論結合的可能。正如前述,在印度的如來藏說中,例如在《寶性論》中,是較強調對佛性、如來藏理的「信」,因此解釋者比較容易流於以 hetu(「因」)來解 dhatu(「界」)而忽略佛性之「因果一如」的如來藏說的隱藏的內涵。從禪宗六祖慧能對佛性一詞的使用,可以看出他意義上的轉變。「佛 性」(在《壇經》有時作「自性」、「真如本性」)不再僅只被當作「成佛 的因或可能性」,而是佛性乃是眾生本具與現成。像這樣的佛性思想已經見於南方的《涅槃經》研究者,而經道信、弘忍、神秀、慧能更發展出禪宗特殊的「見性」思想,這其實反而是較近於《寶性論》、《佛性 論》的因果一如的如來藏說、佛性論的本意、或說是隱藏著的有待被解明的意涵。
就如來禪(如來藏禪)而言,如來藏理為凡夫所難信難解,但印度文化素有強調信的氛圍;所以透過對達摩禪與如來藏說、《楞伽經》、《寶性論》的討論,可以理解下列「信如來藏理」所引生的禪行的心靈程式:如來禪強調對此如來藏理之實有升起淨信心(信其實有,因),由此信而使得自心得到淨化,並得到自信清淨心的諸種功德(信其有德,德); 最後,淨信心與佛性是不二的,因此能有自性清淨心和佛性的種種大用(信其有能,果)。筆者的《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一書等研究成果已經闡明「信」之三義:信其實有(adhisampratyaya)、信其有德(prasada)、信其有能(abhilasa)是通用於《俱舍論》、《寶性論》、真諦 譯《攝大乘論釋》、《成唯識論》。「信之三義」可以「實有」、「有德」、「有能」簡示之。而唯識思想之信之三義之近於阿毘達磨的信之三義者,在於唯識之信之三義是一有機的連結。而《寶性論》之信之三義之更進於唯識思想者,在於《寶性論》多了一個佛性論的佛教存有學的向度(「轉身實體清淨」)。在此向度中,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有一內在連結,涉及意識與存有的交涉的哲學問題的處理。而此內在連結的關鍵在於「因果一如」所提供的契機,亦即在於前述《寶性論》「自性清淨」與「離 垢清淨」。
其實,如來禪強調「信」的特色,不僅見於達摩禪〈二入四行〉之「理入」,亦一直延續到傳為三祖僧燦所做的〈信心銘〉之「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信」(對如來藏裡的信)如「自性清淨心」是不二的。復次,就祖師禪而言:「見性」就是見此眾生內在的佛性之本具與現成,例如《壇經》所說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萬法。」見性思想是要藉禪悟之根本體驗而泯除因位與果位的區隔。因此,相對於印度的如來禪之重視對如來藏理的信,中國祖師則強調見性之直下的禪悟。於印度大乘佛教的如來藏說之三經一論之中,「信」為重要課題 之一,信煩惱為客塵,信如來藏自信清淨心之實有、能有與功德。此中, 信之心靈程式並未落入因位與果位的區隔,但是它並未明言「知見此如來藏」、知見佛性。藤田正浩指出:「根據《寶性論》所引《涅槃經》之文,『見』的原語是作pasyati,《涅槃經》的西藏譯本也是使用相當於pasyati 的 mthonba,基本上他們都只是意謂著普通的『見』。」「見性」一詞 之特義則為中華禪所獨創,經由道信、弘忍至慧能而顯著。其實,由上可知,見性思想是預設了印度如來藏說的論理方為可能,「見性」是中華禪者對「眾生界=如來藏=法身」之「如來藏三義」的有機構成的體證。
總之,達摩禪〈二入四行〉繼承了《楞伽經》的「如來藏說」,所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聖凡同一真性」,而此處使用了「真性」一辭,已將印度如來藏說,結合於中國思想之心性論,處理了意識與存有的交涉(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Being)的哲學問 題,如前所述,印度的如來藏說以自性清淨與離垢清淨為此一交涉的關鍵與契機。歷經道信、弘忍、神秀、慧能以其禪悟深入抉擇「如來藏說」的深義漸漸發展出禪宗特有的「見性」思想。到了慧能法嗣馬袓道一與石頭希遷,則積極將見性思想運用到中國思想中的體用哲學的文化 土壤上,而禪學中,形成了強調「作用見性」的袓師禪。中國思想中的體用哲學在華嚴宗,則形成法界觀(尤其是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其實,體用哲學正是中國思想對意識與存有的交涉的哲學問題的特殊解答。到了總集華嚴與袓師禪的宗密(780-841)作《禪源諸詮都集》遂走向華嚴禪的圓融。從印度如來禪對如來藏說的信,到達摩禪的「真性」,到道信、弘忍、神秀、慧能的「見性」,到袓師禪的「作用見性」,到宗密的華嚴禪──是印度如來禪到中國袓師禪的基本發展軌道。
關於如來藏說、南宗禪與中國體用哲學的關係,吳汝鈞說:
南宗禪的思想乃淵源自如來藏體系的佛性思想以及講求不取不捨的妙用的般若思想。禪能夠揉合此兩大思想,無疑是充實了它的思想內涵,更避免了兩系思想的各執一邊的問題。佛性是發揮妙用的主體,妙用的主體隨意起用而表現的積極性。這種體用無間的哲學,是禪的精妙處,不過,這體不是指形而上的體。它是 與用對比著說的體,是在主體性與其發用關係下說的體。
吳汝鈞在此點出南宗禪、如來藏關係,此為確見,但他在以體用哲學來論述南宗禪時,只把體解釋為主體性、與用對比著的體,而把用解釋主體性的發用。姑且不論海德格對主體性哲學的種種批判。單就禪學史的反省而言,吳先生此論不免又落入了「僅只」以傳統般若學來詮解禪宗與禪學史的限制,遺漏了禪與如來藏說的深密關係。如本文所說的,如來禪以如來藏說為思想預設。如來藏說強調「轉依」、「轉身實體清淨」,此中的「實體」是《寶性論》「無垢如」之八種句義之一,這些 無疑的都是佛教存有學(Buddhist Ontology)的論述,透過做為如來禪的達摩禪,這些論述早已深化為中華禪不可分割的部份,前文對此過程已加以論述。
進而言之,中國思想之體用哲學不論是「即用顯體」或「體用一源」,皆避免了佛教存有學滑轉為實體學(Ousiology),避免落入海德格所批評的「存有神學構成(Onto-Theo-Verfassung)」。而中華禪法 更以實修莊嚴了此向上一機之畢竟空義之菩提道;臨濟禪和曹洞禪就是 結合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之即用顯體與體用一源而有的兩種形態。分而言之,「即用顯體」是性體之直接下貫為心體之顯發,是「縱貫縱生」系統(用牟宗三先生語),馬袓道一的禪法屬之,開為臨濟禪。而「體用一源」是性體直接下貫與心體之顯發皆是契機,而皆由不一不二的共同根源所衍生(雖然在佛教存有學中,此根源亦無實體性),是「縱貫 橫統」系統,石頭希遷的禪法屬之,開為曹洞禪。
綜合上面所述,吾人可以理解不論是後世的「四喝八棒」(臨濟) 或是「五位三路」(曹洞)皆以印度佛教早期如來藏說為隱含的理論背景,因此可以理解「作用見性」,雖然是中華禪法的奇葩,但並無法與印度佛教早期如來藏切斷其歷史連帶,從印度之如來禪到中國的袓師禪,中國的袓師禪「呵佛罵袓」似乎迥異於印度之如來禪「信的強調」。雖然,中國的袓師禪「大機大用」似乎迥異於印度之如來禪「由信而延伸的倫理」,但是,可以了解它們都是為了「傳法救迷情」,而設施的方便。而中華禪在形成的過程之中,融會了中國思想的體用哲學,顯發為中華禪法瑰麗異采,尤其是表現於祖師禪的「作用見性」。「見性」一詞 之特殊義涵為中華禪所獨創,經由道信、弘忍至慧能而顯著。尤其是「作用見性」更是強調主體性的「大機大用」。見性思想是預設了印度如來藏說的論理方為可能,「見性」是中華禪者對「眾生界=如來藏=法身」之「如來藏三義」的有機構成的體證。
本文對於達摩的〈二入四行〉做一分析,指出做為「如來禪」的達摩禪是「如來藏禪」,強調了對如來藏理的信是入道之鑰。筆者也將上述論述延伸至對中華禪宗史的反省。結論在於:「如來藏禪」是印度禪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調「見性」思想,經由《涅槃經》的「見性」思想之過渡,其後開展出祖師禪「作用見性」的大機大用;印度禪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的文化土壤上,綻放奇葩,祖師禪的「作用見性」發揚菩薩禪的大機大用,棒喝交加,風馳電掣。這和印度古貌的「如來藏禪」對「信」的強調,相對而言比較靜態與內斂,二者在風格上和哲學型態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註﹞賴賢宗(1962年6月29日-),臺灣學者,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臺灣藝術大學、佛光大學、華梵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慕尼黑大學東亞學院約聘教師,曾任《國際佛學研究》雜誌編輯、《思與言》雜誌總主編、《新陸詩刊》海外通訊員、台北市丹道文化研究會理事長,舉辦過個人畫展,為笠詩社同仁。現任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長領域為佛教哲學、新儒家哲學、美學、比較哲學,早年亦出版詩集。
賴賢宗於1982年在懺雲法師座下皈依佛教,1983年從聖嚴法師在農禪寺打禪七,後除了修持淨土和禪,也出入密宗、瑜珈、丹道,及基督教的靈修,同時注重理論與實修。1994年入德國慕尼黑大學隨布魯克(Michael Von Bruck)及勞伯(Johannes Laube)學習佛教哲學,指導教授為佛申庫(Wilhelm Vossenkuh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