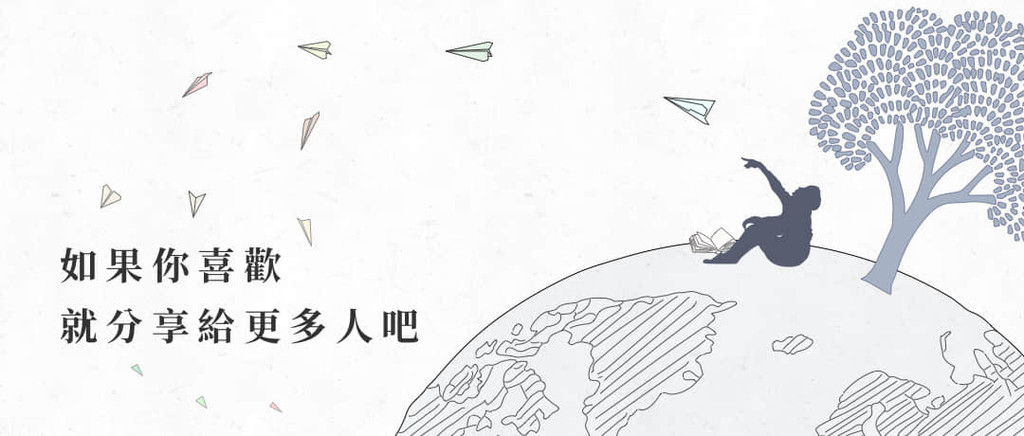*「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世界有多少痛苦歷史...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世界有多少痛苦歷史.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善於書寫世人的苦難與英勇。她在白俄羅斯出生、成長,是作家也是記者,筆下記錄了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事件,而這些事件大多通過她與當事人的訪談寫成。年初,她的新作《二手時間》中譯本在中國出版,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這個夏末來到上海書展和北京的國際圖書博覽會。她說:「現在到了一個孤獨的靈魂建設、家園建設的時代。我猜,人在渴望幸福。」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是個繁忙無比的人。這位白俄羅斯的女記者,習慣帶着她的錄音設備和筆記本滿世界飛奔,「帶着真誠和快樂,繼續做着自己渺小的工作」。
2016年初,她的「烏托邦之聲」最後一部——《二手時間》的中文版面世,我們第一時間給她發去了詳細的採訪信件。在兩個月的等待後,67歲的阿姐發來萬字回覆。據說這些問題她答了好幾天,過程中因觸發「過於深沉的情感」而數度擱筆。
2016年,是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烏托邦》發表500週年。世世代代,無數人類試圖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夢想,從未熄滅,阿列克謝耶維奇看到了這一點,她無不悲哀地預測,「烏托邦還將會長久地對人進行誘惑」。
阿列克謝耶維奇對這個問題憂心忡忡,她看到了後蘇聯時代人在面對普通生活時所展現的笨拙。她不能忘記,在清理切爾諾貝利事故時,一天晚上,她坐在善後處理者的宿舍裏。桌上立着一瓶三升裝的家釀酒,大家聊起了齊奧爾科夫斯基和戈爾巴喬夫,聊起了斯大林和希特勒,聊起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
這時一個上年紀的女人來送吃的,阿列克謝耶維奇看見這個女人的那雙有大大的紅點的手,「您的手怎麼了?」「我們每天給我們的孩子們洗工作服。工作服有毒。上頭許諾說送來洗衣機,但是沒有運送過來。我們只好用手洗。」「這怎麼行?」「上頭許諾了。」辦公室主任擺擺手,繼續高談闊論。
她相信,西方人更樂意談談洗衣機,而不是關於齊奧爾科夫斯基瘋狂的思想。可是俄國人不行,因為「俄羅斯人不想簡單地生活,想要為了什麼意義而生活。俄羅斯人希望加入偉大的事業」。
這「偉大的事業」,卻蛀空了他們的內心。曾有的禁錮解除了,為掙脱禁錮而遭受的苦難,並沒有讓人們的精神變得更豐富。當烏托邦遠去,日常重新回歸,人們還知道該如何生活嗎?
1.見證俄羅斯的經驗:你能找到一個誠實的人嗎?
問:在談這本書之前,我記得你曾說,無論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還是塔吉克人……說到底都是同一種人,叫做蘇聯人,那麼你覺得「蘇聯人」區別於其他人群的特性是什麼?
阿列克謝耶維奇:俄羅斯人,或者說蘇聯人,最大的特性在於,我們的資本是痛苦。這是我們經常獲取的唯一的東西。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氣,而是痛苦。我懷疑,在我的書中,正是它吸引了西方的讀者,讓他們覺得驚奇。就是這種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活下去的勇氣。
今天到處都需要這種勇氣。在薩拉熱窩就曾是這樣。不可計數的墳墓。人不僅被埋在墳地裏,還被埋在運動場上、公園裏。對這些事件的描述就像恐怖故事……一個人體內的人性所剩無幾。只有薄薄的一層。
為了活下來,俄羅斯的經驗是需要的。俄羅斯的文化中,具有人類在地球上建設天堂的最天真、最可怕的嘗試,最終這一嘗試,以一個巨大的兄弟般的墳墓告終。我認為,觀察這個實驗、做完這項工作是重要的,因為「烏托邦還將會長久地對人進行誘惑」。
問:《二手時間》是你的「烏托邦之聲」的最後一部,你會如何描述這本書?
阿列克謝耶維奇:它講的是最近幾年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情。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我們期待了那麼久,但所有人都很失望,無論是曾經持不同政見的人,還是商人、共產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甚至是流浪漢。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大街上的人比作家們更加有趣。
為了理解我們曾生活過的時代,我使所有人發出聲音。每個人都在說出自己的真理。我本人是一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人,但為了勾勒那個時代的形象,我應當聽各種人的聲音。
這本書的先聲和草稿,是《被死神迷惑的人》,一本描述社會主義帝國廢墟上自殺事件的書。一幅解體後的心理肖像畫。我選擇了那些與時代緊緊相連,像粘在膠水上的飛蛾一樣,粘連在時代上的人。他們在自己的生活與一種思想之間畫了等號。今天這顯得怪異、不正常,而當時那就是我們的生活。這都是一些誠實的、堅強的人——阿赫梅羅耶夫元帥、女詩人尤利婭・德魯仁娜、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英勇的守衞者季梅林・基納托夫……
問:在《二手時間》的扉頁上,你引用了大衞・魯塞的話,「受害者和劊子手同樣可惡,勞改營的教訓在於兄弟情義被踐踏。」而你在書裏,亦表達了這樣一種受害者的心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混淆善與惡的差異,「選擇性遺忘」就是一種典型做法。在我看來,善與惡是一個根本問題。《二手時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一個主人公在自己還是個小男孩時,喜歡上了一位成年女性,奧利婭姑姑。後來他讀大學時,改革開始了,媽媽告訴他,奧利婭姑姑出賣了自己的親哥哥,致使他被關進了集中營。這個時候,奧利婭得了癌症,已經奄奄一息了,他來到她那兒,問她:「你還記得1937年嗎?」她回答道:「哦,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是我生命最好的時候。我那時非常幸福,有人愛着我……」他問;「可是你的哥哥呢?」而她回答說:「在那個年代,你能找到一個誠實的人嗎?」他震驚了——關於那個時代有那麼多描述,出版過那麼多本書——而她卻一點都沒有懷疑過自己行為的正確性。
問:對於親歷者的這種「選擇性遺忘」,你會如何評價?
阿列克謝耶維奇:混淆了善惡之後,我們就喪失了判斷力。我們以為出版了索爾仁尼琴的書,生活就不會再像從前那樣。但書籍剛一出版,所有的人都奔向了其他的東西——奔向了消費主義。生活如潮水一般湧來。或許,人們選擇了新型的洗衣機代替卡拉什尼科夫的自動步槍,把精力消耗在這上面是件好事。但這些精力還是消耗掉了。以前還可以說,惡就是貝利亞,就是斯大林,它已經被人格化了。而事實上,惡散落在生活之中,生活的慣性本身將它掩蓋住了。每個人都在過自己的生活,這種生活的慣性,能夠遮蓋住一切它想要隱藏的東西。當然,也還是會疼,會叫。我想:總有一天,所有人都會醒悟。
現在到了一個孤獨的靈魂建設、家園建設的時代。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學習思考自身,講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從這種大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和我們的人聊一聊支撐生活的那些事物。
2.來自歷史的束縛:人變得更加開放,卻不自由
問:在《二手時間》的開篇你曾提到,在為創作這本書而進行走訪的二十多年時間裏,無論你遇見蘇聯時代還是後蘇聯時代的人,總會問同一個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為何兩代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是一個永恆的問題。 我們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義何在?如果不管怎樣都會重複,它們又能教會我們什麼?我經常問自己這件事。當我向我的主人公們提出這個問題時,它迫使人陷入措手不及的狀態。
對於很多人來說,這痛苦,是一種自我價值的體現,是他們最主要的勞動。但事實證明,痛苦並不能轉化成自由。
阿赫馬杜林娜寫過這樣的詩句,「劊子手和受害者在同等程度上毀壞了孩子純真的夢」。而沙拉莫夫的話更加殘酷無情——「集中營的經驗只有在集中營裏才被需要」。我沒有答案。我應當誠實地承認這一點。但我從小就被惡與死的主題折磨,因為我成長在一個戰後的白俄羅斯農村,在那裏每個人談的就是這些。
問:為什麼你們的痛苦沒有轉化成自由?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也一直困惑於這個問題。從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的時代開始,人們就誇大了痛苦的魅力。就像夫謝沃洛特・洽普林所說的那樣:謝天謝地,填飽肚子的時代過去了,人應當受苦。但這已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異化。我開始想,相反地,痛苦固化了人的心靈,它再也不能夠發展。不管怎麼樣,為了發展,人需要幸福的、正常的生活條件。這也是索爾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辯論——我終歸會站在沙拉莫夫那一邊。
問:從「烏托邦之聲」的第一本書《戰爭中沒有女性》到最後一本《二手時間》,你是否認為書裏的主人公發生了什麼變化?
阿列克謝耶維奇:現在唯心主義的人變少了。甚至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他們也感覺自己被騙了,他們從那個大餡餅中什麼也沒有分到。除了那些躺在盒子裏的獎章,他們沒什麼給自己的子孫。而對於他們的孫子來說,這些獎章已經一文不值。
現在人們談論自己的時候更加坦率,他們原原本本地談論一切。也就是說,如果閲讀我們的經典文學和蘇聯文學作品,以前彷彿不存在生物學上的人:那些作品中沒有一個具備內臟器官的人。為什麼人們會讀西方文學?因為那裏談到了身體,談到身體的秘密,談到愛情既是美好的,又是可信的。而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文學中一點也沒有!而如今人們聊天已經百無禁忌。人變得更加開放,卻不自由。
我沒有見過自由的人。所有人多多少少還像蘇聯時期一樣,在某種程度上被束縛,被定在某種經驗之上。但坦誠已經顯露了出來,致力於某種寬闊的才能已經出現,詞彙量在發生改變。我在我的新書中要寫的恰好是這種感官的新脈絡,詞彙的新脈絡。
3.尋找生活的重心:法國人有多少種詞描述愛情啊?
問:蘇聯解體後,上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發生的種種,你會給出怎樣的評價?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評價90年代時,我會更加小心。不管怎麼說,這曾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還記得,人們的臉轉換得多麼迅速,連行為舉止也是。自由的空氣令人迷醉。但剩下的問題是:我們要在這塊地方建什麼?
那時我們想:數千人讀完了《古拉格群島》,一切都要改變了。今天我們不僅讀了索爾仁尼琴,還讀了拉茲貢,還讀了麗姬婭・金茲博格……然而改變得多嗎?不久前我在畫家伊利亞・卡巴科夫那兒找到了表達現狀最準確的形象:以前所有人和一個巨大的怪物作鬥爭,這種鬥爭使得一個小人兒變大了。等我們戰勝了這個怪物,四處回望,突然看到,現在我們需要和老鼠們生活在一起。在一個更加可怕,更加陌生的世界。各種各樣的怪物在我們的生活中,在人的種屬裏鑽來鑽去。不知為什麼,它卻被稱作自由。
問:你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複製品的世界,那我們應當怎樣從這個世界走出來呢?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們的知識分子精英最終應該發聲了。應當作出一些思索,考慮我們處在何處,發生了什麼事情。應當展開與社會的對話。
在俄羅斯歷史中,首次出現這樣的狀況——精英分子遠離了自己的職責。非政治性和奴性成為合乎規矩的、價格不菲的商品。精英們突然開始不加挑剔地為權力和錢袋子服務。不久前我聽一位年輕作家講:「我身價很高。」「你是指你的書?」「不是,是我能提供的政治服務。只要我站對了隊伍。」而以前,正派的作家選擇的是其他的東西。
問:你選擇的是什麼?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選擇探索人的幸福和痛苦之謎。所有人都倦怠、困惑於宂長的歷史停頓。我們依然沒有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有所收穫。這是為什麼呢?它盤踞在了人的腦皮質下層。在這之後,人才轉向個人生活,轉向愛情。
譬如說,表示「雪」,我們只有一個詞「Снег」,而楚克奇人有幾百種表達。他們對於濕雪和乾雪、晚上的雪和早晨的雪都有單獨的詞彙。法國人有多少種詞描述愛情啊!而我們只有「玫瑰」或者「眼淚」,要麼就是黑話。
我們沒有幸福的經驗,我們的整個歷史,要麼是在戰爭,要麼是準備戰爭。我們受到自身歷史的壓抑。
從沒像瑞士人荷蘭人那樣生活過。在那些國家,每個人都有生活的重心:與其他人——男人或者女人的約會。而我們只有戰爭、解體,現在烏克蘭正深陷僵局……而50歲之後聊天的內容只有孩子。我已經採訪了幾百人。在這些人中間幾乎沒有一個幸福的人。有的只是驚心動魄的意外,以及被忽視的幸福。
4.孤獨靈魂的建設:學習思考自身,講述自己
問:今天的俄羅斯人,除了偉大的歷史和平庸的生活這二者的搖擺選擇,是否正在萌發出一種新生的追求?
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家不是占卜師,也不是魔術師。他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能分享的只是自己思想、自己的心靈起作用的那部分知識。
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錯在戈爾巴喬夫、蓋達爾、雅科夫列夫……這都是受害者的心理。或者說,1993年伊戈爾・蓋達爾有沒有權力號召人民去市政府呢?從那個時代的觀點來看,他做的是對的。那或許是人民聽到的60年代人的最後一次呼籲。緊接着現實就破碎了,分裂了。我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那裏鬥爭的文化、街壘的文化,在我看來,已經成了陷阱。
現在到了一個孤獨的靈魂建設、家園建設的時代。我聽到新的話語,其中出現了新的音調。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學習思考自身,講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從這種大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和我們的人聊一聊支撐生活的那些事物。
問:當你在探尋個體幸福之謎時,你會和一個個具體的人談些什麼?
阿列克謝耶維奇:可以談論幸福啊。幸福就是整個世界。那裏有那麼多角落、窗戶、門、鑰匙。這是一個令人震撼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我們的認識還相當模糊。有一個從阿富汗回來的小夥子對我說:「當我的孩子出生時,我痴迷地嗅着襁褓。我瘋狂地跑回家,就為了聞到這種氣味。那是幸福的氣味。」
當一個人愛上別人,或者開始考慮幸福,只有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才不是生活,而是真正的存在感,你接近了永恆。你想笑又想哭。我聽着、看着這個激動的人,對我來說他的心靈就像是進行遠距離宇宙交流的工具。
總之,儘管這是一種沒有希望的行為,我還是想弄明白:為什麼是我們?為什麼我們那樣痛苦地哭泣和禱告?
問:有沒有可能,對於那些經受很多磨難的人來說,活着(幸福)比自由更加重要?在西方,如你所說,他們需要了解的是痛苦的經驗,而我們可以從西方學習的,恰恰是幸福的經驗。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戰爭中,在集中營,人很快就會轉變成動物。甚至有人告訴我轉變的期限——三天。我在研究這條人的道路:向上——抵達天空,向下——成為獸類。我想您所說的幸福,是指人身上的動物性部分吧?
在關於愛的故事中,尤其是在人們越來越多聆聽自我的今天,我了解、探尋到,人身上的動物性,以及那個名為身體的存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今仍然是很少被我們的文化所掌握的、神秘的空間。我們的文化是高傲的,它關注的都是靈魂的問題,而動物性,那些潛藏於自身而被我們所鄙視的東西,受到壓抑和掩藏,等它突然從地下室裏鑽出來——多麼醜陋!又是多麼漂亮!那時我們會認識到自身許多不曾料想的成分:低劣的和偉岸的本性。
不對我們本性中那些黑暗的、獸性的存在進行關注和尊重,怎麼可能寫出一本關於愛的書?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們逐漸在走向自身,走向個人的世界。我們必須學着在沒有偉大事件、偉大思想的條件下生活。平淡的人類生活將會圍繞什麼進行呢?圍繞愛情和死亡。
5.抵禦時代的喧囂:永遠對人的靈魂空間感興趣
問:我注意到,你在談論閲讀和寫作時,頻繁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對你的啟示是什麼?
阿列克謝耶維奇:從青少年時代我就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本讀完的小說是《白痴》。我愛上了梅什金公爵,愛上了他關於善的思想。現在我在重讀《惡魔》。那裏有我們現在思考、談論的一切東西:善與惡的不可分割……我喜歡很多作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歡的作家。可以說,我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成長起來的。
提起他的名字,是因為這一切都在人的本性之中。
我只講一點,惡是一種更兇殘、更適宜、更普通的東西。它比善更加完善。這是一種已經被磨平的人類機制——而關於善卻無法這樣定義。你剛一開始講到善——所有人都能說出一些名字來,關於他們的事蹟人盡皆知,人人明白自己不是那樣的人,永遠也成不了那樣的人。「我不是聖母瑪利亞」,人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不在場的證明。
今天的所有問題都導向了這一點,即應當讀一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托爾斯泰的幸福是某種非塵世的、智力型的幸福。而惡卻長久地環繞在我們周圍。並且我們就成長於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我們長久地處於這種環境之中。
問:你的作品裏總是有各種聲音,各種原文的記錄,你說自己「所閲讀的是聲音」,各種複調的聲音同時匯入大腦……你就像是「一隻越來越巨大的耳朵」,在傾聽中,你的存在感消失了,讀者幾乎就要把作者本人遺忘,面對如此多的故事,你為什麼選擇成為一名傾聽者,而不加入作者的評論?
阿列克謝耶維奇:福樓拜描述自己「我是一個以筆立世的人」,而我是一個「以耳立世」的人。在很長時間裏,我都在尋找一種體裁,為的是將我所看到的世界呈現出來。那種能將我的眼睛、耳朵所體驗到的一切表現出來的體裁,後來我選擇了這種記錄人聲音的體裁……我將在街上、窗外看到、聽到的一切記錄成書。在書中,真實的人們在講述自己這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戰爭、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切爾諾貝利,而他們把所有的這一切留在了話語中——這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是一種通史。既有古老的,也有最新的。而每個人承擔了自己渺小的個體命運的歷史。
問:當每個人都開始訴說自己的經驗史,國家的歷史就以鮮活的方式浮現出來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的。
一方面,我希望我書中人物的聲音像合唱一樣一致;而另一方面,我總希望,一種孤獨的、個人的聲音被人聽到。我覺得,今天人們想聽到其他人的聲音,而不是一切都被壓制成鐵板一塊的、全時代的聲音。
我永遠對一個人的靈魂空間感興趣,一切正是在那兒發生的。
我通過小歷史看到了大歷史,這樣歷史就不再是時代的喧囂,而是我們能夠理解,並且在若干年後依然感興趣的存在。我們對於個人的生活感興趣,因此我把一切都縮小到單個人的規模。
我的耳朵永遠都在窗戶附近,諦聽着街道。我注視、聆聽新的節奏、新的聲音。聆聽新的音樂。街上的生活比我們閉門造車要有意思得多,可怕得多,好笑得多,有人味兒得多。在封閉的空間裏,文學滋養文學,政治滋養政治;而大街上是新鮮的、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
6.寫作在繼續:死亡和愛情是永恆主題
問:如果讓你用關鍵詞概括這三十多年來的創作,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寫作主題?
阿列克謝耶維奇:關於愛情和死亡。在一次採訪中我說,我想和大家聊一聊這件事,我也很高興寫這個主題。我收到了很多故事,但所有的故事都是關於——人們怎樣戰鬥,怎樣重建,怎樣在工作中熱火朝天。我們不能回憶起自己的生活了。就好像沒有生活這回事。
但我們逐漸在走向自身,走向個人的世界。我們必須學着在沒有偉大事件、偉大思想的條件下生活。平淡的人類生活將會圍繞什麼進行呢?圍繞愛情和死亡。看來,講述這件事將會非常複雜。人們不擅長這件事。
問:你的下一本書,主題依然是關於愛與死亡嗎?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的,關於愛和死亡。我覺得,我一直都在寫「愛」。關於戰爭我沒有新的觀點。
所有我明白以及能夠明白的東西,已經在先前的書中寫盡了。我又不是恐懼和痛苦的收藏家,我只是在獲取一個人能夠從其自身領悟的、他所害怕的、個人靈魂的金色顆粒。我的思想停留在了戰爭面前,對我來說戰爭就是謀殺。
今天的戰爭是另一幅面孔——切爾諾貝利、恐怖主義、極端文明對抗。在這些戰爭中意外地顯現出強大的宗教能量。
我認為,今天我們無力去了解的、個人生活的秘密,比任何一種思想都更能吸引我們,令我們着迷。生活充滿謎團,難以解開,又十分有趣,就像一場不乏神秘的奇遇與冒險的漫長旅行。在我們的文化中,這樣的經驗還不太多,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鬥爭的文化、倖存的文化。寫一本最恐怖的、有關戰爭的書要比書寫愛情更簡單。
但我們在向着某個地方回歸。為了寫新書《永恆狩獵裏的神奇鹿》,我已經收集了好幾年的資料。這是一本關於100個男人和女人的愛情自白。在這本書裏,人不是隱藏在阿富汗戰爭的後面,不是隱藏在國家解體的後面,而是敞開自己的內心。
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你是否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某種新的認知?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將繼續從事自己渺小的工作。帶着真誠去做,並且,您知道嗎,帶着快樂。儘管寫作困難重重,但這個世界總歸還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美國、德國、波蘭……以及國內。
當宣告我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時,白俄羅斯人走上明斯克街頭,互相擁抱、親吻。而獨裁者盧卡申科沒有什麼好話送給我,他說,我「給國家抹黑」。當斯大林談到布寧和帕斯傑爾納克,勃列日涅夫說到布羅茨基——這些俄羅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說的也是同樣的話。過去了50年,獨裁者還一點沒變,甚至是用詞。對於藝術家來說,街壘不是最好的地方,但是我們還不能從那裏離開。時間不放我們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