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15 04:00:00阿楨
霍桑:世界百大作家84
納旦尼爾•霍桑

納旦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年7月4日-1864年5月19日)。19世紀前半期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 其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古宅青苔》、《重講一遍的故事》等,長篇小說《紅字》、《帶七個尖頂的閣樓》、《福穀傳奇》、《玉石人像》等。這些都是世界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名著。
人物簡介
霍桑出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賽勒姆鎮。他的祖輩為著名的1692年賽勒姆驅巫案的三名法官之一。父親是個船長,在霍桑四歲的時候死于海上,霍桑在母親撫養下長大。1821年霍桑在親戚資助下進入緬因州的博多因學院,在學校中他與朗費羅與佛蘭克林•皮爾斯成為好友。1824年大學畢業,霍桑回到故鄉,開始寫作。完成一些短篇故事之後,他開始嘗試把自己在博多因學院的經驗寫成小說,這就是長篇小說《范肖》(Fanshawe),於1828年不署名發表,但是沒有引起注意。霍桑將沒有賣出去的小說全部付之一炬。
1836年霍桑在海關任職。1837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短篇小說集《重講一遍的故事》(Twice-ToldTales),開始正式署上自己的名字。其中《教長的黑紗》(The Minister's Black Veil,1836一篇最為人稱道。1841年霍桑曾參加超驗主義者創辦的布魯克農場。1842年7月9日他結婚,婚姻非常美滿。兩人到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村老牧師住宅居住三年,期間霍桑完成短篇小說集《古宅青苔》(又譯《古屋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1846]) 。其中的短篇小說《小夥子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1835)、《拉伯西尼醫生的女兒》(Rappaccini's Daughter,1844)很受歡迎。
1846年霍桑又到海關任職。他從奧爾科特那裡買下了康科特的一座叫做路側居(Wayside)的古老住宅,並住在那裡。他的鄰居是作家愛默生、梭羅等人。1848年由於政見與當局不同,失去海關的職務,便致力於創作活動,寫出了他最重要的長篇小說《紅字》(1850)。當年霍桑在野餐中偶然遇到了居住在附近的麥爾維爾並成為好友。麥爾維爾對霍桑的《古宅青苔》很是讚揚,並且在給霍桑的信裡提到了自己的小說《白鯨》的寫作。愛倫坡也對《重講一遍的故事》和《古宅青苔》非常感興趣,寫了很多評論。
《紅字》發表後獲得巨大成功,霍桑繼而創作了不少作品。其中《帶有七個尖角閣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和《福穀傳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1853年皮爾斯就任美國總統後,霍桑被任命為駐英國利物浦的領事。1857年皮爾斯離任,霍桑僑居義大利,創作了另一部討論善惡問題的長篇小說《玉石人像》(The Marble Faun: Or, The Romance of Monte Beni,1860)。1860年霍桑返回美國,在康科特定居,堅持寫作。1864年5月19日霍桑與皮爾斯結伴旅遊途中,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朴茨茅斯去世。
創作理念霍桑認為:與文明而古老的歐洲相比,美國“沒有陰影,沒有古風,沒有秘傳,沒有絢麗而又昏默的冤孽,只有光天之下的枯燥乏味的繁榮”,給作家提供的素材極少。因此,霍桑把注意力轉向過去,力圖借助想像去挖掘歷史上對創作有益的素材,以便“把過去了的時代與我們面前一瞬即逝的現在聯繫起來”。這也暗示了他以古喻今的創作意圖。但是出於清教徒的審慎,霍桑採取了浪漫主義小說的創作形式。他認為只有這樣,作者才能以自己選擇的方式構思和創作,而又不必拘泥於細節的真實,才能在“真實的世界”和“仙境”之間找到現實與想像得以相結合的“中間地帶”。霍桑的偉大正在於他能以表面溫和而實質犀利的筆鋒暴露黑暗、諷刺邪惡、揭示真理。
作品特點
描寫社會和人性的陰暗面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點,這與加爾文教關於人的“原罪”和“內在墮落”的理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霍桑是心理小說的開創者,擅長剖析人的“內心”。他著重探討道德和罪惡的問題,主張通過善行和自懺來洗刷罪惡、淨化心靈,從而得到拯救。然而霍桑並非全寫黑暗,他在揭露社會罪惡和人的劣根性的同時,對許多善良的主人公寄予極大的同情。正如他的朋友、偉大作家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所指出的,霍桑的黑暗使在這黑暗中不停前進的黎明顯得更加明亮。霍桑對美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對亨利•詹姆斯、福克納及馬拉默德等後代作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霍桑的作品想像豐富、結構嚴謹。他除了進行心理分析與描寫外,還運用了象徵主義手法。他的構思精巧的意象,增添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加深了寓意。但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神秘晦澀之處。
《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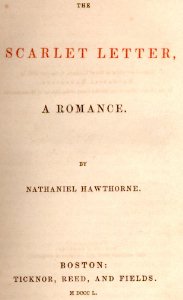
紅字第一版的封面

19世紀美利堅合眾國浪漫主義作家霍桑的長篇小說,發表於1850年。小說以兩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時代的美洲為題材,但揭露的卻是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美利堅合眾國社會典法的殘酷、宗教的欺騙和道德的虛偽。主人公海絲特被寫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裡不一的丁梅斯代爾,同時也在感化著充滿罪惡的社會。
至於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說則把他寫成了一個一心只想窺秘復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說中不但起到情節鋪墊的作用,而且他代表了理性的科學,同時hester代表浪漫主義,丁梅斯代爾代表宗教,三者矛盾是本書的一大重點。
小說慣用象徵手法,人物、情節和語言都頗具主觀想像色彩,在描寫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動和直覺放在首位。因此,它不僅是美利堅合眾國浪漫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同時也被稱作是美利堅合眾國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篇。
內容介紹
納旦尼爾•霍桑生於1804年,是美國19世紀影響最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和心理小說家。長篇小說《紅字》是他的代表作。
在十七世紀中葉的一個夏天,一天早晨,一大群波士頓居民擁擠在監獄前的草地上,莊嚴地目不轉睛地盯著牢房門。
隨著牢門的打開,一個懷抱三個月大的嬰兒的年輕女人緩緩地走到了人群前,在她的胸前佩帶著一個鮮紅的A 字,耀眼的紅字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就是海絲特•白蘭太太。她由於被認為犯了通姦罪而受到審判,並要永遠佩帶那個代表著恥辱的紅字。
在絞刑臺上,面對著總督貝靈漢和約翰•威爾遜牧師的威逼利誘,她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屈辱,忍受著人性所能承擔的一切,而站在她身旁的年輕牧師丁梅斯代爾卻流露出一種憂心忡忡、驚慌失措的神色,恰似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偏離了方向,感到非常迷惘,只有把自己封閉起來才覺得安然。海絲特•白蘭堅定地說:“我永遠不會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的”,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眼睛沒有去看威爾遜牧師,而是凝視著那年輕牧師深沉而憂鬱的眼睛。“這紅字烙得太深了。你是取不下來的。但願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同時,也忍受住他的痛苦!”海絲特•白蘭說。
這時,在人群中,海絲特•白蘭看到了一個相貌奇特的男人:矮小蒼老,左肩比右肩高,正用著陰晦的眼神注視著她,這個男人就是她失散了兩年之久的丈夫齊靈渥斯——一個才智出眾、學識淵博的醫生。當他發現海絲特•白蘭認出了他時,示意她不要聲張。在齊靈渥斯的眼裡燃燒著仇恨的怒火,他要向海絲特•白蘭及她的情人復仇,並且他相信一定能夠成功。
海絲特•白蘭被帶回獄中之後,齊靈渥斯以醫生的身份見到了她,但海絲特•白蘭不肯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並且向齊靈渥斯坦言她從他那裡從來沒有感受到過愛情,齊靈渥斯威脅海絲特•白蘭不要洩露他們的夫妻關係,他不能遭受一個不忠實女人的丈夫所要蒙受的恥辱,否則,他會讓她的情人名譽掃地,毀掉的不僅僅是他的名譽,地位,甚至還有他的靈魂和生命,海絲特•白蘭答應了。
海絲特•白蘭出獄後,帶著自己的女兒小珠兒靠著針線技藝維持著生活,她們離群索居,那鮮紅的A 字將屈辱深深烙在了海絲特•白蘭的心裡。小珠兒長得美麗脫俗,有著倔強的性格和充沛的精力,她和那紅字一起閃耀在世人的面前,在那個清教徒的社會裡,他們是恥辱的象徵,但也只有他們是鮮亮的。
丁梅斯代爾牧師不僅年輕俊美,而且學識淵博,善於辭令,有著極高的秉賦和極深的造詣,在教民中有著極高的威望。但是,自從海絲特•白蘭受審以來,他的健康日趨羸弱,敏感,憂鬱與恐慌彌漫了他的整個思緒,他常常夜不成寐的禱告,每逢略受驚恐或是突然遇到什麼意外事件時,他的手就會攏在心上,先是一陣紅潮,然後便是滿面蒼白,顯得十分苦痛。這一切都讓齊靈渥斯看在眼裡,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以醫生的身份與他形影相隨。
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珠兒漸漸的長大了,她穿著母親為她做的紅天鵝絨裙衫,奔跑著,跳躍著,象一團小火焰在燃燒,這耀眼的紅色使清教徒們覺得孩子是另一種形式的紅字,是被賦予了生命的紅字!貝靈漢總督和神甫約翰•威爾遜認為小珠兒應該與母親分開,因為她的母親是個罪人,沒有能力完成使孩子成為清教徒的重任。但是海絲特•白蘭堅決不同意。她大聲說珠兒是上帝給她的孩子,珠兒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折磨!是珠兒叫她還活在世上!也是珠兒叫她受著懲罰!如果他們奪走珠兒,海絲特•白蘭情願先死給他們看。海絲特•白蘭轉向丁梅斯代爾牧師,希望他能夠發表意見。丁梅斯代爾牧師面色蒼白,一隻手捂住心口,那雙又大又黑的眼睛深處,在煩惱和憂鬱之中還有一個痛苦的天地,他認為珠兒是上帝給海絲特•白蘭的孩子,應該聽從上帝的安排,如果她能把孩子送上天國,那麼孩子也就能把她帶到天國,這是上帝神聖的旨意。這樣珠兒才沒有被帶走。
這一切,都被飽經世故的齊靈渥斯看在眼裡,他一點點地向丁梅斯代爾牧師內心逼近,齊靈渥斯象觀察病人一樣去觀察他,一方面觀察丁梅斯代爾牧師的日常生活,看他怎樣在慣有的思路中前進,另一方面觀察他被投入另一種道德境界時所表現的形態,他儘量發掘牧師內心的奧秘。隨著時間的推移,齊靈渥斯漸漸地走進了丁梅斯代爾牧師的心裡,並向他的靈魂深處探進。
一天,丁梅斯代爾牧師正在沉睡,齊靈渥斯走了進來,撥開了他的法衣,終於發現了丁梅斯代爾牧師一直隱藏的秘密——他的胸口上有著和海絲特•白蘭一樣的紅色標記,他欣喜若狂,那是一種狂野的驚奇、歡樂和恐懼的表情!那種駭人的狂喜,絕不僅僅是由眼睛和表情所表達的,甚至是從他整個的醜陋身軀迸發出來,他將兩臂伸向天花板,一隻腳使勁跺著地面,以這種非同尋常的姿態放縱地表現他的狂喜!當一個寶貴的人類靈魂失去了天國,墮入撒旦的地獄之中時,那魔王知道該如何舉動了。
齊靈渥斯精心地實施著他的復仇計畫,他利用丁梅斯代爾牧師敏感、富於想像的特點,抓住他的負罪心理,折磨他的心靈,他把自己裝扮成可信賴的朋友, 讓對方向他吐露一切恐懼、自責、煩惱、懊悔、負罪感,那些向世界隱瞞著的一切內疚,本可以獲得世界的博大心胸的憐憫和原諒的,如今卻要揭示給他這個內心充滿了復仇火焰的人,最最恰如其分地讓他得償復仇之夙債。而此時的丁梅斯代爾牧師對齊靈渥斯卻沒有任何的懷疑,雖然他總是會感到有一種惡勢力在緊緊的盯著自己,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由於他不把任何人視為可信賴的朋友,故此當敵人實際上已出現時,仍然辨認不出。 就在丁梅斯代爾牧師飽嘗肉體上的疾病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摧殘的同時,他在聖職上卻大放異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公眾的景仰更加加重了他的罪惡感,使他的心理不堪重負。
終於,在一天漆黑的夜裡,丁梅斯代爾牧師夢游般走到了市場上的絞刑臺上,發出一聲悲痛的嘶喊。海絲特•白蘭和小珠兒剛剛守護著一個人去世,恰巧從這裡經過,她看到丁梅斯代爾牧師已處於崩潰的邊緣,精神力量已經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一種悔罪感使丁梅斯代爾邀請她們一同登上了絞刑台:“你們母女倆以前已經在這兒站過了,可是我當時沒和你們一起來。再上來一次吧,我們三個人一起站著吧!”海絲特•白蘭握著孩子的一隻手,牧師握著孩子的另一隻手,他們共同站在了絞刑臺上。就在他這麼做的瞬間,似有一般不同於他自己生命的新生命的激越之潮,急流般湧入他的心房,沖過他周身的血管,仿佛那母女倆正把她們生命的溫暖傳遞給他半麻木的身軀,三人構成了一條閉合的電路,此時,天空閃過了一絲亮光,丁梅斯代爾仿佛看見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字母“A ”。然而,這一切都讓跟蹤而至的齊靈渥斯看到了,這使得丁梅斯代爾牧師極為恐慌,但是,齊靈渥斯卻說丁梅斯代爾先生患了夜遊症,並把他帶回了家。丁梅斯代爾先生就象一個剛剛從噩夢中驚醒的人,心中懊喪得發冷,便聽憑那醫生把自己領走了。
許多年過去了,小珠兒已經七歲了,海絲特•白蘭此時所處的地位已同她當初受辱時不完全一樣了。如果一個人在大家面前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地位,而同時又不干涉任何公共或個人的利益,她就最終會贏得普遍的尊重。海絲特•白蘭從來與世無爭,只是毫無怨尤地屈從於社會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她也沒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希冀什麼報償;她同樣不依重於人們的同情。於是,在她因犯罪而喪失了權利、被迫獨處一隅的這些年月裡,大大地贏得了人心。她除了一心一意的打扮小珠兒外,她還盡自己所能去幫助窮人,用寬大的心去包容一切,人們開始不再把那紅字看作是罪過的標記,而是當成自那時起的許多善行的象徵。
在這幾年裡,許多人都發生著變化,齊靈渥斯變的更加蒼老了,海絲特•白蘭原來印象最深的他先前那種聰慧好學的品格,那種平和安詳的風度,如今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急切窺測的神色,近乎瘋狂而又竭力掩飾,而這種掩飾使旁人益發清楚地看出他的陰險。海絲特•白蘭請求齊靈渥斯放過丁梅斯代爾牧師,不要再摧殘他的靈魂了,但是丁梅斯代爾牧師的痛苦、復仇的快樂已經沖昏了齊靈渥斯的頭腦,他決定繼續實施自己的陰謀,他要慢慢地折磨丁梅斯代爾牧師,復仇已經成為他生活唯一的目的。海絲特•白蘭決定將齊靈渥斯的真實身份告訴丁梅斯代爾。
在一片濃密的森林裡,海絲特•白蘭見到了丁梅斯代爾,他們互訴衷腸,述說著幾年來心底的秘密,他們受著同樣的痛苦和煎熬,同樣受著良知和道德的齧噬。丁梅斯代爾告訴她,雖然他的胸前沒有佩帶紅字,但是,同樣的紅字在他的生命裡一直燃燒著。此時,海絲特•白蘭才意識到犧牲掉牧師的好名聲,甚至讓他死掉,都比她原先所選擇的途徑要強得多,她告訴丁梅斯代爾齊靈渥斯就是她的丈夫,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的榮譽、地位及生命才隱瞞了這個秘密。陰暗兇猛的眼神瞬間湧上了丁梅斯代爾的臉上,他痛楚的把臉埋在雙手之中。海絲特•白蘭勸丁梅斯代爾離開這裡,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去,到一個可以避開齊靈渥斯雙眼的地方去,她願意和他開始一段新的生活,過去的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又何必去留戀呢? 丁梅斯代爾猶豫著,他要麼承認是一名罪犯而逃走,要麼繼續充當一名偽君子而留下,但他的良心已難以從中取得平衡;為了避免死亡和恥辱的危險,以及一個敵人的莫測的詭計,丁梅斯代爾決定出走。
海絲特•白蘭的鼓勵及對新生活的憧憬,使丁梅斯代爾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氣和希望。剛好有一艘停泊在港灣的船三天之後就要到英國去,他們決定坐這艘船返回歐洲,一切都在順利地進行著。他們每天都被這種新的希望激勵著、興奮著,丁梅斯代爾決定演講完慶祝說教後就離開。新英格蘭的節日如期而至,丁梅斯代爾牧師的演講也按計劃進行著, 海絲特•白蘭和小珠兒來到市場,她的臉上有一種前所未見的表情,特殊的不安和興奮,“再最後看一眼這紅字和佩戴紅字的人吧!”她想,“再過一段時間,她就會遠走高飛了!那深不可測的大海將把你們在她胸前灼燒的標記永遠淹沒無存!” 這時,那艘準備開往英國船隻的船長走了過來,他告訴海絲特•白蘭,齊靈渥斯將同他們同行,海絲特•白蘭徹底絕望了。
丁梅斯代爾牧師的宣講取得了空前絕後的最輝煌成功,但隨後他變得非常衰弱和蒼白,他步履踉蹌,內心的負罪感及良心的譴責最終戰勝了他出逃的意志,在經過絞刑台的時候,他掙脫齊靈渥斯的羈絆,在海絲特•白蘭的攙扶下登上了絞刑台,他拉著珠兒,在眾人面前說出了在心底埋藏了七年的秘密,他就是小珠兒的父親,他扯開了法衣的飾帶,露出了紅字,在眾人的驚懼之聲中,這個受盡蹂躪的靈魂辭世了。
齊靈渥斯把復仇當作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可是當他勝利後,他扭曲的心靈再也找不到依託,他迅速枯萎了。不到一年,他死了,他把遺產贈給了小珠兒。不久,海絲特•白蘭和小珠兒也走了。紅字的故事漸漸變成了傳說。許多年以後,在大洋的另一邊,小珠兒出嫁了,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而海絲特•白蘭又回到了波士頓,胸前依舊佩帶著那個紅字,這裡有過她的罪孽,這裡有過她的悲傷,這裡也還會有她的懺悔。又過了許多年,在一座下陷的老墳附近,又挖了一座新墳。兩座墳共用一塊墓碑。上面刻著這麼一行銘文:
“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
精彩片段
他轉向刑台,向前伸出雙臂。“海絲特,”他說,“過來呀!來,我的小珠兒!”他盯著她們的眼神十分可怖;但其中馬上就映出溫柔和奇異的勝利的成分。那孩子,以她特有的鳥兒一般的動作,朝他飛去,還摟住了他的雙膝。海絲特•白蘭似乎被必然的命運所推動,但又違背她的堅強意志,也緩緩向前,只是在她夠不到他的地方就站住了。就在此刻,老羅傑•齊靈渥斯從人群中脫穎而出——由於他的臉色十分陰暗、十分慌亂、十分邪惡,或許可以說他是從地獄的什麼地方鑽出來的——想要抓住他的犧牲品,以免他會做出什麼舉動!無論如何吧,反正那老人沖到前面,一把抓住了牧師的胳臂。
“瘋子,穩住!你要幹什麼?”他小聲說。“揮開那女人!甩開這孩子!一切都會好的!不要玷污你的名聲,不光彩地毀掉自己!我還能拯救你!你願意給你神聖的職業蒙受恥辱嗎?”“哈,誘惑者啊!我認為你來得太遲了!”牧師畏懼而堅定地對著他的目光,回答說。“你的權力如今已不象以前了!有了上帝的幫助,我現在要逃脫你的羈絆了!”他又一次向戴紅字的女人伸出了手。
“海絲特•白蘭,”他以令人撕心裂肺的真誠呼叫道,“上帝啊,他是那樣的可畏,又是那樣的仁慈,在這最後的時刻,他已恩准我——為了我自己沉重的罪孽和悲慘的痛楚——來做七年前我規避的事情,現在過來吧,把你的力量纏繞到我身上吧!你的力量,海絲特;但要讓那力量遵從上帝賜于我的意願的指導!這個遭受委屈的不幸的老人正在竭力反對此事!竭盡他自己的,以及魔鬼的全力!來吧,海絲特,來吧!扶我登上這座刑台吧!”
人群譁然,騷動起來。那些緊靠在牧師身邊站著的有地位和身份的人萬分震驚,對他們目睹的這一切實在不解:既不能接受那顯而易見的解釋,又想不出別的什麼涵義,只好保持沉默,靜觀上天似乎就要進行的裁決。他們眼睜睜地瞅著牧師靠在海絲特的肩上,由她用臂膀攙扶著走近刑台,跨上臺階;而那個由罪孽而誕生的孩子的小手還在他的手中緊握著。
老羅傑•靈渥斯緊隨在後,像是與這出他們幾人一齊參加演出的罪惡和悲傷的戲劇密不可分,因此也就責無旁貸地在閉幕前亮了相。“即使你尋遍全世界,”他陰沉地望著牧師說,“除去這座刑台,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更秘密——高處也罷,低處也罷,使你能夠逃脫我了!”“感謝上帝指引我來到了這裡!”牧師回答說。
然而他卻顫抖著,轉向海絲特,眼睛中流露著疑慮的神色,嘴角上也同樣明顯地帶著一絲無力的微笑。“這樣做,”他咕噥著說,“比起我們在樹林中所夢想的,不是更好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匆匆回答說。“是更好嗎?是吧;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死去,還有小珠兒陪著我們!”
“至於你和珠兒,聽憑上帝的旨意吧,”牧師說;“而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已經在我眼前表明了他的意願,我現在就照著去做。海絲特,我已經是個垂死的人了。那就讓我趕緊承擔起我的恥辱吧!”
丁梅斯代爾牧師先生一邊由海絲特•白蘭撐持著,一邊握著小珠兒的手,轉向那些年高望重的統治者;轉向他的那些神聖的牧師兄弟;轉向在場的黎民百姓——他們的偉大胸懷已經給徹底驚呆了,但仍然氾濫著飽含淚水的同情,因為他們明白,某種深透的人生問題——即使充滿了罪孽,也同樣充滿了極度的痛苦與悔恨——即將展現在他們眼前。 剛剛越過中天的太陽正照著牧師,將他的輪廓分明地勾勒出來,此時他正高高矗立在大地之上,在上帝的法庭的被告欄前,申訴著他的罪過。
“新英格蘭的人們!”他的聲音高昂、莊嚴而雄渾,一直越過他們的頭頂,但其中始終夾雜著顫抖,有時甚至是尖叫,因為那聲音是從痛苦與悔恨的無底深淵中掙扎出來的,“你們這些熱愛我的人!——你們這些敬我如神的人!——向這兒看,看看我這個世上的罪人吧!終於!——終於!——我站到了七年之前我就該站立的地方;這兒,是她這個女人,在這可怕的時刻,以她的無力的臂膀,卻支撐著我爬上這裡,攙扶著我不致撲面跌倒在地!看看吧,海絲特佩戴著的紅字!你們一直避之猶恐不及!無論她走到哪裡,——無論她肩負多麼悲慘的重荷,無論她可能多麼巴望能得到安靜的休息,這紅字總向她周圍發散出使人畏懼、令人深惡痛絕的幽光。但是就在你們中間,卻站著一個人,他的罪孽和恥辱並不為你們所回避!”
牧師講到這裡,仿佛要留下他的其餘的秘密不再揭示了。但他擊退了身體的無力,尤其是妄圖控制他的內心的軟弱。 他甩掉了一切支持,激昂地向前邁了一步,站到了那母女二人之前。“那烙印就在他身上!”他激烈地繼續說著,他是下定了決心要把一切全盤托出了。
“上帝的眼睛在注視著它!天使們一直都在指點著它!魔鬼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時用他那燃燒的手指的觸碰來折磨它!但是他卻在人們面前狡猾地遮掩著它,神采奕奕地定在你們中間;其實他很悲哀,因為在這個罪孽的世界上人們竟把他看得如此純潔!——他也很傷心,因為他思念他在天國裡的親屬!如今,在他瀕死之際,他挺身站在你們面前!他要求你們再看一眼海絲特的紅字!他告訴你們,她的紅字雖然神秘而可怕,只不過是他胸前所戴的紅字的影像而已,而即使他本人的這個紅色的恥辱烙印,仍不過是他內心烙印的表像罷了!站在這裡的人們,有誰要懷疑上帝對一個罪人的制裁嗎?看吧!看看這一個駭人的證據吧!”
他哆哆嗦嗦地猛地扯開法衣前襟的飾帶。露出來了!但是要描述這次揭示實在是大不敬。刹那間,驚慌失措的人們的凝視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那可怖的奇跡之上;此時,牧師卻面帶勝利的紅光站在那裡,就象一個人在備受煎熬的千鈞一髮之際卻贏得了勝利。隨後,他就癱倒在刑臺上了!海絲特撐起他的上半身,讓他的頭靠在自己的胸前。
老羅傑•齊靈渥斯跪在他身旁,表情呆滯,似乎已經失去了生命。“你總算逃過了我!”他一再地重複說。“你總算逃過了我!” “願上帝饒恕你吧!”牧師說。“你,同樣是罪孽深重的!”他從那老人的身上取回了失神的目光,緊緊盯著那女人和孩子。
“我的小珠兒,”他有氣無力地說——他的臉上泛起甜蜜而溫柔的微笑,似是即將沉沉酣睡;甚至,由於卸掉了重荷,他似乎還要和孩子歡蹦亂跳一陣呢——“親愛的小珠兒,你現在願意親親我嗎?那天在那樹林裡你不肯親我!可你現在願意了吧?”
珠兒吻了他的嘴唇。一個符咒給解除了。連她自己都擔任了角色的這一偉大的悲劇場面,激起了這狂野的小孩子全部的同情心;當她的淚水滴在她父親的面頰上時,那淚水如同在發誓:她將在人類的憂喜之中長大成人,她絕不與這世界爭鬥,而要在這世上作一個婦人。珠兒作為痛苦使者的角色,對她母親來說,也徹底完成了。
“海絲特,”牧師說,“別了!”“我們難道不能再相會了嗎?”她俯下身去,把臉靠近他的臉,悄聲說。 “我們難道不能在一起度過我們永恆的生命嗎?確確實實,我們已經用這一切悲苦彼此贖救了!你用你那雙明亮的垂死的眼睛遙望著永恆!那就告訴我,你都看見了什麼?”“別作聲,海絲特,別作聲!”他神情肅穆,聲音顫抖地說。
“法律,我們破壞了!這裡的罪孽,如此可怕地揭示了!——你就只想著這些好了!我怕!我怕啊! 或許是,我們曾一度忘卻了我們的上帝,我們曾一度互相冒犯了各自靈魂的尊嚴,因此,我們希望今後能夠重逢,在永恆和純潔中結為一體,恐怕是徒勞的了。上帝洞察一切;而且仁慈無邊!他已經在我所受的折磨中,最充分地證明了他的仁慈。 他讓我忍受這胸前灼燒的痛楚!他派遣那邊那個陰森可怖的老人來,使那痛楚一直火燒火燎!他把我帶到這裡,讓我在眾人面前,死在勝利的恥辱之中!若是這些極度痛苦缺少了一個,我就要永世沉淪了!讚頌他的聖名吧!完成他的意旨吧!別了!”隨著這最後一句話出口,牧師吐出了最後一口氣。到此時始終保持靜默的人們,進出了奇異而低沉的驚懼之聲,他們實在還找不出言辭,只是用這種沉沉滾動的聲響,伴送著那辭世的靈魂。
http://baike.baidu.com/view/639015.htm?fromtitle=%E9%9C%8D%E6%A1%91&fromid=63187&type=syn
紅字 The Scarlet Letter (1926)


導演: 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
編劇: 納旦尼爾•霍桑 / 弗朗西絲•瑪麗恩
主演: 麗蓮•吉許 / Lars Hanson / 亨利•B•沃斯奧
紅字 The Scarlet Letter (1995)





導演: 羅蘭•約菲
編劇: Douglas Day Stewart
主演: 黛米•摩爾 / 加里•奧德曼 / 羅伯特•杜瓦爾
劇情簡介
故事發生在17世紀。赫絲特(黛米•摩爾 Demi Moore 飾)離開丈夫,孤身一人來到麻塞諸塞灣的英屬殖民地定居。在這裡開拓的英國人信仰堅定,恪守清規,赫絲特的一些舉動在這壓抑的殖民地環境下頗為引人注目。當地的牧師亞瑟(加里•奧德曼 Gary Oldman 飾)英俊而富有激情,赫絲特為他的神采深深吸引,兩個性情相投的人很快陷入了危險的熱戀。不久殖民地方面接到了赫絲特的醫生丈夫被印第安人殺害的消息,本以為可以公開關係的一對戀人等到的卻是東窗事發,赫絲特為保護亞瑟,拒絕供認通姦者,自此被投入監獄直至產下一名女嬰,而亞瑟則在監獄外日日承受心靈的拷問……出獄後的赫絲特戴上了通姦者的恥辱標誌,同時她大難不死的丈夫突然現身,誓要將通姦者揪出以發洩心中怒火……
名著名編 2010-05-25
早就有人說過,文字和電影是不同的表達方式。表達方式的不同也讓內容發生了變化,有些時候,這種變化甚至發生在本質精神上和核心人物的性格上。
我覺得,一個好的電影改編。首先的要求這個導演駕馭大場面的能力。像名著,多數時候是波瀾壯闊的篇章,錯綜複雜的情節和性格深沉的人物組成的。如果沒有駕馭能力,就要顧此失彼。再者,他還要有很好的把握影像表達的素質。不過,最最重要的,是這個改編者的思想深度,也就說他可以和原作者達到什麼樣的精神溝通。
回過頭來說《紅字》。
如果不是因為我看了書,我覺得我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的耐心看一部離自己很遠,很多地方看不明白的一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陰沉電影。不過,說實話,現在的節奏這麼快,人們追求的是速食的快樂。我能在上下班的地鐵上閱讀完這本書也是一件奇跡。就我本人來說,基本上是沒享受到什麼閱讀的快樂。不過,名著的魅力並不是用你看了這本書能獲得多少快樂的來體現的。
雖說我更喜歡電影,但是也不得不承認,電影和書基本上是南轅北轍了。
在小說中,海斯特白蘭是在宗教和環境的壓抑下生存不得不偽裝起堅強來反擊的,電影中的這個女人,從頭到尾都很強。那種強,不但體現在體魄上還有精神上,甚至可以說,有很多女權意識的萌動在裡面。在電影的最後,海斯特問:我為什麼要留在這?為他們所接受,為他們所馴服?然後,這個女人毅然決然的要離開。事實上,根據我的理解,既然小說發生的背景是一個受壓抑的陰暗年代,那麼,那個時候的女人是根本不可能說走就走的。電影增加了海斯特獨立意識覺醒的光輝,這是原作者內心隱隱的想要表達卻囿於時代和思想的局限沒有表達出來的。於是,海斯特的形象固然光輝了,可是卻有些不現實。那種年代,如果女人生出了這種思想,我想,只有被釘在恥辱架上問吊的唯一結局。
電影給了黛米摩爾太多戲,讓我覺得這就是一部女人的勵志史詩。小說中的海斯特從始至終就認為自己是罪惡的,但是電影中她昂起了高傲的頭,從沒承認過自己的愛情是罪惡。
我更喜歡電影,是因為故事發生的年代太久遠,故事發生的背景我不甚瞭解。我更願意接受電影中有幾個具有同情心的婦女在幫助海斯特,更願意接受在海斯特受訓的時候牧師走上前去,還有,最後,在海斯特生死攸關的時刻,他站出來說,我愛這個女子,我是這個孩子的父親,在神的眼中我是這孩子的父親。這其實已經顛覆了原著中丁梅斯代爾的全部人格。在原著中,他虛弱,他懦弱,他偽善,他冷酷甚至殘忍。明明敢愛為何不敢承擔責任?聖壇的光輝吸引著他使他不能放棄自己高潔的名聲。說起他在肉裡陷刻紅字和鞭撻自己,與其說這是他對愛情的懺悔不如說這個宗教的腐朽毒液侵蝕後的必然結果。他對海斯特毫無憐憫,反而認為他們是或許誘惑墮落的一對,這一切都有悖他自認為聖潔的內心。這才是他痛苦的根源。
那些泯滅人性的清教教條,是霍桑想要控訴的,但最終他含而不露。也許是沒勇氣也許是自己也沒有看到自己內心這種訴求。因為人性的糾結和深厚歷史的縱貫,這部小說得以名垂青史。
或者可以說,電影改編不成功,因為內涵和精髓有些離題甚遠。不過,我倒認為這更符合現在的人欣賞的視角。電影的最後,牧師和白蘭以及珠兒一家三口走了,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結局。總而言之,人們希望通過電影得到的,是美好的享受和期盼,而原著的精髓就是一個十足的悲劇。
推崇電影。可是,想要領略名著的魅力還是去看原著。
回應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個人覺得電影與原著差的也太遠了吧,Arthur Dimmesdale 到最後沒死,Roger Chillingworth 卻上吊死了,這就是美國人吧,總是不那麼serious
真是按照霍桑的想法拍的話,就陰暗的一塌糊塗,,估計更沒人看了,電影麼,也為了娛樂大眾麼
文學名著的永恆魅力在於它富有戲劇性的衝突和張力,深刻的人物性格的塑造,鮮明人物對比和突出的矛盾主題才是著作流傳千古的精髓所在…而電影改編承擔著迎合觀眾口味的責任,很多只是刪繁就簡,篡改原著精神面貌,使原有的核心主題喪失,更是經常發生的事…所以不朽的永遠只是文字性的原著,影視改編作品大多只是反應原著的影響力,充當一種娛樂功能…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3293081/
紅字- 霍桑- 小說線上閱讀
http://book.kanunu.org/book4/10248/
紅A的含義 2009-06-22
我不懂美國的清教傳統,更不懂聖經中的救贖觀,沒有能力來評價這部經典中的經典,只能簡單地談一下“紅字A”的象徵意義。
第一層含義,紅字A代表Adultery,即通姦。主人公海絲特•白蘭和年輕的牧師丁梅斯代爾通姦,生下一個小孩,為了保護牧師,海絲特獨自一人承擔了罪過,被“示眾”三小時。並被懲罰戴上紅色的標誌A。
第二層含義,紅字A代表Able,即能力。海絲特在一個遠離人群的地方孤獨地生活,把唯一的愛都放在孩子珠兒身上,她以做針線活養家糊口。這時A代表海絲特的能力:生存能力以及高超的手藝。
第三層含義,紅字A代表Angel,即天使。海絲特並沒有因為受白眼而懷恨在心,而是熱心地幫助別人。後來,由於她的這種美德,大家認為A是美好的象徵。
換個角度看,紅字A還有其他的含義。和海絲特佩戴紅A標誌相對應的是牧師丁梅斯代爾,他由於內心的罪惡,一直飽受折磨,可以說他佩戴的A是無形的,是精神層面的,和肉體相對應。
分析到這個地方,我可以大膽地說,書中的每個人物都佩戴著一個A,生活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正義者”,他們提議以A懲罰海絲特,是A的製造者;那些圍觀的人群是A的旁觀者;海絲特的丈夫是個“道德敗壞的人”,他是A的探究者;而大自然的禮物珠兒是A的罪果,也是A的拯救者。
所以,我的最後一句話是,A代表整個美國(AMERICA)。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85824/
霍桑的救贖 2008-02-20
這是一部有關心靈罪惡的懺悔錄,而非簡單的隱忍的愛情史。儘管霍桑曾經極力想要擺脫父輩遺留(參與了1692年的驅巫案)的罪惡,而其世界觀中的清教徒意識依然存在並因此影響著他的創作,書中苦於掙扎的主人公並沒有表現出過多超越於歷史的自省意識,幾乎所有人都淪陷在犯罪與對罪惡的救贖之中而無法掙脫命運的枷鎖。
在加爾文教義中,一個罪人不可能根據自己的願望獲得贖罪,他的靈魂的拯救完全取決於上帝的“選擇”。這也是丁梅斯代兒始終處於一種脆弱無助心理狀態的癥結所在,作為一個虔誠的牧師,最為接近上帝,甚至被封為聖人,感化了眾人卻無法拯救自己失足的靈魂,甚至無法對自己的罪孽作出彌補,足以淹沒他的讚美與崇拜使他的良心受到了更為深刻的譴責。作為一位虔誠的清教徒,他最終選擇出逃來從新開始,而從本質上說是他對自己信仰的叛逃與否定,所以當他心力交瘁地死在懺悔的邢臺上的時候,這個結局其實早已註定。他與白蘭的密臨約定由此看來更像是一場迴光返照。很多人不喜歡書中這個過於脆弱無助的角色,他試圖用愧疚填滿生命的間隙而從未給愛情留出足以滋長的空間,他難以激起我對他曾經狂熱過的愛情的想像,愛情是他偶爾淘空了自己後拿來慰藉自己的一種寄託。本書的譯者曾用過“偽善”來標定丁梅斯代兒,事實上它源自人性深處的自私,恐慌與手足無措的自我保護,對與丁梅斯代兒我們應該給它予中肯的寬宥,畢竟這份難以堅守的愛情從一開場就代表著一份難以救贖的罪惡,它牢牢地嵌在上帝的戒條之中。
所謂罪惡,在書中應該是給被完全重新闡釋的定義。對於不同的人物都應該具體而微,單單從教義上來看,白蘭與丁梅斯代兒的越軌不當的戀情顯然是不會得到容忍的,儘管他們共同造就了這短被他們看來是錯誤的歷史,而兩人面對罪惡的態度與方式卻迥然不同。海絲特公開地經受罪惡所帶來的懲罰,並通過近乎苦行的生活對自己救贖,並漸漸在一個漫長的七年的時光中覺醒,有了從牢籠中掙脫出來的意識,一種自由與獨立的意識。而正是擁有了這種意識,白蘭能夠在丁梅斯代兒死後坦然自尊地生活下去,並將那個恥辱的標誌A變成德行的象徵。而丁梅斯代兒隱藏了罪惡,備受折磨,當他不堪這種罪惡對心靈的積壓在生命的餘輝中決定徹底地懺悔時他成為了一名殉道者。齊靈渥斯的鬱鬱而終是對人們慎重的告戒,當一個人的心靈完全被仇恨所佔據並不擇手段甚至最為陰毒的手段復仇時,他離撒旦也就不遠了,這是一個人自我墮落與毀滅的過程----純粹的罪惡。
霍桑書在中的對於宗教態度是摸棱兩可的,帶有一種複雜的情緒,雖然在書的後半部分它帶有明顯的批判色彩,而就整步作品而言,對於上帝的這種捆綁式的信仰一方面是對人性的束縛與禁錮,另一方面又是一種淨化。 霍桑並沒有全盤否定宗教的作用,尤其是在這部對人物心理有著如此細微刻畫的小說裡。白蘭是一個被還原於真實的人物, 她並非電影《紅字》中摩爾所扮演的那個無所畏懼的女性形象,應該說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心中時常洶湧著波濤,在一種堅忍之中亦然會出現恐懼,動搖,不安。她不止一次地在精神上將自己交由上帝處置而沒有產生過由那個男人來拯救自己的奢望,信仰成了她靈魂的某種寄託,並使她得到某種警醒,這種警醒時刻引導她在現實中保持勤勞與善良的品質。這成了她的救贖。
書中還有一個最為接近自然人的角色---珠兒,這個遺傳了白蘭狂野與無畏孩子安全脫離于宗教的光環之外並因此保持著一中於生俱來的靈性,即便她偶爾會被視為邪惡的精靈。她的身上因為散發著人類自由的氣息與野性,時刻保持著一種歡快的狀態而很容易受到我們的偏愛。或許她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人類的理想狀態。《紅字》於1994年被改編為電影,而電影中由DEMI MOORE扮演的白蘭事實上活脫脫就是一個珠兒。而與原著不同的是,電影更著力于愛情引導自由與獨立的力量,或許它也是種與 霍桑殊途同歸的救贖把。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08755/
象徵,含混與不確定性 2013-09-07
引言
“令人想入非非——因為它所呈現的世界比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個世界激動人心、更富吸引力;使人受傷害——因為它使心靈不宜於從事種種更為嚴肅乏味的精神活動;讓人上癮——因為每篇小說似乎都只是旨在引起讀者更多的欲望。這些僅僅是通常對小說所發怨言中的一部分。
可是,當小說的大眾性越來越牢固地確立時,上述這些嚴肅的人——而今也包括女人——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開始利用小說為他們自己的嚴肅地意圖服務。他們將哲學思考、生活見解、道德憂慮這些引人思索的東西串在一根令人興趣盎然、或者扣人心弦的情節線上。久而久之,情況變成這樣:儘管我們在一生中讀到、看到和聽到數以千記的故事,可我們僅僅“研究”那些情節和主題均具有可讀性的小說。” ——尼娜•貝姆 鄧延遠譯
霍桑的《紅字》無疑是一部情節和主題均具有可讀性的小說。它自問世以來便得到了眾多評論家的青睞,更有甚者將其譽之為霍桑小說創作中最傑出的成就,美國文學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那麼,究竟是怎樣一部小說能夠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歷時約一個半世紀而不衰呢?
寫於1850年的《紅字》是霍桑四部長篇小說(餘下三部為《七個尖角閣的房屋》(1851)、《福穀傳奇》(1852)、《玉石雕像》(1860))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說描寫了新英格蘭在美國殖民地時期所發生的一段動人心魄的三角愛情故事。由於丈夫長年在外且對其並無感情,赫絲黛成了羅傑所謂體面婚姻的犧牲品。直到邂逅了真正的愛情,赫絲黛終於難掩內心的狂熱與牧師丁梅斯德實行了通姦。不幸懷孕被發現,之後又生下了他們罪惡的果實帕爾。在教權統治下的人民的逼供中赫絲黛堅決隱瞞了牧師的罪行,結果自己被佩戴上了恥辱的紅字。赫絲黛的丈夫羅傑齊靈窩斯聞訊趕回,找來當地眾人愛戴的牧師丁梅斯德,要他查出通姦犯以實行報復。兩人不斷合作,隱隱的羅傑感覺到了牧師的秘密,但並未揭穿。牧師的身體一天一天虛弱下去,直到最後去世,以悲劇收尾。原來牧師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內心的煎熬,他在自己的肉體上用刀在胸前刺下了血淋淋的紅字,並在每天晚上的時候脫下衣服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肉身以向上帝懺悔自己的罪行,結果導致身體每況愈下直到猝然離世。而羅傑的報復手段則是不揭穿這個秘密,讓牧師一直得不到救贖,一直生活在煎熬之中。
在這部小說當中,霍桑描寫了一段陰暗的殖民地時期教會統治下的輝煌的罪惡。當然,如果就這樣平鋪直敘的話,顯然沒有多少懸念可言,妙就妙在作者採用了倒敘的手法,直到最後關頭屏吸之後才恍然發現原來牧師便是人們苦苦尋找的那位通姦犯,令人不得不拍案叫絕。但這又並非一部偵探型的小說,因為文中大量充斥著心理的描繪與感情衝突,並且紅字貫穿始終,以其開頭以其收尾,具有強烈的象徵和暗示意味。
倘若略去其主體的精緻結構及佈局手法,不去思考具體物象背後的隱秘含義,不去關心小說修辭所帶來的閱讀引力,那麼它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個殖民地故事中的一個。而一旦透過小說中人物對其所嵌入的背景進行時代性反思,則往往會驚歎于霍桑對其筆下人物所進行的不確定性處理,這有效的實現了語言的節制和模糊化。因而我們很難一言以弊之說誰有罪,或簡單的將其歸結為一個道德的評判問題。他用象徵,含混和不確定性的手法構築了一個三棱鏡,將小說的主體之光透射出來,呈現出斑斕的色彩。
通過對小說節奏舒緩的把握,意像的反思,則不難隱隱窺見或略微感覺到潛藏在敘事表皮下那推動敘事發展的推力杠杆和引擎所產生的效應。而本文將對表層敘事中的突出意像進行解構,在眾多的詞彙當中選取“刑台”,“A字”,“帕爾”等意象作為切入點。通過對這些線索的分條縷析來理解霍桑小說中象徵,含混,和不確定性的運用,從而更好的理解人物的罪感意識,進而對主題進行發微。
一、“象徵”——他者的介入與融合
黑格爾說“象徵所要使人意識到的卻不是它本身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的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的意義”。問題是是否存在普遍的意義,因為一物體在此領域為此意義,但在另外一領域又另作他解。比如玫瑰象徵愛情,但在非洲一些部落裡卻存在玫瑰與人頭的隱喻。於是我不禁覺得,所謂的普遍的意義是就其所在的系統而言的。而要尋找《紅字》中物象的普遍性意義,就必須得回到文本的系統中去。而要理清象徵的概念又不得不理清它與比喻的分界,只有找出其差異性,這樣才便於主體確立。
普遍性的建構與象徵有何關係。簡單的說是抽象而非具體,是普遍而非個別。 那麼這個普遍性的認同,破譯的密碼從何而來,就好比最初的貨幣流通形式用貝殼一類的東西替代,而貝殼就成了財富的象徵。那麼,象徵所指向的並非其物本身,而是他者所建構的賦予在其特性上的意義。那麼它是否具有穩固性呢,顯然,它早已脫離了其作為名詞的本意,而是作為一種相關性的意義而存在。
象徵是一些文學作品中常會用到的修辭,尤其是在詩歌當中。在一些偉大的浪漫小說當中也會有意識的進行一些詩學的架構,以期達到一種言近旨遠的意蘊和延展空間。在小說《紅字》當中,這類修辭的應用則十分明顯。因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小說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往往會不斷地給人以暗示,其一在於重複,其二在於場景。比如“刑台”,分別在開頭,中間和結尾出現,而“紅字”則是貫穿始終。
“這座台架實際上是整個刑法機器的一部分。從上溯兩三代人時直到現今,這種台架只是作為歷史與傳統的遺留物被我們保存著,但在以前,卻被當做提高公民道德水準的有效手段,就像法國恐怖主義者使用絞刑架一樣。總之,這台架是一個示眾台,上面豎著一個定型刑架,定位架可以將人的頭部緊緊夾住,這樣,罪犯就只能仰臉朝向觀眾,恥辱的概念就是用這個木頭和鐵的裝置體和顯示現出來的。” ——第二章 《市場》第十頁
故事由此發端,赫絲黛抱著出生不久的小帕爾在刑臺上接受不貞的審問,而審問他的卻是牧師丁梅斯德,戲劇性的地方在於,丁梅斯德恰恰就是赫絲黛的情人。他沒有勇氣公開承認,但另一方面又虔誠的信仰著宗教的教義。從他那“續續斷斷的聲音”“深陷,困惑的眼睛”便不難發現,此刻在刑臺上最受煎熬的與其說是赫絲黛,毋寧說是牧師丁梅斯德。
刑台作為一種審判和受難的標誌,從這一具體的情景中被賦予了象徵的意義。
於是邢臺本來的意義漸漸被抽脫,他者介入進來,由物向內滲透,慢慢逼近丁梅斯德的內心。
“她默默登上臺階,一隻手挽著小帕爾,站在台架上。牧師摸到孩子另一隻手,把它握著。就在他握住孩子手的一刻,一股不是源於自身,而是來源於他人的新生命的激流,如奔騰湍急的洪水注入了他的心” ——第十二章《牧師的不眠夜》 第九十頁
在自我的懺悔和救贖中經歷了長久的精神折磨之後,丁梅斯德終於無法用宗教的那套戒律來壓抑自己的本能和內心的聲音。他再一次獨自默默一人在一個夜晚來到七年前他審問赫絲黛的刑台,不過這一次,他審問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他對赫絲黛的愛,對小帕爾的思念,難道也是一種罪惡嗎,人性開始向宗教發出了挑戰。而這時恰好赫絲黛與小帕爾路過,看到了牧師在黑夜中大聲申訴的一幕,於是三個人受本能的愛的驅使,第一次走在了一起,“他們三個組成了一條通電的鐵鍊”。
但夜色過後,當太陽再次升起,他又由自我,情人,轉變為代表神靈說話的牧師。這種角色的轉化使他深感痛苦,卻又身不由己,找不到出路。他不斷的為他人普渡,為他人開脫,為他人尋找彼岸。可是自己卻深陷於罪惡感的牢籠當中,淪陷在此岸。
“請以如此可怕又如此慈悲的、在這最後時刻賜我以神恩的上帝的名義,來做那件——為了我自己的深重罪孽和可恥痛苦——七年前我沒讓自己做的事吧,現在請到我這兒來,用你的力量給我以支持吧!你的力量,赫絲黛;但是,讓它接受上帝授予我的意志的指導!這個卑鄙討厭的老頭竭盡全力——用他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魔鬼的力量——在阻止我這樣做!來,赫絲黛來吧!扶我走上示眾台!” ——第二十三章《紅字的顯露》第一百七十五頁
這是最後丁梅斯德終於悟透,釋然,在白天走上刑台時的場景。他的身體在長久的自我懲戒中變得虛弱不堪,接近死亡的意識讓他愈發的開始反思自己篤信一生的宗教意義何在。它不但沒給自己以出路和解脫,彼岸反而也因此而阻隔,自己一生都處在折磨與受難當中。那麼,出路何在,於是他發出了掙脫的呼喊,它要和魔鬼較量。生命的本來面目不該如此,如果是罪惡,那麼也是宗教賦予和定義了這份罪惡,罪惡本身是不屬於生命的本來面目的。最後,他在眾人面前向赫絲黛發出了愛的渴求與宣告。神的代言人瞬間成了眾人所謂的罪惡的化身,這是多麼大的諷刺,成了對罪惡本身的咭難。
縱觀下來,每一次的遭遇無不是抗爭,第一次是隱瞞姦情的抗爭,第二次是自我解脫的搏鬥,第三次是臨近死亡向宗教發起的挑戰。在這一曲折的抗爭當中,一直靜默不語的,不變的情境是刑台,但每次變化了的卻是主人公的心境。似有畫外之音,作為一個他者不斷的介入,最後完整的融合入於整個事件的發展當中。一解為象徵著宗教不斷讓步於人性,最後人性勝利的過程。這比較符合人們的情理——啟蒙,解放,從而使主題昇華。但是,如果是對宗教的挑戰的話,那麼最後丁梅斯德的死亡又意味著什麼呢,人們並未因此改變,他為罪惡辯護,最後卻為罪惡殉葬。但從某個意義上,他用自己的死亡打開了一道口,劃出了一道亮光,儘管只如流星之一瞬。
“那標誌十分黑暗,唯有一個永遠閃著紅光的光點點綴其上,可它卻比那灰暗部分更加令人沮喪” 他的墓碑上寫著“在一片黑的底色之上,字母A,為紅色”,霍桑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肯定中似乎帶有否定,否定中似乎又隱含著肯定,於是我們僅僅從象徵來看,顯然無法理解這種態度,那麼在他者之外,主體的含混就成了很有意味的一件事。
二,“含混”——言有盡而意無窮
1930年,一位英國詩人在劍橋大學由數學專業轉讀文學專業,師從大名鼎鼎的文學理論家I.A.瑞恰慈。作為學生的他,在瑞恰慈給他批改的一份作業中得到啟示,寫出了震驚現代西方文學界影響久遠的著作《複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一書,也有的翻譯成《含混的七種類型》。該書改變了整個現代詩的歷史,也開創了“細讀”批評範例。從此西方文論當中便多了一條重要的術語——含混,人們闡釋的維度再一次被大大的放開。這位批評家的名字叫做燕蔔蓀,一位與中國頗有緣分的詩人和學者。
而早在古老的中國,劉勰也在《文心雕龍》“隱秀”篇中也提出“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跨過時間和空間,可謂兩個知心人,遙相呼應。
在此之前,西方文論一直推崇語言的明晰性。覺得意義含混不過是詭辯家們用來迷惑人的招數,就像公孫龍著名的“白馬非白”一樣。可是這種一元性的論斷似乎無法解釋“為何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難題,它把語言囚禁在了一個固定的文本的牢籠中。而燕蔔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詞彙從牢籠中解放出來,恢復它多元的生命力。
那麼,在討論霍桑的小說《紅字》時,就不得不去注意這樣一個問題。
彭玉石先生指出聖經原型對霍桑小說創作的影響很大,因為他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同時塑造了聖徒和罪人的形象,顯然,這裡指涉的是丁梅斯德牧師和情人的雙重角色。而在赫絲黛身上呢,說她不貞,這是事實,但是她為的是自己的愛情;說她為的是愛情,可這愛似乎又是自私的,被情欲俘獲的愛情,全然沒有考慮到愛人(老傑克或丁梅斯德)所經受的折磨和痛苦。因此,對於人物性格的刻畫方面,我們不難窺見其匠心之所在。他們較為明顯的表現出含混,模棱兩可,矛盾的特質,這使得我們較難像評判傳統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將其歸納到某一類型或某一標準上去。然而這也是《紅字》一書的獨特魅力所在,言有盡而意無窮,在不斷的被闡釋中得以延續其生命力,確立其經典的地位。
“她對自個兒說,這兒是她犯罪的地方,因此,這兒該是她接受人世懲罰的所在。在這兒,日復一日的恥辱的折磨或許能淨化她的靈魂,使她在喪失純潔之後再次獲得純潔,使她由於不惜殉道而變得更加神聖。”——第四章《見面》第三十頁
“赫絲黛在那個時期的內心交戰永遠滲入了帕爾的心靈,她能在孩子身上認出她自己不顧一切的瘋狂的挑戰心態,情緒的反復易變,甚至看得出曾陰雲般籠罩在她心頭的某些憂鬱和沮喪。”——第六章《帕爾》第三十九頁
在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在世俗的理性層面,赫絲黛對於宗教的教義是全心全意的接受的。她接受懲罰,甘願被流放到殖民地,過著邊緣人的生活。可是,在潛意識當中,她對於自己的行為卻並不後悔,世俗的規則無法取代她內心的信念。那麼,她的心甘情願的接受懲罰,在懲罰中獲得寬恕的行為似乎又是對其懲罰本身的一種嘲諷。可是,最後不能理解的地方在於,當小說行將結束時,帕爾遠嫁歐洲,可以離開的時候,她卻選擇了留下來,並且“從此以後紅字就永遠沒有離開過她的胸前。”
難道是丁梅斯德的死亡讓她再次感到罪孽的深重,抑或是用紅字來昭示世人,人人皆是有罪。在《紅字》當中,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無罪的人,赫絲黛受了情欲的誘惑所犯的通姦之罪,小帕爾是他們罪行的見證,是“惡之花”;牧師隱瞞罪行,犯了不誠實的罪;老傑克報復心重,犯了侵犯他人之罪……
而牧師只有在鼓起勇氣直面罪惡的時候才獲得了超脫,才放下了枷鎖,赫絲黛亦是通過不斷的行善和修行來減輕自己的罪過。這麼看來,這部小說似乎對於罪惡又是肯定的,他們並沒有反抗,反而是妥協了。
含混的效果便顯現出來,從這個維度又可以得出一個截然相反的結果。它們從紅字這一點向四周綿延輻射開來,以至於我們對確定性不禁產生了懷疑。
三 “不確定性”——半飽的詞義
在現代主義的思潮下,修辭學中象徵,新批評中含混概念的運用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了文本。但這種理解從一開始似乎又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常常會走到一種解釋的困境,甚至有時候會走到相反的兩端,矛盾的境地。於是,後現代主義者乾脆以一種反叛的姿態站出來解構一切,他們宣稱“確定文本或詞語意義的不可能性”,甚至有極端者認為具有“不可讀性”。將一切意義都給掏空,掀了個底朝天,因為破壞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常常會有出乎意料的觀點,像是縱火者或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
而不確定性作為後結構主義文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被提出來後亦是激發了廣泛的討論。它的基礎是結構語言學的理論,即索緒爾的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對應關係是人為的,語言的意義則是由符號的差異所決定。去解釋語言符號的意義,就變成了
“以新的能指符號去取代有待闡釋的能指符號的過程,或者說是由一種“能指”滑向另一種“能指”的無止境的倒退。在這一過程中,符號所指代的實物實際上是永遠不在場的,也就是說,“能指”永遠被限制在一個語言符號系統內,永遠不能觸及它所喻指的實體。”
這樣文本就變成了一個半開放的系統,不再封閉,而重心也實現了轉移,由內在的互相指涉轉向了所指,由文本的確定性轉向了物件的不確定性。
《紅字》當中人物的塑造無法脫離前後的語境和語言上的細節,哪怕是一個表情,動作,或者一句話。而這些東西並不是文本自然生成的,它受到整體的影響。如果說含混是由局部的語境所產生的話,那麼不確定性則是由整體的語境延伸出來。
它重視文本之間的關聯,將語境擴大,聯結過去的作品,聯結時代的語境。但這樣永遠也無法飽和,因為關聯具有無限的延展性,語境的延伸又形成互文性。
“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是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分文本的吸收和轉化”——克裡斯提娃《符號學》第九百四十七頁
《紅字》當中對於聖經中原罪的轉化移用,在人物塑造過程中對人物所進行的雙重角色的疊加,在敘事策略上將婚外情的故事加以改造,然後又將自身的殖民地經歷融合起來,將複雜的宗教信仰與自我矛盾的心理注入到文本中去……
經過不斷的發酵,文本寫出來後,就好比脫胎的產兒,不再受到作者的控制。在它進入讀者的視野中時,在眾多的讀者那裡,意義開始交織在一起,讓人不禁發出“作者已死”的感慨。於是對於丁梅斯德,對於赫絲黛,對於帕爾,再也無法做出判定,就連作者自身,在創作的超驗狀態下,恐怕也無法控制。因為在寫作的過程中,他不斷受到以往的閱讀經歷,欲望,歷史,或語言的指涉和介入,並受到前面的情節的牽制。由於無法擺脫文本的關聯性,那麼不再是他控制著文本,而是文本在囚禁著他了。
結語
紅字,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當中開頭的字母,卻蘊含著不止於二十六種的意義,或者,本來就無意義,印證著那句古老的英文諺語“all or nothing”。
但從故事的發生背景來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大衛發現,十七世紀的波士頓,兒童學習字母的書上,每個字母都會附有一首說明性的小詩,在第一個字母A下,小詩是
“隨著亞當的墮落
我們都有了罪惡
我們從開頭就跟著亞當犯了罪”
這期間有無必然聯繫,怎會如此巧合,會不會產生互文性,霍桑有沒有受過啟發,這些無從考證,否則會有過度解釋的嫌疑。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對於研究者而言,無疑受到了啟發。
亞當和夏娃的偷吃禁果,被驅逐出伊甸園,是否成了小說的母題呢?相比之下,丁梅斯德與赫絲黛也是觸犯了條例被流放到殖民地。如果沒有亞當夏娃的走出伊甸園,也不會有人類,因為這意味著神性向人性的轉化。那麼如果沒有赫絲黛的出軌,也不會有後來的秩序的動搖,牧師的反思。到這裡似乎是找到一把鑰匙了,事情變得明晰起來,可惜建立的基礎卻只是相似性,無從考證也無法確認作者是否受其影響。
而象徵,含混作為重要的小說技巧,作者熟稔的運用起來,常常進行一種模糊化處理,更是為《紅字》披上了一層薄紗。它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對於神秘宗教的好奇,另一反面引起了人們的反思。本來象徵,含混最初是用於研究詩歌的,在這裡,在霍桑的浪漫主義小說中,卻彌漫著象徵與含混,這無疑也是一種詩化的處理,耐人尋味,進而增強了可讀性。
在《紅字》中,通過含混,象徵與不確定性的透射,人物的堅固的意義被打碎,具有了流動性。意義依託語境來呈現,而語境永遠不會飽和,不會充分確定。這樣就存在鬆動的可能,它使得人物無法被簡單的裁定出來,而是由晶體變成了化合物,意義在符號的表徵下遊移,通過物象的重複的節奏不斷呈現出迷人的色彩。
紅字的故事雖然結束了,可意義從未凍結,正如小說開章寫到的那樣“在我們這個從那座不祥的牢門開頭的故事剛要開始敘述時,就劈臉看到這叢玫瑰,我們只能情不自禁地摘取它的一朵花,將其獻給讀者”。
【參考書目】
(1) 《紅字》,霍桑著,周曉賢,鄧延遠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 《含混的七中類型》,燕蔔蓀著,周邦憲,王作虹,鄧鵬譯,中國美術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3) 《符號學》,克利斯蒂娃著,朱立元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4) 《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張首映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67109/
[聖經與文學]穿透黑暗的愛與恩--論霍桑的《紅字》 作者:郭秀娟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一章9節)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在殖民兩百多年之後,歷經各種新舊思想的激盪與變動,終於在文學園地開花結果,一部部經典名作幾乎同時孕育而成。其中包括:史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1852),藉著黑奴悲慘的一生探討奴隸解放議題;崇尚個人絕對自由的超驗主議者愛默生,出版了他的思想鉅著《代表性的人間肖像》(Representative Men,1850);梭羅發表他的古典隨筆《湖濱散記》(Walden,1854);惠特曼劃時代的詩集《草葉集》問世(Leaves of Grass,1855);麥爾維爾則寫下美國文學史上的曠世經典《白鯨記》(Moby Dick,1851)。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正是在美國文壇這樣豐收的年代,於1850年寫出使他屹立世界文壇的《紅字》。霍桑在這部描寫「人性的脆弱與悲傷」的小說中,融入影響他個人極為深遠的清教徒遺傳,深刻剖析罪的意識對身心靈的影響、尖銳地批判已經淪為律法主義的清教精神、探討個人在自由與權威中的掙扎、赤裸裸地呈現人性中的愛恨糾葛。為此,霍桑被認為是美國文學史上浪漫小說和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者。
人性的脆弱與悲傷
《紅字》的舞台架設在1642年的波士頓殖民區,比霍桑所處的年代早了兩個世紀,正是他的清教徒祖先踏上麻州的年間。故事第1章從「獄門」的背景開場,霍桑在下面這段精彩的描繪中,似乎預告了小說的重要主題:
新殖民的建設者,無論他們原意是怎樣計劃著人類美德與幸福的烏托邦,然而總是從一開始,便在實際的需要中,認為一定要劃出一部份處女地作為墓地,另外劃出一部分作為監獄的地基。……在這片土地上這麼早就產生了文明社會的黑花--牢獄。但是在門口的一邊,幾乎就生根在門檻上,有一叢野薔薇,在這六月的時光,綴滿精緻的寶石般的花朵,使人想像,當囚徒進門或當被判決的犯人出來受刑的時候,它對他們呈獻出芬芳和嬌媚,藉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胸裡,對於他們還有憐憫,還有溫存。(頁75~76)
牢獄所象徵的罪惡、墓園象徵的死亡、薔薇象徵的希望,正是交織成整個故事情節的基本元素。故事的整體發展,雖然環繞在慘澹、陰暗的氛圍之中,卻隱隱透露出一線曙光。
故事在第2章就切入情節核心,女主角海絲特‧白蘭從這道陰深的獄門走了出來,手上抱著三個月大的嬰孩珠兒。海絲特的胸前,繡著一個腥紅的A字,四周還鑲上美麗的金線。她因通姦罪入獄,但她拒絕洩露孩子的父親是誰,於是被判站在絞刑臺上示眾三個小時,並得終生佩戴那個恥辱的標記。海絲特失蹤多年的丈夫,此刻悄然出現在旁觀的群眾之中,身材略顯畸形的老學究,這時化名為精通醫術的羅格‧齊靈窩斯醫生。他威脅年輕的妻子對他的身份保密,並發誓一定會找出那個藏身在黑暗中的共犯,意圖對他施加報復、使他的靈魂滅亡。
鎮上有一名頗受人敬重的青年牧師,叫亞瑟,丁梅斯代爾,他是海絲特的牧師,齊靈窩斯選擇他作為自己的精神導師。牧師當時身體狀況日益衰弱,一旦遭受點驚恐或意外事件,就會習慣性地將手攏在心上,臉色會驚惶地泛紅變白。他後來接受會眾善意的安排,邀請老醫師同住,接受他的治療。故事一直進行到第10章(全書共24章),齊靈窩斯和讀者才赫然發現青年牧師的秘密--他的胸前也有一個血紅的A字。霍桑並沒有交待這個嚇人的標記,是隱喻式的,還是實際烙在牧師的肉體上,使得這部帶點偵探意味的浪漫小說,更添幾許神秘氣氛。
清教倫理與浪漫主義的衝突
在這部大約十五萬字的小說中,霍桑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楔子,名為「海關」,交待他怎樣獲得「紅字」的歷史殘存文件。大多數中譯本都將這篇文字刪除,認為與小說關係不大。不過,近代學者多數認為「海關」的序言,是解讀《紅字》的關鍵。
霍桑在這篇序言當中,細數他的譜系淵源。在移民到麻州撒冷城(Salem)的霍桑家族中,他特別提到隨身攜帶著聖經和寶劍的威廉‧霍桑(William Hathorne),他是一名法官兼教會首領,在1662年曾經嚴酷無情地逼迫貴格會的婦女。他的兒子約翰‧霍桑,繼承了這種迫害人的稟性,在1692年一樁審判異端的「撒冷城驅巫案」中,扮演主導的角色,處死十九人。霍桑為祖先沾滿血腥的殘酷行為,感到羞恥,他認為霍桑家族的敗落,實在是上帝的詛咒。霍桑甚至在入大學時,在自己的姓氏上加了一個w字母,以示和祖宗有所區別。
另一方面,霍桑在序裡將讀者拉回他所處的時代,追述多位文壇友人。他曾經在愛默生的影響下,加入「理想農莊」,生活了三年,體驗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他述及自己怎樣在華爾騰湖畔與梭羅談論自然;曾經在朗費羅家的爐火旁受到詩情的陶冶;麥爾維爾更一度是他最好的知己。
在這篇序言中,霍桑以相當負面的筆調,描繪他任職三年的撒冷城海關。他為了生計,不得已中斷自己多年的寫作生涯,於1846年出任海關首席檢查官,處在一群愛打瞌睡、沒精打采的老吏中間。不幸由於政權交替,霍桑遭受革職。在妻子的鼓勵之下,霍桑重拾自由的詩魂,靠著妻子的一點積蓄過日子。只花了一年時間,就寫下《紅字》這部傳世的心靈羅曼史。他稱自己的作品為「一個上了斷頭台的檢查官的遺作」,丟了官卻意外使自己被禁閉的心靈獲得重生,雖然他豁達地寫道:「祝福我的朋友平安無事!寬恕我的敵人!因為我已處在寧靜的天國。」(頁73)不過,還是有學者認為霍桑藉著「海關」一文,一方面感懷以寫作為生的辛酸,同時也攻擊罷免他的政客。「海關」中老朽、僵化的氛圍,在紅字的清教徒社會清楚呈現。
霍桑對於清教徒主義,其實並沒有全然摒棄,他仍然不時以自己的優良血統與信仰為傲。清教徒本來就是一群擁有夢想的革命家,為了掙脫英國國教派的種種限制,乃至遠渡重洋到新大陸建構理想國,只是人性墮落的本質,加上政教合一的弊病,很快使一群被逼迫者,成為更嚴苛的立法者和迫害者。但是,霍桑也沒有全然擁抱當時文壇流行的超驗主義。他的世界觀相當複雜,一方面深受這種崇尚人道與自然的樂天思維影響,一方面又信仰悲觀的加爾文主義,即接受絕對的惡以及人性的全然墮落。也因此,孕育出這部充滿歧義性(ambiguity)與反諷性(irony)的深邃作品。
A字的歧義性
A字想當然耳代表「姦淫」(adultery),這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社會,設計出來對付海絲特的恥辱標記。不過隨著海絲特展現針線絕活,以及刻意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卻樂善好施,她逐漸贏得居民的敬重,他們漸漸視A字為「能幹」(able)的表記(頁196),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個紅字已含有如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了」(頁197)。霍桑說海絲特犧牲自己的享樂,積極行善,「恐怕並不是純真堅決的懺悔」,是一種「深深的謬誤」(頁112)。霍桑所指的謬誤,應該是海絲特想要靠行善、積功德而贖罪的心態。海絲特曾問牧師:「用善行來補救來保證的悔悟,會是不實際的嗎?」(頁231)靠工作得救,正是律法主義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傾向。因此,霍桑寫道:「那個紅字還沒有完成它的職務」(頁201)。
這點,在長期不肯認罪的丁梅斯代爾身上,也可以看見。對於這位青年牧師而言,A字首先指涉了他的姓名「亞瑟」(Arthur),也象徵他為了事業「野心」(ambition),過著假冒偽善的生活,沒有勇氣承認真相。霍桑藉牧師之口寫道:「他們畏縮不敢把自己的黑暗和污穢展現在人的眼前;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再有善行;而過去的惡行也無法用良好的服務來贖償了。」(頁166)由此可以看出,牧師也是錯誤地想靠作工得救,他加倍地敬虔苦修,講道充滿能力,即使最後已經計劃偕海絲特母女逃亡,他都還期待著,能夠在講完慶祝選舉的道之後,再完美地結束他的牧師生涯。只是,表裡不一致,終究撕裂了他的身心。
對齊靈窩斯和清教徒社會來說,A字代表了「老化」(aged)與「祖先遺傳」(ancestry),最終象徵殘酷的報復(avenge)。齊靈窩斯為了復仇,隱姓埋名,他「寧願把他的姓名從人類的名冊上取消掉」(頁150)。霍桑描寫他左肩比右肩高出許多,象徵他在知識與靈性的發展上不成比例。他被塑造為惡魔似的角色,因他犯了罪中之罪,越權踏入上帝的領域,想要使對手的靈魂滅亡。不過,他最後也良心發現,將遺產留給與他沒有血緣關係的珠兒。
清教徒社會宣稱珠兒是惡魔生的,海絲特卻堅稱這是上帝賜給她的寶貝,所以為她取名珍珠(Pearl)。當人們要搶走珠兒,海絲特叫道:「她是我的幸福!然而也同樣是我的苦惱!珠兒叫我活在世上!珠兒也給我懲罰!你們沒看見嗎?她就是那個紅字。」(頁144) 珠兒既是活的紅字,那麼她所代表的精神是什麼呢?這點相當難以掌握,或許珠兒是「天使」般的角色(angel),挽救海絲特的靈魂免於滅亡,若沒有珠兒,她可能早就自我了斷,或遠離人群、躲進曠野。珠兒惹人憐愛的容貌和不受馴服的天性,也可能象徵浪漫主義所高舉的自然,珠兒曾經為自己編織了一個綠色的A字。或許霍桑要我們正視人性的情欲,是極為自然的天性,因此不是鮮紅而是新綠。不過他在海絲特佩戴紅字示眾時也同時寫下:
在社會尚未腐敗到目睹這種場景不致戰慄卻反而微笑之前,這種場景裡並非不存著敬畏,而這正是一個人目睹恥辱與罪惡的光景時擺脫不掉的感覺。(頁84)
今日墮落的社會,人們傾向接受「只要有愛就沒有罪」,相較之下,霍桑、或海絲特或亞瑟牧師,他們保守得多,他們看待通姦是軟弱、是罪惡、是恥辱。代表自然精神的曠野,在《紅字》全書一直是相當負面的意象,未馴服的處女森林地,代表寂寞與疏離,是邪靈出沒的領域。
超越一切的恩典
雖然,海絲特多次任自己的精神在荒野徘徊,她的命運使她遠離人群,使她趨向成為一個自然人,但是,霍桑寫道:「這些做了她的教師,而且是嚴峻粗野的教師,他們一面使她堅強,一面也教給她許多錯誤。」(頁241)
七年來的法外生活磨練,使海絲特有勇氣提出逃亡計劃,因她不忍看牧師被齊靈窩斯折磨至死。然而,故事從「一片陽光」的第18章之後,情節急轉直下,迷惘的牧師終於看清:他不能逃走,他必須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事實,更重要的是,他發現神除了是公義的神,祂更有憐憫和恩典,祂是愛的神。
因此,在第23章「紅字的顯露」,丁梅斯代爾講完道後,勇敢地招呼海絲特扶他步上刑臺,他說:上帝在上,他是那麼可怕又是那麼慈悲,在這最後的一瞬間,為了我自己深重的罪孽和悲慘的痛苦,他已恩許我實踐七年前我自己畏縮避開的事。(頁296)
齊靈窩斯企圖攔阻他的認罪悔改,牧師對他說:「感謝那領我到此地來的上帝!」然後轉身對海絲特微笑,悄悄地說:「這不是更好嗎?和我們在森林中曾經夢想過的事比起來?」牧師以顫抖的聲音向會眾喊道:
請看我在這裡,一個世界的罪人!總算是到了這麼一天!總算是到了這麼一天!我終於站到我七年前應當同這個婦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就是這個婦人的膀臂,在這可怕的瞬間,用它小小的氣力,攙我爬到這裡來,支持我不致撲面倒在地上!(頁297~298)
牧師和珠兒親吻,破解了她所受到的符咒,「珠兒,做為一個痛苦的使者,對於她母親的使命,也已完成了。」(頁299)牧師在海絲特的胸前斷了他的氣息。
霍桑以最後一章交待了其他角色的結局。齊靈窩斯在喪失生存的意義之後,很快死亡,將一筆可觀的遺產留給珠兒,使她在異?享受著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而海絲特在消失多年之後,又回到新英格蘭半島邊緣上的老舊茅屋,繼續戴著A字過她懺悔的生活,成為女先知般的角色。她死後葬在牧師的墓附近,兩座墳雖然隔著一段空間,卻合用一個墓碑,全書就結束在這行碑文:
「一片黑地上,刻著血紅的A字。」(頁307)
結語:一部真正的基督教經典(楨:?)
事實上,霍桑對書中四個主要角色和清教徒社會,都是褒貶愛惡皆有,再加上現實的「海關」與虛構的小說之間的交錯,使得《紅字》充滿了雙元性(bivalence),造成評論家對這部作品的詮釋,產生許多衝突。多數人認為海絲特是真正的英雄,稱讚她勇敢的愛情和對自由的追求,視丁梅斯代爾的死亡為宿命式的悲劇。近代學者更喜歡以後現代學者的論述方式,如德希達與傅柯等的閱讀理論,重新探索《紅字》的文本,主張其意義不可尋得。其實,筆者相信任何一個閱讀《紅字》的基督徒,很自然會聯想到聖經中「行淫的婦人」故事(約翰福音八章1~11節),並與之對照。耶穌在那段經文強調祂救贖的使命,指出罪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應該使人類產生同情、彼此相愛。霍桑在寫作《紅字》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聖經和正統加爾文神學的影響--「倘若沒有上帝的慈悲,無論是用言語,或是用標誌,任何力量都不能暴露出那可以埋葬在人的胸懷裡的秘密。 」(頁165)--評論家不應該忽視這點。
惠頓大學的文學教授李肯(Leland Ryken),讚揚《紅字》具備高度藝術技巧和完美的結構,頭尾兩章為序和跋,作者平衡地在開頭、中間和結尾(第2、12、23章)三處關鍵篇章,讓全書最重要的四個角色,一起出現在可怖的示眾刑臺。李肯指出海絲特所面臨的衝突,在全書發展到一半就已解決--她早獲得清教徒社會某種程度的敬重,他指出:
至此我們才發現《紅字》的主角並非海絲特,而是丁梅斯代爾。……整部作品的進展,是為了尋求丁梅斯代爾的得贖。……一部作品能否被稱為「基督教經典」,必須看它是否展示福音的核心信仰。《紅字》,誠如評論家(W. Stacy Johnson)所言:「是救恩的完整呈現。」(Realms of Gold, by Leland Ryken, p.153)
對於認信基督的霍桑而言,《紅字》的終極關懷,應該是在於作家以他卓越的「藝術」形式(artistic),為讀者創造了這部無與倫比的「贖罪」故事(atonement)!
參考書籍:
1. Bloom, Harold, editor of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2. Harper, Preston, "Puritan Works Salvation and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in The Scarlet Letter", Theology Today, 2000, April.
3. Hawthorne, 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 Dodd, Mead & Company (New York: 1979).
4. Johnson, Claudia Durst, Understanding The Scarlet Letter,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95).
5. Ludin, Roger,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from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Baker Books (Grand Rapids: 1998).
6. Ryken, Leland, Realms of Gold - The Classic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Harold Shaw Publishers (Wheaton, Illinois: 1991).
7. 納撒尼爾‧霍桑著,侍桁譯,《紅字》(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再版)。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2002年5/6月號]
http://galilee.campus.org.tw/scarlet_letter.html
上一篇:洛爾迦:世界百大作家83
下一篇:德萊塞:世界百大作家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