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ock Body Lab: 階段展演及分享」- 在永恆的工作進行中,觀眾與策劃人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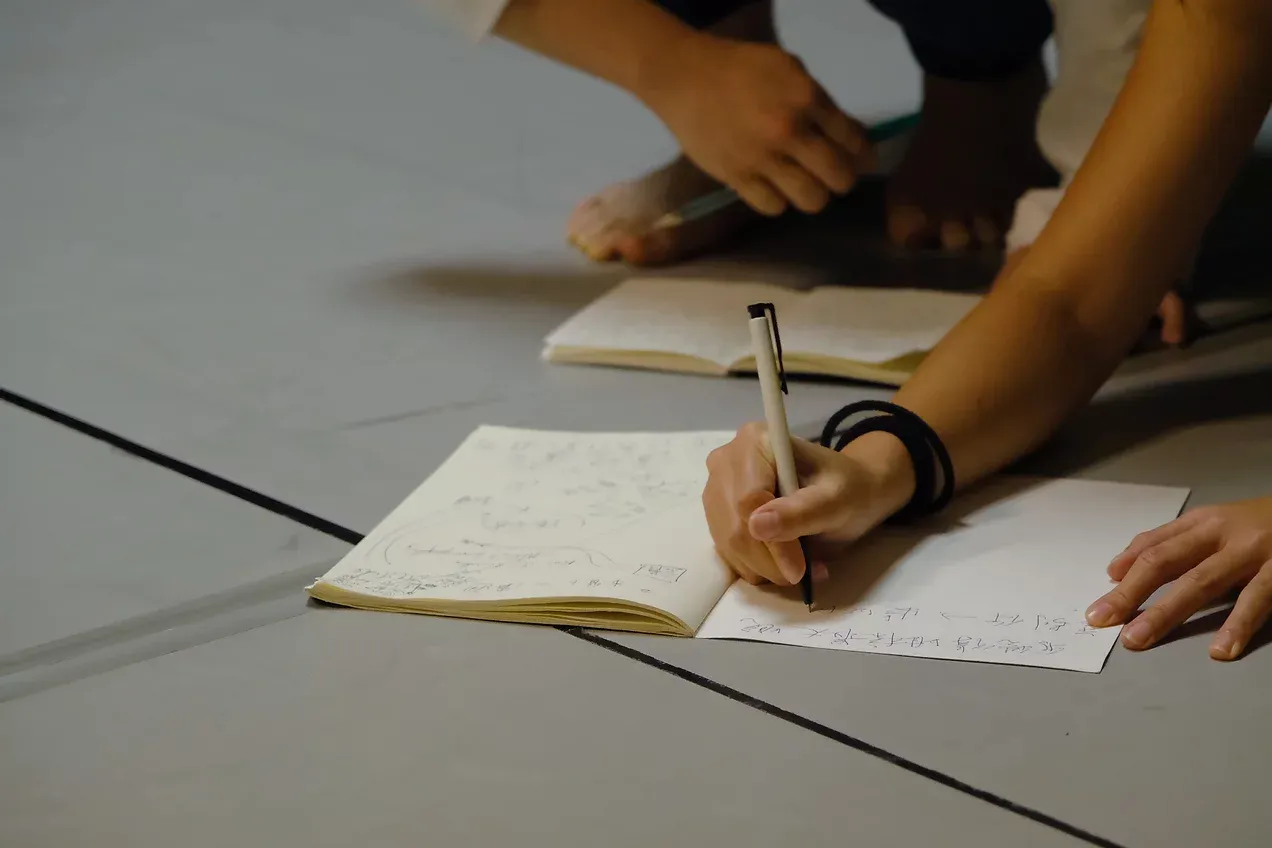 「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 Launch Edition 階段展演及分享」;編舞及舞者:何明恩;照片由不加鎖舞踊館提供
「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 Launch Edition 階段展演及分享」;編舞及舞者:何明恩;照片由不加鎖舞踊館提供
是年不加鎖舞踊館(Unlock)新任副藝術總監李偉能的新策展計劃,請來兩位嘗試編舞的舞者,在Unlock的資源支持下,作階段性創作實驗。「dance-to-be」正是新編舞譚雪華及何明恩經歷多月後的中段測試(Work in process),但礙於疫情嚴峻,最終只能作內部試演,並請來幾位嘉賓參與及討論。據Unlock的說明,為透過藝團資源協助,包括少見地提供長時間的排練場地及工具,及由李偉能為首的分享及指導,來幫助希望嘗試編舞的創作人,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及作品。故此如當晚我們一起討論時提到,從策劃角度到成品,包括是次及疫情稍緩之後的試演,及之後的正式公演,都不比整個編舞創作過程重要。編舞究竟會發展出怎樣的過程,可能才是藝團及策劃最想要的結果。那麼在重視編舞個人成長的作品上,作為舞台上同樣是必須存在的觀眾(及評論),又該如何切入觀看及回應作品?
首先,如果編作過程是主體而非成品,觀賞及評論切入創作的角度就可能不是結果,也不是如概念藝術中作品所呈現的背後概念。那麼,在這種過程比結果重要、更甚是這個未完整的過程的展示時,觀眾該以怎樣的方式投入?答案可能是回到整個策劃的核心:培育編舞。不論是策劃還是觀眾,也得將焦點放在編舞的成長上,簡單來說是同情。然而同情並不負面,而是觀察態度,包含了觀察失敗,思考進度,了解想法及煩惱,陪他們一起走路。我並非要討論觀眾是否必須這樣看待作品,或有沒有義務,這是觀眾的選擇。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態度是以觀眾身份能夠切入是次作品的最佳方式。那麼帶著這份同情,基於重點是關注編舞/作品的未來可能性,而非當下呈現的不完整(因為無論任何結果都能被創作人的話語權歸納為「Work in process」),又是否在說所有的批判都不能成立呢?
當然不是,其中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處理,或這正是整個創作單位及觀眾唯一可以緊密連結的問題︰兩位編舞究竟想要測試什麼?從作品來看,不論是譚雪華及何明恩均旨在拆除所謂一般的創作思維,包括固定舞步及音律性的創作方法,而傾向隨機的,不確定的創作,以及依賴外部力量影響自己。即便如譚雪華通過只設定「遊戲規則」後,給予舞者絕對自由,利用任何方式去回應觀眾寫下來的文字,再呈現遺忘舞步後的錯置,或同樣地如何明恩自己拾起並根據觀眾寫下的文字再作「扮演」,我還是要問,這種沒規律的隨性,究竟在實驗什麼?身體的自律習慣?舞者的不確定狀態?作品的非線性及音律上的延伸?即便在演後討論上,我發現編舞仍然未有準確答案。基於上述的「同情」規則下,我並不在意當下演出的質素及成果,但當看到編舞在這個給予機會創作的計劃中,在進行多月後仍對創作目標不肯定時,就應該要問,一個編舞究竟應該要在有了確切想法後才開始實驗,還是應在實驗中找尋自己的想法,甚至最後有可能找不到?以資源分配及策劃而言,選擇仍未有想法的人,是否也需如上所述予以「同情」?看到兩位編舞不論在討論中以及展示中呈現迷茫,及聽到李偉能說明他們整段時間主要的工作是問及兩位編舞想要做什麼,我便更有疑問
當然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工作坊或創作營,旨在培育編舞創作,讓他們找尋自己創作的方向,可說編舞對創作方向抱有迷茫其實不是問題。然而如何指導從零開始思考創作的舞者,反而是個很大的學問,甚至可說是一門專門的技術:引導創作,讓編舞開發對藝術、身體、結構、形式主義、心理等學術及美學上的認知,可能是一個很艱難及漫長的過程。以至,從當晚結果而言,我思考的是,是次計劃目的究竟是讓參與者學習編舞,而觀眾投入同情,還是更多為策劃單位借來願意付出大量時間及心思的舞者,來做自己的培育編舞實驗?如是後者,當最終演出呈現被定為「失敗」而必需被予以同情時,策劃的位置又可否設於後方,在未說明有何理論配套或參考方向的情況下,評論及觀眾是否亦需要「同情」這種「Trial & Error」式找來參與者做實驗的過程?
 「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 Launch Edition 階段展演及分享」;編舞:譚雪華;舞者:(由左)許煒珊、張嘉怡、黃寶娜;攝:譚雪華
「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 Launch Edition 階段展演及分享」;編舞:譚雪華;舞者:(由左)許煒珊、張嘉怡、黃寶娜;攝:譚雪華
「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 Launch Edition 階段展演及分享」
編舞:譚雪華、何明恩
觀察場次︰2020年7月10日 7pm 不加鎖舞踊館
文章已刊於《舞蹈手札》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