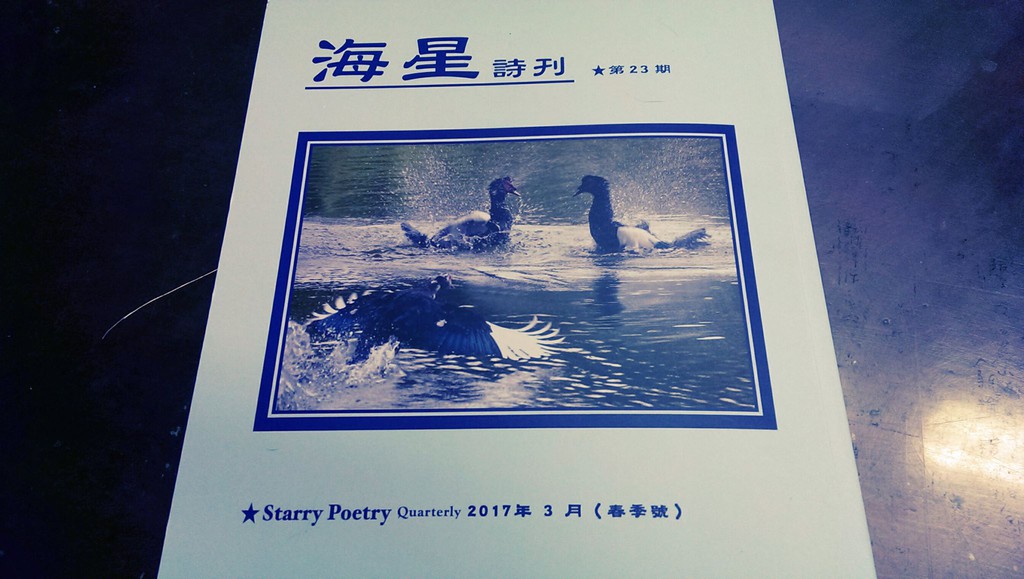〈病與生活的藝術──閱讀孫維民第五詩集《地表上》〉
沈眠/寫
孫維民對疾病、死亡書寫(還有植物)大抵可以說是情有獨鍾,或是不得不然不寫不可的,從《拜波之塔》的「我是有病的/正如每一個人/正如每一棵樹」、《異形》的「一個龐大有病的軀體」、《麒麟》的「傷痛已經結束了嗎/也許舊的走了 又來/新的 像春與病/或者無法迴避的惡人」,到《日子》的「奮力抓住這一根浮木:/白色、橢圓形、10mg//但你知道,主/我其實渴望在水面行走」,皆可見之,乃至第五詩集《地表上》更是病的大規模表現,猶如Brad Pitt擔綱的電影《末日之戰/World War Z》病體反而是活死人災難的唯一生路,孫維民所描繪病之細節與庸俗,有著化哀解愁與明亮微喜的效果。
我相信,他正在寫出病的史詩性(疾病在現代社會所牽連的大景觀),先前的詩集各自承載著一小部分,到了《地表上》則是全面顯現,如〈病理學〉:「……她們為我打針換藥穿脫衣物甚至移往冰冷的器械旁邊赤裸且完全無能為力地面對她們的健康及野蠻」、〈致一位醫生〉:「眾多的肉體,你說,都指向一……一樣的死。/沉默像月亮/堅實如停止工作的金屬、拋棄式管線/不再凝視生者的手掌」、〈致一位護理師〉:「所以,對於健康的堅持……是你現在的疾病?」、〈看護的閒聊〉:「活著有什麼困難呢?/能吃、能睡/再配備狼心一顆/狗肺兩個」、〈說話給病人聽2〉:「她坐在鋁梯頂端時,視角比我們高。我想,她看到的病房……必定和我們不一樣,說不定她看見了某些我們看從未察覺的事物。」、〈論急診室〉:「也有安靜的魂魄/躺臥在某張空床/注視著新來的人。/他已經死了很久/始終還沒有弄懂/生是怎麼一回事」……
病與生活合而為一,《地表上》實是對病與生活的藝術之具體演示。
關於疾病依存症,我總戒慎恐懼牢記Janet Frame《鏡幻天使》的幽然自剖:「……我渴望擺脫此評價,卻又捨不得,即使不公開穿著精神分裂症的外衣,也可以隨時擺在身邊應付緊急狀況,快速穿上,以便遮擋殘酷的世界。……我再也不能求助於精神分裂症了。……精神分裂症這種病是一項才藝,可以使患者免除正常的責任。……當我再也不能狡猾卻必要地從作家的身分轉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分,依情況來回改變時,我如何表明自己?……」
在特別強調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千奇百怪說寫疾病的時代,孫維民卻寧可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寫病與死,寫兩者普遍化、一致性和千篇一律,寫人跟病、死的日常相處,寫得並不獵奇,卻讓人動容,如〈你死後〉:「有些事情沒有改變/例如月亮──它……每個數日,月亮還是。/會完美地複製。/上一次的樣子。」、〈樂園重現的一種方式〉:「你死後/有一部分的我/也死了。/那裡變成虛空//可是,死有仁慈的一面:/祂用你的愛/(已經不朽的愛)/填補那一部分」、……
Sylvia Plath〈鬱金香〉所寫的病之華麗盛大,近乎絕豔:「這些鬱金香一開始就太紅,把我給弄傷了。/即便隔著包裝紙我仍聽得見它們的呼吸聲/輕輕地,穿透它們白色的襁褓,像個可怖的嬰兒。/它們的紅艷與我的傷口交談,傷口回應著。……我沒有臉龐,總想隱藏自己。/耀眼的鬱金香吃掉了我的氧氣。……我喝的水溫溫鹹鹹的,像海洋,/來自和健康一樣遙遠的國度。」到了孫維民手上,依然文字深刻細節華美,但病不再是怪物神魔,病的人間感浮現,病就只是病。
董啟章《心》有言:「……你會被困在特定的病的固定的牆內,失去了自由活動的能力。你會被簡化和非人化為一堆病徵、病情發展和治療方法的總和,失去了定義自己的主動性。……病作為一個現象,本身也是無常的示現,也即是不存在病這個恆常不變的實體,既然如此,病與無病只有相對的差別,而沒有絕對的區分。我們把病當成一個實體,才會如此的痛苦和焦慮。如果我們看到了病自身的空無,我們會不會能夠更安然地面對它?……」
病(與隨後而來的死之懼怖連鎖)是當代人無從迴避的嚴肅議題。病是龐大的社會景象,而孫維民選擇還原病(死)非妖魔邪異的常態,寫病(死)的平庸,寫病(死)的日常與無常。《地表上》的第三輯「有時」尤其教我無能自己,那是對病之本質的看穿視透、細膩承受乃至溫柔包圍,我深切地感覺到其更接近地上的普世胸懷慈悲心腸。
是的,那或可稱之為:我病,故我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