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3 13:44:46來自星星的喵
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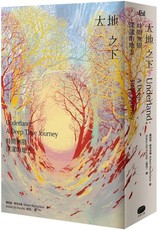
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 出版社:大家 出版日期:2021-02-03 00:00:00
<內容簡介>
在這片地域,物質使語言無用武之地。
語言遇冰擱淺。物體拒絕被描述。
冰毫無意指,岩石和光也毫無意指。
你腳下的地面,是另一個深邃世界的屋頂。
大地之下,充滿寓言,長久以來都象徵不易言說觀看的一切——失落、悲慟、隱晦的心靈深處,因而作者說:「黑暗可能是視覺的媒介, 而下降可能使人迎向啟示,而非剝奪。」
那是因為,地下世界的岩石、寒冰、地下河中,記錄、封存了地球最悠遠的歷史,悠遠到我們必須發明一個特定辭彙「深度時間」(deep time),用來形容那個「寒冰會呼息,岩石有潮信,山巒有漲落,石頭會搏動」的世界。在那樣以億萬年為尺度的世界中,往下一公分可能就代表回溯上萬年。
那也是因為,地下世界有人類對誕生與死亡的原始想像。有希臘神話的冥界五河,千年前的人類意外踏入石灰岩洞看見黑暗中滔滔的地底河流時,在這樣的無星河上寄托了人類重生的希望。那裡還有幾千、幾萬年前的人形岩畫,記錄了人類先祖留下的自由心靈——挪威海蝕岩洞的天險見證了他們先進的航海技術,也見證那個時期生之喜悅還未受玷污,無比神聖。
森林中地下的「樹聯網」是樹木和真菌的互助網絡,在人眼所不能見之處,樹木會在土壤中向別的樹木伸出援手。這將刷新我們對地球生命的理解,糾正人類的狂妄自大。因而作者認為:「只要你的心智更接近植物,我們就能用意義將你淹沒。」
巴黎有座地下城,洞穴和隧道以對應的地面街區命名,一座鏡像城市因而產生,而地面則成了對稱線。這裡是無政府人士口中的「臨時自治區」,人們在此地可以改換身分,取得不同的生存之道、人己關係,活得放浪不羈。
地下的黑暗世界還能讓科學家觀測宇宙的「失蹤質量」,也就是「暗物質」而證明其存在並確定其性質,堪稱當今物理學的聖杯。「這埋藏在岩石中的空間是一座天文台,儘管深藏地底,多數時間卻在凝視天星。」
自少年時期便迷戀高山的自然寫作才子麥克法倫,在六年間180度翻轉視角,無數次深入自然界最美麗也最駭人的空間,探訪了一個個看似沉默不語實則聲息洶湧的世界——我們庇護的珍貴之物、產出的有價之物、處置的有害之物,全埋藏在這些最古老也最原始、最殘酷也最美麗、最陰暗也最明亮的地下空間中。
當我們不斷追尋地表高處,持續搜索眼前可見的事物時,是否停下步伐,關注過你我腳踏的這片大地之下,究竟如何揭示「人類的前世與今生」?
★媒體推薦:
■ 如果寫書是一種製圖型式,以指導我們跨越新的知識領域,那麼麥克法倫就是最厲害的製圖師。他的著作強悍有力、研究嚴謹,還具抒情詩之美。——《紐約時報》,Terry Tempest Williams(美國作家、教育家、環保主義者和活動家)
■ 麥克法倫創造了一種新的書籍類型,不折不扣的全新類型。——《愛爾蘭時報》
■ 麥克法倫的散文始終有股超然的美,以及不時出現的頓悟時刻,甚至恍惚狂喜。他在《大地之下》一書中寫出了我們這個世代數一數二雄心大志的非虛構作品。——《衛報》,William Dalrymple(蘇格蘭歷史學家、作家、藝術史學家及策展人)
■ 他是這一代偉大的自然作家和自然詩人——《華爾街日報》
★得獎紀錄:
☆ 英國《衛報》21世紀100本最佳圖書
☆ 2019年英國溫萊特自然寫作獎(Wainwright Prize for UK Nature Writing)
☆ 2020年愛德華.斯坦福旅行寫作獎(Edward Stanford Travel Writing Awards)
☆ 2019 年美國國家戶外圖書自然史文學獎(National Outdoor Book Award for Natural History Literature)
★目錄:
【導讀】詹偉雄(文化評論人)/文
第一室
1. 降下
第I部 眼見(大不列顛)
2. 墓葬(門迪,薩默塞特郡)
3. 暗物質(柏壁,約克郡)
4. 下層植物(埃平森林,倫敦)
第二室
第II部 藏匿(歐洲)
5. 隱形城市(巴黎)
6. 無星河(喀斯特,義大利)
7. 空心之地(斯洛維尼亞高地)
第三室
第III部 縈繞(北方)
8. 紅舞者(羅弗登,挪威)
9. 邊緣(安島,挪威)
10. 時光之藍(庫魯蘇克,格陵蘭)
11. 融冰水(拉芒森冰河,格陵蘭)
12. 掩藏處(奧基洛托,芬蘭)
13. 浮現
<作者簡介>
羅伯特‧麥克法倫 Robert Macfarlane
才氣縱橫的劍橋文學院士,專長當代文學,也是英國史上最年輕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
能寫擅走,至今已走了一萬多公里,也爬過許多險惡的山,自述「我的腳跟到腳趾的量測空間是29.7公分。這是行進的單位,也是思想的單位」。
被視為新一代自然寫作及旅行文學的旗手,以大量出色的文學修辭(尤其是隱喻)極度延展風景意象及深度,層出不窮的感官描述創造出人的內在風景和外在風景不停親密交流的感受。創新的寫作語言帶動大量評論,並啟發了新一波的地方寫作。當代旅遊文學名家William Dalrymple在書評中便點評道:在這些(顯示了旅遊寫作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旅遊文學為每個繼起的新世代重新創造自己的能力)的所有新作家中,有一個人特別展示了文筆出眾的旅行書仍然可以美得如此渾然無瑕。那個作家就是羅伯特.麥克法倫。
創作領域包括文學、旅行與自然,也熟悉地形學及生態學,同時還能主持紀錄片。
書籍凡出版幾乎必得獎,首部作品《心向群山》贏得《衛報》第一書獎、《週日泰晤士報》年度青年作家獎和Somerset Maugham Award。第三部作品The Wild Places同時獲得英國最重要的登山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Prize和美國指標性的Banff Mountain Festival大獎,並改編為BBC節目。《故道》一書獲Dolman Prize for Travel Writing。《大地之下》獲得英國Wainwright自然寫作獎、Edward Stanford旅行寫作獎、美國國家戶外圖書自然史文學獎,也是麥克法倫自認為的巔峰作品。
譯者:Nakao Eki Pacidal
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譯有《地球寫了四十億年的日記》、《公司男女》、《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等書。
★內文試閱:
‧導讀
一枚墜向地心的螢光,也是逆升的星芒——以全身上下,來閱讀《大地之下》(摘選)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文
……二○一九年出版的《大地之下》是麥可法倫自然書寫系列的第五本。在寫完「鬆散的行路文學三部曲」後,麥克法倫顯然有個新的計劃,如果前三本書分別指向自然裡某個特殊地景——險峻拔高的山岳、隱隱作祟的荒野、凐沒在時空中的故道,這新的一本當然也會有個相對應的宏大主題;顧名思義,《大地之下》深入的是地底——黑暗、幽閉恐懼、未知,而且是更加粗礪、荒涼、時空相忘的自然世界。
先來看幾則評論:《衛報》的威廉.戴倫坡(William Dalrymple)為文〈一場向著深度時間(deep time)的眼花撩亂旅程〉,他說《大地之下》為了探究暗黑裡交錯的地下路徑,作者再度將數個知識領域迷宮般交織在一起:歷史與記憶、文學和地景、地底觀察加上高妙散文,但這些學問最終之所以得有一種啟明(illuminated)的結果,在於麥克法倫「對語言進行了發明(inventive way of language),最好的狀態是」,他說:「這本書有著既是史詩,也是咒語的品質。」《紐約時報》前書評版主編都艾.加納(Dwight Garner)說它讀了「有種刺痛感,閱讀麥克法倫就像閱讀戴爾(Geoff Dyer,以《然而,很美》成名的英國全方位作家)一樣,當你讀著讀著穿越一道圖書館的門、一具下水道人孔蓋、一條蓊鬱林中路,它引領你抵達的卻不是最終章節,而是另一場嗑藥大會與銳舞派對」。
但讓我難忘的,是在美國紐約巴德學院(Brad College)發行的文學期刊《連結》(Conjuctions,雜誌有一個副標題:讀得危險一點/Read Dangerously)第七十三期(二○一九年秋季號),一篇由資深自然文學作家戴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訪問麥克法倫的對話集。黛安的書《感官世界》與《鯨背月色》曾是上個世紀自然書寫領域中的引路之作,但她訪問四十三歲的羅伯特時已經七十一歲,也是準老奶奶級的前輩了。
黛安說:她發現羅伯特所有的書都有「大開眼界」(eye-opening)的特質,特別是針對地景敏銳調控出一套「可口、激賞,有時近乎法醫般」的細節描繪,這些描寫都有一種身體覺察感,彷彿它是一種地球上的生命形式,能夠同時感受與思考,「一個人的心智和身體,怎能如此精緻地與地景交織」,不論在地的感受是崇高、怖懼、骯髒、痛苦或是致命的,「地景將它自己烙印進(inks onto)你的身體,一點一滴(dot by dot)。」而羅伯特總能將激情和無法言喻的誘惑,轉譯成文字,這些文字雄辯滔滔,常常帶有詩意,而且也被迫豐富了英語的字庫,因為作者必須往古代或稀有詞源(但非常精準)去考掘,找出符合眼前大地最恰當的形容,「如果一個作者可以用一百種字來描繪雪,那他肯定是一位與眾不同之理解雪的人。」
同樣身為自然文學作家,黛安說她明白這類型寫作有特殊難處:在現場體驗是一回事,回到書房,要把經歷寫出來讓讀者感受,則是另一件事。她說自己寫作,就有一個麻煩之處,稱之為「修改的冰河化」(glaciation of revisions),點點滴滴,冗長而無休止,別人認為乏味,但她卻認為在字詞上不斷修整,找尋辭意更多的弦外之音,是她志業所在,不管得花掉多少時間,「發現一種方法讓世界能『說出話來』(make the world sayable),讓人感受到一種『礦物氣息般、內在的』(minerally, viscerally)滿足。」她也用一種「麥克法倫式」的修辭,來比喻此類作者拉鋸的兩種內心世界:一種是旅行時「用手指感覺世界」(fingering the world),讓感官來閱讀它,另一種則是寫作時「像僧侶般入定」(monk-like remove),兩種都需要對當下投以高度專注,雖然前者更可能包含讓人毛髮直豎的困局和驚嚇。接著她問麥可法倫:地下的時間和地上的時間,感受有何不同?曾經去過地下,是否對時間的概念有所改變。
在對話中,羅伯特謙遜地說:黛安的問題本身其實就是一篇優美回答的散文,他的回應不會更好,但他也承認,自身也是一個修辭的完美主義者,光是《大地之下》正文的第一句話:「進入地下世界的途徑,是穿過皸裂的老白蠟樹幹」(The way into the underland is through the riven trunk of an old ash tree),就花了好幾個禮拜才寫出來,整本書的前十五頁和關於格陵蘭與芬蘭的章節都花了同樣長度的時間,重寫好幾次,才最終定稿。羅伯特說他對散文中的韻律節奏和聲音模式非常執著,他矢志讓他的每一個句子——橫跨十三萬字的整本書——都擁有近似的韻律魅力和聲響質地(prosodic attention and acoustic life),讓英語讀者讀起來會毫不猶豫地想到十四行詩的「商籟體序列結構」(sonnet sequence)。
看他說到這裡,我馬上翻出書來,找出一個疑似精心打造的段落,對照起英文,大聲地唸起來:在無雲之夜仰望夜空,你能看到億兆公里外的恆星之光,但若是向下看,你的視線卻止於表土、瀝青和腳趾(Look down and your sight stops at topsoil, tarmac, toe),連續好幾個「t」,果然好有土味。
「深度時間」是《大地之下》的一條情感主軸線,相較於人類城市生活中的分分秒秒、生老病死,深度時間是地球洪荒造陸至今,以迄太陽五十億年後熄滅,捻熄生命最後一口氣息間的時間尺度,由岩塊、冰、鐘乳石、海底沉積物與漂移中的地殼板塊來紀年。這時間在陸地表面上難以感受,但當麥克法倫深入地表以下,以身體認識這巨大時間造就的孔洞與穴室,思索最早的人類在石壁上留下的赭色手印,對比巴黎地穴裡探洞者留下的綠手印,又細看當今人類如何將核廢料塞入地底的霸王式佈局,這個抽象時間便具備了巨大的存有論哲學意義——既然人的一生對比起這深度時間渺小得近乎無意義,那我們是就此虛無享樂地過掉一輩子,還是自己模塑出一種渴望搏戰的生命意義,為止住人類毀滅世界的部署,在暗夜中奮力燒出一點螢光?
《大地之下》的空間軸線是高度立體的,它的第一章取名「降下」,最後一章則是「浮現」,橫亙這兩者之間的是四十六億年的地球歷史旅行,從一腳踏入英國門迪丘陵的墓葬場起,經由巴黎地下穴室、倫敦地底菌絲森林到斯洛維尼亞的空心之地;由挪威羅弗登群島史前洞穴、格陵蘭的融解冰帽,再到芬蘭西部晶亮的核子廢料儲存槽(麥克法倫說他從小就是個「北方控」north-minded〕),終曲是回到英國劍橋郡羅伯特家旁林藪中的九道湧泉,與四歲幼子相偕攜行。這趟旅行,除了空間經歷,還包括歷史探求——祖先們總是把最珍貴與最羞恥的埋入地底,知道先人在此發生了什麼事,可讓身體銘刻進更多的感受,反芻人性中複雜和不可說明的質地。而同時,在當今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中,由於人類大量開發抽取,許多過往永恆被埋葬(burial)的事物開始陸續出土(unburial),也帶來許多巨大的不可測結果,整本《大地之下》的行文都可探測到這種不合諧音的嗡鳴,匍匐潛行在商籟體的底層。
因而,相較於「鬆散的行路文學三部曲」,《大地之下》是快節奏與幽暗的驚悚劇,它們相同之處在於內涵都是「身體的詩劇」,麥克法倫竭心盡力設法——要讓讀者感受到他所說的,人類面向地下世界的「癡迷、費解、強迫症、啟示錄」,在地底,即使戴著岩盔,他也努力要讓讀者頭部直擊岩壁和坑道。
‧摘文
〈第四章 下層植物〉
Mycorrhiza一字是希臘文「真菌」和「根」兩字的結合,本身就是一種合作或糾纏,因而提醒了我們,語言也有其沉沒的根源和菌絲,意義藉此得以分享、交換。
菌根真菌和其所連結的植物有著極為古老的關係,約四・五億年之久,主要是互利關係。當樹木與真菌共生時,樹木以真菌所不具有的葉綠素進行光合作用,合成葡萄糖,真菌再由葡萄糖中吸收碳。相對的,真菌則經由樹木所缺乏的酵素,自土壤中獲取磷和氮,再將這類營養素供應給樹木。
然而樹聯網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植物和真菌的這類基本物資交換。真菌網路也使植物得以分配彼此的資源。森林中的樹木可以分享糖、氮、磷:垂死的樹木可能將其資源送入網路,嘉惠整個群落,掙扎求生的樹也可能由鄰居獲得額外的營養。
更令人驚嘆的是,植物還會藉由這樣的網路來發送免疫傳訊化合物。受到蚜蟲攻擊的植物可以透過網路通知鄰近植物在蚜蟲到達前上調防禦反應。植物可以藉由擴散性激素在地面上以類似的方式溝通,但這種空中傳播的目的地並不精確。化合物透過真菌網路傳送時,來源和接收者都可以特定。我們對森林網路的了解日深,得以提出深刻的問題:物種的起始和終點、將森林想像成超大生命體是否最為適切,以及「交易」、「分享」和「友誼」在植物乃至於人類之間的可能意義。
人類學家羅安清將森林地下比喻為「繁忙的社會空間」,數百萬生物在此交互作用,「形成一個跨物種的地下世界」。她在論文〈含納的藝術,又名如何愛上菌蕈〉中有此名言:「下次行經森林時記得向下看。一座城市就在腳下。」
*
梅林和我來到一座極大的櫸木萌生林時,已經在埃平森林走了兩小時左右。截頭——修剪樹木的高處枝幹能夠促進密集生長,的確讓這些樹木享有幾近童話的長壽。在這樹林裡,長長的枝幹嚮往太陽。透過葉隙落下的是綠色的海底之光,彷彿我們正泅泳穿過海帶森林。
我們在樹林地面仰天而臥,躺了一陣子,一言不發,看著樹木在微風中輕輕顫動,陽光在我們上方十五公尺像一條條帶子垂落。在截頭散開形成華蓋之處,我意識到我可以沿著每株樹木的樹冠畫出空間分布的型態:這美麗的現象叫做「樹冠羞避」,也就是樹木尊重彼此的空間,在一樹最外層的葉末和另一樹之間留下狹窄的連綿空隙。
躺在樹叢中,儘管知道要小心擬人化的陷阱,我卻很難不從溫柔、慷慨甚至愛的角度來想像這等樹木關係:羞怯的樹冠彼此尊重而保持距離;交頸擁吻的枝幹;看似相隔遙遠的樹木藉由根和菌絲結成隱形的關聯。我想起貝尼耶(Louis de Bernières)曾就白頭到老的關係寫道:「我們的根在地下向彼此生長,當所有漂亮的花朵從枝頭落盡,我們發覺我們是一棵樹,不是兩棵樹。」我有幸在愛中長久生活,因而知道何謂逐漸向彼此成長、在地下纏綿;那些我們之間無需言傳的事(這有時會發展成令人不安的沈默),以及分享的快樂和痛苦。我認為好的愛會隨時間而生根(to root),而非與時腐敗(to rot)。我認為在腳下交纏的菌絲是為了尋求融合而在土壤中伸展,在我看來也是愛情的作用,只不過是另一種版本。
梅林起身朝樹林中心走去,似乎找尋什麼東西,然後彎身掃開落葉堆和山毛櫸果實,清理出一片茶碟大小的空地。我起身跟上。他捏起一些泥土,在指尖揉搓。泥土並不碎裂,而糊了開來——那是腐爛樹葉所形成的深色腐植沃土。
「這就是我們研究真菌網路遇到的問題。」他說,「實驗很難穿透土壤,真菌菌絲整體而言又太過纖細,無法以肉眼觀察。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發現樹聯網的存在跟作用,就是這個原因。」
樹液之河流淌於我們周遭的樹木。此時若是將聽診器放在白樺或山毛櫸的樹皮上,我們會聽到樹液在樹幹中流動的汩汩聲和劈啪聲。
「你可以把根狀菌索放入地下,觀察根的生長,」梅林說,「但真菌太過纖細,無從觀察。你也可以進行地下雷射掃描,但對於真菌網路來說,雷射同樣太過簡陋。」
這再度提醒了我,地下世界是如何頑強抵抗我們平常的觀看方式,即使在我們這個能見度超高、監控入微的時代,地下世界依舊對我們頗多隱瞞——全球總生物質量的八分之一是生活於地下的細菌,而四分之一有真菌血統。
〈第十一章 融冰水〉
旅行於冰河之上或冰河附近的那些年裡,我透過譯本讀了北方原住民各文化中數十則關於冰河和冰的故事。當中不少故事與危險的地下冰國有關,那是人可能不幸失足陷入的王國。有個普遍的故事(有許多地區性的變異版本)說,有個旅人「落入冰裡」(可能是從海上薄冰或冰隙摔落),大家認為他已經死了,他卻從地府浮現,帶回奇幻景象、艱辛和生還的故事。這主題和事件的順序幾乎與現代西方最知名的地下冰河故事如出一轍——辛普森(Joe Simpson)的《冰峰暗隙》。這所有故事都與從地低深處奇蹟生還有關。我們已在冰河崩裂那日目睹了自己的「浮現」,只不過那浮現的不是任何人類主體,而是寒冰本身,是進入深處之後再度回到光亮當中。
見識冰河崩解後的那幾日,我經常回想我們的反應——當那閃亮的黑色金字塔搖搖晃晃自水中冒出,周身海水奔流,我們的呼喊也從敬畏轉成某種類似恐懼的東西。冰浮現的時候我的胃也猛然一跳——面對這樣的離奇展示,原先的崇高感被一種更本能的反應所取代。以前我常感覺山中物質對一切無動於衷,反而激勵人心,然而那黑冰展現的是另一種孤僻的狀態,如此極端,令人極度不快。卡繆稱這種物質屬性為「厚實」。遭遇到物質的原始形態時,他寫道,「陌生感悄然爬入」:
發覺這世界是「厚實」的,感受到石頭於我們是何等陌生且無法征服,自然或地景又以何種強度否定我們。所有美麗的核心都有某種殘酷不仁……這般原始的敵意從世界升起,數千年來與我們遭逢——世界的這種厚實和陌生,就是荒誕。
我在格陵蘭見識到了此等「厚實」的某種形式(也就是「荒誕」)——其程度刷新我的經驗。在這片地域,物質使語言無用武之地。語言遇冰擱淺。物體拒絕被描述。冰毫無意指,岩石和光也毫無意指,因而這是個古怪的領域,一種舊的、強烈的古怪感,是無法以人類的言詞或型態表達的地形。我想起梅林,想起真菌及其地下灰色王國,那個他協助我看進的顫動、溜滑的地下世界。
在格陵蘭,物質穿透慣常的紗網滲漏出來。那黑星冰河崩裂時,滲漏頓成洪流。日後我還會再次遇上那洪流,在冰臼深處的藍光裡。
〈第一章 降下〉
是的,我們基於許多原因總是對地下不聞不問。但如今我們比任何時候更該了解地下世界。培瑞克在《空間物種》提出「要強迫自己看得更平」的誡命,我則反駁,「要強迫自己看得更深」。地下世界對我們的當代存在乃至於記憶、神話和隱喻的實質結構都至關緊要。這是一個我們每日思索、每日形塑的地形,我們卻傾向於不去承認地下世界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不將它那惱人的形象付諸想像力。我們的「扁平觀點」愈來愈不適合我們所居住的深層世界,以及我們即將在深度時間裡留給後世的遺產。
我們正活在人類世,這個全球性巨大可怖變遷的世代,「危機」不再是恆常向未來延遲的世界末日,卻不斷發生於現在,且總是最無助的人感受最深。時間陷入深刻的脫序混亂,地方亦復如是。本該深埋於地下的東西如今自行隆起。當這樣的東西浮現表面,人的目光很容易便被那入侵的污穢牢牢抓住,難以移開。
在北極地區,遠古的甲烷正透過永凍土融化形成的「窗口」外洩。原本埋在凍土之下的麋鹿屍骸,如今因腐蝕和溫暖而暴露出來,釋放出炭疽孢子。西伯利亞東部的一道隕石坑地面軟化,打著呵欠吞下數以萬計的樹木,並露出二十萬歲的地層,當地的雅庫特人稱之為「通向地下世界的門戶」。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的冰河消融,退回數十年前吞沒的遺體。不列顛近來的熱浪讓古老的建築遺跡(羅馬時代的瞭望塔、新石器時代的城牆)閃現世人眼前,以麥田圈的形式在空中被觀察到——土地沉沒的過去在烈烤的天譴之中隆起,乾燥不毛有如X射線。捷克共和國境內的易北河近來夏季水位下降之多,連「飢石」都暴露出來——過去幾個世紀的人們在這巨礫上紀錄乾旱,也警告乾旱的後果,其中一塊石頭上刻著:「若看到我,便哭泣吧。」五十年前的冷戰時期,美國在格陵蘭冰帽下建造了導彈基地,埋下的數十萬公升化學污染物如今開始向光移動。考古學家佩圖多提(óra Pétursdóttir)寫道:「埋在地層深處並非問題,問題是這些東西很持久,會存在比我們更長的時間,然後以一種不為我們所知的力量反撲……一種『沉睡巨人』的暗黑力量。」從深度時間的沉睡中醒來。
深度時間(deep time)是地下世界的年表,從當下延亙到遠古,是地球史炫目的浩瀚篇幅。深度時間的單位是「世」與「元」,而非人類微不足道的分鐘年月。深度時間是岩、冰、鐘乳石、海床沉積物和漂移板塊的歲月,通往未來也通往過去。太陽將在五十億年間耗盡燃料,地球隨之落入黑暗。我們的腳趾和腳跟同樣立於深淵邊緣。
深度時間裡存在著可以汲取的危險安慰,是食蓮民族的召喚。既然智人這支人種於地質尺度而言轉瞬即逝,我們所作所為有何重要?從沙漠或海洋的角度來看,人類的道德荒謬,可謂非關宏旨。價值的斷言微不足道。扁平的本體論甜美誘人,說眾生在終局的毀滅之前同等卑微。在行星恆常起落衰敗又修復的脈絡下,物種或生態系的滅絕根本無關緊要。
我們應該反抗這種慣性思維。確實,我們應該一反其道,將深度時間視為一種激進的觀點,激勵我們行動,而非因此對一切漠不關心。我們以深度時間來思考,不是為了逃離當前煩憂,而是要重新想像現在,以過去步調較慢的塑造與反塑造的故事,來取代當前的急躁貪婪和騷動。在最好的情況下,深度時間有助於我們認清:我們是過去億萬年和未來億萬年遺贈傳承的一部分,引領我們去思索要留下什麼給未來的世世代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