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1950年代 4】情感與感情 有什麼不同? ◎季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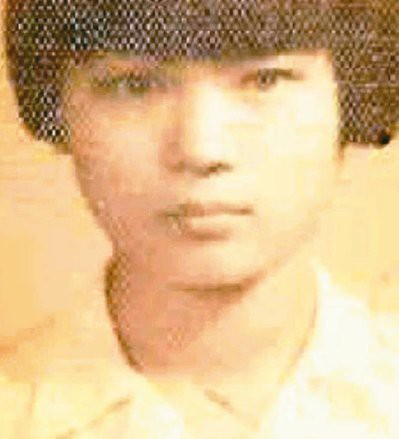
季季1957年進入虎尾女中的學生證照片。
妳有沒有想過,如果不是愛寫作,妳的生活是不是會比較幸福?同學聚會裡,偶爾有人關心類似的問題,我都說,沒有啊,我從沒想過這個「如果」;而且我與寫作的種種啟蒙,早在三歲就已開始。
尊重自由的父親
我出生半年多,二戰結束了,注定無需接受日本教育。1952年進永定國小,六年裡從沒惡補;甚至算術考二十分,父親也沒罵我。1958年初一下學期,讀了王藍長篇《藍與黑》後開始想要寫作,初二因為投稿不願接受訓導處審查,父親曾被請到學校面談,要他勸導我接受審查,但他回家後並沒「勸導」;初三因而被記一個警告,他仍然沒責備我……。──如果沒有一個如此尊重自由的父親,哪有愛寫作的我呢。
父親小學畢業就被我祖父送去東京,在日本大學附屬第二高中讀了六年書,課餘喜歡泡圖書館讀雜書(例如福爾摩斯探案),養成冷靜開明的心性。我是長女,父親影響我一生甚深;1950年代的幾件啟蒙尤其難忘。

季季的第一個母校──雲林縣二崙鄉永定國小,1950年代的大門。
季季(前左)就讀永定國小四年級時,與永定國小校長劉作雲(後左三)及老師、同學合影。
咱來做「里累阿」
我童年時代還沒有現今那許多色彩鮮豔的塑膠玩具。樹葉,雜草,露珠,石頭,泥土……,種種本色玩具隨處可得,都是自然賞賜。唯有一件不是從自然而來,是父親特別為我做的。
每年夏天吃過芒果,父親仔細的洗淨果核,放在竹籃裡曬乾,用鋸子鋸開,再用細繩把兩個串成一個,做一種閩南語發音「里累阿」的玩具;可以上下拉來拉去,發出「里累阿,里累阿」的聲音。──有點像現在的扯鈴。
大概三歲開始吧,父親每次拿出鋸子都說:「咱來做里累阿。」我就站在旁邊專心看。他蹲在紅磚地上,右手握緊鋸子,左手壓著石塊上的果核,彷彿很輕又似乎很重的來回鋸著。父親說「咱來做」,其意也許不是學習,而是參與。然而他低著頭專心手作的身影,從此定格在我腦裡。十四歲之後,我的玩具之一也是寫作,面對500字稿紙一格格寫字時,握著筆也像父親握著鋸子,手彷彿很輕,又似乎很重;文字的輕重拿捏,也像父親在做「里累阿」。
季季的第一個母校──雲林縣二崙鄉永定國小,1950年代的大門。
季季(前左)就讀永定國小四年級時,與永定國小校長劉作雲(後左三)及老師、同學合影。
來去銼刺竹
父親對事熱心,樂於助人,鄉親尊稱他「日長仙」。1952年我剛上小學一年級,下午不用上課,某日母親去西螺街買東西,父親在看農復會新創刊的《豐年》雜誌,我在寫注音符號,二妹三妹午睡未醒,村尾的叔公來了。這叔公和我們不同姓,只讀公學校,喜歡來找父親開講,問些他在東京讀書的趣事。那天下午,叔公又來了,咳嗽聲由遠而近,入門又咳了幾聲,「日長仙,汝有閒否?」說著又咳幾聲,我以為他又要來開講,卻聽他說,「我家門邊的刺竹太大叢啦,騎車、行路出入真麻煩,無小心就會堵到咧──」他的話未完,父親立即說,「有有,有閒──」轉身去工具間拿了斧頭,「咱今馬就來去銼刺竹。」
過了半個多小時,父親回來了,左手摀著左邊眉頭,臉頰有些血跡,說他銼竹頭時太用力,碎片跳到眉頭,擊破了眉皮。父親吩咐我去倒半碗開水,他在衣櫃抽屜拿出棉花、紅藥水,貼近穿衣鏡仔細看,說還好只破一點皮肉,血已不流了。他拿棉花沾水拭去血跡,擦上紅藥水,我天真的說:「叔公有破皮否?」父親說:「憨囡仔,汝叔公感冒真嚴重,轉去厝內休睏囉。」我又關心的問父親,還要去銼竹仔嗎?他說不用去了,出入不會再堵到就好。於是坐下來繼續看《豐年》雜誌,我也繼續寫注音符號。
「哦──,」父親好像想起什麼,抬起頭來說:「汝千萬不要去跟汝叔公講這件代誌啊,」他拍拍眉頭上的額頭說:「我自己見笑,麻袂呼人歹勢。」
在後來的歲月中,我常想起父親摀著眉頭的手,臉上的血跡,以及止血後告誡我的那句話。我的修養不如父親,僅能跟著緩步學習;把自己的「見笑」事藏心底,也把別人的事儘量「袂呼人歹勢」。──這門功課,比寫作還難。
村長婆與《林投姊》
我的生命有幾座分水嶺,第一座是1955年,永定國小四年級女生第一次出遠門旅行。
父親不喜上班,1947年分家後留在家裡與母親共營田園。但他長期擔任農會理事、鄉民代表、調解委員、租佃委員等無給職,不時去外縣市參觀考察;旅行回來總帶幾條羊羹。但他去阿里山會撿幾片美麗的楓葉回來給我做書籤;去墾丁則買幾粒花色不同的小貝殼,解釋它們原是海裡的生物。
那次隨父親去旅行,先在台南縣參觀食品脫水加工廠,台南農業改良場,到台南市後則認識了荷蘭時代的安平古堡,鄭成功時代的延平郡王祠;也看了運河、魚塭、大海,確實增長我對台灣歷史、地理、風物的見識。然而留下震撼記憶的是同行的村長婆;據說她不識字。──那個時代,不識字竟能當村長,也算民主奇蹟!
為了那次旅行,母親特別為我縫製一件黃灰格子的長袖洋裝。上了遊覽車,我和父親的位子在右側第三排,坐下後我又站起來,好奇的前後看看,發現車上只有三個女性:年輕的車掌小姐,小學四年級的我,還有一個看起來比我母親還老很多。我貼著父親耳朵小聲問:伊是誰?他也貼著我的耳朵小聲說:隔壁庄的村長婆。
村長婆坐在司機後面第一排,穿一身暗紅花絲絨旗袍,頭髮盤成一粒球,球頂一蕊紅緞花,頸上圈著粗大的金項鍊,還會抽菸、嚼檳榔。車子上了縱貫道後,她就開始吆喝司機開快一點;有時乾脆站起來,指揮司機超越前面的車子。過了嘉義水上鄉的北回歸線後,我們的車被一輛公路局超過去,村長婆站在司機邊,激動的搖他肩膀:「卡緊咧,卡緊咧,再把公路局超過去!」
一路沉默的司機爆發了:「汝是欲死喲?」
一路吆喝的村長婆也大聲怒吼:「哎喲,賺人的錢還那樣兇,以後不雇汝的車啦!」
司機更大聲回道:「沒關係啦,隨在汝啦!」
車裡響起一陣笑聲,村長婆訕訕坐回座位。
也許庄腳人厚道,無人當面說村長婆的不是,但下了車後都搖頭嘆息。父親把我拉到一邊低聲說:「妳以後要記得,不要做沒知識的女人,會被人看不起!」
●
四年級的分水嶺還包括父親訂了《國語日報》學國語,偶爾也說《福爾摩斯探案》給我聽,並且第一次載我去西螺戲院看《金銀島》,見識了北歐的海盜與探險。但最特別的是我買了第一本課外書《林投姊》。
那時是暑假,母親回西螺娘家,順便帶我去逛書局。
她買洋裁書要學剪裁,我買《林投姊》則是想起有一次父親載我去楊賢庄找朋友,經過墓地旁成排的林投叢,頂頭一粒粒像鳳梨的金黃果子,要父親停下來摘一粒給我;父親說,那不是鳳梨啦,是林投,無肉無好吃……。那麼,書上的「林投」後面為什麼有個「姊」呢?為了這個謎,我要母親幫我買《林投姊》;一本四塊錢。
那天晚上,我把薄薄的《林投姊》看完了。哎喲,那也是我第一次看鬼故事,說清朝時代一個台南女子被唐山來的駐軍騙走了孩子,憤而在林投樹上吊自殺,變成厲鬼嚇人,再隨人飄洋過海去唐山復仇……。我看完拿給父親看,問他這敢是真的?父親看完說,女子被騙也許是真的,上吊根本是假的。我驚訝的哦一聲。父親解釋說:林投葉子有刺,樹幹又彎彎曲曲不夠硬,即便繩子可以綁上去,但是樹幹撐不住身體重量,人頭一吊上就彎下去了;頂多受點皮肉傷,不可能吊死,哪會變作鬼?寫這種故事,至少要了解林投的樹質,才不會寫出這種不合理的情節;如果寫在榕樹上吊就比較合理;《福爾摩斯探案》就不會這樣不合理……。
《林投姊》算是我讀的第一本台灣文學,卻被父親看破這個重大缺點。此後我寫小說,也特別事前做功課「了解」,重視故事情節的「合理」。
初一買《藍與黑》 與父親同讀
1957年小學畢業時,我已是身高155體重50公斤的十二歲少女,考上了雲林縣第一名校「省立虎尾女中」。收到錄取通知不久,上午都需去學校參加新生訓練,下午回家前順路在虎尾火車站附近的租書店看武俠小說。開學後,我看膩了那些大同小異的武功、俠義,改去虎尾街上逛書店;每月總有幾天去翻看《皇冠》、《作品》等文學月刊,幸而老闆無臭臉。
1958年2月過完寒假,下學期開學後我又去虎尾書局翻看當月的文學月刊,老闆知道我喜歡文學,指著王藍的《藍與黑》說:「那本很好看哦。」
我在《作品》看過王藍的短篇小說,就從架上拿下厚厚的《藍與黑》翻閱,第一章只有短短兩句:
──「一個人,一生只戀愛一次,是幸福的。
不幸,我剛好比一次多了一次。」──
第二章第一句也很短:
──「開始聽家人提起唐琪的名子,那年我十五歲。」──
哎呀,第一章兩句話就把我吸住了;第二章則從十五歲開始,全書659頁有多少故事啊,怎能站著看完?趕緊翻到後面看版權頁,哇,「實價:每冊新台幣三十元」,只好靦腆的對老闆說,過幾天有錢再來買。他說,算妳八折啦,二十四塊就好。
我搭台糖五分仔車通學,學生月票才十塊呢。父親會給我二十四塊買《藍與黑》嗎?走出書店時心虛的想:如果沒來買《藍與黑》,以後也不好意思再來看文學月刊了。
然而我不死心。
要怎麼說才能讓父親同意我買《藍與黑》呢?想了兩天,想出了「寫法」;把吸住我的那兩句話,寫在國文課本封面的內頁。回家後翻給父親看,他竟然笑了。
「這是誰寫的?」父親笑道:「真有意思呢。」
我說王藍,是個外省作家。他又問,「是寫在哪一本書?」我說是王藍寫在《藍與黑》裡的第一章。父親哦了一聲,點點頭,問清多少錢,掏出三張十元紙鈔,還說了讓我大為意外的話:「我也想看呢。」
第二天放學後買了《藍與黑》,坐五分仔車回家時迫不及待開始看,回到家吃晚飯邊吃邊看,吃完沒寫功課還繼續看…。父親說:「真好看是否?妳先去寫功課,換我來看。」他一看就入迷,勸我上學要專心,白天把書留在家裡讓他看,我晚上回家再看……。
如此,我與父親輪流看完了《藍與黑》。
王藍回贈《藍與黑》給「瑞月小友」
《藍與黑》的背景,開始於大陸八年抗戰之前的國共內戰,結束於1949來台後。男主角張醒亞是孤兒,先後周旋於孤女唐琪與軍閥之女鄭美莊之間,戀情轉折確實「比一次多了一次」。
然而,我分不清那轉折之間的「情感」與「感情」,三月中旬看完就給王藍寫了一封信,寄到永和鎮竹林路紅藍出版社;自我介紹是虎尾女中初一學生,看了《藍與黑》很感動,想請教「情感」與「感情」有什麼不同?……
王藍是大作家,也許不會很快回信或根本不回信吧?想不到三月下旬訓導處通知我去領掛號;訓育組長「王老虎」已拆封套檢查過,揚著《藍與黑》說:「哇,妳這麼小就會給大作家寫信啊,我都還不敢哩,妳看,人家還送妳一本新書哩!可以借我看嗎?」
王藍的回覆從封面內頁寫到書名頁,起首四字是我的本名「瑞月小友」。他的藍色鋼筆字極細緻,說我是他「最小的讀者」。至於我提出的問題,大略而言,「情感」是內在的個人直覺,「感情」則是外向的人與人交流……。我興奮的拿回家給父親看,父親說:「嗯,王先生的回答,跟我想的差不多呢,咱做人,本來就是有自己的情感,也有跟別人的感情交往,生活才有意思……。」哇,看完《藍與黑》的父親已成王藍迷。
──至於王藍題贈的《藍與黑》,從我初一到高三,不止「王老虎」借去看,其他老師、同學借,畢業後也被文友轉來轉去看,封面日漸磨損,新書已成老書,如今不知身在何處。等我找到那本書,也許再詳細的寫一篇王藍答覆文。
季季就讀虎尾女中初二、初三時的英文老師馬國珍,攝於虎女校園。
(本文刊於2019'04/12聯合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