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文學四月份(詩評論刊登)】 霧影下,隱匿的妖嬈之姿:洪春峰的《霧之虎》
【聯合文學四月份(詩評論刊登)】
霧影下,隱匿的妖嬈之姿:洪春峰的《霧之虎》
文/柯品文(本文刊登於《聯合文學雜誌》2018年.4月,頁78~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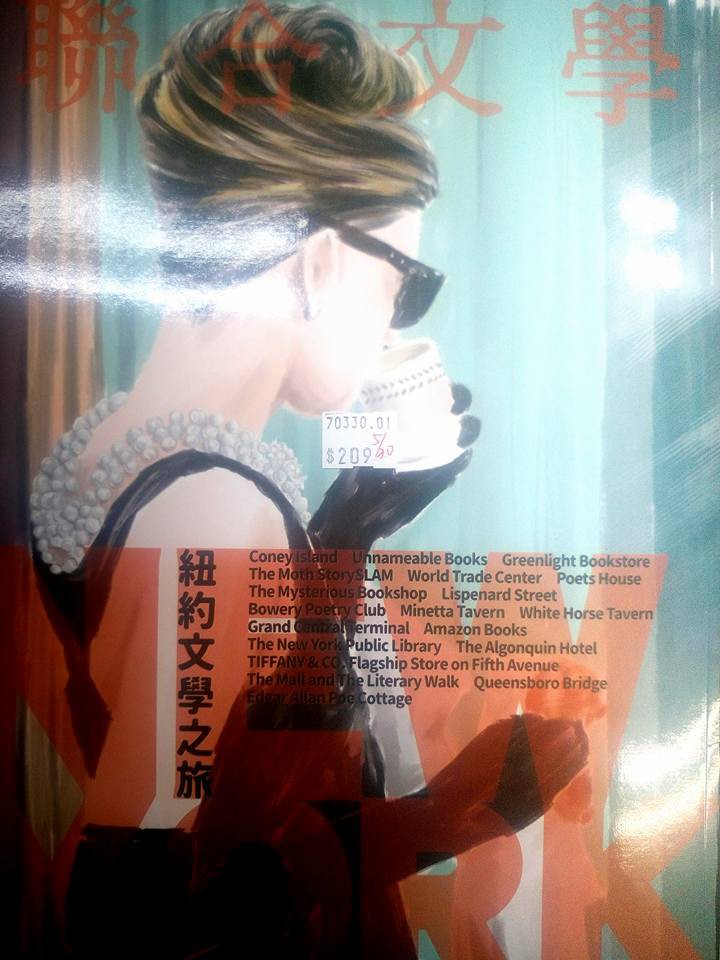
詩評洪春峰雜誌照1.jp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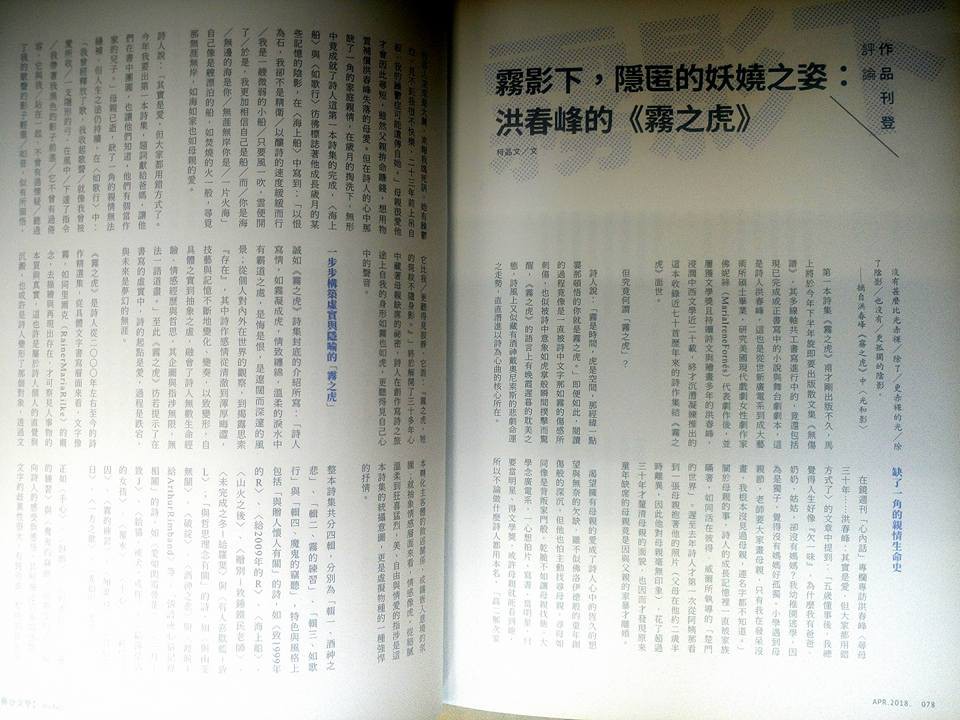
詩評洪春峰雜誌照2.jpg
詩評洪春峰雜誌照3.jp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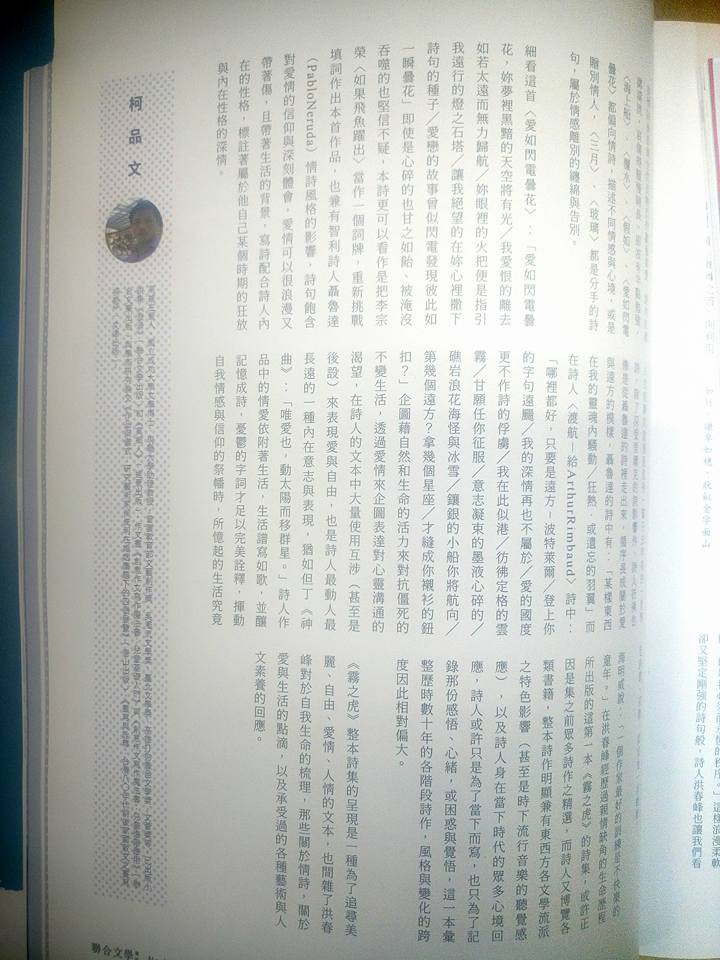
詩評洪春峰雜誌照4.jpg
沒有甚麼比光赤裸/除了/更赤裸的光/除了陰影/也沒有/更孤獨的陰影 。 --摘自洪春峰《霧之虎》中〈光和影〉
第一本詩集《霧之虎》甫才剛出版不久,馬上將於今年下半年旋即要出版散文集《無傷譜》,其多線軸共工書寫進行中的,竟還包括現已完成或正書寫中的小說與舞台劇劇本,這是詩人洪春峰,這也是從世新廣電系到成大藝術所碩士畢業,研究美國現代戲劇女性劇作家佛妮絲(María Irene Fornés)代表劇作後,並屢獲文學獎且持續詩文與繪畫多年的洪春峰,浸潤中西文學近二十載,終才沉潛凝練推出的這本收錄近七十首歷年來的詩作集結《霧之虎》面世。
但究竟何謂「霧之虎」?
詩人說:「霧是時間,虎是空間,那經緯一點霎那頓悟的你就是霧之虎。」即便如此,閱讀的過程竟像是一直被詩中文字那如霧的傷感所刺傷,也似被詩中意象如虎掌般瞬間撲擊而驚醒,《霧之虎》的語言上有晚霞遲暮的耽美之態,詩風上又似藏有酒神戴奧尼索斯的悲劇命運之走勢,直直潛進以詩為心曲的核心所在。
一、缺了一角的親情生命史
在鏡週刊「心內話」專欄專訪洪春峰〈尋母30年...洪春峰:其實是愛,但大家都用錯方式了〉的文章中提到:「5歲懂事後,我總覺得人生好像『欠一味』,為什麼我有爸爸、奶奶、姑姑,卻沒有媽媽?我幼稚園逃學,因為是獨子,覺得沒有媽媽好孤獨。小學遇到母親節,老師要大家畫母親,只有我在發呆沒畫,我根本沒見過母親,連名字都不知道。」關於母親的事,詩人的成長記憶裡一直被家族瞞著,如同活在彼得·威爾所執導的「楚門的世界」。遲至去年詩人才第一次從阿姨那看到一張母親抱著他的照片(父母在他約2歲半時離異,因此他對母親毫無印象),花了超過30年才釐清母親的面貌,也因而才發現原來童年缺席的母親竟是因與父親的家暴才離婚。
渴望擁有母親的愛成了詩人心中的恆久的想望與無奈的欠缺,雖不似佛洛伊德般的童年創傷般的深沉,但他也怕主動找尋母親,尋母如同像是背叛家門般,乾脆不如讓母親找他。大學念廣電系,一心想拍片、寫書、當明星,只要當明星、得文學獎,或許母親就能看到他,所以不論做什麼詩人都用本名,「高二那次家中的客人原來是大舅,來報我媽死訊,她有躁鬱症,見不到我很不快樂,23年前上吊自殺,我的躁鬱症可能遺傳自她。」母親很愛他才會因此尋短,雖然父親拚命賺錢,想用物質補償洪春峰失落的母愛。
但在詩人的心中那缺了一角的家庭親情,在歲月的掏洗下,無形中竟成就了詩人這第一本詩集的完成,〈海上船〉與〈如歌行〉彷彿標誌著他成長歲月的某些記憶的陰影,在〈海上船〉中寫到:「以恨為石,我卻不是精衛/以釀詩的速度緩緩而行/我是一艘微弱的小船/只要風一吹,雲便開了/於是,我更加相信自己是船/ 而/你是海/無邊的海是你/無涯無岸你是/一片火海」自己像是艘漂泊的船,如焚燒的火一般,尋覓那無涯無岸,如海如家也如母親的愛。
詩人說:「其實是愛,但大家都用錯方式了。今年我要出第一本詩集,題詞獻給爸媽,讓他們在書中團圓,也讓他們知道,他們有個當作家的兒子。」母親已逝,缺了一角的親情無法縫補,但人生之途仍持續,在〈如歌行〉中:「我曾經釋放了歌,我收起歌聲/就像我曾被愛所收/一支隱形的弓,在風中/下達了指令/我帶著我黑色的影子前進/它不曾有過倦容,它與我/站在一起,不曾有過懷疑/聽過了我的歌聲的影子輕重/如昔,似有所領悟,它比我/更聽得見寂靜,它說:『霧之虎,牠的斑紋不隨身影。』」終於解開了30多年心中藏著母親缺席的祕密,詩人在創作寫詩之旅途上自我的身形如霧也如虎,更聽得見自己心中的聲音。
二、一步步構築虛實與隱喻的「霧之虎」
誠如《霧之虎》詩集封底的介紹所寫:「詩人寫情,如霧凝成虎,情致纏綿,溫柔的淚水中有霸道之處,是悔是恨,是遼闊而深邃的風景;從個人對內外在世界的觀察,到揭露思索『存在』,其中詩作感情從清澈到渾厚晦澀,技藝與記憶不斷地變化、變奏,以致變形,自具體之實到抽象之虛,融會了詩人無數生命經驗、情感經歷與哲思,其企圖與指涉無限,無法一語道盡。」至此《霧之虎》彷若提示了在書寫的虛實中,詩的起點是愛,過程是跌宕,與未來是夢幻的無涯。
《霧之虎》是詩人從2000年左右至今的詩作精選集,從具體文字書寫層面來看,文字像霧,如同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概念,去描繪與再現出存在,才可察見人事物的本質與真實,這也許是屬於詩人個人的直覺與沉澱,也或許是詩人變形了那個對象,透過文本轉化主客體的敘述關係,或鑲嵌入意境的氛圍;就抽象情感層面來看,情感像虎,從細膩溫柔到狂喜猛烈,美、自由與情愛的指涉是這本詩集的統攝意圖,更是虛擬物種的一種強悍的抒情。
整本詩集共分四輯,分別為「輯一、酒神之悲」、「輯二、霧的練習」、「輯三、如歌行」與「輯四、魔鬼的竊聽」,特色與風格上包括「與贈人懷人有關」的詩,如〈致1999年的R〉、〈給2009年的R〉、〈海上船〉、〈山火之後〉、〈贈別-致鍾鐵民老師〉、〈未完成之冬-給羅葉〉與〈有人喜歡藍-致L〉;「與哲思理念有關」的詩,如〈與山茶無關〉、〈破綻〉、〈酒神之悲〉與〈渡航-給Arthur Rimband〉等;「情詩或心情紀錄相關」的詩,如〈愛如閃電曇花〉、〈三月 — 致J〉、〈給貓,或犬,或你 〉、〈給鐘錶店的女孩〉、〈覆水〉、〈手心〉、〈彼岸之囚〉、〈霧的練習〉、〈如歌行〉、〈投信之日〉、〈一方之歌〉、〈光和影〉等等。
正如〈手心〉、〈但願〉、〈如歌行〉、〈霧的練習〉與〈魔鬼的竊聽〉這類型的詩,偏向詩人的感受與感悟,其所描述的事物感覺,文字的歧異性很大,有時用典,有時則是生命中屬於詩人自己所詮釋的典故,進行一種文本化、藝術化的過程轉化,如〈霧的練習〉:「在輪廓被抽象的過程中,一切/成風,且無關景色與哀愁於是/霧起了/縫補你遺失的步履/如天衣/時間是落雲,事物恰好在此嘆息/命運之軌跡/當陰陽皆謀,而動靜更似/一雙穿花之手」感懷生命風景的更迭,而有些詩作則是透過自我對話來反思自我的改變,像是〈致1999年的R〉、〈給2009年的R〉 (R即是詩人自己)是一種生命自況的隱喻,從詩作裡經常出現的流行音樂的詞句中也可看出,純文學的詩與流行文化的分隔並不明顯,詩如歌是可唱的,可改編的,可影像化的。
詩作中也展現對社會的批判功能,如〈彼岸之囚〉裡則寫道:「我想藉著荊棘的風來訴說,來喚醒/正熟睡中的你,或以冰河的溫度來封存/這一切,我祈求星座的鷹群將你帶離時間的捕捉…/如果可以,我多麼不願打擾熟睡中的你/但是,熟睡的你已是我最後的證人」把情感融入自然界,變形成為荊棘的風、冰河與星座的鷹群,去諷刺國家機器與文明的敗壞,又不失期望與關懷。〈投信之日〉、〈笑聲〉、〈離去之前〉〈一方之歌〉、〈荒地〉、〈相遇十四行〉與〈燒煉之音〉則利用渾然天成的事物,行於當行且止於當止的行雲流水,把古典傳統的東西轉作成當代的再現。
在詩人贈人懷人相關的詩中,如〈有人喜歡藍—致 L〉:「你是避不開孤獨逐愛的天使/酩酊的天使對青春無悔為愛心碎/每當心碎裂,我們不責怪閃電/你給我藍色,中南美洲的夜空/銀河,美麗的山丘,草原的/芬芳,靜靜的河流過/有過你的笑容,我不愛你哭/為我,再笑一次好嗎?/我不怕,我也不愛慶祝/海洋是你的床,海洋,搖晃的水床/我聽你吟誦聶魯達,旖旎的/語言在耳畔,我胸中升起了西班牙」則寫給一位逝去的南美洲人,在海港邊以西班牙文唸唱聶魯達的〈藍〉,詩人則以蘇永康〈有人喜歡藍〉這首歌作為同名詩名,悼念與這位南美洲人交會的一瞬,詩句緩緩敘寫一位異鄉人的孤獨,也表現出詩人對愛與人情的深刻感受。
另外一首詩作〈山火之後〉是紀念鍾理和先生與其〈山火〉這篇小說所寫:
而夫妻並不總是貧賤,你哭,我笑
我們的孩子跳躍,在風中,如香蕉葉
三牲的祭告中如小蝦蟆我願他們堅韌
如竹,謙卑如穗,狀似金字面山
如千堆飽滿的稻禾貢獻,我哭
你笑我愛得過於真切,紙頁上
草坡上,門外的野茫茫,我是愛著的
黃蝶帶走我寫下的字,蚯蚓蠢動
在美得濃烈的單純中,山火欲來
木瓜樹掙脫封建,青青的
欲轉黃,那甜美彷彿情人之眼
對眼相望,天與地交工
泳之游之,情若游絲,我於心坎醮墨
寫下原鄉的哀愁與美麗,願你說我願…
曾於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工作的詩人洪春峰,對於台灣文學這位被譽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詩人的觀察與切入也就更加細膩,美濃鄉鎮的養分給予詩人更深刻的對生活與社會,對愛戀與痛楚的人性詰問,從對美麗的事物癡迷,到對人情有所眷戀與領悟,以詩隱喻自我對生命的觀察,而音樂、文學、繪畫、電影、人群應是給詩人最多養分與傷痕的所在。
三、關於情詩,關於愛,與生活
猶如德國詩人里爾克寫出:「在愛與死亡之間,你是我必須而永恆的秩序。」這樣浪漫柔軟卻又堅定剛強的詩句般,詩人洪春峰也讓我們看見情詩後面最全然而熱烈的歡愉與愛,詩句如潺潺溪流,哀傷得緩慢綿長,卻沒有半點勉強,〈海上船〉、〈覆水〉、〈假如〉、〈愛如閃電曇花〉都偏向情詩,描述不同情感與心境,或是贈別情人,〈三月〉、〈玻璃〉都是分手的詩句,屬於情感離別的纏綿與告別。
細看這首〈愛如閃電曇花〉:「愛如閃電曇花,妳夢裡黑黯的天空將有光/我愛恨的離去如若太遠而無力歸航/妳眼裡的火把便是指引我遠行的燈之石塔/讓我絕望的在妳心裡撒下詩句的種子/愛戀的故事曾似閃電發現彼此如一瞬曇花」即使是心碎的也甘之如飴、被淹沒吞噬的也堅信不疑,本詩更可以看作是把李宗榮〈如果飛魚躍出〉當作一個詞牌,重新挑戰填詞作出本首作品,也兼有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情詩風格的影響,詩句飽含對愛情的信仰與深刻體會,愛情可以很浪漫又帶著傷,且帶著生活的背景,寫詩配合詩人內在的性格,標註著屬於他自己某個時期的狂放與內在性格的深情。
人生短瞬的就像是值得一輩子去吟唱的一首情詩,除了深受里爾克的詩影響外,詩人彷佛也像是從聶魯達的詩裡走出來,循序長成關於愛與遠方的模樣,聶魯達的詩中有:「某樣東西在我的靈魂內騷動/狂熱.或遺忘的羽翼」而在詩人〈渡航-給Arthur Rimbaud〉詩中:「哪裡都好,只要是遠方-波特萊爾/登上你的字句 遠颺/我的深情再也不屬於/愛的國度 更不作詩的俘虜/我在此 似港/彷彿定格的雲霧/甘願 任你征服/意志凝束的墨液 心碎的/礁岩 浪花 海怪與冰雪/鑲銀的小船 你將航向/第幾個遠方?拿幾個星座/才縫成你襯衫的鈕扣?」企圖藉自然和生命的活力來對抗僵死的不變生活,透過愛情來企圖表達對心靈溝通的渴望,在詩人的文本中大量使用互涉(甚至是後設)來表現愛與自由,也是詩人最動人最長遠的一種內在意志與表現,猶如但丁《神曲》:「唯愛也,動太陽而移群星。」詩人作品中的情愛依附著生活,生活譜寫如歌,並釀記憶成詩,憂鬱的字詞才足以完美詮釋,揮動自我情感與信仰的祭幡時,所憶起的生活究竟是詩歌、哀歌,抑或是一首輓歌?
海明威說:「一個作家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在洪春峰經歷過親情缺角的生命歷程所出版的這第一本《霧之虎》的詩集,或許正因是集之前眾多詩作之精選,而詩人又博覽各類書籍,整本詩作明顯兼有東西方各文學流派之特色影響(甚至是時下流行音樂的聽覺感應),以及詩人身在當下時代的眾多心境回應,詩人或許只是為了當下而寫,也只為了記錄那份感悟、心緒,或困惑與覺悟,這一本彙整歷時數十年的各階段詩作,風格與變化的跨度因此相對偏大。
《霧之虎》整本詩集的呈現是一種為了追尋美麗、自由、愛情、人情的文本,也間雜了洪春峰對於自我生命的梳理,那些關於情詩,關於愛與生活的點滴,以及承受過的各種藝術與人文素養的回應。
ps:洪春峰《霧之虎》,台北:斑馬線文庫,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