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表演的原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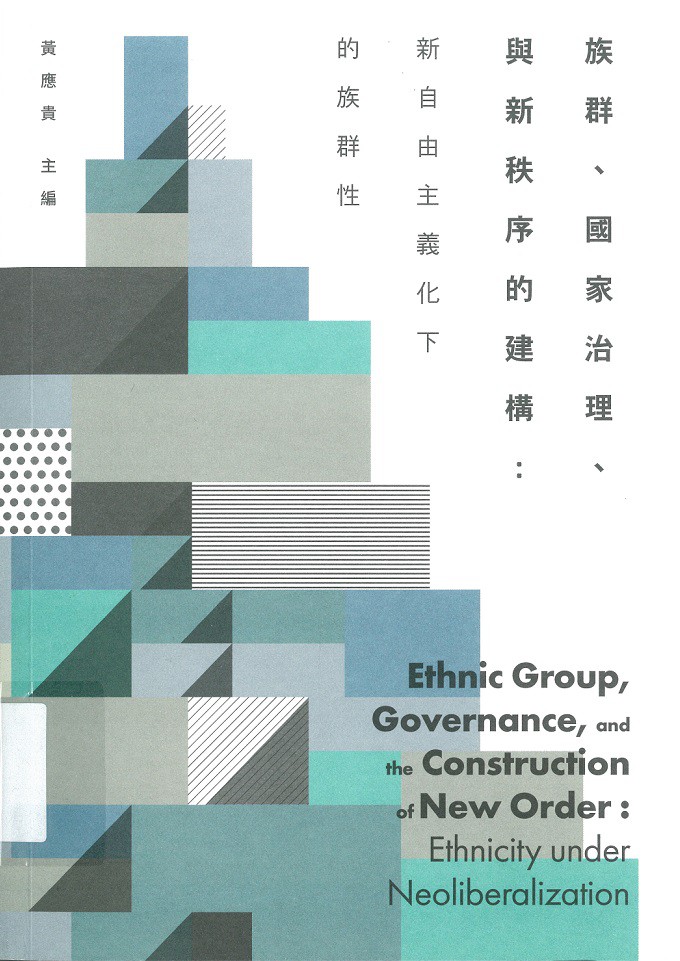
(刊出題名為:有一種性,叫原民性)
依據人類學家黃應貴的研究,在台灣,「族群」依隨解嚴的語境而生;另一方面,我們無法用「現代性的族群概念」詮釋清朝至殖民時期的原住民族歷史,因為原住民族的主要社會單位本來是「社」,而現代國家治理則以族群做為分類,反倒簡化了族群意識與認同的建構。
從國家治理-族群意識的認識基礎進入「原民性」的課題,族群性與原民性並不僅是局部與整體的對比,而更是一種「批判的開放性」的相互補充。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則於著作《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中倡議,「我們應該把原民運動放在轉換的權力關係中觀察,著眼於特定的征服歷史、霸權歷史,以及創造性存續(intentive survival)是如何與新的自由/控制體系互動(new regimes of freedom and control)。」
銜接、表演與翻譯為克里弗德於該書展示的詮釋路徑,林徐達於〈導論〉寫道,克里弗德的民族誌-歷史學現實主義「即著眼於被決定程度較低的轉化過程,注意到新意是如何在實踐中銜接;差異和同一如何被翻譯、詮釋;以及如何向不同的群眾展演原住民群體。」那麼,藝術的展演性,又中介了什麼族群性、原民性?
去年底,水田部落工作室策畫,在地實驗合辦的「當代表演的原民性」三場開放講座,其中兩場聚焦於討論瓦旦塢瑪(母為泰雅族,父為客家人)的行為藝術,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許瀞月教授於第一場講座「剝奪、重生、路徑:瓦旦塢瑪的行為藝術」,開宗明義即拋出提問:原民性是本質主義嗎?瓦旦的行為藝術與早期「泰雅三部曲」(〈祖先的臉〉、〈我愛野百合〉、〈番薯、芋仔-有媽媽的味道〉)會是原民性本質主義的探索嗎?她追問,瓦旦自2000年初發表行為藝術以來,遊走數十個國家,幾乎都不是以原住民身分受邀,這又意味什麼樣的原民性?
接著許瀞月以〈饗宴〉為例,說明這是一件從對母親的記憶出發的行為,小時候瓦旦的母親因不善烹飪,時常做蕃茄炒蛋;轉換至行為表演,他赤身露體在流滿沙拉油的地面上,用自己的肉體滾、翻,做出蕃茄炒蛋,「彷彿在自由與戰慄之間滑動,一直存在滑倒的危機。」她進一步說:「他作品是不是當代存在的危機中,一種藝術分類裡的原型?也就是,在現代藝術的傳統典範裡,無法以實證主義的確認方式找到適合的參照,反倒是在行為藝術的藝術發展樣態中,藉由身體發展出獨特的表達方式。」
在另一場講座「我的朋友瓦旦」,與瓦旦長期合作的藝術家陳界仁則通過他十餘年來與瓦旦的交往,於離散、迫遷、歷史斷裂、在地流放等當代情境中,提出「不純之人」的生命政治,鬆脫族群的分類學、原民性的本質論。他從「安靜或失語」、「輕盈或懸浮」等體會與觀察出發,前者指的是難以言說抑或既有的語言已耗盡的狀態,找不到新的方式去說它,甚至是「『新的世界』,總是在我們還來不及指認時,又迅速消逝?」輕盈或懸浮,則為陳界仁觀察到瓦旦身上有種「奇特的輕盈」,而這究竟「是來自如何在森林中輕盈行走的記憶基因?還是『漂流之人』不得不在總是陌生的環境中,只能『懸浮』地活著?」他疑問,到底是流民還是原民,抑或兩者皆是?
有一次,瓦旦對許瀞月說,他的作品是失聲的,但有身體。依據她近年對瓦旦的採訪與研究,她認為瓦旦的行為,表現的是「不-言說的身體」,「在歷史象徵的前進與退行的運動,屬於退行的,歷史書寫最容易被忽略的」。聽著這段話,讓我想起觀看陳界仁作品《朋友瓦旦》的時候,一開場,瓦旦便從工廠之外,沿著很高的梯子緩緩而下。或者根本沒有工廠「之外」的地方,他只是在不同的空間來回,在這裡那裡的歷史之間,建構不斷流變的,無法被歷史化的,自己的歷史,生命的政治。
※刊於「原住民跨藝平台」《原藝實驗誌》(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