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21 08:46:22讀.冊.人
白露閱讀:彼得‧曼德森《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
白露閱讀:彼得‧曼德森《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
書名:《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
What We See When We Read
作者:彼得‧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
美國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副藝術總監,目前正重拾古典鋼琴。《華爾街日報》讚美他設計出「經典、最好辨識的當代小說封面」。曼德森現居紐約。
譯者:許恬寧
台大外文系畢,現為自由譯者。
作者:彼得‧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美國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副藝術總監,目前正重拾古典鋼琴。《華爾街日報》讚美他設計出「經典、最好辨識的當代小說封面」。曼德森現居紐約。
譯者:許恬寧
台大外文系畢,現為自由譯者。
內容介紹:
當代最具辨識度與思辯力的封面設計師
◆《舊金山紀事報》與美國科克斯書評/年度最佳書籍
◆本書作者經手設計的書封超過600個,包括卡夫卡、喬伊斯、卡爾維諾、科塔薩爾等名家經典作品。
「閱讀就像躲進自己眼睛後方的寧靜修道院。」
由出版界最優秀的書封設計師兼狂熱愛書人,帶給世人這本獨具魅力的好書。書中的視覺與文字範例,帶領讀者多方探討閱讀的現象學,讓人瞭解我們閱讀文學時,如何想像畫面。
我們閱讀時究竟「看」到什麼?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是否真的描述過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容貌?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是否真的告訴過讀者《白鯨記》主角以實瑪利(Ishmael)的長相?書頁上零碎出現的意象──一隻優雅的耳朵、一撮捲髮、一頂頭上的帽子──以及其他線索與意符(signifier),幫助我們想像出人物畫面。然而,覺得自己熟知某個文學人物,和能否具體描繪出他們,其實沒有太大關聯。
當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帶我們到都柏林,當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讓我們踏進倫敦,我們其實是透過他們的眼睛瞭解那些城市。我們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套進作者虛構的場景,然後像愛麗絲的鏡中奇遇,探索先前從未造訪過的世界與年代。
平面設計大師彼得‧曼德森用這本書告訴我們,這種想像畫面的過程是獨一無二的歷程,專屬於閱讀。本書結合了曼德森得獎設計師的專業資歷,以及他年輕時接受的古典鋼琴訓練,從他這輩子最愛的文學出發,用全面圖像化的現象學,探討我們如何理解閱讀這件事。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目錄:
畫畫與「想像」
小說
開場白
時間
栩栩如生
表演
素描
技巧
共同創作
地圖&規則
抽象概念
眼睛、視覺畫面&媒體
記憶&幻想
通感
意符
相信
模型
零&整
模糊不清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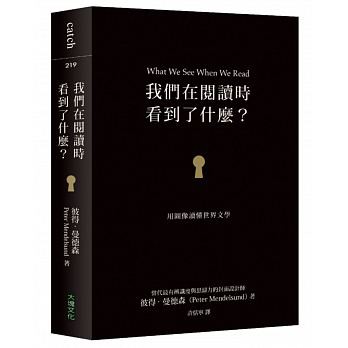
書摘: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書摘:
「小說」
閱讀的故事是一則事後被回想起來的故事。我們閱讀時,心思沉浸其中。在那個當下,我們愈是專心、愈是入迷,就愈難讓頭腦理性分析的那一部分影響我們正在投入的體驗。因此,我們討論閱讀的感受時,其實是在談「曾經閱讀的記憶」。*而這份閱讀的記憶是不實的記憶。
***
如果我請你「描述安娜‧卡列尼娜」,你可能會說她很漂亮。如果你是個細心的讀者,你可能提到她「有著濃密的睫毛」,講到她的身材,甚至告訴我,她嘴唇上方有著一抹毛茸茸的小鬍子(是真的,她有汗毛)。文化評論家阿諾德(Mathew Arnold)則提到「安娜的粉肩、濃密的秀髮、半闔的雙眼⋯⋯」然而安娜究竟長什麼樣子?你可能覺得自己很熟悉一個角色(人們覺得某個角色描寫得很出色時,常會說:「彷彿我認識她一樣。」),但這不代表你實際想像出一個人。你的腦海裡沒有一個固定人像──沒有一張完整無缺的臉。
***
我請大家選一本自己最喜歡的書,然後描述書中關鍵人物的外貌。通常他們告訴我的答案,會是這個主角如何在空間中移動(小說裡發生的事,大多是一連串的動作)。某位讀者選了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癡人狂喧》(The Sound and the Fury),他描述書中的班傑‧康普森(Benjy Compson):「步履蹣跚,手腳不協調⋯⋯」但他究竟長什麼樣子?文學人物的臉模糊不清。他們的五官只會被略微提及,而且就算提到,也幾乎不重要──應該說,五官只有在定義角色代表的「意義」時才重要。描述角色是一種限定範圍的作法,五官幫助界定角色──然而這樣的五官,無法幫我們實實在在想像出一個人。
***
雖然我們以為自己看得到文學人物,但他們其實比較像是一套決定了某個特定結果的原則。一個角色的外貌特質或許只是點綴,但其五官可能暗示了他們代表的意義。(英文中的「知道」〔譯註:see,也有『看到』的意思〕和「理解」〔understanding〕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喜歡一本書,必須極度小心謹慎地思考,再決定是否要看改編的電影版,因為電影的選角很可能變成你心中的那個角色。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在你心中,以實瑪利的頭髮是什麼顏色?捲髮還是直髮?他比你高嗎?如果你並未清楚描繪出他的樣貌,你是否在心中暫時記下一筆,預留一個空白,標上:「這是故事主人翁、敘事者──第一人稱」?或許這樣就夠了。以實瑪利也許讓你感受到些什麼──但這和看見他不一樣。或許在作者梅爾維爾心中,他替以實瑪利設想好一個明確的樣貌。
或許以實瑪利看起來就像梅爾維爾當水手時在海上認識的人。然而梅爾維爾心中的影像,不是我們心中的影像。不論以實瑪利被描寫得多詳細,或是多模糊(雖然我讀過三遍《白鯨記》,我不記得梅爾維爾是否描寫了以實瑪利的外貌特徵),隨著書中情節的開展,以實瑪利在我們心中的樣子很可能一直改變。我們會不斷在心中重塑小說人物的樣貌:我們會加以修改,放棄原本的想像,然後建立新的圖像。出現新資訊時,也會不斷更新⋯⋯
「開場白」
文本沒有解釋的東西,正好召喚我們的想像力。因此我問自己:當作者省略或避免說出太多東西時,我們是不是最能發揮生動的想像力?(在音樂的世界,概念由音符與和弦定義,然而休止符也同樣具有意義。)
***
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部小說叫《未成熟的少年時代》(The Awkward Age)。文學批評家威廉‧蓋斯(WilliamGass)談到書中的凱西摩先生(Mr. Cashmore):
我們可以任意添加對凱西摩先生的描述,加多少句子都行……現在的問題是:凱西摩先生是什麼?我可以給你幾個答案:凱西摩先生是:(一)噪音;(二)一個專有名詞;(三)複雜的思想體系;(四)控制他人看法的觀點;(五)文字系統的表現工具;(六)假裝成現實的指稱模式;(七)文字力量的來源。
我們也可以這樣評論所有的文學角色,例如同樣出現在《未成熟的少年時代》的娜達(Nanda),以及安娜‧卡列尼娜。當然,安娜飛蛾撲火般受到軍官佛倫斯基(Vronsky)吸引這一點(並且因而感到被已婚身分困住),難道不比她本人的外表重要,例如「豐腴的身材」?
在塑造出來的虛構世界中,小說人物如何應對身邊所有的人事物、他們的一舉一動,才是最重要的事(「步履蹣跚,手腳不協調⋯⋯」)。
閱讀的時候,我會離開現象的世界,觀照自己的內心。這聽起來很矛盾:我手上拿著書、要進入那本書的世界時,我是在往外看,但書就像是一面鏡子,透過它,我又覺得自己往內看。(鏡子比喻閱讀,我還可以想出其他類比,例如我可以想像,閱讀就像躲進自己眼睛後方的寧靜修道院──那是一個敞開的中庭,四周被迴廊圍住,有一座噴泉、一棵樹,是一個可以沉思的場所。然而這並不是我閱讀時看到的東西。我沒看到修道院,也沒看到鏡子。我在閱讀時,沒看到閱讀這個行為本身,也沒看到閱讀這個行為的類比物。)
閱讀時,我退出現象的世界。我的退出發生在一瞬間,神不知鬼不覺。我眼前的世界,以及我「內心」的世界,兩個世界不只相鄰還交疊──兩者重疊在一起。書本感覺像是這兩個世界的交叉點或是一個渠道、一座橋,是兩個世界之間的通道。
我閉上眼睛時,我看到的東西(我內眼瞼的北極光),以及我想像的東西(例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像),我隨心所欲在兩者之間切換。閱讀就像是閉上眼睛的世界──發生在某種形式的眼皮後方。一本打開的書就像是一道簾子──它的封面和書頁擋住外在世界不斷出現的干擾,激發我們的想像。
***
你有沒有漫步路肩的經驗,走過那條平常開車經過的路?用腳走的時候,許多坐車呼嘯而過時沒看到的細節會突然湧現。你發現一條路其實是兩條路──一條是行人走的路,一條是汽車行駛的路。兩條路之間的關係薄如紙,只有從地圖的角度是同一條路。它們帶來的體驗完全不同。
如果書本是道路,有些書讓人快速開過──沒有太多細節,有的話也單調乏味──但它們的文字敘述極為順暢,一下子開過去很舒服。有的書,如果把它們看成道路,則是拿來走的──路怎麼彎、怎麼拐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提供的景色。對我來說,最好的書是可以快速開過,但偶爾被迫停下,在路旁讚嘆。這種書可以一讀再讀(第一次經過時,可以快速開過,要多快就多快。但後面再讀的時候,我會悠閒散步,好好享受一番,找出先前錯過的事物)。
「時間」
小說《簡愛》(Jane Eyre)中專橫的里德太太(Mrs. Reed)第一頁就登場,但一直要到第四十三頁,(她的長相)才被完整描述出來。我們終於讀到關於她的模樣時,她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眼前:
里德太太當時年約三十六、七,骨架壯碩,雙肩寬大,四肢有力。她個子不高,粗壯但不臃腫。下顎發達、結實,臉也就顯得大。額頭低,下巴寬又凸,嘴巴和鼻子還算勻稱。淺色眉毛下,無情的雙眼閃著冷光。皮膚又黑又粗,頭髮則接近亞麻色,身體非常健康…… 穿著一身好衣服,神態和舉止故意炫耀價值不菲的衣物。
作者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為什麼等這麼久才描述這個關鍵人物?(在此之前,我們是如何想像這個人?)
里德太太一直到了第四十三頁才被描述出來,原因是故事主人翁一直要到那個劇情緊張的時刻,才第一次真正看到她。勃朗特試圖從簡愛的角度描述里德太太。里德太太是簡愛幼時的監護人,小簡愛被她虐待,關在家中,只有在里德太太盛怒時,簡愛才會偷偷看她幾眼。簡愛用緊閉的雙眼看里德太太──在她畏畏縮縮的時候。因此對簡愛(以及我們)來說,里德太太一點一滴以令人害怕的形象登場:她「目光陰沉,令人畏懼」,體格壯碩,一次跨兩階樓梯。
當簡愛終於起而對抗壓迫者、正大光明看著對方時,她看到了──全部看到──也因此能夠打量對方的樣子。所以說描述(幾乎)不重要;重要的是時間點。
「栩栩如生」
作家近距離觀察這個世界,記錄下自己的觀察。如果我們說一本書「觀察入微」,這是在讚美作家「作證」的能力。這種見證包含兩件事:第一,作者先觀察真實世界;第二,他接著將自己的觀察化為文字。文本愈是「觀察入微」,身為讀者的我們,就愈能體會那樣東西或那起事件(「看到」與「知道」再次是兩回事)。
作者的明確刻畫讓我這個人,也就是讀者,知道自己辦到兩件事:(一)我仔細審視過這個世界,所以注意到這樣的細節(銀色池塘,而且我記得那樣東西);(二)我很敏銳,足以察覺作者苦心刻畫的深刻細節。我因為和作者心有靈犀而興奮,也因為自己很厲害而開心(這種感覺隱而不顯,但確實存在)。有沒有發現納博科夫在前一頁那段話提到了「優秀讀者」?
作者所「捕捉到」的事物抽取自真實世界。那起事件或那樣東西,原先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作者可能留意到汪洋大海中的一片波浪(或「銀色池塘」),那樣東西被他寫下後,就凝結住了,脫離四周一模一樣的海水。這片波浪被挑選出來、以文字牢牢抓住之後,就停止變化,變成靜止的波浪。
我們透過狄更斯的顯微鏡,檢視他的「銀色池塘」。狄更斯抽出這件事,放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就像載玻片上的溶液),然後放大給我們看。我們看到的東西,頂多是被顯微鏡的鏡頭扭曲過的東西。最糟的清況是,我們只看到顯微鏡的鏡頭(借用科學界的話來說:我們觀察到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用來觀察那樣事物的工具)。
因此,我們讚美一段文字「觀察入微」時,我們是在讚美那段話讓人心有戚戚焉,還是在讚揚那段話的表現手法?
大概兩者皆有。
「技巧」
如果說讀者的想像力有高下之分,那麼不同文化的想像力是否也有差異?
想像能力是否會隨著文化的衰老而減弱?在沒有相片和電影的年代,人們的想像力是否更勝今日,比較栩栩如生?人類的記憶力會逐漸退化,我不曉得視覺創造力是否也是如此。我們時常討論文化充斥過度視覺刺激的問題,得出的結論讓人心驚。(有人說,我們的想像力正在死亡。)然而,不論今日人們的想像力相較於過去究竟如何,我們仍在閱讀。無所不在的影像,並未讓我們不再閱讀書面文字。我們閱讀,因為書本帶給我們獨特的樂趣;那是電影、電視等媒體提供不了的享受。
書本給了我們某種自由──閱讀時,心靈可以自由奔馳;我們全神貫注投入某種敘事的構成(或想像)。
或者,我們根本超越不了自己粗枝大葉的模糊想像。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我們喜愛文字故事的重要理由。換句話說,有時我們不想看到太多東西。
愈瞭解這個世界(的歷史、地理),就愈能靠近「作者眼中的事物」。我可以參觀《燈塔行》提到的赫布里底群島,或是閱讀其他描述此一群島的書籍。我可以參考插圖與照片,以求瞭解那個時代的服飾與室內裝潢。我也可以想辦法瞭解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習俗⋯⋯瞭解這些事,幫助我以某種程度的寫實,想像雷姆塞夫人的客廳與飯廳。
作者心中的小說背景畫面,某個程度上可能來自真實世界的某個地點,我們光靠照片或圖畫就能看到那個地方?吳爾芙的小說《燈塔行》背景裡的那棟房子,是否就參照了吳爾芙自己的房子?我很想查索這種資料(我一位朋友讀《燈塔行》時就查了)。要找出斯凱島(Isle of Skye)的燈塔照片很容易,但我會不會因此被剝奪了某些東西?這本書在我心中的畫面會更真實,但少了私密性(對我來說,雷姆塞這家人塞滿客人的避暑小屋,就像我家每年夏天在麻州鱈魚角〔Cape Cod〕租的那棟鬧哄哄的房子。我用鱈魚角那棟房子的畫面來想像《燈塔行》,進而對那本書產生共鳴)。我的朋友原本要告訴我吳爾芙的赫布里底群島的房子長什麼樣子,但我阻止了他。在我心中,雷姆塞一家人的房子是一種感覺,不是一個畫面,而我希望保留這種感覺,不想用事實取代。好吧,或許那棟房子不「只是」一種感覺⋯⋯但那種感覺超越了畫面。
那棟房子的概念,以及那棟房子在我心中引發的情緒,是某個複雜原子的原子核,周圍繞行著聲音、一閃而逝的影像,以及各式各樣的私人聯想。
我們閱讀時「看」到的影像十分私密:我們「沒看到」的東西,則是作者在寫書時想像的東西。也就是說,每一個敘事都會被改變音階調性,在想像中被演繹出來。敘事會被我們的聯想賦予意義,那都屬於我們。
我一個朋友在紐約州奧巴尼(Albany)郊區長大,從小愛看書。他告訴我,每次看書,他都把家附近的後院與小巷當成故事發生地,因為他沒有其他參考座標。我也會做那種事。對我來說,我讀過的書大多發生在美國麻州的劍橋(Cambridge),也就是我成長的地方。因此不論是《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安娜‧卡列尼娜》,還是《白鯨記》,所有經典橋段都發生在地方上的一所公立學校,或是我鄰居家的後院⋯⋯把那些曲折壯麗的長篇故事搬到這些平凡無奇的地方,感覺有點奇怪,甚至好笑。那些發生在遠方的冒險,被意志強拉到某個無聊又不浪漫的地方。即使故事的發生地點變得截然不同,閱讀經歷被個人化,我個人的閱讀理解並未因此受損。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朋友和我做的事,其實是所有坐下來讀小說的人都會做的事。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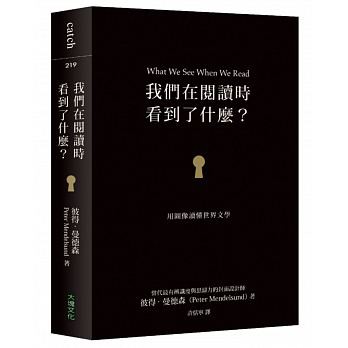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products/0010688474?loc=P_014_0_108&utm_source=Johnsonkuo&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9
(悄悄話)
2015-09-27 12: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