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0 05:54:02PChome書店
食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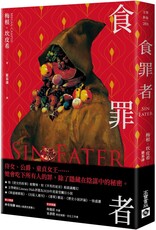
食罪者
作者:梅根‧坎皮希 (megan campisi) 出版社:高寶 出版日期:2021-07-28 00:00:00
<內容簡介>
侍女、公爵、童貞女王……
她會吃下所有人的罪,除了隱藏在陰謀中的秘密。
「食罪者步於眾生之中,無影、無聲。她無法被詛咒。她就是詛咒。」
☆如《使女的故事》般驚悚,如《羊男的迷宮》般詭譎魔幻
☆文學網站Literary Hub評選為2020年度最受矚目小說
☆《華盛頓郵報》、《出版人週刊》、《書單》雜誌、《歷史小說評論》一致盛讚
失去父母的玫因為過度飢餓而偷了一塊麵包,還來不及吞下肚就遭到逮捕,而世界對她的掠奪尚未結束:十四歲的她被判處為食罪者,頸部被鎖上項圈,舌頭被刺上標記,就此失去平凡生活的自由。
食罪者終生背負眾人之罪。每當有生命即將結束,食罪者們就會被傳喚到場。她們聆聽瀕死者自述罪狀,羅列代表罪行的食材,並在葬禮上將家屬準備的罪食一一吞下肚。人們相信食罪者每吃下一條罪,就更接近被上帝扔下地獄的夏娃。所有人都知道,她們不可凝視,不可觸碰。
為母親舉行儀式的老食罪者成為了玫的引導者,也是唯一會正眼看她的人。她們相伴了一段短暫的時光,直到一場王室葬禮中出現了鹿心,老食罪者拒絕吃下這個不曾被提及的罪食,於是遭到酷刑折磨致死。
一場針對童貞女王的陰謀已張開密織的大網。失去了引導者的玫必須自己學會如何聆聽罪狀、列出罪食,設法在危機四伏的冷酷世界中活下來。她該如何破解這個圍繞王室展開、危及她性命的謎團,並為自己的命運做出選擇?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神奇海獅|網路人氣歷史說書人
好評推薦
何曼莊|作家
宋彥陞|時空偵探・文化工作者
「一個黑暗而驚心動魄、讓人欲罷不能的故事,對已消逝的歷史投以反烏托邦的視角,並以令人不安的當代方式呈現。所有人都該為梅根.坎皮希及這本小說喝采。」
——愛瑪.唐納修 (Emma Donoghue),《不存在的房間》原著小說作者
★媒體推薦:
「這是一本黑暗且帶有強烈張力的小說,在閱讀的過程中,你的胃會隨著劇情不停翻攪。」——文學網站Lit Hub
「考究的故事背景、懸而未決的謀殺事件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主角。一本令人讚嘆的小說。」——《華盛頓郵報》
「壯麗、複雜、生動,這種文藝復興時期局外人的視角正是歷史小說愛好者深藏內心的渴望。」——《紐約圖書期刊》
「閱讀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對喜歡女性主義議題的推理小說迷而言,絕對是一種享受。」——《出版人週刊》
「坎皮希創造了一個融合民俗、黑暗迷信與女性力量的故事……喜歡凱倫.梅特蘭 (Karen Maitland) 和黛安.賽特菲爾德 (Diane Setterfield) 的人也會喜歡這本書。」——《書單》
「這部小說是一場都鐸歷史的盛宴,它的核心是慾望、吞噬、賦予生命、謀殺和垂死的女性身體。」——《歷史小說評論》
<作者簡介>
梅根‧坎皮希 Megan Campisi
梅根‧坎皮希是劇作家、小說家與教師,其劇作曾在中國大陸、法國與美國演出。她就讀於耶魯大學與雅客勒柯國際戲劇學院,曾任護林員、巴黎副主廚,並在世界各地擔任肢體戲劇專家。現與家人居住於紐約布魯克林。
譯者:羅慕謙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德國梅茵茲大學翻譯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翻譯。現為專職自由翻譯。
★內文試閱:
‧導讀
吃掉你準備的食物、你的罪就變成我的罪——
小說中,奇特而真實的「食罪者」究竟是什麼?
神奇海獅(網路人氣歷史說書人)
雖然很多人沒聽過,但這個傳統的確已經流傳許久了:在十九世紀的蘇格蘭或威爾士,有些親族會將食物放到垂死親人的胸前,接著他們會雇用一個人來吃掉這個麵包,而在整段儀式結束之際,死者的罪孽也將被洗淨。這個專門被請來吃掉罪食的人被稱為「食罪者」(Sin Eater),他們是誰?這種儀式是怎麼來的?當他吃完食物後,是死者的罪孽已被這樣的善行一筆勾消、還是死者的罪已被「轉移」到了這個可憐的食罪者身上呢?
而這,就是梅根・坎皮西 (Megan Campisi) 第一部小說《食罪者》(Sin Eater)的靈感來源了。故事的主人公是年僅十四歲的玫・歐文斯 (May Owens),她是孤兒、每天都只想著下一餐飯的著落,最後受不了飢餓的她因為偷了一條麵包被抓,之後法庭判決她:成為食罪者。這個判決頓時讓她墜入萬丈深淵,她的脖子被套上枷鎖、舌頭被烙印,成為一名「無影之人」——這代表著她從此不再有朋友、不再能夠跟人擁抱、更不能與別人建立家庭,她將與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訣別,除了工作以外,她必須永遠保持緘默、永遠被拒絕於社會之外。
事實上,真實的「食罪者」處境的確與小說相去不遠:根據現今為數不多的歷史資料,這樣的習俗是基督教與異教融合下的產物。中世紀時,某些貴族在臨死之際向貧苦之人提供食物、好換取他們的祈禱。這本來是一種臨死前的善行,然而隨著時間經過,這種行為背後的動機卻開始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最後竟然變成一種規避末日審判的方法——利用贈與罪食的行為,來轉嫁自己(或他們所愛之人)的罪,而食罪者則成為別人的替罪羔羊。
在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們對來世或煉獄的看法很認真。敬畏上帝的人們害怕自己因為犯罪而墮入地獄,因此他們需要食罪者,但另一方面又很鄙視他們:當時的人相信,隨著食罪者吃下的罪食越多,他們的靈魂也會越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根據一八五二年Matthew Moggridge 的紀錄,「食罪」的儀式是這樣的:「……當一個人去世後,他的朋友們就會叫來該地的食罪者。當他到達時,死者的胸前就已經放上一盤鹽和一塊麵包。當他吃完時,他收到了兩先令六便士的費用,接著他就以最快的方式消失在眾人的眼前。……因為他在這一帶被徹底嫌惡,他被視為一位賤民、一位無可救藥的迷途者。」
也就因為如此,只有極端貧困或絕望之人,才會走上出賣靈魂的絕路。每個食罪者背後大概都拖著一段漫長而淒慘的身世,這也包括最後一位被記錄在案的食罪者Richard Munslow。他本來是一位家境殷實的農夫,然而厄運突然降臨在他的身上——一個星期內,他四個兒子就有三位突然過世,悲傷至極的他便用了這種方法,來消除他兒子的罪進入來生,就此走上了不歸路。
不過跟歷史不太相同的是,比起真實的食罪者傳統比較興盛於十七、十八世紀左右,作者梅根雖然表示小說的時空背景是虛構的,但從文章裡我們還是很容易能找出她影射的是到底哪個年代:「……老國王啟用了新教,他還是國王的時候,每個人都要信仰新教。……他的長女瑪麗絲繼承王位,成為女王。她自己信仰舊教,於是又命令民眾返回舊教,如果你不聽從,就把你燒死。大家把她稱為『血腥瑪麗絲』……她死後,她妹妹貝特妮就成為女王。她又信什麼教呢?沒錯,新教。於是她又命令民眾改信新教。」
是的,小說的時代背景,就是十六世紀的都鐸王朝。那是宗教改革之火燃燒整個歐洲的年代,是各種陰謀暗殺盛行的年代,更重要的是那也是英格蘭史上絕無僅有的女性當政年代。接下來我就稍微解釋一下,那個時代的英格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吧。
說到英國國王,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渣男之王亨利八世了,小說中的「老國王」就是以他為原形。他一生娶過六位妻子,而妻子們的下場正如同一首打油詩說的:「離婚、砍頭、死、離婚、砍頭、活」。而也就是為了第一任妻子:凱薩琳王后的離婚問題,亨利八世才脫離了羅馬教廷、發起了英國的宗教改革。
不過事實上,亨利八世的確是有自己的壓力在的:身為國王,亨利八世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為了生下能夠繼承王位的繼承人。不過自從一五○九年與凱薩琳王后結婚之後,整整二十年都沒辦法生下男性繼承人,唯一平安長大的就是未來被稱為「血腥瑪麗」的瑪麗公主。而就在國王三十四歲的時候,他遇到了情婦:十七歲的安・布林。
國王愛安・布林愛到無法自拔,他寫信給情婦:「整整一年多,我都在瘋狂的追求愛情,不確定會不會失敗,能不能佔據你心裡的一個位置,讓愛情生根發芽……」而在兩年後,國王終於下定決心向王后提出分開的要求。
王后聞訊大哭。長久以來,篤信天主教的王后在民間的聲望極高,人民——尤其是婦女極力支持王后,而教廷對倆人的婚姻更是遲遲未作出判決。但在一五三三年,一件事情的發生突然讓亨利八世驚覺不能再這樣拖下去:安・布林懷孕了!
如果安・布林懷下的是男嬰,那就是能夠繼承王室的唯一子嗣。就因為如此,亨利八世鐵了心要把正宮凱薩琳給驅逐出去。一五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英國最高的宗教人士坎特伯里大主教(當然是親亨利八世的人擔任)代替了教宗、正式宣布亨利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教宗隨即把亨利開除教籍,連帶使得英國正式加入了新教陣營。但亨利八世不在乎,他把一切都押在安・布林的肚皮上,一年之後孩子終於誕生——卻是一名女嬰。國王癱坐在椅子上,問身邊的臣子:「你們曾想到這樣嗎?」而那名女嬰就是未來的伊莉莎白一世女王,但在她即位之前,還有另一個人排在她前面:十七歲的瑪麗公主。
當父王與母后凱薩琳離婚後,瑪麗公主受盡了委屈。她被禁止與母親見面、甚至在三年後母后過世時,都被禁止參加她的葬禮;她必須宣誓效忠新的王后安・布林,就在瑪麗初次反抗後,她的金援馬上就被停掉了。另外,瑪麗原來的侍女也被撤換,新來的侍女完全是新王后的人馬,一再提醒她「妳只是個私生女而已!」甚至告訴她:國王已經示意,不久後就要把她送上斷頭台!終於在身心靈都備受煎熬的情況下,瑪麗病倒了。
最後,瑪麗甚至還必須照顧新生的伊莉莎白小公主。有人說,這是曾作為凱薩琳前王后女官的安・布林的復仇:沒錯我曾經服侍過妳,但妳的女兒將會來服侍我的女兒!而就在這人生的至暗時刻裡,唯一能帶給她慰藉的,就是母親終生信奉的天主教。也因此在二十年之後瑪麗繼位時,她盡了一切方法要英國人民改回舊教,甚至不惜用火刑的方式來殺雞儆猴。但當然,火刑被證明極不受歡迎,反而是那些從容就義的新教教士,讓人民寄予無限的同情。一五五八年,瑪麗憂傷的過世了,最後繼承權,就交給了她的妹妹伊莉莎白。
而這,就是整段小說的時代背景了。從這段歷史中,你不難看出為什麼作者要選擇十六世紀作為他的舞台——那不只是要信天主教或是新教這麼簡單的問題,而是摻雜了各種複雜的情緒:父女、姐妹、夫妻,都因為信仰的問題與對方決裂;為了自己的上帝,人們可以毫不猶豫的運用各種陰謀詭計與暗殺等方法。在小說中,主人翁——也就是那位被判決成為食罪者的玫・歐文斯,就是在擔任食罪工作時,被無端捲入一場巨大的宮廷陰謀之中。
然而,在種種衝突陰謀之外,人們也能在這時代看見一點光亮:這是英格蘭漫長歷史中少有的女性當政年代,在女性服從男性的中世紀裡,作為整個社會群體中最低階的女性,玫・歐文斯看見自己與伊莉莎白(小說中叫貝特妮女王)的相似性:她們都是女性、都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在真實歷史裡,伊莉莎白的姊姊瑪麗一世選擇了西班牙王子作為自己的夫婿,也就是因為如此,民眾始終都擔憂英國終將成為西班牙的一個附屬之地;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那個年代裡,人們反對女性當政的原因之一:女王作為妻子總得順服丈夫,而丈夫所屬的國家或勢力,終將操縱整個英國政局。
但伊莉莎白不同,她終生未婚保持獨立性、成為英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童貞女王」,並在英西海戰中擊敗日不落國西班牙,讓英國在未來幾個世紀裡,逐漸站上歐洲政治舞台的正中央。而主人翁玫・歐文斯也是如此:在背後這個巨大的陰謀、謀殺之中,她唯一能夠憑藉來扭轉命運的,就是自己的智慧與堅強的性格,在被社會遺棄的「無影人」身份掩護下,一點點抽絲剝繭、最終發現了真相。
到底她要怎樣扭轉乾坤呢?一起來進入書中的世界吧。
‧摘文
【之前】
燕麥粥
鹽巴代表驕傲,芥末籽代表撒謊,大麥粒代表咒罵。還有葡萄,紅潤飽滿地鋪在松木棺材上──其中一顆葡萄裂開了,深紅色的種子戳出果皮,猶如碎片戳出血肉。還有燉烏鴉肉佐李子跟一條自製的麵包,小小的,做成線軸的形狀。為什麼要把麵包做成這種形狀?我心想,而且為什麼這麼小?此外還有別的食物,但是不多。我母親的罪過不多。她跟狐狸一樣精明,一嗅到是非爭端,她就雙眼警覺、手腳輕巧地溜開了。只有在確定會贏的時候,她才加入打鬥。我只知道鹽巴、芥末籽跟大麥粒所代表的罪過。都是孩提時代會犯下的罪過,父親母親會因此教訓你,小孩子會在街上唱成打油詩。
傑克被人抓作弊,
只好坐在角落裡,
吃完一塊冬季派,
又會變成好小孩。
接著食罪者來了,她拖著大肚子走進擺著棺木的起居室。棺木的木板才剛鋸好,還很粗糙,釘子已擺好位置,但還未入木。她身上散發出鴉蒜新苗的味道,儘管離五朔節還有整整一個月。我為角落裡的小矮床感到羞愧,因為我們家不夠富有,無法讓我有自己的房間。食罪者粗聲粗氣地表示要張椅子,我們的鄰居貝絲立刻搬來一張凳子。凳子整個消失在食罪者的裙襬下,我想像她的大屁股把整張凳子吞沒的模樣,不禁笑出來,但馬上用雙手摀住嘴巴。
貝絲把我帶到窗邊,在我耳邊輕聲說:「不要看。」她聽到我吸口氣想開口,知道我是我母親嘰嘰喳喳的小麻雀,於是繼續說:「食罪者步於眾生之中,無影、無聲。」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啊──」我低聲說。
「無影、無聲。」她打斷我。
我聽說過食罪者的舌頭上有烙印,但是這個沒張嘴。
貝絲又說話了:「食罪者吃了這些食物,我們身上的罪就變成她的罪,讚美主。你母親會直接上天堂,玫,沒有一點罪過會牽累她。」
我走回去坐在父親身邊。他一臉看起來像是門前別人拿來要洗的床單一樣,皺巴巴地掛在那,皺褶怎麼抖也抖不掉。
「我會把你的臉洗乾淨,」我低聲說,「洗好再掛起來。」
父親又露出那表情,每次我說了什麼不太正常的話他就露出這種表情。他的臉開朗起來,彷彿我剛跟他報了什麼好消息。「我們到底該拿妳怎麼辦才好呢?」
紅潤飽滿的葡萄,線軸形狀的麵包,烏鴉肉。它們深深嵌入我的腦海,猶如燕麥粥緊緊黏在食道上。
【現在】
1 烤鴿子
披肩下的麵包仍散發熱氣,砰砰的心跳聲穿透它脆硬的外皮,我沿著路邊的水溝沒命地跑。
一個棕色的大鼻孔晃到我面前,吐出熱騰騰的馬氣息。
「繼續走!」馬車車夫大喊,他從旁邊一條巷子走出來,趕著母馬擠進大街混亂的交通裡。母馬搖頭晃腦,馬銜抵在黃色的牙齒上。我的路被擋住了。
太明顯了,我怒罵,一邊從水溝裡爬出來,回到平地上。把寶物塞在胸前兩乳之間,衝過倔強不走的母馬跟一輛堆著乾草的推車。
「嘿!就是她!」麵包師傅大喊。我不敢回頭,只管開始狂奔。鑽進一條狹窄的巷子,到了路口,望向一邊,猶豫了片刻,然後跑向另一邊,經過一間馬廄跟一間鐵匠鋪。但是緊追在後的麵包師傅兒子可沒有猶豫,他一手打在我頸子上,把我撂倒在地。一側的臉陷在泥濘裡,我可以從敞開的門看到鐵匠腳上的靴子。剛剛跑得那麼急,我上氣不接下氣。我用雙手把麵包往上推,用牙齒扯掉一塊。還不如現在吃掉,我心想,如果要進監獄,還不如先把肚子填飽。
◆◆◆
「玫.歐文斯。」獄卒把我叫出牢房,連同所有這週被關進來的女孩們。我們總共二十人。三個從外地離家跑來,但是在這裡沒有親眷,也沒有乞討證。兩個娼妓,沒給保安官繳保安費,賄絡他們睜隻眼閉隻眼。五個扒手。八個是行騙或更嚴重的罪狀。最後還有一個跟我一樣是好女孩。她宰了隻流浪狗吃,沒想到那狗是從一個勛爵家溜出來的。真倒楣。
我們魚貫走出監獄,走進初春早晨的濃霧中。濕氣凍得讓人痛徹骨髓,畢竟之前我們那麼多人擠在牢房裡,那麼溫暖舒適。我們沿著道路中央行進,擋住推車與拉車,惹得馬車車夫紛紛怒聲斥喝。法院就在隔壁,但走這段路是我們的懲罰之一。一雙雙眼睛全看到我們的恥辱。他們高聲罵我們壞女人,罵我們是夏娃。
我真希望你可以把五臟六腑顯示給人看,就像你可以把臉展現給人看一樣。這樣一來,大家就會知道我其實一點都不壞。或者是人們可以看到我的頭髮,看到我的頭髮就跟女王的頭髮一樣,是黑色的捲髮。這樣一來,大家就會知道我是個好人,就跟女王一樣。我不是夏娃。夏娃跟造物主住在天堂裡還不滿足,跳進人間找出亞當,亞當是田野與果園的守護者,要亞當把她帶到造物主的樹前,然後偷偷摘下樹上的果實。把果實吃到只剩下一口後,她把這最後一口餵給亞當吃,結果造物主生氣了,說夏娃背叛祂,於是把她貶到地獄去。她是真的很邪惡,比出賣造物主之子的猶大還邪惡。
獄卒把我們帶進一座壯觀的大樓,屋頂高到連長得最高的人也碰不到。我們在長凳上坐成一排,二十個打哆嗦的小女孩。我猜我們當中有些已經是女人了。我自己兩年前就變成女人了,儘管我不覺得自己感覺像女人。但是話說回來,我也不知道當女人又應該有什麼感覺。我轉動手上的戒指。戒指很細,凹凸不平,也不是真的黃金,但是我總想像它是金的。這是我父親唯一留下的遺物。我總戴著,紀念我父親。
「現在呢?」我問那個吃狗的女孩,她就坐在我旁邊。
「法官會做出決定。」遠端一個髒兮兮的女孩說。這女孩偷了一只銀杯。
「他叫記錄官。」獄卒說。
「為什麼叫記錄官?」我問。
「我的命運已定。」一個長得像隻老鼠的女孩說。她試圖賣掉自己的私生子,想必是為了一併洗清遭到玷汙的名聲。
「沒錯,但是還要等記錄官宣布。」髒女孩跟老鼠女孩解釋。
「為什麼叫記錄官?」我又問一次。「因為他要做紀錄嗎?」
獄卒噓我一聲,要我閉嘴。
「聽起來像驢屎。」老鼠女孩輕聲答,環顧大家一圈,等著我們點頭認同。大家都不搭理,於是我也低下頭。
「記錄官什麼時候會來?」我問獄卒,但是他已經站起來了。
記錄官從側門進來,走到一張高高的木桌後,爬上一張高高的木椅。有一片刻,看起來就像個小孩爬上他父親的椅子,我忍不住笑出來。獄卒跟記錄官一臉嚴厲地望過來,但是我立刻擺出一副正經的樣子,其他人也沒揭穿我,就連老鼠女孩也一樣。我突然感到一陣愧疚,趕緊把頭低下來。
「切希.斯朵?」記錄官喊,獄卒揮手要她站起來。「無證流浪乞討。」
「我從切司特鎮來的。」切希小聲說。
「這裡不是切司特鎮。」記錄官頭也不抬說。
「但是我找不到工作,待在家裡也不是辦法!」切希辯解說。
就連我也知道這不成理由。沒有固定住所的人就是會被保安官視為無業遊民抓起來,除非是有女王發的特殊許可證。
記錄官只管盯著眼前的羊皮紙。「妳可以找到兩個可靠的證人為妳擔保嗎?」
真是傻問題。「這裡除了我們就沒有別人了。」我跟吃狗的女孩說。「就只有獄卒,但是他正好是她哥哥的機會也太小了吧?」記錄官把一枝大木槌重重敲在桌子上,我閉上嘴巴。
記錄官宣布切希的刑罰,就跟髒女孩說的一樣。刑罰是鞭笞,然後用根跟男人大拇指一樣粗的鐵桿子,燒燙後在耳朵軟骨上戳個洞。「如果妳再出現在這法庭,」記錄官繼續說,「妳就會被吊起來,直到妳斷氣。」
這話也很傻,畢竟哪個人會被吊起來,直到不斷氣?但是我沒跟任何人講,只是在腦袋中對自己說。然後又責備自己。不仁的想法:食罪者會在我的墓旁吃白蘿蔔。
記錄官一個接一個宣判我們的刑罰。有的是絞刑,有的是鞭笞。老鼠女孩的刑罰是被活活燒死。記錄官看都不看我們一眼。也不問問題,除非是問我們有沒有可靠的證人為我們擔保,儘管他心知肚明我們不可能有證人。每次他這一問,我就惱怒不堪。他問到第六次還是第七次的時候,我胸膛裡燃起一團星狀的怒火,而我不是那種性情暴躁的人。我真想叫他閉嘴別問了,或者至少看我們一眼。
「玫.歐文斯。」他喊。
「在這裡。」我大聲答,大聲到不只是把我自己嚇了一跳,連獄卒也吃了一驚,狠狠瞪我一眼。但是我辦到了,我讓記錄官抬頭看了。
他久久看著我。應該說是盯著我,一雙眼睛瞇成兩道深色的細線。其他女孩都因這陣莫名其妙的沉默抬起頭來,從各自的白日夢醒來。「玫.歐文斯。」他又說,這一次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講,在舌上翻轉每個音節。「原姓戴孚瑞。」
「我是歐文斯家的人。」我說,語氣忍不住尖刻起來。我的手指立刻移向父親的戒指。我不知道記錄官怎麼會知道我母親的原姓。他連眼睛眨都不眨。兩枚黑色的小月亮,盯著,盯著。說不定他可以看到我的五臟六腑,就如同我之前希望的一樣,就像被女巫下了魔咒。
然後他突然大喊:「溫妮.佛萊徹。」瞬間魔咒就解除了。我們全目瞪口呆地瞪著記錄官。「溫妮.佛萊徹!」記錄官望向獄卒,獄卒又望向我們。溫妮.佛萊徹有些猶豫地站起來。「扒人錢包。有可靠的證人為妳擔保嗎?」
宣判了最後一個女孩的刑罰後,記錄官便又從側門離開了。獄卒揮手要我們起身。
「但是我沒有得到刑罰啊。」我對他說。我連個罪狀都沒有。記錄官就只喊了我的名字,還有用那眼神盯了我好一會兒。
我們走過骯髒潮濕的正午街道回到監獄。
「那我怎麼辦呢?」在牢房門口經過獄卒時,我又問。
他只聳聳肩,像是懶得理我,然後走了。我望向其他人。
「那我怎麼辦呢?」她們全避開我的目光,就如同之前我們避開老鼠女孩的目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