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伯佛西:舞台是我要的真實
全文原載於放映週報 619期
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2170
舞國與夢
1986年的《舞國》Ginger e Fred是大師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倒數第3部電影,描述一對專門模仿歌舞片巨星佛雷亞斯坦Fred Astaire與金姐羅傑絲Ginger Rogers的資深舞台藝人,闊別數十年後,再度為了一場直播的電視綜藝秀而聚首,要重現他們的招牌舞蹈。我在想,如果鮑伯佛西Bob Fosse,這位傳奇編舞家與導演,沒有意外地在次一年就猝逝,應該會非常渴望將這部電影改編成音樂劇,搬上百老匯舞台吧!因為那裡面有著太多他所瘋狂著迷的元素:舞王佛雷亞斯坦、雜耍綜藝秀vaudeville、費里尼、女主角茱莉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以及舞台。
對費里尼來說,「夢是唯一的真實」,因為世界上所發生的現實,多是經過化約妥協後所做的選擇,而夢,卻是人所有慾望、感受、想像被扭曲並濃縮,但未遭裁減的經驗,反而更接近那真正複雜豐富的自我。《舞國》最動人之處,不只在於費里尼以他老練的獨門電影語言,述說出對已逝時光的緬懷(還有對當時電視稱霸的嘲諷),更在於他讓我們看到,現實中一切光怪陸離、詭異荒謬的人事物,一旦被搬上舞台,竟就能變得如此理直氣壯、理所當然,才發現,原來舞台正是可以包容各式各樣異態、變形、奇想與夢境的場域,對我而言,這也正是費里尼的信徒:鮑伯佛西,他電影創作中所展現的最重要特質。
極雅與極俗的交融
1927年出生於芝加哥的佛西,和舞台的淵源非常早,青少年時期就輟學在劇院裡表演,他最大的偶像,就是當時叱吒歌舞片界的舞王佛雷亞斯坦,那流暢優雅又細緻的舞蹈風格,還有對禮帽與手杖等道具的靈巧使用,對佛西的編舞生涯都有極大的影響,網路上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佛西模仿舞王的片段(和他第一任妻子瑪莉安奈爾絲Mary Ann Niles),而他在《生命的旋律》Sweet Charity裡知名的「如果朋友們現在看到我」If My Friends Can See Me Now歌舞中,刻意讓大明星送了女主角禮帽與手杖當友誼證明,當然就是對偶像的致敬。不過,當佛西開始進入劇院表演時,原本他所期待參與的雜耍綜藝秀,早已隨著有聲電影的出現與經濟蕭條的打擊而式微,取而代之能夠在全美各地劇場裡生存的,就只剩下脫衣舞孃秀Bourlesque,這個過程在知名音樂劇「玫瑰舞后」Gypsy中有很生動的描繪。佛西年少時,便是在脫衣舞秀中擔任踢踏舞表演兼插科打渾司儀的工作,而這段和脫衣舞孃們近距離相處的經歷,似乎就此潛入並佔據他的意識深處,成為他創作的另一大靈感來源。
《生命的旋律》裡排成一列唱著「灑錢大老爺」Big Spender的舞女們、《酒店》Cabaret裡充滿情色意味的歌舞秀、《連尼》Lenny裡男主角的脫衣舞孃妻子,以及《兔女郎謀殺案》Star 80裡暴露身體求成名的寫真美女,都可以看到佛西對於這些題材獨特的觀點與感應。而在編舞上,佛西著迷於女性軀體的扭動與搖擺,有時是柔軟如無骨般,手或肩單一部位的細微挑逗,有時是誇張地拗出奇特角度,腰髖膝整體的張揚誘惑,搭配著羽毛扇與漁網襪等若隱若現的效果,充滿了輕挑、妖魅與淫趣,也都是來自於脫衣舞孃在他舞台生涯最初始時所留下的印痕。這些舞蹈動作在他的作品裡,變成了湧動著陰暗、病態、情慾與罪惡的潛意識,可以將故事表面說不透徹的幽暗心理給挖掘出來,但或許又怕太過挑釁,所以必須放上舞台,用舞台做為乘載的容器,才能讓舞化為人生與人性的隱喻。像是在他金棕櫚獎大作《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裡為航空廣告所編的兩段舞,便宛如顯意識與潛意識的兩層對比,讓我們地清楚看到舞台上可以並置的兩面:想被看見的我,與隱藏不了的我。
潛意識的舞台
運用舞台來暗指既分裂衝突又層疊融合的心理樣貌,在佛西1969年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生命的旋律》中,便可看到精采的呈現。鮑伯佛西早在1962年初次觀賞費里尼的《卡比利亞之夜》Le notti de Cabiria時,就深深為女主角,也就是費里尼夫人茱莉葉塔瑪西娜,帶著卓别林丑角精神與雜耍喜趣觸感的表演而著迷,於是想仿效費里尼,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百老匯名伶關薇登Gwen Verdon,量身重塑這個經典角色,於是有了1966年的賣座音樂劇「生命的旋律」。好萊塢隨後買下電影改編版權,並簽下當紅女明星莎莉麥克琳Shirley MacLaine擔任主角,而麥克琳因為在百老匯曾和佛西合作過「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佛西編舞,她因替補女主角演出而被發掘)對他的才華極為傾倒,於是卯足全力說服片廠老闆,讓未曾有過電影導演經驗的佛西擔綱重任,這部片最後雖然票房慘敗,但佛西新潮又帶酷勁的編舞與敘事手法,讓許多製片印象深刻,才讓他有機會從《酒店》重振旗鼓。
《生命的旋律》是一部融合歌舞片(歌舞走進平凡自然的生活中),但在情節中仍安排了三場舞台表演:第一場就是舞廳裡的招牌秀「灑錢大老爺」,舞女們個個面無表情地對著顧客蛇舞肢體,像是人不敢直視的原始慾望;第二場則是向費里尼《生活是甜蜜的》La dolce vita致敬、名流顯貴機械做作的「富人扭擺舞」The Rich Man's Frug,是女主角憧憬的華美夢想,一場激勵她跳出泥沼的幻境;而第三場就是被拿來當成中文片名的「生命旋律」Rhythm of Life,小山米戴維斯帶領一群嬉皮,洋溢著宗教性的歡樂歌頌,追求性靈的愉悅與滿足,最後還在絕望中喚醒一縷晨曦。這三個佔去不少篇幅的舞台段落,雖然不見得有劇情推展上的必要,但卻能深刻地讓觀眾感知,女主角這段生命經歷中高低起伏的迂迴心路,反而是再關鍵不過了。
而這種舞台表演做為劇情內在註解與暗示的手法,到了他下一部電影《酒店》則發揮得更為徹底,這齣讓詞曲搭擋艾伯–坎德Fred Ebb & John Kander成名的音樂劇,其墮落陰暗的主題讓佛西非常感興趣,於是在得知原導演哈洛普林斯Harold Prince無法參與電影改編之後,佛西花了很大的功夫搶下了導演一職,大刀闊斧地刪改原劇而拍出屬於他自己的創作。原本音樂劇就是從酒館裡Emcee揭幕的「歡迎歌」Willkommen開場,以晚安告別的「終曲」Finale謝幕,觀眾可以清楚地意識到整齣戲是被包裝在一場秀之中,劇情也是秀的一部分,而佛西卻幾乎將所有「現實」情境下的歌曲都刪除,讓歌舞只留在舞台上,當故事進行時,那奇裝異服、妝容猙獰、暴露撩人的表演,就會如鬼魅般不時地探出頭來,既是娛樂,也是映襯諷喻,並凸顯出1930年代初德國人心頹靡與納粹興起的不安氣息。這部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拿下8項奧斯卡,包括佛西擊敗《教父》The Godfather名導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la所贏得的最佳導演,還有麗莎明妮莉Liza Minnelli的最佳女主角。
舞台下的群眾
有趣的是,最初片廠籌拍《生命的旋律》與《酒店》時鎖定的導演人選,其實是與佛西天差地別的一代舞王金凱利。金凱利的舞蹈比較是一種陽剛健美、甚至像是體操選手般帶著力道的表演,象徵著獨立昂揚、瀟灑不羈的個人獨特性,相較之下佛西的舞則顯得陰柔,有很多像是彈指、屈膝、抖肩的重複細微動作,而且他喜歡群舞,穿著相同服飾的舞者擺動著同步或對稱的舞姿,有些電影學者認為這是對工業時代生產線的模仿(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暗示著一種集體性。那麼,佛西是用他的舞蹈來歌頌集體性嗎?對我來說剛好相反,他作品中的合唱與齊舞,往往反映的其實是他對群眾與集體的焦慮,像是《酒店》裡,唯一一首不在舞台上唱的曲子,就是納粹少年引領大眾高歌的進行曲「明天屬於我」Tomorrow Belongs To Me,朗朗上口、振奮人心,但內在那股偏狹民族主義與法西斯的精神,卻讓人毛骨悚然。
而1975年詞曲搭擋艾伯–坎德繼電影《酒店》(新歌「先生」Mein Herr和「錢」Money)後再度和佛西共事的百老匯音樂劇「芝加哥」Chicago,戲中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諷群眾與媒體一窩蜂的盲目愚蠢,特別是律師舌燦蓮花擺佈記者與陪審團的「我們同時碰到槍」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及「目眩神迷」Razzle-Dazzle兩段群舞,更是讓觀眾看得哈哈大笑又不禁心虛齒顫。
在創作排練「芝加哥」的過程中,佛西遭遇了一場心臟病發,差點就要了他的命,而這齣戲上演後雖然賣座鼎盛也入圍11項東尼獎(1項未得),但那年死對頭麥可班奈特所編舞執導的「歌舞線上」The Chorus Line卻更為風光(獲10項東尼獎),完全蓋過他的鋒頭,讓他耿耿於懷(後來在《爵士春秋》中趁機嘲弄了約翰李斯高John Lithgow所影射班奈特的角色),直到佛西過世後近十年,他的情人安蘭金Ann Reinking將這齣戲與他的舞再帶回到百老匯,才一洗蒙塵之憾並掀起歷久不衰的熱潮(8項東尼獎、連演超過20年至今不輟)。2002年,曾為百老匯重演版「酒店」編舞的勞勃馬歇爾Rob Marshall,身兼導演與編舞,將「芝加哥」搬上了大銀幕,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等6項獎,在電影中馬歇爾展現了他對佛西風格的洞悉,同樣將歌舞全放置在舞台上,並讓表演舞台變成一個寄存幻想、夢境與慾望的逃避空間,而對於群眾集體心理的批判,也玩得逗趣又銳利,確實是個既熱鬧也懂門道的一次精彩改編。
舞台上的自戀、自憐與自厭
佛西在老友莎莉麥克琳的慫恿下,將自己心臟病發瀕死經驗所帶來的震撼與觸發,寫成了電影《爵士春秋》的劇本,在這部宛如懺情錄又像是對費里尼《八又二分之一》8 1/2致敬的半自傳電影裡,男主角面對像是天使又如死神的潔西卡蘭Jessica Lange逼問,大膽地坦露出自己複雜的私生活、創作歷程與心理分析,幻覺的場景不再是光鮮的舞台,而變成了一團混亂的後台,幾乎所有的歌舞都被刻意設計成排練中的狀態,佛西似乎想進一步地探勘潛意識更渾沌的深處,自己不曾也不敢觸碰的禁地,或許是一次次放縱所留下的罪惡感,或許是對死亡的恐懼,也或許是渴望被愛、被注目的無盡需求。
《爵士春秋》裡只有兩度出現真正的舞台表演,一次在電影最後,佛西分身洛薛爾德Roy Scheider走進聚光燈下和佛西老搭檔班維林Ben Vereen合唱死亡之歌「再會愛情/生命」Bye Bye Love / Life,另一次則是斷續在片中片裡出現,克里夫戈爾曼Cliff Gorman演出的脫口秀現場,戲謔人面對死亡的各個階段。後者所指涉的,就是1974年佛西改編自百老匯同名話劇的電影《連尼》,由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飾演這個口無遮攔的單口喜劇藝人(戈爾曼是舞台版連尼),片中伴隨情節不時出現的舞台表演,是他一步步建立自我風格的脫口秀,裡面有著肆無忌憚的言語砲火,轟炸體制、性別、社會價值等集體的虛假與壓制,那既來自於私人的生命體驗,卻也引導他走向自我毀滅。這部非歌舞的黑白電影,讓佛西得以盡情地嘗試各種電影語言,並運用剪輯建立既意識流又具舞蹈韻律的動態特質,襯和劇情內在的焦躁不安,同時主角自戀又自憐的心境,似也可看見佛西自身的投射。
1983年的《兔女郎謀殺案》,佛西另一部真人實事的非歌舞電影,他所執迷的舞台概念變得更為廣義,那是一種站在鎂光燈前的慾求,想被看見,想要成名,佛西曾對主演的艾瑞克羅勃茲Eric Roberts說:如果事業沒有獲得如此成功,自己或許就會變成事件中因妒恨而崩潰殺戮的男主角(佛西早期的編舞成就常被妻子關薇登的絕讚表演所壓倒)。電影最大噱頭雖是演出花花公子跨頁女郎的瑪莉亞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的大膽裸露),但真正的核心其實是那個發掘她一脫成名,自己卻淪為吃軟飯的挫敗丈夫,電影的結構與手法都類似《連尼》,但它的悲劇卻是建築在不被認同、不被欣賞、沒有舞台的恐慌上,佛西用聳動無比的事件,包裹著他藏在心底深處,怕是永遠無法滿足的被愛渴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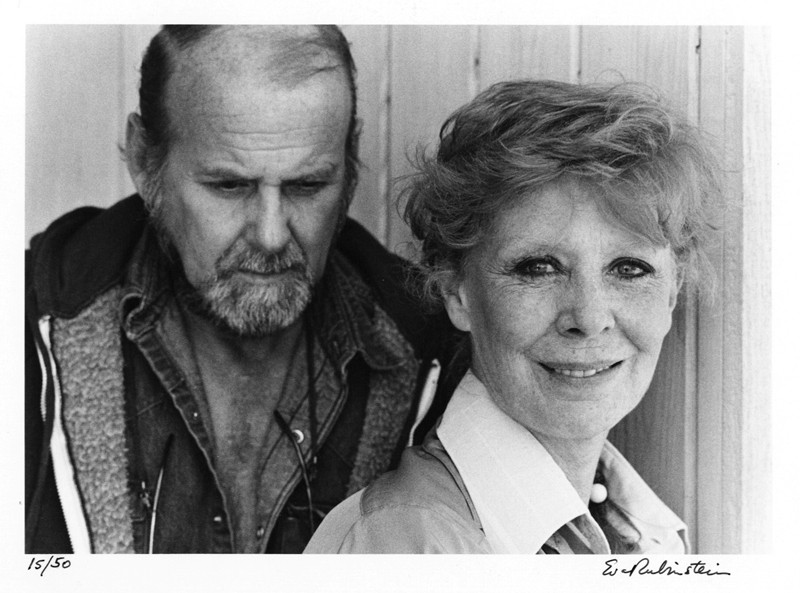
終曲大秀
1987年六月,鮑伯佛西最崇拜的舞王佛雷亞斯坦過世,七月,他的百老匯死對頭麥可班奈特愛滋病逝,九月,就在重演版「生命的旋律」移師華盛頓的開幕當日,佛西在街頭心臟病復發,躺在妻子關薇登的懷中嚥了氣。據說他的遺囑中特別將25000美金留給了66個近親好友,指名要他們以這筆錢辦一場派對來紀念他,於是一個多月後,這些人被聚集到了中央公園的綠苑酒廊裡,啜飲著香檳、親暱地交談、緬懷起過往。突然間,班維林(《爵士春秋》舞台主持)跳了出來,眾目睽睽中隨著音樂擺動起佛西的招牌舞步,而佛西的遺孀關薇登、女兒妮可佛西Nicole Fosse,以及情人安蘭金(《爵士春秋》裡演自己)也真如電影裡死亡降臨病榻時那般,手牽手地加入這情慾滿溢、挑動感官的舞動行列中,悼念追思的餐會,就這麼變成了一場既擁抱死亡也擁抱生命的大秀。鮑伯佛西,這個即使耗損肉體、斷了呼吸,也想登場表演、佔有聚光燈的鬼魂,應該就在某個角落裡,得意地享受著這個,屬於自己最真實的眷戀與渴望:舞台。